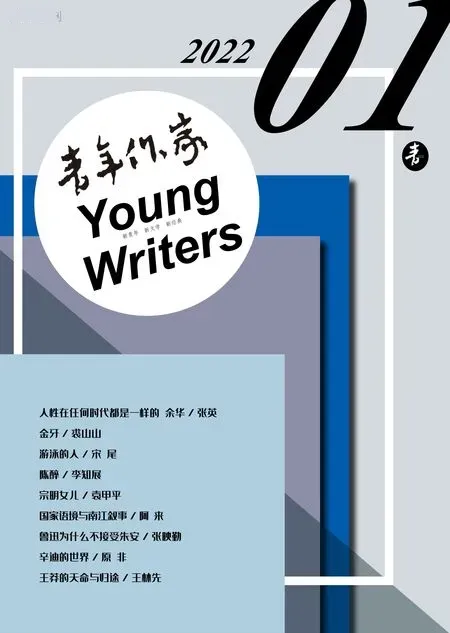金牙
裘山山
一
袁医生有一颗金牙,在左侧,左侧的下牙床,说话的时候刚好可以看到。我想起他的时候总是金牙先出现,闪闪发亮,然后才是他那张略微黝黑的脸庞,和有些泛光的脑门儿。
袁医生的金牙在我们东岙镇远近闻名,以至于很少有人叫他袁医生,而是叫他金牙医生,还有人直接叫他金医生、金大夫,平白无故地让金氏家族添了个人丁。
袁医生没读过医学院,也没参加过什么资格考试,放在今天有可能被吊销行医执照。他只是参加过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一个月而已,然后就在乡卫生院打针换药。乡下人只要见到穿白大褂的一律叫医生。这让他很满足。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受到激励,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他自己找医书看,钻研,成天跟在院长后面不耻下问,还自费跑到县医院去请教,观摩手术,然后找流浪猫狗练手,慢慢的,竟可以做些小手术了。当时卫生院唯一有医生资格的是院长,但院长不动刀子,只开处方。袁医生便填补了卫生院外科领域的空白。
我见到袁医生时,他已经小有名气了,人称东岙一把刀,东岙就是我们所在的镇,人口两万。有人告诉我,他技术了得,动过刀的地方细细一条线,没有疤痕。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妈妈在缝纫机上踩衣服,那也是很细很直的。还有人告诉我,镇里的流浪狗都怕他,哪怕是第一次见到也怕,一看见他就远远跑开,估计他身上有它们同类牺牲的气息。还有人告诉我,乡里的计划生育全靠他了,差不多每对夫妻里就有一个挨过他刀的。还有人说他是个怪人,不结婚不生子,就喜欢动刀子。
那时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熬了大半年,实在是无聊,父亲就托人让我去乡卫生院跟他学习。说学习,其实就是去一个有人说话的地方混日子——我在家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有必要交代一下,那是1977 年上半年。
袁医生见到我,亮出那颗金牙朝我笑,脸上泛着油光,我一下觉得腻歪。医生难道不该是高冷的吗?他本来就其貌不扬,还弄颗金牙,好俗气,像旧社会的地痞流氓。
我很快发现,袁医生和地痞流氓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个宅心仁厚的男人。首先他对病人很好,我从没见过他冲病人发过脾气,我甚至觉得他对病人过于客气了,好像病人是他的客户,需要讨好。病人自然对他感激不尽,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可以佐证,有一面竟然写着“妙手神医,华佗再世”。落款还是刘邦第n代孙。
其次,袁医生对我也很好,从没把我当成小杂役(父亲跟他说,让我给他当个帮手),而是认真地教我打针换药这些技术活儿。当然,我也比较懂事,每天一到卫生院先打扫卫生,再生炉子烧水,给他泡上一杯浓浓的茶(袁医生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喝很浓的茶),然后搓棉球什么的,做些准备工作。我是从小说里看到的,徒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伺候师傅。
我好像挺适合当护士的,很快就上手了。比如打针(学名肌肉注射),从擦酒精棉球到注射完毕,一分钟搞定。只是敲药瓶那活儿我练了一阵子。注射药瓶有个细细的脖子,袁医生给我示范,用镊子一敲就断了。可我不行,要么敲太轻,断不开,要么太重,瓶口断得参差不齐,甚至药液都洒出来了。只好用笨办法,用砂轮砂一下,再掰断。偶尔一下敲开了特别爽,很盼望多一些人来打针,多敲两回。
打针以臀部为主,大概那里肉多不宜感到疼痛。开始我不好意思对患者说“脱裤子”,总是支支吾吾的。后来我就不说了,举着针管让他坐凳子上,朝下努努嘴,病人就明白了,自觉地把裤子拉下去。其实在我眼里,不管是白白的皮肤还是黄黄的皮肤,那就是个扎针的地方。一针刺入,缓缓推进,抽出来按压一下,完毕。
袁医生给我找了件白大褂,很旧,很肥大。我稀罕得不得了,拿回去让妈妈改了一下,每天下班脱下后,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柜子里,生怕被人拿走了。一件白大褂罩在身上,也有人叫我医生了,我顿觉自己高大了许多,真的可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了。外科室的墙壁上挂着这条语录。
二
袁医生全方位培养我,包括说话。比如,不能说打针,要说注射;不能说结疤,要说结痂;嘴唇发绀,不能说发紫;冲洗伤口,要说清创。还有静脉注射,通俗的说法很多,输液、打点滴或挂吊瓶。后三种说法,尤其后两种,袁医生是不允许我说的。
作为一个医生,必须要专业、专业。袁医生说话喜欢重复,就好像现在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静脉注射我也会了:用皮管勒住患者胳膊,拍打两下,找到静脉血管,迅速入针,等血回流上来,就松开皮管。
袁医生狠狠表扬我:嗬,小妹儿比我还利索呢,利索。
我想这大概是我年轻眼神好,加上女孩子天然手巧吧。
很快我就承包了外科室的大部分工作,打针换药连同搞卫生。袁医生得以有些空闲坐下来看书。他翻来覆去看的就是两本书。一本墨绿色的封面,上面写着《赤脚医生手册》,另一本土黄色的封面,上面写着《外科医生手册》。
《外科医生手册》已经像馒头一样又厚又蓬松了,应该是他的葵花宝典。他一打开那本书,可以半天不挪窝,除非有事找他。书已经被他翻烂了,他用胶带横着竖着贴了好几道,五花大绑似的。我很愿意多做一点事,让他去看那本五花大绑的书。
那段时间,父母都感觉我精神面貌大振,每天早早地就出门去卫生院了,比上班的还积极,其实一分钱没有。
有一天来个小伙子,挺高挺壮,但神情木讷,他递过处方单,是注射青霉素。我有些小紧张。因为我还没给人注射过青霉素,这可不比一般的肌肉注射。
袁医生传授技术时一再告诫我:有些人会对青霉素过敏,青霉素一旦过敏会引起喉头水肿,那是十分可怕的。必须马上注射肾上腺素。他把肾上腺素放在药柜最容易取到的抽屉里,再三指给我看。
我按步骤先给小伙子在手腕上做了皮试。三分钟后,我看皮试处没出现反应,但还是不放心,因为袁医生说,偶尔也会发生皮试没事,注射后有反应的情况。我叫袁医生过来看,袁医生看了也说没问题。我就给他注射了,完毕后我嘱咐他观察一会儿再走。
我去给另一个病人换药,换完药过来一看,小伙子还坐在那儿,闭着眼头靠着墙。我有些意外,拍拍他:喂,你可以走了。他忽地一下滑下凳子。吓得我大叫,袁医生袁医生!他死了!
袁医生冲过来喊,准备注射!我拉开抽屉拿出肾上腺素,敲碎玻璃瓶将药液吸入注射器,举着针管捏着酒精棉球就冲了过去——回想起来那一连串动作还是十分流畅的。等我蹲下去撩起他袖子时,他睁开眼睛,迷茫地看着我和袁医生。原来他是睡着了。
吓死我了,也吓死袁医生了。
小伙子走后,袁医生谆谆教导我:做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冷静,晓得不,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大喊“他死了”这种话。
然后,为了掩饰他的惊慌失措,他给我讲了两个因为青霉素过敏而丢命的悲剧,当然不是发生在他手里。
我心里暗想,最好以后不要有人来注射青霉素了,这么吓人。
有意思的是,十年后我因为发烧住院,亲历了青霉素过敏。当时护士给我做皮试没问题,就注射了,哪知刚打完我就有反应了,只感觉嘴皮发麻变厚,呼吸急促。我大喊,肾上腺素!事后照顾我的护士说,好危险,你的血压瞬间降到50。然后她又笑说,你居然还喊了一句肾上腺素,是不是也学过医?
我羞于承认,但马上想起了袁医生的金牙。
三
在我熟练掌握了基本的打针换药技能后,袁医生决定教我创伤缝合技术了。这在他也是顶级技术,属于看家本领。我很激动,如果以前学的是护士手艺,现在学的就是医生手艺了。
袁医生让我先在枕头上练习,就是检查床上的那个白枕头(早已泛黄),他当年就是那样开始的。手术缝合针和缝衣针完全不同,是弯曲的,像月牙一样。要先用专门的钳子夹住针,然后缝一针,打一个结,其实是打两个结,剪断;再缝一针,再打个结,剪断。以至于后半生我一听人说,某人伤口缝了六针或八针,我脑海里会自动浮现出六个或八个小疙瘩。
我在枕头上反复练习,缝了拆,拆了缝。渐渐的,拿钳子的手也自如了。但枕头就是枕头,我始终不知道针线穿过皮肉是什么感觉。
终于,袁医生让我进手术室观摩了。卫生院的手术室虽然简陋,却不乏庄严。我也全身白大褂加上白帽子白口罩,然后学着他的样子反复洗手三分钟,戴上手套,并两只手向上举,不再碰任何东西。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手术,不比在门诊缝个表皮外伤。一个医生替他做麻醉师,另一个医生替他做洗手护士。乡卫生院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我就是个专一的旁观者。
袁医生站上手术台,无影灯下,他的金牙和油腻的脸庞以及浓重的土话都不见了,只剩一双无比灵巧的手,来回穿梭,翻转自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双手,看它给患者备皮,麻药之后,拿起手术刀缓缓切开患者腹部,血慢慢涌出……奇怪,我竟一点儿不害怕。有时候恐惧源于经验,有时候恐惧源于无知,我肯定是后者。助手给他递上一把把止血钳,他一一钳住,快速操作的同时,也没忘了给我讲解。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是一只没能躲过他的大黄狗,他要给它切除阑尾。据说以前他练手艺时总是切除生殖器(阉割术),也许切阑尾更适宜我观摩。
我几乎还没看明白,他已经切除掉阑尾开始缝合了,一层又一层的。我才知道腹腔手术需要缝合五层,腹膜,肌肉,筋膜,皮下脂肪,然后是表皮。前四层用的是羊肠线,可以融化在体内,最后一层用的是丝线,伤口愈合后要拆掉。(现在科技发展,表皮那层也不用拆线了)。只见他的两只手来回穿梭,真能用上行云流水这个词。
不到半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我毫不吝啬地赞美说,袁医生你太厉害了!不是一般的厉害!
袁医生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我的赞扬,说了句今天很顺利、很顺利。然后他用镊子扒拉像蚯蚓一样的阑尾给我看:看到没?上面已经有炎症了。意思是,大黄狗也没有白挨刀。
趁袁医生心情好,我问他,听说你曾经一个人打着手电筒给书记的夫人切了阑尾?袁医生的金牙闪闪发亮,笑道,夸张了夸张了。
他说他刚到乡卫生院时,有两回眼睁睁看着乡民因为干活受伤没能及时缝合,导致流血过多甚至留下残疾,很难受,就下决心自学。他先照着书本在枕头上练,然后买块猪肉来练,再然后为了获得在活体上切割缝合的感觉,就给猫猫狗狗做手术。后来就大起胆子给人的伤口缝合。但始终停留在表皮缝合,没做过手术。
“终于有一天老天爷给了我一次神遇。”袁医生一脸庆幸感恩的表情。那天乡里书记的老婆肚子疼,疼得打滚。当时已经是夜里了,卫生院就他在值班。他马上诊断出书记老婆是急性阑尾炎。可是要送到县医院起码得一个多小时,没有车,只有拖拉机,路上还很颠簸。书记老婆拽着他的胳膊说,袁医生救救我,你给我把肚子切开,把疼的地方切掉,我受不了了。他看着书记不敢应,书记焦急地问:你行吗?他鼓起勇气说,应该可以。书记便签了字。
院长知道后,跑来给他当助手,先换了个一百瓦的大灯泡,又拧亮两把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就在门诊室那张检查床上,袁医生大胆心细地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圆满成功。
首先诊断无误,果然是急性阑尾炎,阑尾处已破溃,几乎要穿孔了。一旦穿孔形成腹膜炎麻烦就大了,有可能丢命。然后手术完美,丝毫没有感染、留下后遗症。书记老婆七天后拆线了,伤口长得很好,于是到处说,金牙医生手艺之好,比县里的医生手艺还好。
袁医生趁机向书记提出,给卫生院建个手术室。书记没理由不同意,那时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了,正好也需要。卫生院终于有了手术室,虽然简陋,一张手术床一盏无影灯一个手术器械车,但袁医生终于可以上手术台了,不用打手电筒了。遇到急症,或计划生育需要,他便一展身手。渐渐的,他的技术被乡亲们认可,金牙的美名四处流传。
四
那次手术后,我对袁医生更加膜拜了。我把他那本五花大绑的《外科医生手册》拿回家,细心展平卷起的页码,用妈妈的铁熨斗压平,再用父亲原先绘图的坐标纸包了个封皮,最后请妈妈用毛笔写了书名——妈妈的字全家第一(父亲语)。
袁医生接过书,金牙亮闪闪地感叹道:太好了,简直好惨了,跟新书一样,我又可以看几年了。
我说,我看到你每次抱起这本书就跟抱了个大馒头似的,恨不能一口一口吃下去,连渣渣都不剩。
袁医生说,你说得相当准确、相当准确。我看你可以当个作家。
我顿了一下,毫不害羞地说,我就是想当个作家。
袁医生没有大惊小怪,笑眯眯地说:可以可以,我看可以。
这是我第一次和人谈起我的理想。我很感谢他让我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并且没有嘲笑我。
袁医生说,你以后能去读个大学就好了。
我说,你怎么不读呢?
他说,我高中还没毕业就搞运动了,大学停了。后来只招工农兵学员。我又不算。我要是能上大学,肯定还能医好更多的人。我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得很呢。
他的眼神流露出无限的向往和无限的遗憾,搞得我也失落起来。
第二次观摩袁医生手术时,我有幸动了手脚。
缝到最后一层的最后两针时,袁医生忽然说,你来试试。
我就鼓起勇气站到他的位置上,屏住呼吸,缝了最后两针。完成后,我的手微微战栗,脸颊发烫。人生第一缝啊。缝真肉皮果然和枕头完全不一样。
不过和袁医生比,差距马上出来了,我的针脚太大,也有点儿歪。
袁医生还是鼓励了我:第一次,不错,很不错。
我的患者也是一条大黄狗,清醒后,我讨好地给它吃了一个包子,请它多多包涵,忽然就体会到了袁医生平日里对患者的心情。
回到家,我隆重告诉父母,我上了手术台,我给狗狗缝了两针。
妈妈说,这个金牙,胆子也太大了,居然让你上手术台。我无比兴奋地说,我以后也要当外科医生,我喜欢做手术。
我居然忘了自己才说过想当作家。
爸爸说,当医生很好啊,哪朝哪代都需要。
妈妈说,就你那个体质根本不行,外科医生做一台手术要好几个小时,你根本站不下来(在妈妈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弱小的丫头)。
父亲安慰我:要有机会读个医学院,还是有可能的。
我一下觉得很沮丧,感觉上大学这事离我太远了,比月亮还远。袁医生那么想读书都没读到,我就更别指望了。
我继续去卫生院混日子,在那里好歹还能有点儿存在感。每天听人叫几声“医生”、说几声谢谢。
五
转眼我在卫生院已经混了小半年了,从春到秋,秋分都过了。
那天早上袁医生一来脸色就不好,说头疼,进到里间休息去了。我猜他昨天连续做了两台手术,累着了。
天气依然很热,秋老虎发威。我坐在诊室搓棉球,对着一台老旧的电风扇吹,听窗外最后一批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叫,一时间有些厌倦,也有些惆怅。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真的永远在这里混日子吗?翻年我就十九岁了。
忽然听见门外一片嘈杂,有人大哭,有人吆喝。我站起来想出门看,却见三四个人冲了进来。大哭的是个年轻女人,捂着脑袋,血从她的指缝流出,像几条红色的蚯蚓爬过脸颊,吆喝的是她家人,说家里盖房子,一根房梁掉下来打在了她脑袋上。
金牙医生呢?金医生呢!金大夫!他们大喊大叫,金光闪闪。
袁医生从里间出来了,他皱着眉,先冲女人大喝一声:不要哭了,哭了流血更多。他很少这么凶,显然有些烦躁。然后他查看了伤口,对众人说,问题不大,缝几针就好了,缝几针。
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说,你来做。我今天人不好,脑壳痛,可能感冒了。我瞪大了眼睛。他说,就是个表皮缝合,伤口不大,缝几针就可以了,你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我点点头,心情很激动,转身去拿器械包。
女人见我忙碌,意识到什么,哭着说,我不要她缝,我要你缝。袁医生说,她也是医生,手艺比我还好,好得很。女人还是摇头说,我不要她缝,我要你缝。
袁医生说晓得了晓得了,你不要激动嘛,安静下来,一激动你的血全流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用纱布给她按压止血。
袁医生让家属出去,把她安置到椅子上,拿出做手术的洞巾盖住她的脑袋,朝我使个眼色。我上阵了。
在此之前,我已看过多次袁医生给老乡缝合伤口,程序已经烂熟于心。先用剪刀剪掉伤口四周的毛发,有些已经被血液黏成一缕一缕的,然后做清创,然后注射局麻,然后穿针引线。
开始缝合时,面对那道血糊糊的口子,我的手还是有些抖。亮晃晃的针下不去手。我闭上眼在心里默念三遍:我是为她好,我是为她好,我是为她好。然后,就下手了。
我每缝一针,就看袁医生一眼,他点点头,我就继续。渐渐地淡定了,手也稳了。一共缝了五针,我感觉我那五针缝得比平日里练习时还要好,针脚、间距都很标准。
袁医生给我比了个大拇指,然后一屁股坐到旁边的椅子上,看上去很虚弱。
我仔细包扎好伤口,摘下女人的洞巾。女人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抬眼看到我,尤其看到我手套上的血迹,还是很惊诧:是你给我缝的?
我装作没听见,去拿绷带给她缠脑袋。她伸手去捂脑袋,好像要确定脑袋是否安在。袁医生在一旁说,不要乱碰伤口。我告诉你,缝得很好,不信拆线的时候你看。
袁医生的语气不容置疑。女人终于不说话了。
走之前女人说,谢谢了,医生。她是冲着袁医生说的,捎带着也看了我一眼。我的满足感瞬间爆棚,早上的厌倦情绪和惆怅心情,都不复存在。我的天,说不定以后我也可以和袁医生一样自学成才呢。我开始想入非非。
我如长辈一般对女人说:今天流了不少血,回去煮两个鸡蛋吃。
六
不料这次缝合,却是我“行医”的终结篇。
就在我给那个打破头的女人缝了针后的第二天,父亲告诉了我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学要面向全社会招生了,也就是说,我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了,忽然感觉天地开阔,激动不已。
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袁医生,开始在家复习。我甚至都没有善始善终,去卫生院给那个女人拆线。什么注射、清创、缝合,都被我抛在了脑后,我抱着仅有的几本书开始死记硬背,甚至仅凭新华字典后面的历代皇帝年表复习中国历史。
某一天,忽然听妈妈说起了袁医生,感觉很遥远。
妈妈说,今天我去卫生院拿药,听说袁医生的金牙没了,成了个“缺牙巴”。
我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想象他张开嘴缺个牙的样子。
妈妈说,你可真是个没良心的丫头。
我一想是啊,我怎么能这么开心地笑呢。袁医生是我师傅,虽然我这个徒儿没出师。我讪讪地说,那个,我的意思是,怎么没的呢?
妈妈说,说是出了一起医疗事故,患者追着他赔钱,他没钱,就把金牙取下来赔了。
哦,这让我很意外。第一没想到他那颗金牙是真的,我曾怀疑只是包了一层金纸。第二没想到他会出医疗事故,那么心细的一个人。这也太倒霉了。我感叹了一句,但也就是感叹而已。
一个多月后,我和五百七十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再之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是医学院,是大学中文系。我那个数理化基础哪里考得上医学院。文科毕竟可以临时抱佛脚。
我安慰自己,读中文系,也算回到初心了。
妈妈说,我看你走之前应该去看一下袁医生。
我没吭声,卫生院已经离我非常遥远了,连东岙镇都要被我抛在脑后了。妈妈见我不搭理,语气严肃地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找袁医生闹事的患者,就是你缝合的那个女人。
我目瞪口呆,简直无法相信,我觉得我缝得很好,袁医生都说我缝得很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妈妈说,我骗你干嘛?我去问了袁医生,他亲口告诉我的,就是那个打破头的女人,只不过袁医生坚持说是他缝的,不准那个女人来找你,害怕影响你复习。他还特意嘱咐我不要告诉你。
我跑去看袁医生。
袁医生一见我就开心笑道:大学生,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晓得你能考上,你可以去上大学了。好羡慕你哟,太羡慕了。
他果然成了缺牙巴。
我说,那个,那个女的,那个伤口……
他摆摆手:莫事莫事。伤口感染很常见。就是掉了一根很短的头发在伤口里,天又热,有点儿感染。现在已经好了,已经好了。
我说,那你的牙,金牙?
他说,也不晓得是哪个造的谣,牙齿是我自己掉的,牙龈炎。原来就是个烂牙齿、烂牙齿,包了一下。
我将信将疑,这和妈妈说的不一样。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但我没有追问下去,选择了相信。因为这样我可以安心些。
我将父亲托人给他买的新版《外科医生手册》递给他。袁医生拿到书,半晌无语,抬眼看我的时候,竟然眼泪汪汪。我是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有人拿到书眼泪汪汪的。他抹了一下眼泪不好意思地说,又有大馒头可以吃了,呵呵,大馒头。
七
等我再一次想起袁医生时,已结婚成家有了儿子。
儿子一岁多时,有一天扶着小铁床没站稳,忽然摔倒,手指被铁床的一个挂钩割伤,鲜血直流。我抱起他冲向最近的医院。那时儿子已经二十多斤了,我就像抱着一袋米,气喘吁吁。他一路大哭,我也一路大哭。我们冲到医院,挂上号,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医生把我们带进外科室。
伤口在小指和无名指之间,手上全是血,我和儿子还在齐声大哭,充分体现出了母子心连心。那个年轻医生戴好手套拿着镊子和针走过来,祈求似的说,不要哭了好吗,你们两个一起哭,让我怎么缝?
我一下清醒过来,想起了袁医生,想起了遥远的卫生院的秋天的早上,想起了那个打破头的女人。
我止住哭,叫儿子也忍住。哭声便戛然而止,显然我们两个完全是习惯性在哭,说收就收住了。
年轻医生定定神,开始操作。他的一双手十分灵巧,完全是袁医生再现,青春版的袁医生。因为孩子手小,皮肉嫩,他选了一根最小的针。我屏住呼吸,以一个内行人的眼光盯着,完全忘了那个针是穿过我宝贝儿子的血肉。清创之后,他开始缝合,缝了两针,应该说是很完美的两针。
我脱口说,你缝得太好了,跟袁医生一样。
他很诧异:袁医生是谁?
我说,就是金牙医生啊,金医生,他有一颗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