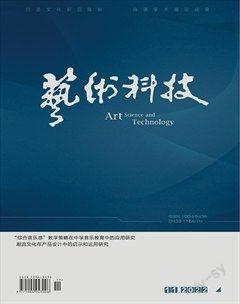民间舞蹈睢宁落子舞的艺术特征及表演形式研究


摘要:徐州睢宁民间舞蹈“落子舞”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一名下邳的汤姓艺人将三国时期的武艺动作、宋代莲花落子舞等元素结合,最终以汉代乐舞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一独具特色的民间舞种已经拥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瑰宝。基于此,文章从睢宁落子舞的发展历史、舞蹈内容、艺术特征、表演形式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期推动落子舞的弘扬和发展。
关键词:民间舞蹈;睢宁落子舞;艺术特征;表演形式
中图分类号:J7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1-0-03
睢宁落子舞发展历史悠久,流行于徐淮地区,是一种典型的民俗舞蹈。舞蹈动作鲜明,伴奏音乐多彩,表演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蕴。落子舞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并忠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研究民俗舞蹈,对繁荣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0 引言
“落子”又被人们称为“莲花落”,是江苏苏北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1],在徐州东部的睢宁县流传甚广。清朝康熙年间,李声振在其著作《百戏竹枝词》中写道,“徐沛伎妇,以竹鞭缀金钱,击之节歌,其曲名《叠断桥》,甚动听。行每覆蓝帕,作首妆”,[2]这印證了落子舞在徐州地区流传甚广。通过深入徐州农村调查发现,直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以竹鞭缀金钱”为道具的落子舞和《叠断桥》相关民歌。
据当地民众回忆,在旧社会,徐州街头巷尾时常能看到民众在街边打“莲花落”乞讨谋生。1958年,睢宁落子舞代表徐州前往北京汇报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与亲自接见,自此,落子舞翻开了新的篇章。睢宁落子舞因独特的地域色彩和特点,于2006年成为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3]。
1 睢宁落子舞的地域特色及发展历史
睢宁县地处江苏北部,素有经济重镇、徐州市东南大门之称,占地面积达1773平方千米,旧名属下邳。史书上的下邳是我国的历史名城。从夏禹(公元前2157年)封予奚仲,建立下邳国到唐末,此地被立国封邑22次;从宋代到清代,此地是州、郡、县的治所,始终是我国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清康熙七年,此地因发生大规模的地动和水患,被淹没而灭亡[4]。
古下邳曾是我国人文荟萃、兵家必争的古战场。汉代圯桥进履、张良名传千古,三国鼓角争鸣、吕布下绞刑门楼等闻名中外的历史典故都发生于此,并留下了很多遗迹。古下邳还是我国最早的禅宗圣地,古有“寺庙之多,莫过于邳”之说,加之风光秀丽,沂、武、泗水相连的交通便利条件,引来李白、苏轼、董其昌等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大量诗篇和墨迹[5]。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使睢宁民众形成了勤奋淳朴、士崇学问的风尚;战乱的环境使先民形成了喜勇尚武、粗犷强悍的秉性和作风,也孕育和发展了落子舞这种独具东汉特色的传统民间舞蹈(见图1)。
据《古邳镇志》《睢宁县志》记载,“明朝时睢宁汤姓‘莲花落已很超群”。明代至清初,落子舞依托下邳“羊山庙会”的方式增强了舞蹈效果。清代至民国时期,落子舞一般活跃在春节前后,并借助“香火会”广为传播,落子演员的数量年年大增。在贫困时期,落子舞又变成一种乞讨方式,乞讨者手拿一根打狗棍(今日落子舞道具“莲湘”),上下敲两肩,舞动有序,边舞边唱,以获得有钱人施舍。新中国成立后,睢宁落子舞得以蓬勃发展,各乡、村均建立了不同的“落子”,活跃在城乡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现在的睢宁落子舞。
2 睢宁落子舞的艺术特征
睢宁落子舞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同于我国其他民间舞蹈的独特内涵和风格特征。
2.1 鲜明的动作特征
在传统落子的基础上,城市不断发展和各种民间舞蹈形式相互融合,因此出现了文武落子之分。“武落子”跳跃幅度大,武打元素多,也称“大架落子”,具备热情、豪放、粗犷等特征,以睢宁县刘保顺为典型,创作有《激情落子》等[6];“文落子”跳跃幅度小,武打成分少,也称“小架落子”,具备清雅、细致、明快等特征,以下邳卢修田为典型,创作有《闹洞房》等。男子行动粗犷勇敢、机敏顽强,女子行动则妩媚多姿、娇柔轻盈,既饱含强烈的年轻生命力和阳刚魅力,又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在分配舞蹈动作时,往往会挑选一名男性领伞人,其右手握伞把,左手拿毛巾,再选派两男两女紧随其后,男性右手握莲湘,女性右手握主板,左手持莲湘。
2.2 多彩的音乐伴奏
我国传统落子舞的重要乐曲有《小抱妆盒》《叠断桥》等,其伴奏音乐仅有三类,即锣、大鼓、竹笛演奏,其中敲击乐以锣为主。尽管敲击乐仅有两种,但其舒缓合理,很有剧情,旋律既可以表达舒缓柔情,又可以表达欢快有力。同时,由于“文落子”“武落子”的出现,伴奏音乐逐渐增加了扬琴、琵琶艺术、二胡演奏等,配乐曲调也越来越丰富。
3 睢宁落子舞的表演形式
3.1 表演形式
落子也叫“乐子”,有大众欢乐之意。徐州话“乐”同“落”音,通过有序的跳跃,可以抒发大众的欢悦之情。其舞姿造型美,活动范围大,力度明快,节奏感极强,为苏北古下邳睢宁一带所独有[7]。传统落子舞由当地一种民俗拳术舞蹈配合走唱方式发展而来,通常由3~5名男女表演者组成一支队伍,全队人员要求男女各一半,男女领舞者是队伍的支柱和核心。表演舞蹈时先由1名英俊男子手执花伞领舞,2名白衣男子打莲湘或舞动霸王鞭,2名红衣女子手打竹板和耍红散巾,随后5名男女表演者依次以走跳步、搓跳步、踩寸子等舞蹈步法反复变换队形,舞动有条不紊,高潮迭起。有虎跃翻身、单双扫腿、手打螃蟹等近似我国武术的高难度动作,也有寒鸦凫水、骜子翻身、白鹤亮翅等曲线优雅且神韵浓厚的形象化动作。
3.2 服饰道具
3.2.1 服饰安排
睢宁落子舞的男女服饰不仅风格独特,而且体现了苏北民众高超的传统技艺。道具花伞、竹板、莲湘、手绢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舞蹈中(见图2)。
其中,领伞人及男青年头系白毛巾,穿中式对襟短袖上衣,白底镶湖蓝色边,湖蓝色的腰带、中式裤子、圆口布鞋。而女青年头系红彩球,穿中式大襟上衣,桃红色底镶深红色边,黑平绒围兜,刺绣图案,镶金色亮片边,中式深褐色裤子,圆口红布鞋。
3.2.2 道具选择
(1)竹板。把青竹劈开,做成长、高约3寸、宽1.5寸的竹板,竹板的一端钻两个小孔,以红绸或绿绸把两个竹板扣住,且松紧要适度。竹板供女角色使用,因为古代战斗通常伴随鼓声,竹板配合鼓的击打,其声具有鼓舞士气、击鼓点兵的作用。
(2)手绢。粉红绸缎手帕共两块,两名女子左右手各持一块,具有搭配竹板,使舞动更有序的作用。
(3)莲湘。用长约35寸的青竹,在相距两端8寸的位置钻一个长方形的空洞,并用铅丝在空洞中穿小铜币,青竹外面用紫红、大红、黑、白颜色的布做套子套上(或画上色彩),且两端装挂粉红色的绸结。莲湘主要由男演员使用,由于“汤家落子”是为庆祝其先祖的威风雄姿,因此将莲湘作为用鞭。后来经历代艺人提炼,在使用莲湘的各种活动中创新了和谐的舞蹈旋律,给人热情、积极向上、豪放、粗犷的感受,在各地演员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便是对莲湘旋律的概括,如“身随步,两臂恍,上下左右挥鞭忙;鞭打四肢肩背部,鞭鞭打出脆声响”。
(4)花伞。花伞的伞柄用高约18寸的竹竿制作,把一端劈开为4半,用铅丝做一个直径约8寸的小圆环,将圆圈与劈开的竹条绑在一起,做成伞架,再把淡紫红色的布缝在圆环上,周围装上约3寸长的绿色绸边,绸边缘放1寸长的黄红丝穗,靠伞顶一圈的地方也放1寸长的黄丝穗。在圆环四周相等长度的部分,还装有4根分别长约4寸的绿绸带,每根绸带下面各挂一个小竹篙。圈顶用直径5寸的白绘小圆环,并用彩色在白环上绘出花纹。花伞原为男演员使用,由于古时伞下的人为最高统领,因此持伞者为领舞。演员在表演时会改变领伞的位置,以指导全场跳舞者和乐队。
4 睢宁落子舞的发展走向
对徐州地区的民众而言,落子舞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还是一项传播文明的活动,更是像灵魂一般生命力传承的延伸。
首先,在政府文化建设方面,未来徐州市须重视文化馆建设,妥善保存多年来流传下来的落子舞文化,使这个传统瑰宝能长久流传。
其次,为弘扬睢宁落子舞文化,政府须增强当地民众的思想意识。
第一,加强产品开发,包装落子舞,打造文化旅游产品。文化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不应局限于观光旅游,应使游客通过落子舞的外在形态,全面认识其背后蕴含的历史内涵,感受徐州地区的文化底蕴。在此前提下,须深入研究传统的落子舞,要在完全掌握落子舞真正面貌的基础上,努力对其复原再造,使其不但具有艺术观赏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参与性,进而吸引旅游者的目光,推动徐州区域旅游发展。
第二,挖掘落子舞的现代民俗传统社会文化产业的附加值,提升现代民俗传统社会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落子舞既有“下里巴人”的淳朴,又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是徐州最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其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且反映了徐州民众对土地的情感,对岁时节日的依托,更是对徐州历史人文、民俗传统特色的集中反映。
第三,定期开展展演、比赛等活动,通过公众性的活动,加深人们对落子舞文化的认知。
最后,教育部可以大力推出与落子舞相关的教材,助推其进入课堂。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年轻人的努力,应通过对学生的培养,加深其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使其意识到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进而为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8]。
5 结语
具有苏北地区传统特色的落子舞极为罕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北地区淳朴善良的民风,也反映了苏北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睢宁落子舞承载着苏北地区自古以来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内容,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地域审美风格,是我国传统民间舞蹈艺术文化宝库中的特殊宝藏,也是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传承、创新、开发的美学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睢宁落子舞以独特的舞蹈形式,传承了我国汉代至今民间舞蹈的血脉,其存在说明我国古代的乐舞并没有全部销声匿迹。如落子舞中男演员表现的“大翻小翻”,可能是汉代乐舞中“飞檐倒立”的延伸,这只能从睢宁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中得到证实。因此睢宁落子舞的发展史绝不仅有文章可寻的几百年,或许是几千年,或许更久远,是千年大汉民族血脉之相传、灵魂之传承。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坚信:每一种落子舞的活动,每一种落子舞的小调,都能带领我们穿越文化的空间,使我们似曾相识、似曾相闻。
参考文献:
[1] 许瑞信.江苏睢宁落子舞教学组合探究[D].北京:北京舞蹈学院,2019.
[2] 吴霜,吴雪梅.徐州落子舞的环境以及形态分析[J].黄河之声,2018(22):142-143.
[3] 李雯.對“同源异流”舞蹈艺术形式落子舞的对比研究[D].聊城:聊城大学,2018.
[4] 相宁.睢宁“落子舞”考略[J].北方音乐,2017,37(16):234-235.
[5] 闫映东,缪思薇.徐州地区落子舞形态研究[J].艺术品鉴,2017(6):137,141.
[6] 丁洁.浅析睢宁民间舞蹈[J].大众文艺,2011(11):161.
[7] 袁永林.睢宁落子舞管见[J].时代人物,2008(11):134-135.
[8] 姜玉梅.“落子舞”的传承与发展需从少儿抓起[J].剧影月报,2013(3):143-144.
作者简介:王非凡(1992—),女,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