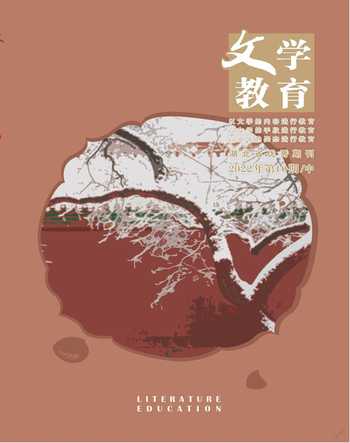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都柏林人》中伊芙琳的颠覆与抑制
王晶晶
内容摘要:《都柏林人》是二十世纪初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包含十五篇短篇小说,《伊芙琳》是其中第四篇,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篇,讲述了同名女主人公人生中的一次抉择。新历史主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新兴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丰富和深化了传统学说。本文拟运用新历史主义中“颠覆”和“抑制”兩个概念对《伊芙琳》中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指出伊芙琳这个人物的思想和举动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都柏林人》 伊芙琳 新历史主义 颠覆 抑制
詹姆斯·乔伊斯是二十世纪初著名爱尔兰作家,以“意识流”创作手法而闻名,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出版于1914年的《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其背景设置于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在该小说集里,乔伊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都柏林中下层人民不同的生活片段,反映了当时爱尔兰人麻木不仁如一潭死水般的精神状态。《都柏林人》中共有十五篇短篇小说,分为童年、青年、成年和社会四部分,《伊芙琳》是其中的第四篇,位于青年和成年部分之间,讲述了同名女主人公在刚满十九时碰到的人生中一次两难抉择。虽然该小说篇幅较短,不足2000英文单词,但它却包含了深刻的主题思想,引发了广泛地思考。
新历史主义的名词首先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2年提出,其具体理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历史主义理论强调文学与历史的交互性,同时扭转了在其之前盛行的形式主义等流派将文学的社会功能搁置的倾向,重新将文学的政治功能列入主要的考量范畴。“颠覆”和“抑制”是新历史主义理论中两个重要概念,史蒂芬·格林布拉特指出:“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而抑制则是把这种颠覆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使之无法取得实质性地效果”。《都柏林人》中对伊芙琳的描述则正符合在“颠覆”与“抑制”之间挣扎的特征。
一.伊芙琳的“颠覆”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芙琳刚满19岁,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普通中下层人家。她的母亲为家庭操劳了一生,早早地因病离开了人世。她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宽裕,伊芙琳经常为钱跟父亲争吵。伊芙琳的父亲作为家庭的主人,脾气很暴躁,动辄对家人进行暴力威胁。伊芙琳是家中长女,她有四个兄弟,成年的两个中一个已经夭折,另外一个忙于生计很少回家。作为家中唯一的女性,伊芙琳不仅要去杂货店工作养家糊口,还承担着照顾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重任。在这样沉重的压力之下,伊芙琳对都柏林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生活产生了厌倦。她偶然结识了常年在海外生活的水手弗兰克,坠入了爱河,于是摆在她面前的有一个全新的选择,她想跟弗兰克私奔去南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新的生活。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写到,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如果她是一个少女,父亲就会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力。如果她结婚,他会把权力交给他的丈夫。”小说《伊芙琳》中两位女性人物的经历正是这句话的体现。在《伊芙琳》的故事中,伊芙琳的母亲没有直接出现,但从情节中可以看出伊芙琳的母亲为家庭操劳了一生,操持家务,照顾子女,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但最终疯癫致死。虽然没有正面描述,但仍然可见,伊芙琳的母亲正是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爱尔兰传统女性。她们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一直在家庭中处于从属于男性的位置,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在家庭事务中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只是丈夫的附属品。乔伊斯创造的这位母亲的形象也有他自己母亲的影子。乔伊斯的父亲不善经营但又喜好挥霍,家中全靠母亲艰辛操持,最终乔伊斯的母亲不幸患上癌症,经历了长期病痛的折磨最终去世。乔伊斯一直认为正是父亲的作为带来了母亲人生的痛苦。伊芙琳与母亲一样,作为一个女性,也在遭受父权给她的压制。在小说的描述中可见,伊芙琳把她自己在杂货店打工辛苦赚来的薪水都交给父亲,但从父亲那里要钱却难于登天,“每周六晚上一成不变地为了钱和父亲大吵一架”,父亲自己游手好闲,但还指责她“花钱大手大脚,没脑子”。在父亲发现伊芙琳和弗兰克的私情后,“随即勒令她不许再和弗兰克讲一句话”。伊芙琳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但却没有支配金钱的权利,对自己的感情,她也不得不听由父亲的支配,由此可见,在这个故事里,“父亲”的形象正是传统父权的典型代表。
伊芙琳生活的二十世纪初正是西方第一次女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女性开始不再满足于父权社会中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定义,纷纷走出家门寻求独立自主的人生。因此在时代的大潮下,伊芙琳有了与母亲不同的思考,弗兰克的出现正是促成她作为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的一个契机。她开始思考自己当下的生活方式和自己对未来的追求,萌生了“颠覆”父权社会中传统女性定位的想法。尽管父亲不允许伊芙琳与弗兰克来往,但伊芙琳仍然和弗兰克秘密约会,她下定了决心要离开都柏林去寻找新的生活,她想到“在新的家,在千里之遥的陌生国度,情况可就天差地别了!到时候她会嫁做人妇——正是她,伊芙琳。人们会善待她,敬重她。他就不会再遭受母亲生前所受过的凌虐。”之后伊芙琳认识到“她母亲牺牲了自己平凡的一生,最后却落得个疯癫至死的结局”,“逃!她必须逃!……她想要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她要活的这样惨?她有权过上幸福的日子。”至此,伊芙琳已经对母亲的人生悲剧有了新的认识,她意识到了自己不想重蹈覆辙,走上母亲的老路,一辈子为了家庭中的男性默默奉献,她想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她的心目中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已经觉醒。
虽然伊芙琳最终没能成行,但在爱尔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乔伊斯笔下伊芙琳的思想已经具有了相当地进步意义,乔伊斯作为一位男性作家,能够惟妙惟肖的写出时代大潮下女性的觉醒非常难能可贵。
二.伊芙琳的“抑制”
伊芙琳在思考是否跟弗兰克私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时,思想意识上出现了觉醒,她意识到自己应当抛弃传统的身份定位而去追求个人的目标,但最终因为强大的“抑制”力量,她却主动选择了放弃逃离的机会,没能完成一次彻底的出走和“颠覆”。
爱尔兰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受到英国严密的控制,同时天主教对爱尔兰的长期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同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小说中的伊芙琳成长于爱尔兰保守的天主教氛围之下,小说中提到伊芙琳家里就有一张圣女玛加利大许愿的彩色图片,还摆放着父亲的神父朋友的照片,每当有客人,父亲就会跟客人谈起他的神父朋友。在伊芙琳即将跟弗兰克一起坐船離开时,她“感到焦躁又茫然,开始向上帝祈祷,祈求他指引她前行”,在她犹豫不决时,“她紧张得想呕吐,只好不停地默默张合嘴巴,虔诚专注地做着祷告”。从上述描述可见,宗教思想对伊芙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个人抉择的关键时刻,伊芙琳并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反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之上。按照基督教的传说,人类中第一个女性夏娃是第一个男性亚当的肋骨所造,并且夏娃偷吃禁果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因此长期以来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一直被认为在智力等各个方面均低于男性,女性只能是男性的从属,需要男性的帮助才能生活,因而要服从于男性。天主教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中最为保守的一个分支,因此不难理解在天主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伊芙琳尽管已经出现了思想觉醒,但最终还是长期影响她的宗教力量占了上风,促使她放弃了对独立的追寻。
从小说的描述中可见,伊芙琳的母亲尽管度过了痛苦的一生,但她却从未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伊芙琳思考自己的抉择的时候,她“记起自己曾经对母亲发过的誓:要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地维持这个家”。伊芙琳的母亲去世时,父亲依然健在,并且家里还有一个成年的兄弟,但母亲却交代家中除她之外唯一一个女性成员伊芙琳照顾家庭,并且要求伊芙琳发誓,由此可见伊芙琳的母亲对于父权社会给女性规定的承担家庭重任的角色深信不疑。即使自己的一生已经成为了牺牲品,她仍然要求她的女儿继续她的人生道路,为家庭继续奉献。伊芙琳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她的回忆中可见母亲对她的强烈影响,所以伊芙琳的思想也同样被传统父权社会的道德观念深深的束缚着,一直理所应当地认为照顾家庭是自己的必然责任。伊芙琳无法挣脱社会性别话语在女性自身的内化作用,考虑到母亲临终的嘱托,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曾经萌发的追求,选择留在都柏林。
伊芙琳个人性格比较软弱,对代表父权的父亲非常畏惧。小说中写到,父亲从小在伊芙琳心中就是权威的象征,在伊芙琳小时候跟住在附近的同伴一起玩儿,“她的父亲常常跑到地里来,举着他那根李木拐杖,想把他们撵回去。”直到伊芙琳长大,父亲作为家庭的主宰依然给她巨大的压力,“即使是现在,她已经是个过了19岁的大姑娘,有时还是会觉得自己时刻处于父亲暴力的阴影之下。她知道这就是自己心悸问题的症结。”伊芙琳从小到大都不敢正面反抗父亲。在父亲强烈反对伊芙琳和弗兰克的私情时,伊芙琳仍然没有反抗,而是选择和弗兰克偷偷约会。即使内心已经拿定主意想要和弗兰克一起离开都柏林,伊芙琳依然不敢直接告诉父亲,而是选择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伊芙琳觉醒的意识最终被“抑制”和个人性格也不无关系。
此外,伊芙琳也并不具备独立的个人经济基础。伊芙琳受教育程度有限,因为养家糊口找了一份工作,但即使她努力工作,一周也只能赚到7先令。小说里写到,伊芙琳想,如果她离开,店里“很快会登招聘广告填补她的空缺”,可见在她工作的杂货店,她也属于可有可无的人,因而经常受到加万小姐的指责和嘲讽。由于经济基础所限,伊芙琳对新生活的向往仅仅寄托在另一个男性弗兰克的身上,“弗兰克会拯救她的。他会给他新生……他会拯救她的。”在伊芙琳的思考中,反复跟自己说这弗兰克会拯救自己,可见她自己也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期望并不一定能实现。把逃离父权束缚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相识仅仅几个星期的男人身上,原本也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难怪伊芙琳最终选择了放弃。
波伏瓦曾经写到“女性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所指正是社会性别话语对女性的强烈作用。对于伊芙琳来说,在宗教、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伊芙琳刚刚觉醒的女性独立意识被“抑制”在许可的范围内。小说的最后写到,伊芙琳想,“不!不!不!我做不到!”接着发出了凄厉的一声惨叫。尽管弗兰克一直在向伊芙琳呼叫,但已经到了港口的伊芙琳还是放弃了上船奔向新生活。伊芙琳面色苍白,“不知所措又茫然无奈,像一只无助的困兽”。她最终没能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仍然选择了爱尔兰传统女性的道路,继续回归她麻木的家庭生活。
《伊芙琳》作为《都柏林人》中最短的一篇,尽管寥寥数语,但依然把一个二十世纪初在“颠覆”与“抑制”的力量之间挣扎的年轻女性人物形象描写的栩栩如生。小说中的伊芙琳从母亲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女性的问题所在,萌发了颠覆父权社会的桎梏,追求个人幸福的现代女性意识,但在传统思想等各方面因素的抑制之下,伊芙琳最终选择了放弃。虽然小说最后没有明确给出伊芙琳的结局,但伊芙琳经历了思想觉醒的洗礼,未来应该会对女性的人生追求有着更多的思考和更合理的抉择。
通过伊芙琳这个人物,乔伊斯既写出了二十世纪初爱尔兰人对于死气沉沉的爱尔兰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也写出了在这个新世纪里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预示了“颠覆”父权社会传统的女权运动大时代的到来。虽然由于强大的“抑制”力量,伊芙琳的觉醒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但是在当时爱尔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伊芙琳身上体现出的独立女性意识的闪光已经充分体现了乔伊斯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积极价值和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Deaubvoir, Simone. The Second Sex [M].London: Macmillan, 1973.
[2]Greenblatt, Stephen.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爱尔兰] James Joyce. 都柏林人 [M]. 安知,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4][爱尔兰] Peter Costello. 乔伊斯 [M]. 何及锋,柳荫,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梁雅玲.无力的挣扎——对《伊芙琳》的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解读[J].科技资讯,2009(21):222.
[6]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J].外国文学评论,1994(03):20-29.
[7]赵静蓉.颠覆和抑制——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J].文艺评论,2002(01):13-16.
[8]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华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