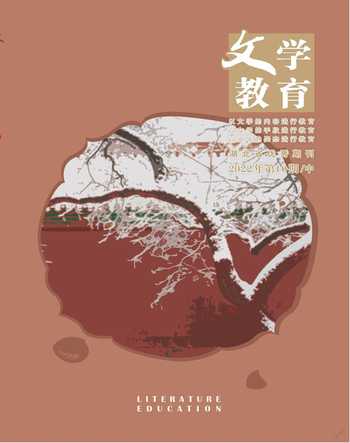鲁迅《铸剑》的诗化与复仇主题联系
刘方圆
内容摘要:诗化不仅是《铸剑》的文体的审美特点,还与小说的主题选择存在影响关系。从创作心理追溯,鲁迅的自卑感与英雄主义情结相反相成,他在当时孤立、悲凉的情绪体验中酝酿成强力的诗意表达倾向,而复仇主题正与这种倾向在叙事特点、审美风格等方面相吻合。诗化与复仇主题的重合的现象,也呈现在《伍子胥》《复仇》等其他现当代作品之中。以《铸剑》为样本,贯穿小说诗化与复仇主题之间的线索,可以更进一步揭示作家从创作动机到策略选择这一条路径的联系。
关键词:鲁迅 《铸剑》 复仇 诗化
在具有诗化特质的现当代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复仇的主题,并且引起的研究者们的关注。关于现当代小说中的复仇研究,论者往往以复仇为切入点,探究作家心理世界的视角,重点多集中在作家思维和小说中人物行为、命运特征的分析,指出作品对复仇主题的颠覆性书写。但是,正是在诸多论者隐约略述区间,几个复仇主题的文本产生了交叉重合的部分,即小说的诗化。钱理群称《铸剑》的题旨“得到了极富诗意的体现”“鲁迅用他那诡奇而绚丽的笔触,将‘复仇精神充分地诗化了”[1]。无独有偶,其他几篇被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复仇主题小说代表作的作品也被赋予了“诗意”的称赞:“尽管《伍子胥》有着小说意义上的完整的故事与贯穿性的线索,但构成小说基本原素的是浓郁的诗情与哲理的氛围融合为一体的意境与幻像。”[2]“这篇小说(余华的《鲜血梅花》)也富于诗意,甚至可以说是余华小说中最具诗意的一篇。”[3]显然,作者在诗化的审美追求和复仇主题的选择之间存在着不自觉的倾向性。寻找二者的联系,以期突破对诗化文本的特征描述,并發展探究创作心理的可能,是研究的出发点。
对诗化小说的性质界定虽然众说纷纭,但是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有一条诗化小说的脉络是基本得到认可的。如果将主题集中在复仇,那么通过不同叙事形态和美学风格的对比,更能清晰地分辨出其中诗化一脉的特质。比如,万杰在《现代革命语境中的复仇叙事研究》中将现当代文学中的相关主题作品大致分为受革命话语影响的复仇叙事和受其他的西方现代价值理念影响的复仇叙事。相比较而言,前者以复仇叙事为无产阶级革命赋予民间伦理上的合理性,更注重情节的曲折性,复仇对象与复仇者对峙而在,着重塑造复仇者的英雄形象。《红旗谱》即以朱老忠为报父复仇为驱动力和线索,展现农民走向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或者着意于激烈的情感,或者淡化复仇的情节冲突,转向人生哲理的思考,体现了以诗化笔法对传统复仇叙事的颠覆。《铸剑》以斑斓的笔触描写了奇诡的复仇场景,将复仇故事的重心从二元对峙转向了复仇者内部激烈的情感表达;《伍子胥》则将复仇推至整个故事的背景,编织了伍子胥心灵漫游的历程。吴晓东总结了诗化小说的一些总体倾向,即“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4]这些诗化特征在以上所指认的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果将复仇主题作为诗化小说中的一个子集,那么这一类作品中的诗化必然有自身更为独特的形态。复仇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姿态,《铸剑》中义无反顾的黑衣人形象是对鲁迅生动的速写。考察鲁迅人生中的复仇观念时,跳出对人格精神的讨论,结合鲁迅对新文学文体形式的创新奠基性的影响,是以《铸剑》为文本进行分析的立足之处。
一.英雄情结:诗情溯源的一体两面
从现有作品来看,诗化小说的作者往往具备诗人的气质。臧克家曾言:“鲁迅是具有着诗人的性格和气质的”[5];冯至本身就是诗人,他的存在之思从诗歌蔓延到《伍子胥》之中;汪曾祺对诗和小说的关系有着自觉的思考:“小说之离不开诗,更是昭然若揭的。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6]汪曾祺将小说与诗的关系推展到短篇小说作家本体体验,对诗化的理解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扩展。冯至创作《伍子胥》是受到过一种诗情的诱惑的。在此之前,他读了里尔克的散文诗《骑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因此产生了浪漫的想象。在他描述的渔夫和浣纱女出现的场景里,还伴随着营造氛围的景色,江边、黄昏、夜色和阳光,无不氤氲着诗意与缅怀。[7]虽然再次提笔创作《伍子胥》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这段时间里冯至对伍子胥故事的想象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从读者的阅读接受来看,最被广为称赞的,依旧是冯至最初在浪漫诗情中想象、又在漫长的十六年间反复酝酿的与渔夫、少女相遇的场景。冯至创作《伍子胥》的例子说明,对于诗化小说的作家而言,诗化不仅仅是有意的语言风格、文本组织的追求,更是潜伏于作家的深层心理模式之中的动机,进而催化了在主题选择的某些倾向性。
从创作心理里来追溯,鲁迅的诗化动机部分来自于他的英雄情结;而与英雄情结相反相成的,是强烈的受辱感。鲁迅在敏感的少年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家庭变故,描述自己在质铺里典当的情景时,是“在侮蔑里借了钱”,至于到江南水师学堂去,也“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8]这种逃避,除了不愿面对在那些家族衰败中暴露了真面目的人,其中恐怕也背负着急于摆脱过往经历的自卑情绪。旅日求学时期,这种自卑情绪从家族层面上升到国族层面,“幻灯事件”便是具体的代表。从鲁迅对外界刺激作出的反应也可以推测:“我们不妨猜测,在任何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举止背后都有一种亟需隐藏的自卑感存在”“很难假定一个带有强烈自卑感的个体会是个看起来柔顺、平静、自制并且和善的人。”[9]鲁迅的能言好辩与尖酸刻薄向来为人所知,不能断言鲁迅要借此隐藏、遮蔽自我,但这些论述从侧面印证了他背负着自卑心理的可能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自卑情绪是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并且存在着成为转化动力的可能。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人们会为超越自卑而设立自己的优越目标,以达成对自卑感的补偿。不同的人有各自不同的优越目标,而所有人优越目标的一个共同因子,便是化身为神,表现为“试图无所不知,掌握普遍的智慧,或是长生不老”[10]等等。如果要对鲁迅的优越目标作出描述,或许可以借用闫庆生提出的“英雄情结”来概括。“他的英雄情结的内涵比较丰富:至少包含有自尊、反抗、复仇、有所作为等心理意象。”[11]这种英雄情结一方面会使鲁迅形成自己独有的审美心态,另一方面则会在外界的刺激下寻求诗意情绪突破的出口,于作品中宣泄,这就指向了复仇主题的选择。
二.复仇高歌:孤勇者的双重抉择
不可否认,鲁迅复仇意识首先是理性层面的、针对现实的战斗意志,这也是《铸剑》被作为鲁迅反思国民思想这个解题角度的原因。鲁迅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赞扬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以其反抗之音作为感动后世的绵延的精神力量。[12]鲁迅要以复仇为利剑,刺破浑噩而庸倦的国民性,他将文学看作具有激发人之斗争性的工具,慨叹屈原提供的文学遗产中,唯有“反抗挑战”没有得到继承[13]。改良“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的国民性就是鲁迅提倡复仇精神显而易见的出发点,即许寿裳所谓“战斗的现实主义”[14]。
但是,正如钱理群所言,《铸剑》是和《野草》同时期的作品,二者存在着思想和艺术追求上的相通性[15]。因此,复仇除了是鲁迅有意识的人生抉择和处世姿态,还在潜意识层面与鲁迅的内倾性、英雄主义情结相适应。在复仇者的悲歌,批判围观者的冷漠之外,鲁迅借复仇的框架来传达一种化身为神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结在鲁迅长期的个人经历中形成,且与鲁迅创作《铸剑》时的心理状态有关。《铸剑》大致被确定为创作于1926年底至1927年,在此之前,鲁迅目睹了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等事件;辗转至厦门任教,对院校负责人的行为感到不满。鲁迅在这一时期郁积了强烈的悲切和孤立感,他总是在“无情”地解剖,并且害怕别人看到他完全的真面目。如果完全暴露出内心的怀疑与冷漠,也许再也无人敢于他同道为友;此时还愿意站在他身边的“真正的朋友”,是遥不可及的。[16]但即便身处孤悬之境,鲁迅依旧坚守直面真实与惨淡的姿态,成为“正人君子也者之流”的世界的“缺陷”,直至自己归于衰亡。鲁迅“于天上看见深渊”[17],具有清醒的现实搏斗精神,而在这位面对无物之阵的勇士的内心,必然燃烧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浪漫英雄情结。“创造精神是美的,战斗精神是力的,这二者互相关联;美者必有力,力者必有美。”[18]在孤寂的环境中鲁迅向壁对影,化身为神的潜意识转化为血色飞溅的力量之诗美,这是《铸剑》诗化创作的出发点。
对于《铸剑》的改编,鲁迅称“只给铺排,没有改动”[19]。改动必然是有的,但是鲁迅如何留下“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创作印象的呢?世上没有偶然的记忆,鲁迅的这一段创作印象暗示了他对于《铸剑》的潜在审美预期。“‘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20]鲁迅的故乡有着绵延的报仇传说,这种地域文化因素影响他的行事风格,同时也包裹浸润着他的审美体验。可以推测,鲁迅在最初接触干将莫邪的原文本时,便将其纳入了自己诗意化的接受视野。因而在创作中“没有改动”的也许不是意指故事情节,而是氤氲的一种审美情绪。这种情绪在鲁迅最初读到故事时被调动,并且长久留存在他的心灵体验当中;对他而言,《铸剑》是重拾这种审美情绪进行渲染,而不像《补天》那样有意识地针对当时的社会事件加以讽刺。《铸剑》是鲁迅在外部环境恶劣,独向内心探寻的创作,创作的激发部分来自于由自卑情绪、曾经的审美体验等形成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绪化的创作动机在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个人性和诗化倾向,由此进一步诱发鲁迅的诗化情绪对于“复仇”主题的选择。
复仇故事的艺术色彩契合了演绎悲壮英雄的强力审美的需要。与这种强力的诗意审美效果相缠绕的,还有對人之野性的崇拜。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此极度推崇,这虽然是拯救国民性的一个方面,但也不乏审美的因素:“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21]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不乏拯救族群危难、展现深明大义的英雄,而鲁迅却偏偏选择了复仇故事中的角色。相对而言,复仇的主人公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神话本身所带有的英雄色彩和所包含的古代人民无意识中的英雄情结,无形中有力地激活和鼓荡着作家无意识中的英雄情结。”[22]虽然在传统故事中,复仇的角色的合理往往体现了伦理的诉求,但是鲁迅更看重的是他们在复仇过程中主体精神的张扬。《铸剑》中从眉间尺到黑衣人,就是复仇情绪由压抑走向高扬的状态。小说对眉间尺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他复仇意志的摇摆上,在小说开篇,眉间尺便为是否杀死水缸里的老鼠而犹豫不决;在踏上复仇之路时,他的母亲不无忧虑地发出了“失望的轻轻的长叹”,也暗示了眉间尺的命运。行至街上遇到仇人时,他时时担心剑会伤到他人,又被一个无赖的少年缠住不得脱身,这种种纠缠不清的环境和心绪产生了极大的压抑效果。眉间尺将头颅割下交给黑衣人、复仇使命转移之后,鲁迅便撕开了之前极度压抑的状态,以绚丽张扬的笔触描写黑衣人复仇的画面。无论是色调的选择还是诡谲的三头厮杀的场面,都以强力的诗情渲染了悲壮审美效果。
鲁迅以诗意的笔调诉诸传统复仇主题的改写,与之相似的还有冯至的《伍子胥》和汪曾祺的《复仇》。尽管前者强力、郁结的风格基调与后二者不同,但是它们建立在复仇叙事框架上的对存在的思考却是相似的。复仇故事作为人生成长历程的象征,提供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存在,并设定复仇这个明确的目标。王立认为“西方文学侧重表现复仇主体意志磨炼过程”,而“中国的复仇英雄们被突显于伦理实现动机的果决”[23],现当代文学中复仇主题文学恰恰是在“果决”方面进行了改写。眉间尺的犹疑是鲁迅对复仇行动的反思,因而这种诗意动因,其实也蕴含着存在主义哲学之思,是当时中国处于大的社会变动下包蕴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参考文献
[1]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从〈孤独者〉到〈铸剑〉》,《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第33-34页.
[2]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第125页.
[3]黄曼君:《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 中国当代部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4页.
[4]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第119页.
[5]臧克家:《杂花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年,第1页.
[6]季红真:《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7]冯至:《伍子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第104页.
[8]鲁迅:《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页.
[9]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杨颖译:《自卑与超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0]同[9],第57页.
[11]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4-385页.
[12]同[8],第197页.
[13]同[8],第200页.
[1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81页.
[1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16]同[8],第362页.
[17]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1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82页.
[19]鲁迅著,徐文斗,徐苗青选注:《鲁迅选集·书信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452页.
[20]同上,第450页.
[21]同[8],第195页.
[22]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4页.
[23]王立:《中西复仇文学主题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