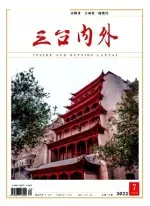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寓禁于征”政策研究
李游
摘 要:清末民国时期,云南鸦片泛滥,屡禁不止。为阻止鸦片进口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出于增加财税、筹集军饷的考虑,云南开始实行寓禁于征政策,通过征收土药厘金等方式,以期逐渐在云南实现禁绝鸦片。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得云南鸦片种吸及贸易合法化,甚至出现愈禁愈烈的情况。本文即以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寓禁于征”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南鸦片种植情况、“寓禁于征”政策的提出及不同时期这一政策的发展演变分析,以探讨这一时期云南禁烟难行的社会背景及原因。
关键词:云南;鸦片种植;寓禁于征
一、云南之鸦片种植
关于鸦片在云南种植的历史,其记载最早为康熙时期之《使滇杂记》,其文曰:阿芙蓉、阿魏,《腾越志》谓不产本地,而滇中者为佳。当时之鸦片仅作为药物或花卉,且种植面积十分有限。其后随着印度烟土的大量传入及鸦片吸食的普及,云南鸦片种植面积大增。对此,礼部左侍郎郭嵩焘曾明确表示,鸦片吸食之风“浸寻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云贵总督阮元以“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一事上奏朝廷,认为由于“费工少而获利多”,使得民间私种罂粟“积习已久”,承认了云南民众偷种罂粟的事实。这一时期,云南鸦片种植逐渐由沿边遍及内地,出现“罂粟遍地”的情况。
随着鸦片种植面积的增加,云南鸦片产量及外销数量亦呈现出剧增趋势,甚至成为云南商业出口的主要构成。《云南地志》记载在云南商业出口中,“土药为大宗”。单以姚安地区为例,光绪年间之出口,“年多至四百余驼,民间视为农产收益,商贩视为牟利渊薮”。而以通省论之,至光绪末,云南“销售外省之土,约在一千万上下,而坐地销售者,亦在三四百万,至迤西以及各府厅州府县边地所产之土,未经运销本省,向来就近分售邻封省份,数目无可稽核”。这一时期,单由开远、广南运往粤、桂两省销售之烟,每年即能达三千万两。
光绪末年,清朝政府与英国当局订立协定,约定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中国政府在十年内逐渐完全禁烟,英国当局承诺逐渐减少印度殖民地对华鸦片出口量,最终于1917年在中国完全根绝鸦片。此后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开展,云南地方政府亦积极响应,云贵总督锡良甚至将期限缩短至一年,下令于光绪三十四年年底在云南实现全面禁烟。在一系列严厉措施下,云南鸦片种植面积大为减少,除个别沿边地区尚有偷种现象外,绝大部分内地区域之鸦片种吸都得到有效制止。民国初年,禁烟政策在云南继续推行,并相继制定了《各属禁烟事务所章程》《铲烟规则》《巡警稽查专则》《各属查获烟土办法简章》等,对于违反禁烟规定者给以严厉制裁,“故一时官绅人民,莫不动色相戒,而烟苗乃得肃清焉”。
二、“寓禁于征”政策的提出
对鸦片征收捐税之议始于咸丰七年(1857),其时海禁大弛,各省渐种有鸦片,且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而朝廷军饷无所从出,闽督王懿德遂奏请抽捐济急。咸丰九年(1859),朝廷下旨“将所产土药分别收税抽厘,迅速办理”。此后,朝廷为筹饷又曾多次征收土药厘金。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署云贵总督崧蕃“遵旨筹饷,加收茶、糖、土药捐输”。二十三年(1897)十月,其以“滇省土药出产,难计其数”为辞,奏请“酌量加收厘金专款,存储听拨”。可见这一时期对鸦片抽捐更多的是用于“暂给军饷”。光绪三十二年(1906),热河都统廷杰以土药、洋酒、水旱纸烟等类嗜好品,“或无关食用,或有害卫生”,提出应当“酌量加收,寓禁于征,即以征为禁”,从后对土药征收厘金逐渐被视作“正供”,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鸦片产销在云南合法化,“良田美地尽作烟产,每值开花取浆之时,地方官巡历各乡,收纳税钱,肆无顾忌”。
云南土药厘金征收,初由云贵总督劳崇光酌定厘金章程,每一百两抽银一两。同治七年(1868),因兵饷支绌,迆东道蔡锦清奏禀将土药改照洋药收税,免其抽收厘金。但试办六个多月后,由于“商贾俱怀观望,厘税日见短收,军饷更形掣肘”,遂又止税收厘。其后为增加收入,云南地方政府曾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将土药厘金由原来的每百抽一降至每千抽六。据云贵总督崧蕃奏报,自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二年(1896),云南各地税局抽收之土药厘金数额逐年增加,二十年时为22,688两4钱,二十一年达到25,332两4钱,至二十二年由于“土药丰收”,更是达到34,000余两,“比历年收数为最多”。此后这一征收标准不断提高,如总督崧蕃即曾“请于正厘外加征作抵,照部议每土药一担,计重一千六百两,先后议定征额,每担寔共收银十九两二钱。其运赴远省者,仍照正厘征收”。另据《清续文献通考》记载,“云南土药原征税厘每百斤计银三十三两六钱”,度支部于宣统三年(1911)奏定将之比照洋药,酌量加税每百斤征银二百三十两,则土药厘金又由每千抽三十三两六钱增长至每千抽二百三十两。
在禁吸方面,清政府出于“稽查吸户,寓禁于征” 的考虑,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实行吸烟牌照捐章程,通行各省。但云南并未行此捐税,据宣统元年(1909)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称,推广牌照捐一事,前督臣锡良“以滇省禁烟,无论栽种贩吸,均先后奏明缩限于上年年底一律净尽。毒苗既绝,出产毫无,趸售之商、零贩之店靡不依限歇业,实无买卖烟膏烟土之人,牌照捐无凭开办”。沈秉堃亦持此论,认为作为产烟最盛之地,滇黔禁烟莫善于禁种,“种绝则贩与吸随之而绝,故牌照捐之推广于两省殊不相宜”,且其担心征收牌照捐会导致私贩私吸者更加明目张胆,使鸦片之风死灰复燃,故其毅然拒绝牌照捐之议。但云南之禁烟情况却并非如其所奏,经度支部派员核查,云南虽经奏报一律清除,“其实并未净尽”。另据《各省禁烟调查表》统计,宣统二年(1910),云南鸦片产额仍有7,351担,土烟消费额共计9,744担。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寓禁于征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改良,主要体现于禁种、禁运与禁吸三个方面。在禁种方面,国民政府对云南种植鸦片田亩在丁粮之外又加征地亩罚金。此项罚金又名烟亩罚金或禁烟罚金,自1920年开始办理,至1926年共办理六届,每亩征旧滇币二元,这一时期之禁烟罚金被称为“舊案亩罚”。由于“历时稍久,群以为病”,自“民国”十五年下半年起取消地亩罚金,改为印花罚金。凡贩运烟土者,均按数量由各商贩购贴印花。但此举施行以后,不但收数锐减,且流弊甚多,1928年四月一日遂又废止印花,仍改行地亩罚金,并以十七年秋季起为新案第一届,至1937年结束,共计九届,史称“新案亩罚”。“新案亩罚”时期之各属亩数,“以前六届中各县自行呈报之数为标准”。其罚金收取,据1928年所颁布之《云南禁烟暂行章程》规定:凡种烟一亩者,科收罚金本省通用纸币5元,半亩者(即5分)照数折算,以后逐渐酌加。但在实际收取上,往往高于此标准。据1935年出版之《云南省农村调查》记载,云南禁烟局“限定各县最高种烟亩数,每亩须纳滇币十五元,若超出所指定的亩数,须预先呈报,照章纳税,不然被区公所查出后,罚十分之三,经县长查出,罚十分之五,经禁烟局查出倍之。所以云南百零七县十五设治局,每县平均八千亩,每年的地亩捐,约在旧滇币一千四百万元以上(罚款在外)”。
在禁运方面,1920年——1927年间,云南省内运输或邻封入境之烟按每百两新币六元征收罚金。“民国”十六年改征印花,“每货一两,贴印花一角,一两以上,照数递推,不及一两者,免贴”,如需贩运出境,还需缴纳出境罚金。邻邦邻省之烟运入云南,亦需购买每百两十元之印花粘贴货上方准入境。1929年废止印花后,虽规定年内所产新烟在一年期内准其在本省境内自由运销,不另行收费,但必须年产年销,一旦留至次年四月后即视为老烟,需粘有每百两十元之印花,否则即查获处罚。而运出本省境外之烟,则需集中省城,向禁烟局领取出口证,方准起运,每百两科收罚金二十元,如系老烟,则另加征每百两二十元之罚金。其距省较远之边地各属,可就近在边局领取出口证。但在实际征收中往往高于此数,据《云南省农村调查》记载,运至昆明之鸦片,报关时“每百两生鸦片烟,须纳特税旧滇币百元,报关五元,公路捐二十五元,据说每年仅特税一项,约旧滇币两千万元以上,报关公路捐约六百万元以上”。
在禁吸方面,国民政府曾试图由调查吸户发照入手,令吸者按期缴纳罚金,以期借此逐渐减少烟量,并最终实现戒烟。但此举并未取到预期效果,由于鸦片吸食因循日久,地方政府虽屡经催促,但“查报者寥寥无几。或以困难搁置,或以少数搪塞。文电往返,委员查催,迁延年余,仅有少数罚金,略敷开支,其于立法本旨竟未收效,故自十八年以后,即行取消”。此后,国民政府又推行了救济公膏办法,对四十岁以下吸户,限期服药戒断,四十岁以上者,则责令购吸救济公膏,分次递减药量服用。如姚安于1937年奉令罚给救济公膏,每两二元,月发公膏千两。至1939年,公膏减发至十六兩,两价增为五元。顺宁县于“民国”二十八年起颁发吸户公膏执照,每天收费新币四角。吸户凭照领膏,每六个月为一期,期满换发执照,不增数量。至1940年,公膏只发半数,每两价增为国币二十元。三十年,又增至国币三十元。
三、实行“寓禁于征”政策的原因
1.争夺利权、防止渗透
清朝末年,鸦片泛滥于中国,清朝政府虽行禁烟,却始终未能取得良效,甚至“愈禁愈滥”。以英国输入鸦片数量而言,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2,576箱,至道光十五至十八年(1835-1838),更是达到每年35,445箱。即使在虎门销烟的道光十九年(1839),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仍达40,200箱。中英贸易的不对等,使得大量白银流入海外。道光十一年(1831),监察御史冯赞勋便曾以烟土“私相售卖,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上奏朝廷,认为此系“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
鉴于财政日绌、私种难禁,清政府遂从消除“漏巵”出发,认为如果能够设法稽征,“既可裨益饷需,且亦收回利权之一助;并可以征为禁,隐寓崇本抑末之意”。当时朝廷上下持此论者不在少数,如郑观应认为广种罂粟可以“使漏巵不致外溢,西贾不能居奇”,并称“洋药之所以不能禁者,半以英人阻挠耳,今自种罂粟以杜来源,英人岂能责问……自云土、川土、西土、关东土及鄂皖江浙之土盛行,籍分洋药之利,而清江汉口以上更赖土浆御诸门外,否则洋药毒如水银,无孔不入,内地元气剥削尽矣。所憾者未得印度秘制之法耳,将来大弛禁令,广种而精制之,不出十年,利权可以尽复”。
此外,有从防止英缅渗透破坏角度而主张弛禁鸦片者,如云南腾冲人李学诗即曾指出:“自云南禁烟令下,英人为投机之谋,凡与滇接近之处,概准种烟,有愿移居其地,每户借洋三千元为筑屋制器之资,不取息,三年后分期偿还。愿居山地者,使之种烟;居平地者,使之垦荒种稻。种烟,即年纳税;种稻者,食荒三年后纳粮。有能邀集至百家者,使为头目。故自禁烟令1908年至1913年间,其至威远(今景谷)、澜沧等处移住孟艮者已达万家。其他沿边一带所迁移者又不知凡几许也。”对于这一情况,《续云南通志长编》亦有所记载,其称在云南禁烟之际,邻邦属地乘机“广种而吸我之金钱;复使边民因羡利之故,而移居缅界,甚至潜运界桩,失地失民”,因此认为实行弛禁鸦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抵制英缅政府破坏的作用。
2.增加财税、筹集饷糈
相较于一般经济作物,鸦片种植成本低而获利高,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时,即有大臣奏称:“云南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由于云南气候条件适宜鸦片种植,且所产烟土质量较高,易于销售,使得云土声誉及价格日渐高涨。也正是由于鸦片获利较高,政府遂将之视为增加地方财税收入及筹集军饷的重要来源。御史陆应谷即认为由于鸦片栽种获利较多,使得钱粮能够及早完纳,而“地方官利其催征之易,只知自顾考成,并不计民间利弊,所以听民栽种而不为之禁也”。宣统元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在筹备禁烟时,曾指出鸦片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称“少此大宗烟土以入计,出不敷甚钜”,并认为牌照捐等寓禁于征办法,实则“观望迁延,冀捐税之不无小补也”。
“民国”时期,因饷糈问题,各省对鸦片多行弛禁政策,云南亦出于筹饷考虑而实行寓禁于征。据《云南省志》记载,“民国”九年因驻川滇军撤回,唐继尧为弥补每年60万元之军费,遂决定开放烟禁,实行寓禁于征政策。除用于筹饷外,地方政府亦可从禁烟罚金中抽取一定比例用于地方性支出。如罚金内有坐扣办团补协一项,“各属赖以整理团务,清剿盗匪”。1928年所颁布之《云南禁烟暂行章程》对于这一扣除比例及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凡由地方官结认收解者,所收罚金准提4%为办团补助费,3%为团保办公费,2%为地方官办公费,1%为禁烟公所办公费。共准坐扣10%,实解90%”。因此,出于办理地方团保等事宜考虑,地方政府亦不愿厉行禁烟。
四、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政策虽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但却无形中使得云南鸦片种吸及贸易合法化,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禁烟的难度。《云南省农村调查》曾指出云南禁烟难行,主要因为“云南烟一旦禁绝,财政收入则必大减少,况且除特税、附加税、地亩捐等收入都出于鸦片外,尚有价值一二千万元的特货输出,可以从外省换来大批的洋纱布匹等,这都是云南当局看得到的”。而鸦片厚利所带来的诱惑,也使得不少地方官员卷入其中,他们或“每指土产为外货,内销为外售”以此榨取高额罚金,或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中,甚至充当起保护者的身份,如云南省商务总会曾与云南省筹饷总局签订协议,由地方武装部队负责将滇西鸦片押送至昆明附近,并“按百收银六十元”的标准收取保护费。以上种种使得寓禁于征政策在云南不仅未能起到逐渐根绝鸦片的作用,反而限于“愈禁愈滥”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
[1]徐 炯.使滇杂记.物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清官修.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一[M].道光十一年六月丙午
[3]清官修.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三[M].道光十二年六月甲申
[4]清官修.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九[M].道光十九年二月丁卯朔
[5]云南省富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宁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6]卢金锡修,杨履谦、包鸣泉纂.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三[M].“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7]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8]《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六[M],1983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