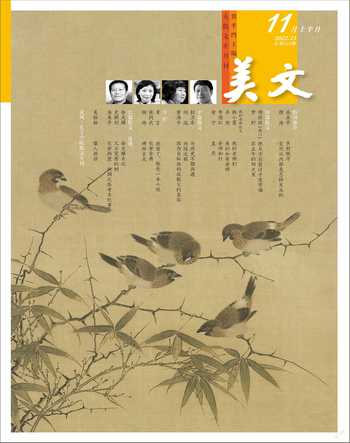徐光耀日记

徐光耀
1953年10月4日 我见了毛主席
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也是个难忘的日子。
以前也见过毛主席,1950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前和群众的队伍游行通过,见过他;1951年,“七一”党员干部大会上,在先农坛上遥遥地见过他;1952年,国庆节,依然是在天安门上遥遥地见过他;今年,10月1日,去天安门观礼时,已经是较近较真切地见过他。然而,以往之见都不能算,只有今天才算是真的见过。今天不仅看见了身形,还看见了面貌;不只面貌,还看清了眉目,看见了他的举止、手势,还有笑容和激动的表情。
下午3点,文联大会突(然)休会,秘书让大家去怀仁堂后院空场上去照相。人们早知是主席要来了,排着队,怀着一颗紧张的激动的心,进了后院。我甚至不敢朝那一排凳子看。我见丁玲同志就坐在那里,中间正腾出一排座位来。我总觉得有的同志在看着我笑道:“你们看徐光耀多紧张、多怯啊!”
我挤进了后面凳子上的第三排,我又急着往中间挤。我是多么想挤得靠前一点呀!
排好队了,旁听的人们也站好了。怀仁堂的门打开了,只看见郭老先出来一个人影,人们便鼓起掌来,一直鼓啊鼓啊!啊,毛主席出现了!胖胖的、黑红红的脸,宽额,长方颊,迈着稳健的缓缓的步伐,走近前来。一过那葡萄架,他就一面鼓掌,一面举手,向大家还礼。然后,停在草场中央,突转脸朝西,问了西边站着的人。周扬大约告诉他是旁听的,他便点头朝我们走过来。他向大家望着,微微笑着,一面举着手,这面那面地致意、还礼。他后面是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周总理,还有习仲勋、陈伯达、胡乔木等同志,还有不少中央同志。可惜我不认识,也不及细看了。
毛主席坐在中央位子上,仍和大家点头、示意,并返回头向艾青、天翼、刘白羽问了一两句什么,我还听见他叫了丁玲同志两声,让到他身边去。丁玲同志只是点点头,向那边稍稍靠了靠(我见她流泪了)。这时,毛主席离我只有1丈远,隔有10来个人。
大家的掌声这么响,什么都听不见。我自己也鼓得累了。
开始照相了,照了两版。我尽力使我自己照得好——太阳光很好,原是应该照好的。
照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立起来。大家又鼓掌相送,毛主席又返回身来,鼓掌还礼,并向我们这一带注视。我甚至感到我和他的眼光相碰了。
毛主席走过葡萄架,人们拥过去,突然又是一阵掌声,我也拥过去,见毛主席正站在堂门口向大家鼓掌,举手告别。他是满脸的激动,他的感情,也和我们的感情交流而汹涌呢!
终于,毛主席进去了,不见了。
难道这不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吗?重新听报告的时候,我半天都没有摆脱兴奋,半天才听入了耳。
上午,文协大会听了邵荃麟的总结报告,又施行了选举。
下午,文联大会听了廖梦元(鲁言)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又见了毛主席。
晚上,我去“大众剧院”之前,给芸打电话,告诉她,我今天看见了毛主席,她也为我兴奋。
在“大众”看了三出戏:《闹天宫》《奇双会写状》《将相和》。三出戏我都高兴,我都喜欢。我真是幸运至极,美坏了!
11点回到家来,给我亲爱的读者章铁英写了封信,并把一本《平原烈火》送他。昨晚在芸处,我已根据她的意见,把《平原烈火》中的几处错误校改过了。但我又发现了不少其他错误,拟最近再全部校阅一次。
1953年10月5日
上午,怀仁堂开文代大会,第一个是丁玲同志发言。今日,人们用同样热烈的情绪欢迎她讲话。她今日讲的和在文协大会上讲的大体相同,基本精神也相同,只是更发挥了。她从对生活的态度,又讲到人物创造,讲到感情,而最后,又回到生活问题上来。很明白,她这次讲话又是文代大会上有数的好报告之一。
她讲完之后,古巴代表发言。再之后,曹禺、吕骥、蔡楚生、郑振铎、戴爱莲、王尊三等发言。会议在下午1点半才结束。下午,竟宣布了休会。
下午的时间,我利用了一点空隙,又重新看了刘建藩给我的文章《评〈平原烈火〉》。打算最近即给以回复,以便了却心头的一件事。我愈来愈感到需要加倍努力,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了。
晚上,芸说我去看戏。可我并未觉得曾去看什么戏,仿佛是很忙了一阵才回来。
1953年11月9日
十多天来,我总想给丁玲同志写封信,可是却不知写些什么好,有什么要说,有什么问题可解决呢?仿佛都没有。然而总是想写。
1953年11月18日
丁玲同志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仍给我以鼓舞和启发。
我总想给她去封信,报告一下我近来的情况,却总是感到无话可说。这已渐成我的负担了。
1953年12月17日
早飯后,再读了丁玲同志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便开始给《文艺报》的编辑部写回信,回答他们关于我对文代大会的体会和所考虑的一些问题的询问。
1954年2月4日
天大黑后,与芸去马凯食堂吃饭。一进门,正遇见丁玲、田间、艾青、厂民夫妇等人在那里等吃饭。丁玲同志叫我上她那儿玩儿去,问我在乡下工作得很好吗,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她告诉我,要多跑跑,多在上层转一转,不要只是扎在一个地方。但目前还要深下去,深入半年之后,再往上层领导、别处去看看。不要只是死扎在一个地方。
匆匆间,只好各人分桌而坐。我与芸单挑了一桌,丁玲等同志另坐满一桌。
1954年3月23日
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延安集》。丁玲同志在这中间只提供了一些史料,这确乎不是文艺。我想,这对她,也确乎是一个学习。她又是那么善于学习的人。
1954年4月28日
下午,给芸写信之前,给丁玲同志写了一封郑重的信。我主要是请求她的帮助,希望她对我写《区委书记》一稿以指导和启发。我说我愿意完成这个任务,却缺乏办法,挑选不着题材,这使我信心不足,而散文能力差,也妨碍着我。
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很久以来(自下乡)没有给她写信和没有去找她。
1954年6月6日
我不明白丁玲的话,写散文怎样可以锻炼人的思考呢?怎样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有条理呢?
1954年6月12日
之后,看了丁玲同志的《到群众中去落户》几篇文章,看了看《文艺报》的来信,打算寄篇体验生活的稿子去。
1954年12月31日
丁玲还没有出马。她干什么呢?难道创作吗?在去莫斯科前,也应有些文章才是。或者由于前段《文艺报》是她主编,也在检讨吗?
1955年2月6日 丁玲一席话
进了屋,一坐下,丁玲同志便说:“一定要写人,要搞出两个人物来,硬是要先搞出人物来,拼命地搞人。你应该有写《平原烈火》时的那股冲动,要下决心,狠命地搞,要搞结结实实的作品。”她接着谈到《红楼梦》和其他的作品,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只令人记得它几个人,小说没有人是不行的。”
狠命地写人,这是她对我宣传的第一点。
她问我有计划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她又告诉我:“写作品要写生活,写问题。不要写人家已写过的、已说过的,人人都那么说、那么写的,就避开。一定要看得出生活,叫人家知道和懂得些生活,看见生活的样子。不要有顾虑,问题多得很,就写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解决不解决是在乎人物的处理,你对人物是怎样看法的。至于怎样解决正确,那不是你写小说的事,那是农村工作部的事。我们是给读者人的形象,不是传播先进经验。有人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叫我谈谈土改的经验,我只是笑一笑。”
她又谈到《静静的顿河》,说:“那里有很多问题,他怎样去解决的呢?他就是让人物自己去搞、去活动,他就是表现生活,让人看见那个时代的生活面貌……”
写生活、写真实、写问题,是丁玲同志跟我宣传的第二点。
关于这第二点,她还说道:“农村中问题是很多的,特别老区,要写它,不能割断历史。有些人,过去打游击,很有办法,可是他不能领导生产;又有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或者在历史上是反革命的,可是在如今领导生产上,他又是很有办法,很有能力和成绩的,而我们的支部又得和这种人合作;有些过去很好的共产党员,现在做起小买卖来了。这都是问题,有的就很阻碍农村工作前进的,这都是我们应该解决、应该去表现的很有意义的题材,并不一定都去写中农的入社退社。”
丁玲同志给我谈的第三点,“是要有激动人的情绪。一部作品读了总要使人激动,要有感情。只是生活,不能叫人激动,也不成的。一部扎扎实实的作品,是必须激起人的感情来不可的。”——然而,我现在竟就是害怕这一点呢!
丁玲同志让我学习陈登科。“他无所顾忌,说干就干,干得很快。不怕说错,不怕做错,这精神是很好的。写作品,就要有个冲劲、有个干劲。《保卫延安》还不是咬住牙磕了好多年磕出来的?”
关于创作,她就是谈了这些。虽是老话,却是富有新的意义。
我到饶阳、邢台一带去转转的计划,她似乎是同意的。
她曾表示,我下乡不应在家乡一带搞,那是有困难的。
后来,谈到了陈企霞。对我去看他,没有批评,反而是赞许的。她说:“陈企霞对我们这些人很好。这次他犯错误,缺乏精神上的准备。他又太爱激动了,一激动,错就犯得更大,有好处也没有说头了。陈的留党察看,怕是会批准的。”她以感叹的口吻说:“几乎开除党籍。”
她让我多去找陈企霞玩玩,劝他写点文章。写了,发表了,精神上就会愉快些,而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会是:“他还在活动着,并没有消沉下去,并没有被打倒。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他被打倒了。同时,他不转变一下情绪,带着这样一个鉴定及情绪下去,不论在哪里,工作都不会搞好的。”
丁玲同志对陈企霞是极为体贴的。
她说:“陈企霞一打下去,便撑不住。过去自尊心又太强了,跟同志关系处不好,到现在朋友也没有一个。苦闷自苦闷,没有人去看他,他也无处可玩。”
丁玲同志对陈企霞也是极为了解的。
告辞出来时,丁玲同志在门口向我喊道:“等着看你那本好书啊!”
1955年2月20日
据他说,丁玲同志曾表示把我弄到作家协会去。好像别人也说过。但他向丁玲同志表示反对把我往那儿调。
1955年2月23日
丁玲的《春日纪事》写得多抒情、多美。只要能表达出你的感情来,什么方法和形式都可采用的。
1955年3月19日
黃昏,读了丁玲同志的《生活、思想和人物》,谈到对生活采取主动和主人翁的态度,多帮助人,从社会斗争中提高、丰富自己。这启发了我,使我要努力打开自己这孤僻的小圈子,更勇敢热情地去接近一些人,去多给自己交些朋友。
1955年7月20日—25日
散场时见到丁玲,但我回避了,未跟她说话。不知是什么情绪,大约有一点儿自惭吧!
1955年12月27日—30日
丁玲、陈企霞成了反党小集团。我头脑中的两个偶像,一下子全部毁灭了。当时,我简直昏了头。
这真是不能立即就使人相信的事。
在文艺界,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谁呢?就是他们两个人。
然而,在情感上总不是一下子就能扭转过来,总是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丁玲难道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吗?
1956年1月3日
下午,把所有的信都查过。结果查出陈企霞的7封信,丁玲的2封信,丁玲和田间合写的1封(实际是田间写的)。此外,没有了。原来胡可的信,我也竟有5封之多呢!这真有意思。
可回来翻读1949—1951年的日记时,我几次发现过去竟是这样强烈地反对舞蹈来的。大约印象的转变,还是从李纳处听了王海的看法。
丁玲、陈企霞给我的影响、教育,凭良心说,大部分是具有党性的、好的。当然,里面也确有培养个人主义、骄傲的东西。但失去了这样的人——尤其是丁玲,将多么可惜呀!老实说,在现有中国的老作家中,有谁能像丁玲这样热心于青年作家的培养呢?丁玲之受青年们的欢迎,不是无因的,不是凭虚伪能换得来的。
1956年1月4日
读过去的日记,单找陈、丁给我的谈话及影响,而今看来,他们的很多话还是有价值的。如按了他们的话去做,仍不失为一个好的党员的。难道这些好的一概不谈,只拣那些坏的去说吗?
1956年7月14日
但不知丁玲同志怎样了,好久好久不见她的文章、不知她的消息了。但愿她一切都没有问题才好。她如能一切恢复,该是使我多愉快呀!
1956年12月8日
下午夏信荣来,除带来薪金,还带来作协党组给我的一封信。提出六个问题向我查丁玲错误的事实真相,并附来丁玲的自我检讨一份、辩证材料一份、补充辩证材料一份。我于是立即看这三份材料,看了一个下午。丁玲的辩证很激动,我必须好好写一写,且必须把听课记录、日记都查一查。只可惜丁玲给我的信件不在了。
1956年12月9日
上午,翻了一下日記,晚上又翻了一回,查丁玲给我谈了些什么话、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影响等。
1956年12月10日
为写丁玲材料,查了一天日记和笔记,把有关丁玲的全部标出。一面拟起提纲,到晚上,便动笔写了一点儿。
1956年12月12日
晚上,写丁玲材料的《我的想法与意见》部分,完。总共5页,约3000余字。我明日或者最好给胡、杜二人谈谈,请他们给裁定一下吧!
1979年1月16日
今日很忙碌:上午,先去看了张凤珠。原想通过她找李涌的,结果临时商定先去看李纳。
在李纳处坐了小半天,中午饭后刚要告辞,丁宁给她打电话,邀她一起坐车去看丁玲,于是我们也加入。下午3点半,丁宁、李纳、张凤珠、我4人,一车到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在二楼的211号找到了丁玲。
丁玲老多了,大花白头发。当认出我后,双手握手,一握再握,还说“是我连累你们了”。但见面很高兴。
丁玲很健谈。谈到现在的文学,说:“你(指我)们这一代是主花,一定要多写,好好写。”谈到她在北大荒及长治的遭遇。她真正有生活是在1957年之后,有很多东西要写,只可惜精力差了。也谈到她的残酷经历,几乎叫煤气熏死。谈着谈着,她突然说:“看到了你徐光耀当年写的调查材料,我哭了……”
后来,丁、李走了,她留我们再玩一会儿。一会儿,人文社王立耘等二人来了。5点半我再告辞,她约我明天再去看她,她要我谈谈长篇小说(正在写的)。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