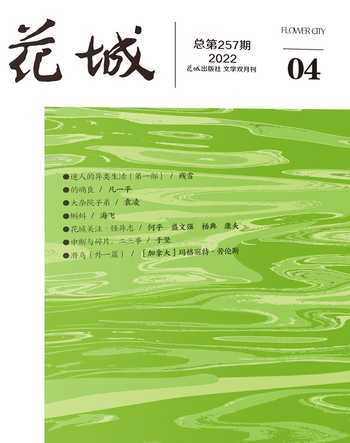东海绮谈集(二题)
盛文强

盛将军事略
公敏毅忠恪,尤善治兵,终以积劳,卒于任所。
——严澍《盛将军神道碑》
爱新觉罗氏当国之际,东海海盗蜂拥而起。水师出兵征剿了几回,却是败多胜少,折损了兵卒战船,到后来龟缩在旱岸上不敢出海。那时节,海盗啸聚岛屿,行踪不定,随时登陆大肆劫掠,抢夺钱财粮食,还要掳走男丁和女子,胁迫男丁为盗,强娶女子为妻。
海坛岛常有海盗过路,岛上百姓苦不堪言。到了嘉庆年间,终于有一位盛将军奉命弹压海盗,带兵进驻海坛岛。盛将军抵达海坛岛那天,海面上摆满战船,盛将军在船头的太师椅上端坐,手按剑柄,四顾睥睨。他身后站了两个兵卒,左手边的捧着茶壶,右手边的捧着水烟袋,随时伺候。将军就在从容悠闲中冲向了码头,船速飞快,而盛将军的举止迟缓,快与慢之间的巨大落差,更显得胸中有甲兵。大船停靠在海岛,盛将军在众人簇拥下登岛,留下部分兵丁看守船只,大队人马在码头列队,向岛上进发。
岛民在旁观看,还抬手指指戳戳,盛将军和他手下的兵卒,都觉得身上不自在。民宅的院墙上探出头来,手搭凉棚向海边瞭望。在海滩上拾贝的渔妇也直起身,望着密集的兵船。阳光经海水反射,照得人睁不开眼,盛将军和他的兵卒都成了影子,在海边移动。到了近前,一个个从黑漆漆的剪影中走出,摇身一变,胀大为圆滚滚的人形。
岛民以手加额,互道万幸,原来朝廷还没有忘记这弹丸之地,终于派兵来保护百姓了。在战船之上倚着一排生铁铸就的烟囱,烟囱的开口斜指天空。有人说那是火炮,用火点燃了烟囱屁股上的油纸捻儿,烟囱口就能放出霹雷电火,还伴有巨响和强光,足以令人双耳不聪、双目不明。无坚不摧的霹雷,连高山也能瞬间铲平,要是对准了人,千军万马也会化为灰烬。这东西也不太准,有时会炸裂开来,伤到自己人。可又听说海盗手里也有不少铁烟囱,到了开战时,火光闪烁,朝着水师的战船喷吐火舌,多年来水师战舰损兵折将,就是输在了火炮上。盛将军这次带来了十门红毛国的大炮,堪称当世威力最大的火炮。为了增加大炮的威力,炮筒上还贴了龙蛇蜿蜒的朱砂灵符。
有了火炮助威,盛将军有些飘飘然。他对左右说:“在东海,红毛的大炮不会超过十门。”他本想说只有自己这十门红衣大炮,而左右随从却没反应过来,掰着手指还在计算。自从盛将军在岛上屯兵,海盗许久不敢来犯,只派出哨船,装扮成渔船,远远地窥探过几次,见盛将军的兵营里人来人往,海盗的哨探赶紧掉转船头回去了。岛民对盛将军刮目相看:“早就该派一位将军前来坐镇了,不过,现在来也不晚,正是时候。”
盛将军原本是行伍出身,早年是伙头兵,专司埋锅做饭。行军时他背着锅跟随,与敌兵交手时,他也要上去冲杀一阵,后背的铁锅帮他挡过不少兵刃。他是从伙头兵一步步拔擢起来的,后来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出身,还引以为荣,逢人就要大谈“兄弟当年做伙头兵时”云云。那年他隶属李西岩总兵的麾下,军中得到情报,海盗要大举登陆劫掠,李总兵率部提前赶到,在野外安营扎寨。透过树林的枝丫,看见远处海面上透来的波光,探马来回穿梭,报知海上的动静。
那时盛将军还是伙头兵,红日西沉时,他开始做饭。前一天刚下过雨,柴草潮湿,他含着竹管在灶下吹火,呛得眼泪直流。火燃起来了,照亮了他脸上的汗滴,锅里炖着狗肉,是留给几位长官享用的。
肉还未熟之时,探马来报,海面上出现海盗船,正朝着岸上驶来。李总兵下令,全军开拔,向海滨地带进发。狗肉加了艾叶,在锅里随着沸汤抖颤,盛将军不舍得扔下,急切中拿绳索穿了铁锅的把手,连锅带肉一并拎走。他一手在前抓着缰绳,另一手提锅,随着大队向前进发。
战马飞跃沟壑,锅里的沸汤溢出来,溅在马身上。马惊了,猛地摇头摆尾,盛将军没提防有这股大力,手里的绳子也撒手了,热锅飞了出去。紧接着,这匹马急往前冲。海盗已经登陆,盛将军骑着惊马,闯进了海盗的队列之中。海盗顿时阵脚大乱,还以为是官兵的主将冲杀过来,只见马上骑着一人,正在闪电般突进,马来得太快,面目还来不及看清,马蹄已经踢倒了好几个海盗,海盗的阵形大乱。李总兵见状,当即下令擂鼓,带着兵卒冲杀上去,竟然获得大胜,海盗自相践踏,倒在泥水之中,海盜的两艘战船也被缴获。
战后论功行赏,伙头兵作战勇猛,论功排在第一。功劳簿呈上来,李总兵特意在伙头兵盛某的名字下点了两个点,不久便破格提拔为把总。此后这位把总见风使舵,半夜时总兵军帐里的灯还亮着,人影闪动,知道总兵还没睡,他便亲自下厨为总兵烹制夜宵,深得总兵欢心。此后十年之间竟然一路扶摇,做到了参将,这即是后来的盛将军。
盛将军刚做参将不久,上峰派他带兵驻扎到海岛去独当一面,与陆上的守军互为掎角之势。在海岛的日子里,盛将军经常亲临灶间,检查伙食,看米面肉菜的成色,兴起时还亲自下厨,施展一下旧时的刀勺功夫。锅里暴起大火,照亮了众人的脸,只见他手腕一振,将锅里的菜蔬抛上了半空,人们抬头观看,望着那些菜蔬的碎屑升上了最高处,稍做迟疑,就开始坠落。他肩膀用力,带动手臂,锅随臂走,落下的菜尽数收到了锅里,一众伙头兵齐声喝彩。
亮过手段,已是意兴阑珊。他把锅交给伙头兵,众星捧月般走出了厨房。临出门之前,盛将军指着墙上挂的刀铲,命人都收纳到木柜里,免得伤人。他的手下连连称是,做出恍然大悟状。更多的时候,盛将军在厨房里并不动手,而是看伙头兵做,火候不到,放盐过多,他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得伙头兵原地转圈,脸上隆起五条手指印。
有人劝道:“请将军手下留情,些微小事,不宜惩罚过重。”盛将军怒道:“不能打人,我做这将军还有什么意思?”说完便叉开右手的五指,作势要打,“老子做到将军,还用你来教我?”兵卒不敢多言,退在了一边。他们私下里议论道:“到底是个伙头兵出身,整天围着厨房转,这样的人怎么能带兵打仗?”
话音还没落地,就传到了盛将军耳中。毕竟有些殷勤的告密者,像蜜蜂一样不知疲倦,嗡嗡出入将军的大帐,将军就是最艳丽的花朵。起初盛将军只是一笑而已,毫不介意。后来听得多了,不由得有些恼怒了。思量再三,他决定主动出击,去海上寻找海盗的巢穴,与海盗的主力来一次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到那时,就没人笑他是个伙头兵了。
他的船队在薄暮时出发。本想借着夜色掩护,哪知刚到海面便迎头遇到大雾,先前的星斗月光也都藏匿不见,雾气汩汩流泻,堆叠在船头,愈是驱赶便愈发浓烈。船队难辨方向,在海上踟躕不前。这时船舷一侧出现了两盏红灯,在大雾中施施然前来,眼见那两团红光渐大,似要撞进船队中来,众将官身上脸上都映出了红光,盛将军也变成了红头发、红胡子。船头一阵骚动,满船兵将都以为那红灯是海盗的舰船袭来。
在慌乱中,盛将军看见了大炮,赶紧从兵卒手中夺过火把,擎着火苗往引信上戳去。海上大雾,引信潮湿,燃烧时冒着浓烟,过了许久,大炮才隆隆醒来,炮弹向着那两盏红灯飞去。炮弹扰动气流,在浓雾中凿出了一柱空白地带,从那空荡荡的圆筒里望过去,红灯的光亮更为刺目,像太阳一般炽烈,令人不敢直视。后来盛将军还念念不忘,经常跟部下说起那时的场景:“就像一口烧红的锅。”
只听扑的一声,居然打中了,中弹之处似乎柔嫩,不像是硬物。两盏红灯骤然灭掉一盏,另一盏忽亮忽灭地闪烁。盛将军又点燃了大炮的引信,还没等射出,只见剩下的那盏灯跳跃着远去了。就在这时,海面上起了大风,将雾气吹散。炮弹飞出,径直落在海水中,海面上炸起了巨浪,空中下了一场急雨。月亮和满天星斗又回到海上,只见海面空荡荡,并没有海盗船只。后来有人说,盛将军开炮击中的不是海盗船上的红灯,而是龙的眼睛。在大雾弥漫之际,龙看不清道路,就要拿眼睛点灯。
盛将军的出征一无所获,在大雾中胡乱放了一炮,竟然打中异物。人们都说他打灭的是龙的眼睛,他也起了疑,不知是真是假,终归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里犹觉胆寒,此后龟缩在军营里不敢出门。这一战使盛将军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他的声望达到了一生的顶点,远胜于剿灭一股海盗。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盛将军成为天神一般的人物,他打瞎了龙的眼睛。盛将军听闻以后,也暗自得意,命军中的书吏写了捷报,派人送去总兵那里请功。总兵看了捷报,以为荒诞不经,随手往桌案上一扔。
盛将军没有想到,海上射龙目,是他戎马生涯的顶点,到了顶点之后,便要走下坡路了,像他锅里抛到最高处的菜。这一日他觉得烦闷,趁着天色大晴,便带着几个兵卒出营去闲逛,美其名曰查看地形。一行人登上了岛屿的制高点,俯瞰全岛。这里是岛屿中心的一座山,登临目送,海风扑进胸襟,眼望着脚下房舍,还有远处的万顷波涛,不由得豪气顿生。盛将军抬起右臂,指点前方的海面,对众人说道:“自从我来岛上,海盗逃匿,不敢来犯,就连海上的孽龙,见我也要让路。”
话音刚落,空中飘过一块方形的乌云,平移到众人头顶,乌云的四条边缘刀切般整齐,若不是内部有黑云翻滚,众人还以为那是一块黑毯。乌云来得出奇,盛将军和部卒仰头观看,乌云投下阴影将众人笼罩在内。这时,乌云中降下闪电,电光的鞭梢触到了盛将军的头顶,把电流传进了他体内,盛将军的全身都被电光包裹缠绕,瞬间又都熄灭了。
有人闻到了焦煳味,走到近前细看,盛将军已变成了焦炭,脸和手都是黑漆漆的,身上的衣服裂成碎片,在风中剥落。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盛将军仰面倒地,他指向前方的手臂仍保持不动,此时的指尖已经垂直指向天空。众人沿着那根焦黑的手指,一齐朝天上看去,翻滚的方形乌云中露出了一只巨大的龙爪,五个趾尖形似黑铁秤钩。龙爪缩回时扰乱了云层,现出了窟窿,周围的云絮齐来聚集,及时填补了漏洞。在那一刻,众人隐隐看到乌云中有一盏红灯。方形的乌云自行卷起,缩成一条黑线,随后凭空消失了,阳光重新照在了众人身上。
盛将军的儿子闻讯赶到岛上奔丧,随船带来了一位风水先生。据说这位风水先生是南七省的堪舆名家。盛将军的儿子今年刚十九岁,沉沦下僚,不得拔擢,父亲亡故以后,更是断了倚靠,他想要重振盛家的门楣,于是想到请风水先生泛海来到海岛,为他的父亲盛将军寻得一处佳穴。按照秘传的风水理论,死者在风水宝地安葬之后,其子孙必能得以显贵。盛将军的富贵来得太快,去得也快,他的儿子有了更上一层楼的野心。这正是:由穷入达易,由达入穷难。
在岛上盘桓几日,风水先生无所事事,终日饮酒,四处游荡,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处向阳岙口中停下来,不再挪动脚步,眼望着岙口吞进的一湾海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碎金,他眯上了眼睛。盛将军的儿子听说了,急忙赶来和风水先生相见。
刚到了风水先生的身后,风水先生就知道他来了,没有转身,就说:“有一处佳穴,却是在这岙口里的浅滩之下,海水之中,沿着岙口的中线,去往海中二里,用船做棺,到了位置把船凿空,就能保你盛家子孙代代显达,出现的大人物难以计量。”
盛将军的儿子将信将疑,他倒不是担心父亲葬在水里:“那么,盛家将来的大人物有几何?”
风水先生朗声道:“就像东海的岛屿一样多。”
东海的岛屿,大大小小加起来,少说也得有几千个。盛将军的儿子掰着手指暗自盘算,面现喜色。
船棺如期下葬,盛将军的儿子也就放了心,盛将军去世后,朝廷新任命的将军还没到,这时节,盛将军的儿子俨然是一岛之主,随意驱遣父亲的旧部,日渐跋扈起来。风水先生也受到了冷落,减去了酒肉,换成了窝头,撤去了丝绸被褥,换成了干草,许下的酬金也想赖掉。日子久了,忽想起这风水先生既然会布局,同样也会破局,这样慢待,恐怕他前去施个破法,干脆把他关进马厩里,用铁链锁了,和马在石槽里共同进餐,好教他无法动弹。
这一日,食槽里有兵卒加水,水中有小鱼一尾,风水先生捉鱼在手,又撕下一条衣襟,咬破手指写了几个字,塞到鱼嘴里,向空中一扔,鱼不见了踪影,一直在空中飞行多时,终于落入海中,摇头摆尾,直向北游去。
风水先生的徒弟在遥远的北方。这天早上,他在井中打水,摇动辘轳,来自大地深处的木桶重见光明,水桶里有一尾鱼,在水里转圈,忽然抬起头,吐出了书信,正是那风水先生的衣襟。徒弟展开一看,才知道师父落难,被人锁在了海岛,不由得勃然大怒。这口水井的底部通着海眼,小鱼从这里进入内陆。徒弟急急南行,到了东海边,乘船前往海岛。
他到达海岛时已是夜晚,潜入军营的马厩,找到了师父,将师父的铁链砍断,看管马厩的兵卒正在赌钱,师徒二人互相搀扶着逃到了海边。
“徒兒来得正好,今天一定要帮为师报仇。”风水先生说。
“怎生报仇?他们人多,我们只有两个人。”徒弟说。
“你要把他家的风水破掉,我们再走脱,就算是报仇了。今天晚上,那座船棺会有动静,盛家后代的大人物,今晚都要从船棺里出来,到尘世当中去游荡,到了合适的时候,便会降生到盛家,成为显赫的人物。你只要候在海边,登岸一个,你便拿刀砍一个,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一个。”
徒弟点点头,扶着师父在礁石后倚靠。师父连日来遭毒打和捆绑,又不得饮食,失去了力气,这大开杀戒的事,只好由徒弟代劳,好在要杀的不是真人,而是一团团人形似的虚影。这时,船棺上方光华大炽,先有一人蟒袍玉带,头上顶戴花翎,骑着马从海面上经过,如走平地。等他到了岸上,徒弟从礁石后窜出,手起刀落,将那人斩于马下,人和马都消失不见了。骑马的似乎是武将,官服上的补子绣着猛兽之形。紧接着,还有乘坐轿子的文官,补子上绣着珍禽之形。
“原来是一群衣冠禽兽。”徒弟心中暗骂,攥紧了刀柄,一一砍杀了。再往后出来的大人物,却一改本朝服饰,换作了贴身装束,上衣有四个方形口袋,下边是笔直的裤子,再往下是黑皮鞋。徒弟一个也没放过,照样把他们砍为两截。这些人都是虚影,倒地之后轻如败絮,随即消失不见。再往后,还有人穿着半截袖的白衬衣和黑色直筒裤,也被一刀砍中。
此时的徒弟已经力乏了,他挥刀砍了一夜,船棺之中车水马龙,纷纷涌上岸来。再往后更有奇装异服,又出来五位,有男有女,都在青春年少,一路谈笑风生,从海面上踏波而来。他们穿着黑袍子,戴着黑色的瓜皮帽,帽子上顶着一块四方的黑盖,其中一个尖角指向前方,方块黑板的左侧,垂下了一束红穗,每个人的手里还拿着一卷白纸,不知是做何用。
“那方块的帽子,是两百年后的装束,就像现在的状元帽,是科场功名的标志,不要让这奇装异服给吓住,年代不同而已,并无大变,赶紧上去砍杀了吧。”
徒弟强打着精神,一连砍掉四个,还剩下一个,砍得偏了,砍掉了头上的帽子,那人匆匆逃上岸,往松林里一钻,就不见了。
这时的船棺不再有动静,看来就是这么多了。“只逃走了一个”,他跟师父说。“不妨事,这个已经被你削去了帽子。两百年后,世上才会降生这样一个人,他难以靠帽子招摇,却要凭真本领,对他来说未必是祸。”
在夜幕的掩护下,师徒二人离开了海岛。盛将军的船棺从此暗淡无光,再也无人知晓。据说后来逃掉的那一个就是我——早年科场蹭蹬,如今只能靠卖文为生。
老人鱼
天有长庚星,海有老人鱼。
——聂璜《海错图》
金山卫的王农山御史致仕还乡之际,已是古稀之年,齿牙松动,两鬓萧疏。想起宦游在外的日子,顿觉平生无趣。他的后半生都在矛盾中度过,昔年同游的朋友风流云散,夏允彝、陈子龙抗清战死,而他却做了清朝的官,旧友便都不上门了。他在康熙年间做过御史,暮年回归故里,勉强算是乞得了骸骨。他终日往来于山林之间,倚在树下听着风声,策杖攀上山顶看海上波涛翻滚。
王御史想把山林景致挪移到家宅之内,有这种想法已经不是一两天了。适逢有人卖地,便派人去买了下来,筹划建一园林,种千竿竹,竹林后盖书房三间,在此读书,名曰旧雨斋,自己题了“旧雨斋”三个大字,请工匠刻了匾,他指挥着仆人爬高挂在了正堂之上。又据地势起伏,在高处堆叠假山,有石阶盘旋通往高处,山顶有凉亭,可在此纳凉。园中点缀奇树幽花,耳目为之一明。又在低洼处掘地为池,引入活水为溪流,注入池塘中,又从另一边开了泄水口。园林无水不活,经溪流的蜿蜒贯穿,园中景致都与溪水相邻,沿着水流的方向前行,便寻到了池塘。池上拱桥斜跨,可趴在桥头观看水中游鱼,一看就是半天,直到太阳跃入中天,晒得他脊背发烫,才起身回转。
此处园林作为养老之地,工程耗费甚巨,当地百姓称之为“王家花园”,眼睁睁看着平地上起了一座宅院,院门紧闭。王家花园落成那天,亲朋好友都赶来祝贺,众人聚在书房中,但见窗外竹影沙沙,窗台上兰叶葳蕤,桌案上珍本图谱堆叠如山,香炉中烟雾笔直升起,众人啧啧称奇,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皆是清雅之物,用王御史的话说,就是要“去一去三十多年的官场秽气”。这是过来人的话,年轻的小子们,哪觉得官场有秽气,只觉得香喷喷。
仆人献上一轴手卷,是王家花园的全景图,由王御史亲自绘制,参照了工匠的图纸方位,均用青绿山水之法绘出,草木竹石皆有明朗润泽的风致,每处景致用小楷标出名目。两个书童各执手卷的一端,王御史在图上指指点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众人在纸上先行游览了一遍。
这时管家王福来报:“禀老爷,外面有个渔夫求见,说是从海上得了件宝贝,好像是个活物,在筐子里一拱一拱的,也不知是什么,他说要献给老爷。”
王御史来了兴致,对王福挥了挥手:“让他进来,请到外面凉亭去。”转回身又对众宾客道:“诸位和我一起去看看,是什么稀奇宝贝。”
众人簇拥着王御史,穿过了回廊,在廊柱、画栋和藤蔓、叶片的光影交错中缓缓通过,众人身上光斑频闪。来到凉亭之内,亭子外面有溪水环绕,白鹅卵石铺的底子,明净可人,众人皆称妙。王福引着一个渔夫,朝凉亭这边走来。渔夫戴着斗笠,挽着裤腿,脚上穿着泥浆浸透的草鞋,身上的衣服倒是干净,不见一个泥点,在他手里拿着竹篓,似乎格外沉重,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来到凉亭之内,见王御史居中坐在石椅上,还有几位白须的老者坐在王御史身侧相陪,年轻一辈的就在左右侍立,凉亭内狭窄,有的人站在了凉亭之外,向渔夫这里观望。渔夫还真认得王御史,上来就要磕头,王御史绕过石桌,把渔夫搀起来。渔夫抬脸看着王御史,说:
“今天我在海上得了一件奇物,要献给御史大人,听说王家花园今天落成,特地献来宝物庆贺。”
说着,他把竹篓放在石桌上,揭开盖子,这竹篓的外壁是活的,能分成四片,向外展开平铺,其中有一坨白亮的物什显露出来,人群中惊呼起来。原来是一个硕大的头颅,俨然画屏上的寿星,头圆而长,额头球状凸出,两眼目光炯炯,口中喷气呼呼作响,再往下是皱纹密集之处,褶皱中有小蟹出没,还有两条细长的腿,向前盘成了一圈,将这大脑袋稳住,不至于歪倒。就在石桌之上,凭空生出了这件怪物,打开的竹篓平铺在桌上,怪物身上有水渗过竹篓的缝隙,沿着石桌边缘滴落,地面上已经积了一摊水,在水滴的连续坠落之下,这摊水动荡不安,镜面破碎又聚拢。
王御史老眼昏花,只见渔夫把竹篓拆卸开来,露出一坨白亮的圆球,他凑到近前,俯身细看,圆滚滚的肉球蠕蠕而动,在白色的底子上,还罩着青灰的薄纱,不细看难以发现这层颜色,它们由无数细小的颗粒组成,在凉亭的阴影之下,怪物的颜色也随之变得更深了。吸引王御史的,是怪物的眼睛,两只鸡蛋大的眼球,镶嵌在头颅两厢,眼眶围了一圈翠绿,金黄的眼球明亮而又活络,眼波流转,在眼球中映出了狭长的黑瞳孔。
王御史逼近了细看,与怪物的眼光交接,怪物的瞳孔骤然收缩,缩成了一条竖线,从那竖线里窥人,王御史一惊,赶紧往回撤身,怪物的大脑袋也晃了几晃,幸亏有两条腿盘坐,才稳住下盘。怪物的嘴部是凸出的一截圆管,随着气流的鼓动而起伏,发出“呼——呼——突——噜”的杂音,众人侧耳细听,想要分辨它在说些什么。人群安静下来,怪物的声音格外清晰,均匀递送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起初众人认为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杂音,来自异类的啼鸣,或许是被执之后痛苦的呻吟。生活在高檐广厦之下的大人先生们,何曾接触过这类奇幻生物。听了多时,才发现它的发音并不简单,它的语调愈发急速,音节也复杂多变,似乎是在讲述自己的来历,眼珠转动,向众人扫射,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听得懂。
人群中走出一位老者,打断了怪物的话,他环顾四周,对众人说:“诸位,此物从海上来,似乎是神物,故能口吐人言,只是所说语言难以通晓,似应为上古之音,佶屈聱牙,看来此物当有千万年的寿数了,今日得闻上古正音,幸甚至哉。”
渔夫赶忙接言:“不错,此物是鱼中最长寿的,能活三千年以上,俗称寿星鱼,也叫老人鱼,俗语云‘天有长庚星,海有老人鱼,说的即是。此鱼深藏在海底,一百年才出现一回,恰逢御史大人花园落成,正是福泽綿长的吉兆,大大的吉兆啊。”
“不错,果然是好兆头。”又有一青年书生进了亭子,朝王御史拱了拱手,又向众人道,“记得《神异经》里提到过‘西海有神童,乘白马,谓之海童,道是个孩童模样的少年郎,今日见到老人鱼,当属海童之类的神物,不过,看它皱纹堆叠,倒像是耄耋老叟,不妨称之为海翁,若有张华再世,便可以记到《博物志》里头了。天工造物之奇,实在难以逆料,跟随伯父左右,真是开了眼界。”
这青年书生是王御史本族的侄子,当众卖弄了一番,还不忘拍马屁,众人纷纷点头称善,王御史也是捻髯微笑,对那年轻人道:“贤侄果然渊博得很。”青年书生甚是得意,他环顾左右,用力瞪了瞪眼角,想让那双小眼看上去更加明亮。他东瞧西看,眼光落在了老人鱼的嘴上,耷拉的肉管,管口黑洞洞的,滴着水珠,他上前拨拉几下,笑道:“这嘴还真像是那活儿。”
人群中一阵哄笑,也有几位长者皱起了眉头,青年书生见势不妙,讪讪退了下去。然而,众人的兴趣却不在他身上,而是围拢过去看老人鱼。有那擅长丹青的,早已掏出随身携带的笔墨,开始在纸上摹写老人鱼的形貌,身后围着一群人在看。又有一人取出洞箫,呜呜咽咽地吹奏起来,更为老人鱼增添了几分幽玄之境。在乐曲声中,老人鱼恢复了安静,它似乎也懂得音律,眼皮向下低垂,眼球沉浸在眶中,在泪水中悬浮。
王御史转而问渔夫:“我看你谈吐不俗,也像是个读过书的,怎不求个功名上进,也能光耀门楣,却做了渔夫?”
渔夫道:“小人自幼读书,怎奈连战连败,未能如愿。如今逢进必考,眼看无事可做,家中贫寒,只好跟舅父到海上去捕鱼,补贴家用。”
王御史命人赏了渔夫五十两银子,说:“你拿着银子回去,就不要出海打鱼了,好生读书。”渔夫千恩万谢:“多谢老大人厚赠,我回去攻书,争取早日上岸。”说罢,向众人长揖,带着银子,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
老人鱼搁置在王家花园里。消息不胫而走,全城轰动了,都说王家得了个海怪,人们来到王家花园,都想要一睹老人鱼的尊容。
一天之内,王家花园的访客就有三千多人,老人鱼早就被移到了竹林之中的空地,摆了一张桌子,老人鱼趺坐在桌上,桌子四周钉了木桩,拦着绳子阻挡观众,只能在绳子之外观看,不得靠近抚摸。在密集的人头潮水中,独有一处空白,那是风暴的眼,老人鱼位于风暴眼的中心,偶尔颤抖一下,浑身的褶皱荡漾,隐约看到内瓤里的脏腑,漂浮在水做的身子里。人群中也不乏饱学之士,有一位赞道:“好,肝胆皆冰雪,如此透彻,定然不是妖邪之辈了。”
前来看热闹的人群,王家一概欢迎,大门敞开,刚装的门槛磨掉了油漆,竹林里的土地松软,众人合力踩出了三条小径,王御史命匠人沿着人们踩出的小径,铺设了石板,变成了石板路,石缝之内撒了白沙,那是去往竹林中心的通道。
王御史坐在凉亭里,石桌上搁置茶点,他的客人已经散去。现在,更多的游客聚集在竹林中,从凉亭望过去,人流在竹林中出入不绝,形同集市。管家王福欲言又止,王御史看了看王福,问道:“你想说什么?”
王福说:“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小人的父亲在海上营生,从小跟父亲在海上,见过不少新鲜玩意儿,这个老人鱼,倒像是个大章鱼,只是有两条腿,就显得有些奇怪了,章鱼有八条腿,方才我细看了,好像是有人切去了六条腿,只剩下两条,切口的断茬还在,就在大脑袋下面。”
“我岂会不知这种献祥瑞的把戏,只是园林新成,图个吉利,不便点破罢了。暂借这怪物一用,来传一传我家园林的名声。你传出话去,有谁想看老人鱼,尽管放进来看,门房不准阻拦。”
王福愣了一下,应了声“是”,转身去门上照应了。不多时,又有人流拥入,在回廊檐厦的转折之处,都有王家的仆人在引导行人通过,朝房中窥探的乡民,皆被仆人劝阻。此刻的王家花园,变成了博物馆,展陈的是一奇幻生物,人们焦灼不安,唯恐奇迹消失。
在不远处的竹林中,人群不愿散去,眼看夕阳就要沉陷下去,却仍在地平线上徘徊,迟迟不肯落下。这时,老人鱼忽然膨胀,浑身上下攒着力气,忽从嘴中喷出大团水雾,仿佛时间停滞,众人惊得张大了嘴巴,水雾升腾,恰似热锅的蒸汽,团团涌出,将老人鱼覆盖在白雾中,影影绰绰的,看不真切,人流的包围圈受惊向外扩散,风从竹林顶端落下,那团水雾散尽,再看桌上的老人鱼,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一摊水渍,倒映着半空中交错的竹影。
“妖怪,妖怪!”人群中炸开了锅,早已有人跑到竹林外,但还是有人眼尖,看到桌子底下有异物蠕蠕而动,浑身沾满土,身子圆滚滚的,正是方才立在桌子上的老人鱼,它在水雾的遮蔽之下,滚落到了地上,还滚了一身泥。逃走的人重新折回,蹲在地上看老人鱼的狼狈相,泥土和竹叶包裹在身上,随着它的喘息,沙砾从身上滚落,落下大片的土痂,露出里面耀眼的白肉,两条细腿像鞭子,在地上抽打,方圆七尺之内的地面烟尘四溢,沉重的肉身匍匐在地,或许正在宣泄它的愤怒。
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孩童折了一根竹枝,去捅老人鱼,老人鱼吃痛,一条细腿抽出,卷住了竹枝,夺了过去,拿着竹枝向孩童打来,嘴里还发出了吱吱的尖叫,震得众人耳鼓生疼,那孩子吓得哭了起来,蹲在原地动弹不得,竹枝抽打在他脚踝上。孩子的父亲从人群中出来,赶忙扣住孩子的腋下,把孩子凌空拔走,孩子的双腿还在半空中踢腾。
老人鱼扔掉竹枝,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椭圆的肉球一起一伏。经过这一番剧烈的运动,它身上的泥沙脱落大半,露出里面青白的皮囊,还有几处擦伤,狭长的伤口,白肉向外翻着,流出了淡蓝的汁液。难怪它的外皮有些发青,在它体内,流动着蓝色的血,当它愤怒时,血液在体内奔涌,脸面上就会呈现出鸭蛋壳的青碧,清澈之中又有阴郁,仿佛暴雨来临之前的天空颜色。
原来它没有什么神通,最多只是会喷水罢了。众人心里稍稍安稳了一些,同时也觉得兴味索然,这等神物,也有灰头土脸的一面。原本指望它显露一下神通变幻,起码要宝相庄严,令人心生敬畏,毕竟是跟天上的长庚星相对应的,哪知如此狼狈。
天黑了下来,众人陆续离开王家花园。老人鱼被人们看了一天,又掉在地上摔了一跤,奄奄一息。王御史见老人鱼委顿在地,于心不忍,命两个仆人用竹筐抬着老人鱼,到海边去放生了。仆人来到海边礁石上,合力挟持竹筐,如同泼水一般,硬生生地把老人魚泼出去了。黑暗中白影入水,两条长腿催动,瞬间不见踪影。
不出三天,王家花园就名声在外了。官宦之家的私家园林,原与百姓无关,却因老人鱼的陈列展示而打开了大门。在乡人眼中,王家花园是一处神秘的所在,亭台阁榭与奇花异木的交织,令人迷失归路,又有老人鱼这样的奇物在王家花园里公开展览,见者到处传讲,就愈发神奇了——王家花园的植物叶片肥硕,秋来结成一人多高的硕果;日暮时分,王家的用人四五人合抱一只果子,喊着号子,朝宅院深处走去,果子熟透时自行爆裂,汁液喷洒红雨,院墙上浸染堆积的也染成了紫色。据说还有西洋使者送给王御史的礼物,一株食肉树,护院的家丁夜里在树下小解,被食肉树的锯齿叶子裹去了阳物,尖叫声在大宅中响起,楼中渐次亮起了灯火,人声和犬吠搅乱了夜晚。
王家花园的秘密不止这些,老人鱼在此展出,似乎与王家花园的气息正相宜。在一座充满异物的私家园林中,老人鱼适时出现,镶嵌在奇花异卉之间,与那些花木一道,共同展示造化之奇。老人鱼是活物,似乎更能吸引人,它成为当地人的共同记忆。到后来,竟传说老人鱼能口吐人言,预知未来之事,更有甚者,说老人鱼能飞天遁地,瞬息间千万里之外,还能穿宅过户——它在深夜里从海中飞出,在低空翱翔,到了海滨人家,便跳窗而入,用两条细腿倒悬在房梁之上,起夜的人在黑暗中猝然相遇,半空中倒挂着一只头颅,还有两只眼在夜里放光,看一眼就会失魂落魄。
王御史听到这些,暗自好笑,所谓野叟乱弹,难免荒腔走板。那只经过修剪篡改的章鱼,如同鬼魅一般,在人们茶余饭后被频频提起,成为平淡生活中的调味品。上至八旬老叟,下到三岁孩童,都在谈论王家花园。王御史走在街上,听到背后有人说,看,那是王御史,就是那个王家花园的主人。这种结果,是他乐于看到的。又有人说,王家花园里有长寿的老人鱼,王家的御史大人定然要长寿了。这种话,也是他乐于听到的。渔夫得了赏钱,王御史得了美名,可谓皆大欢喜,这都要感谢那头怪模怪样的老人鱼。
又过了一个多月,王家花园的细处已经收拾停当,工地上的废料运走,假山上的青苔滋生,移栽的花卉也重新打起了精神,新宅退去了火气,人工添置的木石,在空气中暴露久了,也变得熨帖,此时的宅院最为宜人,王御史叹道:“又离自然天趣近了一寸,可惜的是,人工之力,永远无法抵达天公之力。”
这天王御史正在读书,阳光透过窗纸,管家王福跑进来,说:“老爷,上个月来献老人鱼那个渔夫,在海上出事了,半边脸皮让海怪给撕掉了。”
王御史一愣:“他遇见什么怪物?”
“说是府台大人的母亲要过八十整寿,渔夫出海去找什么祥瑞,好去府台大人那里去讨些赏钱。他舅父说,网里打上来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有八条腿,腿上有吸盘,吸住了他的脸,他硬往下拽,就把脸皮拽掉了。”
“如此说来,倒像是又抓到了大章鱼,难不成他又要故伎重演?”
王御史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达官贵人家的喜事,比沙砾还要多,只要家业不败,便日日是好日,上哪里去找那么多祥瑞?”
王福说:“要找祥瑞,去海里找,倒是不难。海里异物最多,只要选些不太常见的货色,再动点手脚,就能蒙骗一时了。”
王御史听了,眉头紧锁。他想起渔夫的面孔,黑灿灿而有光泽,如今被章鱼的吸盘撕去了半边脸,恐怕要半边红、半边黑,成了阴阳脸。想到这里,王御史不觉头皮发麻。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