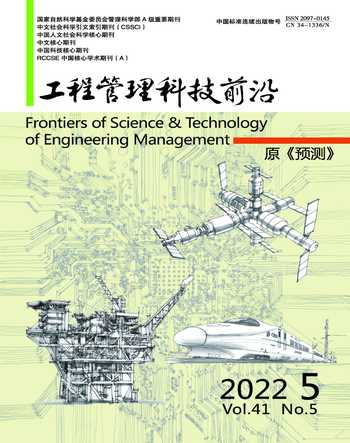制度质量对金融市场表现的影响
万金石,周孝华,刘斌



摘要:制度作为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将制度质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解为制度完善指数和政治稳定指数以消除制度质量指标间存在的相互干扰,利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制度完善指数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完善指数既减少了市场收益,也减少了市场波动水平。政治稳定指数提高了市场波动水平,而与市场收益不相关。本文的实证结果解释了为何中国这类兼具制度不完善和政治稳定特点的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极高,为我国金融市场管理体系和发展战略的优化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制度质量;金融市场表现;GMM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7-0145(2022)05-0034-08doi:10.11847/fj.41.5.34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Finance Market Performance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 Model
WAN Jin-shi, ZHOU Xiao-hua, LIU 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engineer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plays a key role in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e marke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panel data model, and breaks down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to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index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dex to eliminate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dicators. The economic freedom index released by the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is used as a tool variable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index not only reduces the finance market return, but also reduces finance market volatility. Political stability index increases finance market volatility, but is unrelated to finance market retur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xplain why the finance markets of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China,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both institutional imperfec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extremely volatile.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inance market.
Key words:institutional quality; finance market performance; GMM mod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1引言
金融市場表现除了受到上市公司自身因素影响以外,往往还受到一系列政治事件以及各项政策的冲击。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一个国家治理框架的质量,这是因为公司会受到它们所在地区治理系统的影响。从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治理框架的优劣取决于相关制度的运行机制。制度已成为区域间争夺发展主旋律的重要考量因素[1]。政府行政效率越高,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就越容易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越有利于投资行为[2]。当前,越来越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进入发达经济体进行“逆向”投资[3],也证明制度质量较高的市场对资金具有比较高的吸引力。投资者需要从进化和适应性的视角了解金融市场[4],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金融市场表现影响不同,如不同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等[5]。本文聚焦国家一级制度质量水平对金融市场表现的影响。在研究跨国制度质量指标时,学者们使用较多的是Kaufmann等[6]构建的制度质量指标体系,包括6个制度质量子指标。一些学者在利用这一制度质量体系作为制度质量指标研究金融市场表现时,对其包含的6个指标的相关关系缺乏严谨的讨论,导致许多研究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而其他对制度质量指标的研究和探索成果主要包括:蔡长昆[7]认为政治制度环境中权力结构的开放程度、产权体系的完备程度,以及社会制度环境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是理解制度绩效的关键。钟昌标等[8]使用政府管制指标和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来反映我国的制度质量。金祥荣等[9]使用司法制度质量和产权保护制度质量作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戴翔和郑岚[10]使用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支出比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地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数值越大意味着制度质量越低。文雁兵[11]在研究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促进效应时选取了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和对外开放度四个指标, 通过主成分方法合成为一个制度质量指标来探索这个问题。然而这些学者对制度质量指标的选取也存在特殊性和局限性,更多侧重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相关指标,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足。
基于上述研究的局限,本文可能产生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Kaufmann等[6]构建的制度质量指标分解为相互独立的两个影响因子,将他们分别定义为制度完善指数和政治稳定指数,消除了制度质量指标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同时利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制度完善指数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二,以往文献多集中于考察政策对金融市场的短期影响,本文则考察了制度质量对金融市场表现的影响,通过对国家层面治理的分析取代对具体政策事件的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宏观治理变量对金融市场表现的影响。第三,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协助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优化。
2文献综述
适应性市场假说的基本思想逻辑认为有效市场是不成立的。长期以来,金融市场存在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围绕制度因素对金融市场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宏观治理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影响公司各个方面的活动,尤其会反映在金融市场表现上。比如,Hooper等[12]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全球金融风险和各种业绩指标的影响,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金融市场收益。良好的国家层面治理质量降低了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公司的增长前景和利润,增加了对股东的回报率。因此,较高的制度质量会提升金融市场的回报率。Lombardo和Pagano[13]强调了法律和执法在影响公司治理、公司价值评估、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Chiou等[14]认为制度质量会通过影响外部融资可用性、融资成本、市场估值和投资质量来影响该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运作。Fan等[15]证明治理结构不良的金融市场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高于治理框架良好的金融市场,在管理不善的市场中,股权需求会下降,导致股本回报率降低。Chen等[16]的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方面,企业层面的公司治理在影响公司政策和决策方面的有效性受到制度质量的影响。焦豪等[17]通过实证证明制度质量对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制度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对该地区金融市场的投资越有可能获得收益。Sherif和Chen[18]认为制度质量与风险负相关,推进制度质量提升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
从微观层面来看,制度质量能够改善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良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层隐瞒负面消息的可能性降低,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从市场层面来看,Harvey[19]通过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治理结构比发达市场弱,因此具有較大的股权风险溢价和较高的收益波动。Claessens[20]也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开放、跨境资本流动、贸易自由化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而通过完善制度可以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抑制非效率投资产生的负面经济后果。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依旧存在着众多非市场因素[21,22]。杨高宇[23]发现我国2001年到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中,每次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价格波动。王明涛等[24]同样发现政策因素是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政策因素在牛市行情中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大于熊市行情,对股市向下波动的解释程度大于向上波动的解释程度。
不过Soo-Wah等[25]考察了制度质量与全球股市收益之间的联系,发现制度质量与股票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制度质量得分较低的国家的平均股本回报率高于那些制度质量得分较高的国家。Gul等[26]通过对巴基斯坦股市进行研究发现,政治不稳定对股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使用事件研究方法来测试这种关系,发现恐怖袭击、政治人物遇刺、部落武装冲突,以及美国无人机袭击等政治事件对股市产生了明显的冲击。Bittlingmayer[27]发现了股票价格波动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不同政治事件的组合发生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更高。他的研究还证实革命、战争、暴力和罢工直接导致股票收益波动性增加。Mei和Guo[28]调查了政治动荡对金融危机的影响,采用2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这些经济体发生的总共9次危机中,金融市场波动性很大。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发生频繁更迭的阶段对是否投资金融市场犹豫不决。Hussain和Qasim[29]将金融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代表来研究政治动荡对经济形势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股票价格会随着不同的政治事件而波动的假设。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制度质量和金融市场表现的关系,学术界存在广泛的争论。这可能是未将制度指标进行合理细分造成的。
3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3.1制度质量指标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 2002—2019年全球范围内的代表性样本,包含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非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及地区12个,欧洲国家11个,拉美国家3个,北美洲国家 2 个,大洋洲国家2个,测试了这些国家制度质量与金融市场表现的关系。Kaufmann等[6]构建的政治治理指标体系包括政治稳定程度(PS: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公民话语权与政治权利(VA: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府施政有效性(GE:government effectiveness)、市场经济限制程度(RQ:regulatory quality)、司法有效性(RL:rule of law)和贪腐控制(CC:control of corruption)。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政府施政有效性(GE)与贪腐控制(CC)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6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由于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会使得参数估计不准确,因此需要将制度质量6个指标进行“降维”,用少数几个变量来替代6个指标,同时使6个指标的信息基本都包含在这几个变量里,并且用来表示的这几个变量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性,这种方法称为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少数几个变量称为主成分因子。
通过因子贡献率的分析结果,最终从中提取了两个主成分因子,得到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2.6%,即6个变量中的92.6%的信息可以用这两个因子来进行说明。KMO和SMC的结果检验显示,KMO的度量值为0.932,表示非常适合做主成分分析,而SMC检验也显示变量之间线性关系较强,应该使用主成分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之后,提取的两个因子为fac1和fac2,在fac1中,CC、GE、RQ、RL对其贡献较大,其中最小值为0.421,最大值为0.426,由于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国家制度建设成果,因此将因子1称为制度完善指数(ipi)。对于fac2,变量PS和VA对其的贡献为正,分别达到0.691和0.489,其他因子为负,这两个指标主要反映国家政治团结和稳定,因此也将因子2称为政治稳定指数(psi)。
3.2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2002年至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参考张光利等[30]的做法,本文以金融市场表现(M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市场收益(asp)和市场波动(smv)指标来衡量。将衡量制度质量的两个指数(ipi、ps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制度完善指数(ipi)和政治稳定指数(psi)是由6个制度质量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而得。金融市场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因此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形式(lgdp)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控制变量并采用地区虚拟变量(as、eu、af、na、sa、au)控制地理因素。一些国家存在制度发展不平衡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将股票交易所建立在该国经济较为发达、制度相对完善的地区。因此將一国股票交易所是否设立在首都,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控制,变量名称为制度水平是否匀质(cap);许多国家金融市场表现在2008年出现巨大波动,这是由于该年度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31],因此将数据的时间以2008年为节点分为两个部分构建虚拟变量d;而经济自由度指数(ltscore)为工具变量。有关变量的具体解释如表1所示。制度质量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GI数据库。股指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连续变量在第1和第99百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处理。此部分分析均采用Stata15.0完成。
3.3模型构建及检验
3.3.1模型构建
参考已有文献[12],构建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1)OLS模型
基本回归模型如模型(1)所示
MP=β0+β1ipit-1+β2psit-1+β3Control+μ(1)
解释变量MP由市场收益(asp)和市场波动(smv)两个变量来度量,考虑到制度质量对于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模型考虑滞后1期的制度完善指数(ipit-1)以及滞后1期的政治稳定指数(psit-1)进行分析。控制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形式(lgdp);时间虚拟变量d;地区虚拟变量as、eu、af、na、sa、au;cap为主要股票交易所是否设立在首都,反映国家治理是否均衡。
(2)2SLS模型
在上述OLS模型中,如果核心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那么参数的估计将失效,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因此引入工具变量法建立2SLS模型来消除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
模型的第1阶段为(考虑ipit-1具有内生性)
ipit-1=α0+α1pist-1+α2Control+α3ltscoret-1+ε′(2)
于是可以得到ipit-1的估计值为
iit-1=α0+α1psit-1+α2Control+α3ltsoret-1(3)
在模型的第2阶段中,被解释变量对iit-1以及其他变量进行回归
MP=γ0+γ1iit-1+γ2psit-1+γ3Control+μ′(4)
在模型加入变量ltscoret-1作为控制之后,解释变量ipit-1变得不再显著,且系数由正数变为负数。通过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变量ipit-1与变量ltscoret-1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的问题,因此考虑将变量ltscoret-1作为解释变量ipit-1的工具变量。
3.3.2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对于解释变量是否能够对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非常重要。下面将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以说明其使用的有效性。
(1)工具变量有效性经济意义检验
经济自由度指标是由以下10个因素构成的,分别是:营商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合理政府开支、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产权保障、廉洁程度和劳工自由。与反映制度质量的制度完善指数贡献最大的四个因素(政府施政有效性、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贪腐控制)存在关联。而经济自由度指标并不能直接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但是经济自由开放会促使国家进一步完善其治理。经济自由度指标可以通过影响制度质量完善程度对金融市场产生间接影响。
(2)工具变量有效性实证检验
对于工具变量的检验,分别进行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以及过度识别检验。在不作iid扰动项假设下,不可识别检验统计量的值为116.458,其p值为0,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在iid扰动项假设下,统计量的值为 344.895,p值为0,同样拒绝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对应的F统计量的值为1130.722远大于真实显著性水平不超过15%的值8.96,显示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的原假设。在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中,为满足过度识别检验的条件,将滞后1期经济自由度指数对数(ltscoret-1)以及滞后2期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对数(ltscoret-2)作为制度完善指数(ipit-1)的工具变量,对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在不作iid扰动项假设下,Hansen统计量为0.227,对应的p值为 0.634,说明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假设;若是在iid扰动项假设下,Sargan统计量的值为0.297,p值为0.586,同样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
4实证结果分析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市场收益asp的平均值为0.130,市场波动smv的平均值为1.27,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差分别为0.330和0.621,说明不同国家间金融市场表现存在显著差异。而制度完善指数ipi的标准差为2.309,远大于政治稳定指数psi的标准差0.586,可见样本国家制度质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是否完善上。其他指标也均和已有文献相符。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制度完善指数与政治稳定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几乎为0。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结果与预期相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
4.2OLS回归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市场表现(分别以asp和smv表示) 与制度完善指数(ipi)均显著负相关(β=-0.029,p<0.01;β=-0.087,p<0.01),第(2)列中smv与政治稳定指数(psi)显著正相关(β=0.178,p<0.05),而第(1)列中asp与政治稳定指数(psi)的关系不显著。控制变量实际GDP的变化(lgdp)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考察制度水平匀质程度变量(cap)和金融市场表现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时间虚拟变量(d)与asp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2008年后各国市场收益显著下降,对smv的影响不显著。制度质量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运行效能的信息。国家级治理结构和企业级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金融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因素,制度质量的优劣直接体现了这一宏观环境的优劣。契约环境的改善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债务融资约束,影响企业股票的价格[32]。而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的差异化特征也影响了金融市场表现[33]。
4.3核心变量的2SLS模型及其对比
本文建立了静态面板模型,并进一步采用2SLS模型进行检验。如果2SLS的估计系数和GMM的估计系数基本一致,可以判断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再由LIML模型与2SLS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比较,若其回归系数趋于一致,则可以进一步印证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回归结果中,采用GMM法和LIML法的结果和采用2SLS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弱工具变量问题,偏R2统计值和Sargan统计值检验结果均显示工具变量有效。
由表3第(1)列可知,制度完善指数对市场收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28,p<0.05),投资者将较低的制度质量与投资风险联系起来,因此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政治稳定指数则对市场收益影响并不显著,否定了Soo-Wah等[25]的观点:政治风险高国家的投资者因承担较高的风险而获得更高的股权回报。表3第(4)列显示,制度完善指数对市场波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33,p<0.01),而政治稳定指数对市场波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13,p<0.05)。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全球化,政治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更容易得到巨额国际游资的青睐,国际游资的冲击提升了股市波动水平。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实际GDP的变化对于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地区控制变量对于金融市场表现的影响未完全显著。而变量d对于市场收益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的金融市场结构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各国金融市场回报率有所降低。一些国家由于制度发展不均衡,并未将股票交易所设置在首都以期减少股票交易受到政治偏好和腐败议员的干扰,所以这里发现cap对金融市场表现并未产生影响。表3的实证结果也赞同了Harvey[20]的观点,即新兴市场制度不完善,治理结构总体上较发达市场较弱,因此具有更大的股权溢价和更高的股价波动性。而政治稳定又导致中国这类新兴经济体更加吸引国际游资进入,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場波动。
4.4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分别使用滞后2期的制度完善指数ipit-2和政治稳定指数psit-2来重新检验制度质量因素对金融市场指数是否有显著影响。通过内生性检验,ipit-2仍然存在内生性问题,分别取滞后2期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对数(ltscoret-2)和滞后3期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对数(ltscoret-3)作为变量ipit-2的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使用滞后2期的制度完善指数ipit-2和政治稳定指数psit-2替换原有的核心变量(ipit-1和psit-1)后,制度完善指数和政治稳定指数的系数与表3第(1)列和第(4)列中回归结果的系数变化不大,且在至少5%显著性水平上仍然显著,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不变;Sargan等统计量检验仍然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其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结果仍然保持一致。
5结论与启示
依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制度质量的高低对于各国金融市场表现有显著的影响,影响期滞后1年。在制度质量的两个因素中,制度完善指数既减少了市场收益,也减少了市场波动。
(2)政治稳定指数和市场波动呈正相关,这一观点与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的国家制度质量减少金融市场波动水平的结论相反。原因在于:政治稳定水平较高的国家金融市场更容易得到国际游资的青睐,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波动水平较高可能与巨额国际游资的进出有关。
(3)政治稳定指数和市场收益不相关,投资者仅会对制度不完善的金融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
(1)中国若要进一步完成金融市场改革,首先需要在制度层面(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取得突破和进展,注重制度的全局性和前瞻性。同时为了完成对整个金融市场管理体系和发展战略的优化,金融改革的主导权需要放在最高层。
(2)新兴经济体兼具制度不完善和政治稳定的特点,因此市场波动相较于发达国家更为明显。要在政局稳定前提下积极完善证券市场的配套制度。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减少非市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不合理干预,提升市场自由度。
(3)由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更容易成为国际游资的“狩猎目标”,对此应当有所警惕并谨慎地安排国外资金有序进入本国金融市场,避免剧烈的股市波动和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段忠贤,黄其松.要素禀赋、制度质量与区域贫困治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3):144-160.
[2]Libman A.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b-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does sub-national democracy matter[J]. Energy Economics, 2013, 37: 82-99.
[3]李新春,肖宵.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J].管理世界,2017,33(10):99-112.
[4]周孝华,宋庆阳,刘星.适应性市场假说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6):111-125.
[5]陈其安,雷小燕.货币政策、投资者情绪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理论与实证[J].中国管理科学,2017,25(11):1-11.
[6]Kaufmann D, Kraay A, Mastruzzi M. Governance matters II: updated indicators for 2000/01.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R]. Working Paper No.2772, 2002.
[7]蔡长昆.制度环境、制度绩效与公共服务市场化:一个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16,32(4):52-69.
[8]钟昌标,李富强,王林辉.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1):13-21.
[9]金祥荣,茹玉骢,吴宏.制度、企业生产效率与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J].管理世界,2008,24(11):65-77.
[10]戴翔,郑岚.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J].经贸论坛,2015,(12):51-64.
[11]文雁兵.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促进效应——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15,31(2):28-42.
[12]Hooper V, Sim A B, Uppal A. Governance and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J]. Economic Systems, 2009, 33(2): 93-116.
[13]Lombardo D, Pagano M. Legal determinants of the aspurn on equit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6, 22: 235-270.
[14]Chiou W J P, Lee A C, Lee C F. Stock aspurn, risk, and legal environment around the world[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0, 19(1): 95-105.
[15]Fan J P H, Rui O M, Zhao M. Public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3): 343-364.
[16]Chen K C W, Chen Z, Wei K C J. Legal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9, 15(3): 273-289.
[17]焦豪,焦捷,刘瑞明.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7,33(10):66-78.
[18]Sherif M, Chen J.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momentum profi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19, 51(5): 1-16.
[19]Harvey C R. Predictable risk and aspurns in emerging markets[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5, 8(3): 773-816.[20]Claessens 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J].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6, 21(1): 91-122.
[21]刘贯春,张军,丰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效率提升——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7,33(6):9-22.
[22]彭俞超.金融功能观视角下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来自1989-2011年的国际经验[J].金融研究,2015,(1):32-49.
[23]杨高宇.中国股市制度缺陷與股市功能异化[J].中国经济问题,2013,(2):91-100.
[24]王明濤,路磊,宋锴.政策因素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J].管理科学学报,2012,15(12):40-56.
[25]Soo-Wah L, Si-Roei K, Lain-Tze 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11, 40(3): 361-384.
[26]Gul S, Khan M T, Saif N, et al.. Stock market reaction to political events (evidence from Pakistan)[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4(1): 165-174.[27]Bittlingmayer G. Output, stock volatility,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in a natural experiment: germany, 1880-1940[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53(6): 2243-2257.
[28]Mei J, Guo L. Political uncertainty, financial crisis and market volatility[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4, 10(4): 639-657.
[29]Hussain F, Qasim M A. The Pakistani equity market in 50 years: a review[J].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1997, 22: 863-872.
[30]张光利,薛慧丽,高皓.企业IPO价值审核与股票市场表现[J].经济研究,2021,56(10):155-171.
[31]苗文龙,钟世和,周潮.金融周期、行业技术周期与经济结构优化[J].金融研究,2018,(3):36-52.
[32]杨畅,庞瑞芝.契约环境、融资约束与“信号弱化”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33(4):60-69.
[33]张述存.“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J].管理世界,2017,33(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