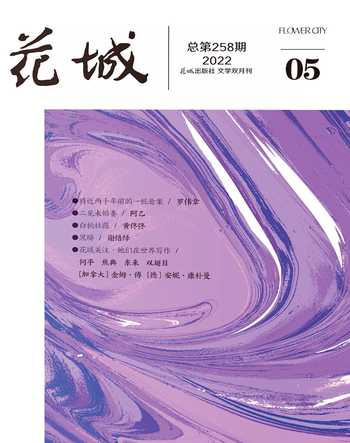夏 夜
[葡萄牙]埃尔德·马塞多
睡眠开始的瞬间是死亡的画面。
——热拉尔·德·内瓦爾
那不是长者的故乡。
——威廉·巴特勒·叶芝
众神怜悯苦苦哀求的奥菲欧,允许他到地狱冥洞去寻找他的爱人尤丽迪丝,但对他提出要求:“你不能回头看她,因为现在你失去了她。”那他是如何失去了她;何以错过了她?她的容颜谈吐都已改变,不再是他曾爱着的尤丽迪丝了。
——曼努埃尔·特谢拉-戈麦斯
时光逝去,永不归还。
——若热·德·塞纳
太阳被割断喉咙。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 没有钢琴的钢琴家
我碰巧知道了您的电邮地址。不,不是碰巧。我早应该问到的,不该是碰巧。毕竟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现在大家都认识您了。我一直在关注您,一直关注您的事业、您的成功,还有您的恒心。艺坛风云变幻,而您依然坚持绘画。您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若那真是您的意愿和方向。您还记得我吗,记得我们吗?我们是那么多死去的人,如今……但是我还留着您写的诗。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以前除了绘画还写诗。况且那时条件也不怎么样。绘画对空间有要求,但那时太困难了。我曾经也想做钢琴家,而我没有钢琴。不过寂静不曾把我们分开。您曾说您写下的那些文字不是诗,我却认为是。那是您画家才情的流露。因为绘画也曾是您的写作方式。您的诗仿佛变成了词语的影像,字迹间填补着白色的空间。空间则是寂静的影像,用以言说不可言说的事物。我的音乐也是以寂静做成的。您有好几次把诗留在了咖啡馆的桌上。它们被用各种颜色写在餐巾纸上,等着被揉皱了扔进垃圾堆。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都没有注意,我把我救下的那些好好收起来。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我至今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您与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们想要不同于过去。我们已经活过很多次了,几乎穷尽了生命的全部,也几乎穷尽我们全部的生命。这不是一回事,对吧?我们正在抵达词语字迹间的空间。我们又可以重逢了,您不觉得吗?一如初次。我能去拜访您吗?提前三天告诉我就好。为了第三日的复活。
另:我们从前以“你”相称,您还记得吗?
2. 玛达莱娜
不,他不记得。那封未署名的电邮没有告诉他任何信息。邮件地址是一串毫无规律的字母:aaea.mdln。四个元音和四个辅音,被一个句点隔开,然后是@。他在纸上把字母写成对称的两栏,然后把元音安插进辅音。这个名字赫然出现——Madalena,玛达莱娜。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玛达莱娜是谁。要说一个如此亲近的人他不应该会忘记。或者之前有段时间,他有不止一个朋友叫这个名字,也有可能。青春年少总是让人多情又健忘。但也有可能这个玛达莱娜有别的更常用的名字,但她现在觉得没必要说。可能是玛丽娅,就像萨拉查统治时期葡萄牙所有的女人都叫玛丽娅,后面才跟着自己的名字。或者是莱娜,缩写的玛达莱娜,这么想的话,也可以是缩写的伊莱娜。伊莱娜确实有一个,玛丽娅·伊莱娜,但他对她非常了解,不可能是她。要是调换一下这个名字的字母顺序,名字的前两个元音和最后一个辅音就构成了Anna,安娜,这样一来就是安娜·玛达莱娜,以纪念巴赫的妻子安娜·玛格达莱娜,因为在信中她说她是钢琴家。这倒是最适合她的名字。Anna也是否定词缀。不合时宜,不符逻辑,不分本末,不受关注……没有钢琴的钢琴家。那她就“不是·玛达莱娜”,她是被遗忘的、去而复返的人,不同于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她是对于一场遗忘的记忆,是倒置的时间。
但那是在里斯本,在去巴黎之前吗?他刚离开葡萄牙,他喜欢的女孩伊莱娜就立刻嫁了人,接着她丈夫参军入伍,从战场回来以后把他当成了假想敌。而里斯本一度让无数的遇见错过。那里原本还有其他的可能,那里的未来还不知道会怎样。那是遗恨之地。而巴黎则是匮乏之地,属于一段梦游的时光。他曾幻想在巴黎结识里斯本遇不到的先锋画家、葡语圈里找不到的文字创作者、从欲望之地移民梦想之国的自由诗人。但是这些画家和诗人早在非洲存在以前就往那儿去了,他们的战争是别的战争,等他到了巴黎,那些人早就不在了,留下的也不是像他一样初来乍到的人能搭上话的,像他一样的逃兵也走了,不是为了和谁相聚,只是为了逃离自己。他们在流亡中盼望着,有人能在他们的国家发动一场革命,他们等着战争结束,而另一些人战死在那“不存在的非洲”。他记得有人说过,还一边笑着,无聊透顶:“鬼知道是不是真有个非洲,我从来没见过。”但是后来别人踏上那片土地,非洲也日渐为人所知。
对他来说,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就是他看到一群笑容满面的士兵,正炫耀着钢叉上的黑人头颅。黑人的嘴唇和双眼伤痕累累,死亡反倒结束了疼痛的折磨。正是那时他明白自己必须逃离战争,这样才能逃离自己。不过他带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也可能就是他自己。想离开葡萄牙不是难事。他没有犯罪记录,作为对欧洲最后的道别,他选择去巴黎,赶在征兵之前。只是一去不复返就比较复杂了,好在他还是得以生存,而不用被迫杀害那些死后仍在照片里继续存在的人。他也不用被人杀害,不用抹去存在,或是带着从自己身体上截断的部分记忆残存于世:残腿,断臂,空洞的双眼望着空洞。他再也没有见过伊莱娜,为了被人所爱,她不再爱他。不过这个玛达莱娜真的不是伊莱娜吗?到底是何时,何地?他想不起来。
那时候是有一些女孩子追随他们那帮搞艺术的人。其中几个还算有天赋,有明确的志向和个人风格。可能他当时和哪个女孩走得很近吧。对了,很可能是在咖啡馆,他总会玩些文字游戏,在厚实得像毛巾一样铺散在桌面的纸张上,或者就用手边那些印着孔隙的餐巾纸。那时候他总这样做,在里斯本和巴黎都是。那些东西算不上是诗,前言不搭后语的,没有人会拿去出版。但那位玛达莱娜却说她认真读过并且认为那是诗。那封邮件字里行间透露着亲近的语气、错过的机会和生活的其他可能。那个女孩,那个女人,现在应该和他年纪相仿,她是对于一场遗忘的记忆。是突然浮现在白色画布上的古旧字迹①,是一个没有钢琴的钢琴家。是一个没有原因的结果。是一段遗忘的暗喻。
3. 西班牙新娘
无论是不是暗喻,自从答复了她,他一连三天都过得不太安稳,一连三晚都睡不好觉。玛达莱娜,这样称呼着她,就好像真的认识她一样。听从她的建议,他们约定三天后见。地点是他家,在画室,7点左右。正是夏天,如果她愿意看看他最近的画作,那时的自然光也足够。或者啜饮一段不曾发生的往事。但他没说这些。只是确定了日期、时间、住址,他补充说这是个老房子,藏在新住宅后面的一个庭院里。画室在地面层,有单独的入口,在右侧。所有这些都是找到他家必需的细节。像是词语之间的寂静,他以前若是这样说过,后来他就能想起,而她也就能意会。抑或像是那瓶珍藏多年的木桐·罗斯柴尔德,一直在等待某个特殊场合,后来却被抛诸脑后。
而另一个暗喻的来源,是在葡萄牙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一个新的开始。这则新闻占领了所有报纸的头条。法国人神情激动地谈论着葡萄牙,邻居大肆宣扬说以前见过他,知道他是葡萄牙人,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好像这场革命是他的成就。而他呢,想说也许真是这样,因为否认也是一种肯定,突然间他想,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摆脱眼下的悲惨生活,到葡萄牙做画家,因为在巴黎就算看再多、画再好也成不了画家。不是法国人欺负他。他们不好也不坏吧。就算被警察当作阿尔及利亚人拦下盘问也没什么。他甚至还找到一些临时工作,比如在玛德琳广场附近的建筑设计工作室做绘图员。虽然报酬微薄,但至少能让他这个战争逃犯拿到办理居留的文件,有个地方住。
他算了算交通成本。坐火车便宜些,画廊给的钱还能剩几个法郎,足够买路上的干粮。但实际情况是,他一到玛德琳广场,就鬼使神差般迈进了那家葡萄酒精品店①,以前他只能在橱窗外巴望。那个场合真应该配一瓶香槟。他进门说清楚缘由,带着满腔爱国热情。他保持着一贯的谨慎,询问着合适的品牌,看哪一种酒可以致敬仁人志士,他仿佛看见浆熨过的衣领上方高昂着革命先哲的脸庞。权衡再三,香槟毕竟是挥之即去、昙花一现的美酒,旋开瓶塞,泡沫喷涌,四处飞溅,然后迅速恢复平静,到第二天则气数散尽。
“这场革命就像五月运动②,亲爱的
先生。”最后,他选定了一种木桐·罗斯柴尔德期酒③。多花几个法郎就能拿下,太值了。就是这一种红酒。颜色深邃,酒体醇厚,适合收藏。正好他也要开始崭新的生活了……“就是这样,就像您的国家一样。总之,像您自己一样,亲爱的先生。”售货员补充道,仿佛其中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刚好在那一年,那片葡萄种植园的主产区地位终于获得官方认可,虽然实际上一直都是,但那一年才算名正言顺。
“就像葡萄牙一样?好吧,那什么时候可以喝呢?”
“至少得给它20年吧,甚至40年。毕竟是红酒。或许国家也一样。多好的时机啊,亲爱的先生!”
于是他买下这个昂贵的暗喻,花光了买干粮的钱。仅剩的零钱只够买一小圆盒乐芝牛牌劣质奶酪,里面装着黏糊糊的小三角块,他还买了三个实在的橙子。得靠这些撑过三天的旅程。他坐着西班牙的三等车厢,入境换乘时等了很久,被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全方位监视着。破败不堪的木质座椅收容着太多的流浪汉,逐渐被嘈杂所占据,座椅上的人寻找着也许根本不会有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阴郁的站台,一阵接一阵。饱经风霜的男人,被迫奋斗的女人,疲惫焦躁的孩童。身体,汗水,积聚的气味。工具袋,鸡笼,里面塞着几只羽毛稀疏、双眼惊恐的母鸡;锄头;一头身陷囹圄的献祭公羊,正用犄角顶撞板条箱。即便如此,旅客之间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坐下,他的脚搁在座位下面一个露出半边的袋子上。
他拆开“乐芝牛”的包装盒,觉得应该和周围的乘客分享这些软软的小三角。奶酪不够分给所有人,他就用橙子瓣儿补偿了眼巴巴的小孩子,这下热闹了,西班牙人纷纷拿出各自的食物跟周围人分享——黑麦面包块、自制奶酪,比他给别人的好吃太多了,还有刚用折叠小刀切下的腊肠串,装在皮质小酒壶里新酿的红酒——游走于乘客手中。
疲惫向他袭来,面包和红酒仿若一顿圣餐,他睡着了,靠在了旁边女孩的肩上。她一动也不动,不想弄醒他,当他醒来时,她不好意思地抖了抖肩,周围的人起哄说他在她身上睡着了,得娶她为妻才行。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女孩。大眼睛,面目和善,黑發上披着一条红丝巾。她永远是他的西班牙新娘。或许他也曾忘记,但是和那位想不起是谁的女子约见时,他又想起来了。就这样,他等了三天,在画布上勾勒着想象中女子的肖像。他的手仿佛比记忆知之更多。
4. 品尝红酒
到了约定日期的那个下午,他准备尝一尝那瓶红酒。他把画笔洗净收好,和每天结束工作时一样。他从不把未完成的画搁在画架上。他不喜欢让别人看见,绘画早已是他一个人的事,必须每次都从头开始准备。在咖啡馆桌上一边画画、一边和朋友聊天的日子太过遥远,如今他们天各一方。虽然画架上的还称不上是一幅真正的画,但确实留存着消逝时光的残迹,他用这幅自认为完成的画作替换掉那些想象出的肖像。这幅画是很有冲击力的红色,间有橙红的瘢痕,要说它是什么,大概是对火焰的书写吧。
而那些画着肖像的画布,甚至都没有什么可能的意指,无非是些支离的碎片而已:眼睛,嘴唇,红色丝巾下面的黑发。无非是会被白色油彩抹去的东西而已。但必须等到事情明朗以后才能把它们抹去,那就是陌生女人的身份与他刚被唤醒的记忆之间的关系。他把肖像画和其他未完成的画归置到一起,朝墙立放着。然后,等品尝完红酒,他就去洗澡,剃须,更衣,等待过去来临。他有一种预感,命运正在变为现实。那时他才意识到“玛达莱娜”这个名字与玛德莲酒庄之间隐秘的联系。的确,这瓶留给未来的红酒,是时候打开了。哪怕只是为了证明未来确实存在。因为“未来”从来都是一种信仰,而非一种证据。
酒塞轻巧地旋出。他的手有点颤抖。这还挺奇怪的。他画画时从不会这样。有时他会碰倒东西,也越来越不修边幅,但只有这时候他会觉得自己老了,画笔和刮刀已然是他的义肢,让他青年的手更为强壮。这也意味着现在他画画不需要去想画些什么了。即使内容不同,画与画总有相似之处。他的作品一眼就能认出,评论家和买主都这么说。他的作品完成即售出。人们称他为大师,好像“大师”就是他的姓氏,好像除此之外别无他名。他常常出现在著名人士的行列,就在记者列出的名单底部,那偷懒的“等等”以前。这是忠诚的证据吗?这就是那位与他失联的陌生女人所谓的没有违背初心吗?他苦苦追寻不凡、规避相似的那段时光已然逝去了。
他很讲究地点了一支蜡烛,把它放到刚好能照亮瓶体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看见葡萄酒倒入水晶瓶时缓缓接近瓶口的样子。他注意到酒体的颜色已然黯淡。许是放了太久,看起来失去了醇厚的质感。他闻了闻,有酸味。他往杯里倒了些,尝了尝。已经不是红酒了。只剩个红酒的残影。他把杯子放在红酒瓶和水晶瓶旁边。熄灭蜡烛时手仍在颤抖。
他坐下来。
平静了一会儿。
画室的小冰箱里通常放着香槟。可以提起买主的兴致。不算惊喜也不是惊吓。等那位陌生女子来了,他会打开一瓶香槟。
他打开电脑查看邮箱,想要删掉和陌生女子的往来电邮。她等会儿就到了。
但他没有。他决定不删了,又关掉电脑。时间还来得及,要是他立刻出门,家里就没有人了。
他走出去,把门关上。这样她来的时候他并不在家。
但是他把钥匙留在了门锁里。给命运一个机会。
5. 河岸
他不想见人也有一段时间了,不单单是逃避这位陌生女子。他避开了主要街道,因为那儿经常会碰到熟人。他不知道还能去哪儿,不知道自己正往哪儿走。
从家出去很远,他才发现出门时没有带钱,也没带信用卡、证件和装这些东西的钱夹。他身上是墨迹斑斑的工作服,还有一身汗没来得及洗去。他焦躁不安,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没有公众身份,还走在自我实现的路上。他方才意识到自己在往河边走。可能是长期习惯使然,他年轻时的习惯。夏天拖缓了时钟,白天延伸至原本属于夜晚的时间。如果脚步快些,还能赶得上河边的日落。太阳在水面上纵火。他现在很少去河边了,去的话也是坐车。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坐车去就像被装进一口棺材,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毫无停顿。看着将尽的日光铺洒在想要成为大海的河面上,却不能用脚掌踩一踩它。他已经不记得入夜时分城市的味道了。不记得鸟儿从远处飞来,带着夜晚寂静的声音。不记得如何观望寂静,如何融入夜晚寂静的轮廓,如何深入夜晚,在被寂静包裹的轮廓之中找出隐藏的色彩。
之前有段时间,这里有一处断墙,流水从缺口打开一条窄路,仿若一个从未完工的码头,一座倾塌在河水中被岁月侵蚀的石桥。他常去那里。一片愿望之地。仿若另一条河流的入口,一条无边的河流。那时他还年轻,是在流亡之前。那时他喜欢看船,看船的小窗亮着灯,消失在远方,看河流变成大海。想象着自己坐在船上,渐渐进入黑暗,或许自己能过着船上其他人的生活。他现在记起来了,觉得一切仿佛就在眼前,某个夜晚,在那座倾塌在河水中被岁月侵蚀而今消失不见的石桥上,他被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占据了,他在河上踽踽独行,不知去往何方。城市被永远地抛弃了,连同身后全部的生活。但眼前的城市也是河流,正延展成另一片遥远的海,零星的街灯和爬在山丘上散漫的房屋,如同海浪间隐现的船只。
就是这样,那时候,就像是回忆一个第一次做的梦,漂浮的身体在虚晃中摇曳。他听见心脏在跳动,在停滞的时间里。河水黑浑而稠密,在两岸的灯火间。他感到面部一阵痉挛,双手颤抖,颈后一阵重压紧锁而上,把他往河里拖拽。他朝市区的方向猛跑,但城市越来越远,他能听见的只是自己的脚步声。一阵连续的低吼脱口而出,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然后转为一声尖叫,消散在他自身的黑暗之中。他靠在碰见的第一棵树上,此时已远离河岸,到了城市边缘的房屋,公路的另一头。一阵巨大的疲惫从他的下腹爬升。这个描述十分色情,却又十分恰当。彼时,此时。因为此时,在某个瞬间,就如同彼时,如彼时一般苦闷地年轻着。
但是现在河岸修砌得一片整饬。石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接连不断的露天茶座和餐馆,情侣长椅,自行车道,不知道要跑步去哪儿的厌食爱好者,设计精美的观赏灌木,高大的公用灯柱,开阔的视野范围。这里没有角落,没有危险,没有惊讶,一片光明。没有惊恐的理由或者抗议的动机。青年男女在公共场合接吻。在摆姿势自拍。有笑容。有满足。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加美好。这是好事,当然了。这都是依靠进步得来的。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的权力,依靠当权的人民。以前好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这样,后来人民不再掌握权力了,或者说权力不再惠顾人民了。
即便如此,他也還希望能留下几处神秘的、鲜为人知的地方,那里有河水延续着很久以前未能达成的旅行愿望,向往的生活,许多种恐惧,四周盘踞着死亡的寂静。他多次想过这件事,他不止一次地发觉,年轻时,死亡比现在年老以后离自己更近。那时候有些朋友为了逃避死亡选择了自杀,为了不向不可避免的死神低头。或许并非如此,只是当时他和那些死去的朋友都太年轻,死去的人青春永驻;又或许当时那些年轻人就已经有了他现在的感受。
现在他已然察觉不到死亡与自己的距离,因为确实太近了。为了避免数着剩下的日子发疯,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两年?五年?他戒了烟。要是运气好,看收费昂贵的医生,再少喝香槟,或许还能再撑个十年。像极了获刑的囚犯,在美国的监号里,靠一连串的司法手段推后行刑日期。与此同时,身体也做着准备,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适应。今天是这里一块肌肉,明天是那里一个器官,然后,某个时候,也许就是活着的念头。但他觉得自己还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那个念头还没有和身体同步。他还不是他想要成为的人。镜子在说谎,镜子里的长者看不出是谁。然后,他背过身朝着灌木丛最不显眼的地方释放掉膨胀的前列腺早已承担不起的液体,像一只谨慎的小狗。最后一阵抖动完毕,他发现自己饿了。天终于完全黑了,热气减下几分,快12点了,餐馆里除他以外的人聚在一起咀嚼着,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进去。
现在要回家吗?对,当然,他想起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事。他没打算做饭。奶酪,面包,最多再加个炒蛋。用舒伯特或者莫扎特伴奏。或者做个快手千层面,煮上四分钟就能咬动,只加黄油和帕玛臣干酪粉。倒一杯新开的红酒,没有什么暗喻,然后洗澡睡觉。那个从阴影里走来的可怕女人,就算是看见了门上的钥匙,进门等过他,现在肯定也走了。毕竟她是一个没有钢琴的钢琴家。但他还不想回去。于是又走了一会儿,往没有餐馆的地方,想找一张长椅坐下。啊,那些青年男女的恋情仿佛是永恒的。他们在用舌头做奇异的事,甚至能够在气喘吁吁的间歇用舌头说话。仿佛生活不仅仅是上一场死亡与下一场死亡之间的空间,不仅仅是联结死亡两端的带扣。因为有爱,它才能伪装成死亡与死亡之间的生活。茫然的月亮挂在空荡的天上。
他找到一张无人光顾的长椅,坐了下来。那里看不见河,倒也不值当继续看它。他躺下去,两腿蜷起来缩进长椅。合上了眼睛,就这样待着,半睡半醒,把远处断续传来的声音和他脑海中聚合的图像合成入睡时梦境的碎片,年轻的晚风轻抚着他衰老的身体。
6. 守护天使
一个声音叫醒了他:
“您还好吗?需要帮忙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收回长椅上的腿,费力地坐起来,试图起身,然而腹部僵直,肌肉松弛。
“别动了,就是看看您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
他知道她把他当成了流浪汉。这位女子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内在美丽,正待发现。她的长发绑在颈后,身形瘦削,穿牛仔裤、宽松针织衫,颈上系一条红色长丝巾。猜不出她的年龄。可能长相比实际年轻,也可能更成熟。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她还没他一半年龄大。
“不用了,没事,我很好,谢谢。我只是在休息。”
“您打零工?还是画画?”
“您怎么知道?”
“嗨!T恤和牛仔裤上的油彩呗。生活挺难的吧?”
“嗯,是……最近没什么新鲜的能画……”
“所以现在没地方过夜。您今天吃过东西吗,我能帮您吗?我可以给您买点东西。我不会给您钱,但这边有不少餐馆。我可以带您去,买点您想吃的。”
“您也叫玛达莱娜吗?”
“什么?什么意思?不过随您叫我什 么……”
“我在开玩笑呢,抱歉。”
“那个玛达莱娜是对您不好吗,还是对您好?”
“我还不知道呢。不过您看见我为什么要停下?您是经常帮助流浪汉吗?难道你是这里的守护天使?圣心女神?”
他繼续用调侃的语气说着,无意冒犯。她也没有生气,顺着他说:
“您说得对,真抱歉。我不该打扰您。毕竟您也有自尊心。不好意思……”
“对啊,自尊心……不是这个意思,应该道歉的是我。”
“……不过我觉得您和一个人很像。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您。”
“不稀奇,我总是和别人撞脸。”
“不,不是您和人撞脸,是您让我想到了一个熟人,我认识的……”
“好吧,那您在这坐一会儿吧,证明您没生我气。”
“好,但我不能待太久。”
“他也是画家吗?”
“谁?哦,他呀。不是。是,他什么都做会一点儿。后来他失业了,转行失败。”
“那巧了,我也是。”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小。现在我知道您……我搞错了,抱歉。可能那时候我把他的年纪想得太大了。那是一年暑假,在阿连特茹,我祖父母家。那个大叔到处打工,做些零活儿。他跟祖母叫我小姑娘。‘那个小姑娘,让我发笑。他教我画彩铅画。‘铅笔的复数是什么?铅笔笔吗?我每画一幅,他就照着我的画给我讲一个故事。最后,家里的活都干完了,祖母就给他找些琐碎的家务做,好付给他钱,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直到起了一场大火,我的祖父母没了。祖母被割了喉咙,伤口横贯脖颈两头,就像戴着红宝石项链。因此那个大叔被捕入狱了。多不公平啊,凶手不可能是他。是我梦见起了那场大火。”
“但是那个大叔……那个工人,和我很像的人,这个故事,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真的有那场大火吗?”
“是的,在我梦里。但是我祖母的红宝石项链消失了。而他一言不发,再没有故事可以给我讲了。而我也画不出画来。您知道阿连特茹经常发生自杀事件吗?有很多老年人自缢。所以您看,我才不是什么守护女神,我打扰您纯粹是有私心,真抱歉。我只是想起了这些旧事,或者说我是寻仇女神吧。她们从不宽恕。我不知道我应该向谁寻仇。”
“复仇向来始于家庭,对不对?亲近都是给别人的。”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突然间我们一无所有,家破人亡,在革命以后,土地改革以后。您知道吗?那时候我刚出生。我祖父之前参军打仗,在非洲总是半夜惊醒,噩梦里要么是杀人,要么是被杀。我父亲就是这些噩梦的孩子,出生在这些死亡之中。所以他从没有存在过。所以母亲和我突然间一贫如洗。仿佛这也是我梦见那所失火的房子酿成的错误。所以我报读了传播学,这是有志向的穷人才学的。‘有利于社会阶级流动,那些不需要流动的人一般这么说。现在我在一所学校教书,那里的孩子们都不爱学习。我带晚课班,没有人愿意上,因为下课太晚了。虽然对别人来说很晚,我倒觉得还早。所以现在您对我一清二楚了,比我知道您要多。我只知道您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没关系,也许这样更好。好了,现在我得走了。晚安。”
“但是,听我说,告诉我,先别走。为什么要用‘所以?这一切,这些对您来说都是‘所以吗?”
“什么‘所以?”
“您告诉我的一切。这些真实发生的事穿插着小时候的梦。梦境,大火,祖父参加的战争,被割喉的祖母……不存在的父亲,陷入困境的母亲,刚出生的您记着这一切。时间线对不上啊。都是您杜撰出来的吗?和我很像、到处打工的大叔。或者说和他很像的我。您画的画和他讲述的故事……至少那些画和故事是有关联的吧?”
“啊,那些画。是的,有时候是。但只有我听过故事以后才是。他的故事填补了我画里的空白。所以,他们才有关联。”
“所以现在您讲故事,不画画……”
“不是的,我和您说了。我现在给不爱学习的小女孩、小男孩上课。但您注意到不公平的地方了吗?故事的作者认识故事的角色,决定他们的命运,但是这些角色却不认识他们的作者。”
“……现在您讲梦里的故事,那场大火就是一个。您杜撰故事,您也在杜撰我,对不对?您写作。您是诗人。”
“我祖母才是。我想成为诗人。我喜欢诗人。但是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也是诗人吗?”
“我不是。现在不是了。但我觉得您应该是,就像没有原因的结果。那是诗歌该有的样子,您不觉得吗?或者绘画。应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全部。”
“就像您本来应该叫我玛达莱娜,是吗?”
“好吧,也许是。但是听我说,刚刚您邀请我吃晚饭来着。”
“啊,是啊,当然。抱歉。我已经吃过了,但是我可以给您买点东西。您想要什么都行。要是您需要,要是您想的话。”
“太好了,谢谢。但是今天就算了,明天吧。就在这儿,还是这个时间?晚上12点。可以吗?做我的客人。”
“今天已经是明天了。”她说。
见她走了,他说:
“可您还没说您的名字呢!”
她远远地笑了:
“什么?玛达莱娜,不是吗?没有原因的结果。”
他觉得最后听到的是这些话。
他又躺回了长椅,看着似画一般的词语。他一直躺着,直到预告清晨的微风催他回家,零星的人影急匆匆地消失在远处。如同曾经他和死去的朋友在空荡的城市里漫步,直至夜晚的方阵来袭。
如今他踽踽独行。
7. 红宝石项链
钥匙还在门上。
所以他称为玛达莱娜却没什么印象的女人没有进过屋。她可能按过门铃,等了一会儿,又按了按门铃,最终放弃了。或者她看见钥匙,进了门,在屋里等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她把钥匙留在了门上,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但是,这么说的话,她也可能还在屋里。胡说,当然不会。他觉得很荒唐,自己竟然陷入这种恐惧,而且还像孩子一样逃走。但他又觉得自己年轻了,熬了通宵虽然疲惫,但却很清醒,也很兴奋,因为遇到了那个女孩。她肯定不是玛达莱娜,她那么说只是为了逗他。杜撰那些梦里的大火啊,时间对不上的凶案啊,也是为了逗他。
那个女孩喜欢艺术,或许她从报纸上、杂志文章里见过他的照片,甚至可能看过他的展览,见他像流浪汉一样躺在路边,就编了其余的故事。这小妖怪。可能她就是和他通信的玛达莱娜。他们虽然没在画室见到,却在河边碰到了。一个追随而来的仰慕者。有可能,这种事也有。一段并不存在的往事令他容光焕发。不管怎么说,他都感觉状态更好了,充满活力。他有几十年没熬过通宵了,更别说挨饿。现在他只想用咖啡和烤面包片开始这一天,和每天早晨醒来一样。
但是刚把门打开条缝,他就看到走廊有亮光,灯光似乎是从画室照出来的。他确定自己走的时候没有开灯,那时天还大亮。他检视四周。似乎一切都是出门时的样子。但确实,有一盏灯开着。是画架上面的灯,那盏灯他从来不开。他只在自然光下画画。他还在油彩的气味里闻出了残留的香水味。不过,也许那根本不是香水味,或者不是刚留下的,而是其他香味长期积累而成的气味。那盏灯或许也是他顺手打开的,着急出门,还以为自己在关灯。红酒瓶,水晶瓶,酒杯和蜡烛都还在他放在桌上的托盘里。这都是发生过的事,真实可感的证据。但他也发现画架上正放着那幅肖像草稿,畫着他想象里的那些女人,可是他记得他用完成的画替换掉了这幅啊。好吧,是的,也可能是他当时想这么做,但是最终没有碰那些画。
画中的一个女人颈上有一圈红色小圆点。像那些面墙而立的旧画拥有的神圣光环。或者说像一串红宝石项链,占据了原本属于颈部的位置。像河边遇见的女孩说的那样。于是这张脸变成了被割断喉咙的血腥画像。这他绝对没有画过。并且,在这些面孔之中,他觉得这张最像那个女孩,最像他遇见的摄人心魄的妖怪——不,是她遇见他的——半夜,河边,游移不定,他是谁又不是谁。死亡的年轻的面孔。所以河边的女孩就是年轻的玛达莱娜,他想不起她是谁也不可能想起,因为他从不认识她。是的,他逃避死亡的年轻的面孔,是为了三日之后的遇见。因为明天已经成为今日,如她所说。他还想起了她关于角色和作者的看法——作者认识角色,角色却不认识作者。他当时没有评论,没太在意,但是的确,他同意,正是这样角色才能够永远保持年轻,就像死去的人一样,他们活在书里。或许也是因为这样他才想不起与他通信的玛达莱娜。因为她想象着他年轻时候的样子。而他则是一幅画,属于她那时正在讲述的故事,就好像是那架钢琴,而她终于成了钢琴家。因为明天已经成为今日。
所以,现在他想着,所以……
所以没有所以。所以最好去睡觉。
8. 大火
所以,要是那晚他做了什么梦,梦境应该是这样的:他正在他房前的院子里,院门关着,但不是不带院子却藏在街边庭院里的那所房子。院子的边墙上,有一些横向的缝隙,从那儿可以看见染红的残云。他既不能走进家门,也不能到街上去。栅栏院门锁着。然后,房门自己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个男人,是他自己。他们相遇了。这个“他自己”拿着院门的钥匙。他穿过院子,打开院门,独自走到街上,云彩是从街边房屋直冲而上的火舌,房屋则是情侣被砍下的头颅,相拥在凝固的血河之中。一个面部遮着红丝巾的女人站在房门口,叫他进屋,她就是那个早就在屋里等他的人,躺在一张烟床上,那床是河上的吊桥。屋内一片炽热的光亮,宛若日出,但是方向不同,是从屋内向外,像是从一面镜子或是一个地洞里来的,像是一盏油灯。她对他说道:“我们已经历过很多轮回了,几乎穷尽了生命的全部,也几乎穷尽我们全部的生命。这不是一回事,对吧?我们正在抵达词语字迹间的空间。我们又可以重逢了,您不觉得吗?一如初次。我能去拜访您吗?提前三天告诉我就好。为了第三日的复活。”于是他明白,若是除去她脸上的红丝巾,他们两人其实早已死去。然后,梦中的大火与大火的梦重叠,而他将会听见有人敲打屋门的声音,消防警报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远处唤他的名字。
责任编辑 许阳莎
①一种古老的稿本,旧的字迹可以擦除,存在于新的字迹之下,可以通过化学方法复现。
①原文中使用法文之处均为斜体,译文处理为楷体格式。——译者注
②1968年5月爆发的法国学生运动,也称“五月风暴”,引发了大范围的罢工罢课。
③期酒(法文en primeur),指在年份酒上市一年或18个月以前先行付款购买葡萄酒的方法。消费者有机会在当年的葡萄酒还在木桶里尚未装瓶时进行购买,期酒价格可能比它装瓶后在市场上出售的价格低很多,不过这也不一定,葡萄酒也可能贬值。
埃尔德·马塞多(Helder Macedo,1935— )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小说家、教授、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人生经历特别国际化,且充满起伏和不定:出生于南非,后随父母前往莫桑比克生活。12岁上,又随父母回到葡萄牙生活和学习。曾修读文学与历史专业,读书期间钟情于诗歌,开始诗歌创作。后因反对“备受争议的”安东尼奥·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诗歌创作受到干扰,作品被禁止发表,正常生活也失去了保障。在此情形下,他于1960年不得不流亡英国。1960年至1971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撰稿人。其间,考入伦敦大学修读文学专业并取得博士学位。1971年起在伦敦国王学院任教。萨拉查独裁统治结束后他有机会回到葡萄牙,并于1979年担任葡萄牙文化部国务秘书。
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马塞多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同时也赋予了他宽广的艺术视野。接近老年时,他厚积薄发,开始推出一部又一部作品。1991年,他以非洲经历为主题的首部小说《非洲碎片》出版后,获得不俗的反响,已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葡萄牙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品。欧美评论界称赞马塞多的虚构类文学作品是葡萄牙当代最具风格的文学书写。2018年,他又凭借专著《卡蒙斯及其同时代人》获得葡萄牙迪尼什国王文学奖。
《夏夜》是异常凝练、细腻、丰富而又内在的短篇小说,一如作者曲折人生的浓缩和结晶。一位神秘女子发来的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一下打破了老画家正沉浸于其中的人生的“寂靜”。于是,追忆开启,思绪回溯,意识漫游,老画家开始“追寻消逝的时光”。青春,爱情,战争,流亡,革命,艺术历程,疼痛记忆,像“倒置的时间”,更如杂乱的碎片,重现于他的脑海。作者并未打算讲述任何完整的故事,小说中只有片段,只有点滴,只有空隙,只有意识自由地流动,但哪怕从片段,从点滴,从空隙,从意识流动中,读者也能通过发问窥见或捕捉到一段段动人故事的线索。比如,那个他一离开葡萄牙便立即嫁人的女孩伊莱娜。他们明明相爱,可她为何突然决定“为了被人所爱,不再爱他”?比如,他已定好约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为何又临阵脱逃,去到河边?再比如,那位唤醒他并给他讲述大火的故事的“守护女神”,究竟是现实中的存在,还是梦境中的幻象?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充满了各种隐喻、象征和暗示,钢琴、大火、红酒等等,那么,小说本身是否也有可能是个隐喻,表面上讲述一位神秘女子在画家心中引发的波澜,实际上是在讲述一幅画或一件艺术作品的完成过程?而一幅画或一件艺术作品的完成过程和人生绝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有时候就是一场人生。
沧桑目光,忧郁质地,诗意氛围,哲理沉思,使得这篇耐人寻味的小说散发出贴心、迷人的气息。作者显然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而是自然而然地调动起隐喻、暗示、跳跃、留白、心理分析、梦境、意识流、超现实等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突破了现实和梦境、时间和空间、死亡与复活、艺术和人生、记忆和遗忘等各种边界,让这个“夏夜”变得神秘莫测,似真似幻,却又诗意盎然,仿佛“是对于一场遗忘的记忆。是突然浮现在白色画布上的古旧字迹,是一个没有钢琴的钢琴家。是一个没有原因的结果。是一段遗忘的暗喻”。留给读者的则是互动,是想象,是对人生诸多基本问题的持久思考。
高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