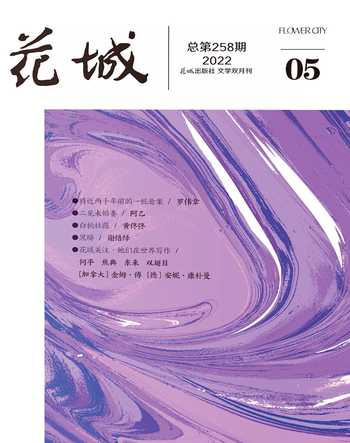海涛汹涌
[德国]安妮·康朴曼

康朴曼的长篇小说《海水会涨多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巨浪滔天的大洋中,一个石油平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暴风雨的袭击。钻井台机手文策尔·格劳查克(即瓦克劳),在那个不祥之夜失去了唯一的挚友和生命中的依托。文策尔首先前往匈牙利,将朋友遗物交回其家人。在那里,他回忆起自己卑微的生命起点:昔日的困顿、童年时代的采矿小镇,以及多年前他留下的米兰娜。现在她情况如何?他还该回去继续他的钻井生涯吗?他将工作服抛下,驾驶一辆旧车,带上信鸽从意大利出发,穿越阿尔卑斯山,来到一个被废弃的工业区。他一步一步地在靠近米兰娜,这是他的初恋与挚爱!他跟米兰娜靠得越近,就越不确定他们的这一天会否到来,他对未来就越感到迷茫!
康朴曼的小说,用词简洁,出人意料。她以富有感性、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为广众所不知且陌生的世界:“她以自己独特、不同凡响的新声音,创作了这部处女作。”
小说《海水会涨多高》出版后获得德国出版人奖,还被提名美国最重要文学奖——国家图书成就奖,并冲刺莱比锡书展奖和德国图书奖。《海涛汹涌》为小说的第一个章节。
亚瑟·米勒言:威廉, 你家门前就是一片新大陆!
外部世界的风暴,并非因为人类的存在而生成!假若你来自遥远的他乡,这里将会长夜漫漫。排山倒海的巨浪将把疾风骤雨吞噬,将闪电吞没,一切闻上去像金属、像咸盐。然而人类或已不复存在,没有了如初的嗅觉,眼睛业已消亡,唯独如山的惊涛骇浪一次次崛起,匮失去了南北走向。大海吞咽着风暴自身的咆哮,不再会有耳朵来倾听。黑暗,高耸入云的海平面;巨浪,在漆黑的暗夜中炸裂。于远远逝去的后方,绝无仅有的星光闪烁,被波涛吞灭,留下瞬间即逝的光亮。
坎塔雷尔
他们沿沥青道上修长的马路线前行,马蒂亚斯健步在先,鼓风机旋叶的风把他们的衣衫吹得紧贴在身,仿佛难以感知的劳顿及秋毫不察的困惑,只有马达的轰鸣。离得远远的,在那直升机机坪的背后,他瞥见防波堤一道白色尖顶,海浪肆虐其上。远处咆哮的灯塔,惊涛拍岸,轰然崩裂。
清晨,乌云密布,从法罗群岛的大西洋上空,一场低压的风暴呼啸而来,朝着摩洛哥海岸直扑过去。几天来,甚至已是几周,这里是暑气蒸腾,人们在直升机机场的板条凳上慵懒而卧,他们对一切浑然不知。油毡垫上的可乐自售机,上方灯光闪耀,人们翘首以盼直升机的到来已久。
与上次凌晨5点不同,那是他们黎色蒙蒙中从这里出发。今天马蒂亚斯第一回看到别样的西迪·伊夫尼直升机机场。天色尚未放明,而候机大厅已人满为患。大把男人把自己的旅行袋推向安检。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味,乘客不苟言笑。有些是昨夜才抵达的拉巴特,继而向南远行。在他们到达之际,大海依然灰蒙蒙,无际无垠。风很大,以至于他们为了抽烟,自觉进了小屋,像是已经登上钻井台甲板,进了封闭的房舱。在那里,桌子和长凳都被死死拧在地板上。
马蒂亚斯紧挨着瓦克劳跪在地板上,当第一架直升机终于着陆时,他仍然在旅行袋里翻腾东西。人流穿梭,那些大男人越过玻璃门,鱼贯而出。那扇门悄然无声地不停启开又合上,门框四周散发出蓝色光芒,有如来自一把精致的剃须刀片。
有人把行李扛上了肩,也有人戴着墨镜。在等候大厅明晃的灯光下,人人显得步履沉重且冷峻。瓦克劳只跟他们其中几人有过交情。钻探工作已开始两月有余,大西洋的汹涌跟他们擦肩而过,正向着北非大陆架啸鸣而去。他们钻穿了离海岸八十英里的砂岩、玄武岩,结果除泥浆和岩石,一无所获。
就是底下有石油的话,还得钻得更深更远。虽然一开始就有人提醒告诫过,然而,只要尚未在其中一个钻井眼里有所发现,他们就会一直神经紧张,接下去的流程会更为艰难。这里不像在墨西哥,不是在坎佩切海湾,这里是坎塔雷尔。在坎佩切海湾,人们只需不停地用新钻轴刺进鼓胀的油包,就可以守着钻台酩酊大醉几年,像极了马蜂刺破暮秋后熟透发酵的瓜果。
然而此地非彼地。上了岸,男人们个个精疲力竭,神经异常敏感。一件行李高高飞过,一只大小形如海豚抑或野猪的旅行袋。喂,布达佩斯,几乎在最后的刹那间,马蒂亚斯举起双臂去接,旅行袋重重地在他跟前砸落在地,他满头的卷发跟着朝下甩去,他俩瞬间相对而视。喂,德克萨斯,紧接着气壮如牛的弗莱施贝格说着朝他扑来将他拥住。
“屋外的天气简直是见了鬼了!”特雷弗说,“看来你是绝对不可能玩帆船的了。这场暴风雨要是再这么下去,我看港口非给关了不可!”
他嘴里嚼着一块肉干,他的英语实在“佶屈聱牙”,说起话来好像在搬动成吨的岩石。
那位新伙计怎么样?馬蒂亚斯问,罗伊站了过来,瞬即围成了一个圈。这些人有的刚到,有的要启程。行前,谁都被极度的疲乏困扰,被浑身的臭汗折服。瓦克劳不由得想起场面宏大的赛马,想起新手赛前的紧张和马被三名马师牵过来时神经质的颤抖。骑士弓腰曲背,坐驾其上。还有那些钢架,后面的观众在奔马飞驰而过的瞬间被隐匿在赛道里,一股汗马的骚味随气流飘逸而来。
是个娘儿们,罗伊这时喊,难道你们有谁在屋外见过打领带的?30年都不会有这种事!
看起来,是非他莫属的了——他将眉角拱起,拿手指搁在嘴里咂巴几下。那些男人不禁开怀大笑,还有拍手叫好的,互相拍拍肩膀,而罗伊却依然神情严肃。我的意思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该拿他怎么办,他说。他要当着我们的面结账?
他最后的几句话说得很轻。他将目光转向瓦克劳。那些人毕竟还是年轻,他道,他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大家在一起又待了一会儿,接着,玻璃大门在那些刚才等待出发的人身后关上了。
西风
今夜的大海兴许是你所能遇到的最为黑暗的一次。月亮被厚重的暴风雨云层遮挡,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山脉一样的海涛所筑起的黑色与地平线别无二致。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做着深呼吸。然而风,从波涛及咆哮中汲取能量,鞭挞着海涛的浪尖。
背后远远的深处,被摇撼得不能安宁的钻井台,高高的钢柱支撑着,死死铆足了劲拽扯着埋入深深海底数米以下的销轴,对汹涌澎湃的深棕色海浪散发着明亮的光环。
这已是上班后的第八个钟头了,狭窄的踏板上,他把自己绑紧在安全带上,用双臂牢牢抱住钻井塔的支杆。咸涩的潮气如同一股强有力的重吸力将他重重包围。已经有些时候了,他一直等待着停止作业的信号。要是换了裴波,他肯定早就发信号了。但对新来的钻井领班而言,这像是无关紧要。他情愿让工友们喝个酩酊大醉,也不愿意中断钻机。瓦克劳可以感觉到海浪撞击在钻井台支脚上的响声。他们将会撤离平台,他这么想,然而现在已为时过晚,眼下只好再耐心等待了。当雨水在探照灯灯光前几乎平行扫过时,除了对焊缝的拉拽,撞击着钻井平台的大海,酷似发了疯的野牛群,加之在风暴中突奔的海浪,一切的一切都朝他们袭来。
朝下方的转井盘远远望去,他看到有人在呼喊,他能看到他们的嘴巴在翕动。然而他唯一能听到的叫喊是风暴声,是海浪的怒吼和那只海鸥徒劳地展翅扑腾。海鸥一次又一次地扇动双翼,翅膀下摆闪烁出白色光亮。
差不多过了半小时,信号才响起,作业停止了。他刚才是将身体支撑在狭窄的踏梯上,就这么坚守着,才忍了下来。
所有其他的钻工都退了下来,有人打开沉重的门,进了小屋。他看到门缝的亮光,第一批钻工走了进去。他的四肢已被冻得冰冷,他步履蹒跚,身子僵硬。他的双脚像是测量着地面前行。每个梯级都灌满了水,海水早已悄悄渗进了油布下面。在他返回钻台甲板之前,瓦克劳其实已经冷冻过度,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屋里的灯光显得明亮晃眼,空气温煦宜人,甚至在他们用架子搁放靴子和晾挂工作服的小间里,也是温暖惬意。当他来到大家中间,心绪似乎欢畅了起来。这是一支新的团队,其中只有少数几位他相识已久。比如阿尔伯特,他坐在靠后的旋转餐桌边,在发号施令,他在这里说话一言九鼎。
暴风雨恶劣的情绪有增无减。瓦克劳一声不吭地把脚塞进浴用拖鞋,沿着狭窄的走廊进了他们的小房间。灯光闪亮,然而马蒂亚斯的床是空的。他们的被褥放在下铺,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马蒂亚斯躺在那里,但床上并没有人。耳机垂到了地板,随身听留在枕头边。他用手绕着电线,唤一声:马蒂亚斯?没等得及有人答应,他已开了浴室的门。当时是凌晨4点。他打开热水龙头。
他赤着脚,浑身依然是湿漉漉的,他来到他们的床前。
盖了两床棉被,他仍然觉得皮肤潮湿得不行。暴风雨似乎顷刻间退得遥不可及。他等待着。溫暖的感受使他觉得浑身疲劳,从傍晚到现在他还没有吃过东西。这对他来说也是破天荒的事。是钻井总管将他们分在了不同的班次。
每次来到走廊上,在成排的霓虹灯下,他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出奇的苍白。当他来到餐厅时,围坐餐桌的那些男人默不作声,转身都坐去了酒吧台。在他转过脸去时,在沾满调味酱的塑料瓶后,他注意到了那些人在打量他,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在远离他们的一旁,坐着弗朗西斯,他脸色苍白,略显神不守舍。他是一只病了的海鸟,正蓬松着羽毛,为最后的几天在做准备。
他密切留意着开吊车那人的每句玩笑,那家伙胖如肥猪,平常总坐在靠一旁的邻桌上声声咆哮。而在新同事面前,莎纳习惯地充分表演自己,大声叫嚷,向团队的钻探工指手画脚,让他们往灌洗装置里加进更多的液化原料。他让人取来清水,一次又一次地冲洗甲板,直到大家精疲力竭、有气无力地瘫坐在他身边,忍受着他粗俗的玩笑为止。这时他会流露出某种神不守舍的表情,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满足感。接下去他可以这么心安理得地坐着出神,眼球像是玻璃球。然而当那扇大门被人甩开时,他的表情顿时活跃了起来,瓦克劳听到的是一声引人注意、不无讽刺的口哨声。喂,喂,莎纳装模作样地问,你还以为我们在找谁呐!他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浑厚且低沉,仿佛出自一个大胖子之口,而他却神态憔悴,长相鹰鼻鹞眼的。他们是两年前第一次相遇相识。自那以后,这只挂在脸上的鹰钩鼻子一直跟随他们寸步不离。至此,包括他的双臂,他依然是浑身上下油腻不堪。
门外的甲板上,他戴着黄色工作手套,两只手形同鹰爪。那是他例行公事的讲话。瓦克劳从来不会觉察到有人会从背后注视他们。弗朗西斯静坐一旁,在大家的嚷嚷噪声中,他沉默寡言地连干两杯。因为马蒂亚斯的不在场,瓦克劳很不开心。他从保温锅里抠了两勺,搁上一片薄得几乎透明的面包片,开始吃了起来。同样,这里同样是灯光亮得耀眼。汤看上去显得过深的褐色,而皮肤被照得过于苍白。渐渐地,餐厅里人多了起来。活儿一旦停歇下来,那些人若不来这里聚餐,就回房间上床休息。
走廊里,暴风雨近乎已变得寂然无声,还有那种摇曳晃动,仿佛一切都退去了远方。从电影室里,瓦克劳能听到说话声,还有自己急促加快的脚步声。门上的铝制把手被明晃晃的塑料膜裹着。他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最后一扇门,房间里四处昏暗不明,唯独角落里那盏小灯亮着,它是不会受到气候的影响的,一如既往地灯光闪烁。他们这群工友时而会在这里邂逅,几块小地毯铺在地上,按照麦加的风格。然而,几乎没有谁来此做祈祷。
说到马蒂亚斯,若是遇上他笑声弱弱地靠在墙上,这会让他深感惊诧吗?随着那道门的开启,一束光亮落进了黑色。室内依然寂静无声,唯有地毯上留下一层无奈的寂寞。他往他们的房间走去。透过门缝,他能瞥见安德烈躺在板床上,手机形如小鸟栖息在他的肩头——还有他那便便大腹和经年破陋的浅色外裤。那首此时传入他耳郭的民谣《丽淑西客淑璐》,他无疑会彻夜回唱。
袜子和汗水浸透的背心散发出的气味饱蘸着薄薄的舱壁。也许是4点半了,黑夜,离他通常回到钻机的铁柱旁,不到三小时了,这或将是马蒂亚斯开始上班之前最后的几小时睡眠。也许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室外依然是一片漆黑得不能再黑的夜色,没有丝毫的亮光可言。曾经有一回甲板的门没关严实,海水倒流进了小屋。那是在他认识马蒂亚斯之前很久的事儿了,紧接下去的几周,室外的气温变得不一样,恍若一抹色彩,恍若一幅他能重新辨认的画面,即他们的东西堆成他所了如指掌的杂乱无章。
他越过行囊,上到自己的铺位,仰卧下来,舒展着身体。他把灯朝向自己,试图闭上眼睛。人们可以尽管放心,这副钻井台会往上浮动,他们还有足够的高度,还高出海平面12米,还远不至于轻易被海水淹没。然而世上又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确信无疑呢!这个漂浮物是钢铁,因此,在被拖来南方之前,这个“海洋君主”在北海已沉睡多年,它算半个漂流者,一个年事已高的庞然大物。瓦克劳头部上方的墙上,前任同僚留下的油腻腻的斑迹熠熠生辉。那些数不清的夜晚,在那遥远的地方。马蒂亚斯解析着钻探出来的碎末,对从积淀层底下采集上来的取样和残渣,他可谓了如指掌。他对远古时代海底生长着哪些森林知晓得巨细无遗。这些星期以来,从未有谁见过像他那样笑得如此灿烂,这是一种近乎稚童般的“海上阳光”。自第一天起,他的面部表情就让瓦克劳想起古老的扑克牌,那身着黄色服装的哈勒昆。
在宽敞的大厅里,当教官给他们上培训课时,讲述着世界海洋及其生产基地几乎漫无垠际的自由时,他将美国式的 R 发音犹如岛屿的基石留进每个句子的底部,马蒂亚斯两眼穿透教官的卷发,盯着远方,咬文嚼字地难为着每个单词。他父亲是匈牙利人,一场起义将其家人从布达佩斯市中心转移到了乡下。在那里,他在农场学打铁。铁蹄、蒸汽、小马驹、白眼,无穷尽的乡村出行,以及他叔叔车里的气味,着实令人作呕!
六年来,他们一直同住一间房。从去年起,他们告别了墨西哥湾。那里屋外咆哮不息,到了深夜成了狂风肆虐,相形之下,在大西洋只不过是大同小异。这里,紧挨大陆架前沿,傍着摩洛哥海岸线,大西洋彰显着疯狂且辽阔。瓦克劳把手伸进行李袋,掏出一件毛衣,他忽然感到寒气袭人。
他想起了裴波,想起了他们年迈的石油钻探老前辈,他因恶性疟疾的发作而屡次数周卧病不起。
有人预言,他会很快变得完全不正常。
那是靠近海岸的钻井台,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从海岸附近沼泽地飞来的蚊子,那里几乎没有风,然而酷热,没有谁能永远受得了那些用来预防传染病的药片。那时裴波来这里有多久了?他知道马蒂亚斯是喜欢他的。但当他们回到钻台上时,仅仅安德森在他的岗位上,也没做个自我介绍。他们在海岸边共同度过的那几天后,一盏明灯,如同被风刮走了一般。
他一定还在做梦,警报声的尖叫,在他的记忆里只留下了碎片、旷野的树木、几座山丘。那是马蒂亚斯的闹钟,轮到他上班还剩下几分钟。灯还开着,空气闷热潮湿,他忘了关上浴室的门。
马蒂亚斯不在舱里。风吹在机舱壁上,走廊里很安静。他们会将开工时间再停上几小時。瓦克劳把身子转向侧面,看着自己的东西,一切安然无恙,连他随身携带的装着滑石小包囊也原封没动,完好如初。
瓦克劳把被子更紧地裹住身子,他觉得当时只是闭上了眼睛一小会儿。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将他惊醒,一种沉闷、很遥远的声音,不是过道里传来的噔噔脚步声,更不是提醒继续上班、具有穿透力的信号声。这种让人不安的感觉来得出乎意料,而且强烈,它像是从浅色的舱壁上传来,从那里,日光突然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线。同样,马蒂亚斯暖人的羊绒衫依旧挂在衣柜里。
于是他给他捎上这件毛衣。那天清晨,天色放晴,浓厚的云朵像是行色匆匆地离去,越过黎明的蓝天。远处,一道银光闪耀。他给马蒂亚斯拿来了这件羊绒衫,像是马蒂亚斯嘱托他这么做的。这时,刹那间他感到机器的运转显得那么不真实。我们来了,当彼得罗夫绕过浅蓝色的油桶来到背后时,他这么说,他们在那里清理钻屑来当作取样。
他看着那些熟悉的容器,里面满是淤泥、石块和污秽的土壤,他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一切,摇筛、监控器和塑料软管,看到彼得罗夫开心的微笑,但他却没见到马蒂亚斯。你朋友今天早晨去哪儿了?
彼得罗夫摘下护目镜,直视着他,就像瓦克劳瞪着他看那样。
彼得罗夫本来还想再等等,等到马蒂亚斯自己会来。他可能觉得夜晚刚过,工作启动会来得慢条斯理一点。谁都没必要提醒彼得罗夫,昨夜的大海是那么漆黑。
他们不停地搜寻。后来,在他们找遍了每个房间、整个甲板、每个角落和每截踏梯,以及下方的救生船停放处,还有健身房,餐厅是来去查看了好几遍,连自己的房间也进出看了好几回,大喇叭里广播声不断,钻台机长对每个员工进行了例行公事的常规问话,天空云开日出、晴朗了起来,迎来了一个几乎是阳光灿烂、光芒四射的中午,像是那天的一切,还有水面上的海鸟,似乎都成了不再可能的现实,广播里还在不停地找人,有人给他拿来了热饮,而他却全神贯注地细细察看着每个钻井架,还有那明晃耀眼的海面,有人试着想把他拉进屋去,把他安置在油槽之间,让他休息。一轮光溜圆润的太阳坠入海水,那是昨天的傍晚,眼前是平坦的地平线,而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突然想起他手里始终紧握着的,正是马蒂亚斯的羊绒衫。
那天晚上,月亮沉浸在摇曳的海面上,似乎不太乐意露脸。瓦克劳躺在床上,靴子还没脱去,他的枕头上刺出几根羽毛。一个巨大的不明物,就是昨天的那个,它会把一切拽走。他站在房间里,后悔当时不该把他的耳机线盘绕在手,他略作回忆,没错,是他把耳机拿走了,像是身不由己地这么做了,那已是临近傍晚,狂风暴雨过去了,天色也黑了下来,一切如同往常。过道里他听到有脚步声,那些人身着汗水浸透的T恤衫,浑身放松地进了餐厅,他们已急不可待,膳食的香气扑面而来。他无法逗留于此,他出了餐厅。
大海可以说是风平浪静的。他们时不时地会派人来照顾他,彼得罗夫也来看他一回,给他递上香烟,瓦克劳看着他在一边无言地抽着烟。
瓦克劳说,弄不好这会让你丢了这份工作的。彼得罗夫哑然失笑,又吸了一口,瞭望着大海。
他们肯定还会来盘问你的,瓦克劳这么说。
他们是不会派人去找他的,不是吗?
我想不会的,彼得罗夫说。他们肯定不会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放出来的天然气雷打不动地继续燃烧着,一只海鸥穿越聚光灯飞过,它们有时是从油轮方向飞来的。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彼得罗夫问,你会去哪里?
他们低头望着脚底下的海水,天色渐渐地变得昏暗不明,暴风雨后的波涛,上面漂浮着微微光芒。
回去,瓦克劳说。
回哪儿去?
在他的眼睛里,他感觉像是看到了一丝微笑。
你这是怎么了?瓦克劳最后问。
老婆,还有孩子,彼得罗夫说,真他妈的见鬼了!他们谁都以为這份钱我们在外面那么好挣!他们谁都会这么想。
最后的一道亮光远远地传来,落在他下巴灰白色的胡茬儿上。
天下起了雨,水珠滴落下来,掉在他们身后空空的油箱上。海风渐起,在联动器和粗大的缆索上来回磨蹭。彼得罗夫将他的兜帽套上。
文策尔,你跟我们一道回屋吧!我不能现在就这么让你坐在这里。
他将一只胳膊搂在瓦克劳的肩膀上,这只胳膊懂得接下去的几天还会风雨交加,还会云雨连绵地扫过天空。他无法回房间去,他对彼得罗夫道了声晚安,然后去了餐厅。酒台后站着体态丰腴的卢卡斯,愣愣地出神,指间夹着厨师帽,仿佛自己是一道影子从他身边经过。瓦克劳这时注意到,那些人说话时都压低了嗓子。
米凯尔、瑞、史蒂夫,其中一人将自己的椅子向后挪了挪。
文策尔,你愿意坐到我们这儿来吗?
谢了,我待不了一会儿就走。
然而他后来一直留了下来,如同画了一道长长的破折号,守着一杯速溶柠檬茶,杯子不冷不烫。因默默无语地坐得久了,那些人裸露的胳臂都粘在了桌面上。
又有谁见过这类T恤衫,颜色鲜红抑或绿色的?而那个瑞,身着一件洗旧了的毛衣,上面印着动漫电影的图案,公主与剑。他的桌子与那些人的桌子隔开将近一米。他注意到了他们在窥视他,眼神悄悄地朝他瞟来,好像有谁的扑克出不了牌是他的过错。或是他们无法坐在餐厅跟卢卡奇直接交流。卢卡奇漫不经心地揩拭着玻璃杯,像是今天才发现了薄薄油脂背后炸过的冷冻丸子在闪光发亮。
他记不清是不是就在这个屋子。现在他让卢卡奇给他煎几个鸡蛋,而后就着带皮的土豆吃冷的。他突然间感到饥饿袭来。他不愿用叉子刮盘子,生怕划伤了盘子。这不再是他们曾经的餐厅了,尽管屋子还是原来那间。早晚地会有新的十年的到来,借着爆竹声声、硝烟弥漫的火力劲儿,他们在此饕餮、尽情玩闹,还有那马蒂亚斯,他当时还真是够年轻的,活蹦乱跳的。那时,瓦克劳在这里的餐桌边还从未有过通宵达旦。他当时突然间来到这里四海茫茫的远方,对此,他曾是无与伦比的情有独钟。
空气中弥漫着卷心菜和油煎脂肪的香味。门开了,奥尔金把脑袋探了进来。
瓦克劳,有人正找你呐!他们会给你派一架超级彪马,就在明天一大早,是从大陆飞过来的。专程为你,是超级彪马!
他听着大家七嘴八舌地插话议论,他明白,他们现在谈论的是直升机,权衡着不同型号各自的优劣性,比较之后彪马脱颖而出。他静坐一旁,洗耳聆听,卢卡奇往自己的嘴里抠着东西。随即他的目光落在门上方的黄色时钟上,11,什么意思,是晚上11点的意思,他看着表盘,感到某种东西在体内油然而生。那些人的说话依然回荡在耳畔,直至他穿过走道,进了房间,来到金属马桶边呕吐。是时三更半夜,没错,是半夜。他呆坐在那里,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这双不由自主的手,像是别人的手。这一夜,他颇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过于清晰,然而却又摇摆不定,是一幅经受磨损的图像,四周无形而难以把控。在经过一小时的谈话后,钻井队长安德森爽快地给他剩下的四天放了假。
队长依然正说着话,而瓦克劳却已神游在海鸟身上,鸟儿模仿下雨发出的声响,以引诱蚯蚓钻出地面。
他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往下问。透过安德森办公室的窗玻璃,瓦克劳看到那些员工继续他们的作业。他看到钻井台的那个转盘,那些五彩缤纷的工作服和明晃耀眼的白色头盔。海水已平伏了下来,静静躺着,向四处伸展开去。谁也没有来,没有谁会来这儿往海里扔个花圈,没有人来致悼词,什么也没发生。
在他的脑海里,每次有人告别,没有不在这昏暗的小餐厅的,加上那些暗棕色的调味酱汁。他想到的是鲁尔区沸腾的炼钢炉,那些他在孩提时就听大人讲述过的炼钢工人,在多年穿插其间的狂欢节和大杯烈酒之后,他们会大白天消失。他想到了一片炽白的烈焰,在万劫不复的战争岁月过后,紧随而来的是沉默的橡木支架,那狭窄拥挤的矿工住宅区,还有人物传记,其相比高炉里钢水鼎沸的灰烬,可谓是少之又少。
孩提时他刻入脑海、留下的画面是更衣室里的景象,和那些夜幕降临后不再有人光顾的街头鞋。
他眼前出现圣·西里亚库斯教堂的唱诗班,身穿厚重民间服装的寡妇们站成一排排。教区公益所,屋里满处都是大圆蛋糕的底座,从那一望无际的住家小花园收集来的各色水果、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有如揩净、光洁的餐盘。吟唱着波兰及日耳曼歌谣的稚童,大人们把他们的衣领烫得笔直。海浪已消停了下来,四周连色彩都起了变化: T恤衫和五颜六色的头盔,布满茸茸汗毛的腿肚子。极目远眺,尽收眼底的是一汪明亮的海水。
安德森不止一次地问他,是否想回家了。他几经重复地告诉他,作为公司应急选用的旧地址已不复存在。
然而安德森的意思却是,如果他能尽早上岸不是件坏事,这样他就能及时将人员损失报给总部。安德森耳边紧贴着电话筒,说话间提到了马蒂亚斯的名字,他的话听上去像在罗列一堆人们不再需要的东西。或许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他在力求把事情的原委讲述得更实事求是。
墙上悬挂的是一幅陌生水手的合影,拍照时用了闪光灯,此刻烁烁发亮。船员红色的工作服上、胳膊上方和腿上的反光条纹比起他们的脸更显光亮夺人。瓦克劳在尽力估计安德森的年龄,他确定对方比自己肯定要小去15岁,或许他还是年届而立。安德森的花格衬衫,衣袖稍稍往上卷起,裸露出一只浅白色、近乎油腻肥墩的手。他的身体哪儿都显得苍白,毛发稀少,他的嗓音带有铁棍般的强硬能量,像在呱呱然搅动着热水池塘。
阿列克谢泪流满面,这于安德森是不知就里的。阿列克谢因身处大海没能赶上儿子的出生,加之婴孩产后不久的夭折。安德森无法想象别人进入梦乡后会采用何种各自不同的语言。他语气平淡、无动于衷,只是频频点头。他伸手从口袋掏出一个黄色皮套,用钢笔记录下几句话,然后朝瓦克劳望望,好像是刚刚成就了一桩重要大事。
安德森告诉他,在他上岸几星期后,他会尽其所能让人安排他转去另一个钻井台。
这样您是否会感到心里好受些?
他报以微微一笑。
那他怎么办呢?瓦克劳问。
安德森惊讶地看着他。
您指的是?
瓦克勞迟疑地摇了摇头,接着指了指墙上的那张海示图。
格罗扎克先生,您清楚这些阴影意味着什么?
有那么一会儿,两人都把眼睛盯在了标明测试钻孔和钻井平台的海底地形图上。
是的,他接着说,像是心不在焉。
安德森从窗口向远方眺望。同样,他的嘴也软了下来,他不敢正视瓦克劳的目光。瓦克劳非常怀念裴波。他不禁自问,要是裴波还在,他又将会怎么样呢?裴波双手毛发旺盛,如果遇到难题,他会急得双手冒烟。
裴波对自己的团队了如指掌。在别人开怀大笑时,他的脸只报以一个优雅的微笑。然而他说话的口气,俯仰间会变得像鲈鱼的背脊骨一样坚硬。这无疑会得罪人。他从未有过像只宠物小狗跟女秘书细声蜜语地通过电话。
安德森用头朝门口示意了一下。
我的男子汉们要是看到了什么异常情况,会通知我的。
他的身子往后仰靠在扶手椅上。
我们会再去电话联系。他们的直升机大约3点会到。
而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愤怒,让瓦克劳腾地站立起来。椅子靠背拱起的位置,他用大拇指紧紧抠住。此刻安德森看到他这么直立,戛然变得沉默无声。没错,他大惊失色,其作态犹如不期遇到了大甲壳虫而惊慌失措。或是路遇莫名的声响,袭击会向他迅猛扑来。
瓦克劳就这么木木伫立盯着他。
你别犯傻!安德森低声道,咬紧嘴唇。我说话是当真的!
在回房间的途中,他突然感到四肢沉重,像是已有好几星期未曾睡眠。他用力扯开他们的橱柜,把自己的衣物胡乱地收集在一起塞进旅行袋。一共两个背包,把它们提出房间,来到甲板。遽然地,海风四起。
他爬上直升机停机坪,钻探作业还在继续,他们往海底注入更多的润滑剂,以持恒过度的压力。彪马尚未出现,他觉得行李沉甸甸的。仅有彼得罗夫陪他登上了停机坪。他弓着腰,歪扭着身子像一棵橡树,说话时谨言慎语。
瓦克劳靠在一堵墙上,注视着别人继续干活。起重机转过身来,风依然是寒冷的,然而他的脸热得发烫,他两眼浮肿。身后,他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是弗朗西斯,他仍穿着他的工作外套,肮脏得惨不忍睹。
文策尔,他说,深吸了一口气,他们刚才说了什么?你现在要去哪儿?
弗朗西斯摘下手套,像两条死鱼扔在身边。瓦克劳看得见他靴子的缘口印拓在裤腿底下。他身上对他来说什么都显得过大,衣服、头盔。弗朗西斯的形态让人想到一只皮毛被水淋湿的动物,他这时蓦然间看上去变得可怜巴巴的、一副病态。
现在他们该怎么办?他问,他们现在该拿他怎么办——他言语结巴,像是不敢继续往下说。
拿马蒂亚斯怎么办,他的名字依然是这么叫,瓦克劳平静地说。
他觉得自己扮演这个角色不对劲。在他继续往下说时,他几乎满怀好奇地留意到自己说话的口气,听上去异乎寻常的坚定。
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他看到弗朗西斯嘴唇紧闭,他的皮肤闪着亮光,显得油腻腻的,像是有些日子没洗澡了。你还记得几年前的那条小船吗?在梅赫迪亚海滨。他们都已快靠岸了。后来其中的三人始终没能找到。他们中还有一个是潜水员——瓦克劳摆了摆手不说了。
你还会回来吗?弗朗西斯急忙问。
他显得神经紧张。上班马上又要开始,他必须赶过去。尽管来这里时间已那么久,但在那些人面前他仍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肯定会的!瓦克劳拍了拍他的肩,肯定会回来的!
接着他看到他从甲板上下去,走过钻台天桥上了钻井台。这么看着他,让他感到一阵刺痛,对方迅疾消失在人群中间。
直到临近傍晚,彪马才姗姗来迟。
这儿不是墨西哥。
这句话在他脑海里已蹿跃了多少回!但他对此爱莫能助。这里不是墨西哥。大海恢复了平静,然而马蒂亚斯却不在了。
那天夜里,钻井台上留下的只是海水上方的那盏小灯光,和一道向远处延伸的黑色地平线。
他头戴用来保护听力的双层耳罩,倚靠在窗玻璃上,身上穿的是汗水浸透的求生服。在他的头顶,发动机旋转不停,他看到了那片闪亮的斑块,那是天然气燃烧的火炬,还有那被照得灯火通明的建筑顶部,越往下就变得越模糊不清。
他凝视着那块亮光,不由想到了父亲,想到了阁楼小房间和家里那扇椭圆形窗户。每当瓦克劳坐到父亲身边,父亲的肺部因受尘埃的侵蚀,咳嗽起来战栗不已。他的眼神里蕴匿着惊怵,这种惊怵与他那只抚慰着瓦克劳胳膊的手掌是何等的难以协调。他想让儿子描述的是另一种大海,一片不同于波罗的海的海洋,那里是污秽不整的渔船和房舱,以及撒哈拉热风漂洋过海携带来的沙尘,弄得他们整天牙缝里磨蹭得嘎吱作响。瓦克劳向父亲讲述着海岸线、世上最好的沙子堆积起的沙丘,它们与大海直接相连。
他们谈论的还有旅行,人所乐意向往的旅行,去那无人追踪且又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不会有人随行的地方。父亲低声细语,瓦克劳默默首肯。
走,去那无人跟随你的地方。
他尽力让自己保持坚强,如同他有生以来一直坚强那样,而后他们在屋子的暮色中久久静坐。房间是如此狭小,以至他从床上可以用手摸到对面的墙。父亲几次微微入睡,继而睁开双眼,呼喊瓦克劳的名字。
直升机在天空左右摇摆飞翔,它将在某处海岸线上找到降落点着陆,一艘船只会把他从那里带去暮色苍茫的丹吉尔港口。
飞转的螺旋桨下,他手提两只出海行囊猫腰一阵小跑,行李袋现在并排放在出租车后座,他们朝渔船方向出发。一阵清风细雨,漫卷着挡风玻璃上的尘土,留下红色条纹状。他们朝前驶去。
低矮的简易平房,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或这或那的,他不时看到车间的窗户被安装了铁栅。夜色寒峭的灯光下,背后是升降机平台和几个防守严实的库房。这里是靠近海岸的一个工业区,从外表看去,它们似乎更适用于堆放废旧材料,或用来做汽车贸易。瓦克劳困惫不堪,他身边的司机口中不停地啃嚼着吃的;他耳朵充斥着雨刷子的哗哗声,它们在挡风玻璃上拉出道道划痕。还有那些雨珠,在这稀奇陌生的街景中晶莹闪烁,被不经意地抹去,新的一波随即到来。
责任编辑 梁宝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