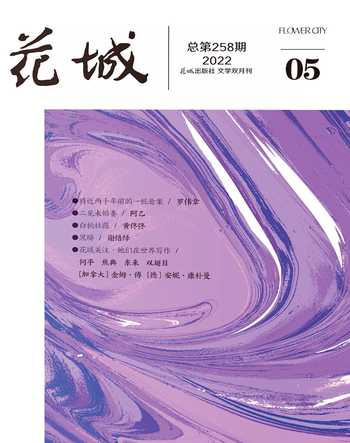六脚马
焦典

哎,我跟你讲,你莫看我是个女的,在这一片,骑摩托没有哪个骑得过我。你们不是都爱去大草原骑马吗?你坐着我的摩托,跟着这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呢,不就跟骑在马背上一样吗?
你讲我骑得不快?这你就不懂了。这里的山路这么多弯弯,快一点就翻下去,这么老高,警察来找都找不到尸体。你莫着急嘛,路还远得很,慢慢看风景噻。
对了,你晓得我们这里那场著名的猴子大战,到现在红河人还在津津乐道。
有两群猴子,一群从河谷那边游得过来,成群结队龇牙咧嘴的;另外一群就从山上慢慢地下来,一只接一只地倒挂在树上。一边攻一边守,嘴撕手挠,打得满林子的猴毛乱飞。山里面那些鸟啊雀啊的吓得全都飞起,连我也只敢远远地望着。按翻一只就往死里挠,周围那些猴子见了,也就全部围上去,等得打完走开,地上那只猴子往往血肉模糊,整头整脸都被抓烂了。你问为哪样打架?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听人说是因为原来的那些香蕉园被整成生态林,林子绿了,猴子的脸也跟着饿绿了,打仗就是自然的嘛。
跟着猴子打仗的消息一起传到我们耳朵里边的,是斗波从山边边上掉下去,摔死了的消息。他是个正经八百的当地人,这个正经也好像让斗波生下来就跟通到外面的东西有点仇,每次不管是坐板车还是面包车,都要出点麻烦,不是摔掉点皮,就是擦掉块肉呢。所以喽,听到斗波在山路上摔死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一心只想看猴子打架。看着看着,发现在那乱战的猴群中间,正奔着一匹马,左突右避,艰难向前,四条马腿都直直地绷着。
马腿绷着还怎么跑?
我赶紧大喊:“是哪样?”
这一喊,马上的人转过头来,没有提防,竟是斗波的老婆,前面牵绳引缰的人是春水,戴个红头盔,我差点以为她脑袋被猴子给挠得开了花。再仔细往前看呢?哪是什么马,不过是春水那辆吹风吃土了许久的大摩托。两人四条腿,紧紧箍在上面,远远望去,挤出马腿的样子。山路又窄,左跳右跳的猴子碍得她们,骑得越来越慢,摩托汽缸当当地响两声,低头丧气地停了下来。
自然喽,这次又是没有跑脱。
几乎都是这样的,在尿意把人憋醒之前,那辆老摩托扎扎的引擎声就已经把人吵醒。睁开眼睛,又是一天的清早。春水的老公鼾声响得跟什么似的,一双黑脚,一直黑到膝盖,板板地伸在外面。至于春水呢,早已三把并作两把洗了脸,一条腿已经跨到摩托车上去了。
春水是这附近第一个跑摩的女人,日日年年,在山路和柏油路之间转。车站、路口,摩的一排排地停起,人一走出来就乌泱乌泱地挤上来,拽包的拽包,拉衣服的拉衣服,身材小点的,还不等你说不,就已经被按得摩托上坐着了。然而春水,也不拉人也不吵架,有人来问就轰起油门走,没得人来也就趴在摩托上,手轻轻地拍着摩托,好像在安抚一匹真正的马。家里平素的开支,都在她那汽油马背上。最怕送那种拖家带口去大医院看病的,一家三四个,屁股全部压在摩托上,都要多扭两转油门才跑得动。掏起钱来,像被抽枯了的井水,挤不出多的两块,转两个山弯弯,遇到个交警,反倒可能被罚出去。
为了这一辆车,吃苦不少。大女儿去世的时候,春水还在摩托上。不知道遭了什么虫,大女儿嚷身上痒得很,大个大个的疱,抓得十個指甲里都是血。当爹的耐不住闹,拔开一罐杀虫剂,手指尖上喷喷,慢慢往女儿皮肤上抹。土方法,见效快,抹了立马停了痒。背上腿上还好说,身子前面,自己不能抹,把杀虫剂丢到大女儿手里,自己蹲门外面吸水烟袋。猛地听见摩托的隆隆声,以为春水回来了,站起来一看,是别个。那人嘿嘿笑:“等老婆呢?”懒得说话,蹲下继续大口吸水烟,水泡咕噜咕噜响。那人捏一把刹车,扎在门前,“等不着喽,载一个小白脸,故意颠起骑,骑一路,颠一路,早就颠到宾馆里去喽。”说完,拍了拍屁股灰,又扭起走了。水泡是咕噜不起来了,这种话听了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满肚子憋火进了屋,大女儿仍旧在那儿号。啐一口,“毛叫了,跟你那个妈一样,天天叫起给老子丢脸!”大女儿渐渐止了哭,待到晚上春水回家,手里拿一条白药膏,地塞米松,大女儿身子已经硬完了。春水咧开嘴想哭,被老公一拳头打在脸上,“跑你妈的车,天天在外面乱搞,这都是报应!”说完却自己哭起来,嗷嗷的,像狗叫。
哎,你也莫骂他,他一辈子没读过几天书,每天在家里帮着看娃娃,在这边男的里面已经算是可以的了。春水,春水读过书,她妈是马帮红颜。你不晓得马帮红颜?这是说了好听,其实就是没了老公的寡妇。说是她爹以前跑马帮,有一些钱,可惜有一次走烟帮就没回来,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跟那些没良心的一样在别处找了新的,这种事都是很常见的。
哦,斗波,你是问斗波的老婆为哪样要跑?这种事,我也不好和你直接讲,毕竟人家两个现在还在一起。我这么和你说吧,斗波的老婆是从河那边来的,不是自己来的,是别人带过来的,你明白不?不明白就算了,今天天气好得很,你来的时间还挺合适的。
你看你看,你们大城市读书的人就是不一样,讲哪样一点就通。你晓得就行了,莫到处去讲,小心他们来打你。其实斗波老婆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晓得她待不住。直挺挺一个杵在门口,不讲话,眼睛里黑黑的,像要下大暴雨。我见过的,她这种就是长了马眼睛的女人,别个女的像驴,温顺吃得苦,每晚被老公骑在身上打几个巴掌、踹几脚,第二天还是起大早干活。她这样的不行,哪个都管不住她,只要她那两条腿还长在身上,她就一定会跑。
斗波老婆叫什么?这我还真不知道,她刚来的时候不会讲我们的话,到后面点也不管她叫什么了,这些从河那边过来的女人,名字就是拿来忘记的。这个女人真的是胆子大,第一次是让人从河里给捞回来的,自己拿绳子捆几捆木柴捆,就敢往河里放,还没到河中央就被水冲得七零八落。河里好危险,面上看着流得不快,其实下面水冲得你游都游不动。第二回更胆大,敢往山里没路的地方跑,那山路,是能随便走的吗?山也是活物,山里的时间会伸长也会缩短,一下雨,就会泡发膨胀,跟干木耳似的。反过来,如果是毒辣的大晴天,就会被晒得起褶皱,走一步其实就迈过了三四步的距离。那几天正是雨季,连下了几天的雨,等人找到时,破衣烂衫,饿得直啃草,然而一双赤脚,还踩在隔壁山头。
你莫笑,她不是当地人,哪里会晓得土山土水的威力。你问后来?后来脑筋就转过来喽,晓得土办法是对付不了土山土水的。能指望着离开这片地界的,除了长翅膀的鸟,就是春水的那辆大摩托了。
一转过山,更多的弯弯绕在眼前。
“走起!”
一声喊,新的屁股又落在摩托车坐垫上,一层假黑皮,磨成个蜘蛛网,时不时吐出点黄黑色的纤维棉。
去哪里还不是几脚就到,天没刮风,但耳边呼呼的,感觉山都在转着跑。上到一个大坡,舍不得给油,干脆两个人跳下来,扶着往坡上爬。
“大姐,坐你的摩的还兴自己推车呢?”
春水撇撇嘴,怪人多话似的:“冲到半截上不去,我们一起摔到沟沟里,你的这点儿车钱还不够我买药的!”
“我看是你太抠搜了吧!舍不得磨摩托,留着给你养老呢。”
脸上红红,落得有点儿难堪,转眼看见自己的手指盖里,积了一层泥,赚钱吃饭,还管那许多!“莫讲了,不想坐就算了,这一截路我也不要你的钱了。”
巴巴地望一眼那山,要是自己腿着走,还不软成根面条?只好不说话,跟在后面推摩托,慢慢地过了坡。
这招屡试不爽,又省下几滴油钱,春水喜得按两下喇叭,招呼着又跳上车:
“走起!”
等到送完客,这时候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这个时候还在路上转,天黑都到不了。天一黑,人的眼睛就蒙上了,山兽精怪,都敢在路上拦着你。然而春水还是一个人,在路上慢慢跑。日头远远地挂在西边了,老摩托红漆银把,肚子里发动机轰轰响,像匹老战马刚下了战场,银枪还支着,喘确实免不了的。遇到大坎子颠一下,嘎吱叫一声,后车架屁股,前转向照灯都擦破点皮,这又是挂了点彩。速度很慢,春水一双腿闲闲散散地,老将军似的,跟着自己的老马前前后后晃。
遇到个电三轮,才从城里回来,按按喇叭:“嫂子,还不回去?没得人了。”
“晓得没得人了,我就转着看看。”
“有哪样好看的,除了石头就是车。”
“车子好看噻,有辆车么哪里都可以去。”
“莫看喽,天黑了赶紧回家烧火,你老公娃娃都要饿死了。”
这正是说到春水怕处:“白天娃娃吵,晚上男人骂,在我这辆老马上才能有点清静哟。”
这哪里像是一个母亲说的话嘛,斜着眼睛看看她,踩起电三轮又走了。
其实倒是听了话早点儿回去好,不然也不会惹得那么多人笑。
缓缓骑过一个弯,耳边的声音突然之间转换了频道。那些风声鸟声都停了,轰隆隆的响声慢慢地压过来,震得耳膜都在动。莫不是地震?心一下子抖起来,在这山路上遇着地震,那石头下饺子似的滚下来,还能有个活?春水捏起油门想跑,光一下子暗了,太阳哪落得了这老快。这一抬头看,满头顶都是直升机的轰鸣声。因为山高,简直就从头顶上擦过去似的。里面坐着什么人?黑乎乎一团看不清,手里拿着的黑色枪杆倒是泛着光,看得明显。一点圈子不打,刹那间就直直地飞过去,在空中越来越小,最后连个影子也不剩下。
再不敢耽搁,油门拧到最大,也不在乎那点油了,轰轰地往家赶。
一进屋就插上门,卷被子收衣服,双手忙得看不清影,“赶紧走了,刚才我看见部队的飞机都来了,个个拿着枪,肯定是有恐怖分子来我们这边了。”春水老公一把拽回行李,對着春水小腿就是狠狠一脚,拖鞋都踢了飞出去:“你这个癫婆娘,去了几趟昆明脑袋都进水了,还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来这里找你这种老婆娘?那是治安巡逻!”
第二天出门就遇着笑:“嫂子,昨晚恐怖分子个钻你的被窝了?”
说完旁边嗑瓜子的老奶也跟着捂嘴笑,笑完还把几个白头凑到一起,不知道在说什么话。
走两步发现斗波老婆在那里招手,满脸也是笑,春水就皱起脸来瞪她,怎么,不学好光学坏。近了才看见眼里一包泪,心里一下软起来。斗波老婆说:“姐,我请你喝酒嘛。”
白喝哪个不愿意,跟着就去了杂货店,前面卖东西,后面喝酒打牌。焖锅酒端上来,喝一口,辣得上不来气,肯定是刚蒸出来的头道酒,度数高得很,呛出眼泪来。旁边看一眼斗波老婆,倒是喝得香,一碗酒放在中间,自己拿一把小调羹,小口小口地舀起饮。春水觉得好稀奇:“你怎么喝酒跟喝汤似的,还拿调羹?”斗波老婆笑笑:“我们那里都是这样喝的,喝得慢,不会醉。”说起家,春水也为她感到难过了,转个话尖:“昨天你看到飞机没有?”“看到了,黑黑几个,一下子就飞过去了。姐,我相信你说的,我们家那里常有坏人,走在路上掏出刀来就砍。这些人什么都没见过,所以哪样都不害怕。姐你见得多,心眼好使,反而会受苦。”这样说着,倒是春水眼里酸起来,人家反过来在同情自己了。自己何曾是瞎说的?那次送姑娘去城里读书,在火车站刚下车,就遇到坏人,半米长的西瓜刀拿出来,白闪闪的。抱着姑娘钻在一小妹开的书报亭,外面的喊声是一样都听不见了,眼前模模糊糊地扩开一片景,有一匹矮脚马,好像就是爹没走以前送给自己那匹。自己跟姑娘跨上去,跟飞似的,一下就高过树,高过山,飞到云里去。云里有雨,湿湿地沾了一脸。伸手往脸上一抹,手里一片红,那个小妹,已经是倒在自己眼前了。
斗波老婆于是说:“姐,你带我走嘛。”
你看你看,前面又有个老脓包把别个车子撞下山,现在跪在交警面前哭。你莫看我骑摩托是肉包铁,比那些坐在车里面铁包肉的要安全多了。这种弯弯都是小意思,我骑摩托,可以把弯路拉直,把直路卷得弯起,往上的坡变成水往下淌,向下冲的坡升起来变成个楼梯,走着都可以爬上去。你个见过人家打铁?这些山弯弯就是我骑摩托日日年年捶打出来的。太阳大,我就轻轻地压,给路面磨得又光又滑,像小女娃娃的脸蛋。下起雨来,技术差的么就莫开山路了,但对于我来说正是好天气。路里面吸饱了水,我就屁股压摩托重重地磨,把路压得又紧又踏实。有裂开的口子,压着摩托朝两边甩,几转就合拢了。没得我嘛,每年修路都认不得要修多少回。
你看,那个老脓包打电话喊他老婆,算他聪明,让他老婆跪着哭比他哭值钱多了。哎呀,莫乱来嘛,咋个要往山下跳嘛,这个女人也太憨了,赔钱偿命都轮不到她嘛。好了,我们又得等起了,这下子救护车又得多叫一辆。哎呀,这些医生快点嘛,再晚几分钟么这个女的肯定救不回来了。哪样事都不能拖,一拖准要出事情。就像当时要是不等那个法国人唱歌嘛,斗波老婆也早就跑掉了。
春水给斗波老婆看相片,旧旧的一张,几面墙做背景,自己小小一个拿着个鼓锣。两人默默地看好久,春水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家,墙是掺了糯米面粉砌的,多少年都不会坏,我们马帮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看着听到外面面包车轰轰响,伸出头去望。五颜六色的服装,还有两台大音箱,隐隐约约探个头,在车厢里颠。
斗波老婆觉得稀罕:“这么大音箱,不得把人耳朵震聋?”
春水去城里经常见过的,商场门口搭个台子就放起歌,其实什么都抽不到,白白给人凑了人气:“没哪样好看的,回你屋头收下重要的东西,我们趁着他们闹赶紧走喽。”
斗波老婆仍旧探着头:“姐,我们听完那个法国女的唱完歌再走嘛。我出来一趟,什么世面都没见过。这么老久没回家,让我听听她唱歌,回去我就说去了法国了。”
话筒里“喂喂”两声,大家都聚拢起来了。聽着报幕,法国女人走上来,棕头发、红花裙,皮肤却白。听介绍,说是当年跟着滇越铁路来云南的法国人后代,喜欢喝普洱,喝着喝着就留了下来。这也难怪,在法国当药卖的好东西,在这里不过就是一碗水。然而还是新奇,掌声雷动。随即唱一首《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每到一处“哥哥”,下面人便“蝈蝈蝈蝈”地叫。一曲唱完,掌声更加响,个个都高兴得很。
斗波老婆说:“姐,怎么法国女人也是这个样子呢?”
“不管它是洋猫还是洋狗,到了山里滚一圈泥就是土猫土狗。”
斗波老婆沉思一下:“姐,你说的话很有道理。”往屋头赶的脚又加快了些,“这下回家又怎么跟他们讲我去过法国呢?”
水继续淌,鸟只是飞,台上依旧在那里演。
换了一男迓腔,穿一身灰衣,一双大脚故意小小地迈,在那里唱楚剧。行弦过门拉起,哦呵哦呵地,唱的是泼辣农妇焦氏,勤俭持家但又嫌鄙婆婆,为着琐事动手要打老婆婆。老公曹庄见状怒火中烧,举一把砍柴刀就要把老婆砍死。老太太跪地求儿,家中的狗嗷呜一声血溅三尺,一命呜呼。唱到爆彩处,台上曹庄大喝:“贱人休走,看刀!”
台下斗波登时站起,两太阳穴青筋暴起:“连个戏子都敢拿刀治住婆娘,让她伺候老妈,我真是个(尸从)货!”
喊一圈没找着人,拉都拉不住,就往回跑。等走进屋子头,斗波老婆正在床上,袜子沾着灰,披一件斗波的迷彩外套。不等斗波走上来,自己先迎出去。拿一块毛巾拧拧水:“怎么弄得满头汗,我来给你擦擦。”这下弄得斗波倒有些哑口,一手接过毛巾坐在条凳上,一手伸去想去拿水瓶。“我帮你拿嘛,要哪样?”水瓶怀里圈住,送到斗波手里,转身又坐回床上,衣服纽扣闲闲地解散了,将着就要躺下去。此刻也管不得什么男人气概了,两只脚鞋跟一踩,拖着鞋就窜到床边。斗波老婆手推推:“莫着急嘛。”斗波说:“我其实爱你爱得很,我要有五十块,我都会给你一百块,另外五十块我去卖血给你。”“我晓得的嘛,我也爱你噻,你以后莫那么防得我了,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家的猪嘛,不会跑到别人嘴巴里头。”“好的嘛,好的嘛。”说是这么说,眼睛耳朵已经不在脑壳上,早就转到了手心里,手摸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打个战,抖两下,不消说,连自己老娘叫什么都早就忘到沟沟里去了。
天黑了,想要扭灯,却看见一个背包鼓鼓地躺起。刚才也是心急眼瞎,这么大个包都没有看到。鞋也顾不上了,窜过去两手一拽,行李塞得实实的,按都按不动。火气一下又冒到头顶,转过头,一双黑黑的眼睛望着他抖,说不出一句话。终于是几个拳头,肚子软软的,一打就会陷下去,脑壳是脆的,像西瓜,拍起来砰砰响,哭喊声也布满了这一个天空。
是呀,不要说你,我们哪个听了不怕嘛。人不是猪狗,哪能那样打的。要不是春水去了么,那天人怕真的要被打死喽。具体的我也没有亲眼见到,所以我也不能跟你乱讲,反正威风得很。那天我刚跟朋友吃菌子回去,对了,你个爱吃菌子?现在七八月份,正是菌子旺的时候哩。哎呀,没的事情,哪里会那么容易中毒嘛,那些都是自以为胆大的人吃杂菌才会出事。我们只吃自己认得的,黄牛肝菌拿点干辣子炒炒,金黄黄的,又油又香。
反正就是那天我吃完菌子回去,就遇着春水。香味还在嘴巴里头,看见一帮人扛着铁铲、大锄头、斧子镰刀,霸着路走着。虽然认得不是冲着我,也把我吓一跳。春水甩起根鞭子走在最前面,打到地上噼噼啪啪响。我躲得一边问她:“去哪点?”她摸摸我的头:“去斗波家,斗波那个没娘养的,不把人当人。”我拉得她的衣角,跟她讲:“你们吓吓他就行了,别闹出事情。”春水拍拍我的屁股让我赶紧点回家,然后喊一声:
“走起!”
喝这一声彩,真是让我腿肚子打战。身上的血一下子往双腿灌,挨了电门一样,我要是匹马,当场就得抬蹄子飞跑起来。平常听人这样吆喝,晓得不过就是赶羊吆鸭,究竟不怎么有气势。春水的鞭子一打,嗓子一喊,地上和心上都被卷起旋。我躲在后面看他们,一行人也不多言多语,把家伙都紧紧地握起,跟在春水后面走。好像哪个也拦不住他们,毒蛇猛兽拦不住,恐怖分子拦不住,逢山开路,遇水过河。我想当年迤萨马帮闯天涯,走通东南亚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我跟你讲,这世上有些事情真是奇怪得很。小的时候听外公讲,二十世纪里也不知道具体哪年哪月,反正他们一些人驻扎在金沙江旁边的一处小野山。等得月亮把窗户填满的时候,山谷里面哗啦啦作响,风声隆隆的,个个都从梦里面被吓醒。等得提起脚赶到时,一道巨大的切口从小半山处直刺入金沙江,两边的树木都向外边翻起,仿佛有哪样巨大的东西挤压过去。抬起眼一望,只见得一个庞然大物轰然滑入金沙江,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有一个当地的住民就讲:“是巨蛇。”第二天大家就忙起收拾东西,不敢再待下去了。你说光天化日之下,咋个会有能把山都劈开的蛇嘛。不过想想,现在脑壳顶上就有宇宙飞船在太空里飞,山里有条大一点的蛇也是很自然的了。所以这并不算得奇怪,真正奇怪的是一个人,昨天见到还威风凛凛,眼睛里翻着火,第二天再见到,那个身上的火好像就灭了,这种事,你说怪不怪嘛。
后来我看到,春水的心好像就是这样说麻就麻的。
第二天春水家门口聚了一帮人,都是些白头发、灰头发的男人,间或杂着几个黑头,不停地吸烟,搞得乌烟瘴气。斗波拿绷带缠了手,纱布裹了头,蹲在地上哎呀哎呀地叫。春水拨开这些臭气走出来:“搞哪样嘛?”斗波叫得更凶:“哎呀,我不跟女人讲,喊你家男人出来。”我来到门边,睁大了眼睛看起,很害怕他们会动手打人。这时一阵怪响突然从林子里面传出来,嘶嘶的,像马叫,又像鸟叫,甚至还有点像蛇吐芯子。我看那些人还在吐痰吸烟,我就跟春水悄悄地说:“有奇怪的动物来了。”春水把我拉到旁边:“是六脚马,哪个找着了哪个就可以骑上它飞上天。”“飞到天上干什么?现在不是有飞机吗?天天在天上飞。”春水没回我,只是拍拍我,让我去树林子里看六脚马。我走了好久,和我比起来,山太大了,一棵树比我高,一块石头比我重,有时连一棵不知名的野草也比我强韧。绿得很,野得很,转几个弯也不见有什么东西。日头越走越沉,四面冷寂下来,我什么都没看到,只好转头回去。回去就看到春水正在给斗波递烟,左边脸蛋又红又黑的,她跟斗波讲:“对不起。”
第二天全个屋子都漫着豆腐香,我闻着味来到厨房,春水在炸石屏豆腐,斗波跟春水自家老公坐在堂屋里,等着吃赔礼。听人平常讲,这个豆腐出了这地方到哪里都做不成。你就把师父带着,把点豆腐的酸水带着,只要脚迈出这片土地一步,这豆腐做出来不是苦就是涩。香得很,看那些好豆腐,一块的肚子鼓起来,一块的肚子瘪下去,翻一个面,又在锅里弹两下。转头一想又气得很,这样的好豆腐,等会竟要进了坐在堂屋的那些坏嘴的肚里。
春水手里抓了把什么?白灰白灰的粉,哪里有这样子的作料。往豆腐上划几道小口子,蘸着粉往里塞。凑近了一闻,这股子味道再熟悉不过了,这不就是那水烟袋落下的烟灰吗?平日里都是这样的,那些个男人或坐或蹲,挨在墙边,嘴巴对着烟袋嘴猛吸一口,水烟筒就烧开水似的咕咚咕咚响一阵水泡。眯起眼睛,把烟咽进肚子里滚两圈,吼吼哈哈地猛咳两声,拎起烟哨子抖抖烟灰,又传给下一个,那烟味混着汗臭味,熏得人眼睛疼。
把露在外面的烟灰擦掉,抹上一层辣椒面,稳稳当当地挨个放盘子里。春水对着我狡黠地笑笑,眼睛里亮亮的,好像歡喜得很。这样的心思,我自然立刻心领神会,拼命忍住笑,端起盘子就往堂屋里走:“豆腐来喽!赶紧吃起!”
我憋笑憋得肚皮又酸又痛,时而眼睛看看盘子,时而又落到窗户外面去。豆腐早已下肚几块了,依旧是在那高声喊:“好兄弟!”“吃!好哥哥!”焖锅酒一大钵端在桌上,一手是碗,一手是筷,就着一口酒,两块豆腐又烫烫地下肚。夹一筷子就落一点,盘中剩下的豆腐被烟灰落满头满身,像发霉了一样。偏头偷偷看一眼春水——眼睛紧紧地望豆腐,激动得喘气都快了许多。春水老公看一眼那烟灰豆腐,夹起来往嘴巴里头送,咂摸两下,肥舌头转两圈舔舔嘴唇,依旧是:“好弟弟!吃好喝好!”
我看着他们把那些烟灰豆腐都直直地咽了,一下子觉得舌头好麻,用手一擦,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咬破了一大块,流出好多血来。我转头看看春水,一张脸呆呆的,好像陷入一片很远很厚的雾气里,咋个都走不出来。春水的心,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和我的舌头一样麻掉的。
我们这里的生活其实平淡乏味得很,但我们这里确实有六脚马。
六脚马比人心善,早晚寺里和尚念经,它就会自己慢慢去听。大殿里不去,自己一个马悄悄地到偏殿。虔诚得很,六条马腿屈着跪地,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木鱼,僧人敲一下,马蹄子点地一下,照样清脆。长年累月地听,也就真把自己熬成了块木鱼。死了以后寺里办超度,跟木头棍子一样,一点就呼呼地烧,马蹄子烧碎了掰开一看,是一粒已成形的舍利子。所以喽,这就是佛祖给六脚马盖了戳了,从此就不是凡马,超脱俗世。这不是讲来骗小孩的那种故事,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的。
那天斗波老婆最后一次来找春水,头发乱蓬蓬的,像鸡窝草。其实走得很慢,手里边拿一根半粗不细的树枝丫丫,当根拐杖使。实在耐不住,话都憋不到进屋就破口说:“春水姐,你再最后带我一次嘛。”
其实哪个都晓得是最后一次了,我不好打扰她们,坐在外面抠墙皮。小块小块的,抠了一半天,龇得我指甲都快出血了,才白了一小片墙。看看旁边,都是黑阴阴的,这一小块白反而显得很难看。我又只好看狗,两条土狗屁股挨在一起,八条腿在地上走。实在是见不得,随便捡一根树枝就往屁股中间砍,结果树枝断了也砍不开,气得我狠狠踢了那公狗的屁股一脚。两条狗嗷嗷地跑开了,留下我一个显得更加寂寞。于是我实在等不了了,准备去向春水告别,说我先走了。
手慢一点儿,还没来得及敲,听见里面说:“我晓得他会跟着我,山路那么抖,推下去摔死了哪个也不会怀疑哪样。”“做了心不安的,以后走夜路都会怕。”“我倒想走这条黑路,死了就在路上继续走,走到寺里求菩萨把我送回家。”“你信我,把你自己搭进去,我吓吓他嘛,保准他颠得屁股跑掉。”我赶紧缩回手,蹲在墙边继续抠墙皮,等到身上的汗像雨一样把一切秘密都冲刷干净后,我才站起来,使劲跺跺酸麻酸麻的脚,对着屋里喊:“我走啦!别人还等着我一起搭车呢!”
后来的事大家就都晓得了。
斗波老婆说要去城里逛步行街,买几件新衣服,从家里带来的那些,脏了脱下来揉搓,穿在身上也被撕打,这破一个口,那刺啦两线,穿着实在有些羞。屁股刚坐上春水的摩托,斗波就也跟着上来了。犹犹豫豫地,想上车又想起自己以前回回坐车出事情,摸摸脑壳,摸摸脸巴,感觉得哪点都好像有点儿疼。
春水捏起钥匙要走,斗波又往前挨挨:“再加我一个嘛。”春水把头发往头盔里塞塞,“我骑得快得很哦,你也晓得,到时候么你莫怕嘎。”一面想得,斗波一面屁股挪到坐垫上——城里边不像这土山土水的,老婆一下子跑掉么,喊多少个人都找不回来。伸手把老婆往前推推,三个人把摩托坐得满满当当的,“哎呀不怕的,过了天生桥我就下来自己走。”斗波老婆轻轻掐一把春水的腰,春水左手收离合,左脚挂一挡,听得发动机速度起来了,高挡一挂,摩托就跑起来了。
这一路走起来自然是熟得很,遇到紧缩弯,入弯路长长,出弯路一小截,收油、刹车、降挡,春水屁股往内侧一倾倒,两个车轮子就漂亮地划过去,再错开一点就要冲到路外面。最痛快的还是过大弯,住在这点的人,比喝焖锅酒还喜欢的,就是坐着春水的摩的飙大弯。大弯肚子庞大,跟大象肠子似的,过的时候紧紧挨着内侧,靠看是看不出弯道深浅的。就算是那些骑着川崎、杜卡迪的,在这种老山路上看不出明显的弯道顶点或临界点,想跑山跑赢春水的老国产顶杆机,还是差点儿意思。春水慢入快出,该放速度的放速度,摩托一点不向外偏,要是只有春水一个人,那膝盖都能碰到地上,擦出煳味来。春水和斗波老婆都快活得很,只有斗波,吓得满头冒汗,抓得摩托的手都捏青掉。
过了就是那条长长的直路,春水最喜欢的,平素里没客人便在这条路上慢慢骑着吹风。刚才过弯冒的那层汗,经风一吹,丝丝孔孔地凉进心里,舒坦得很。张起眼睛看,视线开阔空旷,好像不是山,是在一片青天上。
忽然地一转,云没有了、天没有了,是大块大块的山石,长在薄薄的山坡上,声音喊大点么都要掉下来。这段路却没有见过,又小又窄,地上尽是些牲畜的脚印子。“嫂子,走错掉了吧?刚才直直走就对了。”春水油却给得更多:“这条路更近。”这些山弯弯一个都没见过,一下子这里有一个拐,一下子那边有一个圈,转来转去,一路给油往上走。
斗波怕得有些遭不住了,说话都抖起来:“嫂子,怕是不对吧?我咋个感觉越来越走到山上了呢?”春水接着开,过弯不走漂亮的弧线了,直进直出的,扭头冲着斗波一句:“你打你老婆的时候威风得很嘛,现在咋成(尸从)包一个了?”想想前不久的事,斗波晓得春水啥意思,左望不是,右望也不是,只是干干地咂咂嘴。
春水盛气地啐一口:“怎的,你还敢整她,我今天就敢挨你整废掉。”老摩托突然地颠起来,油门一紧,手捏刹车前轮哧哧擦地,颠得斗波屁股飞起来。刚落回坐垫上,油门又一松,右脚踏板前一踩,后轮咯吱咯吱地叫,磨得斗波满嘴牙齿酸。
再往前面就是个大急弯,斗波往路外面望望,大片的田小得跟块青苔似的,烂棉絮一样的薄云就飘在路下面,心都要吓得吐出来了,哑着嗓子喊:“整慢点!”春水问一句:“以后个还敢?”直接方向打死,给高油门,迅速弹开离合,老摩托直接原地转了一圈。
没听到回应,就只有一声怪叫,斗波想自己跳下摩托,一松手,直接就被抡一圈甩了出去。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拉,斗波就悠悠地掉下了山。山很高,风也很大,斗波死得又轻又安静。
春水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本来是想吓得斗波回家去,以后不要再找麻烦,哪个想到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松手跳摩托。捏起刹车停下来,老摩托哼哧哼哧地喘着,斗波老婆在后面讲:“春水姐,各路神仙都看着,他摔死了不是你的事。”春水扭头望一望她,斗波老婆嘿嘿地傻笑,眼珠里黑黑的光一下子就灭了。
再往前走就遇到了那两群猴,龇牙咧嘴,斗得血肉橫飞。比往常多走好远路,摩托车胎也烧得严重,渐渐行得慢,汽缸当当地响两声,低头丧气地停了下来。斗波老婆下了摩托,对春水说:“姐,连猴子都来拦路,我注定是跑不脱了。”春水拉拉她,意思是不怕的,一起走出去,斗波老婆摇摇手:“其实我想做的事也做完了,斗波死了,我不想走了。”
我说过的,我们这里确实有六脚马。
等得大家跑过来找到斗波老婆,春水已经不见了,她那辆老摩托留在原地,发动机都还没熄,沙沙地喘着,单腿撑在地上,窸窸窣窣地抖。像匹老马,跟随主人厮杀了大半辈子,肌肉缩成张老皮,四条腿都发麻,颤颤巍巍地要走了。
大家正手忙脚乱,一阵奇异的味道好像突然从草根里,从树杈子尖上,甚至从猴子的屁股脸里涌了出来。猴子的叫声全变了,疯狂地四散开来,露出惊恐的神色。铺天盖地的气味笼罩了我们,像寺庙里烧得浓浓的香,但又夹杂着雨后树林子的植物骚味。想赶紧跑,鼻子脑袋里都灌满了这味道,腿轻飘飘地,使不上力。
然后就响起了那声熟悉的吆喝:
“走起!”
好像一把老木桨,深深地往水里一划,脑子里糊涂的一片就清亮起来。水波一层层,连接了过去和未来,荡开那些发腥的水萍和臭鱼一样的腐烂记忆,荡到了猛野井的盐水里,荡到了越南的棉花地里。真是奇怪,不知道是谁的声音,好几个,随着水波一下下地涌到耳朵里。手里拿几团花边丝线,就换了半包白胖棉花,说着这下好了,回家去么,老婆又可以做几件新衣服。可是自己一个十来岁的女娃娃,哪里来的老婆?转身又拍拍身上灰,不知道在外面走了多久,头发里一股酸味,手上却沉甸甸,一箩筐鹿茸、熊胆、麝香,药材的苦味涌到舌尖上,让人尝到瘴气的湿热和山石的冷酷形状。
再往前走么,怕就要穿到水波的背面,走到上辈子的时间里去了。赶紧掉个方向往回跑,撒开了腿跑,扯开领子跑,让风呼呼地往里灌,像很久之前和很久之后的母野马那样,把自己里里外外都吹个干净,吹个透亮。风很大又很软,吹得头皮凉凉的,拿手一摸,头发已经全数脱落了,然后是手和脚,常年被紫外线晒得黄黑黄黑的皮肤渐渐透明,那些支棱着的骨头也渐渐融了形状。不晓得跑了好久,跑得烧豆腐和烧饵块的味道忘了,自家房子的样子忘了,山路哪里有弯也忘了,在跑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的时候,又响起一声:
“走起!”
那些丢了的颜色、味道和名字一下子回来了,又把今世的自己全部想了起来,我对着人群大喊:“是她!是她!”
空中突然传来湿漉漉的嘶鸣,像猛地剥开一个多汁的桃子,桃汁四溢飞溅出来,落到眼前、落到脑后。春水驾一匹马在空中奔腾而过,六条马腿飞快地交错着,出后蹄,出前蹄,接着是一个潇洒的飞跃,中间的两条马腿始终嗒嗒嗒地敲击,像愉悦的三拍子音乐。像春水的老摩托过弯一样,在人们脑袋顶上划一个精确的弧度,无论是身姿还是速度都震得我们双眼发直。
我们当中有胆小的,不敢看,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发抖,像一只落水的老公鸡。我刚从混沌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像一张湿透了又被大太阳晒干的纸,又脆又透明,什么也不怕。春水骑着六脚马在我们头上打转,我就对着天上喊:“还有我!还有我!”喊了老半天,嗓子眼里都喊干了,六脚马也没有落下来,也许它根本就不会落下来,如果它落到地上就会变成春水那辆气喘吁吁、半死不活的老摩托。
很快六脚马就飞走了,大家全部浑身大汗,在地面挤成一团,像一个湿淋淋的大拖把头。
你看,我说我骑车厉害得很嘛,这不就到了。像刚才那些抢速度撞山的,水平不够冲到路外面的,在我这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给你留个电话嘛,你以后要是还需要坐摩的么,随时喊我噻。
哎,这个风吹得真是舒服得很啊。你来的这个时候真是太好了,田里还水汪汪的,你看看这些梯田,这么陡的山,硬是变成一块块田,平平整整的,你看最大的那块,有两三百米长呢,哪个能想到这是我们的老古人做出来的。
你回去么我怕是接不了你了。我家在城边上,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差不多就要往家走了。哎呀,这点好是好么,哪个会几辈子住在这里嘛。特别像我们这些读过书的女的,在这点是住不下去的。说了你莫笑,我真呢还是正经读过书的。
对了,刚才挨你吹了这么久的牛,都没跟你讲,春水就是我妈撒。她骑着六脚马飞走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一直想走的不是斗波老婆,而是我妈。不骗你的讲,看得她走掉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的,甚至有点恨她,我想大声地喊她,你快点回来!但是她一转过脸来,我看到她的腿已经跟六脚马的腿融在一起了,我一下子哪样都想明白了。春水的腿本来就是马的腿嘛,她两条腿骑到四条腿的马上,不就变成六脚马了?
所以呢,最后我就对着她使力喊:“妈!你跑快点!”
好了,不挨你多吹了,我真呢要赶紧回去了。等会儿天黑了,山路上有好多古怪呢。30块钱,现金、微信、支付宝都可以,零头就不要你的了,留个回头客嘛。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