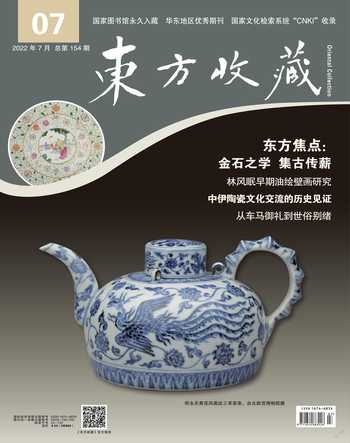从车马御礼到世俗别绪



摘要:依托汉画像石蔚为大观的车马出行图像,送行人物逐渐得到重视并得以再现,形成人物送行的图式。一方面,送行之人往往作为御礼的一部分,此时仅占据画面边角;另一方面,由于出现清晰可辨的妇女和儿童,人物占据画面中心,送行已有家居生活的意味,基本能够构成独立画面。从车马御礼到世俗别绪,这两条线索的交织和衍变,唱响了后世送别图式的先声。
关键词:汉画像石;人物送行;图式衍变
从传统信仰的祖道仪式脱胎而来,送别活动逐渐融入社会风俗,更成为“递相沿袭而又常写常新”[1]的文艺母题。伴随送别活动的世俗化倾向,早在《诗经》时代,送别元素就已经进入诗歌,《燕燕》《渭阳》等篇章尽管只是零星闪现,但都描绘了亲友送行的典型场景。汉代以“苏李诗”为代表,抒发别情的意味愈趋浓厚。经魏晋定型,送别文学在唐代达到创作高峰。
这种对离愁别绪的共同感受,经由文学蓝本的渲染,促成了中国古代美术史中送别图式的生成。近年来,学者们追寻送别诗与送别图的源流和关联,以沈周、弘仁为中心聚焦明清江岸送别图式的衍变,已有丰硕成果。实际上,上个世纪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的美术考古就已发现一件以漆彩绘的木篦,“木篦的一面表现送别,另一面则是表现相扑”[2],这表明,送别图式可以追溯至秦。及至汉代,即使以送别为主要对象的单幅画面仍不多见,但涵盖这类情形的图像已初具规模,多以汉画像石为载体。
通览《中国画像石全集》,至少有17幅关涉送别情节。其中,5幅画像的命名中明确使用了“送”的字眼,皇甫昱先生《浅析汉画“长亭送别”》一文也初步关注了这一美术史现象[3],但与此相关的研究似还未展开。本文即围绕《中国画像石全集》中的17幅画像,探讨其中送别图式的衍变及其意义。一般来说,送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送”,一是“别”。由于这一时期的图像偏重于刻画送行一方,告别的人物和动作尚不明晰,因此,将其称为“送行图式”或许更为贴切。
练春海先生在《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中对“御礼”的含义作了界定,若与送行相联系,那么当做御禮讨论的送行礼仪是指“宾车起驾时,主人或他的代表欢送宾客的礼仪”,而“一般意义上的家眷或下人恭送主人出门”[4]则是世俗家居生活的体现。我们讨论的17幅汉画像中的送行图式,同样不出这两类。
一、作为御礼的人物送行
依照汉代的交通状况,车马是主要的出行方式。车马出行的图像形式在战国及秦时已有发现,之于汉代,早已成为主要的艺术创作题材之一。我们发现,在两汉数量浩繁的车马出行图画中,常有人物立于队列前后,作恭迎之状,承担着迎宾和送行的礼仪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凝结或记录了汉代的御礼”[5]。
17幅画像中,共有13幅出现这类送行的人物。从年代归属来看,只有1幅《迎送人物画像》(图1)在西汉平帝时期,余下12幅皆成于东汉时期。
先看《迎送人物画像》。画面中心是一人一骑,伴有两个卫士,“后有二人送,前有三人迎,其中二人跪、一人立”[6]。未脱稚拙粗率的创作特征,人物刻画和构图都较为简略,但身体动作的着意突出,使我们能够辨识基本的内容,只是送行之人的性别和身份似难以确认。尽管如此,这幅画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在汉代早期的画像石中,送行之人的形象就已经得到重视并镂之于金石。
余下的12幅(表1)中,10幅出土于山东,1幅出土于安徽,1幅出土于江苏徐州。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地都被信立祥先生划分在汉画像石的第一分布区中[7]。“汉画像石在某些时期流行于某些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不同区域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又独具一定的地方特色”[8],这一分布区域汉画像石的送行图式的确体现了一些共性特征。
其一,人物送行仍然依托于车马出行的队伍,但车队行列往往声势浩大,车马形制多样,随从属吏的身份组合也各有不同。因此,无论在单层长幅横向画幅中,还是在多层构图的某一层中,送行的人物都只占据画面一角,有时并不起眼。
其二,细究人物的动作,实际是对御礼的细节性再现。也许是出于程式化的要求,人物位置基本固定,但身体动态却有变化。这些变化就与礼仪有关,存在是否执物和是否跪送的区别,所执之物一般是笏。执笏躬身是上下级之间的拜谒之礼,既可用于迎接,也可用于恭送。《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龛西侧画像》《安丘汉墓前室西壁画像》《人物送行画像》《迎送画像》《迎宾画像》中的人物都是执笏躬身送行的代表,《西王母、季札挂剑、邢渠哺父、二桃杀三士画像》中二人所持之板,应该也是指笏。另外,在《西王母、季札挂剑、邢渠哺父、二桃杀三士画像》的最右侧,即持板之人身后的亭中,还有一人拥篲而立(图2)。拥篲是汉代的迎宾之礼,表明送别的对象是宾客而非亲属,再次凸显了送别的御礼性质。另一区别是人物在立送还是跪送。在本文统计的画像石中,只有《沈刘庄墓门西门楣正面画像》中的人物是双手举物跪送。
其三,送行人物周围时常伴有飞鸟和熊。如《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龛西侧画像》人物右上有一飞鸟,《人物送行画像》人物后有二熊挽手相对而立。飞鸟和熊都是汉画像石中极具代表性的象征性动物,如此一来,送行人目送车队向前延伸,送行的意义就不仅是送别宾客的礼仪,在他的眼中,车马行列“仿佛要超越这幽冥的墓葬,通往辽远广阔的空间”。因此,“这类图像具有表现真实的礼仪事件和表现虚构的死后时空的双重功能”[9]。
二、进入家居生活的人物送行
事实上,汉代车马并非仅贵族可以使用,我们于图中所见的车马形制也不一定能与墓主身份对应,只是一种宣扬威仪的宏大叙事。而表现亲友送行的画像中,车马的形象已不再占据主要位置,亲友间的情感交流已经与一般的送行礼仪相区别。顾森先生曾指出:“这些从祭祀活动、政治活动中游离出来的私人生活内容题材,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最应引起注意的”[10]。
这类画像共有4幅,我们将其分为两组来讨论:
1.安徽出土《人物画像》(图3)与《东王公、讲学、出行、庖厨画像》(图4)
《人物画像》与《东王公、讲学、出行、庖厨画像》都出土于安徽宿县褚兰镇,两地相当接近,因此,相似度也极高:⑴两图都被分隔为四层,送行情节位于中间的第二或第三层,是对人世生活的再现;⑵马都被系于屋檐下,旁边悬挂着盛有草料的篮子,尽管马匹十分健硕,但只占据边角位置;⑶送行由单人和多人的礼仪组合,变成了一位妇女带着三个孩童的组合,妇女和儿童在画面中出现,无疑表明了亲属送行的性质;⑷在此基础上,基本可以确定出行之人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尤其是出行的仪仗都已备好。两幅图有确切的时间归属,都处于东汉晚期。由此看来,至少到东汉晚期,尽管展示财富地位的观念仍旧不可动摇,但描绘世俗生活中家庭成员出行和相送的情节,已经可以独立支撑一幅画面。
2.徐州出土《送行图》(图5)与四川出土《送行》(图6)
在《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册中,徐州出土的这幅图被命名为《建筑、辇车画像》[11]。本文更认同武利华先生的观点[12],认为应是《送行图》。这是一幅较为规整的画像,横纵尺寸相差甚小。外围以垂幔纹装饰,用界格分隔上下两个部分。上格有门阙,二人对坐于厅堂之内,相向交谈,似在话别。下格中心为一辆马车,从车型判断,应是輂车。车箱装有卷篷,常作妇女乘车,与孙机对輂车的考证相符[13]。
再看四川出土的《送行》。将要远行的人与车马、送行之人各占据画幅一半,人物成为画面描写的主要对象。这里的车是辎车,车厢分为前后两部分,御手坐在前厢。将要远行之人面对送行的三人,也似在道别。
相对安徽出土的两幅画像来说,在这两幅图中,车马原有的作用已被削弱,如今只能作为交通工具的标志指示画中人将要出行,表达的重点已经转向了送别的两个基本要素——“送”和“别”。对于作为御礼的“送”而言,车骑绝尘而走,除身份地位之外,看不出远行人与送行人有任何交流;对《人物画像》和《东王公、讲学、出行、庖厨画像》而言,即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已经开始展露,但只是一条隐性的线索。而最后这两幅图的刻画中,送行之人与告别之人由相背走向了相向,等级的装束逐渐脱去,“送”和“别”之间尽管没有类似执手的其他表情手段,但是已经勾连起一种有关离情的交流。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亲友间的叮咛嘱咐、泪眼相看的难舍,画幅不长,空间也未延展,但复杂的情绪充斥其间。
三、送行图式分化演进的意义
汉画像石蔚为大观的车马出行图像中,人物送行的图式开始出现并逐步分化演进。由于画面仅描绘人物、车马,刻意虚化了背景,不妨称其为“人物车马送行”。从作为御礼成分的礼仪送行,到进入世俗生活的亲友送行,汉画像石人物送行图式的衍变,体现为人物与车马的动态共存关系,体现为对“送”“别”双方的不同侧重,在对送行母题的重复再现中,循序渐进地走向创造与突破。
“送”“别”双方的在场或缺席、送行人物的配置和组合、构图的空间延展性问题,由这些因素分化出的图式類型,是后世常见的各类送别图模式的先声,诸如董源《潇湘图》未见告别,沈周《京江送别图》呈现了完整的呼应,弘仁《晓江风便图》未见送者[14]。其中传达的动人离情,在传为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人神徘徊不忍离去的场景、李公麟《阳关图》的豁达与希冀中,显露无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经六朝至唐,孤舟送别意象入诗入画的尝试,启发了“江岸送别”图式的初成,“以山水画形式出现的送别图始于两宋时期,并在明代达到了顶峰”[15]。
进一步说,汉画像石人物送行图式的衍变,实际是汉代艺术创作对于传达自身微妙心绪从无意到有意的感知和表现,从对礼教的着重再现转向对世俗的描画,伴随着汉代艺术创作重心的转移。从“人物车马送行”到“江岸送别”的转变,更是中国古代绘画整体向文人画方向发展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龙剑梅.别离文学中人际传播的送别文化习俗[J].新闻传播,2020(21):47-48.
[2]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第1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66.
[3]皇甫昱.浅析汉画“长亭送别”[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6-7.
[4][5]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08,7.
[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册)[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目录25.
[7]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3-21.
[8]朱存明.论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及特征[J].地方文化研究,2013(01):14-22.
[9](美)巫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汉代艺术中的车马图像[J].郑岩译.中国书画,2004(04):50-53.
[10]顾森.秦汉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16.
[11]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册)[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目录8.
[12]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M].北京:线装书局,2001:26.
[13]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95-98.
[14]邱才桢.盛景、送别与隐居山水——弘仁山水画的图式、时空与意涵[J].中华书画家,2016(6):10-74.
[15]李瑾鸽.明代送别图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1.
作者简介:
李琼玉,202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艺术理论和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