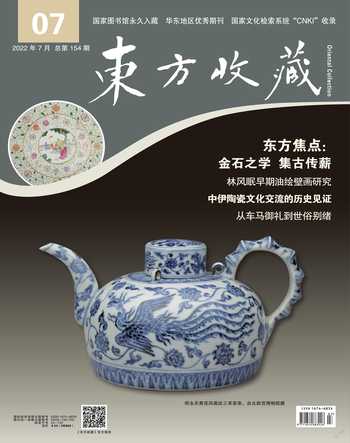河北地区战汉时期金石遗存对当代印学创作的启示
李国良



篆刻艺术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赋予国人以丰富的情感,而篆刻学所呈现的图义则集合了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和科技史。河北地区战汉时期丰富的金石资源,对地域印风和当代印学的创新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平山县的“中山三器”、满城县刘胜汉墓的铜壶文字、元氏县的祀三公山碑,从“印从器出”“印从壶出”“印从碑出”三个方面,对篆刻本体的传承与创造均有一定的取法启示,使印学创作向更高层次迈进和延伸。我们要以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宗旨,构建出属于自己的艺术程式,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作品,如是必将在赓续民族血脉和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河北古为燕赵之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河北拥有众多的金石碑刻。当代艺术承担着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重任,而篆刻艺术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能够承载起丰富的内在能量、主体精神和民族之魂。面对历史长河中丰富的取法资源,篆刻工作者要深入历史、挖掘史料,通过篆刻作品讲好时代故事,忠实记录、深刻反映时代的进步。篆刻审美的思路既要尊重历史,又要体现地域特色。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与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风格来源于丰厚的人文积淀。河北这方热土上的历代遗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从器出”——以“中山三器”为例
河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钟鼎金文及刻石形式多样、数量巨大,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在燕南赵北之间,曾经存在一个神秘的“中山国”。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平山县三汲乡发现了中山王厝墓,出土大量璀璨夺目的瑰宝。其中就包括镌刻长篇铭文的“中山三器”,分别是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和中山王方壶,揭开了中山国度的神秘面纱,开创了当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书法等学科对战国新领域的研究。
我们之所以研究中山国古文字篆书,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山文化,为当代印学创作另辟蹊径。在中山王厝墓中,共发掘出带有文字的器物118件,篆书铭文共计2458个字,主要集中在“中山三器”的器身上面。其中,中山王鼎计469字、中山王方壶计450字、中山王圆壶计182字,文字铭刻精致、体型修长、端庄秀丽(图1)。
“中山三器”的铭文风格可以说是北方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从篆字的构形到具体的笔画局部,都展示出迥异于其他国家的独特风格,从这些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身处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人之审美喜好。中山国篆书文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使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为我们当代的书法创作、印章设计提供了又一条取法之路。当代的书法家和篆刻家有责任向中山国文字取经,让存在千年的中山文化再铸辉煌。
研究中山国文字能够丰富当代篆刻创作取法的种类。以中山国篆字为创作导向的篆刻作者,弥补了当代篆刻创作蓝本导向的不足,其引导大家关注契刻文字风格的研究(图2)。古文字的范畴涵盖着“中山三器”的铭文,对于中山国的篆字构形也应该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去探究。在中山国的铭文当中,有一些没有使用目的和象形意义,这些面貌整齐的篆字篆法、章法,与同时期金文体系的错落有致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秦代“婉而通”的小篆拉开了距离。中山国的文字从构形到笔画、从风格到审美,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我们不仅要从书法的技巧角度去体味,还应该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去考察。
“中山三器”的篆字铭文属于战国时期金文的体系,我们看到的实物并非是墨汁书写而来的。据专家考证,这些精美的文字是采用以铸造为主、凿刻为辅的手法结合而成,呈现出金石的浓郁气息。其整体气象有类于秦代的小篆,但实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山三器”篆书铭文的线条,看似尖起尖收,甚至有柔弱之态,但是近观实物能够发现存在着丰富的变化。当代的很多作者,只是將其写得尖细而坚挺,看似文雅,却失去了中山国篆字铭文线条的精神内涵。我们观察原物,发现它的线条质感,既有北方民族的刚强坚韧,又有南方诸国的温文尔雅。所以,对于“中山三器”铭文的书法、篆刻创作,应该从它的精神内涵延展到线条质感、用笔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尝试和探究,切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以中山国篆字铭文风格进行篆刻的创作,要从构形、用笔等方面进行琢磨,需要下更多的字外之功。要对古中山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比如中山国篆书体系并非只有“中山三器”铭文,还有一些其他风格的篆字出土,有的与“中山三器”篆书风格截然不同,甚至吸收了楚系文字、齐系文字的基因。只有对中山篆字体系的脉络、文化背景有所熟知,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中山国篆字的本源和要旨。将一种体系的古文字印化到印面当中,并非单纯地将它从原有的载体转移到另外一种载体中去,而要遵循篆刻的规律加入变化的因子,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丰富艺术魅力的中山国文字印。明代书法家赵宧光就曾这样说过:“大抵制作须着刽子手段,鉴赏须着金刚眼睛。”
“印从碑出”——以祀三公山为例
石家庄地区元氏县封龙山的《祀三公山碑》(图3),为缪篆神品。所谓缪篆,是汉代摹制印章所用的一种篆书体,它虽然属于篆书的一种,但有别于大篆和小篆,篆法也不完全按照《说文解字》的要求,有其自身特点。它的碑字结体方正,字形平匀有序,不同于前朝秦篆字体修长,也不同于汉代流行隶书的逸纵取势,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平直俊朗,与印章刻制有契合之处,使得结字庄重沉实、妙趣横生,整体章法茂朴天成、遒劲浑厚、醇和典雅,进入一种纯粹的艺术自由状态。缪篆使得入印的笔画刻起来更加便捷,其结构呈现出方、平、均、叠、满的特点。汉印形制多为正方形,出于章法布局的需要,因此每个字形也设计为正方形,以求字形填满空间,凡笔画转折处也由篆书的弧形变成方折。由于缪篆相对于小篆、大篆较为简单,所以缪篆入印比明清流派以篆书入印相对好学。河北的《祀三公山碑》便是缪篆学习的绝佳实物,其碑拓是后世临摹的优秀范本。
汉代的篆书刻石非常少,它已经步入隶书成熟的时代,秦代及之前的篆书慢慢地退出了文字的舞台。但是在祭祀等重要场合,仍不得不用篆书。为了显示威严和礼仪,当时有些书写者不太熟悉篆书,于是大胆地取隶书的形态置换篆书的反复盘绕,从远处看以为是通篇的篆书,但是细看这些字体又并非篆书,似隶非隶、似篆非篆,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后人便把这种介于篆隶之间的字体称作缪篆。缪篆也并非是求新求异,而是当时的书写者对古文字掌握不熟悉所致,“将错就错”,与书法即兴创作相结合而孕育出来的结果。清代方朔云《枕经金石跋》记载该碑:“隶也,非篆也;亦非徒隶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亦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亦不能为此书者;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篆书与隶书的杂糅通融,演绎了汉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祀三公山碑》是篆书向隶书进化的代表作,它减少了篆书的反复盘曲,加入隶书的蚕头燕尾、横平竖直。该碑的书法浑厚遒劲、高古茂朴,历代篆刻家都非常重视此碑书体的学习。清代书法名家康有为、杨守敬称该碑为“瑰伟”;日本书道界人士也赞叹其为“神碑”,看到此碑均如获至宝,认真领悟习摹。
《祀三公山碑》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还有对当代篆刻家、书法家的启迪,便是如何在创新与传统之间进行取舍、与时俱进,如何博采众家之长开创出一种具有古人传统又有横生天趣的独特风格。吴昌硕在看到《祀三公山碑》之后就深受启发,他将《钟鼎文》《石鼓文》《祀三公山碑》三者之间的文字进行融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齐白石在看到吴昌硕的作品之后也深受启发,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开拓与发展,其长足进步取决于《祀三公山碑》。翁方纲云:“碑凡十行,每行字数参差不齐,字势长短不一,错落古劲,是兼篆之古隶也。”齐白石的书法正是受到该碑的影响(图4),篆隶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方正雄伟,异于常人,符合他爽辣的个性,形成独特书风,主导了他的篆刻风貌。齐白石学习篆刻,先学江浙大家丁敬、黄易,又向赵之谦、吴昌硕学习,最终从《祀三公山碑》等名碑当中得到启发,他将文字的圆笔篆书改为方笔篆书,形成了独开局面的单刀入石的刻法,齐白石的篆刻章法强调疏密关系,在空间分割上大起大落、猛利冲杀、淋漓畅快,创造出大写意篆刻的独特风格。
齐白石在艺术见解上推崇“独造”,不走常人之路并且身體力行。他曾经说过:“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古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独到处,如今昔人见之,亦必钦仰。”由此可见,齐白石对自己的文字取法充满着自信和自负。当代的林健、王增军等先生,以《祀三公山碑》文字风格入印自成一家,别有天趣(图5)。
“印从壶出”——以满城县刘胜汉墓铜壶铭文为例
我国的汉字源于象形,来自于对万物造化的深刻感悟,与生俱来就蕴含着被装饰美化的可能。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吴越、楚国等地就在青铜器皿、兵器上面采用错金银的技法对篆字进行刻意的美化,由此产生了赏心悦目的装饰效果。反观北方地区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粗犷沉雄,这种精雕细刻的文字实属罕见。然而到了西汉时期,却出现能够和南方诸国相媲美的篆书杰作,它就是满城刘胜墓铜壶铭文。
满城刘胜墓出土了两件铜壶,它们在珠光宝气的陪葬品中只是不太起眼的日用器,然而两件铜壶上刻制的铭文以其娴熟高超的技巧和异于常人的想象力,令翻译者目瞪口呆,这些装饰的文字震惊了世界,也为印人创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这两件铜壶的造型大体为侈口,束颈,鼓腹,矮圈足,与同时期的青铜酒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件铜壶的尺寸和形制基本相同,我们将其称之为甲壶和乙壶。铜壶上的文字是一首优美的颂酒诗文,自上而下,朗朗上口,非常具有韵律,它没有着重歌颂诗人吟酒时的美妙意境,而是着重说明饮酒有“充润肌肤,延年祛病”的好处,这些字样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结合的早期记录,主旨都是为了祈福健康长寿。两把铜壶的纹饰和文字都用金线和银线勾出,绚丽夺目、金碧辉煌,产生了误把文字当成纹饰的错觉,由此可见其装饰工艺的极致和艺术效果的逼真。
甲壶的壶盖铭文以蟠龙为中心,将12个花体篆字进行均匀分布,形成整体极佳的视觉效果(图6、7)。它的线条起始处多饰以凤凰头部,中间装饰鱼的形状,鱼游离于线条的外部,但又不脱离字体本身。考虑到主人的地位和身份,该壶所装饰的鸟,乃是能和蟠龙相对应的凤凰,那些萦绕盘曲的躯干线条应该是简单化处理的凤凰的身体,归附于它的短线就是凤翼和凤爪。南北朝时期,梁庾元威在《论书》中讲到,他经常在屏风上面挥洒各种书体,其中就有凤鱼篆书之类的作品,因此可以推论甲壶的壶盖铭文应该就是凤鱼书。这些篆字的纹饰无不彰显出南方诸国富丽婉约的风韵,探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乃中山靖王刘胜的祖上刘邦与他的谋臣干将如周勃、曹参、萧何等人都是楚国人,在夺取政权后,他们自然会将楚文化影响到各地,使之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在这种政风之下,原来处于南方的楚风必然影响到北方,并逐渐与中原文明相融合,刘胜作为刘邦的嫡系子孙,当然不会游离于潮流之外,因此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南方风格在北方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极其富丽堂皇的铭文内容都暗示着主人的高贵身份,透露出古代上层社会祈求常保富贵、吉祥美满的美好寓意。
满城刘胜墓铜壶铭文鸟篆纹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书法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当代印人的鸟虫篆风格印章也有着诸多的有益启示。鸟虫篆是大篆金文的变体,它的笔画蜿蜒灵动、盘曲莫测,有着鸟虫的形状,极富装饰意味,如果用于印章的创作则易于变化、风格独特。鸟虫篆印最早见于春秋,兴盛于两汉,篆刻艺术成熟之后,至明清仅仅有少数印人偶尔尝试,只因受当时理论家“几于谬矣”的消极思想影响。时至当代,篆刻界鸟虫篆印风逐渐恢复并形成一种时尚,它的金石气息和华丽面貌深深吸引着众多篆刻家跃跃欲试,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与近百年来发掘和整理研究古代鸟虫篆印及春秋战国铜器上的鸟虫篆铭文是分不开的(图8)。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需要古代文字资料的滋养,利用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化为己用,用新近发现的古文字入印,经过自身印化的处理过程,这无疑能够为篆刻艺术的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结束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无论精神力量的汇聚、思想共识的形成,还是社会风尚的引领,都需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篆刻艺术在开拓地域文化的传播中,有必要将其背景的搭建、语言的交流、价值的认同进行整合,传统艺术必须要主动适应当代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趋势。要创作出“文质兼美”的艺术作品,必须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独特的地域取法资源正是形成艺术个性的精神家园。燕赵之地留下的历代文字遗产,形成“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核,撑起它的骨架,篆刻艺术的追求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向自然生命运动的投入和沉浸,讲求天、地、人的相合。“和,故万物皆化”,就是这种审美理想的极致体现,这种内在的和谐性是我们今天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篆刻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人生教育和伦理构建功能,指导了篆刻创作的功能要求和审美判断。
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的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批判各类艺术形态,努力追求个体体验向心性修养境界的提升。向燕赵金石资源取法是传统艺术创新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篆刻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中华民族的审美和情感有着天然的亲近。印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历代优秀遗产与传统的篆刻程式相结合,充分运用各种表现手法,甚至“跨界”,增强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传统艺术必须进行创新探索,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与当代审美相适应,才能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钱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