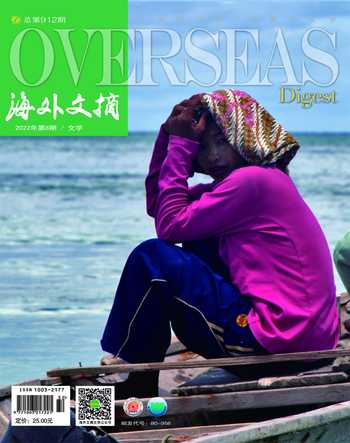洗面
蔡华建

寒冷好像一条凶猛的蛇,咬噬了一切,僵硬地蜷缩和静止着。
那个冬天的早晨,母亲挑着装满东西的箩筐快步走着,我跟在后边,拉着箩绳,几乎是小跑地跟着母亲,走上赣江的浮桥。一艘连一艘的木船连着,上面铺着木板而成的浮桥,人走一步,那桥板就微微地沉一沉,船头点一点,仿佛是向我们母子打着招呼。
江上的雾气迷蒙,迎面撞来,脸上湿冷难受,但母亲走得有些急。我们必须在9 点以前到达才能见到父亲。母亲从洗脸水摊档的那团湿热水汽前匆匆而过,却在前边十几米处停下,拉着我返回到摊档前。我看见,那个黑黑木条的面盆架上,一个瓷面盆装着些热水,挂钩上攀着一条半新旧的毛巾。
“洗面多少钱?”母亲问。
“8 分钱。”那人说。
“两个人也是8 分钱吗?”母亲指了指我。
摊主迟疑了一下,还是点头同意了。他拿起地上用细竹篾包壳的热水瓶,倒了半盆滚水,盖上木塞,看了我们一眼,又拎起差不多要放回地上的水瓶,再添了一些滚水:“洗吧,赶紧趁热洗吧!”
母亲放下箩担,拿下那条毛巾放入盆中,她伸手试了试水温,有些烫,便快速地用拇指食指捏住毛巾边边提起,在盆上来回晃动几下,再双手抓了毛巾拧起来。她散开毛巾,在中间对折,用手掌撑住,蹲下身便帮我洗起脸来。那热热的毛巾,灼得我有些痛,却无比舒畅。母亲换只手,用毛巾的另一面又给我再抹一遍。母亲把毛巾放回面盆,雙手在面盆里搓洗起来,脏水散漫出来,一盆干净的洗面水,变得有些浑浊了。母亲拧干毛巾,自己洗了脸,又放回盆中搓了搓,再洗了一次。那盆水,已经变黑了。我仿佛感觉这一路的风尘、那火车上的黑烟粉尘,还有被急急叫醒还停留在眼角的眼屎,都洗在了这盆热水中,我清醒又精神了许多,母亲也一下子白净、年轻了许多。我隐约明白,在父亲离开家之后,母亲哭了很多次,遭受了无数的冷语风言,此刻,即使赶路,她也花点时间、花点钱,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地在码头洗了面,整理一下自己的面容与状态再去见父亲。
母亲带着我急匆匆地赶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填写探视表格,终于走进了高墙内。父亲仍是不低头,甚至有些不屑,没有一点劳改犯的样子,也没有看我一眼,但他一定看到了母亲年轻而干净的脸,或许这是他此后五年从不担心家里的原因。
我的记忆在六岁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晰。
那一年,爆竹响起了,这是父亲第一次不在家里过年。我感觉到似乎欠缺了一点什么,新年更冷。
我开始上学,时而会遭受一些同学对我的嘲笑,而母亲则需要在这五年里面对更可怕的现实:她除了要支撑着这个家,抚养四个儿女,还要承受来自公婆、娘家、生产队与邻居们的指责与讥讽。那些言语在耳边嘈杂一片,嗡嗡作响,像一千根钢针扎到身上,一万只蚂蚁啃咬骨肉。那些目光,那些背后的窃窃私语,让她想遁地,想隐身,可是这个世界太亮了,在众人的视野之下无处躲藏。母亲有时从外边回来,眼角有泪,或者累得疲惫不堪时,她会在厨房打一面盆水,使劲地洗面,拧了抹,抹了搓,搓了拧,站在面盆架前发呆。我不知道,要如何穿越这内心的地狱,抵达澄明。
终于,父亲回家的时候,是一个傍晚。在大门口,他的衣裳被西斜的阳光染黄,影子在他前面,长长的,像一渠水,悠长地伸进了家里。
母亲喊我:“你爸爸回来了!打盆水给你爸洗面!”我把装着半盆热水的面盆放到面盆架上时,我看见挂钩上有一条新毛巾。
母亲已经四十岁了,她好像迎接贵客一样迎接父亲。
有父亲的新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