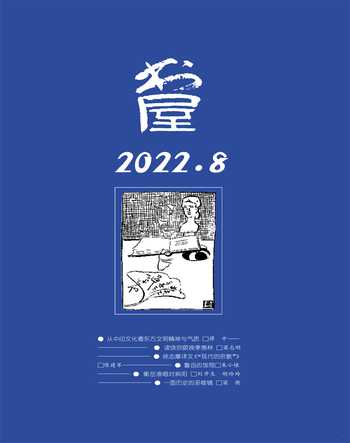读饶宗颐挽季羡林
梁志刚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香港,他的好友饶宗颐写了一首挽诗:《七律·挽季羡林先生》〔用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韵〕:
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
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
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不愧是大家之作,言简而意赅,既表达了对亡友深切的悼念,又恰如其分评价了季老的主要学术成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首诗,缅怀两位敬爱的学界前辈。常言道,诗无达诂。本人的理解难免有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我们先来说说饶公在标题下括弧里的说明。《长沙送李十一(衔)》是唐代诗圣杜甫的最后一首七律,创作于770年秋天,原文是:“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记述的是杜甫与李衔在四川共同躲避安史之乱的经历,表达了他们如胶似漆的友谊。此时饶公得悉季老逝世的噩耗,首先想起杜甫的这首诗,即用该诗的韵脚创作了这首挽诗。
诗的首联是说:我遥望北方,和住在那里的季羡林先生交流对国学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遥睇”犹遥望,古诗有“遥睇月开云”等句子。“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是历史地名,指现在的北京、河北、山西一带,此处指北方。“旧学”就是国学,因为国学也称“国故”。
饶公和季老“商量旧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早在1984年,季羡林就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撰写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序文,向内地读者全面介绍饶宗颐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他说,饶宗颐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露头角,此后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
而1997年蔡德贵写的《季羡林传》出版,饶宗颐在序言中写道:“我所认识的季先生……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夸、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要有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所置喙。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言的。”
中国学术界有“南饶北季”的说法,是说饶宗颐和季羡林是二十世纪并峙的两座学术高峰。他们走过的学术之路截然不同,却殊途同归。季老出身齐鲁贫寒农家,靠苦读而上清华,留学德国,成为东方学泰斗;饶公出身潮汕富商之家,幼承家学,自修成家,终成国学大师。他们都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心竭力,成为学界领军人物,一北一南,相互呼应,惺惺相惜,双峰并峙,形成国学界绝美的风景。
我们再看颔联,说的是季老耄耋之年的两部巨著,《糖史》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新博本译释》以及季老对古代西域语言研究的杰出贡献,这两部著作都是惊世骇俗的学术成就。“榜加”,南亚古国,在现在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糖法”,制糖的方法。据季羡林考证,中国的精炼白糖就是明代从这里传入印度的,所以在当地语言中,“精白糖”一词的意思又是“中国的”。“弥勒奇书”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新疆焉耆七个星废墟中出土的四十四页八十八面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是现今存世篇幅最长的吐火罗文献。季羡林用了十几年时间成功解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佉楼”是古代印度人名,被称为“驴唇仙人”,相传是他创制了古印度拼音文字佉卢文,称为“驴唇体”,这种字母传入新疆,在和田、库车一带有佉卢文献出土。季羡林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佉卢文”词条。笔者理解,饶公此处是泛指印欧语系古文字。季老是研究印度和中亚古文字的权威,所以饶公说“释佉楼”。季老译释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用焉耆文而非佉卢文书写的,属于吐火罗文的一种,是古代西域语种。
颈联的内容,是继续列举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上联“史诗全译”说的是季羡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将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八巨册从梵文译成中文的事。怎么会“骇鲁迅”呢?我理解,这个“骇”是吃惊的意思。鲁迅早在1907年就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印度两大史诗,并给予极高评价。如果他还活着,知道了季羡林翻译史诗时的处境,翻看译文之精妙,一定会感到吃惊,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罗摩衍那》中的猴王哈努曼太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了,这和鲁迅判断的孙悟空的原型是无支祁的意见相左,不能不让鲁迅吃惊。下联的“释老渊源”说的是佛教和道教如何开始传播。季羡林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人尽皆知。而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佛教、道教写入史书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魏收(506—572),《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而季羡林考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对魏收记述中的讹误进行了匡正。
尾联的上句,很明显是化用杜甫原诗中的“李杜齐名真忝窃”句。只是饶公把“李杜”换成了“南北”。这当然是饶公自谦的说法,“李杜齐名”在唐诗中双峰并峙,文学史早有公论;“南饶北季”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公认的,饶公的“忝窃”之说如同季老的“三辞”桂冠,都是难以辞掉的。末句用了“乘化”一词,乘化的基本释义是顺随自然,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季老对生死看得很透,他喜欢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饶公对此一清二楚,所以他用“乘化”借指季老的辞世。此时的饶公想到失去了一位難得的知己,以后在敦煌学、西域学、宗教学方面遇到问题,再没有人可以商量了,不禁感到孤寂与悲凉。
那是2008年10月28日,来京办画展的饶宗颐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下午二时四十五分,饶公到了医院,径直通过安检来到四楼的病房。媒体记者抢先走进季老的房间,只见季老身着浅灰色中装,满面红光,如孩童般期待的神情,双手合十,翘首盼望。这时,饶公出现在门口,双手抱拳,兴高采烈地向季老走来。两位老先生紧紧握手,饶公对季老说:“您是全中国最高的老师。”两位老人一个合十,一个作揖,都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表现了既不同又相通的南北风范。双峰并峙,风景独特,数十年来,他们曾多次相见,把手交谈,可惜,这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