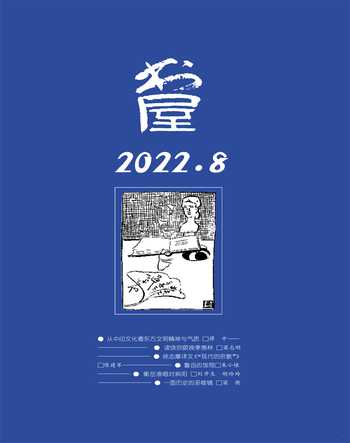一泓源泉各奔流(二)
徐达斯
中国源远流长的“道术”似乎也具有这种弥散化的灵知特征。华夏道术同样针对自然、社会、生命各个面向。据说得自尧舜心传的《尚书·大禹谟》篇,用四个概念标明了华夏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一切大原则,也是中国文化下的人生成长历程,此即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指人在思想、行为方面的修養、持守,相当于吠陀体系里的“法”;“利用”属于经济、政治范围,即运用自然、社会资源,使万民得利、生计足用,相当于吠陀体系之“利”;“厚生”相当于吠陀体系之“欲”,其意为使生命得到厚养;就其精神性而论,“惟和”相当于吠陀体系之“解脱”。此处所谓解脱,非佛教之寂灭,其本质指向一种纯粹、清静、和谐,不受欲念干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状态,也就是“中和”的境界,相当于吠陀哲学的Sattva guna,而Sattva guna正是获得瑜伽觉悟和证梵解脱的根基。在中和之境的基础上,华夏式的解脱可以表现为得道升天,也可以表现为内圣外王。所有这一切,都归属于“道术”,也通过“道术”之实践而得到实现。正德、利用、厚生,三者相辅相成,《左传》所谓“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颜习斋曰:“正德,正利用、厚生之德也;利用,利正德、厚生之用也;厚生,厚正德、利用之生也。”而中和,这种具有超越性的生命状态则始终贯穿于前三者,使入世的人生获得了超越的维度和终极的归宿,用吠陀灵知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即身解脱的境界。
吠陀文献从广义上讲由本集、梵书和经书三部分组成。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主要分为三部分:一为业分,有关婆罗门教日常祭祀和义务的实行;二为智分,涉及超越自我之关系的哲学问题;三为教分,是对自在主的崇拜、奉献。其中,天启圣典的祭文集录以及梵书属于业分,而《奥义书》则属于智分。业分有关现世和来世的繁荣幸福、善恶果报,而智分旨在自我觉悟、证梵解脱,但从学问的立场或从方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将天启圣典作为一切知识的绝对的根据。但在《薄伽梵歌》里,祭祀和解脱、业行和智慧、入世和出世又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以舍离心奉献、以形上智慧驾驭世间业行,显示了业、智之间微妙的体用关系,而吠陀之教分又融摄、渗透业、智,成为最终极的归趣。吠陀典业、智兼备,这种体用合一、内圣外王的学问结构,也是华夏“道术”所一贯标榜的。例如前面讲到的《庄子·天下》篇就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神降自天,明出自人,而圣、王并举,圣者天人合一,王者祭祀通神,皆不离古之道术。庄子又叹后世天下大乱,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道术将为天下裂”。《老子》一书,旨趣玄远,却言不离“侯王”,明显也是传承于“古之所谓道术”。既如“罕言性与天道”的儒家,也必从正心、诚意、修身之内圣功夫入手,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儒、道分流,儒尚事功以保民,道凭内证而逍遥,各立门户。
就认识论而言,吠陀量论有专门的讨论。量,梵文为Pramana,其字面意思是“用来衡量某事物的那个”,通常译为“证据”或“证明”,作为判断活动,它取决于判断者把什么证据接受为是真实的。量有四种:一为现量,梵文Pratyaksa,即从感性知觉产生的直观经验;二为比量,梵文Anumana,即逻辑的推理、类比或类推;三为比较量,梵文Upamana,即从已知推未知的历史类比方法;四为圣言量,梵文Agama,即超越感性经验和意识思量的权威性言论,指吠陀经典和圣者所说,前者来自天启,后者源于禅观,皆赖神性之智慧而得成立。在吠陀文化里,圣言量被视为获得“绝无错误的知识”的最佳途径。这种面授真理的程序,称为师承世系。《泰迪黎耶奥义书》有言:“那就是梵,如果意识和语言去探寻它,必定无功而返。”
梵是宇宙人心的真谛,而为意识和语言所无法了解,“道”亦如是。《庄子·天地》讲了一则寓言:黄帝在赤水的北岸游玩,登上昆仑山巅向南观望,不久返回而失落玄珠。派才智超群的智去寻找未能找到,派善于明察的离朱去寻找未能找到,派善于闻声辩言的吃诟去寻找也未能找到。于是让无智、无视、无闻的象罔去寻找,而象罔找回了玄珠。黄帝说,奇怪啊!象罔方才能够找到吗?
玄珠比喻天道,智辩明察成了得道的障碍,只有去知去识,才能与道相应。故事的立意与《泰迪黎耶奥义书》之说如出一辙,其实也就是老子所谓的“涤除玄览”。
《蒙查羯奥义书》有偈曰:“梵学人谛观,修业所得界,必不动其意。‘彼非创造成,必非由业致。故当往寻师,多闻敬梵者,捧薪求教义。”
这里的“彼”就是梵。梵非业力创造而生,故亦非修业力所能证致,唯觉悟之明师可以授受。吠陀古礼,弟子捧柴薪拜师,以示谦卑奉献。《唱赞奥义书》亦有言:“有师者乃得知天。”《薄伽梵歌》第四章讲说瑜伽之传承:
1.薄伽梵克利须那说:我将这门不朽的瑜伽传授给太阳神维筏斯万,维筏斯万传于人祖摩奴,摩奴又传于伊刹华古。2.这至高无上的知识便如此通过师承世系流传下来,那些圣王们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它的。然而,时光流逝,传系中断,瑜伽的本来面目仿佛湮没了。3.我今天就告诉你这门阐释天人关系的古老学问。你既是我的奉献者,又是我的朋友,必能了解瑜伽的奥秘。
摩奴为人类之始祖,至今尚有《摩奴法典》传世。伊刹华古则为远古之帝王。而师承世系之第一人——日神,乃日神一系帝王之鼻祖。可知《薄伽梵歌》所传之“道”,实为秘密之灵知,且为“圣王”所传承,既是成圣之“道”,又是帝王南面之术。故《薄伽梵歌》称之为“皇华之秘”。在《薄伽梵歌》中,克利须那屡言此歌乃为圣王所作,亦为历代圣王所传承。按此歌以贯通宇宙—神—人为其宗旨,其中实已蕴藏了至高之帝王道,非一般王霸南面之术可比。盖王者受命于天,奉天化民,开物成务,其道与《薄伽梵歌》所倡之业瑜伽相通。或有谓《摩奴法典》为印土之第一帝王书,尚未进于形上之道。从精神旨趣来看,作为帝王书的《薄伽梵歌》或与老子的《道德经》更为接近。
与吠陀体系一样,华夏道术亦特别重视传承。孔子述而不作,自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告子游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尚书》之“洪范九畴”传自亦神亦人的伏羲、大禹。《庄子·大宗师》里更有一份类似天启、圣传之“大宗师谱”: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在这份“大宗师谱”里,“道”排在第一位,后面从神仙至于君相,从太古之初至于三代,序列宛然可见。并且也说到“日月得之”,与出于吠陀“圣传”之《薄伽梵歌》日神传承说相合。
拙著《世界文明孤独史》考证这份名单里的好几位,都与吠陀灵知神话里的人物有关。例如“伏戏氏”即伏羲,为吠陀之造物者毗湿奴;“豨韦氏”即吠陀神话里主毁灭的大神湿婆;黄帝即吠陀神话里主创造的四面大神梵天;西王母即湿婆之明妃难近母;气母即阴帝女娲,为毗湿奴之配偶Rama devi。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帝。道家黄老派之书,甚至很多术数、方技类的古书,比如《黄帝内经》,大多依托黄帝立说。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之《十大经》的记载,中外很多学者如叶舒宪、郁龙余等都以为黄帝与梵天可能为同一神。饶宗颐先生在《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中且考证道教之老君,最早亦有四面,而“四面老君”即出于黄帝四面的传说。黄帝即是殷商卜辞上所说的“黄宗”,周时楚、汉、唐则称作黄神。湖南宁乡黄材地方出土的殷器人面方鼎,四周作四个人面像,状貌慈和,饶先生以为即象征黄宗四面。
老子之学本于黄帝,汉世称黄、老。老子《道德经》中“谷神不死”数句,即出自《黄帝四经》。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黄老之学可谓根深蒂固,不但远超儒家,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甚至与上古婆罗多之灵知神话与灵知义理相通。据此看来,黄老之学可能更接近庄子所谓“古之道术”。
在吠陀“往世书”部分里的另一部重要灵知作品《薄伽梵往世书》里,有薄伽梵克利须那于创世之初传“薄伽梵法”于“黄帝”——梵天的记载。其中的四句偈被认为是世间万法之种子。其第一颂云:“梵天啊,在创造之前,除了我之外,一切都没有,存在着的只有我——至高无上者,超出因果之外。你现在所见到的一切也都是我,在毁灭之后仍然存在的也只是我。”
我们将这首偈颂与《庄子》“大宗师谱”开头的一段话来对比一下: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这段话被历代学者们公认为是《庄子》全书论道最重要最完整的文字,是其道学思想的总纲。按“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即是四句偈之第一颂里的“在创造之前,除了我之外,一切都没有,存在着的只有我——至高无上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即“你现在所见到的一切也都是我”;“无为无形”故“超出因果之外”;“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即“在毁灭之后仍然存在的也只是我”。表面不同的是,作为形上本体的人格性之宇宙大我,梵文Aham,转成了存在论的非人格性之“道”。不过庄子却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无形”是“道”非人格性的一面,而“有情有信”却透露出人格性的本体特征。“道”是整体大全,一阴一阳,通乎神明,合为天地;“天地”是自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非人格性存在的体现;而“神明”是精神、生命、超越性的人格性形上本体。假如“道”能够“神鬼神帝”,而自身却缺失精神与生命,岂非荒谬之极?道“有情有信”,为天人之感应,非人力可以袭取,故“可传而不可受”,道“无为无形”,必去智离形而后可以证得,容不得丝毫情识攀援,故“可得而不可见”。证道之途,亦与瑜伽之法如出一辙。《薄伽梵歌》第九章揭示了同样的“玄理”:
4.我以无形之身,充塞于天地之间。众生皆在我里面,我却不在他们里面。5.然而一切受造之物又不住我之中。看哪,这就是我的玄通大用!虽然我是一切有情的养育者,虽然我无所不在,我却在天地之外,因为我是天地之根。6.要知道,就像强风处处吹遍,却仍在天穹之内,一切受造之物皆住我之中。7.贡蒂之子呀!当劫终之际,天地万物皆消融入我的自性;当下一劫波开始,我又以自己的力量再造天地。8.天地大道从我流衍。在我的意志之下,天地不断自行复生;也是在我的意志之下,天地最后又归于崩坏。9.檀南遮耶呀!所有这一切作为不能束缚我。我冲虚自处,绝不会对此有所执着。10.贡蒂之子啊!物质自性在我的意志之下运化,创生动不动一切存有。天地顺乎自然之道,往复生灭以致无穷。
“万有”与“我”,宇宙表象与精神本体,即一即异,并行而不悖,一体而共存,共同构成了既内在又超越的终极实在之整体。这在中印古圣看来并不矛盾,反倒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或者acintya shakti(不可思議之能)的体现。
印度教几乎各大宗派都有对《薄伽梵歌》的传承注疏,除了商羯罗一派,最古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支即梵天传系。该传系历史上有记载的传承者包括十四世纪著名的经学大师摩陀婆、十六世纪的精神领袖摩诃波菩,以及二十世纪的吠檀多学者巴布巴。其师承世系上溯至毗耶娑,亦即吠陀典之撰述者,最终推到梵天以至克利须那。假如这个自梵天或曰“黄帝”传下来的道统成立的话,中印经学比较将为华夏经子乃至中国文明的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因而,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彻底检讨中国文明、华夏经子的起源和演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