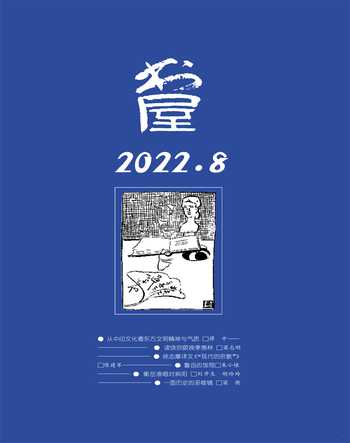从中印文化看东方文明精神与气质
谭中
一
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作《大亚洲主义》演说,认为“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古希腊、古罗马等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认为“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孙中山说的把文化传给古希腊、古罗马的亚洲以及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的亚洲,指的主要是印度。这“大亚洲主义”现在没人讲了,代之而起的是季羡林的另一个著名理论。他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从整体观念来看,本不应该把文明分割成“东”“西”两半的,这种分割是西方文明强加于我们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既是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既崇拜西方文明,又看到西方文明的严重缺点。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中说:“在别的(西方)国家有堆积如山的财富,生活好像是在古埃及国王的坟墓之中。那些财富凶恶地嚷道:‘滚开。当我在你们国家(中国)发现日常物资的魅力时并不感到它们在驱逐,而是听到它们的邀请:‘来吧,请接受我们。”
泰戈尔甚至把西方的统治精英形容为碾死“东方和西方的伟大文明”的“超前的小学生们”,说他们“都是些自作聪明的、吹毛求疵的自我崇拜者,利润和权力市场上的狡猾讨价还价者……”1941年泰翁临终前写了《文明危机》(Crisis in Civilization),结尾说:“我环顾四面八方,看见一个骄傲的(西方)文明倒塌,变成一大堆枉费心机的垃圾。”又说:“可能从这地平线上、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会来到。”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与泰翁的评论取得共鸣。
以中印两国文明的共同智慧为支柱的东方文明有三大气质:(1)中国的“世界大同”与印度的“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2)中国的“天人合一”与印度的“Brahmatmaikyam”(梵我一体)相輝映,发展出中国的“和谐”以及印度的“Santi”(和平)与“Ksanti”(容忍)美德;(3)提倡精神高尚的“清流”,提倡“真善美”。
中国文化对人类智慧的一大重要贡献是“大同”概念,是一个无法翻译成外国语言的思想符号。阐述这一光辉概念的著名文献是《礼记·礼运》,开宗明义地道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把这句话移植到现代生活中来,意思就是:如果全世界都被真理照耀的话,公共的利益就应该成为大家的普遍关注与行动指南。
从泰戈尔著作中可以看出“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思想。他说:“在印度历史上有客人不远千里而来,那时这个国家(印度)和世界联通。但是那间客舍早已关闭,基础垮掉。我们必须从母亲的仓库中找出所有的物资来把它重建。”他又说:“在现代世界地理的边界已经丧失意义。世界不同民族更为接近。我们必须认识这点,同时懂得这种接近应该建筑在爱心之上。”
泰戈尔在自己的事业中试图把“天下一家”的观念付诸实践。1920年12月11日,泰戈尔在纽约写信给中国文学家许地山说:“让我们使地理障碍的幻景消失,至少在印度的一块土地上——让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成为这块土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名叫“Visva-Bharati”,是泰戈尔根据《吠陀经》引语“yatra visvam bhavati 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聚会)起名。1928年应泰戈尔邀请去国际大学教书的谭云山,自认为是效法玄奘“白马投荒”,进了泰戈尔这“世界鸟巢”就无法像玄奘那样变成“大雁”飞回中国了。相反地,印度土地上却多了一所“中国学院”。
“中国学院”是“中印学”的发祥地。它实际上也成为地球上少有的、实现印度“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理想的世外桃源。它在印度独立前与印度民间领袖例如国大党不同时期的主席甘地、尼赫鲁、苏·鲍斯等都有联系。印度独立后,共和国的第一、二、三任总统(普拉萨德、拉达克里希南、侯赛因)都因为是早期“中印学会”会员而与谭云山保持接触,开国总理尼赫鲁更是“中国学院”的常客。“中国学院”也是海外少有的迎来了两位中国重要人物的学术机构,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访问于此。
季羡林对中国的“天人合一”与印度的“Brahmatmaikyam”(梵我一体)相共鸣的解释是:“印度与中国都把宇宙(自然)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人类和大自然互相热爱、互相友好,和睦共处。”
从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梵我一体”的共鸣中,出现了中国的“和谐”以及印度的“Santi”(和平)与“Ksanti”(容忍)的美德。中国古代哲学以一个“仁”字为核心。这“仁”字右边是“二”(社会由“己”与“人”两个人组成),又是两根平行线(各自发展不会互相冲撞)。印度“Santi”(和平)汉译为“寂”,由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文学中增加了“寂定”“寂寞”“圆寂”“禅寂”“寂灭”等新的概念。印度“Ksanti”(容忍)的诉求最为突出,佛陀也叫“忍仙”或者“忍辱仙”,印度“忍”的诉求对中国精神修养贡献很大。许慎《说文解字》上的两个“忍”字,上部从“刀”的是“怒”的意思,从“刃”的是“能”的意思。
中印两大文明都提倡精神高尚的“清流”,贬抑物质贪婪的“浊流”。印度教传颂最多的《薄伽梵歌》强调“灵魂纯真”,认为功利是对身心的亵渎。中国文人以“濯清泉以自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骨可朽烂心难穷”(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等心情提倡气节,不和世俗“同流合污”。中国的“真善美”概念来自印度,意译印度教徒祷告中的理想境界“Satyam”(真理),“Shivam”(神的纯真),“Sundaram”(美感)。印度这一格言意思是:真理就是神,神就是美,美就是真理,如此循环无穷。
著名佛学家僧肇(384—414)在《肇论》中突出“真谛”与“圣心”,正是“Satyam”(真谛)与“Shivam”(圣心)的准确翻译。唐儒李百药(565—648)在《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中用了“舍俗归真”与“德润慈云”,也和僧肇的“真谛”与“圣心”同调。“苦瓜和尚”石涛说:“治心功夫在定静,治人功夫在诚信,治事功夫在精规,治身功夫在勤养。”又说:“修道人要遣其欲、静其心、平其虑、改其恶、从其善。”石涛是名画家,不但是山水画的始祖,又有精辟的山水画理论。他说:“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这不但把“禅”的思想境界贯彻到中国山水画上,也把美术与“真”和“善”结合起来了。
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于2004年6月14日在北京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五十周年的研讨会上讲演说,这“五项原则”是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理念在现代的发扬光大,是中印两国谈判西藏贸易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先提出而为印度代表团接受的。尼赫鲁总理在印度国会欢迎这“五项原则”,举了佛教“五戒”(Panchsheel)为例,又说,他在印度尼西亚看到这“潘查希拉”(Panchsheel)被政府宣布为施政原则,他因此觉得这是个“吉祥的词”。
纳拉亚南1994年作为副总统访华时,在复旦大学讲话中说:
1955年在三藩市庆祝联合国十周年的会上,中国问题得到了讨论。尼赫鲁在1955年7月20日写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说:“私下的建议是吸收中国加入联合国,但不参加安理会,而让印度去占安理会的席位。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是要把中国排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在安理会内是不公平的。当时我们就对做出这一建议的人表示反对这一建议。我们更进一步表示,虽然印度也是大国,也应该进入安理会,但在这一时刻我们不急于进入。现在第一步是应该恢复她(中国)的合法地位,以后再另外考虑印度的问题。”
尼赫鲁这种在国际上维护中国利益的高尚行为也是东方文明气质的具体表现。
纳拉亚南在担任印度总统期间于1998年11月7日亲自到圣地尼克坦去主持谭云山誕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且在纪念大会上称赞谭云山“使(中印)两大文明相互靠拢,进行意义深长的了解和积极的合作”。他于2000年以总统身份访华时,曾在北京大学说了“印度和中国的相互吸引并不限制在宗教、哲学和学问的领域,而是覆盖着人的活动、行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在智慧、美感、人道的基础上深深扎根”。他认为“印度和中国在互相交往、学习、合作上可以大展宏图”,这些话都是东方文明气质的表现,旁证中印关系“天造地设”。
二
季羡林写《商人与佛教》文章,认为印度佛教初期僧侣与商人“互相依赖、互相支持”,我们从石窟艺术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中部到西海岸到阿富汗、到中国新疆、甘肃传到中原的运行轨迹看出:“丝绸之路”与“法宝之路”是一而二、二而一。中印文化交流繁荣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唐、宋两朝佛教兴旺、贸易繁荣就是最好的例证。
茶叶在古代是药石,是佛庙为了款待贵人施主而使它变成高贵的“香茗”饮料的。高贵茶叶生产始自佛教繁荣的唐朝,由于“香茗”需要漂亮茶具,产茶工业刺激了瓷器工业的诞生。这样看来,中国这一千多年的两项著名出口生产贸易——茶叶与瓷器——都得益于中印文化交流。
还有印刷工业与出书工业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物质结晶。从汉明帝邀请佛教来华开始,中国历代政府花大量财力、人力、物力“译经”,坚持了一千余年。所谓“译经”,实际上是把印度高僧嘴里讲出来的话用中国头脑消化了变成中国文字。古代印度重口授,没有纸,经典写在树叶和树皮上,难能传承。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藏经》,绝大多数找不到印度原文,都是根据印度来华的文化大师口授而成为中文经典的,中国文库把很多在印度本土已经遗忘的古印度文明的精髓保存下来了。十九世纪,英、印学者是依靠了中文佛教文献(包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才把许多重要的印度考古发现(包括阿育王石柱等)弄清楚,中国文献对弄清印度古代历史功不可没。
《墨子·贵义》提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可以证明中国文明几千年来重视文字传统。中国早就有了笔墨纸砚,印书工业却千呼万唤出不来。个中原因是:中国传统缺乏大众化的教育机制。到了唐朝,出现了两大潮流:一是旨在“以寒素代替门阀”掌握政权的科举制度,要求民间多出“读书人”;二是佛教被统治者和权贵提倡,而佛教不像儒家那样限制在知识精英阶层,而是要渗透到全民中去的宗教文化运动。正是由于庙宇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而又成为农村与城市广大爱好读书的青年看书与借书的地方,唐朝科举制度才能够成功地把新鲜血液吸收到统治机制中来。
印度摩亨约·达罗(现在巴基斯坦境内)三至四千年前就有印章,比中国战国古印早得多。向达等学者认为,中国印刷术是受到印度拓模佛像的启发。可是印度古代重口授,没有中国这种文字传统,也没有唐朝那种扩展大众文化的动力,所以其原始的印刷传统就像藏在草丛中的鸡蛋,只有到了中国的鸡窝,在中国母鸡羽翼下,才孵出印刷工业和出书工业来。
我和北大耿引曾合著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书中(第十二章)谈到“印度文明送给中国文明的文化、艺术礼物,可以分成科学、技术礼物和非科学、技术礼物两大方面”,包括植物、医疗、算术、天文、艺术、烹饪、武术等。薛克翘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与《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对此介绍得更为详细。但中印文化交流在“器”(物质文明)的方面如何使中国文化大变样仍然值得更深入地研究。
印度文明的投入使得中国精神文明“道”的含金量大大增加。宋儒张载就是中印文化“融合”的典型,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发扬孔、孟、老、庄的思想传统,又是中国传统言论中的新潮。这四个“为”中最有新意的是“天地心”“往圣”与“太平”。“天地心”显然是引了六世纪当了和尚、法名“慧地”的刘勰(465?—532?)所著《文心雕龙》中的“天地之心”,刘勰却又融会贯通了佛家的“八识心王”“心王如来”等概念。“往圣”是泛指宇宙圣哲,这是佛家在中国非常强调的。“太平”当然不是中国过去那“太平无事”的观念,它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境界,使人想起《大乘起信论》的“如来平等法身”和《金刚经》中被视为“无上正等菩提”的“法平等”。
我认为张载“为往圣继绝学”涉及中国学术的内容与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刘勰在《灭惑论》中就探讨过了,刘勰赞扬中国政府与民间大力把佛教理论从梵文翻译成中文说“一音演法,殊译共解”,是指不同印度高僧来到中国用不同的词汇与思维逻辑诠释佛的“法音”,中国又通过翻译使得这些不同的诠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共识,这就是他说的“梵汉语隔而化通”(虽然中印两大文明语言不通,可是经过中印文化交流就变成志同道合了)。中国原来研究方法比较贫乏,孔子说“述而不作”,只引述古圣贤的教导而自己不发挥。中国古代的学术作风大致可以称为“语录文化”,总是围着名人语录转圈圈,很难离开语录发挥自由思想。
宋明“理学”“心学”专家明显地继承了佛学研究传统。最喜欢重复张载“四为”名言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在赴京赶考时,袋子里装着禅师大慧的语录。朱熹发扬“水月”方法而强调“月印万川”,强调“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这样看来,“理学”融合了中印文化,在学术上扬弃了“语录文化”传统。王阳明(1472—1529)提倡的“心学”,他在《传习录》中把《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发展成“良知”,又发挥“心即理”,与朱熹《观心说》的“存心而可以养性事天”相呼应。其中更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名言,这就更明显地采用佛学方法来阐明他的哲学思想了。如果它们是“新儒学”,那这“新儒学”就是中印文化的融合了。
中国“五湖四海”精神,经过中印文化交流的“鼎盛”期得到弘扬与巩固。僧祐(445—518)在《弘明集·后序》中说:“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狭隘的在“华”与“夷”之间设置楚河汉界的传统,符合中国作为许多不同民族建立起来的共同体的实际。
“五湖四海”曾出现在李白727年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文中有“浮五湖,戏沧洲”与“浮四海,横八荒”,也许正因如此,“五湖四海”变成代表宏观整体中国概念的代名词。李白诗句中也贯彻了这“五湖四海”情调:“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日从海傍没,水向天边流。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赠崔郎中宗之》);“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古风》)。印度传统把人生比作“逆旅”(客舍),这一典故由佛教传到中国。宗炳写道:“若鉴以佛法,则厥身非我,盖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长存而无已。”李白作《拟古》诗,有“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他也是看透红尘却怀着天地逆旅观念的诗人。
在中印文化交流的良性影响下,中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逐渐丰富,结束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规律,夜晚的活动多了,神州大地出现对“明月”的新的敏感性,李白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静夜思》以二十个字创造了新鲜而又绝妙的诗境。如果只念一两次,这诗十分平淡,可是越多念它就越体会到“千里共婵娟”的情感,把中国变成一个整体的文明世界,又使人感觉到“明月”是这个文明世界的灵魂。这首诗的灵感出自玄奘以印度语“月亮”(Indu)为“天竺”正名,改为“印度”以形容在佛法照耀下“白日既隐,宵月〔烛〕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
中印文化交流在中国传统的“和为贵”基础上添上“慈悲”与“戒杀”精神,铸造了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隋文帝举义旗创建隋朝以后,仿效印度阿育王在战场上建塔。唐太宗也效尤,颁布《收埋骸骨诏》与《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这明显是用佛教“慈悲”与“戒杀”思想来倡导和平治国精神。七世纪唐儒李君球劝阻唐高宗伐高丽说,如果人民“疲于转戍”,就会“万姓无聊生”“天下败”。韦凑劝阻唐玄宗征安息(中亚邻国),认为崇尚儒术的汉武帝征战频繁,使“中国疲耗,殆至危亡”。
唐朝诗人不遗余力地传播和平、反战思想。李白的《战城南》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春望》都是反战名诗。毛文锡(十世纪人)作《醉花间》,描写闺中少妇“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正是对陈陶(812?—885?)《陇西行》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回应,读了令人厌战。和平、反战文化的积累使得宋太祖与宋太宗创立宋代内政、外交“重文轻武”传统。
中印“心”“性”修养融合起来形成坚韧乐观的性格。著名宗教学家任继愈等认为:印度“心”(Citta,汉译“质多”)泛指一切精神现象,佛教“一切属‘心之现象,称为心法”,这样就大大扩充了中国“心”“性”双轨道德建设发展道路。佛教把印度哲学的重要法宝“Bodhicitta”(菩提心)赠送给中国。禅宗有“心即是佛”“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朱熹和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心”“性”双轨道德建设的最大专家,使中华文明生命力更加强大,也使中印两国在“修身养性”(例如“太极拳”“瑜伽术”)上成为杰出榜样。
三
古代印度由同一文明的众多国家组成,是“文明世界”,古代中國是同一文明的统一实体,是“文明国”。中印文化融合使中国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具有世界性的“文明国”对邻近部落、民族吸引力越来越大,吸引他们参加进来。中印文化融合又使中国精神文明的“光谱”扩大许多倍,使“文明国”内部矛盾得到调和与控制,使中国发展出促进大一统的凝聚力。泰戈尔对中国文明“器”“道”兼备,既重物质,又重精神,深为欣赏,1924年在中国讲演时说:
在中国,你们并不是个人主义者。你们的社会本身是你们合群的灵魂的产物。它不是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头脑的结晶——不是无限止竞争的混合而拒绝承认对别人的义务……诚然,你们对这个世界,对你们周围的物质的东西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从来不用独占的高墙把你们的财产围起来。你们和别人分享财富,你们热情招待远朋远亲。你们并不是富得不得了。这些都是因为你们不是物质主义者。
他在1924年的中国讲演以及1937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揭幕式上,一再重复赞扬中国文化“直觉地掌握事物的秘密——并不是科学中的那种能源的秘密,而是表现之秘。这是一种神力。我羡慕这种神力,希望我们人民能够与他们分享”。他认为中国文化气质比片面强调精神文明的印度传统优越,却没有强调这是印度文化投入中国所产生的良性结果。
中印文化起初在神州大地重叠,交流以后就产生“识别大演奏”现象而使原来的识别模糊。中印文化融合是“潜移默化过程”,需要不戴教条主义眼镜、不把文化套上“儒”“道”“佛”框框才能敏锐发觉与深刻体会。这样的体会还可以帮助中国国学研究摆脱西方学术界强加给我们的种种歪曲,使中国文化发展恢复其历史真实面貌。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以使未来少走弯路。当今世界秩序受到“地缘政治范式”统治,国际关系研究权威把“文明”打入冷宫,以致中国和印度变成两个互不了解的陌生国家。我们必须把泰戈尔和谭云山提倡的“中印学”振兴起来,必须从季羡林“天造地设”的观点更深刻地总结中印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使中国大变样的具体细节,构成一幅“地缘文明范式”的历史蓝图。以这一蓝图为典型,可以把今后的中印关系发展成新的“地缘文明范式”。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