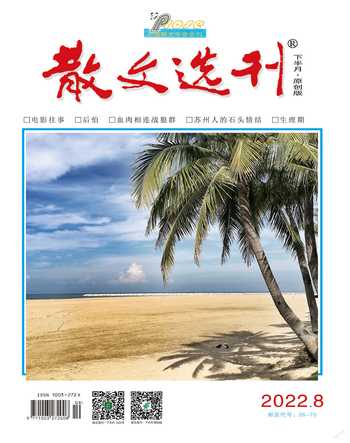后怕
冯积岐

这是2002年春天里的事。
那天,因搭错了车,才到了东新街。下了车,去找702路的站牌子,抬眼一看,马路东面围了许多人,耳朵里钻进去的是刀刃一般的叫声,出于好奇,就围过去了。拨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到跟前去看,叫声发自躺在地上翻滚着的一个人的口腔。他的头被上身的灰色夹克服罩着,不见面目。从不断喊叫的声音和毫无款式的姿势上看,年龄在三十四五岁左右,不知是什么时候开打的,我目击的只是打人的一个片段。一个四十左右的男子抡起小圆凳子的铁腿在躺在地上的男人身上毫无节奏地乱捶。凳子的座面已被打飞,躺在被打者的身旁。还有一张凳子的座面和失去体面的凳子腿乱七八糟地撂在被打者的身旁。我估计,这张凳子也是招架不住人的肉体而被打得魂飞魄散了。可见,那具活生生的肉体是很能挨得起人的击打的。那个抡着凳子腿的男人气喘吁吁,站在他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可能是他的同伙,不时地用脚在地上的男人身上乱踢。凳子腿击打肉体的声音越来越灿烂,而人的喊叫声越来越苍白了。周围围着的大约一百号男人和女人都屏声敛气似的,悄无声息。这镜头,比影视剧中施暴的场面真实得多,可怖得多,残酷得多。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当那男人举起凳子腿要向被打者的头上猛击过去的那一刻,我抓住了他的胳膊,那男人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他将举在空中的凳子腿慢慢地落下来,然后,撂在了地下。这时候,有两三个女人走过来,劝那男人不要再打了。两个男人拍拍手,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连一眼也没再看躺在地上微弱地呻吟着的被打者,急忙去赶车了。
坐在车上,我只是想,那男人为什么在我拦住他以后,不再打了?他是不是把我当作了派出所的便衣?抑或是,他打的程度恰到好处,我一拦,正符合了他的意愿。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人家绝不是怕我。我没有任何威慑人的气质,也没有使人惧怕的外貌和年龄优势。因为他没有打下去,被打者的头颅才保住了,不然,那狠狠的一击,他的脑袋非被打成米饭不可。说实话,我没有见义勇为的崇高想法,我只是觉得愤慨,觉得残忍,觉得憎恨,觉得人对同类不能施以暴力。于是,就上前去毫不犹豫地拦住了一个施暴者。
回到家,妻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我将在途中发生的事情给她叙说了一遍。妻听罢,吓得脸色苍白了。她说,如果那个人把铁腿抡过来,盖头朝你打下去,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了。我一想,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施暴者能打坏两个凳子,足以说明,他已失去了理智,或者说,他是一个生性十分残忍的人,一个嗜血如命的人,一个亡命之徒。面对这样的人,我不后怕才算是怪事。
我将同情、怜悯、善心、爱心以及人的尊严作为做人的底线,因此,也就极力去这样做。可是,现实生活迫使我不得不承认,人的良知良能、人的尊严和自尊随时有失去的可能。要保证人的尊贵性不丧失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支撑,这就是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仅仅靠老百姓去创造是不行的。因此,我不能说,面對施暴者,那些围观的人就麻木不仁了,也许,他们的心也在狂跳,热血也在沸腾,理智告诉他们,不能去“见义勇为”。也许,那一板凳腿下去,由于一时的冲动,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将失去一个好丈夫或好父亲。他们不明不白地倒下去未必能有好报,我们的媒体披露的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一些见义勇为者被被救者反咬一口的事例也曾见于报端。我想,没有出面阻拦的这些人大概是“前怕”吧。
其实,“后怕”和“前怕”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我祈求的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什么时候能活到既不“前怕”又不“后怕”的份儿上,那就好了。面对暴力,面对威慑,面对一切不公正,能够大义凛然,一身正气,有几分英雄气概,我们的生存环境就能纯净一些,宽松一些。
美术插图:曲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