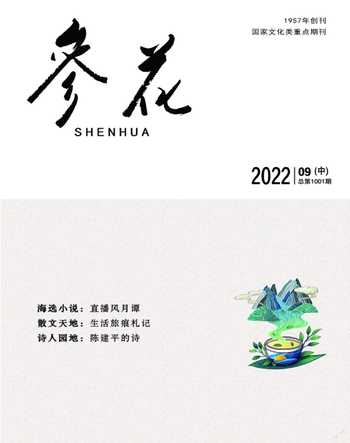浅析《红楼梦》中的“隔”之美
一、引言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以李商隐、韩持国、董其昌等人的诗句和词句为例,认为“他们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明确指出:“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1]在美感的养成、艺术的诞生上的重要性。“隔”带给人们一种层次感、一种距离感、一种朦胧感、一种神秘感,[2]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同时,“隔”也能使对象复杂化,甚至拥有一种矛盾之美。在《红楼梦》中,有不少容易被人忽略的蕴藏着“隔”之美的情节,如大观园中的各种“障景”之美,李纨、妙玉性格中的“隔”之美,人物出场艺术中的“隔”之美等,不仅体现了曹雪芹深厚的笔力、精妙的构思,也彰显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二、“青山缭绕疑无路”——大观园中的“障景”之美
大观园承载了“金陵十二钗”和整个贾府的悲欢,其第一次正式亮相以贾政、贾宝玉一行人的游览为引,通过他们的路线和所见所感展现给读者。据此,曹雪芹为大观园绘制了一张“地图”,而如此详尽的叙述也非常利于发掘大观园的造园艺术和其中蕴藏的“隔”之美。
刚一进园门,便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3]这一带翠嶂,正是使用了“障景”的手法,体现了“隔”之美。翠嶂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在藤萝掩映之间,只“微露”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使用障景手法所带来的天然引导性。因此,宝玉在给这处拟定匾额时说,此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提议直接写上“曲径通幽处”这句诗。依靠翠嶂,不着痕迹地完成了由曲径通幽到豁然开朗的这一过程,体现了“隔”的艺术感与美感,同时,也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内敛之美。
跟随贾政一行人的脚步,继续深入园子,会发现园中的各处房舍也大都遵循了“隔”的原则,不少院落都以自然景物作为障景。如后来黛玉居住的潇湘馆,以“千百竿翠竹”作为遮掩;李纨居住的稻香村,附近不但有“青山斜阻”,需“转过山怀中”,才能隐隐看见“一带黄泥筑就矮墙”,且“墙头皆用稻茎掩护”;宝玉居住的怡红院也是如此,进院需先“绕着碧桃花,穿过一层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
在这些房舍描写之中,有两处使用的障景手法是较为特殊的。一是宝钗居住的蘅芜院。蘅芜院附近诸路可通,于是贾政直接评价这处院落“无味的很”。直到走进院门,“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贾政不禁笑道:‘有趣!”[4]此处欲扬先抑,先写蘅芜院周围没有遮掩,条条路皆通畅无阻,让人心生失望,再写院内的山石障景之奇,并插入贾政的两次评价。从“无味的很”到“有趣”,贾政的评价变化恰恰体现了障景的重要程度,体现了“隔”带给人的美感。二是宝玉居住的怡红院。除了院落外围使用了自然景物作为障景,怡红院卧房内也有着十分特殊的一处障景。贾政等人“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又有窗暂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书挡住。回头再走,又有窗纱明透,门径可行;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相一样——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及转过镜去,益发见门子多了”。[5]怡红院卧房内设了大西洋镜,再加上书架、门户等的巧妙排布,使整个房间显得左右皆有路,但左右皆不通,如迷宫一般。这处障景很有意思,带给人的美感是活泼的,是古灵精怪的,整体布局既符合怡红院富丽的特色,也契合宝玉性格中的乖张成分。
王安石《江上》有云:“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6]障景带给人的美感正是如此,先叫人在一片模糊狭窄之中顿生疑惑和失望,再忽以一豁然开朗之景使人顿悟,拍手叫好。障景手法的使用准确地抓住了人的心理,欲扬先抑,完美地显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含蓄美学观念,顯现出了“隔”之美。
三、“不同桃李混芳尘”——李纨、妙玉性格中的“隔”之美
李纨和妙玉在“金陵十二钗”中,都是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李纨是唯一的寡妇,妙玉是唯一的尼姑。同时,也由于二人的特殊身份,使她们的人生与其他姑娘、奶奶们相比有所不同,处于一种与红尘隔断的状态:李纨被社会规约和礼教所隔开,妙玉被清规戒律所隔开。但其实,二人始终不能完全做到与俗世隔开,其人性的本真在不为人所注意之处悄悄伸展,与规约他们的礼法、戒律不断冲突。这种隔断、矛盾冲突构成了李纨与妙玉性格中的亮色,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且真实可感。
(一)“红衬湘裙舞落梅”:幽闲贞静之姿与青春生命之跃
明清时期,宋明理学占重要地位。李纨作为贾珠的未亡人且育有一幼子,须遵守相应的行为准则,于是李纨“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7]只能被迫沉默着,扮演好一个贞静的寡妇。因此,李纨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笔墨并不多,其大多数时候都是随众人一笔带过。从第一回至第三十六回,除了在第五回中通过判词暗示了其结局外,李纨甚至都没有一段单独的描写与对话。曹雪芹极少刻画李纨,正是因为她寡妇的身份限制了她说话的权利,[8]如此看,落笔极少反而更加突出了李纨的娴静形象,不可谓不是曹翁的巧思。
清人洪秋蕃认为,李纨“幽闲贞静,为《红楼》中极有德行之人”,[9]“有德行”即“理胜于情”。从李纨在第三十七回之前的行为举止看,确实如此,她似乎是一名标准的节妇。但《红楼梦》的十六字纲便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10]可见“情”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正如李纨在元春省亲时所言:“红衬湘裙舞落梅”。李纨虽已如湘裙上绣着的“落梅”,但是内心依旧涌动着翩翩起舞的欲望,渴望展示青春生命之跃。因此,从第三十七回,也即入住大观园开始,李纨的本真性情逐渐展露在读者眼前。
在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众人商议结诗社,是李纨站出来拍定并自荐掌坛的,后响应黛玉所言,提议大家起俗号,配合探春所言定诗社罚约,又主动提议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11]于是在李纨的组织下,便有了咏白海棠的第一社。除在结诗社之时,李纨有着惊人表现外,她对于品评诗歌也有着独特的才气。在评宝钗、黛玉二人的白海棠诗时,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且面对宝玉的质疑,李纨直言,“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12]宝玉这才罢了。在这一回中,不仅展现出李纨充满勃勃生气的另一面,同时,也让读者第一次看到了李纨身为贾府少奶奶的磊落风范。
在诗社以外,对于李纨的着墨也多了起来,不少地方都展现了李纨妙语连珠的一面。第四十五回中,李纨更是让一向牙尖嘴利的凤姐只有赔笑认错的份:“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他还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13]在第三十七回之后,李纨暂时逐渐褪去压抑许久的一面,显露出其本真性情,显得生动活泼、风趣幽默、磊落果决。由此可见,是长期的大家族生活压力生生将李纨的性格隔断,成了互相矛盾的两边:一边是表象的幽闲贞静之姿,一边是内心的青春生命之跃——而李纨不断地在两边徘徊。这便构成了李纨性格中的“隔”,也即李纨矛盾心理中蕴藏的耐人寻味的美。
(二)“浓春色相未全空”:槛外超脱之旨与槛内俗世之往
第十八回脂评道:“妙玉世外人也,故笔笔带写,妙极妥极。”[14]类似于李纨,由于妙玉身份的特殊性,若是过多地描写反而坏了其身份,因此,作者大多时候只是“带写”或者侧笔写妙玉。所以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关妙玉的笔墨也不多:仅正笔两次,侧笔四次。虽只有六次描写,但妙玉此人的真实性情已经尽付其中。
在《红楼梦》中,除第十七至十八回提到妙玉被请到大观园,一直到第四十一回,都没有对妙玉与其他姑娘、奶奶交往的描写,由此可见,妙玉与大观园众人是较为疏离的,也并不热心于攀附权贵,只在栊翠庵独自修行。不特意交代妙玉的生活状态,反而衬出了其幽尼的形象。但正如清人姜祺的《红楼梦诗》:“芳洁情怀入定中,浓春色相未全空”所言,妙玉内心始终挂念着红尘。妙玉是因自小多病才带发修行,而正所谓“尽断三千烦恼丝”,妙玉却是“带发修行”,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妙玉出家便是迫不得已,并非出自本心,她一直与红尘、世俗保持着联系。在第四十一回中,妙玉烹茶招待贾母等人,其中对茶具、用水的细致描写,暗示着妙玉的饮食欲,她对吃食用度的讲究,足以体现其并非完全的“槛外人”。在第六十三回则更为明显,妙玉自称“槛外人”向宝玉“遥叩芳辰”,但祝寿本就是“槛内”之事,以“槛外”之身行“槛内”之事,不正是妙玉心系俗世的写照吗?[15]如此种种,都显现出了妙玉闺阁小姐的本色。
妙玉既是于槛外带发修行、超脱凡俗的幽尼,每天守着青灯古佛过日子;又是真性情、真本色的闺阁小姐,向往着知音,渴望着神交。因受清规戒律的限制,只得在明面上将自己安置在隔绝俗世的那一端。正是这种“隔”,构成了妙玉半幽尼、半小姐的独特身份,她既不能不顾修行,亦不能断绝俗世,只好在其中不断徘徊。这种挣扎、沉浮正是妙玉性格中的独特之美。
四、“千呼万唤始出来”——人物出场艺术中的“隔”之美
《紅楼梦》的人物出场艺术向来为人称道。因人物众多且关系复杂,曹雪芹并未在一开始就直接安排人物出场并单独介绍,而是采取侧笔法,虚敲傍击地通过第三者之口来介绍。这个第三者正是贾府陪房周瑞的女婿冷子兴。在第二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向旧友贾雨村,也向读者介绍了贾府诸人,从宁荣二公至草字辈儿孙,交代得格外清晰。借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之机,在人物正式登场之前,先以侧笔将人物框架搭出,既推动了情节发展,也不使人物介绍显得突兀、冗余,同时,使读者心中已隐隐有了对宁荣二府的印象。侧笔法是一种“隔”,隔雾看花,给人朦朦胧胧的印象,待到后文的正笔描写,一一印证侧笔所叙述的人物特点时,便能叫人恍然大悟、拍案叫绝。
除此之外,在后文的正笔描写中,为使行文显得丰富、流畅,不落窠臼,曹雪芹也想办法安排了“隔”。贾府众人的第一次亮相是在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通过黛玉之眼将众人一一呈现的。其中较为特殊、尽现曹翁用心的,则是黛玉未当面见到的贾赦和贾政二人。曹雪芹虽未安排黛玉见到两位母舅(也即未安排读者与贾赦、贾政见面),不过二人截然不同的个性已经在院落的布置摆设中尽显。在贾赦处,黛玉所见是这样的:“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贾赦是长子,但是所居之所却是隔断过来的,只此一句,便暗示了贾赦虽为荣国府长子,但权力不如弟弟贾政许多。“一时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这句话则从侧面点出贾赦的好色、荒淫。而贾政处的布置则大为不同,“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在正室荣禧堂中,“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再看时常居坐宴息的三间耳房,“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所坐“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而“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16]贾政的居所是荣国府的正室,且贾母亦居住在贾政处,可见相比长子贾赦,贾母更看重次子贾政。同时,日常起居的耳房内的引枕坐褥等物都是半旧的,通过房内摆设,便足见贾政用度节俭、端方正直。
通过院落的布置摆设,而非直接的肖像、言语描写来刻画贾赦、贾政二人,是曹雪芹特意安排的一种“隔”。在先前已有大篇幅的正面描写来介绍贾府的女眷们,若黛玉拜见两位母舅时依然沿用前文之法,不免使文章行文单一呆板,缺少可读性。因此,由黛玉在前往拜见的路上观察贾赦、贾政两人的院落布置,侧面展现两人的性格,既合情合理,又不落俗套。
《红楼梦》中的人物出场艺术真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人物正式出场之前,不断铺叙、侧笔傍击,在人物正式出场之时,又将正侧笔与多种描写手法相结合,充分彰显了曹翁的深厚笔力、缜密心思与“隔”之美。总而言之,《红楼梦》中的“隔”之美,既体现在景物描写中,也隐藏在人物描写中;既表露于人物性格,亦彰显于艺术手法。这不仅使小说整体行文更加生动流畅,也增强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带来了丰盈的层次感、距离感、朦胧感与神秘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王乐.论文学艺术的“隔”之美[D].山东师范大学,2007.
[3][4][5][7][10][11][12][13][1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8][15]李晓华.《红楼梦》中女性夹缝生存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2014.
[9][14][清]曹雪芹,著.[清]脂砚斋,评.脂砚斋评石头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作者简介:李纯叶,女,本科在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