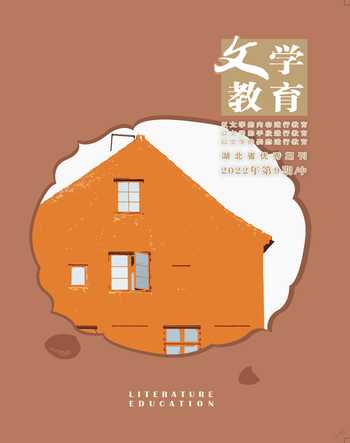论乌热尔图作品的民族书写特色
汤静雯
内容摘要:乌热尔图为文坛带来了独特的鄂温克族之声。回溯童年记忆和直视部族危机,成为乌热尔图自我阐释的两种路径。他以“内在人”的身份建立起非对抗性的言说策略,传达出这一部族对世间万物(包括部族自身)的独特理解,反之也成为维系部族意志,重造文化记忆与传递群体生存经验的有效手段。但需注意的是,乌热尔图的自我阐释并非纯粹,其民族自觉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的历程。对比于迟子建的鄂温克族书写,我们可见二者在叙述身份与意图上的差异。
关键词:乌热尔图 鄂温克族 自我阐释 言说身份 叙述意图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鄂温克族及其生存空间是乌热尔图孜孜耕耘、频频回望的一处精神家园。在9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随笔,如《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声音的盗用与声音的替代》《弱势群体的写作》中,乌热尔图反复提及“自我阐释”这一权力运作的必要性及不可剥夺性,并表现出代群体发声的“非个人化写作”倾向。本文通过细读乌热尔图的作品,意在阐释:回溯童年记忆和直视当下危机是乌热尔图自我阐释的两种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其民族自觉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的历程。对比于迟子建的鄂温克族书写,我们更可见乌热尔图叙述者身份和叙述意图的独特性。
一.从童年记忆到当下场景
为实现自我阐释,回溯童年记忆、书写鄂温克族人的成长故事,成为乌热尔图的叙事选择。但有趣的是,这与同时期书写“独自远行”这一成长经历的小说(如《十八岁出门远行》)构成鲜明反差。乌热尔图的书写基调更为昂扬、明亮。具体表现在:第一,在乌热尔图笔下,人与其所处的文化形态之间是相互顺应、依赖与促进的。一方面,他们尊重自然与文化传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以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底色。另一方面,他们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尊严与力量的张扬、善与美品质的存留。第二,在乌热尔图笔下,人与人之间也是和谐的。鄂温克族内部在代际沟通上表现出的亲密的传承关系,他们以乌力楞为单位,形成命运共同体。年长一辈自觉成为传统的护卫者,将其所知的关于部族起源、迁徙历史的故事以及生存技能传授给年轻一代,以便维持族群的长久发展。年轻一代的个人成长历程也便表现为对部落文化理解的深入和对集体身份的逐渐认同。
由此,回溯童年记忆成为乌热尔图自我阐释的首要路径。但其书写不止于此。他不愿将这一不同于汉民族的生存图景简化为几个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符号,或是对其做猎奇化处理,而是进一步直视鄂温克族人的生存处境与命运变迁,表现出更为厚重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品格。这成为其自我阐释的第二种路径。
首先,乌热尔图直视鄂温克族人生存的艰辛。在《森林的歌声》中,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无法满足族人的生存需求,狩猎成果颇丰时,却“一年到头来还是没粮吃,没布穿。”①简陋的医疗条件更使得鄂温克族女性屡次失去自己的孩子。其次,鄂温克族人的精神世界也遭遇着危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以独特形式表达群体意识的“隐形文本”,诸如部族起源、仪式内涵等随着老一辈的逝去,而面临着失语的困境。《你让我顺水漂流》中,萨满的圣物——神袍被人偷盗,廉价地卖掉,成为博物馆中凝固的文物。萨满,曾作为族中沟通天人的神秘存在,最终却只能以生命的凋零来反抗被物化、商品化的境遇。这不仅是个体的死亡与悲哀,更是集体记忆的磨灭与信仰的失落。
从追溯童年记忆,到直视鄂温克族的当下境遇,乌热尔图携带着宝贵的民族经验与童年记忆,进行着自我阐释。这对于进入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方面,尽管现代医疗、教育、社会公共设施等的完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同样产生了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就在这时我们惊异地发现,为了挣脱压抑与异化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竟要悖逆线性进步发展的时间观念,回溯根深叶茂的传统文化积层,返回原始健康的人类的童年时代。因此,乌热尔图所执着的“自我阐释”,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存图景与认知人与自然的方式。“丰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②另一方面,乌热尔图以发展的眼光书写鄂温克,忠实地还原鄂温克族地当下危机与生存本相,为这一弱势群体发声。鄂温克族所面临的危机,同样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生存窘境与精神迷失的一种反映,也警示着我们反思现代进程中的尴尬与失落。
二.自我阐释的内在流变
当乌热尔图用汉语书写鄂温克族,作为鄂温克族的阐释者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作家的个人形象早已与鄂温克族的整体形象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可以说,乌热尔图是以一个“内在人”的姿态出现的。而此时不可忽略的问题是,言说对象即倾听者是谁?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乌热尔图不是说给自己的族群成员听,而是面向汉语持有者和主体文化进行讲述。在这一言说过程中,乌热尔图的民族身份及民族自觉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的转变。
回顾乌热尔图的早期创作,从族人與地主间压迫与被压迫的紧张关系(《森林里的歌声》),到共产党对鄂温克族人实施救助,从而使族人对山外人有所改观(《瞧啊,那片绿叶》),这些情节都提示着我们,这一处土地并非“关外化境”。鄂温克族始终与主流历史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其困顿与希望、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命运中的重要部分。但乌热尔图的早期创作在处理新生国家政权与鄂温克族人的关系时,往往有公式化与概念化的流弊。鄂温克族人被笼罩在“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这一巨大符号之下,他们被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之上,是等待着被拯救的弱势群体。对主流话语的强烈认同与皈依可见一个弱势群体意欲融入主体的诉求,但也反映了这些弱势群体欲建立起自身主体性的艰难。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乌热尔图逐渐淡去在“胜者”的大写的历史中定位本族群的写作姿态,发出了作为独立自主的“鄂温克人”的独特声音,民族自觉意识更为强烈。此时,乌热尔图作为一个“内在人”的写作优势就凸显出来,而且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乌热尔图更有可能触及这个内含层层叠叠社会文化关系的实体,从而发掘出隐匿在日常生活、习俗、禁忌之中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乌热尔图在面对神秘、丰厚的历史故事与族群传说时,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适时地施以祛魅。这一点在《丛林幽幽》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首先,这一由部族老人讲述的传说充满着神秘与魔幻的色彩,但同时又有着切实的现实指向性。例如鄂温克族人信仰的玛鲁神及其代表物象被遗忘,在置物架上落了灰这一细节,表明了由于老人的逝去而加速的集体记忆的断裂。“游荡萨满”的出现意味着古老精神信仰的复归,但是萨满预言的有效性却在不断地减弱,说明曾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不再圆满。乌热尔图将鄂温克族的生存本相一一呈现,而非意在讲述一个凌空蹈虚的神秘故事。
其次,故事虽然是在一个部落老人的追忆中展开的,但乌热尔图作为一个“隐含作者”经常有意偏离主体故事的讲述,将有关鄂温克族的历史、社会形态、风俗习惯、萨满信仰等知识,以人类学手法冷静客观地呈现出来。于是一方面,这些文字对主体故事构成了背景知识的补充说明。例如在阿纳金的妻子乌妮娜生下孩子额腾柯前,乌热尔图转述人类学家史禄国记录的鄂温克族生育习俗;在“游荡“萨满出现前,作者事无巨细地对玛鲁神进行素描与意义阐释。
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构成对主体故事真实性的质疑。例如在叙述阿纳金抛弃熊孩额腾柯前,乌热尔图依据史禄国的考察记录及历史资料表明:“对于奥彼莱村色勒木老人断断续续描述的故事,关于那被称为熊娃幼儿的遭遇,我一直存有疑问,无疑这里大剂量掺杂叙述人的想象,那想象肯定早已误入迷途。”③乌热尔图率先对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进行质疑与反叛,这并不是说他不追求故事的真实性,相反,这更说明了乌热尔图在言说时,对本真的一种追求。
乌热尔图正是因为看到了叙述本身具有的想象性和不可靠性,深知“事实”乃是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因此他才对传说本身持有一种疏离和审视态度。而这样的姿态反而更能够揭开传说的神秘面纱,抵达另一种真实。此时,虔诚的萨满信仰,敬畏生命的精神世界,粗粝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危机、子孙与先祖难以隔断的血肉联系等等,都在作者的批判性反思中以一种更加真实可靠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不美饰,不做猎奇化处理的真诚书写,正是基于乌热尔图书写鄂温克历史的虔诚态度,更可见其追求文化平权的努力。
三.鄂温克书写的两种声音
《丛林幽幽》在叙述形式上将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相分离,由此形成了过去与当下的时间闪回。这一叙述结构与新世纪以后,迟子建的鄂温克族书写具有相似性。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借一个老人的追忆展开,且同样存在着二重时间的交替与切换。但其不同之处也是鲜明的,这与书写者的身份与叙事意图有着密切的关联。
两个文本最突出的差异表现在叙述者及其叙述风格的不同。《丛林幽幽》的文本内部存在两种叙述风格:一个是人类学式的考察描述,冷静准确;一个是口耳相传的部族传说,真假交织。由此两重叙述之间发生着断裂、矛盾,是一种相互对抗,甚至是消解的关系。而迟子建笔下二重时间的主体是统一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在讲述她的一生。其情感线索也是统一的。迟子建将大历史——中国近代革命历史——放置在“从清晨到黄昏”的生态时间当中,以个体追忆的形式复现历史,追溯逝去的家园。这一叙事结构的设置凸显了挽歌的意味,因为记忆的再现、故园的存在是在“历史在场”的形式中完成的,因此苍凉之感始终弥漫在叙事始终。也由于这一追忆性质,迟子建借“我”之眼凝视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都完成了一个浸润的过程——美的浸润,故事充满着抒情性色彩与乡恋的牧歌情调。这与乌热尔图节制、冷静的笔触与理性反思、审视的目光是截然不同的。
由此,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汉写民”与少数民族自我言说的不同。乌热尔图进行鄂温克族书写时,没有刻意渲染自己的身份,在叙述者身份的切换上更加自在从容,并进一步实现祛魅。而迟子建为了遮蔽书写者“非本族人”的身份位置,达到增强叙述可信度的客观效果,选择将自己的话语镶嵌在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话语当中。尽管迟子建极力以一个本族人的姿态进行叙述,也确实真诚地书写了额尔古纳河畔鄂温克族的式微。但是有时也会流露出作为局外者的审视与评价,例如描写“我”看“达西”生吃肝脏时,迟子建写到:“有一次我看见他生吃肝的情景,他浸着血,下巴上也是星星点点的血污,看着令人作呕。……我吃生肉,但不吃动物的内脏,因为我觉得那些脏器都是储血的容器,吃它们等于是在吸血。”④这样的目光更近于一种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注视,这与审美化的鄂温克族图景一样,都是在现代性滤镜之下的一种观照。
其次,二者书写鄂温克族的叙事意图不同。迟子建书写鄂温克族这一举动的萌芽,起初归结于童年记忆的启发。在她的记忆中,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有相似性:
“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地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地寂寞。后来我才知道,当汉族人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们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冻土上了。”⑤
但此时迟子建并未提笔书写,而是在走异路,到异地之后,才再次激发了对鄂温克族人的书写冲动。迟子建曾到澳大利亚访问一个月,在候车大厅偶遇一对大打出手的土著夫妻,这件事对她触动很深。他们与相隔万里的鄂温克族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困境,他们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困惑和痛苦着的人。因此可以说,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困顿与迷惘,促使迟子建书写鄂温克族。此时迟子建的书写是一种“寻找”——寻找使灵魂得以摆脱理性羁绊与现实枷锁的“第三地”,寻找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区别的文化构成与知识结构,最终达成对现代文明症结的一种揭露。因此在具体的叙事上,尽管乌热尔图与迟子建同样描写鄂温克族某一个家族的生存图景,也涉及到族人的生存危机。但是迟子建更倾向于借外部危机下鄂温克族人的坚守与解体,来反思与批判现代文明。
但乌热尔图有所不同,他的创作更像是一种“自我找寻”的过程。而且越是在异质文明的包围和参照下,他越要追问自己是谁,也才更能知道自己是谁。《丛林幽幽》中虚实混杂的故事流淌着古老传统的神秘气息;《萨满啊,我们的萨满》《我们顺水漂流》中,老萨满在传统溃败后选择自杀。种种书写何尝不是对将逝的古老文明的一次招魂?随着不同文化的接触面越来越宽,这些人口少、居住分散的民族面临着习俗、历史和传统散失的危机,乌热尔图深刻地意识到文化母体的逐渐消失,由此激起了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希望通过写作,再造文化记忆。他的书写是民族自觉意识的不断加强的一个过程,目的在于进行“自我阐释”,借以修系着通往族群历史的那把钥匙。在《美国黑人文学的自我确立》《发现者还是殖民开拓者》《声音的盗用与声音的替代》等一系列随笔、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乌热尔图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其对异域、异族命运的关注。但是我们更可见乌热尔图深层的渴求:从这些具有同样处境的人中,汲取自己的话语力量,并最终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
八十年代初,乌热尔图为我们带来了鄂温克族的声音。但是个体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尔后也一度陷入沉寂,直到迟子建奏响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之歌,鄂温克族人的生存图景再次徐徐拉开。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多民族共存、共同发展的文化环境中,如何让少数民族的声音得到更多人的倾听与关注,而少数民族自身又应该如何进行言说?乌热尔图主张的“自我阐释”有其必要性,正是他以内在人的身份对鄂温克进行书写,我们方才从其鲜活的童年记忆和当下书写中,感受到鄂温克族人蓬勃的生命力,也更加正视少数民族群体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危机。但是“自我阐释”也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褊狭当中。我们还需持有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在呼吁自我言说的同时,也承认他人对自己理解和解释的必然合法性,在彼此相互理解、阐释的交往中,方能展开更宽广的音域。”⑥
注 释
①乌热尔图.乌热尔图小说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3.
②刘大先.文学的共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0.
③中国作家协会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鄂温克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33.
④遲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42.
⑤迟子建.锁在深处的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145.
⑥姚新勇.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J].读书,1997(10):16-19.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