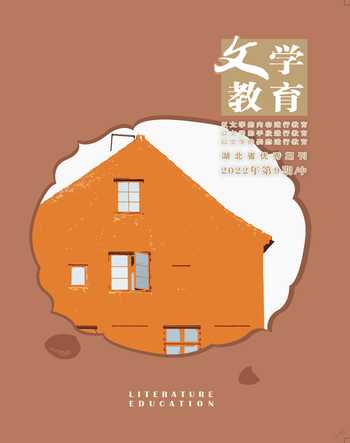艾青诗歌艺术情感基调探析
王亚鑫 李建伟
内容摘要:艾青诗歌艺术情感基调是忧郁与快乐的互补共融。那种单一地认为艾青的诗是“忧郁情绪”表达的观点是片面的,从艾青情感来源以及艾青诗歌创作的两次高峰时期的代表诗篇中都能得到验证。
关键词:艾青诗歌 忧郁与快乐 艺术主旋律 倾吐忧郁 期盼光明
历时性的文化积淀和共时性的中西文化熏陶,使艾青成为世界文化的载体。全球文化的视野,丰富的痛苦磨难,多种文化信息的融汇,在对中外各流派大诗人和画家的创作及共理论的扬弃与综合创作中,使艾青在巨人的肩上崛起并形成自己的独异性。忧郁与快乐的互补共融是艾青情感的根基和底蕴,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彰显。笔者不能同意某教科书和学术专著把艾青的情感特征定为“忧郁的诗”[1]的观点。根据朱光潜的观点和对悲剧心理的考察:“忧郁来自对不愉快事物的沉思,因为它是活动收到阻碍的结果,所以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在被强烈地感觉到并得到充分表现时,又可以产生快乐。”[2]故此,笔者认为艾青的诗歌情感基调是忧郁与快乐的互补共融。
一.艺术情感来源
忧郁与快乐的互补共融,作为艾青情感结构的底蕴和根基,积淀在他的集体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层次里,尤其是在其意识层次更加明显。情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与互相作用的结果。而主体的情感反应是多种情绪的掺和,绝非单一性的,所以教科书和某学术著作把艾青的艺术情感定为“忧郁的诗绪”,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远不能反应艾青艺术情感的全貌。
综合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剖析解读艾青的情感结构,可把其情感结构分为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个有机层次,与之对应的是他的社会性情感,情绪经验和感性欲望三个部分。这种静态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已,实际上这三个层次是动态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双向逆反运动,这三个层次交汇融合统一构成艾青丰富的个性化的情感世界。
艾青情感的无意识层次是他的情感世界的生物生理基础,它虽然是感性无意识的,但积淀着生物学和社会文化因素,是艾青生物的驱动力和情感的原动力之所在。人类的远祖对雷电、森林大火、瘟疫所造成死亡的恐惧,形成悲痛忧郁的心理;而狩猎丰收的兴奋喜悦,各种具有神巫性质的原始庆典活动,则生成欢乐情感,从而形成忧郁与快乐情绪的底蕴。艾青的潜意识层次是他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情绪记忆,它们可以被意识到,但平時未被激活时,只是一种信息贮存。在艾青幼嫩的心灵中最早的情绪记忆是“爱”与“恨”。艾青之父因他“逆生”难产,相信算命瞎子的话,认为他“克父母”,于是把艾青送到村子里最穷苦的“大堰河”家去寄养,并不许他管生父母叫“爸爸”“妈妈”,而只能以“叔叔”“婶婶”。然而,这位穷苦善良的“大堰河”作为保姆,对艾青像对待亲生儿般无私的爱,她把舍不得吃用作换盐的鸡蛋省下来,给这个乳儿吃,使艾青在“大堰河”怀抱里感受到最纯洁无私的伟大的“爱”,从此这种纯洁神圣的“爱”,成了艾青情感的根基和原点。随着年龄的长大和他活动范围由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鲜红闪光的“爱”与传统文化的“仁爱”和西方文化的“博爱”思想相结合交融,不仅成了他的道德观的核心,而且成了他诗歌创作艺术情感的源泉。
与“爱”俱来的是“恨”。当艾青五岁快上学时,被父母接回家去,到家后一种无以适应的窘迫感,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做了生我的父母家的新客。”父母也看不上这个从穷苦家庭生活过的孩子,认为他下贱,使他无比的压抑痛苦。艾青在与妹妹玩暖手的小炭炉,失误烫伤了妹妹的脖子,本来责任不在艾青,父亲却狠心地痛打了他,小小的艾青气得拿了笔在纸写上“贼父打我”四个字,压在父亲的案头,借以发泄内心积累的愤懑,这是艾青最初的由恨而反抗的情绪表达。
爱与恨是艾青潜意识情绪的根基。由于爱受压抑而得不到正常表达而产生忧郁,由于恨而反抗,使情绪得到发泄而产生快感,因此,忧郁与快乐成为艾青情绪的底蕴与原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和艺术实践活动使他的抑郁与快乐由个人到家庭,传统文化到世界文化逐渐地扩大递进,从而忧郁与快乐不仅作为他情感的根基,而且更成为他的艺术情感个性的基地和源泉。
在艾青情感的意识层,由于他的活动受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因此更受到他的理性的规范与制约,所以在他的社会性情感中明显地呈现出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根源是中西文化的撞击与黑暗社会环境的刺激和压迫。具体而言,根源与“大堰河”怀抱中的无私的“爱”作为他情感的根基或原点,与儒家文化的“入世”“仁爱”因而产生的忧患意识,与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其以“爱”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所亲眼感受到的黑暗的社会现实体制下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在抗战流露过程中所经历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逃难民众的痛苦、饥饿和死亡,那些令人惊恐心碎的场景,使他对苦难的中国大地之子,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爱,因为他对苦难着紧贴着大地生活的下层民众“爱得深沉”,又无力挽救,所以内心无比痛苦。根据情感心理动力论学说“痛苦则是生命力在其离心活动过程中遭受阻碍的结果”。忧郁情感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由国内到国外,当他感受到越南、印度和欧洲下层民众悲惨的生活时,使这种忧郁不断深化。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他所经历的“五四”“五卅”时期国人进步分子反帝反封建的反抗情绪对他的感染,使他在童年的潜意识中埋下的对不合理制度和黑暗社会产生的“恨”中爆发出反抗的情绪,因这种反抗获得成功使增强了信心,从而产生快乐的情绪。这种反抗的快乐和信心的增强,在他接触并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叛逆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更加强了这种反抗和快乐的理性认识。
艾青无意识层次中原始祖先积淀情绪元素,与其潜意识中的忧郁与快乐的最初记忆,特别是与意识层次的作为社会情感的忧郁与快乐这三个有机层次的双向逆反沟通融汇,构成了艾青忧郁与快乐的情感根基和艺术情感的主诠释。
二.艺术情感体现
忧郁与快乐的互补共融作为艾青情感结构的根基,以倾吐忧郁与祈盼光明互补的抒情模式以一贯于他毕生的创作活动中,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由于艾青心中充满阳光,所以即使用最苦难悲惨的语句,也并不绝望抑郁,而对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憧憬。用达·芬奇的话说,忧郁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从悲剧心理的角度考察,“忧郁苦难被强烈地感受到并得到充分表现时,又可以产生快乐”。艾青认为“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那种把艾青的诗定为“忧郁的情绪”的看法,至少是具有片面性的。艾青是喝着《大堰河》,举着《火把》迎向《太阳》,走进《光的赞歌》的,他毕生都在走向光明,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路上”。
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自我需要的层次论说,把个体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即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艾青不仅实现了自我需要的最高层次,而且为20世纪中国新诗作出了四足鼎立的贡献:“创立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现代派,把自由体诗由‘尝试推向自律成熟,创作了一批典范性作品,创立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诗学美学理论体系。”[3]艾青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创作生涯中出现了两次创作高峰,第一次创作高峰是1937年至1941年,创作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火把》《黎明的通知》等为标志的他毕生最辉煌的诗篇。当他“归来”后,1978年至1983年又出现了第二次创作高峰,创作了《礁石》《鱼化石》《古罗马大斗技场》《光明赞歌》等为标志的既涵盖广阔又极富哲理的诗篇。
1932年艾青从巴黎去马赛的归国途中而作的《当黎明穿上了白衣》,是他的诗意与画展的融合展示,是他内心充满阳光对光明的渴望与对希望的憧憬。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活动中,他始终沿着这条光明之路走下去,为他赢得了初次创作高峰,从而实现了人生和诗歌创作的辉煌。如果说《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上这土地》等是渗透着“土色的抑郁”的“土地意向”体系的代表作则是他对光明的祈盼与追求的“太阳意向”体系的代表作,二者互补共融,正是他的倾吐忧郁与祈盼光明的情感主旋律。
1933年1月13日傍晚,站在上海牢房铁窗下的艾青望着灰蒙蒙的天上纷纷扬扬的雪花,浑身冷得发抖,由身上的冷激发起了对温暖的渴望。是谁给过他温暖呢?是亲娘吗?没有!只有乳娘给过。可是亲爱的乳娘已深埋地下,他想起乳娘荒草遍生的坟墓,想起早已逝去的童年生活。于是,对乳娘的感恩和对她命运的愤慨不平之痛,猛烈地冲开了艾青灵感的闸门,拿起笔飞快地写着,写着: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头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就这样,中国新诗史上的一首杰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在上海一个看守所的铁窗下诞生的。
1937年12年28日一个雪夜,艾青蛰后在武昌艺专的传达室里,感到刺骨的严寒,寒冷打开他思绪的闸门。积淀在他潜意识中的从中国到越南、印度再到歐洲的底层民众的贫苦与挣扎,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掠夺把国人推进苦难的深渊——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全国,无家可归的民众冒雪逃亡的惨景,饥饿和死亡不断带走他们的生命,茫茫林海中戴帽的农夫赶着马车逃亡,在江南雪夜的河流里坐在乌篷船里失去男人保护的蓬头垢面的少妇,拉扯着外人的衣襟,不停地絮叨着,应合着这悲苦凄凉的场景,一个声音仿佛从艾青的灵魂中迸发出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就这样,中国文学史上一首标志性的经典作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如果说《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个人的悲歌的话,那么,《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则是战乱中发出的民族悲歌,只不过由艾青唱出来而已。《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用底层百姓的苦难,特别是挽救战争爆发后中国百姓的痛苦与不幸熔铸成,是迄今都难以超越的忧郁诗篇,国籍、民族、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社会阶层各异的读者对其解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忧郁与痛苦的体验,它是忧郁的,《手推车》《北方》也是充盈着“土色忧郁”的诗篇,从悲剧心理动力学角度考察,忧郁得到正常顺利的表达,便产生愉悦快乐,艾青的心里充满阳光,即使在最沉闷忧郁的时候也祈盼光明。而《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则是倾吐忧郁后对光明的祈盼与赞颂。如果说《北方》以其开阔丰盈而又单纯的意象抒发特色,沉郁、雄浑具有历史的悲郁来代表艾青新诗风格的话,而《向太阳》是热爱赞美光明,赞美民主,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抒情诗。他在《向太阳》中这样抒发着情绪: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就这样,太阳穿越历史,穿越黑暗,死亡,震惊,群山和大沙漠,向我们“滚”来。其顶天立地磅礴大气,难以用语言形容,这种写法前无古人绝妙无双。《向太阳》把象征意象以其实体的“镜头”与“我的激烈情绪”为核心交织在一起,凝结成一副广阔而神奇绮丽的图景,抒发表达了全国民众摆脱忧郁苦难的阴影,一齐奔赴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光明之梦,那浩浩荡荡的队伍向着“太阳”走去。
《火把》是专篇叙述诗的典范,而艾青1941年到达延安后,为那里的欣欣向荣的气象所感动而创作的《黎明的通知》,则是以“光明”为第一人称拟人手法,向世界和不同人群呼唤,“通知”为他们送来了光明。
第一次创作高峰,展示了艾青诗歌创作的辉煌,忧郁与快乐的互补共融铸成艾青艺术情感的主旋律,他的诗绝不仅是“忧郁情绪”的表达。
艾青的第二次创作高峰出现在1978年至1982年这四年间。在1950年代,艾青因批判胡适时“说真话”惹了祸,遭受20多年的人生灾难,当他被“平反”“归来”后已年近古稀,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使他的情感已趋近于平缓,从而把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际遇提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展开,创作了《礁石》《鱼化石》《古罗马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既涵盖广阔又极富哲理的诗篇,成为艺术和思想升华的代表作。《光的赞歌》是继《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后又以艾青里程碑式的大作,是他新诗哲学的体现。诗中写道:
“每个人的一生
不论聪明还是愚蠢
不论幸福还是不幸
只要他一离开母体
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
……
让我们从地球出发
飞向太阳……”
艾青从“光”这一特定意象出发,使想象的翅膀在时间和空间无比广阔的领域中飞翔,时间——从周口店到天安门;空间——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而抒发了引人深思的哲理命题,全诗最后用“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以实现诗人和人类的最终理想结束全诗。
《光的赞歌》是艾青的宇宙观、真理观和美学观的表达,是他终生祈盼光明而对“光”的赞颂的一支大曲,是他的诗体哲学和对宇宙人生的哲思概括。
艾青诗歌中的意象绝非仅仅对现实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艾青诗歌中最突出的两个意象分别是土地和太阳。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大多用来表现底层民众的困苦,体现艾青情感基调中的忧郁色彩。而“太阳”则体现艾青对于美好未来的一种乐观快乐情感,“土地”与“太阳”互补共融成为艾青诗歌的主要意象,忧郁与快乐互补共融形成了艾青的艺术情感基调。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
[3]吕汉东.艾青:新诗史上四足鼎立的辉煌[J].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改革项目《红色文学经典融入专业教学的德育教育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M20211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