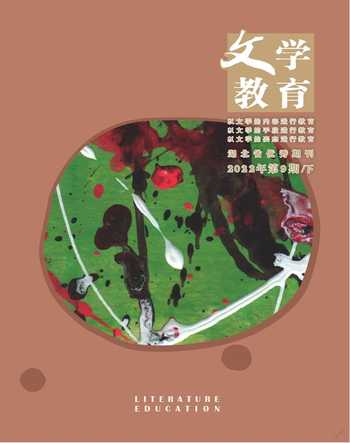论《红楼梦》的褒贬艺术
《红楼梦》有没有褒贬?即《红楼梦》有否作者的立场?这似乎不是问题,因为即使是后世的“零度”写作,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立场。但有一种观点,似乎觉得《红楼梦》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只将生活呈现于读者,而不作任何评判。特别是对作品中的年轻女性,既曰“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作者对所有年轻女性都取同情立场,没有真正的贬损。这种观点,影响人们对作者立场的判断。
其实《红楼梦》肯定是有立场的,即使是对年轻女性,也并未平分秋色,一律给予褒扬赞美。今且以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为例略分析之。
第三十二回的重点正如回目所示,一是宝玉向黛玉明确表白自己的爱情,二是金钏之死。但这一回中牵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袭人,一个是宝钗。两个人物在本回的表现似乎平平,不过一些家常琐事,而实际上,在家常琐事中,不仅两个人的性情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而且两个人的品行也得到了进一步暴露,作者的倾向性也暗示得更充分。所以并不能以平常叙事对待之。
先说袭人。袭人似乎是“有口皆碑”的人物,除了晴雯对她有所“攻击”,黛玉也曾揶揄取笑(以嫂呼之),其他人无不高看。特别是王夫人和宝钗。王夫人放心将宝玉交代于她,宝钗对她心存敬意,的确证明着她的“温柔和顺”。就连脂砚斋,在批语里也常常大赞袭卿如何如何贤德。这其实是很不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曹雪芹写袭人,使用的方法是“明褒暗贬”,明里袭人的确称得上“温柔和顺”,实际上用心深邃,暗箭伤人,绝不是什么善茬。宝玉向来对袭人有所依恋,年节的时候,还专程到袭人的家里探望,并表明决不让袭人离开贾府,不可谓不喜欢。但宝玉对袭人的喜欢是有分寸的,与其说喜欢,不如说是依赖。宝玉对袭人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直到晴雯被逐出大观园,惨死在外面,宝玉基本上明白袭人是地地道道的“告密者”,是自己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宝玉对袭人的一番推理是严密的,怎么大家私底下说的话、做的事,王夫人都知道?怎么单单没有袭人,以及与袭人密切的秋纹、麝月的过错?就连袭人自己也讪讪地说,她原也是说过一些顽皮的话的。宝玉显然是在问罪于袭人,虽然不便明说,袭人也不是不知道,故此赌咒发誓,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但这其实还都是明里,而真正需要我们分析的,还是情节中暗藏的臧否。
第三十二回宝玉向黛玉诉肺腑之前,有一段袭人和湘云的对话。这段对话看似平常,实则是袭人人品的大关节。湘云到怡红院看望袭人(实是看望宝玉吧),袭人请湘云帮忙为宝玉做鞋,两人“不知不觉”中围绕宝钗和黛玉发表起意见来。袭人本来是一个丫头,就算她身份特殊,也终不过是一个奴才,是不能对主子妄加评议的。可袭人却对宝钗和黛玉有所褒贬,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在拉帮结派。湘云专程给袭人送来戒指,袭人说她已经得了,怎么又送?湘云就问是谁给的,袭人答是宝姑娘。湘云说:“我只當是林姐姐给你的,原来是宝钗姐姐给了你。”然后夸了一通宝钗,称如果有宝钗这样的一个姐姐,就算没了父母也无碍。宝玉听了,说:“罢,罢,罢!不用提起这个话。”湘云道:“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怪嗔我赞了宝姐姐。可是为这个不是?”这本是宝玉和湘云之间的话,宝玉未必就是湘云说的那意思,湘云自是前回的气未消,也是嫉妒。袭人却来了一句:“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口快了。”袭人这话是什么意思?表面上也是玩笑,其实已经站了边,自觉成为“宝钗一党”。袭人很明显流露出不喜欢黛玉的意思,且对宝玉护着黛玉也有所不满。如今正好借了湘云的话表露出来,也算是她的一点“狡诈”。
接下来是袭人请湘云帮忙做针线。袭人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话语里颇有点自得,“我们这屋里的”几个字耐人寻味,与晴雯讥讽过的“我们”如出一辙。湘云说:“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于是说到黛玉剪扇套子的事,湘云道:“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这当然还是吃醋斗气的话,袭人又添言加醋了:“他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语气里全是不满,甚至让人觉得黛玉过于娇气,而老太太也过分纵容。这与上面的话比,又更进了一层,更是身份的僭越。
再就是袭人直接夸赞宝钗。贾雨村来了,要见宝玉,宝玉抱怨,湘云劝他就当与这些为官作宰之人接触,学些仕途经济之道。宝玉听了,大觉逆耳,直接下起逐客令来:“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话说得很重,以宝玉在女孩子跟前的小心奉承,这就算是当面打人耳光了。袭人也是怕湘云下不来台,于是说宝玉对宝钗也是如此。“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给湘云解围原也不错,错的是拿宝钗和黛玉作比较,褒一个贬一个,还说宝钗如何有涵养,心地宽大。这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倒是宝玉有涵养,没有当面呵斥袭人,算是袭人的面子大。
有研究者批评袭人,拿袭人后来嫁蒋玉菡为口实,多少有点不能服人。但是袭人的结党营私、使阴招害晴雯和黛玉,就实在难以教人原谅。俞平伯在《〈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中有段话说得好:“盖黛晴二子,虽在‘红楼皆为绝艳,而相处洒然,自属畸人行径,纵有性格上的类似,正不妨其特立独行;且不相因袭,亦不相摹拟。若拉拢勾结,互为朋比,便不成其为黛玉晴雯矣。”这说的是黛玉和晴雯,反过来放在宝钗和袭人身上,则宝钗和袭人就应该是“互为朋比”了。儒家文化向来反对朋比为奸,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拉帮结派、互为朋比是十足的小人,曹雪芹通过具体生活细节所给予人物的评价,不可谓不尖锐了。“明褒暗贬”,这就是曹雪芹塑造袭人和宝钗等形象的绝妙方法。
再说宝钗。宝钗在《红楼梦》中算得上出奇的大好人,人长得丰满漂亮,性格又随顺,不像林黛玉动不动就耍小性子,对下人尤其宽厚,所以得到上至贾母,下至周瑞家的、袭人等的称赞。贾母的称赞虽然有点客套的意思,但周瑞家的和袭人应该是发自肺腑。十二钗的判词中,对宝钗的评价是“可叹停机德”,一个“德”字概括了她所有的特征,一般人当不起。但就是这个以“德”著称的美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好?这是需要甄别的。
宝钗的特点是冷,她吃的药名为“冷香丸”,可见一斑。她素以涵养深著称,但其实也偶有失态的时候,比如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见了宝玉的玉,想起和尚说过的话,也不禁走神。但这还可理解,小女儿有此微妙心理也不是什么缺点。到了元妃归省,在为宝玉贡献“绿蜡”典故的时候,就多少有些孟浪了。这也可恕,不必责之过苛。虽然与黛玉比较,不仅才气可分高下,关键是对待宝玉的问题上,黛玉是知己相助,宝钗的心思还在元妃的喜好上,因为她知道元妃是不喜欢“红”“绿”等字样的。而且还说出“金殿对策”之类的“混账话”来,精神境界与黛玉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也还算不上多么严重的缺点,不过是她的人生观决定的,可以不喜欢,但不值得深究。认为是宝钗真正“污点”的,就是“杨妃戏蝶”一节中的“嫁祸于人”。其实细想想,这一节着重表现的还是宝钗的自我保护,不希望被刁钻的丫头怪罪下来,是她的一份狡猾。硬说她要陷害黛玉,似乎牵强。试想想,宝钗不金蝉脱壳便罢,要金蝉脱壳,脱口而出的对象只能是黛玉,因为别人怎么可能和她这么玩?湘云也许可以,但湘云此刻并不在大观园,要扯也扯不上。这除了表现宝钗的机智之外,并没有额外的贬意。而真正不能原谅的还是第三十二回中对金钏之死的看法上。
宝钗既是宽厚之人,可在对待金钏之死的问题上,她说了什么?她本来在宝玉处,同袭人等说话,得知金钏死讯之后,立即来到王夫人处,为王夫人宽解。金钏之死王夫人脱不了干系,连王夫人自己都觉得罪过。宝钗作为晚辈,说几句宽慰的话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宝钗的话说得太过分。她说:“姨妈是慈善人,固然这样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话前面一半可恕,后面几句就未免太冷酷了。金钏好歹也是一個生命,她的死连王夫人都感到震惊,宝玉更是沉痛,她倒好,将金钏说成“糊涂人”,死了也不可惜,这还是人话吗?一方面她在下人面前装得宽厚仁慈,一方面却这样冷酷无情,对比之下,作者的倾向还待说明吗?这同贾雨村草菅人命,胡乱判断冯渊一案有何区别?看来宝钗的“冷”不光是性格,而是她的一颗心,一颗缺乏人性同情之心!表面上,她能够体贴湘云和邢岫烟的处境,而真正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候,她的假面就丧失殆尽,立刻现出其无情的本相。一个人对待生命居然可取如此立场,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生命态度和人性立场,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品底线,有违此,其他的所谓“善”就都要大打折扣了。
以上就是作者曹雪芹的褒贬,就是曹雪芹的倾向和立场。曹雪芹不是不持立场,而是将立场隐藏起来,不动声色,让读者自己去分辨体会。为什么如此?一方面固然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致,另一方面也与美学原则分不开。
夏元明,1957年出生,湖北浠水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喜欢阅读废名、汪曾祺等人的抒情小说,撰写过数十篇论文,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爱好诗歌及古典小说,出版过《中国新诗30年》《田禾新乡土诗鉴赏》及《小说红楼梦》等专著。偶写散文,有散文集《满架秋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