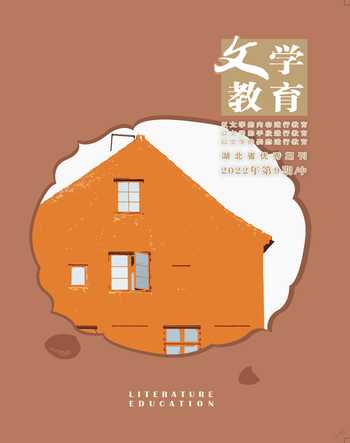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名利场》中女主人公蓓姬的伦理选择
贺思琪
内容摘要:维多利亚时期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是作家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展现两个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命运归宿,揭示了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书中女主人公之一蓓姬以独特的魅力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位经典的女性形象,但是该人物的道德清白一直在评论界饱受争议。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名利场》中女主人公之一蓓姬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以及她由此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由于蓓姬的伦理环境的影响和伦理身份不清晰导致她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的模糊性是造成她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名利场》中蕴含的深刻的现实伦理意义,对当今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冲击仍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萨克雷 《名利场》 文学伦理学 伦理环境 伦理选择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的小说《名利场》是作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847年《名利场》(Vanityfair)开始以每月一期的形式在《笨拙》杂志上连载,到次年七月的时候,萨克雷也由此获得了“英国一流小说家”的美名。小说取材于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书描写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女主人公蓓姬·夏普出生贫寒,步步挣扎挤进上流社会,爱米莉亚·赛德立家境良好,机灵乖巧。小说对人物的细致刻画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生活。
国内学者长久以来多关注《名利场》中的女性主义、创作思想及其叙述策略等方面,鲜有论及小说女主人公伦理困境的研究。实际上,自从我国学者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这一理论后,我国众多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拓展。“文学伦理学主要是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予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评价”[1]。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紧扣蓓姬·夏普的“成长”路线——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这一主线,通过解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着力剖析萨克雷潜藏在作品深处的伦理图旨:蓓姬·夏普的迷失并不完全归咎于自身,而在更大层面上投射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和腐朽堕落的本质。
一.蓓姬的倫理环境
在文学批评学理论中,伦理环境是指文学作品所存在的具有一套伦理观念体系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视域。“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1]。在19世纪前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中产阶级的蓬勃兴起,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名利场》问世之时,正值英国空前强盛之际,在萨克雷的笔下的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物质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客体的品质和主体的品质可以自由地交换;产生消费欲望并激起想象力的是商品,而不是商品背后的人。”[2]琳琅满目的商品促使人们进行消费,加大人们的消费欲望,进而使人逐渐物质化,人们逐渐变成了消费主义的奴隶。对此,萨克雷在初次描写乔斯时就体现出来了:“两个姑娘进门的时候,一个肥胖臃肿的人正在壁炉旁边看报。他穿着鹿皮裤子,统上有流苏的靴子,围着好几条宽大的领巾,几乎直耸到鼻子;上身是红条子的背心,苹果绿的外衣,上面的铁扣子差不多有半喀郎银元那么大”[3]。萨克雷对于乔斯的外貌特征描写并不是很具体,反而对他的穿着打扮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用林纳德的话说就是“商品抢了乔斯的戏”[4]。而这种物质化的世界显然让蓓姬更加堕落,因此在见到乔斯后,蓓姬就把主意打在这个花花公子身上。除此之外,书中还有类似被这奢靡的生活同化的人,比如对生活餐具极为讲究的毕脱爵士、经常喝酒的沃波尔勋爵、穿着最为考究的乔治和对各种盛大的宴会趋之若鹜的克劳莱牧师等等,这些人和蓓姬一样都在这种环境下迷失。因此萨克雷以名利场为题,借用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的比喻,无非就是要暗示世人名利场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在书中萨克雷没有直接描写关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的具体画面,但是他却指出这种金钱主义已经渗透在小说中每个人物之中。萨克雷在谈到他塑造的某些人物的是非过错时曾经说过:“我想谁都没错,错的是这个世界。正是因为在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人们才变得贪得无厌,金钱至上”[3]。
另一方面,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也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众多男性作家利用写作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期望,并按照他们的标准来树立不同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暗含的是当时维多利亚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萨克雷作为维多利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难免不能免于俗套。“亏得这些亲爱的小姐们都像野地里的畜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能耐,要不然准会把我们治得服服帖帖”[3]。在这段描写中,萨克雷将年轻女性直接比作野地中的畜生,毫不掩饰自己的男性优越心理,将男性对女性的轻蔑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萨克雷在书中花费大量笔墨塑造出的两个女主人公也体现着男作家对于女性的期望,两个女主人公的性格可谓是大相径庭,她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男权文化视域下的两种女人类型,一个是贤妻良母类型,一个代表了精明算计型。根据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男性作家创作的“天使”和“妖妇”,文章认为:“这两种类型其实都是男性投射到女性身上的审美理想结果。为男人无私奉献的人是天使,而那些自以为是、拒绝为男人承担风险的人则被称为妖妇”[5]。在书中爱米莉亚是一个天使,萨克雷对她的喜爱在书中溢于言表。爱米莉亚代表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未出嫁时,她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温柔善良;结婚后,她是一个尽职体贴的模范妻子和慈爱母亲的结合,爱米莉亚体现的是萨克雷对理想女性最大的期待。但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男人心中女性并不是自己的同类,她们是属于人类范围之外的,社会始终属于男性,政权也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5],所以其实爱米莉亚这种天使气质是男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世世代代灌输给女性的心灵鸡汤,是在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长期灌输和主导下,女人主动或被动接受的一种现实际遇。而通过对比爱米莉亚的表现后,对蓓姬在名利场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更能凸显她道德的缺陷。
除却社会环境带给蓓姬的影响之外,家庭环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蓓姬出生在一个底层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画家,穷困潦倒但是却嗜酒如命,母亲是一个流浪歌女,在生下她不久后就离开了。她从小和父亲过着到处赊账的日子,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和各色人打交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她学会了许多甜言蜜语。蓓姬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浸泡,性格难免受到影响。平克顿女校时,虽然拥有着出色的音乐天赋和口才,但是却因为家庭条件卑微而处处碰壁。而同学爱米莉亚却因为自己家境良好而备受老师同学青睐。对于蓓姬而言,从小便看尽世间炎凉,她深知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由金钱和地位决定的,她认为自己在才貌上并不输给别人,因此,想要在这个社会实现阶级的跨越,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几分姿色和一些骗人的手段。
二.蓓姬的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与伦理身份有关”[7]。伦理身份是指人物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中的定位,这也是文学伦理学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小说中人物的伦理身份是维系故事中各种人物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纽带,是人类道德伦理最基本的伦理指向。“一旦人物的伦理身份发生改变,原有的伦理秩序就会遭到破坏,导致伦理混乱”[8]。在《名利场》中,女主人公蓓姬从一名家徒四壁的孤儿到名利场中步步为营的女人,在其伦理身份发生异化的过程中,蓓姬逐渐对人性道德走向迷失。
从蓓姬年幼时,母亲便离开了她,而他的父亲却每天嗜酒成瘾,即使家中负债累累也从不关心家中状况。所以在她只有八岁的时候,蓓姬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应付形形色色的讨债人。作为一个女性,她的成长环境是糟糕的。很显然,蓓姬不负责任的父亲给她的身份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事实上,是蓓姬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承担了本应由其父亲承担的家庭责任。因此,这不得不让蓓姬从小对自己的认知与别人不同。尽管上述严酷的成长条件促使蓓姬在未来生活中遇到每一个问题都有快速的解决方法和能力,但是这同时也导致她容易陷入一种伦理身份的混乱之中。尚必武认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种二元结构,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使这种平衡打破,从而变成一种单一的一元結构。而伦理选择只能在二元结构中进行,一元结构中不能进行伦理选择。”[9]由此可见,蓓姬由于从小失去父母的庇护,导致对自己亲情认知的不准确。在小说中,观众几乎看不到蓓姬对儿子的爱。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蓓姬对她的儿子没有爱,她身上的人性因子似乎对她的儿子完全消失了。确实,对蓓姬来说,两边结构都不存在,所以要确认她作为一个正常的女儿和女孩子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孩子来说,失去父母意味着失去了他们的道德模范,这导致他们在道德选择的过程中,人性因子失去了对兽性因子的优先权。”[9]蓓姬失去了她的父母,就意味着失去了她心理意义上的道德指向。在对待她儿子这件事上,她身上的兽性因子比人性因子要多。因此作为一个母亲,在以后的生活中蓓姬就用不恰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子。
而在蓓姬的婚姻中,早早就没有母亲的教导,使得她只能自己处理各项事物,她用自己出色的口才和表演技巧来伪装自己。她知道必须用一个合格的妻子来武装自己才能迎合上层社会有钱男子的口味,这样她才可能在其他女孩中更具有优势。比如,在爱米莉亚家,她在乔斯面前假装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将乔斯看成是进入上层社会的踏脚石。在听说别人更有钱时,她就立马去追求更富有的人。蓓姬对待婚姻的态度就像是对待工作,在这里她的婚姻身份也是模糊的。对于她而言,婚姻只是一块跳脚板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有钱人对她来说只会更好。在处理婚姻的事时,她无时不渴望有一个母亲能帮她,然而,尽管她使用了她的女性的能力,但这也使她与罗宾的婚姻中颠覆了性别角色。这反映在蓓姬几乎解决了他们所有的财务问题,对她来说金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而这些问题原本是属于认为是男人的责任。她为罗登争取到了考文垂岛的总督。为了得到这个任命,她竭尽所能让自己讨好斯泰恩勋爵,她利用斯泰恩勋爵来帮助她的丈夫。这种意识和能力使她成为她丈夫的支柱。但是她这种爱丈夫的方式是基于对自己伦理身份的不清晰,所以尽管她在不同的男人身上挣扎了这么多年,她的婚姻还是以一场闹剧告终,最后仍然失去了这么多年想要得到的名利和金钱。由于身份是与伦理相连的,而蓓姬在从女儿到女人的身份转变过程混乱,因此这必然会带来伦理混乱并最终导致伦理上的困境。
三.蓓姬伦理选择
聂珍钊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在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主观的道德评价”[1]。人们在做决定时通常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同时交锋的复杂决定。人性因子是人类人性道德的一面,指的是伦理意识,兽性因子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性的表现。蓓姬的能言善辩,机巧灵活的本能天性和她从小生活环境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决定了她勇敢好胜、自信聪明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两者结合使她在名利场中自信果敢、如鱼得水奠定了基础。
虽然蓓姬为了进入上流社会做出许多为道德所不齿的选择,但是她也做出了一些合乎情理的伦理选择——促成好友爱米莉亚和都宾的姻缘与对丈夫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作为朋友,蓓姬在其人性因子的指导下做出的道德选择之一是她促成了爱米莉亚和都宾的结合。战争把乔治带走了,爱米莉亚无法从失去丈夫的悲伤中走出来。而都宾上尉在爱米莉亚的丈夫乔治去世后,一直给她提供帮助。蓓姬知道爱米莉亚实际上是喜欢都宾的,但对爱情和她死去的丈夫的忠诚成为了她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负担。蓓姬把她的朋友从这种两难境地中拉出来。蓓姬促进了爱米莉亚和都宾关系的发展,使他们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蓓姬这种勇于打破女性传统规则的做法,宁愿承受道德上的批评也要成全好友的姻缘,吉尔伯和格巴认为在这里萨克雷可能在暗示“一个坏女人可能隐藏在外表和内心深处”“一个坏女人可能隐藏在一个好女人的外表和魅力背后”[5]。蓓姬在伦理道德上并不是一味地违反,相反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个传统女性更关心自己的名声,并像爱米莉亚一样严格遵守道德价值观。而蓓姬选择了一种更真实的方式。虽然她很羡慕爱米莉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并且有母亲来管理她的婚姻,但她还是选择了帮助她的朋友走出困境,而不关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女性没有自己追求婚姻的权利。这样一来,她自己也走出了道德的混乱。
作为妻子,蓓姬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是罗登的支撑,她的魅力和交际能力使她很容易吸引男人的注意。在当时金钱万能的英国社会,追求名利的社会氛围必然会产生像蓓姬一样遵循“丛林法则”的人,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精明和算计,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追求名利的投机场所。蓓姬只不过是“名利场”中小小一隅,她认为只有变得精打细算、世故精明才能适应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但她却慢慢抹去了自己原本美好的女性特质。为了进入上层社会,她先是勾引了乔斯,然后讨好皮特爵士,与乔治调情,并与斯泰恩勋爵保持可疑的关系。显然,在大多数时候,她为了金钱和虚荣心而屈从于兽性因子。但对于她的丈夫罗登,蓓姬身上的人性因子优于兽性因子,或者说至少她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相抗衡。毫无疑问与乔斯、斯泰恩和其他追求她的男人相比,她最爱的还是罗登。在遭受了许多婚姻挫折后,她的伦理选择依然是竭尽全力去争取罗登,尽力去爱,去支持和理解罗登。露西·伊利格瑞认为,女性只有通过接受父权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才能够“将自己的隶属地位转化为肯定因素并最终消解这种隶属身份。”[10]男性作家通过对小说中女性的刻画,将忠贞不一、温柔如水和无怨无悔为丈夫付出品质赋予给女性,以此来引导社会对女性的偏见。男性作家作品中的理想女性正是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下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期待。对社会而言,蓓姬超越男性的智慧是反常的,她努力进入上层社会的勇气,在上流社会斡旋也是不恰当的,她的精明极致是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待的,因此,即使蓓姬仍然爱的是罗登她的婚姻还是受到了重创,最后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应当的。
在小说中似乎看不到蓓姬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讲蓓姬作为母亲身上依然存在人性因子。小罗登的童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孤独地躲在楼上,不让母亲看到。因为蓓姬此时不希望意识到她是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在家里的事实是对她的责备和痛苦。此时人性因子与她身上的兽性因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兽性因子最终获胜。但是当蓓姬知道自己欠下巨额债务后,她首先确保罗登和他们的儿子安全回到伦敦,然后她留在那里用仅有的1.5万英镑偿还他们的债务。她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生活是多么的悲惨。在维多利亚时代,母亲的义务是照顾她的孩子,确保他们长大成人。根据当时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蓓姬当然不是一个好母亲。她唯一耐心地陪着小罗登的时间是为了加强她对完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天使形象的塑造。当她看到小罗登坐在姨妈身边被简拥抱的时候,蓓姬把这种温柔看作是一种时尚,然后她叫小罗登过来亲吻她并对他说晚安。她利用她的儿子来获得简女士的认可,而之前她是以如此仇恨的态度欺负小罗登的时候就像许多年前,她的父亲利用她来逃避债务。蓓姬从小失去了母亲,所以在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她的人性因子很容易失去对兽性因子的优势,因此在对待小罗登的态度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1]《名利场》中女主人公蓓姬的命运悲剧清晰地映射出,人的命运走向和伦理环境、伦理身份及所做的伦理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蓓姬的伦理环境限制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等级制度和父权制造成的。她的伦理身份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反映在她作为女儿、朋友、母亲和妻子的身份的模糊性。她对财富和名声的偏激看法反映在她把自己所有的错误和痛苦都归咎于贫穷,她向自己身上的兽性因子投降。“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启蒙、学习和教育提供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启迪和指导。”[1]解读《名利场》,从蓓姬的伦理悲剧中我们可以得到些许警示:社会的伦理规则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只要一个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就必须保持伦理意识,遵循伦理规则,否则不恰当的伦理选择将会导致伦理悲剧的发生。因此,每个社会公民都应该加强自己道德和伦理教育,强化个人伦理认知,遵循伦理道德规范,才能做出适当的伦理选择。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克里斯托弗·林德纳.商品文化的虚构: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后现代[M].汉普郡:阿什盖特出版有限公司,2003.
[3]萨克雷.名利场[M].杨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殷企平.“进步”浪潮中的商品泡沫:《名利场》的启示[J].外国文学研究,2005(03):81-87+172-173.
[5]德拉·吉尔伯,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M].纽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32(01):12 -22.DOI:10.19915/j.cnki.fls.2010.01. 003.
[8]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语教学,2012,33(03):82-85.DOI:10.16362/j.cnki.cn 61-1023/h.2012.03.004.
[9]尚必武.成长的不能承受之轻: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的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J].外语教学,2014,35(04):71-74+83.DOI:10.16362/j.cnki.cn61-1023/h. 2014. 04. 003.
[10]露西·伊利格瑞.非一之性[M].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