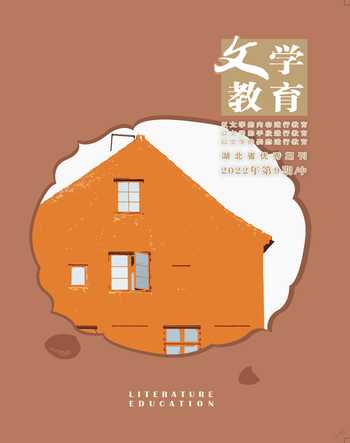库切小说《耻》中的宽恕伦理精神
刘路路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库切小说《耻》中宽恕表述,探究宽恕在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学意义。面对后种族隔离时代黑白对立局面,库切倡导人与人之间应该讲求宽恕。库切所推崇的并不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大主教图图倡导的公开性的宗教神学宽恕,他主张伦理道德上的宽恕作为一种美德,将在情绪上引导人们克服愤怒和报复,践行最为现实的宽恕实践。库切强调伦理道德对于后殖民环境中种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改善作用,认为只有真诚的爱与宽恕才能够改变南非矛盾重重的现状,真正实现种族间的和解。
关键词:库切 《耻》 宽恕 伦理 南非文学
宽恕以往常被作为一个纯粹神学上的观念,其重要性经常被低估。阿伦特赋予宽恕以重要意义,她认为宽恕来源于日常生活中,在伦理学上是必要的,能修复关系,让双方摆脱仇恨的重负。[1]宽恕能够让受害者放下对施害者的愤怒和憎恨,与施害者建立新的联系,给予双方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为受害者和施害者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新生。[2]库切的小说《耻》描写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矛盾与冲突,一直被视为一篇关于宽恕的小说[3]。库切虽未明说宽恕对南非实现种族和解和民族复原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他通过《耻》中人物大卫·卢里、大卫·露西和贝芙·肖等人物含蓄地告诉读者,宽恕将会给南非社会未来发展乃至于当今世界和谐提供一种现实指引。库切在接受德里克·阿特里吉教授的采访时曾经说过,“使我免于做纯粹愚蠢的蠢事的办法,我希望,是一种慈善的方法,我猜,那是一种宽恕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寓言化的方法。”[4]库切将宽恕与慈善等而视之,认为二者都能够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从伦理上使人们摆脱困境。
本文聚焦库切以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为背景所创作的小说《耻》,首先提出卢里的听证会审判像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其大主教图图式的宗教宽恕具有欺骗性,只是形式化的过场。库切在《耻》中主张宽恕作为一种美德,能让受害者积极地从情绪上克服愤怒和报复,摆脱过去痛苦回忆的桎梏,走向未来。最后结合南非社会现实,库切指出重新分配土地将是南非社会白人寻求黑人社会宽恕,获得黑人社会接纳,从而建立和谐新南非最具现实意义的宽恕实践。
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大主教图图主张的宽恕——形式化过场
《耻》中的听证会是开普敦科技大学为调查教授卢里性骚扰女学生案件,并决定是否对卢里采取纪律行动而举办程序化会议。卢里收到副校长办公室发来的被学生梅拉尼投诉的通知,投诉内容是性骚扰学生,大学就这一投诉事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它来决定是否有免除卢里教职的充分理由。大学的听证会是库切在《耻》中投射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缩影[5],他将听证会的主持设置为研究宗教学的教授,而现实世界中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由大主教图图主持,二者都是在一种图图所倡导的和基督教融为一体的乌班图宽恕精神的引导下运行。大学听证会企图通过大主教图图的类似宗教宽恕形式对卢里进行宽恕,以解决卢里性骚扰学生事件为校方带来的舆论问题。事实上,校方不甚在意梅拉尼所受到的伤害,不甚重视缓和施害者卢里和受害者梅拉尼之间的冲突以及促成二者之间的和解,其目的只是在于向大众传达出校方对卢里案件的重视,并依据程式化的审问过程掩盖掉整个事件,使学校摆脱不良舆论的影响。库切认为在这种宽恕形式下,施害者和受害者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进行忏悔和宽恕,这样欺骗性的忏悔与宽恕具有形式化特点,只是权宜之计,很难切实解决种族矛盾,为南非人民带来真相与和解。
听证委员会成员德斯蒙·斯瓦茨和哈金,和真相與和解委员会主持大主教图图一样,作为南非人民都信奉一种和基督教融为一体的乌班图哲学价值观。其是源于祖鲁语或豪萨语的非洲传统价值观,核心是每个人都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建立自己[6]。秉持乌班图的南非人们相信没有宽恕没有未来,只要施害者进行真诚的忏悔,就应该得到宽恕,从而修复创伤,重建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让施害者有机会重新加入这个社会。图图在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时,他重新制定了这一古老的非洲概念,宣布人类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我们需要重新创造一种条件,让施害者重新加入到社会中来,让他们有机会再次拥有自己的人格。只要这些施害者在乌班图精神的指引下,坦白自己的罪行就会获得宽恕,宽恕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未来[7]。和图图一样,斯瓦茨和哈金坚持认为要找到一条道路或者创造一个合适的条件去宽恕卢里,让施害者卢里能够重新回到到学校。斯瓦茨在听证会上对卢里说,“坐在桌子边的我们并不是与你为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们都不过是凡人。你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我们想为你找一条能继续你目前职业的路。”[8]斯瓦茨找到了一个妥协方式,即如果卢里能发表一篇声明,就可以免于丢掉教职。斯瓦茨所采取的图图式的宽恕方式看似实现两全的局面,不仅卢里自身可以保有尊严地摆脱惩罚,而且学校也能平息掉老师性骚扰学生的丑闻,摆脱媒体的注意。但是实际上只是通过欺骗大众的形式化程式达到表面的和解,未能真正解决卢里和梅拉尼之间的冲突。
听证会结束后,主持马塔贝恩教授打电话对卢里说校长不打算采取极端措施,但条件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一项既让我们感到满意,自己也满意的声明。马塔贝恩已经准备好一份完全符合校方要求草拟的声明。只要卢里走个过场发布校方准备好的声明,公开承认自己诱奸学生有罪,就可以获得宽恕并重新返回学校任教。卢里问,“是不是我发表一份道歉书,而根本不在乎也许我根本没有诚意?”马塔贝恩回答道,“评判的标准不是你是否有诚意。那是你良心的问题。我们评判的标准是你是否打算当众承认自己的过失,并采取措施加以弥补”。[8]研究宗教学的教授马塔贝恩并不在意卢里的宽恕是否真诚,只是在利用宗教理念引导卢里进行宽恕。[9]宽恕是基督教教徒得以存在的方式。其主张人生而有罪,但只要担当责任,远离罪恶,就能获得上主的宽赦。即便人犯了罪,不要再犯,并为过去的罪祈祷,消除内心的罪恶,也能得到宽赦,重新获得内心的解放与幸福[10]。不是主持马塔贝恩自己去宽恕卢里,宽恕只是马塔贝恩的一种宗教立场,一份需要完成的工作。[11]在听证会主持人看来卢里的忏悔根本不必真诚的,哪怕他为了获得宽恕,为了被免除罪行去进行形式上的道歉也能免去失掉体面工作的噩运,但是在卢里眼里这是有违道德的。卢里不认同听证会公开宽恕方式,不愿意和听证会合作,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伤害梅拉尼的责任,而不是仅仅靠口头上的公开形式的忏悔与宽恕。
和大主教图图、马塔贝恩一样,梅拉尼的父亲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希望卢里能够皈依基督教,进行宗教形式上忏悔与宽恕。面对卢里真诚的道歉,梅拉尼的父亲回答到:“出事时我们都不好受,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好受?问题是除了不好受上帝还需要我们做什么”。[8]梅拉尼的父亲向卢里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为卢里进行祷告,认为卢里只要遵守上帝的禁令就可以被宽恕。库切在《忏悔与双重思想:陀斯妥耶夫斯基、卢梭和托尔斯泰》中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后得出结论:“真正的忏悔源于信念和宽恕,并非出自于自我干巴巴、毫无结果的对话,或者带有自我欺骗性的与自我的对话。”[4]库切认为宗教那种在神父面前干巴巴说出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然后获得上帝宽恕的宗教形式的宽恕形式化,且带有欺骗性。只有直面自己的内心才是真正的忏悔,宗教神学上的忏悔是虚无缥缈的,不是真正的忏悔。卢里说,“我已经跌到了耻辱的最底端,再想爬上来十分困难。可这样的惩罚我真心接受”。[8]男主人公卢里宣称他并不信上帝,也没有接受梅拉尼父亲这种宗教教化形式的宽恕。他所追求的正是伦理道德上宽恕,一种出于良心和真诚而发自内心的一种诉求,是施害者的真心悔改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库切曾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一场恶棍的游行,只不过是作恶者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作恶故事,然后就可以被宽恕赦免,这种有罪不罚的表现在挑战人类尊严。[12]如同在全世界播出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一样,听证会试图通过施害者回忆过去的暴行然后被宽恕这种形式化的程式来试图解决卢里事件造成的影响,这种走过场式得宽恕只会公开揭露过去的伤疤,再次给受害者带来新的创伤。卢里的听证会当天有人将一个录音机塞到他面前,并询问很多问题,如“你感到后悔吗?那你是准备接着干吗?等等”[8]直白露骨的提问,次日卢里的照片刊登上了学生报纸。卢里的事件被公开报道,听证会成为为一场在公众面前的表演,卢里再次感受到了耻辱,“出了这样的形象,他还有什么躲闪的机会”。[8]听证会这种公开的宽恕形式不仅仅没能让卢里摆脱耻辱,为其带来真正的忏悔与宽恕获得重生,反而使其陷入更为沉痛的羞耻之中。
卢里身上承载着库切对他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理想型宽恕的希冀。作为一位研究浪漫主义的大学教授,性格极富个性又不乏浪漫激情的卢里认为性和情感乃是人的本性,是值得尊敬的。卢里不认为性情有什么过错,甚至于认为性情和头脑是世俗人类身上最为坚硬的部分。卢里认为这不是一种辩护,他与梅拉尼的关系是他私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清教徒时代,私生活不是公共事务,不能像表演一样被公开。[8]他拒绝发表校方带有善意的声明书,因为作为非基督教徒,他认为自己的罪不能以公开性的宗教宽恕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得到宽恕。由此,库切认为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大主教图图所倡导的公开形式的宗教神学宽恕都是无效的,不会带来真相,只会让作恶者变相摆脱罪责,掩盖其应该承担的责任。而真正的宽恕很难实现,需要长时间的反思与实践,不是说像卢里的听证会这样,详细讲述事情发生就可获得赦免。只有出于伦理道德的发自内心的自省才是通过真正的宽恕的道路,才能真正拯救受害者和施害者。
二.伦理宽恕精神——一种美德
宽恕是一种美德,拥有这种美好品质的人更倾向于克服愤怒和怨恨,努力以一种新的更具建设性的态度来取代这种不良情绪。因为具有这种美德的人为了做一个道德上完整的自由人,往往会克服报复情绪,更容易选择宽恕他人对自己造成的不可逆的伤害,以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13]。《耻》女主人公白人女性露西是个同性恋者,离开城市,来到距离萨莱姆镇好几英里的农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她一直努力做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护养狗,忙菜园,看星象书,穿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这都是露西的独立宣言。露西一生没有受到什么人保护,离开父母,离开生活在人的欺压之下的猪狗那样的城市生活,努力在偏远的农场上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独立生活。
被三个黑人男孩强奸后,露西阻止了父亲报复的冲动,也拒绝听从父亲的意见逃离存在巨大潜在危险的农场。卢里反复动员:“露西,事情本来很简单。把收狗所关了。立刻就关。把房子锁上,付点钱给佩特魯斯让他看着点。去休息六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直到这里的情形好一点再回来。到海外去。去荷兰。我来出钱。回来后看看情势,重新开始。”[8]父亲卢里一直想让露西离开农场,认为这里不是露西应该呆的地方。然而露西坚决地选择回农场,在农场上像以前一样生活。遭受黑人的伤害后,露西虽然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摧残,但是她克服自己的愤怒与怨恨,以一种新的积极宽恕态度对待未来的生活,在哪里出了事,从哪里再开始。波伏娃曾经说过,“女人之所以感到劣等,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要求确实贬低了她。她本能地选择了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主体和自由人[14]。面向未来的自由人露西深知农场从来就没有安全过,但是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她都想要留在农场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从一无所有开始,像狗一样开始。露西为了捍卫自由主体身份不惜自我贬低,即便是像狗一样没有尊严,露西也要在农场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自主生活。
露西是个“向前看”[8]的人,她没有一味沉浸在过去的伤痛中,而是在想自己未来的生活,未来怎么生活。她认为“那都是过去的事啦,都随风而去”[8]。尽管露西所经受的一切都会成为她未来的一部分,但是带有宽恕美德的露西选择不将自己的人格建立在强奸受害者这个错误事实的基础上,没有一味地埋怨社会制度,仇视作恶者,而是放下过去,选择无条件宽恕他人,最终是自己从过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正是杨凯列维奇一贯的立场,宽恕始终沿着革新的方向前进,不断向前,解开过去的枷锁[15]。风停了。一阵完全的静寂,和煦的太阳,静谧的午后,在花丛中忙碌的蜂群;而在这幅画面的中央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刚刚怀孕,带着顶草帽。这就是露西想要的农场生活,也是露西摆脱过去的桎梏所创造的美好的乡村生活。
罗伯茨认为,“宽恕的目的是和解”,怀有宽恕精神的人有同理心和修复破裂关系的冲动。[16]露西说,“那些人完全是在泄私愤,那时候带着那么多的私愤,那才是最让我震惊的”。[8]具有宽恕精神的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黑人对自己的强奸不是出于情欲,而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导致的,她理解黑人强奸者的心理,认为这是自己作为白人的后代应该承受,并选择无条件宽恕他们。卢里对佩特鲁斯说,我女儿露西想做个好百姓,好邻居。她热爱东开普[8]。她想在这里生活下去,她想和人人都和睦相处。露西努力修复和黑人社群的关系,寻求曾经被剥削,被奴役,被殖民的黑人社会的宽恕,期望实现最终实现和解。每逢星期六的集市,露西开着车,拉着一盒盒的鲜花,一袋袋的土豆、大蒜和包心菜向格雷汉姆镇那条路走。露西生意做的十分红火,很多上露西这里买东西的人都叫得出她的名字,镇上有些前来买东西的人对卢里说,您一定对您的女儿感到骄傲。可见,竭力修复黑人和白人关系的露西已经成功融入到格雷汉姆这个小镇,赢得了许多附近人们的尊敬和接纳,和部分人民已经建立友好的社群关系。按照特鲁迪·高维尔(Trudy Govier)的理论,受害者选择宽恕他人意味着其对未来关系的有信心,并且相信施害者能够改过自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13]露西毅然决定生下黑人强奸犯的孩子,不会因为孩子的父亲憎恨这个孩子。露西相信未来,认为自己即使现在不爱这个孩子,但是爱会滋长起来。脚踏实地的露西“走在了前面,而且走的很远”[8]。女人的宽恕心,有时候真的让人很惊奇[8]。库切借助露西的口吻来表达女性天生就有一种宽恕,慈爱的美德,这种精神力量超乎常人所能想象。
和露西一样,肖这位善良的女性人物也拥有宽恕美德。她打头在原本一度十分活跃的动物福利会慈善组织的原址上经营了一家动物诊所,然而这个由破败不堪的房子支撑起来的动物诊所并不是一个救治疗伤的处所,而是走投无路之下的最终去处。肖的医术充其量不过是业余水平,离救治疗伤所需差得远。肖不是兽医,不能救治伤病的动物,她是牧师,试图减轻濒死的动物痛苦,和动物分享人类的特权,在做慈善。然而这位五短身材、身材矮胖、又一脸黑麻子的女人的善良,不仅体现在解救那些痛苦的狗时,面对露西和卢里这两位受尽耻辱的白种人,肖这位拥有宽恕品质的善良女性无条件宽恕了这两位历史错误的遗留者,即便是面对卢里这种“不悔罪,不承认错误,也不寻求宽恕的白人”也一样。
《耻》中肖和露西分别作为非白人和白人的一份子,都选择无条件宽恕他人,这说明在库切认为后种族隔离时代,宽恕这一美德将指引不同人种的南非人民能携手医治直种族仇恨的创伤,摆脱过去的痛苦记忆,建立健康和谐的新南非。
三.伦理宽恕实践——重新分配土地
重新分配土地财富是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寻求黑人宽恕最为现实的实践方式。虽然南非在反对制度上的种族隔离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白人与黑人的分野仍然盤踞在民众意识形态中,黑人和白人在经济层面上还存在巨大的差距,白人仍然在把控南非的经济命脉,能够在教育、居住空间等领域与非白人间保持隔离。南非黑人视土地为提升其生活水平和经济现状的直接手段,而且他们认为白人的土地和财富本该属于自己,因为这是在种族隔离时期被殖民者无情剥削的,白人有义务将其归还给自己。土地问题由此成为南非社会急需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尽管新南非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土地改革,但没能使得所有黑人得到土地成为可能,占有巨大土地和财富的白人就成为了黑人愤愤不平的对象,由此引发了无数黑人抢夺杀害白人农场主的例子。因此,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提升南非黑人的经济水平是解决南非社会阶级冲突的关键,这也是南非白人寻求黑人宽恕的最为现实的方式。
露西的黑人雇佣佩特鲁斯就是这一典型,面对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露西,佩特鲁斯不是以宽恕和仁慈之心保护白人露西,反而趁人之危以保护露西在农场的安全为由拿走露西的土地和财富,他对土地的渴望使其迷失了“以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为核心乌班图价值观[12]。佩特鲁斯起初是露西的好帮手,帮露西经营管理农场,去市场上帮露西卖东西。在露西遭遇抢劫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呼喊佩特鲁斯,企图寻求他的帮助。在露西看来,佩特鲁斯是“值得信任的好邻居和好伙伴”[8]。但是露西被强奸后,佩特鲁斯却提议让其成为自己的妻子来保护她。佩特鲁斯的初衷似乎是担心露西自己一人生活在农场上不安全,但其目的一是为了袒护强奸露西的男孩普鲁克斯,因为他是佩特鲁斯自己的亲戚。佩特鲁斯让这个男孩住在自己家里,将其完完全全保护起来。二是佩特鲁斯想借此拿到露西的土地,他并以潜在的安全威胁为条件胁迫露西签署土地转让协议并嫁给他。佩特鲁斯认为白人应该承担黑人报复的后果,甚至主张未来五十年内,黑人都不应对白人感到忏愧,因为黑人已经经受了无尽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殖民的磨难,发生在露西身上的强奸事件也是无数南非黑人女性曾经所遭受[12]。佩特鲁斯不是慈善家,迫切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条件。虽然新南非政府宣布撤销多项种族法律,如《土著土地法》《特定住区法》《人口登记法》等,规定黑人和白人拥有平等的生存机会,但是种族隔离制度这颗历史毒瘤的残留毒素未得到完全清除,很多像佩特鲁斯这样的南非黑人仍然没有获得自己的土地[17]。因此,这些黑人只能以不正当的方式,甚至选择暴力冲突来抢夺白人名下的土地。
正如英格兰所言(England)土地、赔偿与宽恕的问题是南非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事项[18],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是南非白人补偿黑人,寻得黑人宽恕而要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财产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容易的,经过长期的殖民和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的土地再分配不仅仅需要政府竭力去进行改革做出赔偿,更需要种族隔离时期享受特权的白人需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将自己的土地主动分配给黑人[18]。在库切的《耻》中被黑人强奸的露西承受了巨大的身心痛苦,不仅选择放弃报复和惩罚施害者,放下尊严去无条件宽恕强奸自己的黑人,还试图通过土地寻求黑人佩特鲁斯的宽恕。露西的父亲卢里打算卖掉自己在开普敦的房子,把露西送到荷兰去生活,到一个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去重新开始。露西拒绝道,“不,我绝不离开。我要去找佩特鲁斯,把我说的告诉他。告诉他我放弃土地。告诉他他可以得到这土地,包括所有权证和所有的一切。他听了一定非常高兴。”[8]露西热爱南非这篇土地,喜欢在农场的生活,即便遭遇到抢劫强暴事件,仍没有改变留在这里的想法。露西选择接受佩特鲁斯的协议,企图以这种方式对黑人进行弥补,弥补长久以来白人殖民者对黑人所犯下的罪行,寻求其宽恕与接纳。露西认为白人应该寻求黑人宽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黑人强奸暴力事件完全是个人事件,是自己的事,这是白人应该承受的黑人的报复,也是白人对黑人的一种补偿。露西知道自己这样做很是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力,没有尊严。像狗一样。”[8]白人殖民者曾经用武器和暴力抢占黑人土地和财富,践踏黑人的尊严甚至剥夺其作为“人”的权力。而今南非社会发生剧变,黑人和白人身份更迭,白人必须重新思考自我身份,重新建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寻找新生活的起点。库切认为这个起点是宽恕,曾经享有尊严、权力和土地财富的白人放下自尊自傲,分配自己的土地给黑人被殖民者,使其生活有保障有体面,逐步获得生而为人的权力,而不是被白人殖民者无情剥削和欺凌的生活。被人像狗一样放下尊严,分配自己的土地财富是南非社会后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寻求黑人宽恕最为现实的手段。
露西不仅选择宽恕他人走向未来,还竭力通过自己便利黑人社会的实践活动获得黑人社会的接纳与认可,并与其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她帮贝芙·肖照看动物流浪站,在市场上出售水果蔬菜花朵,与来购买物品的黑人顾客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放弃自己的土地,努力寻求黑人社会宽恕的露西不仅为南非社会和解带来深远且积极的影响,而且自己最终也从创伤和耻辱中解放出来并获得治愈。遭遇不幸的露西通过自己的宽恕实践已经重拾生活的闲适和美好,搭建了通往新南非的桥梁,露西的孩子作为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是露西宽恕的结晶。露西的一生是坚实的一生,她的孩子会是她生命的延续,也是南非社会的未来。库切借露西来表达对南非社会未来的信心,相信南非社会黑人和白人终将实现和解。
宽恕是一种美德,可以让人从内心生发出一种道德力量,指导人们积极践行宽恕实践,这是库切在《耻》中想要传达的伦理宽恕的意义与价值,只有直面内心且经过漫长时间的反思与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宽恕。库切曾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一场恶棍的游行,只不过是作恶者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作恶的故事,然后就可以被赦免被宽恕,这种有罪不罚的表现在挑战人类尊严”。[12]库切认为《耻》中卢里的听证会像南非真相委员会上运行的宽恕实践只不过是一场形式化的过场,欺骗观众,制造解决问题的表象,不能为社会未来带来切实积极影响,最终受害者仍深受其累,而作恶者仍逍遥法外。库切被视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斗士[19],其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称道:“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20]。作为一位关心个人命运和对社会发展的有高度责任感的小说家,库切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诫世人的生存哲学。他通过《耻》这本小说创作揭示了伦理上宽恕能指引南非人民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得以更好地生存,指出无论是在南非充满恐惧和暴力的土地之上,还是冷漠孤立的现代生存环境里,人们都应该重新找回自己的关爱、宽容之心并以平等、互惠的原则与人交往,从而重构和谐而有希望的生存环境。
參考文献
[1]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2]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236–43.
[3]Baroga Park. Forgiveness as Nonviolence in Disgrace.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Vol.46, No.4(2020), pp. 39-58.
[4]J.M.Coerzee. “Confession and Double Toughts: 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37,No.3,1985.
[5]Rosemarie Buikema. Litera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mbiguous Memory 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 in Coetzees Disgrace.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Vol.10, No.2(2006), pp.187-197.
[6]周鑫宇. 南非乌班图思想与新兴大国本土政治思想崛起[J].现代国际系,2018(02):56-62+67.
[7]德斯蒙德·图图, 江红译.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8]库切著,张冲,郭整风译《耻》. 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9]Willemijn de Ridder. A Narrative of Forgiveness: South Africa Forgiveness in the Novels of J.M. Coetzee. Nijmegen: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2010.
[10]高予远.论儒家的“忠恕”与基督教的“宽恕”[J].宗教学研究,2006(02):108-112.
[11]Jo?觕lle Zwaal . Allegorie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Achmat Dangors Bitter Fruit, J.M.Coetzees Disgrace, Nadine Gordimers The House Gun and the TRC. Utrecht: Universiteit Utrecht, 2010.
[12]Rosemarie Buikema. Litera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mbiguous Memory 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 in Coetzees Disgrace.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Vol.10, No.2(2006), pp.187-197.
[13]Trudy Govier, Forgiveness and Revenge, London: Routledge. 2002.
[14]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15]Vladimir Jankélévitch, Forgive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6]Roberts, Robert C. Forgivingnes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 1995, pp. 289–306.
[17]石云龙.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颠覆他者——对库切《耻》的研究[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2(02):40-56.
[18]Frank England. Lucy Lurie in J.M.Coetzee's Disgrace: A Post-Colonial Inscription Seeking Forgiveness and Making Reperation. “Journal of Theology for Southern Africa”, Vol.128 (Jul 2007) pg. 104.
[19]Herbert Mitgang, “Coetzee Wins Writing Prize,” New York Times 16, 1986.
[20]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 es/laureates/2003/press.html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