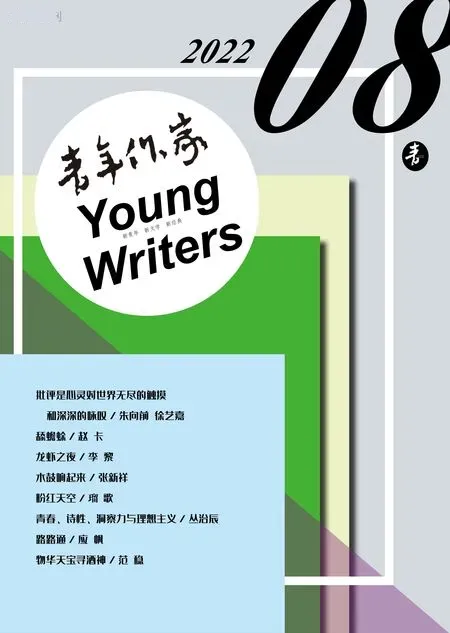异人异行录
喻言
余生涯
余生涯请我去武昌喝茶。
武汉被长江汉江分割成三个独立的板块,以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三座城市的集合体。我住在汉口,一般不涉足武昌。两地往返常常耗费两个小时,我实在找不到花这么高成本去喝杯茶的理由。
不过,余生涯仿佛犯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魔,一遍又一遍孜孜不倦请我。有一次,余生涯在我办公室候了足足半下午。
我问他,汉口又不是没有茶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武昌喝茶?
他却暧昧地笑起来,说,不一样不一样,去那儿喝的茶汉口喝不到。
我说,喝茶还能有啥不一样,能喝出花来?
他说,就是,就是,真能喝出花来。
他好说歹说,我还是没去。
我不去,其实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理由。余生涯是我工地上做铝合金窗的包工头,作为甲方,我一般不与乙方走得太近,大家按游戏规则做生意,关系清爽些比较好。
余生涯长得不像包工头,外表白白净净、斯斯文文,戴副秀郎架眼镜,完全没有常年在工地日晒雨淋摸爬滚打略带匪气的粗豪气质,更像一个从机关下海的前公务员。这副长相,有很强的欺骗性,但我与他接触一段时间下来,觉得这家伙其实比那些满脸匪气的包工头胆子更大路子更野,让人敬而远之。
他接我的活儿,是我从前在部委工作时的一位同事介绍的。他与余生涯是战友,曾在湖北某驻军为同一位首长服务。那位同事,曾经在工作上帮过我不小的忙。这个世界绕来绕去,总有人情绕不开。
余生涯恰好是那种抓住一点关系就能无限延伸放大的人。他经常从工地出来,一头扎进我办公室,趁我有空,神侃几句。在公司其他人看来,他与我很熟络,也许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当然他要的绝不仅是这个结果。我心中透亮。
有志者事竟成,过了两个月,我到底跟余生涯去武昌喝了一次茶。
那次,我有事去武昌拜访省上一位领导,他听说了,就主动请缨陪我去,他说领导的秘书是他多年的老关系,并且当着我面打通那位秘书的电话。
由于余生涯与秘书提前沟通,打好了铺垫,那天的拜访异常顺利。从省府大院出来,余生涯又要请我喝茶。这一刻不好驳他面子,就从了。
余生涯引我去的那家茶楼门脸看上去与大多数茶楼大同小异,木结构的仿古假门楼,挂两盏大红灯笼。进门有一道小石桥,从一道枯山水的假河道跨过去。大厅不大,稀稀疏疏摆了三五组藤沙发,空空荡荡,并无一个客人。大厅正面靠墙安放一扇巨大的红木镶边的磨砂玻璃屏风,屏风上一幅彩绘的天女散花图。屏风前面设一个小吧台,吧台后坐着一个脸上涂着厚粉看不出年龄的女人,正在电脑上玩游戏,游戏的音效尽管开得很低,在这静寂的大厅还是有些刺耳。我们进来,她只是翻起眼皮看了一眼,又埋头继续玩起来。余生涯也不搭理她,引着我绕过屏风,推开墙上一道暗门,进入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灯光晦暗,四周借着梁柱围了一圈卡座,卡座间用到顶的软包隔开,前面垂着一层薄薄的布帘,灯光透出来,几乎每个卡座都坐着一对男女在轻言细语。大厅虽大,并不喧闹。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一个服务员模样的女人,灯光太暗,看不出年龄。余生涯伸出一个指头,往斜上方指了指,服务员也不说话,转身把我们引到墙角,打开一扇钢制的防盗门。
防盗门后是一道窄窄的楼梯,余生涯带头往上走。楼梯口站着一个穿旗袍的浓妆女子,看着我们上来,对余生涯笑道:“余哥,您贵人事多,好久没来,是不是把我们忘了啊?”然后又笑吟吟对我说:“这位大哥面生,是第一次来吧?”说着,也不待我答话,曼妙一转身,把我们引进一间包房。
这是一间带卫生间的包房,足有三四十平方米,无窗。屋顶悬了一盏铜质宫灯,照度调得恰到好处,泛着柔和的暖光。墙上挂着几幅做旧的字画,房间中央摆放两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四尺见方的云石茶几。靠墙有一架实木的书橱,摆放了几本精装书。书橱前有一张原木大板的案台,陈列着文房四宝。
落座后,余生涯点了一壶大红袍、一只果盘、几碟干果。然后催促那浓妆女子道:“快去喊两个妹子出来陪我大哥喝茶。”末了,还来了句:“要气质清纯的,我大哥是讲究人。”趁浓妆女子去安排的工夫,余生涯低声介绍起此处喝茶的不同之处:女大学生陪聊,按时收费。女学生都是正经人,客人不能像一般声色场所那样动手动脚,也不会跟客人外出。说着,他又暧昧一笑,说:“当然,聊出了感情又是另外一回事。”接着又说了几个我认识的生意人,都在这儿与女学生成功聊出“感情”了。我心中暗笑,几百年过去了,也没进步,玩的还是当年秦淮河畔的清官人卖艺不卖身的套路。
一会儿工夫,浓妆女子引着两个妹子捧着茶水和果盘进来。两个妹子脸上化着淡妆,看上去不到二十岁,清纯不清纯不知道,青涩感倒有一点。浓妆女子介绍说,都是师大的学生来兼职的。其中一个挽着发髻,扬着一张小尖脸、穿健身裤的是舞蹈系的;另一个圆脸大睛的,外语系学日语的,相对成熟一点。我看舞蹈系的同学小尖脸发冷,身姿挺拔,走路有点外八字。
我对日语系同学说了句中式日语:“你哄我我哄你都是一码事。”她立刻笑起来,坐到我旁边。冷脸的舞蹈系同学坐在了余生涯一边。说实话,作为一个历经社会毒打的老江湖,与两位青涩的女大学生也没啥可聊,一时竟找不到话头。
日语系同学应有些该阅历,看着冷场,一边端起茶壶给我和余生涯斟茶,一边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喝茶。
余生涯立刻接过话头,我大哥平时出入的都是香格里拉这些高档场所。当时,武汉三镇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就是香格里拉。
我立刻纠正说,从香格里拉门前路过的时候,经常进去上厕所。
日语系的同学立刻凑趣笑起来,说大哥好幽默。
舞蹈系同学有些奇怪地打量我,好像要分辨我与余生涯到底谁在说谎。
余生涯又问两个女生老家哪儿的?日语系的女生说是沙市的,舞蹈系的说是十堰的。余生涯立刻与舞蹈系同学攀起老乡来。
记得余生涯给我说过他是随州人,离十堰还有几百公里。攀老乡这种江湖上比较低级的套路,让我觉得智商受辱,立刻打断说,我们都是地球上的老乡。
这一句话怼得他们天聊不下去了,有些尴尬。我一把抓起茶几上的扑克牌说,来斗地主。舞蹈系的同学连称不会,只能负责给我们当端茶倒水的丫鬟。
不想日语系的同学却是个高手,连庄了十多把地主,打得我和余生涯怀疑人生。
我发现舞蹈系的同学时不时眼睛往余生涯手腕上瞄,就笑着说:“老余,这个妹子怀疑你戴了块假表。”
舞蹈系的同学连忙说,这款表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从来没见过真的。
老余就把手表解下来塞给舞蹈系同学说,汉正街买的,花了500块。
这块表是积家近年新出的月相表,当年武汉的表行没得卖,余生涯是从香港买回来的。
他刚认识我的时候,请我吃饭,送我一个领带礼盒。我回家拆开一看,发现里面藏了一块表。我印象中,这块表的价值大约十五万港币。作为一个商人,我清楚送礼背后的商业逻辑,它意味着十倍以上的回报。
第二天,我就把余生涯叫到办公室把表退给了他。他表示,买都买了,无法退货,让我勉强戴了。
我说领带很好,我很喜欢,我不喜欢戴表,这款表比较符合他的气质,这种勉强的事情就由他克服了。
他见我态度坚决,就笑嘻嘻戴上自己的手腕。
舞蹈系女生认真研究了半天积家表,最后的结论是汉正街造不出这么精致的玩意儿。一直被吊打的我们,地主也斗累了。
我站起身说,不玩了,回汉口,晚上还有事。
余生涯还有些意犹未尽,看我兴趣缺缺,也只好埋单走人。临走时余生涯问了两个妹子名字,要留电话,两个妹子却说下次来再给他。
一上车,我就笑着对余生涯讲,不给你电话是钓你鱼,这是MBA教案里的饥饿营销。
余生涯说他以前经常来,所有的妹子都不轻易留电话,一定要吊客人胃口,又问我对哪个妹子有兴趣。
我摇摇头说,都不是我的菜,你自己消受。
他说,大哥的眼界太高。
我说不是眼界问题,只是与这种女孩子有交流障碍。
余生涯说,无交配障碍就行。
我立刻作以手掩面状,对他说,我的段位比你差得太远,穷此一生,都无法达到你的境界。
余生涯估计往下聊,要受伤,赶紧转移话题说,舞蹈系女生的气质像个初出道的明星,不定哪天就出名了。
我说跳舞的能出名的全中国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余生涯说那女孩看上去很纯,必须把她泡了。
我说就你们这些坏人自己浑浊不堪所以喜欢纯的女孩子,不过世上纯的女孩子都被你们这些坏人泡浑了,哪有几个真纯的?所以市场上就应运而生许多绿茶出来,绿茶很费钱,性价比不高。
余生涯说,无论什么茶,我都可以免费喝几口。
我笑着摇摇头说,为了激励你,我们打个赌,如果你喝到免费茶,二期工程的门窗还给你做。
他立刻来劲了,说,当真?
我说开玩笑的。
他说,我可当真了!
我任他自说自话,并不搭腔,有点后悔孟浪地说出打赌的事。
余生涯这种人天生具有鳝鱼的本能:见缝就钻、咬住就不松口。
余生涯原名余生芽,乡场上父母取的,他嫌太土,就改成余生涯,这三个字印在名片上,让他对大城市有了融入感。他虽高中未毕业就参军进了部队,脑子却好使,又舍得下功夫,三混两混就混到首长身边当上勤务兵。到了首长身边,又讨首长喜欢,提了干。首长离休前把他安排到部队一家保密的科研单位做后勤,混了几年又混成后勤处处长。后来辞职下海做起生意,依靠以前在部队的老关系,赚了不少,开了家小有规模的铝合金门窗厂。这家伙要没这种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精神,就不会有屌丝逆袭的人生。
此后再未与余生涯出去喝过茶,我俩对茶的兴趣南辕北辙,实在喝不到一块。不过余生涯依旧经常从工地出来跑到我办公室转一转,顺手送两条新出的黄鹤楼香烟。黄鹤楼香烟以前名不见经传,后来请了个叫叶茂中的高手来策划,隐隐成了高档香烟第一品牌,时不时有新品推出。黄鹤楼也搞饥饿营销,每个销售点限量发售,供不应求,一时间,黄鹤楼新品香烟成了身份的象征。余生涯总能在第一时间通过部队渠道弄出几条来。
有一次,我一边拆封他送的黄鹤楼,一边打趣问他,免费茶喝上没有?
他笑着说,快了,我现在搞饥饿营销,反钓鱼。
一周后,余生涯约我吃饭,我正待婉拒,他却说要让我见证他这两个月成功喝上免费茶的成果。
在汉口江边一家粤菜酒楼包房,我再次见到那位舞蹈系同学,依然是发髻高挽,穿紧绷绷的健身裤,小尖脸居然不再高冷,在余生涯面前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我腹中忽然冒出一句老话:好一棵白菜被猪拱了。好在牙关尚算紧,这句话仅在腹中荡了一圈,并未脱口而出。
一顿饭时间的观察,足够让一个久历江湖的成年人作出判断:二人不是对我进行专场表演,他已成功在肉体与精神上占领了她。
过了几天,余生涯到办公室向我招供了他钓鱼的全过程。
自从我们上次去喝茶后,他又隔三岔五去了几次,每次都点舞蹈系同学,却没有任何收获,连妹子的手机号码都没要到。一想到我的二期工程,他就忧心如焚,夜不能寐。情急之下,他终于灵感上头,憋出一大招。
他连续十来天,每天下午三四点钟都去那茶楼,单点舞蹈系同学陪。每天下午五点钟,他叫司机准时用一个大布袋装二十多万元钱拎到茶楼交给他。他就让舞蹈系同学帮她点钞,一万一捆用橡皮筋绑扎起来,点完后他就装回布袋,起身埋单,拎着布袋一摇一摆走了。
前两天还好,舞蹈系同学虽然数学有可能是体育老师教的,但手指灵活,点起钞并不费力,只是默默帮他把钞票扎好,也不多言。
第三天终于没忍住,问他,大哥,做什么生意?每天都收这么多钱?他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现在生意不好做了,每天才这点利润。这轻描淡写一句,让她的眼睛陡然一亮。
此后七八天,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数钱流程依然不变,期间双方交换了电话号码,余生涯也以感谢她辛苦帮忙数钱为由请她外出吃了一顿西餐。
当双方渐入佳境,冰美人脸上冰霜开始解冻的时候,余生涯突然从茶楼绝迹,玩起人间蒸发。
当天晚上,那妹子就给余生涯发短信问他为何没去喝茶,余生涯过了两个小时才回短信说在出差。之后,两人开始频繁短信互动,妹子嘘寒问暖,余生涯暧昧应对,逐渐演化为隔空调情,从闷骚转明骚。
看看火候熬得差不多了,余生涯突然从“外地”回来了。一切水到渠成,余生涯带着妹子到东湖宾馆开了房。
余生涯的故事讲完,我大笑着拍案站起,指着他说:“这么损的招数也只有你们九头鸟想得出来!把一杯绿茶喝成了花茶!”然后祝贺他即将成为我们二期工程的分包商。
不过,很快我就失言了,并没把二期的铝合金门窗工程包给余生涯。一期工程验收的时候,发现他与我公司工程部的人暗中勾搭,把80的型材换成70的,镂艺玻璃换成了普通玻璃,所提供的检测资料上数据全部是造假的。
这件事之后,余生涯再未在我的办公室出现过。有一次,在一家餐厅吃饭,他从另一桌跑过来打招呼,身边跟着一个女孩,已不是那个学跳舞的妹子,不过也有些眼熟。过了半晌,才想起,是那个与我们一起喝过茶的外语系同学。
再之后,听说他出事了。
武汉项目结束,我回了北京,光阴荏苒,已历十余年。
有一天与那位部委工作的前同事重聚,酒至半酣,他提起余生涯。我知道前同事一直对当年介绍余生涯到我那儿接工程的事有点愧疚,所以从不主动提及,他也一向默契地忽略,这样免去彼此尴尬。
也许那天酒喝到位了,他话匣子收不住,说起当年他给老首长当秘书,余生涯做勤务兵的往事。
“又勤快又朴实,一说话脸就红,文化不高,脑袋却异常灵醒。”余生涯当年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他还做过余生涯的入党介绍人。
余生涯最后的结局让他非常吃惊,他通过过去的战友,陆续收集到一些信息,慢慢拼凑出完整的轮廓。
问题出在余生涯到那家部队科研所当后勤处长的时候。经常有上级领导来视察,研究所的领导就让余生涯负责接待。余生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这个位置,异常珍惜,对领导布置的任务绝对超预期完成。每次都安排超规格的接待和礼品,每次都让上级领导满意而归,科研所的领导自然也很满意。但部队每项经费预算都有限额,由于他的超规格安排,接待经费打不住,他就挪用研究经费。日积月累,挪用的额度太大了,没有哪个领导敢给他签字报销,账目就挂在他头上。年深日久,最后成了一个天文数字。
他感觉这个账目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让他粉身碎骨,就想转业。但一提出,没有哪个领导敢批,都说转业前,必须把账上的窟窿填平。余生涯一看躲不掉,就向领导提出保留军职自己出去做生意,赚钱来填窟窿,也请领导提供方便。几位领导凑一起一商量,无奈之下就同意了。
刚开始的时候,单位为其提供了不少资源,他狠赚了几笔。不过随着老领导们离休和调离,新来的领导支持力度逐渐归零,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一看,这样赚钱的速度不知何时才能把窟窿填平,就打起偷工减料的主意。这样下来,快钱没赚到,却把关系做绝了,名声也做坏了。
眼见还钱无望,余生涯最后走上破罐破摔的道路。他把婚离了,孩子跟了老婆,自己一个人在江湖上胡混。公司账上还有点积累,足够他挥霍一阵子,他便开启了纸醉金迷的最后疯狂。
不久后军队整肃,从上到下内部审核,单位新来的领导根本就没有捂盖子的动力,他就顶着一颗巨雷进去了。
“这家伙坏就坏在脑袋太灵醒了,太灵醒了!”
那晚,前同事喝得大醉后,还一个劲为余生涯惋惜。
这个已在我记忆中淡漠的名字,又重新变得深刻,我们交往过程中的一幅幅画面重新浮现脑海。余生涯请我喝茶那段时间,也许是他在做最后的挣扎,如果把二期工程继续包给他做,他会不会走向自暴自弃的境地?即使给他做了,对于他那个巨大的窟窿,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也许能给他带来希望,让他有所坚持。不过这又能坚持多久呢?也许每个逆袭的屌丝都无法逃脱顶雷的命运。
高老三
十多年前,我曾在武汉硚口汉江边一座公寓住过。刚搬进去那段时间,每天下午,就有一个矮胖的中年人骑着车,来到楼下喊高老三。嗓门很大,我在10楼书房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照例没人回应。中年人却不知疲倦,一声接一声喊,一声比一声响。喊得楼里所有的人都禁不住从窗户探出头去看。这时中年人立刻住嘴,腼腆一笑,转身骑车就走。
那个中年人每天准时出现在楼下,喊了大约一周时间,就不来了。楼里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有位叫高老三的邻居,至于谁是高老三,我问门卫室的保安,他也不清楚。
一天下午,我沿汉江边上小街闲逛,走到距离我住的公寓大约五六百米的地方,又听见有人喊高老三。抬眼望去,还是那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这次因在平地上,距离稍近,看得真切。他长着张圆脸,穿一件皮夹克,脸上与皮夹克都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也不像一个长年干体力活的,倒与汉正街那帮商户气质类似。他骑在自行车上,两只脚杵着地,双手作喇叭状,对着面前几栋宿舍楼喊,声音依然响亮而具穿透力。
宿舍楼大约是八十年代的建筑,归属附近一家已停产的国有厂,六层楼高,三栋楼呈凹状围合,住着百十户人家。中年男人喊了几声,突然从一个单元门钻出个五十多岁的妇人。那妇人穿着件大花的睡衣,顶着一头发卷,看样子正在家里冷烫头发。她对着中年男人大声嚷道:“么子人?昨天就说,这里没有叫高老三的!你又来鬼嚎么子?吵得心烦!赶紧走,再不走,我叫警察了!”中年男人尴尬一笑,想说什么,支吾着却说不出来,骑上车一溜烟跑了。
武汉女人的泼辣厉害让我暗自咋舌。中年男人也勾起我的好奇心。前段时间到我们公寓楼下喊高老三,今天又在这里找高老三,说明他并不知道高老三到底住什么地方,只是抱着瞎猫碰死耗子的侥幸,来撞大运的。这中年人看上去挺稳重的一个人,行为却有些无厘头。高老三又是何许人物?是不是欠了一屁股烂账的赌鬼?当年武汉三镇江湖上烂赌鬼不少。但中年男人看上去不像道上混的,更不像吃讨债这碗饭的。讨债的大都一脸凶相,气焰嚣张,绝不会被一个妇人怼得落荒而逃。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一圈,便搁下了。毕竟事不关己,犯不着深思。这年头,光怪陆离的事太多,要都弄通透,估计得脑坏死。
武汉三镇入夜甚是热闹,沿街餐饮店把夜宵摊摆满了人行道,卖小龙虾的、铁板烤鱿鱼的、炸臭豆腐的、炒田螺的……冒着各种香气的推车占了半边马路。背着电吉他卖唱的残疾人、挎着篮子卖鲜花的小姑娘如穿花蝴蝶般游走其间。我住的公寓在汉口偏西稍显僻静的地界,依然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路灯下斗地主、喝茶、吹壳子,时不时还有人挑着装有鲜菱角、盐水花生、煮毛豆的竹筐凑上来。一些闲汉,就从附近杂货铺拎几瓶啤酒,坐在街边的台阶上,就着花生毛豆喝开来。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我晚饭后总要绕着附近的小街走一走,感受感受汉口市井的烟火气。
“高老三是么子人?”“我家在这片住了几代人,就没听说过有叫高老三的!”武汉人嗓门素来响亮,每走一条小街,总听得几声街边闲人的议论。我在心中暗自好笑,高老三这个只闻其名的神秘人物,短短十多天,俨然成了附近人们口口相传的角色。
日子转瞬已近中秋,汉江瘦了一大截,浑浊的江水有了几分清澈,江堤下露出大片大片泡得发白的石头。有天黄昏,我从寓所出来,沿着江边小街往西溜达,欲觅一家餐馆安抚辘辘饥肠。东边更近主城中心,饭馆鳞次栉比挤满小街两侧,惯常外出吃饭都是往东,对于有选择综合征的我其实是一种折磨。这一天,特地往西。西边这一片仿佛与城市忽然断裂,突现一种郊区的僻静。往前走了几百米,已过国有厂的宿舍区,印象中的几家小饭馆居然都关门歇业,我抚着咕咕叫的腹部正待折身返回,猛然看见不远处靠江一侧一幢孤零零的二层小楼上霓虹灯闪烁,门口摆着几只花篮,像是刚开业的饭馆。定睛细瞧,小楼顶上竖着一大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上书五个大字“高老三菜馆”,黄昏晦暗的天色中,霓虹灯的光影下,却也分明。
“高老三?”这段时间时常被挂在耳边的名字,让我一下来了兴致,大步流星跨过去,要去见见此人到底是何角色?那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找到他没有?
距离饭馆还有七八步远,迎出一位满面堆笑的中年女子,留着齐耳短发,身上的简装旗袍十分熨帖。女子一口一个大哥,热情却不让人腻味。听口音,不似汉口本地的。
饭馆不大,楼下店堂摆了大小不一七八张饭桌。桌面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搭配的是包布垫的软靠椅,看上去比寻常家常饭馆油腻腻的木桌椅干净、舒适。这饭馆装修简单,墙面刷白色乳胶漆,间隔挂着几个画框,画框里镶着一幅幅美食照片。照片拍得很用心,洁白的瓷盘盛着色彩鲜艳的菜肴,光影效果恰到好处,屋顶射灯柔和的光线打在上面,活色生香,勾人食欲。店堂靠里是一面玻璃墙,玻璃墙内是厨房,收拾得十分整洁,一个戴着白色厨师帽和口罩的厨师和一个伙计模样的正在忙碌。
店堂已坐满八成客人,颇有些眼熟,仔细一看,均是散步时见过的附近居民。店里没有其他伙计,中年女子极为利落,开单、上菜、端茶倒水的活计她一人全包了,且极有眼力,看到客人等菜时间稍长,立刻送一小份混嘴的味碟,总在客人的杯子被喝空前及时满上茶水。看她动作,忙而不乱,说话爽利,落落大方,应对有礼,当在这行浸淫多年。
落座后,要了几个本地家常菜,很合我口味,难得是少了本地菜素来的油腻。吃得六七分饱,终于没有忍住好奇心,趁中年女子来给我茶杯续水时,问了句:“有人天天在找高老三,是不是就是找你家老板?”话一出口,其他几桌客人也扭头看过来,想来,来吃饭的客人都有揭开这个悬疑的动机。女子捂嘴笑道:“什么老板嘛,就一个烧菜的厨子。”说着又朝着厨房方向喊道:“高老三,快出来见客!”
玻璃墙后的厨师闷头应了一声,过了约莫两分钟,才掀开厨房的白色布帘,端着一只大托盘走进店堂。男人先把托盘中切好的水果挨桌送了一份,这才揭下帽子解下口罩。几乎所有客人都咦了一声,这位高老三居然是天天到处找高老三那位矮胖中年人。
他双手抱拳行了圈礼,说道:“各位街坊,前段时间多有打扰,今天给各位赔礼。我老家在黄陂,堂客是湖南的,以前在湖南开饭馆,如今回到汉口重操旧业。汉口好口岸的门脸房房租太贵,小本经营负担不起,这一大片住的人不少,就租了这幢小楼,又怕地段偏僻,酒好也怕巷子深,不得已想出个歪主意,到周围小区楼下喊高老三,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好奇,来试一试我家的菜品。”说完,又转头对中年女子说:“待会儿结账,给各位街坊全部打八折。”店中客人不由笑起来,说,黄陂佬就是奸,耍得我们汉口佬团团转。高老三腼腆一笑,赶紧接话说:“各位多担待!多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