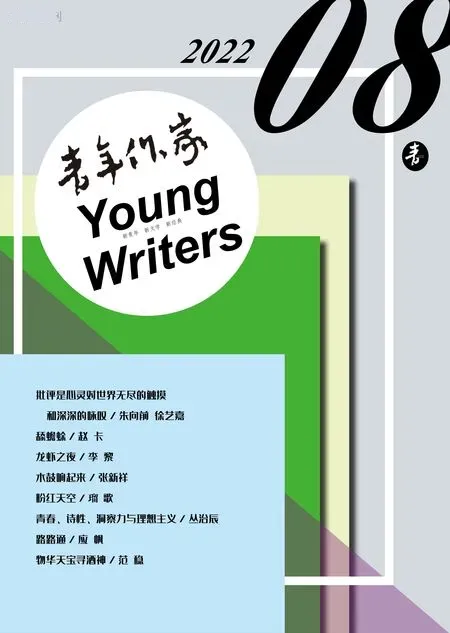呼格罗
瑠歌
一个少女
行走
在旷野上
马儿们
在独自
吃草
饮水
它们之间
隔着
漫长的梦
云层
才是世界的道路
大地
不过世界的边缘
只有看着天空
地上的马
才能继续迷失
第一夜。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入睡的,躺在沙发上,凝望着城市的月光,整个晚上没喝一口水。夜晚的时候,我不敢拉上窗帘,我总是担心,如果没有白天的存在,我会在这个封闭的小房间里永远地睡去。
在梦里,起初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我只看见蒙蒙一层雾,之后看见了草原,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匹马,为了吃到眼前的草,而散漫地走着。我看见了别的马,我们之间隔着不可穿越的迷雾。马儿们都在低头吃着草,我们离自己真正的目的地,似乎还很遥远。
醒来后,第一件事情,我从沙发上摸到了一盒香烟,里面只剩下一支。我的双眼还未适应白日,惺忪中,我将一口浓郁的香烟咽入喉咙,那股热辣的脉冲,终于让我适应了白日的光芒。
“妈的……”我挠着散乱的长发骂道。
我的窗户外,唯一的景色,是一栋灰蒙蒙的楼房,它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植物,就像医院的停尸房绽放出的死亡之花那样。楼下一条干枯的街道,街上堆满冷清的店铺,兜售着牧民宰杀后运到城里的牛羊肉。
这座城市里盖着许多摩天大楼,土地很便宜,人民很便宜,钢铁很便宜,它们像野草一样肆意增长,在这片无尽的高原,它们的存在就像一团野草,拥有直入云霄的意志,事实上,不过在地面上挣扎。
云层才是世界的主角,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繁华,不过像是在旷野上,立了几块规整的砖石,不久之后,就随风而去。
在这座城市,任何人走在街上,都有感受到天空的权利,除了像我这样住在出租屋的女人。
我从沙发上起来,从箱子里取出一瓶矿泉水,我喝的时候太用力,水撒到了裙子上,我任凭它湿漉漉的,又躺到沙发上。
一个月前,我拥有不错的生活,我和一个男人过了三年,我们卖掉了店铺,攒了一笔钱,要去人更多的地方生活。他突然告诉我,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无法控制自己。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女人,亦未感受过她的存在。他说那个女人很可怜,他不得不付出一切去照顾她。我便将我们的钱,和一辆越野车全部划给了他。整件事情发生得很快,下午的时候,他就已经搬着东西离开了。
起初的几天,我除了不停抽烟外,没有任何感受,直到一天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希望自己赶紧得肺癌死掉,我才意识到自己非常伤心。那是一种无法因为眼泪缓解的伤痛,睁眼,闭眼,胸口时刻如刀割。
我必须立刻搬到别的地方,我的身上只有三千零三十块钱。因此我来到了这个没有天空的小房间。这真是个糟糕的决定,我要在这么没有生机的地方,逐渐殆尽。而我终归没有勇气,直接走到外面,走到草原的深处,平静地面对死亡。
第二夜。
那个梦又回来了,我还是那匹吃草的马,但这次,我抬起了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团巨大的风团,马上要吞噬地上的一切。我吓得低下了马头,就像其他马儿那样,继续吃着眼前的草。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五分。手机屏幕堆满了信息,我已有一个月没打开了。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醒来吃了一口放在桌子上的锅巴,我咬了一口,就几乎要将胃一同吐出来。人们说,饥饿而死是极度痛苦的,也许真正的饥饿还未来临,到那个时候,我会出于恐惧,而往嘴里塞满食物吧。
我突然觉得,这样子活着,也蛮有意思,我开始觉得,明晚也会继续做那个梦,期待那个梦的内容。可我实在睡了太久了,总该找点事情干,这里有一台旧电视,我连上了手机投屏,打开了一部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它的标题是《奇怪的科学》。
那个时代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画面质感,那种模糊的色彩,对我而言,比如今过度真实的蓝光画面更有吸引力。
影片的主角是两个十四岁的男孩,他们渴望女人的身体与爱,可从未接触过真正的女人。在一个周末,他们在父母的别墅里,看到了电影《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是十八世纪一个疯狂科学家造出的人造人,他们受其启发,利用电脑,按照自己的理想,制造了一个人造美女。
女人赤裸着身子,从淋浴间的迷雾间出现了,她的名字叫丽萨(Lisa)。看见丽萨的一瞬间,我便意识到,她和我太像了,我们的身子一样纤细,腿占了身子的五分之三,胸脯很小,从腰部到屁股的曲线如出一辙。她的苹果肌和我一样高,我笑起来更飘忽,她笑起来更自信。最大的不同是,丽萨的头发是卷的,我是直发。
丽萨给了两个男孩爱,她和他们接吻,让他们的胸脯贴近她的乳房。丽萨用魔法编出了一辆法拉利,孩子们驾着跑车,在夜幕下奔驰,他们在酒吧里,和不同肤色的人讲着笑话,黑人、拉美人、白人。他们和自己的老哥们儿讲述着自己不存在的性爱经历。
第二天,两个男孩要在父母的房子里举办更大的派对。他们请来了镇上的酷孩子,学校里受欢迎的两个女生。女孩子们看见了丽萨,对她心生嫉妒,又为她的美貌发狂。她们看见两个男孩与丽萨亲热,对他们又崇拜又爱慕。这期间,男孩们为了通过电脑让丽萨的乳房变得更大,甚至将房子弄出了一个洞。
几个流氓闯入派对,这一幕很奇怪,像是一起离奇的巧合,又像是丽萨为了给两个少年英雄救美安排的场景。总而言之,两个男孩起初躲在衣柜里,看着流氓们大闹现场,最后终于鼓起勇气,靠一支真枪赶走了他们。女孩们也因此死心塌地爱上了男孩们。
在故事的结尾,两个男孩发现,他们只是像同龄人一样,渴望对少女的爱情。他们对丽萨心怀愧疚——他们创造了她,得到了她无私的爱,却无法保护她到最后。温柔的丽萨理解了他们,最后他们拥抱了彼此,丽萨通过魔法让混乱的家里恢复,同时又教训了日常霸凌他们的表哥,消失在了浴室的迷雾中。
等到周末结束,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回来时,他们发现,家里安然无恙,孩子们也是两个普通可爱的孩子,没有狂野的派对,没有堕落与放逐。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拥有了心爱的小女朋友,他们不再是普通的男孩,而成了幸福的普通男孩。
丽萨做完了一切后,便心安地消失了;这使我觉得,死亡也不是那么恐怖。我感到心满意足,可我却伤心地哭了,我趴在这枕头上,失声痛哭起来,我从未这么哭过。
第三夜。
在梦里,我看到一道彩虹,它在云团间,并不显眼。可是整个大地,都染上了那种和煦的光泽。草场也是和煦的黄色,四周没有一匹马,只有我。
死亡或许并不可怕,在草原上生长的我们,死后便会化作一匹马,在原野上安逸地吃着草。可那之后的事情呢?你有想过那之后的事情么?马儿被人类宰杀,装进箱子,送到餐桌上,痛苦不停地轮回。
我今天感觉还不错,起来的时候阳光尚在,我走下楼。我已经两周没下楼了。在街角的面馆,点了一大碗荞麦面。我大口吃了下去,又一口气吐出了一半,感觉真不错,咳嗽的时候,我好像要死了,但是活过来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活着的时刻都要强烈。
我回到房间里,对着一只蚊子发了半小时呆,它始终没有叮我,或许它觉得我没有营养。因此,我觉得我不该扼杀它,打开窗户,让它回归了天空。
对了,回归天空,死亡的归宿不是大地,或许是天空。
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了晚霞,即使在这个封闭的小阁楼,也能感受到粉色的天幕。天空的力量真是深不可测,我从未意识到,它可以穿透到这个角落。那些死在大地上的人是多么悲哀,他们至死,也没明白天空的力量。
生活似乎有了希望,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一共有三百一十六条消息。其中一百五十条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五十条是群聊中,寻求他人眼光的人,发出的呻吟。十六条是广告。七条信息(每条长达五百字),是前男友发来的辩解,我实在无法入目。还有一些琐碎的朋友发来的问候,有两个人过来借钱,有五个男人向我示爱;他们有的知道我的感情状态,有的不知道,所有男人,一有机会,就试图和我发生性关系。
我挑选了其中长得最好的那个男人回复,他长得像一个三流歌星,胡子像,穿得也像,他似乎有两三家餐馆,这给了和女人交媾的资本。或许在空寂了许久后,我也产生了交媾的念头,或许我只是需要钱了,或许我像所有人类那样,凭着本能选择了外表更好的对象。
他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告诉他前段时间工作很忙,他让去一个高档公寓里,他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我答应了。
我换了一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褶皱上沾染了未知的黑色,它们或许就是空气中蕴含的暗物质,一点点微弱地吞噬着希望。
我走在街上,几乎忘了如何迈步,我拖着摇晃的腿,恍惚地注视着街上的人,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无论在这里,还是繁华的大都市,人们总是只能看见眼前的生活。
那座楼在一座巨型商场的后面,这里的一切建筑,尺寸都比别的地方大上一倍。三栋长条状的楼屹立在黑幕下,只有几盏灯微微亮着。
这个该死的地方,只有拥有门卡的业主,才能使用电梯。我给他们打电话,没有回应,酒精和女人的喧哗掩盖了手机铃声。我只能一层一层地往上爬。过了十七层之后,我已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楼道里没有任何光芒,我只能凭手机的电筒,缓缓前行,到最后,我几乎是趴在楼梯上前行。
或许不知不觉间,我已走上了奈何桥,这是死前所遭受的最后苦难,真该死,人直到死了,还要艰辛地活着。
我终于来到了楼顶,迎来了解脱,我喘着气站了起来,望向窗外。
月光凝视着城市,白芒穿透了我的手臂,我从未意识到,月亮有如此强烈的光芒,在我心中,太阳都不具备如此的力量。
我随后看见了它旁边的云与星星,就这样过了许久。等我回过神来,有数条来电提醒。我才恍惚地离开楼道,走进了房门。
几对男女坐在一条细长的沙发上,中间是那三流歌手长相的男人,桌上摆着昂贵的洋酒,空中挥舞着烟头,所有人都在自说自话。
“你怎么才来?”他审视着我,眼神因为酒精,已有些浑浊不清。
“没什么。”我别过头,没有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
他一把将我搂了过去,两边的女人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怎么了?”
“没怎么。”我木然道。
“你和托卡分开了么?”
托卡就是我爱的那个男人,我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他抓住我的下颚,朝着脸颊亲了一口。
他说:“别在意,托卡不是坏人,但是他很懦弱,忘掉他吧。”
我摇摇头,没说什么。
之后,两边的男人开始朝我说话,我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没记住他们说的任何话。烟灰落在我的大腿上,我什么也没说。他们将酒精灌入我的喉咙,黄色的浆液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我没说什么。
所有人都在自说自话,我觉得无法忍受。我突然站起来,举起一大瓶麦卡伦威士忌,灌了下去,大约持续了十五秒。
结束后,我环顾四周,说道:
“谢谢大家。”
周围的男人不再向我搭话了。
“阿成。”
“阿成!”
我听见有人呼喊我的名字,将意识从虚无的白色中拉了回来。
三流歌手长相的男人拍着我的肩膀,他的胡子刺痛了我的脸颊。
“阿成。”
“怎么了?”
“你为什么总是不开心?”
“没什么。”我回答,“只是最近有点不开心。”
“不,你一直都不开心。”他突然严肃地对着我。
“和托卡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开心过。”
“或许吧。”我的左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右胳膊。
“阿成。”
“又怎么了?”
“你看着我。”
我注视着他,有点帅气的脸,有点锐气的眼睛和鼻梁,也有点无聊。
“我是个很无聊的人吧。”他问道。
“是的。”我点头。
“我有一群朋友吧。”说着,他指着周围的人。
“是的。”
“我每天都和他们混在一起吧。”
“没错。”
“不是的。”他摇摇头。
“其实,我每天都在干这件事情。”说着,他取出一副耳机,连上桌上的一台播放器。
“戴上。”他将耳机插入了我的耳朵。
音乐开始响起了。
我不是有文化的人,我说不清这是什么乐器,我好像听见了鼓声,还听见了琴弦;这一切又有些不一样,好像它们不是真实的乐器发出的,而是来自某种虚拟机器的模拟。我不知觉,随着它们的节奏,点起了头。
“什么感觉?”他问道。
“说不清楚,有点像是……”
“像是什么?”他注视着我。
我指着窗外,“像是月亮的旋律。”
“真是有意思的说法。”他笑道。
“总之,”他继续道,“我每天晚上,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快乐。”
我明白了什么,我们亲吻了彼此的嘴唇。
“谢谢你。”我说道。
之后,又恢复了嘈杂,一个女人开始给一个不在场的男人打电话,她一会儿破口大骂,一会儿又放声大哭,周围的男女都在鼓舞她,鼓舞她去做那些明明很无聊、他们却不敢做的事情。
再之后,人们变得不省人事,一对男女离开,剩下的一个女人昏倒在地毯上,另一个男人还在喝着闷酒。三流歌手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在听他的音乐。
喝闷酒的男人试图靠近我,我试图拉醒三流歌手,让他带我离开。他眯着眼睛,朝我碎念道:“阿成,和他回去吧,他是个有钱的男人。他会善待你的。”
“胡说什么!”我在他耳边骂道。
他继续低语着:“阿成,你要对自己好些,让自己快乐,快去吧。”
我几乎要用力拍醒他。
“别打扰我欣赏音乐。”说完他一把推开我,陷入了昏睡。
我缓缓抬起头,看着那个喝闷酒的男人,他黑色T恤的胸口上,印着一个金色的美杜莎头,他是个光头,眼神凶狠,但笑容和善。
我突然看见惨白的自己。
你这个丑陋的女人,你身上身无分文吧,你假装要死去,难道不想苟活下去么,你不需要钱么?快去舔那个男人,让他把钱塞入你的屁股。你在犹豫什么?你难道不饿么?你不要活下去么?
我看着他厚实的脸,哭泣道:“我好饿……”
男人将我扶下电梯,上了一辆黑车的后座,他带我去了一个露天排档,桌上摆满了各种羊肉,我狼吞虎咽着,又将肉和酒全都吐在桌上。
他将我送入一间洗浴中心的大床房。他帮我冲澡,我感受不到水流的刺痛。他把我压在床上,狠狠进入了十分钟,我除了痛,什么也感觉不到。
临走的时候,他给我放了一叠红钞票,在字条上留下他的电话,在我耳边温柔地说道:
“想哥的时候,给哥打电话。”
第四夜。
我记不清梦的内容了,因为太长、太真实,我几乎作为一匹马,过完了完整的一生。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裸地躺在酒店的床上。
我站起来,看着试衣镜里的自己,我看上去很白,比以往都要白,我的嘴唇破了,或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它因为痛苦被牙齿咬着。
我还发现,那个男人替我付了一周的房钱,他看出了我是一个可怜的人。他真好,他比托卡要温柔许多。但他的金钱也是温柔的吗?他的钱像是从街上的那些可怜人那里抢来的,令我深感不安。
我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产生了一个可耻的念头。
只要有男人,我就能活下去。
我躺在床上,替自己拍了一张裸出锁骨的照片,我刻意强调咬破的嘴唇,强调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我犹豫了一下,将它用做了微信头像。
之后的几小时,我在是否要变得放荡与忧郁之间摇摆着,我打开电视,里面放着喧哗的综艺节目,台上台下的人都在疯了一般大笑,我立刻换了台。另一个电视剧里,一位看似歌厅小姐的女主角,在和看上去像打工仔的老板柔情似水地谈着商业利益。
我又换了台,肌肉猛男正在纽约市拯救世界,和他的金发美人。那里的一切看上去很贵,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一切,就显得不值得拯救。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漂流瓶,去添加周围的男人。我立刻感到后悔,所有的头像都像是骗子,尽管他们尽力在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好人。即使在这种商业不发达的地方,骗子也像街上的老鼠一样多。
有几个人看着像正直的商人,反而使我看着像轻贱的小姐。我几乎要打消这个念头时,看到了一个独特的头像。
内容是一片大草原上的一条孤独小路,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570停在路边,平静地等候着前方的道路。
在我和托卡相爱时,那辆车曾是我们的梦想,它谦逊,马力十足,拥有征服大漠的勇气,又不会过度骄傲,而提早殆尽机械的寿命。它的价格不菲,在我们的钱能够支付它时,我曾提出过这个梦想,但托卡拒绝了;现在想想,他可能对大漠没有兴趣,他想攒下更多的钱,好和他的心上人,去南方的城市生活。
这个微信头像的名字叫“阿坚”,性别是男,所在地是未知。
个性签名是“寻找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前往呼格罗”。
呼格罗是哪里?
我的母亲是在草原上长大的,她懂得部落的语言,在我的记忆里,草原上没有叫呼格罗的地方,这个词并不存在,或许它不在这里,在更远的地方。
我申请了好友添加。
我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打开了电视,又关上。打开手机,没有新的提醒。或者他是个疯子,迷失在自己的路途上。呼格罗是哪里?我止不住地思考,就这样,闭上了眼睛。
第五夜。
草原上浮现出一座工厂,似乎很久以前,就停止运作了。为什么草原上会有一座工厂?我继续啃食着脚下的草地,大脑似乎没有过多思考这个问题。这里是所有马儿的归宿吗?我们顺着脚下的草,不知觉走到这里,等待着被宰杀,装箱,运往人类的归宿?
我被这个梦吓醒了,汗水浸湿了全身,我感觉到白色的液体进入了我的体内,我用热水冲刷了数遍,那种恶心的沉淀感仍挥之不去。
我不敢吃任何东西,我担心食物会让恶心加重。我只有大口喝着水,希望纯净的水带走五脏六腑的黏液,顺着下体尿出去。
我才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我打开微信,“阿坚”添加了我的好友,那是昨天晚上四点零七分的事情。
他没有说话,我点开他的资料,也没有朋友圈。
我输入了一条信息:
“呼格罗是哪里?”
没有回应。
我接着去洗澡,冲刷自己,又回到床上,打开电视,关上,躺下,起来。
晚上八点十五分的时候。
他回信了。
“你好。抱歉,我每天晚上都在赶路,早上才睡着。请问怎么称呼?”
“阿成。”
“Hi,我是阿坚,我们的名字都有‘阿’字,真巧呢。”
我没有回复,他接着打字道:“你知道呼格罗在哪里么?”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要去往那里么?”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在哪儿。但是,我梦见了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就叫呼格罗,它是一定存在的。”
我心里一惊,随即问道:“你做了什么梦?”
“我梦见我是一匹马,一直在朝着月亮的方向行走。”
“然后呢?”
“月亮总是飘忽不定,所以我怎么也找不到终点。”
“这样啊。”我叹了口气。
“我或许知道呼格罗在哪里。”我回应道。
“真的么?你真是个神奇的女孩儿。”
“但是……”我回复道。
“但是什么?”他有些疑惑。
“我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寻找它,或许我们之后还会联系。”
“这样啊。”阿坚说道。
“没关系,你慢慢寻找吧,我也要继续上路了。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能感受到呼格罗的人,谢谢你。”
我放下手机,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梦,毋庸置疑,梦的终点就是呼格罗。我只想赶紧睡着,无所事事的我,究竟该如何入眠呢?向别的男人求欢,再虚度一会儿光阴呢?还是就这么等待着。无论如何,我感到心安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前方必然会发生什么。
第六夜。
那个梦没有出现,整晚,我看见自己被不知名的男人强暴,托卡却报了警,把我当作小姐抓了起来,临上警车时,那个女人依偎在他的手臂前,用悲哀的眼神望着我。
醒来的时候,我有强烈的自杀冲动。我冲到窗台边,看着楼下灰蒙蒙的石砖地。自言自语道:“原来如此。”我的声音很淡漠。
原来我们从来没离开这座城市,这片草原上立起的几块碎砖和稻草——原来这里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爱与恨,全部发生在这里。
我洗了个脸,从桌上抓起一桶方便面,直接将干面饼大口咬了下去,又用一大口矿泉水咽了下去,舒缓地坐在椅子上。
我觉得欠阿坚一个道歉,我妄自菲薄地宣称知道了真相,给了他虚假的希望。
我拿起手机,看着头像里那个雷克萨斯越野车的背影,欲言又止。
直到三小时后,天色又暗下来,我打开了手机,觉得自己终归有责任告诉他真相。
“阿坚。”
过了五分钟。
“他突然拨来了语音。”
“喂?”听声音是个爽朗亦羞涩的男人。
“抱歉,我在开车,所以只能这么跟你说。”
“嗯。”我淡淡点头。
“你的声音真好听。”他笑道。
“谢谢。”我含蓄地低下头。
“阿坚。”我叫道。
“怎么了?”话筒里不时传来汽车的轰鸣。
“我要跟你道个歉。”
“怎么了?”他有些困惑。
“我没有看见呼格罗,我只是疯掉了,做了许多梦,分不清现实和幻境了。”
“没关系的。”他朗声道。
“什么?”
“没关系的。”他重复了一遍。
“什么意思。”我皱起了眉头。
“人生就是一场幻境,人们总是闭着眼睛在生活,他们以为自己空想的一切是现实,只有睁开眼睛的人,才能看见现实,现实就是幻境。”
“现实就是幻境吗?”我捂着嘴呢喃道,我没上过什么学,也许我听不懂这样抽象的道理。
“好好看看天上的月亮吧。”他大声说道。
“月亮?”我困惑地望向窗外。
“对,月亮。”他继续说道,“阿成。”
“怎么了?”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抵达呼格罗。”
“你是认真的么?”我问道。
“认真的。”他的语气十分坚定。
“所以你啊,好好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吧,我要继续赶路了。”说着他大笑着,挂掉了通话。
我望向天上的月亮,就像那晚在楼顶所见一样明亮,它照亮了街上的白墙、广告牌、以往在白天我厌恶的事物。
第七夜。
我中午就睁开了眼,但是我拉上了窗帘,防止任何光线进入。我洗了澡,刷牙,吹头发,用热水煮熟了方便面,吃了下去。
我打开手机,给三流歌手打了一通电话。
他还没睡醒,迷糊地喃喃道,“怎么了?”
“把你的歌单传给我。”
“歌单?”
“对,那天晚上你给我听的音乐,有多少传多少。”
“好,发生了什么吗?”
“我要去旅行了。”
“旅行?”
“你别管了,总之把歌单传给我。”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之后,我管前台要了几张纸和笔,坐在写字台上,开始画画。
我试图把梦见的马和草原画出来,涂涂抹抹后,我只画出了一片碎草地上一只低着头的黑色生物,和远处类似烟囱的建筑物。
“太难看了。”我放声大笑。
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拨打了阿坚的微信电话。
“喂。”
“怎么了,阿成?”
“你起床了么?”
“我在车里睡了一觉,正准备上路了。”
“你大概在什么位置?”
“从你所在城市往北四百多公里了吧,我中间绕了许多路,我大概已经在国境线了吧,这边的地图都失灵了,很难找到正确的路……”
“往回开。”
“什么?”他没听清。
“往回开。开到我这里。”
“阿成……”
“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找到呼格罗,不是么?”我笑道。
过了几秒钟,他笑着点头道,“嗯,我来了!”
我躺在椅子上,一会儿后做回了在草原上行走的梦,我还是那只孤单的马,只不过这次月亮指引着我的路,我似乎还听见了音乐,鼓点在敲打着远方的山谷。
等到晚上九点,阿坚的白色越野车停在酒店门口。我穿着浴衣冲了出去,车上下来一个干瘦的小伙子,皮肤有些黝黑,眼睛明亮,带着坚毅的笑容。
“阿坚!”
“你是阿成。”他的笑容变得羞涩。
我拉着他上楼,收拾了东西,在楼下的大排档点了一整桌肉,我嘴里塞满羊肉,和他激动地讲着我的计划,我甚至忘了自我介绍,忘了告诉他我的过去, 忘记了询问他的过去。我将梦里的内容全部告诉了他,我认为那就是前往呼格罗的必经之路。不知怎的,阿坚就认可了我的话,使劲儿点着头,大口往嘴里塞着羊肉。
我告诉他:“草原的尽头,有一座工厂。”
“工厂?我没找到那样的地方,这里应该没有还在运作的工厂。”
“它早就停止运作了,那里是梦境与现实交汇的地方,在那里选择了正确的路,就会通往真正的呼格罗。”
“我知道了。”阿坚用力点头道。
说罢,我吞下了一大口啤酒,接着转过头,一口气全部吐到了地上。
“不好意思。”我嘴边挂着啤酒沫子,笑着看着他。
“你有钱么?”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就要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我一把抢过他的手,从兜里取了一些钞票,扔在桌上。
之后我又带着他在旁边加了油,那之后,我们就上路了。
我还穿着那条夹杂着黑斑的白裙子,我只有那一件衣服。
在这里,只要朝着城市外开出半小时,天上的星星就变得格外闪耀,地上看不见一丝光污染,再往前,彻底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真是奇妙,我们明明离未知那么近,却从未感受过它的力量。
我们在夜路走了许久。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三流歌手的歌单,我们一直跟着节奏,忘记了跟对方说话。
“你喜欢这些音乐么?”过了足足半小时,我才开口道。
“喜欢啊,这是什么东西,真好听,真奇妙。”他笑道。
“我也不知道。”我干脆地答道。
“世界上奇妙的东西真多啊,不是吗?”
他点点头。
夜晚十二点,抵达了一间小休息站,我走进幽暗的洗手间,他在草地上接地解决,我们尽量不去看彼此。
出来的时候,他问道,“阿成。”
“怎么了?”
“你出生在这片土地么?”
我的手掌撑着脸颊,看着窗外飞过的草地,答道:“算是吧。”
“这是很大的土地,我只是来自其中一个角落。”我补充道。
“这样啊。”阿坚说道,“我来自一个很干枯、炎热的地方。”
“阿成?”
“怎么了?”
“你的父母也是生长在这里么?”
“我的母亲是放羊的,我的父亲是从南方过来打工的,生下我后,他就离开了。”
“这样啊。”
“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和你爸妈相比,他们好无聊啊。”阿坚沮丧地握着方向盘。
“怎么会。”我忍不住放声笑起来,他受到我的感染,也放声大笑。
“你的母亲还在么?”
“死了。”我干脆地答道。
“这样啊,她死的时候,也在这片草原上么。”
我点点头。
“真好啊,有的人只要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就可以回归自由。”
“为什么?一生无法走出这里,难道不是一种不自由么?”我皱着眉头,望着他。
阿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继续说道,“我的父母生长在干枯的土地上,老在干枯的土地上,他们希望我能陪伴在身边,但是那样太无聊了。”
云层就在路的尽头,几乎要和地面融为一体,他看着前方的云,意味深长道:
“你相信,人死后会升到天堂么?”
“不相信。”
“这样的,我相信天堂,我相信天堂就在这片土地的尽头。”说完,他朝我莞尔一笑。
之后我们又走了很久,我的思绪随着音乐到了一座从未见过的城市,那里的一切很干净,又没有人,就在我要探索它时,阿坚停下了车,朝我说道:今晚,我们就在这里睡觉好么?
我点点头。月亮的光芒刺眼,却丝毫不影响我们进入梦乡。
第八夜。
老实说,白天睡得很糟糕,我梦见了过去的事情。我到了七岁才会说话,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我与母亲。十三岁的时候,一个男人摸了我,我吓得说不出话。母亲认为我智力低下,给我找了一个纺织厂的工作,劳作的时候我走了神,差点切断了手指。那之后,母亲就悲伤地死去了。
醒来的时候,我们被路过的羊群叫醒了,它们喊叫的时候,就像女人被男人用力折磨时,发出的声响那样。
我拉开车帘,让阳光进入。上百只可爱的小羊呼啸而过。
“你喜欢羊羔么?”
“它们很可爱。”阿坚揉着眼睛说。
“我的母亲就是放养少女。”我说道。
“你吃羊的时候有罪恶感么?”我接着问道。
“有。”阿坚回答道,“我爱吃它们的肉,就像我爱拥抱抚摸它们。”
我们接着上路了。
我们看见了成群的马儿和金黄的草。我激动地告诉阿坚,我们就要到地方了。
“为什么我之前,看不到你说的那个工厂?”
我思索了片刻,回应道:“它一直存在在那里,只不过,你的心里没有它的存在。
“是这样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谢谢你,阿成,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又过了一会儿。
“阿成。”
“嗯?”
“我爱你。”他爽朗地笑道,就像小朋友诉说友情那样。
“我也爱你。”我捂着嘴唇,呢喃道。
不久之后,下了一场雨,草原上的雨水并不常见,雨后,起了雾,我们只能看清眼前的路。
雾散去后,我指着左边车窗外:“你看见了么?”
迷雾之后,一座工厂,两座烟囱露出银白的浮影。
“真是不可思议。”阿成感叹。
我说道:“我想了很久,终于知道了答案。”
“什么?”
“这是一道分水岭。”
“没有灵魂的,会被送往工厂,切成块儿,当作驴肉卖给城里的人。剩下的,会继续前进。”
“看见那先迷失的马儿了么?”我指着前面,它们悠哉地吃着脚下的草,一步步通往工厂的方向。
接下来的夜,变得很漫长,我们没有做过多思考,只是在前行着。
快睡着时,阿坚叫醒了我。
“看见前方的黑夜了么?”
我顺着他的目光而去。
“云层才是世界的道路,大地不过世界的边缘。”他坚毅地说道。
“确实,在草原上,除了地上一截短短的草,一切都融入了天空,被天空吞没了。”
“所以,我们在世界的边缘,我们要前往世界的主道。”他说着。
第九夜。
这里的道路已变成了起伏的山丘,从之前的视野开阔,到现在只能看见前面的一个小土包,信号变得缥缈,除了吃草的牛羊,没有一辆车、一个人。
我们的食物仍然是水与干粮。我想去路边宰杀一只羔羊,又想那样是否过于残忍。
“阿坚,你知道么?”
“什么?”
“所有的这些羔羊,都有主人,总有一天,它们会被宰杀。”
他很惊讶。他并不知道,这里也住着牧民。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人,每一片土地既是世界的边缘,也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这里已经不一样了。”我补充道。
“是啊。”阿坚还在思索我刚才的话。
“前面的路,只有真正有勇气的人能走下去。”我总结道。
在我们翻越山坡时,音响奏起了原始部落的鼓声。
“我知道为什么了。”我自言自语。
“知道什么?”
“为何男人要抛弃我。”
“为什么?”阿坚饶有兴致地问。
“他想活在太阳底下。”
“太阳底下?”
“对,他想和女人结婚,交媾,生下孩子,将孩子送进漂亮的学校,住在干净的房子里,拥有几件漂亮的衬衫,周末去餐厅吃饭、看电影。”
“他想要阳光照亮他生活的一切。”我总结道。
“你知道么?”阿坚说道。
“怎么了?”我问。
“我辞去了国土局的工作。”
“为什么?”
“大学毕业后,本来想当地理学家,后来我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
“世界的道理,不是靠在地表上的计算与研究能够获取的。”他回答道。
“所以你要辞职么?那是份不错的薪水吧,换做是我,说不准留在那里混日子。”
阿坚没回答我,接着说道:“我辞职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跪在我面前。”
“然后呢?”
“他们祈求着,说我离开,就去死。”
我没说什么,我的母亲很早离开了世界,她的世界太过于简单,爱人的逃离,女儿的漠然,对于一个牧民生下的七个少女之一,太过复杂。
“他们不会自杀的。”他笑道,“但他们会更早死去,因为悲伤、羞愧、不理解。”
“是啊。”我轻松地说。
“阿坚。”
“怎么了?”
“你讨厌人类么?”
“我只喜欢人类中的少部分,但我不讨厌所有人。”
“这样啊。”我叹道。
“我总说讨厌人类,但是却爱上了男人,真是可耻啊。”
“一点也不可耻。”他专心看着眼前的路,回答道。
“世界上只有一种可耻,就是不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们已经许久没看见白天,或许白天不会再出现了,这里是世界的边缘与主道的交界地,世界的主道是没有太阳的,月亮反射了一切光。
路越加难走,车上的汽油只剩下两箱,我们的内心却十足平静,并非因为我们笃信,呼格罗就在前方;即使它永远不现身,我们的内心也可以平静下去。
曲折的路终于结束了,接下来是平缓的夜路。
我似乎看见了许多花,在夜晚看似荒芜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我们望见了一座宫殿,它石灰的框架,被月亮照得透亮。我们下了车,走了过去,那之后,立着许多未完成的水泥塔楼。
我们在墙角,找到了一枚奇异的蓝色石头。
我想起了一个久远的故事,在我还未完全张口说话时,母亲就一直念叨的。
“曾有一群人,他们迢迢千里来到草原的尽头,为了生活在离他们的神更近的地方,他们怀抱着理想,建造自己的乐园,在未完成的时候,他们被一场大风吹到了天上,留下这些塔楼的骨架。”
我看着阿坚的脸,我们躲在一扇墙后,在月亮看不见的地方,亲吻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