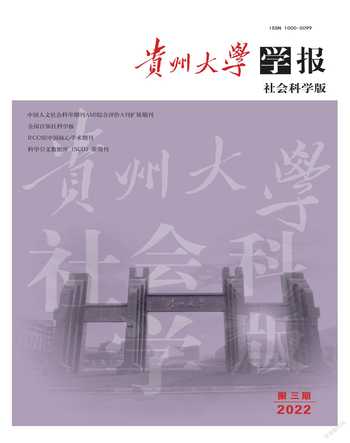论福柯的空间思想
摘要:福柯的空间理论起步于他的早期讲演《他种空间》,后来在《规训与惩罚》等一系列著作中,亦多阐发。福柯认为伽利略开启的世俗空间传统,今天依然有待开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等的对立,依然没有破除。故他推崇巴什拉,即揭示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洞的空间里。在《他种空间》里,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是他空间思想的一个核心。异托邦是真实的地方,不是虚构空间。异托邦在又不在,历时与共时并存,将同一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真实场景同时呈现出来,又同时彼此冲突和反转。但诚如乌托邦可以走向它的反面——反乌托邦,异托邦同样也走向它的真实存在过的反异托邦。因此,规训空间当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关键词:福柯;他种空间;异托邦;规训空间
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3-0001-08
言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间思想,福柯早年的一个讲稿文本《他种空间》在当今风起云涌的后现代“空间转向”中广为传布,并已成为一个经典。虽然这篇讲稿的刊布,是在他去世的同年1984年。多年以后,在今日亦成故人的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看来,当时福柯已经在酝酿类似于他本人“第三空间”那样的理论体系了。索亚对福柯的空间思想与列斐伏尔有过一个比较:跟列斐伏尔相反,福柯自己的空间理论建构从未进入高度自觉的细节,他也很少把自己的空间政治学转化为明确定义的社会行动纲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说(福柯若经提示也会同意),他的全部著作,从《癫狂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癫狂史》(1961)到1984年他去世前不久(以及之后)出版的多卷本英译性史的著作,其核心就是对空间性进行全面的批判的理解。[1]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本人在1974年出版的标志性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已经注意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也谈到了空间。但列斐伏尔写作此书时,显然还未读到福柯先时以及后来的空间热情,并认为福柯没有解释清楚他所说的空间到底是指什么东西,以及它如何沟通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福柯当然知道空间是什么。作为读者,我们反倒纳闷,假若列斐伏尔写作《空间的生产》时,业已闻知福柯《他种空间》这篇著名讲演的内容,是不是还会埋怨福柯谈论空间不够深入?
一、空间的历史
福柯在1967年3月14日的一次建筑研究会(Cercle détudes architecturales)上,发表过一个题为《他种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讲演。这个讲演的刊布姗姗来迟,直到福柯本人去世之后的1984年10月,才发表在《建筑,运动,延续性》(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é)杂志的第5期上,后收入《福柯言述集》(Dits et ecrits)第四卷。因为发表的文本未及经作者本人审核,故福柯的正式文集通常不收此文。但在福柯谢世前不久,这个讲演的手稿在柏林的一个公共场合有过一次展示。由此可见,《他种空间》作为福柯空间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其著作权是不成问题的。
1967年是结构主义方兴未艾,或者说是如日中天的年代。所以不奇怪福柯的这个《他种空间》讲演,开篇谈论的也是结构主义。福柯说,19世纪的一大困顿是历史,发展与停滞、危及与循环、过去的不断积累与世界降温,诸如此类的主题叫人迷茫。故而,19世纪的神话资源从根本上说是来自热力学第二定律;即是说,能量可以从温度高的物体传递到温度低的物体上面,但是反过来不能从低向高传递。但是今天却不同,今天的时代是空间的时代,其特征是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我们处在一个并列、远近和散布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不复是时间串联起来的悠长生命,而成为一张用它自己的线索交叉连接起点与点的大网。故而:陸扬:论福柯的空间思想结构主义,或者至少集聚在这个稍许有点笼统的名号之下的东西,是在可以连接到一根时间轴线上面的诸多元素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集合,以使这些元素呈现为并列的、彼此冲突的,又彼此包容的模样,简言之,呈现为一种建构。事实上,结构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时间;它认真关系到某种同我们称之为时间和历史的东西打交道的方法。[2]752这是说,空间本身有一段历史。结构主义虽然奉行共时性的空间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排除历时性的时间线索。这以空间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理论以及各种体系的视野里,并不是新鲜事情。对此福柯指出,在西方的经验里,空间有空间的历史。回溯历史,中世纪就是不同地方的等级有序的集合,有神圣地方和世俗地方,被保护的地方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地方,城市地方和乡村地方等的对立,所有这些地方都关系到人们的真实生活。而在宇宙学理论里,下面是陆地人间,陆地上面有天国,天国上面还有超级天国。有些地方的事物已经被剧烈移位过,有些地方的事物则天生稳稳就在那里。而正是所有这些地方的等级排列、反向排列,以及交叉排列构成了我们大体可以叫作中世纪空间的那东西。简言之,中世纪的空间,就是“确认方位的空间”(espace de localisation)。
这个“确认方位的空间”,在福柯前一年出版的《词与物》中,被表述为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交被新柏拉图主义复活的一个古老概念——“小宇宙”。据福柯所言,它是将两个具有相似性对象的相互作用,应用于所有的自然领域之中。它意味着知识主体在每个事物中都能发现自己的映像,以及对浩大宇宙的深信不疑。反过来,最高领域中的可见秩序,将同样反映在地球最深处的黑暗世界中。所以它表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的四周勾画了所有被造物的界线;在世界的另一端,存在一个享有优先权的创造物,它在自己的有限向度内,产生了有关天空、星星、山脉、河流和风暴的巨大秩序;相似性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一基本的类推的有效界线内展开的。因这个事实,从小宇宙到大宇宙的距离无论有多大,但都不可能是无限的。[3]很显然,这里以人为小宇宙,对应于自然大宇宙的空间观里。在福柯看来,它们终究还是有边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大自然,类似符号与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依据宇宙的复制形式,把自身封闭了起来。
福柯认为这个确认方位的空间,是始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因为伽利略遭受迫害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他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在于构建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空间。在这个无限的空间里,中世纪的方位纷纷消解,不复具有任何意义,而化解成为其运动中的一个点。换言之,从伽利略和17世纪开始,“广延”(eténdue)替代了方位确认。空间由此从中世纪的方位确认转移到近代的扩展模式。及至今日,广延又被“位置”(emplacement)所替代。“位置”可以定义为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而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位置或者生活空间问题,并不仅仅是探究世界是不是有足够空间供人类生存,同样也在于探问人类因素以什么样的相邻关系,怎样储存、循环、标签和分类,方能在特定环境中达到特定目的。所以,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时代里的空间形式。这也导致今天时代的焦虑,何以从根本上关牵着空间,而远胜于关牵时间。
问题是,伽利略开启的世俗空间传统,在福柯看来今天依然有待于开拓。对此福柯指出,今天我们的生活依然是被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所统治,我们的制度和实践依然没有摧毁这些空间。例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休闲空间与工作空间等,不一而足。对此,福柯高度推崇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的诗学》,认为巴什拉此书中的现象学描述可以给予我们许多启示。福柯说:巴什拉的划时代著作和现象学描述教导我们,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洞的空间里;恰恰相反,我们生活的空间也深深浸润着各种特质,甚或通盘就是异想天开。我们第一感知的空间、梦幻空间和激情空间,各各具有自身的内在特质:有亮丽的、轻盈的、透明的空间,也有晦暗的、粗粝的、蒙障重重的空间;有高高在上的最高空间,也有深深塌陷的泥淖空间;还有涌泉般流动不居的空间,以及石头或水晶般凝结固定的空间。[2]754但福柯也认为,巴什拉的分析对于思考今日之时代固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主要还是涉及内部空间,而他现在同样希望来谈一谈外部空间。
福柯所说的外部空间,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他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在不断遭受侵蚀。这个空间说到底,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空间”(espace hétérogène)。异质空间不是真空,不是我们在其中可以随意安置某人某物,可以把它点缀得五光十色的空间。反之,它是一系列关系,而正是这关系在界定着我们的交通、街道和运动。通过这个关系群集,我们可以描述咖啡馆、影院、海滩这些休闲场所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描绘封闭或半封闭的栖居地,如住宅、卧室、床榻,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场所之间,福柯指出,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在这一大张关系网里,具有特别属性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可以质疑、抵制,甚至颠覆它们所反映的关系集群。这些特殊的空间,福柯认为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种联系着所有其他空间,那是乌托邦;一种对立于所有其他空间,那是“异托邦”。
二、异托邦
“异托邦”(hétérotopia)是福柯空间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异托邦,是相对乌托邦而言。福柯对于乌托邦的定义:它是没有真实方位的地方。但总体来看,这些地方同社会的真实空间多多少少有着曲曲直直的关系。它们以完美的形式表现社会本身,或者把社会颠倒过来,那是反乌托邦。不过说来说去,大凡乌托邦,指的都是非真实的地方。
但异托邦不同,异托邦是真实的地方。福柯指出,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文明里,都有这样一些确实存在的真实地方,它们有时候就像没有方位的乌托邦,落实在了真实场地,同一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真实场景,同时呈现出来,又同时彼此冲突和反转。这样的地方,其实是在一切地方之外,即便它们在现实中能找到具体方位。这样一个历时与共时并存,在又不在的地方,便是福柯的“异托邦”。对此,福柯做了一个镜子的譬喻:因为这些地方跟它们所反映和言说的场所完全不同,考虑到跟乌托邦的对比,我将它们称之为异托邦。我相信在乌托邦和这些完全不同的他种场所,即异托邦之间,还可能有某种混合的、联合的经验,那可能就是鏡子。镜子说到底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方位的地方。在镜子里,我在我不在的地方看到自己,那是一个敞开在平面背后的非真实的虚拟空间;我就在那里,可是我并不在那里,是一种影子让我看到了我自己,让我在我不在场的地方看到自己,这就是镜子的乌托邦。但是就镜子存在于真实世界,就我占据的位置起到反作用而言,它也是一个异托邦。[2]756对此,福柯进一步的解释是,从镜子出发,我发现我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镜子里我的目光从虚拟空间的深处看过来。我在照镜子,这本身是真实的,但是镜子里的我却是真实又不真实的幻相。这面处在真实与虚拟空间之间的镜子,在福柯看来,其功能就照出了乌托邦和异托邦的双重属性。
那么,异托邦的意义又当何论?即是说,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我们如何来系统研究、分析、解读这些他种空间呢?福柯提出,围绕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异托邦空间,其真真假假的论争可以称之为“异托邦学”。福柯进而条分缕析,阐述了异托邦学和异托邦的六个原则。
福柯认为乌托邦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普天之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构成异托邦。这是说,异托邦无所不在。但即便无所不在,异托邦却没有绝对统一的形式。它形态各异,不过大体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型。其一见于原始社会,可名之为危机异托邦。比如说有一些圣地和禁地,专门留给处在危机状态的人众,如青少年、处于经期的女人、怀孕妇女、老人等。迄至今日,危机乌托邦已日渐消失,但也有若干剩余,如19世纪的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兵役服务等。福柯并举了“走婚”(voyage de noces)这个一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的古老例子,指出女孩子失落贞操,可以发生在许多“乌有之地”,火车和蜜月旅馆就是这一类乌有之地,它们都是没有地理标志的异托邦。
异托邦学的第二个原则是同一个异托邦在社会历史中,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功能。对此,福柯举了公墓的例子。墓地当然不同于普通的文化空间。但是它跟城邦村庄都有关系,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亲人埋葬于斯。福柯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公墓事实上一直存在,但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直到18世纪末叶,公墓还一直位居城市中心,紧挨着教堂。公墓里也有等级,有骸骨教堂、个人坟墓,教堂里还有墓穴。但是从19世纪开始,随着骨灰盒普及大众,公墓向城市边缘迁移。这跟担忧墓穴传染疾病的恐惧直接相关。如是公墓不复是城市的不朽神圣心脏,反之变身为了“他种城市”,每个家庭在这里都有一个幽冥居所。
第三个原则是指异托邦可以将互不相容的若干空间和场所,并置在同一个地方。在这一方面,舞台和电影院便是例子。舞台上互不相干的地点接连展开,影院中我们在一方二维的银幕上看到了大千世界的三维空间。但这一类异托邦里,最典型的例子是花园。对此,福柯高度赞赏古代东方花园,指出波斯的传统花园是一个神圣空间,它的长方四边形代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心有喷泉水池,它较外围更要神圣,好比世界的肚脐。花园里各种草木汇聚到同一空间,构成了一个微观宇宙。就此而言,波斯地毯也是花园的复制品,它将整个世界的完美符号聚于一体,是在空间中流动的花园。因此,花园就是一个普世性的幸福异托邦。今天的动物园,就是从花园脱胎而出的。
第四个原则指的是异托邦经常联系着的时间的片段。这是说,为了对称的缘故,异托邦经常走向所谓的“异托时”(hétérochronies)。对此,福柯又举了墓地的例子,他指出,当人们同传统的时间彻底割断,异托邦就开始全力以赴了。所以,墓地是异托邦的典型地方,因为人生到头,墓地就伴着这个古怪的异托“时”,开始进入貌似永恒的另一种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异托邦和异托时错综复杂交合在一起。比如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异托邦就在无穷无尽地积累时间,将各个时期的文物、文献和档案,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形式、所有的趣味,集聚在同一个空间。福柯指出,这个无限积累的理念是属于我们的现代性。不同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永久性,福柯发现异托邦和异托时的连接方式还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形式,那就是节庆。节庆的场合通常是在市郊的一片空旷地上,一年一度或一年两度,三教九流各式人众汇合过来,摔跤的、耍蛇的、算命的,无所不有。这是为异托邦和异托时的另一典型景观。
第五个原则,异托邦应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彼此隔绝又彼此渗透。总体来说,异托邦的空间并不像公共空间那样可以自由出入。进入是强制的,如兵营和监狱。有一些地方要事先提出申请,或者经过洁净仪式,方可入内,如穆斯林的土耳其浴室。还有一些地方仿佛是敞开大门,谁都可以自由出入这类异托邦空间。然而,那只是幻觉。如巴西过去有些大农庄的著名卧室,游人尽可以推门进去,睡上一晚。但是,这些卧室跟主人家庭区域并不联通,所以游客到底是过客,并不是主人邀请的贵客。你以为是进去了,实际上还是没有进去。
最后一个原则是在异托邦跟剩下来所有空间的关系中,在两极之间发挥功能。两极都旨在创造一个虚幻空间,可是在这个虚幻空间里又见出一切真实空间,它们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反过来说,两极的功能是意在创造另一个真实的空间,一个完美的、精工细作的、有条不紊的他种空间,而不似我们自己的空间那样杂乱无章。所以,它可以作为真实空间的一种补偿。对此,福柯举了殖民地的例子。他指出第一波殖民热潮发生在17世纪,英国人在美洲建立的新教徒社会,就是绝对完美的他种空间。与此相似的还有南美洲耶稣会的殖民地,井井有条堪称奇迹。如巴拉圭的耶稣会村庄,就严格按照长方形来布局,矩形的底部是教堂,一边是学校,一边是公墓,教堂前方有一条街道伸出,跟另一条街道十字相交,沿着这两根轴线,居民各就其位,如是完美演绎了基督的十字架符号。是以不奇怪,在福柯的《他种空间》这篇讲演中,最后的话是:封闭屋舍和殖民地,是异托邦的两种极端类型。说到底,我们可以想象船是一种漂流空间,一个没有地方的地方,它自给自足,将自己封闭起来,同时又漂向无限的大海,从港口到港口,从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从屋舍到屋舍,一直漂到殖民地,寻找它们藏在花园里的珍贵宝藏。这样想象下来,你就会懂得从16世纪到现在,为什么船是我们文明中经济发展的伟大工具(今天我不谈经济),而且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想象载体。船是最典型的异托邦。没有船的文明中梦想枯竭,间谍替代冒险,警察替代了海盗。[2]762至此我们发现,福柯谈他种空间再是云遮雾罩,终究还是围绕着以大西洋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展开的。乌托邦也好,异托邦也好,大陆文明跟它们没有关系。大陆文明在福柯看来,在他的“他种空间”里不值一道。
三、规训的空间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1969年面世,该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质疑历史研究的连续性。用福柯本人在该书“引言”中的话说,那些被称为思想史、科学史、哲学史,以及文学史的学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大都业已偏离传统史学家们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故人类思维的连续性,今天正在受到挑战,反之断续性的重要性呼之欲出。就他本人而言,福柯指出,对于精神病理学、医学、政治经济学这一类传统学科,他不会贸然深入它们的内在形式和潜在矛盾,但是他会提出问题:它们根据什么样的规律形成?它们在什么样的话语事件基础上被割裂出来,以及它们最终是否在它们被接受的并且近乎成为制度的个体性中,不是那些更为稳定单位的表层结果?我接受历史给我提出的这些整体,只是隨即对它们表示质疑;只是为了解析它们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或者是否应把它们重建为另一些整体,把它们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4]福柯这里的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他的新历史主义话语研究是将主要使用空间的方法,放入传统史学想当然的连续性形式之中。惟其如此,可望打开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将澄清原始材料即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作为视为一切批评行为的先决条件。
福柯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被认为是受早期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等现代性批判家的影响,系统且细致描写了现代世界的空间转化谱系。批判的主题固然一如既往,但福柯在此书中表现出来的空间意识,则被认为是以身体为中心,通过追溯刑罚体系的变迁,来写权力机制的衍变。酷刑、惩罚、规训、监狱,由此成为该书的四个典型场景。在该书中,福柯从落笔开始即不厌其详,细数18世纪以降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惨不忍睹地撕裂肉体。进而表明,西方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空间转化的历史,故必须在权力、知识和肉体的关系之中,来分析现代社会的转型。
《规训与惩罚》开篇写的是公共空间中的公开处决,描述了18世纪的刽子手如何在广场上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子撕开犯人的胸膛和四肢,用硫磺来烧犯人执弑君凶器的右手,再用融化的铅汁灌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尸。对此福柯的感想是,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是消失了,这是事实,即在数十年间,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脸上和手臂上打烙印、示众以及暴尸,这些现象终究是消失了。但是惩罚没有消失:因此,惩罚将逾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应该能够阻止犯罪;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结果之一是,司法不再因与其实践相连的暴力而承担社会责任。[5]至此,我们可以说,福柯下沿的是与他的本国同胞列斐伏尔迥异其趣的另外一个空间的批评传统。诚如福柯《他种空间》和《权力的地理学》等文献中阐述的他种空间与异托邦理念,多被嗣后学者赋予多元空间的后殖民解读和性别解读。从《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18世纪中期以来刑罚机制现代变革的分析,以及对全景畅视监狱机制下空间、身体、权力的关系考察,也都启发了我们对社会空间与主体认同的新认知。
福柯的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对文艺复兴戏剧的重新解读。格林布拉特本人在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暴风雨》中通力破解权力关系,读出普洛斯庇罗对卡列班的无情殖民,即为一例。福柯的权力—空间地缘政治学,终而演绎为性取向—性别建构的主体性空间对峙。这一方面,大卫·贝尔(David Belle)等人的《绘制欲望:性的地理学》、罗宾· 朗赫斯特(Robyn Longhurst)的《身体:探索流动的边界》以及琳达·琼斯顿(Lynda Johnston)等人的《空间、地方和性:性向地理学》等一批文献,都可以显示福柯的影响怎样在性别和地缘政治的每一层面蔓延。
就规训与惩罚的主题而言,在福柯看来,欧洲社会的规训,是从空间的分配起步的。具体来说,为了实现规训的目的,需要以下数种机制的配合。第一是需要一个封闭的空间,圈定一个自我封闭的、有别周围世界的场所。这方面有对流浪汉和穷人的“大禁闭”,也有一些更谨慎也更为隐蔽的措施。还有逐渐采用修道院式寄宿制的大学和中学,以及兵营,它可以约束大军,使不至扰民,避免驻军与地方当局的冲突。福柯枚举的统计数字是,直到1745年,法国大约有320个兵营。1775年,兵营内的总人数达到20万人。此外,工厂也逐渐形成大面积的单纯而明确的工业空间。日趋集中的管理模式,便于获取最大利益,消除偷盗、怠工、动乱等不利因素。
第二,有鉴于“封闭”原则在规训中不可能一劳永逸,第二种机制是根据单元就位或者分隔。它意味着规训空间可以进一步细致化,按需分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上都有一个人。如是便于监督施行,谁到场了,谁缺场了,谁尽力了,谁开小差了,一目了然。这是用纪律组织起来的一个可解析的空间。福柯发现这个机制类似修道院的密室,它通常是分格单元式的,适合禁欲主义之需。他并引法国18世纪警官尼古拉·德拉马尔(Nicolas Delamare)《论警察》中的描述:“睡觉是死亡的影像,寝室是墓地的影像……尽管寝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挡,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寝都不会被人看见。”[6]163即便如此,福柯认为这一方式,也还是显得粗糙。
第三是按用途分隔出特殊空间。比如陆军医院和海军医院,就有严格的隔离区域,以防传染病的流行。每个病人都被记录在册,分床隔离,对症处置。随之形成一种行政空间和政治空间,借此医疗空间形成了。还有18世纪末叶出现的工厂,它将人员分配、生产机制的空间安排,以及其他岗位分配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布局是一方面可以统揽全局,一方面可以监督到每一个岗位。工人的体力、敏捷性、熟练性、持久性都历历在目。这一规训空间的形成,故而成为大工业兴起时期的必然。
第四是教育空间的等级排列。等级替代作为统治单位的领土和作为居住单位的地点,成为新的规训空间形式。福柯举了班级的例子,他指出在耶稣会的大学里,每个班级有二三百名学生,十人一组。这呼应了当年罗马和迦太基行伍中的“十人团”基本形式。每个学生的位置,根据他作为“十人团”中一名战士的角色来加以确定。从18世纪开始,“等级”愈益彰显,学生在课堂和校园中的座次和位置、每个学生完成各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难度排列的科目序列等,皆排定在等级空间之中而交替换位。对此福柯说: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每个学生受到几分钟教师的指导,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学生无事可做、无人照顾)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组织了一种新的学徒时间的体制。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6]167空间与时间的因素在这里再度交叉起来,成就为多元并置异托邦的又一种规训形式。据福柯自己的解释,规训的策略与自然分类法不同,后者是以特征与范畴为基轴,规训策略则是以单数和复数的关系为基轴,既对个体作特征描述,又对特定的复杂对象加以整理,从而为“细胞权力”(cellular power)的微观物理学打下了基础。
福柯认为规训空间的典型,是18至19世纪英國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发明的全景畅视监狱(panopticon)。这类监狱的构造是在一个环形建筑群中心,修建一个高高的瞭望塔。瞭望塔顶端有一圈大窗户,面对包围着它的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隔成一个个狭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群的横切面,佩以两个窗户,一个朝里跟瞭望塔顶的窗户相对,一个朝外用于采光。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病人、罪犯、工人或者学生,其一举一动,假以跟瞭望塔恰好相反的光源角度,被塔顶的监视人看得清清楚楚。由于犯人知道自己时刻暴露在监视之下,以至于即便塔顶无人,他们的举动也习惯成自然,变得规规矩矩。福柯认为边沁设计的这一全景畅视监狱,颠覆了传统监狱的原则,更具体说是推翻了它的三个基本功能:封闭、黑暗和隐蔽。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6]226。简言之,权力不复体现在个人身上,而是变相体现在了空间与光的精心安排之上。作为《规训与惩罚》中被引述最多的这个全景畅视监狱的建筑理念,它不妨说是肉体在空间中的另一种定位,这个身体为权力所规训的定位,可见在福柯看来是无所不在。不仅是监狱,医院、兵营、工厂和学校亦然。由是观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空间,不啻是一个规训和惩罚的大监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学》开篇即称其为人类最高贵感官的视觉,由此也与权力狼狈为奸,成为了监禁与惩罚的帮凶。
美国批评家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Wegner)在他题名为《空间批评》的文章中,认为福柯的空间思想是跟列斐伏尔分道扬镳。列斐伏尔关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中的空间关系,福柯则致力于探究权力结构空间转化的历史谱系,特别是把聚焦的中心转向了身体。如是在福柯笔下,个人的身体成为公共“剧场”中的主体,承受远离日常生活的仪式空间中的严厉惩罚。然而,正因为这一体系变身为了惊心动魄的公共景观,也导致它极不稳定,随时有可能被颠覆过来。故而:在这一古老的权力逻辑中,逐渐滋生出来一个新的体系,其中每一个身体发现自己被定位在“一个巨大的封闭、复杂,有等级森严的结构里”,而屈从于一个监控与操控的连续体制。一个福柯名之为“规训”的整个运作系列——“工具、机制、程序、应用层面、目标”——应运而生,以便生产出“规范”的主体,同时标记出一个精心完成的异常行为王国:“如此规训生产出顺从的熟练的身体”,“驯服的”身体。[7]韦格纳上文引号中的文字,都出自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规训的空间由是观之,该是福柯谓之“他种空间”的一种资本主义权力压迫的空间范式;更具体地说,这是他不厌其详规定出的六条原则的“异托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诚如乌托邦可以走向它的反面——反乌托邦,异托邦同样也走向它的真实存在过的反异托邦。规训与惩罚的空间,不过是不算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例子罢了。
参考文献:
[1]SOJA E.Third 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 Places[M].Malden:Blackwell,1996:147.
[2]FOUCAUL M.Des Espaces Autres [M].Paris:Editions de Gallimard,1994.
[3]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43.
[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1.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0-11.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7]WEGNER P E.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uality[M]//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183.
(責任编辑:张娅)
On Foulcaults Thought on Space
LU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Abstract:Foucaults space theory, formed in his early speech “Des Espaces Autres”, is illustrated in a series of later works such as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Foucault believes that the secular spac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Galileo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today,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rivate space and public space, cultural space and practical space has not been eliminated yet. Therefore, he praises Gaston Bachelard for revealing that people do not live in a homogeneous empty space. Foucaults “heterotopia” concept, first proposed in“Des Espaces Autres”, is a core of his spatial thought. Heterotopia is a real place instead of a fictional one, both here and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the coexistence of being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resenting a collage of all real scenes in the same culture simultaneously, with every single scene conflicting and reversing each other though. However, as Utopia can go to its opposite Anti-utopia, heterotopia may go to its opposition that really ever existed as well, which is illustrated by the space of discipline, one of the important cases.
Key words: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heterotopia; space of discipline
收稿日期:2022-01-20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
作者简介:陆扬,男,上海人,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