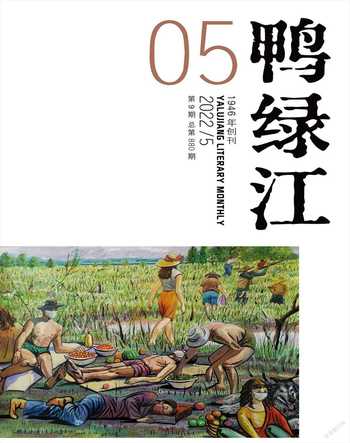诺曼不曾死去(短篇)
19:21
“他死了!”她说。
冬天的最后一个夜晚,她牵着一条金毛犬闯进我的房门。她的双眼圆睁,把黑色小羊皮的手包随手扔在了鞋柜上,那只狗撒着欢儿,摇晃着尾巴围着她不停地转圈,指甲和瓷砖地面间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她并不在意,踢了踢狗儿的胯子,依旧盯着我看。她的大衣被随手扔在沙发上,我看见她面上现出潮红。
我把热茶摆在她面前的茶几上,那时她正在沉思,一缕近似透明的蒸汽从茶杯中升腾而起,飘忽着往她刘海儿里钻。大金毛忽地起身,莫名地向着角落里吠叫两声。这声音似乎惊扰了她,她猛一抬头,前额的发梢好似利剑,将郁积的雾气斩为两段。
“谁死了?”我问。
“他!”她的眼皮正在颤抖,“诺曼,诺曼死了!”她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她说,其实他早就不是我爷们儿了,至少我认为不是,或者说,他都不是当年那个人了。他就死在我面前,小洋!四分五裂,血流如注。他的左手压在右脚上,屁股贴在脸蛋前,你说,他还能活吗?这不重要,你听我说——我跟了他九年,十八岁,他追的我,十九岁,我就跟了他,其实仔细算起来,是十一年。这你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当时就在一个班里。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要细品,而不是牛饮。杯子很烫,我的手也跟着颤抖起来。我想起诺曼,诺曼姓张,十二年前,我和他都是育才中学十四班的同学,我们俩都是艺考生。我是女人,他是男人。我学画,而诺曼学声乐。他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至今仍记得他写的一首歌中的两句:“秋天的落叶不曾落入春天的河水里,离群的夜风依然会拥抱你。”当我们毕业时,张诺曼抱着吉他把这首歌唱给我听,他说:“小洋,这是我为你写的歌。”
金毛狗躺在她的脚下,她立马很厌恶地将脚挪开,她说:诺曼死了,可是他把狗给我留下了,这条狗就是当初他非要养着的,我烦死了,小洋,我们结婚以后,我没有一天好受的日子!我知道一切都不怪他。可有时候我就突然会想他马上死掉。这回好了,他真的死了,可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是个寡妇了。诺曼从前多爱我啊,追我的时候,你知道吧,他给我买好吃的,给我写信,写酸溜溜的情书。傻乎乎的,就那么直不棱登地放在我的课桌上,也还没傻透,知道署名,我看到结尾,才知道是他写的。他的名字也起得奇怪死了,不知道他妈怎么想的,算了,不提她,想起那老太太我就来气。你知道吧,当时我打开信封,上面写着:致我最爱的人。是不是俗死了?不过那首情诗还蛮有品位,我还记得呢,我给你背一下:
致我最爱的人
张诺曼
你与月的距离是八十万米
飞鸟注定着彷徨,褐色鲜花铺满长廊
远行的人们折断翅膀
我看到神祇化为你的模样
爱人哪
刺破黑暗的辉光突降
我们就无须
躲藏!躲藏!
唯有杀死巨狮的赫拉克勒斯
他在清晨如是说
她忽然间愣住了,嘴里念叨着:后面是什么来着?什么什么夜风?后面还应该有两句的,小洋,你说对吗?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我喝了一大口茶水,“这确实不应该是结尾!”我的心乱起来。这感觉就像行走在春分到立夏的街头,飞拂的柳絮飘荡在你眼前,它们充满空间,又占据在你的心上,赶不走,擦不掉,抹不完。那只金毛真烦人,它在我眼前走来走去,口水滴落在我光亮的地板上,尾巴随着身体而左右晃动,险些扑折了花瓶中的万代兰,还有它身上的毛,在我的眼里,仿佛如瀑布一样掉落着。
“说真的,今天我的心情非常糟糕!”她的身子忽然贴近,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说话时口中喷出的温热哈气,还有强烈的香水气味。我向来不喜欢浓烈的气味,若有若无的最好。但我并不好对她表现出反感。实际上,我甚至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不体面。或许这也是我选择和她成为朋友的原因,她和我是截然相反的兩种人,她那么洒脱,她可以在任何场合之下大爆粗口,她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别人大打出手,她也可以不顾形象地在深夜街头烂醉如泥,她是我见过的最真实的女人。如今,诺曼已经死了,她成了寡妇,作为朋友,我似乎应该陪她度过艰难岁月。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她转过头紧盯着我,一如趴在角落的金毛狗。“我知道,我懂你的感受!这种事情任谁都无法释怀!”我睁大眼睛回应着她的眼神,只是让她能看起来特别真诚。我觉得我虚伪,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人就是这样的,不像其他动物,赤裸相见,毫无遮掩。她摇摇头,依旧盯着我看,嘴角微撇,身子向后一歪,半躺在沙发上。“你不懂——”她说,“你不是他的妻子。”“当然了,但我们却是很好的朋友!”我快速地说道。“亲爱的,我们也是!”她迅速地拉住我的手,我本能地抽了一下,就握紧了。
我冲她笑笑,她也冲我笑笑。
20:43
她说,诺曼还在的时候,我有时候夜里会偷偷哭,哭到眼睛都肿了,他呢,就一直认为我有失眠症。其实我哪有什么失眠症,我就是怕有一天我们的好日子忽然间就没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好像,你装万代兰的花瓶,它可真漂亮,你总担心它有一天会碎掉。小洋,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了。我知道我们俩看起来不般配,可是这么多年不也走过来了吗?年轻的时候,诺曼的家里发生了变故,他爹死了,肺结核还是肝癌,我也忘记了。不过那次守灵我也在场的,那时我们才确定关系不到三个月吧,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什么规矩。爱一个人不就是要陪在他左右吗?我陪在他身边看着他哭,陪他跪着给他爹烧纸钱,陪他看着那盆子里的火星乱窜——后来他就不上学了,他妈,那个老太太!在灵堂上吵吵嚷嚷要改嫁。他爹的遗体就躺在草席上。开始来了很多人,烧点纸就走了,最后,整个屋子里就剩我们俩,他妈妈在紧把头儿的一间屋子里,和几个男人乌烟瘴气地搓麻将。诺曼那时候对我说,他就剩一把吉他了!我就把他的头抱在胸前,像哄孩子一样,其实我也没哄过孩子!当时就是觉得很心疼,我知道他能听到我胸膛里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后来——”她突然停下来,仿佛在用力思考一些事,她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原来回忆也能如此刻意。好一会儿,她才面向我,她的眼里有一万年的冰雪。我搂住她,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不断揉搓着,我并没感觉到她浑身冰冷,却又怕见到那溺水者的目光。她的手忽然拉住我,她对我说:“小洋!其实从那个时候起,我的人生就无法回头了。对吗?”她用力捏住我的手说:“没法回头了,真是悲哀!”
我很少见到她哭泣,她似乎披着坚硬的鳞甲,从不在人前坦露脆弱。我刚刚认识她时,她并不是这样的。她梳着两个朝天辫,穿着白衬衣和深色百褶裙。她把书包轻轻地放在座位上,然后轻声地对我说,你好。我时常回忆起她那时的微笑,一缕泛黄的头发在她前额飘荡。是因为诺曼吗?金毛犬不安地打转。冲天辫女孩正迅速离我远去,消失在微光里。一张脸从黑暗里浮起,布满油光,鱼尾纹中藏着泪水,她的腮凹陷下去,显得颧骨高耸,一头弯曲杂乱的金发。她问:“有哪个女孩的初夜会是在灵堂中度过呢?”
“是啊!”我说,“也没有哪个男人会在自己父亲的尸体旁做爱。”
我抚摸着她的鬓角,一如十二年前,我怀念那缕泛黄的头发。
“我们当时就在灵堂里。”她说,“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诺曼拉着我躲在柜子下面,我一歪头,就能看见他父亲脚前的长明灯。有一股风吹过,蜡烛的火焰像跳动的鬼火,我透过死人的脚底板向上看去,能看见两根胫骨。诺曼在吻我,我害怕极了,搓麻将的声音从外面持续不断地传来。诺曼的手在我身体上不断地游走,我不敢看他,只能听见一声比一声重的喘息,于是我只好转头去看他父亲的尸体。有一排小人儿,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大概有六七个,他们手拉着手,从死人的大腿往上爬,其中一个胖得像球,需要两个人在上面拉,一个人在下面推,才能勉强爬上去。然后他们就排着队,还可能唱着歌儿。从大腿根走到小肚子,在肚脐那里绊了一跤,又绕过他父亲的乳头,走到下巴的地方才停下。诺曼一用力,我感觉自己都快被他撕裂了。一滴汗珠掉在我的眼睛里,他父亲的尸体在我眼前跳动起来,那排小人儿,拉开他父亲的嘴,一个一个排着队跳进去,死人的脸像是纸片一样苍白,他大张的嘴里堵着那个圆滚滚的小人屁股。然后我又看见了他妈妈,可我知道那不是他妈妈,那个人一张口,是一连串的狗叫声。我知道我语无伦次,小洋,我说的你可能都不信。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我只是没法形容,我脑子里的东西太真实,也太恍惚了。总之,说起来,那天的一切,都很不正常。到现在我都不确定,那天到底是不是一场梦。”她的嘴嘟起来。“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和诺曼,在他父亲尸体旁,做了第一次。更糟糕的是,我还因此怀孕了。”她说不下去了,站起来,甫又坐下。茶杯被她的衣角扑落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淋湿了她的小腿,可她仿佛浑然不觉。
我埋头为她擦拭腿上的茶水,她在轻轻啜泣。死亡和孕育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就像终结和开始,就像日升月落。
22:12
小洋,你觉得诺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诺曼——陶瓷碎片划破我的指肚儿,血从割开的皮肤间涌出,如同那个晚上,吉他弦划伤我的手指。诺曼在背后紧抱住我,胸膛滚烫火热,不停地呢喃着什么。在我的面前,张诺曼敏感多情,歌声美妙动人,弹一手好吉他。他留长发,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他经常问我,为什么不找个男人恋爱结婚,对我说那些古老的情话。但我对诺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一直如此。失落时我会联络他,而他随叫随到。他会对我讲很多事,有些事,连他妻子都不知道。诺曼曾对我说过,婚姻不如爱情更能给他安全感。说他小时候,亲眼看见父亲和别的女人上床,而这个秘密,他的母亲一直不知道。他抱怨已经死去的父亲,为了外面的女人,对家人大打出手,这个脑袋长在生殖器里的男人!诺曼曾经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她把纸巾递到我的面前,自顾自地说道:“我知道你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小洋。诺曼他是个很复杂的男人,这一点我早有体会。”
她说,有时候你用十年的时间都没法看透一個人。我怀孕以后,就没法再去上学了,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孩,还能去哪里呢。我爹,那个二十五岁就从部队拖着一条瘸腿出来的老头儿,把我倒吊在院子里,用皮带抽了半小时。我用手死命地护住肚子,我活下来了,他也活下来了。我的后背没有一块好皮,在家里躺了半个月,逃出去,找到诺曼,我对他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我们结婚吧。诺曼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过几年再生?听听,这是什么屁话!可我当时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我只会傻傻地点头。我们搬进了一个郊外的小旅馆里,那里又脏又乱,挤满了赌徒流浪汉和吸毒者。那种地方,连妓女都不会住。诺曼有时候付不起房租,那个嘴里常年一股韭菜味的女老板就会在半夜的时候用脚踹我们的房门,骂那些不堪入耳的脏话。那时候诺曼的钱都是向朋友们借来的,我见过他们其中的一些人,都是一些玩音乐的,凑在一起,组成个乐队。就整夜整夜地混在夜场,喝酒,吃药片,玩摇滚。他们管这叫艺术。当时诺曼说我不懂音乐,因为我是个粗人,粗人不配谈艺术。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懂,他的那种他妈的狗屁艺术,就是把我,一个怀了他孩子的女人独自扔在破旅馆里,被人骂,被人欺负,被那些混蛋揩油?可当时我却不那么想,我整夜整夜不睡觉,去研究他的艺术,多么可笑。爱一个人真的会丧失理智,即使他当时做出那么过分的事。
“这些我从没对别人提起过。”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缓步走到阳台上,双手环抱而立。那只金毛狗立马摇着尾巴迎上去,她看准时机,一脚跺在狗爪上,那只狗呜呜咽咽地倒下去。她背对着我说:“我的孩子就是那时候没的,诺曼有一次半夜回到家里,我知道他嗑药了,他的整个状态都不对,满头大汗,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时候我都已经显怀了,他突然把我推倒了,用拳头打我的脸,用脚踢我的肚子。他声声地嚎叫,就好像野兽一样。我的孩子就这样没了,躲过了外公,死在父亲手里。小洋——你不知道——”她高高耸起的肩膀剧烈抽搐起来,沉重的哭泣声从胸腔挤出来:“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疼,流了好多血。可我又不疼,疼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他一疼,我就更疼——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声了——我有时候,都能感觉出他在我肚子里又踢又踹——可是他就这样——”
她开始哭出声音,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两只手紧紧抱住她颤抖的身体,阳台外是夜空里星星点点的灯火,我们也是那灯火的一部分。我把下巴搭在她的肩上,嗅着从她的身体深处飘出来的气味,那不再是香水,而是她的体味儿,我的身体里有一把火。我在她耳边呼出热气,看着她不断翕动的眼睫毛,我轻轻伏在她耳边对她说:“都过去了,亲爱的,过去了。”
她停止了抽泣,我注意到她似乎有些不适,她的头轻轻左右摇摆,身体从我的怀抱里抽出,她用手擦擦脸,面向我,她说:“你知道我当年有多么卑微吗?我原谅了诺曼,甚至我还曾——曾在深夜跪在地上扯着他的裤腿。我怕他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我知道他的心不在我这儿,他总说,我们的思想不在一个频道,我理解不了他的灵魂。可是我又没见过他的灵魂,让我怎么去理解呢?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魂,我那瘸腿的爹有没有灵魂,还有我那胎死腹中的孩子——他总是在深夜出门,我甚至能感觉到外面那个女人,仿佛她就站在我面前。我知道他们是同一种人。有时候我会偷偷去闻诺曼身上的气味儿,他身上会残留那个女人的气味儿,那气味儿就像——”
“小洋!”她突然间叫了我一声。我恍惚着点点头,正好与她四目相对。她的眼里红红的,但精光十足。我强迫自己与她对视,她反而躲避掉我的目光,绕过我的身体,重新坐在了沙发上,她在背后对我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是不是搞艺术的身上都是这种味道?”
我紧咬着嘴唇低下头,那一刻,我像是一只开膛破肚在泥土中翻滚的斗鸡,这样一点儿也不体面。
23:05
“这不重要!”她摇摇头说,“我还有很长的故事要讲。”
她说,“后来诺曼真的抛下我走了,他走得义无反顾,他说他要去追求他的梦想,他要去挣大钱,让我等着他。等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会回来娶我。于是我真的就在原地等着他,我当时也没处可去,现在想想,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姑娘,未婚先孕,还被男朋友打到流产,她还能去哪里呢?回家去?我那个当过兵的爹会打死我的。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回家,诺曼经常告诉我,家人是靠不住的,而我当时唯一的依靠似乎就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男人,就是他一个月两条超长的短信息。起初我在一个餐馆打小时工,后来我跟着一个女老板批发衣服,再然后,我去做推销员、保洁、商场的导购员——我做过很多份职业。这期间,我的身边也出现过许多男人,他们形形色色,匆匆忙忙,跌跌撞撞。但我知道他们都不是我的男人,我那时候想,要是诺曼一年不回来,我就等他一年,要是十年不回来,我就等他十年。我那时候真的是那么想的,我不知道诺曼在外面是如何风流快活,以至于染上脏病,但我就是为他守身如玉。就是这样,两年以后,我终于等来了他入狱的消息。”她的话语波澜不惊。
“我在监狱见到了他!”她说,“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告诉我,诺曼那时候黑瘦,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我又问他判了几年,他还是不肯说话,一直低着头,我就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他的眼眶乌黑,额头和脸上有伤,在监狱里一定过得艰难,那么骄傲的一个人,连抬头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
“时间总会磨平一切。”我微笑着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她把手抽走,像是端起茶杯喝水那么自然,“是啊,我要讲的就是关于时间的故事。诺曼当时不肯说话,我就大声对他说,张诺曼,我会等着你的,等你出狱了,我们就结婚。诺曼忽然抬起头,他乌黑的眼眶里藏着一双遍布血丝的眼球,他瞪着我,开始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他说我是个贱货,是个婊子,在他走的这段时间里一定是靠卖肉维持生计的。他说,他就是死也不会娶一个破烂货,千人骑万人睡的烂裤裆的。他让我死了这份心,外面有比我更漂亮更有钱的女人在等他。诺曼骂得慷慨激昂,而我只能委屈巴巴地哭,看着他在我面前张牙舞爪。我是哭着走出监狱大门的,不管诺曼怎么骂我,我都无所谓。可是他竟然说他在外面有了女人,比我漂亮也比我有钱,那么之前每个月他对我说过的话、做过的承诺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段时间里,我心乱如麻,可我憋着一股劲儿,有一口气,也要吐给他张诺曼看,我要让他知道,我比任何一个女人都要强。他越是不要我,我越是要紧贴上去,他是我的男人,他是我死去孩子的父亲。奇怪吧,想想也不奇怪,我和诺曼——我们都贪婪而愚蠢,这是我们的原罪。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去监狱看望他,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诅咒谩骂,后来,他开始给我讲他和外面那些女人,她们有多性感。他掰着手指头给我算,和多少个女人睡过觉。我就只会哭,他骂我的时候哭,他讲述的时候哭,他算数的时候也哭。我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时候我想,也许只能等到他出狱,才会有一个结果。”
茶几上的手机响起铃声,我看了一眼,迅速摁灭了它。这声音惊扰了角落里酣睡的金毛犬,它的两只耳朵直立起来,头颅茫然地左右晃动。“我打扰到你了吗?小洋。”她问道。我握住她的手,她这次没有抽开。“只是每晚提示睡觉的一个闹钟。没什么!你在这里待到多晚都行。”我笑着对她解释着。她忽然咯咯咯地大笑起来:“你真搞笑,闹钟不都是早起才设置的吗?”我也随着她咯咯咯地笑起来。
她忽然伸手撩起我的头发,端详着。就像是从前我经常对那个冲天辫的女孩做的事情一样。她的眉头皱下去,轻声问我:“你还是一直在失眠吗?”
“是啊,有时候会。”
她双手扶住我的脸颊,我们额头相抵,我们的眼睫毛似乎都缠绕在一起,我看着她瞳孔里的深渊,她离我近在咫尺,又似乎是相隔整片银河,这感觉让我呼吸急促。她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又拍拍我的颈背,像是说悄悄话一样:“你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咱们都是。”我用力点点头,她笑颜如花。
她说,“像是每个童话故事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的故事也接近尾声了。小洋,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定会认为张诺曼是一个坏透顶的男人了。可是啊,当他从监狱走出来,他找到了我,他说他得到了一笔钱,我们终于可以结婚,终于可以过好日子了,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我们的婚礼办得比较潦草,这该算是一个遗憾吧。婚后的诺曼像是变了一个人,或许他早就改变了,毕竟,我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了。他再也不去鬼混,不去喝酒,也再不碰那把吉他了。他找了个踏实工作赚钱养家,对我百依百顺,清晨做好早餐端到我面前,晚上给我洗脚、揉腿。有时候我骂他,甚至打他,他也不气不恼,像是个没脾气的泥娃娃。从前我受过的苦难,似乎正在连本带利地偿还我。就这样,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小洋,不是的。我,我不知道怎么的,没有了安全感,没有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当初他出去耍,再后来他坐牢,我前后等了他五年,可这五年我心里是踏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结婚以后,一切都变了,他变得不像他,我也变得不像我了。再后来,我就出轨了,不同的男人,不止一次。我,我并没有报复他的意思,我发誓,我真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个意思。我鬼迷了心窍,一定是那夜他死鬼父亲身边的怨灵。每一次之后,我都能梦见那个堵在他父亲嘴里的肥大屁股。诺曼应该是知道这种事情的,他不是个笨人,甚至有一次,他险些抓住了我,当时我在宾馆里,浑身光溜溜的,那男人胡乱套上裤子,脚踩在空调外机上,藏在窗子下面。诺曼推门走进来,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說,晚饭好了。那一次,我甚至想要直接从窗户跳出去,老天见证,我都能看到那个野男人扒着窗框的两只手。我想好好地和诺曼生活,我用贡香烫自己的大腿,我无数次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我真的成了诺曼口中的‘婊子’‘贱货’和‘烂裤裆’了。我也许是一面凸镜,我抵不住他的恶,也盛不住他的好儿。可我们就是谁也离不开谁,像是藤缠着树。树根铲断了藤条,藤蔓吸干了树干。我们互相折磨,可能这也是一种爱吧。”
她低着头,久久地沉默着。一滴眼泪落下来,随后是一连串泪珠,没有哽咽,没有抽搐。只有它们噼里啪啦地掉在瓷砖地板上,粉身碎骨。
“诺曼,真的死了吗?”我轻声问。她背对着我,打开房门,“也许吧!他是个该死的人。也是无辜者。”大金毛追随着主人远去的脚步声,身子一蹿,尾巴顺势扫过我的花瓶,万代兰随着碎片散落一地。我蹲在沙发前,呆呆地观望着,我忽然发觉我的心中并无不舍。我的爱就像是晚春清晨的霜,风一吹,就化了。
00:00
春天来了。
【责任编辑】安 勇
作者简介:
王图,原名王浩,1994年出生,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短篇小说处女作《陈风在1931》发表于《延河》2012年第7期。三次获得盛京全国网络文学大赛小说奖。中篇小说《火车经过》发表于《黄河文学》2017年第6期,《无用的脚趾》发表于《少年文艺》2018年第4期,短篇小说《风从低处来》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9期,中篇小说《狂风席卷一切》发表于《清明》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