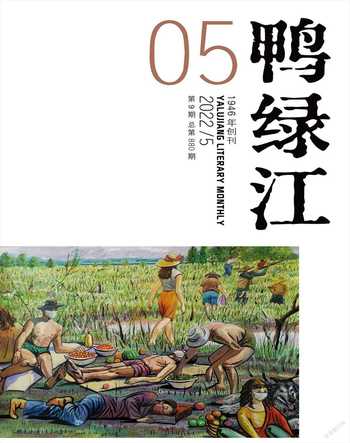《讲话》引导下东北文学的勃兴
1942年,解放区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的根本鹄的是要解决“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以及如何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社,1950年版,第10页)。《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文学创作的最初“原料”,才能将文学创作与群众生活紧密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社,1950年版,第21页)。在《讲话》的引导与感召下,解放区的诸多知识分子摒弃以往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有习气与创作风格,深入群众去改造与学习。其中,周立波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周立波不仅全程参与了《讲话》的酝酿、讨论和最终发表的全过程,而且还从自身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出发,宣扬与践行《讲话》精神。特别是1948年,周立波身体力行深入东北,参加土改运动,主编《文学战线》(后更名为《鸭绿江》),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值得我们珍视与深入探讨。尤其是今年恰逢《讲话》发表80周年与《鸭绿江》创刊7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以周立波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为探讨中心,勾连起其与《讲话》和东北文学的脉络谱系与深厚情缘,无疑具有别样的价值与意义。
一、《讲话》引导与深入东北
《讲话》发表的直接背景是当时迫切的政治形势。1938年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之而来的是抗战初期中国文坛那种高昂的革命情绪不复存在、文艺界开始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这股反思思潮相应,1940年前后的延安解放区,也在迫切地思考文艺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要不要和工农兵的生活相结合、文艺要不要暴露黑暗、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当时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一时之间莫衷一是。毛泽东作为解放区的领导人,从延安面临的种种文艺问题出发,一方面开展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以座谈会的形式征求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期酝酿文艺政策的深度变革。通过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检验,终于酿就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并最终形成了《讲话》文稿。而在《讲话》的酝酿过程中,周立波全程参与,并受到《讲话》的深刻洗礼与教育。
周立波于1939年接受党的委派从广西桂林来到延安。到达延安的周立波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解放区的工作当中。他被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系教员,并兼任编译处处长。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立波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又被增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周立波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正是延安整风和《讲话》酝酿期间,加之周立波的多重身份,因此周立波自然成为毛泽东主要谈话的对象之一。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立波和何其芳、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等“鲁艺”的几位党员教师应邀,参加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召开的座谈会议,会后,他们又同毛主席同进午餐。这次会议留给了周立波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毛泽东轻松幽默的谈吐风格和亲切和蔼的待人态度,令其终生难忘。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与修订的三次会议,周立波也全程参与,完整见证了《讲话》的生成过程。《讲话》发表以后,周立波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贊誉:
这个划时代的文献,用马列主义的夺目的光辉,照耀了我们的文学,解决了我们文学上的从来没有这样正确地、明确地和彻底地解决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文学事业的方向确定了,使得工农兵的形象,大量地涌进了作品,而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遭受了有力的批判。(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文艺报》,1952年6月25日)
与此同时,周立波也数次谈到《讲话》对其自身的深刻影响。他曾坦言,在《讲话》发表以前,也曾去过前方,并非常敬爱战斗在前方的战士,但也仅仅“止于敬爱”,对他们的生活、心理和感情并不熟悉(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也曾到过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待了50天,就匆匆地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文艺报》,1952年6月25日)。
为了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周立波渴望深入到人民群众和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于是,他毅然参加了王震和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体验军旅生活。在这段极其艰苦而又充满惊险的旅程中,周立波冒着严寒酷暑和战火硝烟,与同行的战士们跋山涉水,徒步走过了一万五千余里的路程,跨越了七个省的战场,经历了严峻的生命考验与历练。后来,周立波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写进了他的作品《南下记》和《万里征尘》中,为这段生活经历的点点滴滴留下了珍贵的见证与纪念。
除了南下的经历,最令周立波难忘的是他深入东北的岁月。1946年,解放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国共之间签订的《停战协定》,并调动部队,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在危机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相关指示精神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果断发动1200多名干部深入东北农村,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增强东北根据地的实力,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当时在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担任副社长的周立波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请求参加这场关乎东北革命斗争成败的广大群众运动。于是,在党委批准后,周立波追随李德仲的部队深入东北,从热河来到了松江省。
二、东北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
周立波在东北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是从事编辑工作,他曾花费大量精力用于编辑《松江农民报》和《文学战线》月刊。《松江农民报》是由松江省委主办的一份小报,创刊于1947年5月上旬,于1948年4月停刊,其主要的读者是广大的农民和乡村干部。在报纸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周立波带领着四个文学青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他们在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东北农民所喜好的快板、大鼓、小调、民谣、儿歌等多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同时还刊载一些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相关文件,以及松江省各地开展土地改革的相关情况,以此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群众更为深入地了解农民斗争地主恶霸的先进事迹,激发广大农民的反抗与斗争情绪。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周立波不仅担任主编工作,还身体力行,以松江省委宣传部的名义主持编写了《农民文化课本》,课本包括《东方红》《共产党》《解放军》《介绍信》《节令歌》等15课内容,向农民系统地介绍了政治、军事、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知识。课本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编写,浅显易懂,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与好评,同时也很好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落到了实处,被广大农民理解与接受。
《文学战线》是继《松江农民》停刊后,周立波编辑的另一份重要的期刊。《文学战线》由东北文协主办,于1948年7月创刊,是继《东北文艺》之后东北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文学阵地。《文学战线》主要以刊载小说、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为主,同时也经常性地刊登文艺评论和曲艺作品。在当时,《文学战线》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许多来到东北的知名作家都在期刊上发表过作品。比如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部分章节、舒群的《无敌三勇士》、刘白羽的《战火纷飞》、马加的《江三村十日》等,都曾在该刊发表。另外,茅盾、白朗、草明、严文井、舒群、戈宝权、古元等作家、翻译家和画家,也曾大力支持《文学战线》,并发表了诸多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表不仅壮大了《文学战线》的阵地,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东北文学的勃兴与繁荣。
在这庞大的队伍当中,周立波自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1948年上旬,周立波被调至东北文协工作,担任《文学战线》主编,于是与《文学战线》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周立波担任主编期间,文戎担任其助手,两人协同合作,到1948年年底前共完成了6期的编纂工作,并将其合为第一卷出版。周立波在担任主编期间,不仅兢兢业业地全面负责刊物编辑工作,而且亲自撰写文章在期刊上发表。比如在鲁迅先生逝世12周年之际,周立波就撰写了《纪念鲁迅先生》一文,发表于该刊的第一卷第四期。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周立波于该年12月上旬随东北文协迁至沈阳。1949年3月,《文学战线》在沈阳出版了第二卷第一期,但此时,周立波已到鲁艺任文学教研室主任,不再担任《文学战线》的主编。尽管如此,周立波依然担任该刊的编委,并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学战线》的编辑工作。比如,周立波曾将自己翻译的最为重要的一篇译作《梭罗柯夫<肖洛霍夫>论》发表于该刊的第二卷第二期。
周立波在东北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的同时,还抽出时间用于开展土改运动。1946年冬天,周立波到达松江省珠河县元宝镇开展调研工作。到元宝镇不久,按照中共珠河县委的工作部署,周立波担任了该区的区委委员,与林蓝同志共同承担区委的领导工作。在元宝区生活的岁月里,周立波一心深入群众,与贫苦的劳动大众同吃苦、共患难,每天和大家一起吃三顿的苞米 子和咸菜。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经常是零下三四十度的恶劣天气,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周立波在这样的天气下很难适应。但周立波依然坚持和大家一样,“用一件军用黄大衣严严地裹着身子,戴着一顶耷拉着耳朵的风雪帽,踏着一双靰鞡鞋,照样坚持走村串户”(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周立波与农民聊家常、开唠嗑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深得人心。与此同时,周立波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也了解了许多东北的风俗民情、方言土语,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7年5月,周立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元宝镇,根据中共松江省委的指示,他被调至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周立波一方面从事《松江农民报》的编辑工作,一方面深切地回味着在元宝镇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土改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而又惊心动魄的场景,以及那些朴实的、亲切的农民的身影,使周立波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此时,他又学习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深地为全国农民踊跃地开展土改运动、坚决反抗强权的精神所感动与震撼。于是,周立波毅然决定要创作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从1947年中下旬开始,一直到1948年年底,周立波终于完成了《暴风骤雨》的写作。《暴风骤雨》以松花江畔的元茂屯村为背景,非常真实地再现了1946—1948年东北地区土改运动的全过程。《暴风骤雨》发表后受到了东北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被人们作为反映土改运动的教科书加以学习。《暴风骤雨》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原因大体有三:一是采用传统的文学技法,以讲故事的方式结构全文。整部小说以共产党领导群众反抗地主强权为主线,生动活泼地演绎了广大底层人民如何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通過发生在元茂屯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以韩老六为代表的元茂屯“三大粮户”的罪恶发家史和覆灭史,以及赵玉林、郭全海为代表的贫苦农民的血泪史和翻身史交织在一起,跃然纸上(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成功地诠释了在中国地主势力终将灭亡、人民群众势必获得自由当家做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二是作品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比如出身贫农且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农民英雄赵玉林和郭全海,新旧思想交织、风趣幽默的车老板子老孙头,机智勇敢、果断干练的土改运动工作队的萧队长,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农村妇女赵大嫂、刘桂兰、白大嫂子,以及凶狠毒辣、无恶不作、奸猾狡诈的韩老六、杜善人,等等。这些人物形象真正体现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尤其是作品中出现的农村的富有新思想的文学新人形象,在当时的文坛是非常富有新意的。三是小说中大量生动活泼的东北方言的运用。在作品中出现了“不大离儿”“黑价白日”“蝎虎”“老鼻子”等大量的东北特有的方言,这些方言土语的运用不仅使整部作品笼罩着一层东北地域特有的色调,而且使东北的民众感到异常亲切,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当时东北民众为何那么喜欢这部作品了。
三、《暴风骤雨》:当下的经典意义
1949年,全国获得了解放,周立波作为东北代表团中的重要一员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这次文代会以后,周立波被调到文化部编审处工作,从此离开了生活近三年的东北,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虽然周立波在东北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东北的经历却见证了周立波对《讲话》精神的实践过程,也成为其长篇代表小说《暴风骤雨》诞生的重要土壤。
回首那段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不觉间已经跨越了近80年的时间征程。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忘怀周立波深入东北,践行《讲话》精神的那段不平常的历史,无法忘怀他根据自身的东北生活经历创作出的经典之作《暴风骤雨》,因为它们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一)深入在场、切身体验。《暴风骤雨》之所以出版后获得东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认可与欢迎,并且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源于真实的生活,源于周立波对东北农村生活的深入在场和切身体验。他曾坦言:
1964年冬天,我参加了东北的土改,工作的地方是松江省尚志县的元宝镇。松江是现在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元宝镇就是《暴风骤雨》里的元茂屯。这是一个靠山的穷屯,有四百户人家,绝大多数是农户,也有小手工业者和小学教员。……初到东北,对于那里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是不熟悉的。为了搞好工作,我们必须和农民打成一片。……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东北的土改工作队当时普遍采取了探贫访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我们挑选那些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对他们进行家访,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交上朋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谈心和耐心深入的宣传,我们不但教育和发动了他们,而且更细致地了解了他们。……在运动中,通过种种方式,我在半年里了解了平常几年都不能了解透彻的情况,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东北农民生动的语汇。(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红旗》,1978年第5期)
周立波将元宝镇的这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有机融入了《暴风骤雨》之中,但在书稿修改过程中,他又深感材料的不充足,于是他又到周家岗、五常、拉林、苇河等村屯进行采访调研,最终才展示出《暴风骤雨》的全貌。
可以说,周立波的写作经历,对我们当下的作家来说是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的。当下的许多作家身居城市,大部分作品是城市生活的演绎,作品的构思与生成源于“虚构的热情”,大多数作品都是空泛的形式演绎,难有让人为之振奋的内容,也很难感觉到作者灵魂的重载。同时,也许正是因为大多数作家身居城市的原因,所以如今都市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而乡土题材的作品却越来越少。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底层的声音变得日渐微弱,乡土叙事也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这当然与农民的文化水平偏低、难以书写自己的性靈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缺乏能够真正地深入民众生活、与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作家。所以,要想创作出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品,可能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像周立波一样,深入民众生活现场,与民众打成一片,否则可能一切都是空谈。
(二)紧贴时代、关注民生。后现代主义批评家阿多诺认为,“一个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就在于其能否表达时代的真理内容”(曹征路:《要科学,还是要玄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确实,好的作品应该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应该为了“反抗遗忘”而存在,它应该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而关注时代最终的落脚点是关注民生疾苦,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处境、精神风貌和人性特征(参见侯敏、王卫平:《情感与审美: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与书写》,《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侯敏:《不断争论中的<子夜>——兼及经典意义之再思考》,《郭沫若学刊》,2021年第1期)。
在这方面,《暴风骤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暴风骤雨》紧贴时代,完整演绎了《讲话》引导下20世纪40年代东北土改运动的具体样貌,鲜明地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地主压迫下的凄惨生活处境,生动地描绘出底层人民反抗地主强权势力的崭新的精神风貌。整部作品充满作者对时代的使命感与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底层民众深深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这恰是我们当下的作家所应该汲取与借鉴的珍贵的文学精神与文学品格。
(三)注重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一直有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说法,就是说文艺作品的内容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但又应该用艺术的审美的眼光去打量、去修饰,这样才能成为艺术的、审美的文本,这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准则。今天的“非虚构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并非不允许虚构,而是应该注重生活实际的同时,也要对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否则它就成为新闻,成为报告文学,从而失去文学与艺术的审美韵味。在这方面,《暴风骤雨》的艺术化设计同样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人物塑造方面,《暴风骤雨》中的农会主任赵玉林的原型是作者在周家岗遇到的农民英雄温凤山。他是在土改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贫农积极分子,因工作积极,被选为县里的头等模范,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次抓捕逃亡地主的过程中中弹身亡。周立波将这个农民英雄形象形塑为作品中的赵玉林。赵玉林是一个从山东逃荒到关外的穷棒子,因为缺吃少穿,被人称为“赵光腚”。他因迟交了韩老六家的租粮,便被罚跪碗碴子,后来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蹲了三年大牢,导致媳妇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外出讨饭,一个七岁的女儿活活饿死。但这些惨痛的人生经历并没有使赵玉林消沉和屈服,当土改工作队来到元茂屯时,他积极拥护工作队,勇斗地主恶霸,后来担任了元茂屯的农会主任,最终在追捕地主的斗争中光荣牺牲。显然,作品中的赵玉林经过作者的艺术化处理,要比原型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和有血有肉,尤其是“赵光腚”这一称号,一方面使作品充满了趣味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了贫农生活的艰难。再如在情节设计方面,周立波将周家岗“七斗王把头”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集中概括,演化成《暴风骤雨》中“三斗韩老六”的故事,使整部作品的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另外,《暴风骤雨》中对东北方言的运用,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情。本来对一个南方作家而言,运用北方的方言进行创作势必有很大的难度,但周立波却跨越了重重障碍,将东北方言有机融入作品,充分彰显出作者的创作天赋和艺术水准。
综上,周立波是《讲话》从最初酝酿到最终发表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实践《讲话》精神的优秀典型。他在《讲话》引导下深入东北,在东北从事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北文学的勃兴与繁荣,尤其是取材和创作于东北这片沃土的《暴风骤雨》,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周立波为《讲话》的传播,为东北的文学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讲话》与东北这片热土也为周立波的文学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并最终奠定了其在文坛上的地位。或许正是因此,周立波对《讲话》与东北始终念念不忘,直到晚年,他还对亲友满怀深情地表示:要是当年不离开东北就好了!
【本栏目责任编辑】陈昌平
作者简介:
侯敏,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现已出版著作《文学艺术之梦》《五四新文学与百年新文化运动》,参编中宣部“马工程”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多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六项,获辽宁省政府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