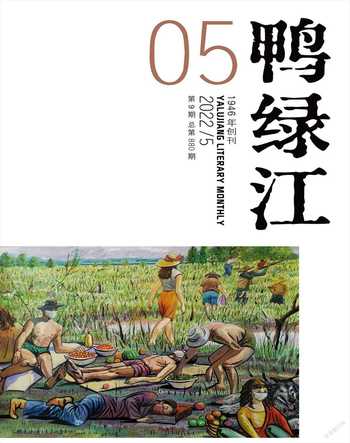“对不变的蓝天白云做深呼吸”
沙克自称“老资沙克”已经多年,究竟他“老资”的含义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想,大概是为了区别于所谓的小资。因为小资一般会显得肤浅些,有小情小调,却不会深刻,而这是沙克看不上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不论老资还是小资,显然都带了文化或美学上的追求,有自来的“资”。这自然不是“资产阶级”的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资历的资、精神资质的资、写作资本的资、可资用途的资……且什么东西一旦“老”,皮就厚些,也不怕别人嘲讽,与其被人视为“资”,不如干脆自诩,且直接升格为“老资”。
以上纯属我的瞎想。上海人有个说法,叫作“老克腊”,大意指老上海的一种有格调的男士,不一定有特别不寻常的身份,但一定会有特别不一般的格调。这个词,要么是来自英文“colour”,要么是“classic”,是颜色,或者层级之意,都可以引申为情调或者格调的意思。不知为何,我时常把沙克想象为一个类似于“老克腊”的身份,一个有不同寻常品位的、有着追求别致生活方式的人——他的履历,与上海那座老资扎堆的城市或许有些连带关系,或者毫无关系,却应有时空上的微妙感应。
说了这么多,当然是为了谈沙克的诗,弄不准他的身份,便不会准确解读他的作品。反过来,如果读不懂他的诗,也大概不会明白他为什么叫老资沙克。
沙克的这组诗,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用比较轻松和轻便的口语表达其沉浸和深入的文化思考,或者生命态度。他刻意让自己的语言脱离华美的不及物,而落地于日常性与细节化的宣叙,连描述都很少用,更遑论象征与隐喻。这大概是他从年轻时代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卷入者身份那里继承来的,是一种相当定型的文化态度,或者是由诗歌观决定的。怎么写和写什么,以什么样的风格调性来写,他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但是沙克有非常自觉的精神与文化方面的“人设”,他不会允许自己的诗歌真的仅仅成为日常性的叙述,必然在其中有各种深度设置。因为他是老资沙克,所以必然有其别致的、沉浸和内在的东西在。
这组非洲主题的诗是怎么来的,我拿不准。从朋友的角度,我好像并没有听说沙克有在非洲工作或较长期的旅居。从作品看,比较大的可能是他有一次或多次的旅行史,至少到了北非和东非的许多地方,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以及东非高原的肯尼亚等,到了那里的城市、草原、丛林和沙漠,或许是一次纯粹的“纸上旅行”也未可知。但从诗中看,绝对是充满了细节意味与现场感的。
這个当然很重要。我在想,没有现场经历,没有身临其境,很多感受是不会产生的,产生了也不会真正感人,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浩大的旅行,是多个情境下悉心的观察与思考,那些自然、历史、现实的城市风情,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很难写出如此丰富的感受。
而且就地理差异而言,北非的埃及和摩洛哥,与欧洲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非常深。而东非高原的肯尼亚,则是非洲的高原与丛林,与前者差异巨大。
都不管了,我们姑且设想作者是用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漫游了这两大区域,而且还由此以历史与文明的触角,思考了更多更远的问题——比如他还写到了纳尔逊·曼德拉,那位为南非独立而斗争了一生的黑人总统。
让人吃惊的是,他一会儿是在马赛马拉草原,一会儿就来到了摇曳着地中海风情的卡萨布兰卡,一会儿还站在河马和鳄鱼的前面,一会儿就来到了四千年前的卢克索。这一切都被他整合为一种黑色的或者褐色的文明,它们有着自古至今的连贯性和某种总体意味,是一块有着莽野的自然蛮力,又有着久远的古老文明的巨大陆地,至少我在读这些诗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种整体感。
依照我个人的趣味,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组诗中的《卡萨布兰卡》。如同电影史上的那部名片一样,这首诗把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的诸般侧面生动地再现。“忽闪忽闪/三种美人鱼摆动尾花/名字好听/白里透红的卡萨布兰卡//王宫,绿,清真寺,绿/五官偏蓝的尼格罗—欧罗巴/融进大西洋的风和景/头巾随时散落/绽开曲身长腿的三个她”。将城市的主调与标志性的建筑,以印象派绘画的方式斑驳交错地点染出来,并与那部著名的电影的形象进行了暗自的接通与对应。
里克咖啡馆,烤鱼香
游在窗外的白鱼,乳沟深
混血鱼的臀,翘向一月的迷情
英格丽·褒曼还在扮演一只躲闪的猫
怀旧的敏感两世通达
这种蒙太奇式的印象叠加,如同一幅地中海风格的风情画,让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
当然,最壮观和最令人震撼的,还要数开篇的一首《马赛马拉草原》。这块非洲大陆最生气勃勃的土地绽放着地球上最动人的生命史诗。沙克以叠加刻写的笔法,浓墨重彩地描画出了这一史诗场景,写出了“比胸怀大十倍比视野大百倍的马赛马拉”。仿佛一只鹰或带着广角镜的摄像机飞过草原上空,他注视着这生命世界中的弱肉强食,注视着丛林中固有的生存法则,它的血腥和残酷、壮美与永动。他用刻意冷静的目光与对生命世界中生存斗争的沉思,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悖谬与感动的境地:“辽阔吗,壮丽,野蛮吗,静谧/比胸怀大十倍比视野大百倍的马赛马拉/对一只狮子扑倒角马无动于衷/对一群鬣狗撕碎羚羊……/一只猎豹咬断斑马的脖子无动于衷”。
这就是生命世界的真相,生命史诗中永恒的伦理与悖谬。“眼神空茫的马赛马拉站在原地/遍体草茬,碎骨零落/对不变的蓝天白云做深呼吸。”
作为《马赛马拉草原》姊妹篇的,还有《蓝天邈远如飞》《奈瓦莎湖畔之夜》《原野上的伞》《夜雨后的清晨》《这一角人类》诸篇,它们分别从不同视角续写这个生命世界的不同侧面。有安详的静谧,有飞翔的舒展,有星夜的柔情想象,也有烈日下的风景变幻。它们都可以视为沙克对一首生命史诗的反复展开与变奏,正如《夜雨后的清晨》这样写出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背后一个个温馨美好的静谧时辰:
织巢鸟起得早些
叼着草叶细麻飞到合欢树的枝杈间
就着旭日的柔顺光线
摇晃脑袋,编织可旧可新的一天
危机四伏与万象丛生中,生命的曙光照常升起。实在是太美了,这才是史诗的主题,虽然没有史诗的規模与长度,却有史诗的灵魂与意义。
除了自然部分之外,便是历史文化的寻访了,《卡萨布兰卡》是其中之一,而《踩点内罗毕》《纳尔逊·曼德拉》《入埃及》《碎瓷公主》都属于这一部分。这是时间之维、历史之纵深的部分,前者是空间与自然的世界,这是对文明的理解与造访。平心而论,我对这一部分没有什么资格评论,因为在我个人的履历中,非洲这块大陆,我只到过埃及,且只限于尼罗河终点处的开罗和亚历山大,对于上埃及的卢克索那些古文明之地还没有去过,所以很难做出有意义的判断。但是在笔者的写作履历中,也写过一首《曼德拉》,是纪念他去世的一首,与沙克诗的立意大概也很像,是对于他半生坐牢,为非洲的独立与尊严奋斗的一生的追祭。沙克所写,可谓深得我心。
埃及是写不尽的,沙克写出了他的埃及观感,仿佛是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他一路感叹缅想,把埃及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这感受与我去埃及时的观感很像,这古老的国家,经过了四次文明的断裂,依次被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和统治,剩下来的,便只有金字塔、木乃伊和伟大的古代传说了。这谜一样的文明,甚至难以为今人做出解释,沙克写出了这复杂的感受。
总体上,沙克的这组诗是当代诗歌中比较罕见的文本,书写非洲的自然与历史文明,对中国的诗人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沙克算是一个大胆的试水者。需要交代的是,沙克近期出版了一部书写域外地理历史与人文风情的诗集《忆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在我读这组非洲主题诗时还没见到它,或许可以猜测它作为关联深厚的人类文明的认知背景,能够为非洲组诗的必然生成而非偶然出现做坚实的托底。作为朋友,我对沙克兄有着深远的阅读期待。
【本栏目责任编辑】林 雪
作者简介:
张清华,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学术著作15部,诗集和散文集7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批评家奖、省部社科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北师大教学名师奖等。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