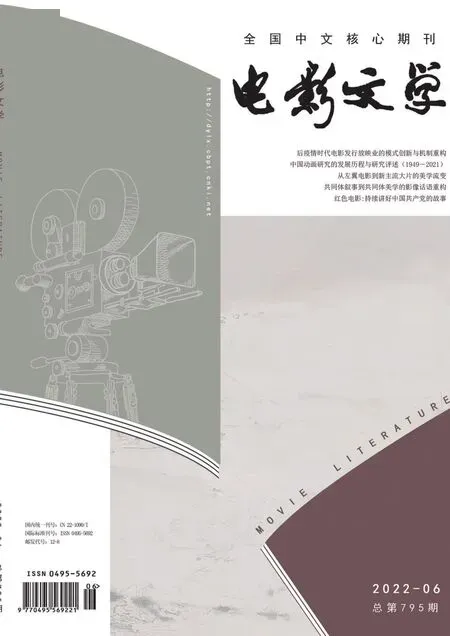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风格解析
王 璐 高字民
(1.西安培华学院传媒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5;2.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如同小众电影之名,其从未缺失关注,却很少被大众提起,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时至今日,小众电影不存在明确且完整的界说。目前,小众电影更多地被归为文艺电影之类,指那些创作手段相对特殊,比如采用隐喻、象征等类文学修辞方法,剪辑手段和运镜方式都较独特的一类电影。小众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刻意迎合大众口味,具有思考上的奇特性和深远性等特点。青春片虽是电影片种之一,但是其并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电影类型,其主要围绕青少年于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喜怒哀乐乃至各种问题,比如生理和心理上的蜕变、精神上的发展、关于成年的困惑等展开。例如青春期焦虑、恋爱、叛逆和父母冲突等,体现青春阶段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对情感的认知等。国产青春片中,青年初入职场所遇到的竞争、友情甚至背叛等问题,也是热门的拍摄题材。青春片的创作目的是吸引青年男女观众观看。犹同小众电影,小众青春片同样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这种类型的青春片具有广义上的小众电影特点,与其他类型小众电影最大的不同是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试验性,且小众青春片的导演个人色彩往往十分浓重,导演个人对青春和成长的理解对此类电影影响较大。因此,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风格实质上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学术问题和社会现象;通过分析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特点,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观察青春亚文化在小众导演电影中的表达可以深刻解析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风格。
一、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特点
在庞大的电影市场中,青春片属于主流边缘类电影,其中小众青春片更显得与高度商业运作下的电影市场格格不入,也时常不被主流群体所理解。这就使得这个本不大众的电影类型中的小众创作者有着群体特有的个性鲜明的特点,比如灰色青春与纪实感、选材立异以及强烈的时代和导演个人印记。
(一)灰色青春与纪实感
青春之所以为青春,就是因为其自带“反叛”和“迷茫”属性,青春片亦是如此。古今中外的小众青春片导演几乎无一例外地格外青睐聚焦令人耸动的人和事,似乎一个人的青春不经历伤痛和悲情就是不完整的青春。他们通常固执地认为青春是灰色的,是充满悲情色彩的。例如,导演娄烨镜头下的青年男女之情总是充满晦涩残酷,他们身上的青春总是带有苦涩的痛。纪实感堪称青春片的标志,原因在于青春片小众导演尤其偏爱精练的电影艺术加工手法,而往往电影艺术加工手法越少,其纪实感越强。娄烨执导的电影《周末情人》(1995)以及贾樟柯执导的电影《江湖儿女》(2018)是非常典型的应用纪实手法的电影代表。
(二)选材立异
小众青春片导演在选材上常常“标新立异”,惯于过度强调事物的某一面,以期获得强烈的情感和主题表达。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一部电影不可能完整地表达青春的全貌,而且常态的青春千篇一律,非常态的青春却各有各的遭遇,这将带给电影无限的新鲜感。但是,一味追求立异却很有可能走向极端,导致一大批“狗血、做作”的青春片大行其道。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青春片导演们十分热衷于描写青年人的性、吸毒和犯罪,而正常的青少年世界完全得不到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正经历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的导演偏爱塑造青年人的空虚、反抗和对过去的批判,同样忽略对普通青年的关注。总的来说,青春片立异的程度决定了其质量,一部优秀的小众青春片一定是既有特点,又不夸张。
(三)强烈的时代和导演个人印记
电影艺术诞生以来就有青年人的身影,但是青春片的开端很模糊。1913年讲述贫困青年人追求爱情的传奇电影《来自布拉格的学生》(1913)是青春片的开端之一。梳理青春片的发展发现,青春片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和导演个人理解。二战前青春片已经大量出现,美国社会积极向上发展的日子里,美国电影《大学一年级生》(上映年份不详)、《现代少女》(上映年份不详)等影片展现了青少年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二战结束后则出现一批反思战争和控诉战争对青年儿童造成伤害的电影,比如1951年在意大利上映的电影《米兰的奇迹》。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影公司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出现了许多描述青少年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并走向犯罪的电影,如《飞车党》(1954)。
现代中国青春片小众导演的电影作品中时代和个人印记更明显,主要体现在电影的题材、表达手法和思想倾向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建设道路曲折,经历了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变革。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曲折道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导致这一时期文化与艺术等均被压制。当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思想和艺术领域必然会出现思想和艺术上的报复性行为。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必然“强势”袭来,这种强势体现在当时的西方社会确实更发达和文化软实力更强上。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题材和内容渐渐放开时,一批感受到中国社会落后并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电影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此时的青春片导演以一种反抗者的姿态出现,时代带给小众青春片导演和电影深深的烙印,他们反抗,他们不拘于现实,他们被学术界称为“第六代导演”。
赞美他们的话语太多,是否存在过度吹捧的嫌疑呢?时代的印记到底带来了什么?作为时代的反抗者确实值得赞扬,因为反抗需要代价。但是,青春片小众导演可以把北京、上海等城市描述成肮脏不堪的所在,镜头下全是阴暗,他们所描画的“污浊的中国”使他们频频获得国际大奖,收获了无数赞美与荣誉,他们很快被推上神坛,被誉为“电影的良心”或“中国的良心”。然而,普通人却很难接受这种艺术,这主要体现为这类电影往往只有低迷的票房。中国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在一部分第六代导演眼中似乎只有扭曲的阴暗一种。
二、华语青春片小众导演案例分析
(一)贾樟柯
贾樟柯被誉为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他的作品在国际影展屡屡获奖,深受业界好评。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特征鲜明,尤其乐于展现中国社会财富剧烈膨胀时期社会转型下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贾樟柯的长镜头影像下,非职业演员表现的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物全面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社会巨变下的创伤。贾樟柯前期作品《小武》(1997)、《世界》(2004)等青春气息彰显,但相较于其后期代表作如《三峡好人》(2006)和《山河故人》(2015)等营造的后青春话语,从某种意义而言,是其青春意识的下沉,其韵味更加耐人琢磨。
电影《三峡好人》的男主人公韩三明去往重庆奉节寻找多年未见的妻子的经过是电影的故事主体。韩三明的寻妻过程一波三折,16年未见的妻子却一直未出现。老实巴交的韩三明决定留在奉节做苦力,直到等到前妻出现。与此同时,来自山西太原的女人沈红为了早就与自己貌合神离的丈夫同样来到重庆奉节县城,虽然她深知最终结局,可是沈红却坚定地想要一个正式的说法。观众对《三峡好人》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喜欢的人认为《三峡好人》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是少有的经典作品;不喜欢的人则认为《三峡好人》节奏拖沓、情节臃肿,拍摄得毫无美感。
电影《故乡三部曲》即《站台》《小武》《任逍遥》是贾樟柯浓厚乡土情结的体现。电影场景均取自山西地区,萧条的小镇、露天的煤矿和荒凉的土地等都是山西的风土人情。电影呈现了社会巨变的大时代面前,小城青年的茫然和不知所措而又试图摆脱困境的人生状态,他们像世界的弃儿一样在时代面前被边缘化。
总而言之,贾樟柯是“新生代”导演中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导演,他敏锐地挖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阵痛,敏锐地体察到小人物的命运和弱势群体的无奈他用镜头表达了青年人的迷茫和无望。
(二)娄烨
娄烨是一个获奖无数的导演,但娄烨的作品却很少有高票房,艺术界拼命为娄烨的作品叫好,普通人对其电影接受度却有限,因此娄烨的青春片成了小众青春片的典型代表。娄烨电影的风格似乎与世格格不入,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神圣不可侵犯,他试图打破世俗法则,打破电影的条条框框来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电影。娄烨的镜头在向世人讲述一个狂野热血的青春影像,社会底层人物的彷徨、焦虑和欲望在娄烨电影中集合。作为国内第六代学院派导演,娄烨的影片追求小人物的生活还原,他没有受到民族和历史的影响,勇敢地将人独立出来,以求真切地展现关于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境遇。然而,比较遗憾的是,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自我满足且封闭于个人思想境界,电影内容过于关注社会的某一个方面,使得普通人感觉电影与生活很远。娄烨比较典型的电影作品有《苏州河》(2000)、《颐和园》(2006)、《春风沉醉的夜晚》(2009)等。
电影《颐和园》讲述了一个漫长的爱情故事,围绕一个成长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女孩的经历展开,电影以五个城市为落脚点讲述一个曲折的故事,这些城市包括图们、北京、武汉、重庆和柏林。女主角余虹从图们到北京上大学,遇到了男主角周伟,两人陷入爱河。毕业后,余虹留在了国内,周伟则去了德国柏林。而多年之后,二人又在中国重庆重逢。周伟有时犹豫不决,有时又很果断,具备典型中国当代男人的毛病和优点,而余虹挣扎在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之间,他们之间的爱情来去匆匆。批评者认为电影《颐和园》制作粗糙,光线背景压抑,性爱镜头过多且过于裸露,除了大段文青式的独白外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然而《颐和园》的影迷给予其极高的评价,比如勇于突破现实的枷锁,反映这个社会最痛的现实。电影《苏州河》讲述的是男主人公马达先后与两个长相酷似的女人——纯真少女牡丹和美人鱼表演者美美之间的恩爱纠葛,影片同样引起巨大反响。
(三)姚婷婷
1986年出生的姚婷婷是典型的80后,仅有三部长篇作品的她虽然产出有限,但是收获的评价甚高。其中,她执导的青春片《谁的青春不迷茫》不但收获了1.79亿票房,而且豆瓣评分也达到了6.7(我国国产青春片评分普遍偏低),这已是不错的成绩。她的青春片之所以在这里被归为小众,主要在于其作品关于疼痛青春、恋爱青春的背离。她追求真实摒弃做作的创作风格在国产青春片中比较少见。
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作品,但其内容却与原著几乎毫不相关。这部电影除了沿用原作的名字和主题,其故事架构全然不同于原著。电影讲述的是“学神”林天骄和“学霸”高翔阴差阳错之下的命运交织,二人从心怀偏见到互相和解并最终心生好感的过程很好地诠释了青年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该电影因此被观众视作“难能可贵的青春历程”。
1995年,姜文推出了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自那之后,我国青春题材电影发展稳定并一度达到“井喷”状态,不过拍摄数量惊人的背后,却不是质量的提升。大量青春片习惯游走于“边缘”青春,将堕胎、打架、犯错等相对极端的事件当作青春的协奏曲,大肆创作,使青春在这些电影中失去本来面目。相较于大多数其他同类电影打着“不痛苦、不青春”的旗号贩卖疼痛不同,《谁的青春不迷茫》侧重于表现青春中的正能量,这里边的青春也有痛有累,但却真实无虞,令人信服。
比如,在塑造青春期的残酷与迷茫感方面,电影开篇便就林天骄这个“天之骄子”做出交代。她成绩优秀,却并不是老师家长眼中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她会代替同学做功课,帮助其他同学旷课、早恋,甚至在一场重要考试中试图通过“作弊”过关……她如此行为正是家长与老师的高压逼迫下产生的青春期迷茫作祟,关于这些,电影做了赤裸裸的展示,没有夸大和掩饰,也没有打造一个和谐完美的乌托邦世界,而是简单地做真实的展现,并以此提出创作者对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质疑和对青春期学生成长的关注。
另外,在情感表达方面,林天骄和高翔二人的感情变化印证了林天骄的成长。不同的是,林天骄的个人成长是带有独立性的,并不是与高翔之间爱情的附属品;林天骄的爱情是具有自我价值的,她勇敢追求自由,拒绝做男人的附庸。这样的情感塑造是一种正向且有意义的带动,比那些山盟海誓、情比金坚的爱情要来得更加深刻。由此可以看出,姚婷婷所塑造的青春是每个人的青春,不狗血、不做作,正如人们回望自己青春的样子。这样的青春电影虽然不惊心动魄,但足以动人心弦、令人神往,这是青春片本该拥有的样子。
三、青春亚文化对小众青春片导演的影响
青春亚文化是一种非传统的社会文化形态,是由年轻人群创造的,与父辈文化和主导文化不紧密相连,而是形成了一种既抵抗又合作的关系。青年亚文化崇尚夸张的、带有反抗主流性质的文化符号,比如妄诞的音乐、独特的形象(服饰、发型等)、特殊的语言等。透视小众青春片导演在电影中亚文化的表达对解析其创作风格十分重要。
20世纪50年代的“嬉皮士文化”和“朋克运动”是最重要的两个美国青年创造的亚文化现象。当时电影反映的美国青年亚文化主要包括毒品、音乐和滥性等,电影《边缘日记》(1995)和《半熟少年》(1995)都描述了美国当时青年亚文化的面貌和形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社会矛盾和思想转变的集中爆发期,青年人出现了思想空虚并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这个时期电影人对社会和艺术的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以快速、高质量发展为标志,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其变化都是掀天揭地般的,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使一切关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固有思维变得总是无法适应时代。小众青春片导演对青春亚文化有着特殊的偏爱,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作品始终无法获得普通大众的认可。
青春亚文化并不是小众青春片所独有,主流电影中仍可寻见其身影,其在电影中表现出的不同,一是刻画的比重,二是时代赋予的特殊性。在第六代导演的镜头下是社会阵痛期小镇边缘青年形象;中国社会转型期后,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这种形象转化为都市消费主义青年形象,电影《小时代》(2013)就是典型的代表。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的发展,青春亚文化特征在电影中逐渐发生新的变化,网络社区的聚集和自媒体等的兴起导致新媒体时代下的“后青年文化”特征形成,这对小众青春片的影响不可忽视。
结 语
我国的小众青春片中,第六代导演的作品相对质量较高,也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然而国内外普通观众却都难以对这类电影形成比较高的接受度,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不然,这只不过是部分小众导演在自我封闭的环境里创造出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对中国臆想的电影,使西方人在这种电影中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中国,一个肮脏、落后、拥挤不堪的中国。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小众青春片的发展趋势。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应该多元化,从题材到手法最后到思想,千篇一律地聚焦某一点犹如盲人摸象,这种作品永远只能取悦影评人和研究者受众,社会大众无法接受。另外,青春片小众导演的创作风格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对青春亚文化的表达和书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和社会现象,是值得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