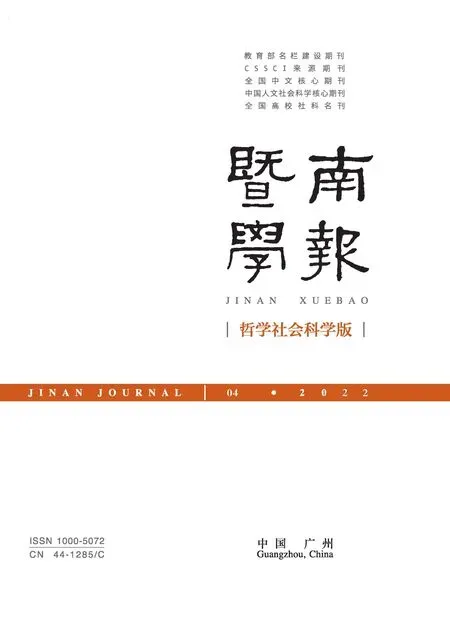“作文害道”是儒家学说吗?
——“文以载道”再评价之四
刘锋杰
人们在评价“文以载道”时,多将程颐提出的“作文害道”说视为其当然内涵,这是一种误解。欧阳修提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时没有“作文害道”的丝毫想法,相反,他把“能文”作为载道的前提与目标。章学诚认为:“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引用了“文以载道”说法,看到此,必定以为他会提出“作文害道”说法,可却笔锋一转,明确反对害道说,强调“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不是轻文而是重文。尤其认为:“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这意思是,作文当然要载文外之事理,但作文又有自身文理,这与所载之事理不相同,文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或美或丑的面目是大家都能清晰辨认出来的,这必须加以重视。如此理解“文理”,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具有自身审美性相一致,表明章学诚虽然承认文要载道(即事理),但也承认文学必须同时是自身,有自身的文理规定性才足以明文外事理。由此表明,千万不要一看到某人主张“文以载道”,就以为某人会提出“作文害道”说。事实是,绝大多数的载道论者,同时是重文论者。不能把害道说简单地赘附于载道说上,它可能另有起源。我认为,宋代理学家体现出非原儒的思想特性,由于强调极端性命之学,把道德修养高置于一切之上,又处于与苏轼等古文家相对立状态,才滋生了“作文害道”思想。从思想根源上看,这是受道家而非原儒影响而形成的,代表着文道论的异变,试图向取消文学审美性的方向发展,这是应当予以反思与摈除的。
一、“作文害道”是理学的独门观点
“作文害道”不是原儒的文论主张,是理学家的特有思想观念。至二程才在周敦颐主张的“文以载道”之外旁生出“作文害道”说。
周敦颐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这段话可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用车应载物来指文应载道,强调车子只是用于装载,对车的轮辕加以修饰无助于装载。车上没有装载什么,车子再漂亮也失去了存在价值。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文道关系,强调文只是装载道的工具,当然是重视所载之道而轻视载道之文。第二部分借用传统的文质论框架,认为文辞是技艺性的,道德才是创作所要表现的内容,强调只有思想情感充实了才能进行成功的创作。这与白居易倡导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说法相近,没有什么错。尤其是周敦颐强调文辞创作只有达到美妙程度才能使读者赏爱,这样的文章才能传得久远,是有说服力的。这合于“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古训,使其与二程轻视这句话形成了强烈对照。他指出:“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这意思非常接近苏洵说的“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蔽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如果不能否定苏洵所说的合理性,那就不能否定周敦颐所说的合理性。苏轼记住了父亲的这一忠告,为纠正“文工道蔽”的偏颇说过:“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此言清楚表明文质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好作品,仅有文辞美妙是不够的。其中的“有为而作”指创作时要内容充实,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是指单纯追求技艺不能提高创作质量,结合起来看,这是强调文质统一,且把质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上加以思考。考虑到周敦颐的活动时期与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的活动时期大体同时,能否也说周敦颐重质的文质论也对那个时期古文创作的流弊具有校正作用呢?我以为是的。但是,周敦颐这段话中的第二部分是服从于第一部分的,即文质统一论服从于装载工具论,这就使得应当统一的文与质的双向结合变成以质去文的单一倾斜,导致文质关系论的空洞化。从周敦颐的另一段话中也可见他的轻文是前后一致的,如认为:“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设一个“陋”字来讲文辞之弊,可见厌憎以文辞为业。如果说坚持文质统一论时,欧阳修、苏轼等人心目中始终有一个堂堂正正的文士形象存在,且这个文士可以通过立言而不朽,那么,在周敦颐心目中恐怕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不朽的文士。于是,既要看到周敦颐一些言论的合理性,也要看到在周敦颐这里已经萌发“作文害道”想法。这与他的哲学相表里。周敦颐讨论道性时主静,对于所有动态的东西都有所警惕,强调“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也许正是认为文学创作表现情感,属于人欲部分,其特性是动荡的,所以成为他欲驱除的对象。不过,周敦颐极少讨论文辞,因而体现出来的轻文倾向还不是十分突出,提出“甚焉,害也”的观点与“害道”的思想有关,但还没有直接提出“作文害道”命题以全面对抗文学家的创作。
宋理学家的师承意识非常强烈。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朱熹则是弘扬周敦颐与二程学术的后起之秀,他们的思想观点高度一致。二程接受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认为:“《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又认为:“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程颐还说:“夫子删《诗》,赞《易》,叙《书》,皆是载圣人之道,然未见圣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圣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圣人用处。”二程与周敦颐的区别在于没有用“装载”之义来理解载道说,但他们对载什么道、载道之文有什么特性的理解,是与周敦颐大体一致趋向极端的,走了一条不与文学审美论相兼容的载道之路。二程的精细处在于研究六经与载道关系时分了一个体用来加以阐释,用《诗》《书》《易》来对应道之体,表明了道理是由《诗》《书》《易》来建立的;用《春秋》来对应道之用,表明了载道中仍然存在着由体到用的实用功能,进一步明确了载道的实用内涵。从理论逻辑上讲,这是一种深化,但也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思维特点,更加注重探究道理,而不像欧阳修、章学诚等人那样,几乎把六经平等对待,甚至更重六经中的记事,不过分地讨论抽象的道,而是充分地强调具体的人事,从而更加关注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后人批评理学家重理轻事,与他们的这种认识与选择有关系。
二程最为著名的观点当是提出“作文害道”说,把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的必须统一观变成了“文可能载不了道”的文道对立观,比老师更进一步地轻文。程颐的看法最著名: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程颐认为,若不专心致志为文,则达不到工巧状态,可一旦专心致志,却又必然分了精力,使得自我有所局限,不能与天地同其大。故他判定文学创作是一种玩物丧志的职业,不值得推崇。在这里,程颐所许诺的“同天地之大”与“为文”构成了内在冲突,为文者必然达不到天地之大的境界。这与文学家强调创作“天地之至文”的说法相冲突,在后者看来,为文是可以达到天地之大的,关键是要具备达到天地之大的条件。所以,要说轻文,程颐恐怕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在自己的观点中设置了为文无法实现与天地同其大的目标,而这个与天地同其大正是道的状态,故程颐设置了文与道的绝对冲突场景,从道的绝对性出发,驱除了文的合理存在性。我曾有一个想法,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在“理想国”里驱除文学的主张,可同时期的中国先秦哲人如孔、孟却在宣扬文德,为文学加冕,他们高度重视文学,把它引进社会政治治理。难道我们早期的儒家道德文化中没有驱除文学的思想吗?没有的。到了宋代理学家才提出了这个驱除命题,他们驱除文学的思想不是藏于原儒的思想中,而是别有所藏。
另有一处看法是:“向之云无多为文与诗者,非止为伤心气也,直以为不当轻作尔。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这段话证明二程主张“作文害道”说是一贯的。参照他们的另外一句话,“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更可明了他们的害道是指作文中没有义理的表达,失去了“辅翼圣人,为教于后”的伦常实用功能,故以文害了大道。二程还把义理之辩的学习视为“学之本”,把研习李白、杜甫、韩愈之诗视为“学之末”,近于公式化地把一切文学创作都视为离道、害道的邪术。二程有“得正则远邪,就非则违是”的话,在他们看来,“以词章为务”的作文既失正就是非,属于邪术之类。他们强调的不要轻易作文,不是指审美构思上的不成熟则不作,而是指没有形成明确的义理就不要创作,其所谓的创作是指儒家学者的写作论文,而非包含作家的想象与模写世界万物。故“作文害道”说是以学者的论文写作方式要求了作家的审美创造,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取消文学审美特征的极端做法。故当他们主张“学者当以道为本”,指的是以探寻道理为本,要求写是非曲直的对错,即所谓“夫心通于道,然后能辩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如孟子所谓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则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后见也”。欧阳修等人也强调创作时要“道足”,但这个道足指思想情感的饱满与生活内容的充实,所以深通于文有助于创作的成功。
朱熹全盘接受了“作文害道”说。他承认自己喜欢过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但在所谓深思以后认为他们的作品具有危害性,“其言虽侈,然其不过悲愁、放旷二端而已。日诵此言,与之俱化,岂不大为心害?于是屏绝不敢复观”。朱熹认为苏轼的为害更甚:“况今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学者始则以其文而悦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则渐涵入骨髓,不复能自解免。其坏人才、败风俗、盖不少矣。”在朱熹看来,苏轼讨论了更多的问题,其观点流传的范围更广,危害更大。朱熹的观点是“文从道中流出”,认为文与道是同一的,要阐扬儒道,就得完全服从儒道而作文,稍有间离,就成了害道之文。“夫文与道,果同耶异耶?若道外有物,则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无害于道。惟夫道外无物,则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但其害有缓急深浅耳。”朱熹认为,只有儒道才揭示了人生规律,而儒道自会形成合乎儒道的文章,因此,那些不符合儒道的文章,或发挥较多的文章,也就加害了儒道。如此一来,他把文与道等同了,看不到文的相对独立性,限制了文的独自发展;他把文与儒道等同了,不表现儒道就不能产生文学,实际上否定了世界上还有其他认识真理的途径。又因为朱熹仅仅重视论说之文,以为它们能够明道,所以文学在他这里也就等而下之,是外于道,故在驱逐之列。
理学家的害道说有三点判断:其一,作文中所负载的老、佛害了儒家正道。这是争道统的正统性。他们认为,苏轼所代表的文学家即使肯定儒道,也不是儒道的正宗。其二,诗文中的“性情不正”害了儒家道理。如朱熹评《诗经》中的多数情诗为淫辞就是典型症候。这是争道之理。强调依理创作,当然反对抒情而强调归于“性情之正”。其三,把精力用在作文上害了自己的道。在理学家看来,追求“能文”,不关伦常日用,影响修身养性,所以文学在当斥之列。
二、“害道”说出自《淮南子》
那么,“作文害道”说是宋理学家的发明吗?不是。“害道”说来自《淮南子》,而理学家运用了这个概念。
道作为世界的本源,不是一个物质实体,故无法直接刻画它,但可以描述它,揭示其作为万物之源的特性与运行规律。“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滂,冲而徐盈;混混汩汩,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在《淮南子》这里,道是可以大到无边,小到只有一握,既能高又能深,既能阳又能阴,既能实又能虚,既能柔也能刚,既能浊也能清,一句话,它是万物之本根,促使万物不断生长。离开道,万物不能生长;离开道,万物也不能认识。这样一来,道论就是关于建构世界本源的论述,揭示世界本源的规律。为什么会说“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呢?就是强调得到了道,就掌握了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就不愁治理不了天下。
《淮南子》专门讨论了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无为者”是指“不先物为也”,“无不为者”是指“因物之所为”。将其落实在社会治理上,则是“无治而无不治”,“无治者”是指“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是指“因物之相然也”。故要体现自然规律,就要秉持无为与无治的态度,一切以自然为准绳达到无所不治的目的。其他则是“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这是用老庄的道论解释万事万物的成因及运行特性,形成了自然无为、清静空虚的思想认识倾向,把一切纳入这一模式去理解。虽然在讨论社会治理时常常批评儒家及墨家思想,却也不得不援引儒家的仁义思想形成“持以道德,辅以仁义”的以道家为主、儒家为辅的社会治理策略。如说:“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终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事不更者也。”《淮南子》虽然强调仁义礼乐的治理作用,但认为它们还是低于无为之道的,只是治理工具而非目标与方向。这是《淮南子》道论与时推移的一个表现。不过,就《淮南子》在吸收儒家文论的问题来看,它又裹足不前,在理解社会治理时与儒家思想合作,在理解文的重要性时与儒家思想不合作,提出的“害道”说为后世理学家贬斥文章提供了思想基础。
《老子》与《庄子》中无“害道”一词,是《淮南子》明确提出来的,在具有总结意义的《泰族训》中强调:“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苟削伤德。”这与开篇《原道训》中一段话相一致:“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邪、失、过、累”都是害的表现。又说:“小快害道,斯须害仪。”认定小小的痛快会伤害大道,片刻的小获利会伤害大义。由此可知,《淮南子》提出“害道”说,不是某一篇的语义,而是贯穿全篇、体现在整个体系中的。关键在于,《淮南子》不仅提出“害道”说,还直接把它与“文章”关联起来,具有“文章害道”的意思。请看这段话:“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这表明,要想实现“至人之治”,就得消灭“聪明”“文章”,返回到自然素朴状态,才能获得最好的治理效果。当《淮南子》将“害道”与“文章”直接关联加以论述并主张“灭其文章”时,“作文害道”说法已经呼之若出。
这与《淮南子》对于文的认识水平相一致。一方面处于道家道论的语境中,认为文作为表现是对道的混淆,故文的地位不高,甚至要去文才能把握道的内涵;一方面处于文礼论的阶段,文是礼的文饰,不是后来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书面写作。再加上不像儒家那样重视礼的表现,故而将儒家文礼论中的文放置在文是对于道的混淆层面加以理解,所以,虽然运用了儒家文礼论的话语,实际上却具有道家文论的实质,没有救治得了道家文论的轻文偏向。在《淮南子》中,文的语义都是极其简单而缺乏魅力的,根本不像刘勰那样对于文是顶礼膜拜的。

从传承上看,这是在文质论框架内分析文的属性,但没有从文质论第一阶段的文礼论发表到文质论第二阶段的文道论。文道论与文礼论的区别在于:在刘勰那里形成文道论的时候,经过了魏晋的文的自觉,故文道论同样代表着文的自觉,重文成为重要指向。而文礼论处于文的自觉之前,当然无法像文道论那样重文,《淮南子》即如此。它指出:“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又指出:“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足以变易心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这是说“为文”应源自真实的情感需要,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满足欲望,会使自己的心志不稳,心绪不宁。故“为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节制,使人的情感恢复平静。因此,所谓“为文有质”,其实是指“为文”应当有助于帮助人们保持心境的宁静,不使血气动摇人的精神大本。《淮南子》所说的“为文有质”与儒家强调文质结合有相同的一面,但由于没有选择原儒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类更加突出为文重要性的观点而加以阐发,故又不知重文。相反,《淮南子》具有“不文”或曰“反文”倾向。如强调“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斫,大豆不具,大勇不斗,得道而德从之矣”。此处的“不文”指的就是不用文采。如谈到古代王者的布政之堂是这样描述的:“土事不文,木工不斫,金器不镂。衣无隅差之削,冠无觚蠃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飨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这里出现的“文”“斫”“镂”“削”“理”等,都是装饰、文饰之义。《淮南子》从节俭出发是不强调文的重要性的,一切以自然质朴为好。这是主张“不文”的典型思维,而其思想则来自道家的反智主义。
三、“害道”说是道家“反文”思想的体现
从根本上讲,“作文害道”说是道家思想的体现。老子的很多观点可以往“作文害道”上面延伸。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中的“五色”“五音”“五味”就是文的表现,由于它们仅仅满足欲望,有害于道,所以予以否定。老子持有“不文”说,他的目标是消灭文章。庄子的思想大体类同,如说: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在庄子看来,那些极力追求色彩斑斓华丽、声音高亢激越、高倡仁义以沽名钓誉、善于诡辩尽说空话的,都是旁门左道,违背了“天下之正”,不合于事物的本然实际,给人带来危害。总括庄子的“不失其性命之情”“失性有五”与“生之害”等语可知,“失其性”就是“失其道”,“生之害”就是“害生”,“失其性”既是“害生”,就是“害道”。所以,在庄子论述中,为了保全人与事物的真性命,必须极力反对色彩、声乐、文辞、礼乐等外在的属于表演性、装饰性、辩论性、引导性的行为与创作,同时希望回到原始直朴的状态,以为只有在那个自然而然中人才能成为真人,才有真性情,才有真生命。因此,说庄子接近于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不是想当然的。其实,宋理学家在讲“作文害道”时,他们所谓的“道”也是指“性”“生”等问题。由此来看,宋理学家接上道家的“害道”说而讲自己的“害道”说,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顺承过程。区别在于:老庄时期的文是宽泛意义上的典章制度、文采装饰等,而宋理学家的文已经包括文章之文,用以指书面写作。由于前者可以包括后者,老庄的“作文害道”意思与程颐的“作文害道”思想是一致的。
若照此一观点推论下去,庄子既然是“反文”的大将,为什么他又吸引了后世无数的艺术家拜倒在他的理论之下呢?这有些吊诡,但又不吊诡。庄子在推行老子发端的“反文”路线以后,又有所修正,这才导致他是“反文”的大将,却也成为后世“崇艺”的榜样。原因在于,庄子与老子有所不同,他有否定文采技艺的言论,也有肯定文采技艺的言论。比如他看到了技艺与道的关系颇为遥远,却没有断定它们之间不能结合,故庄子对于技艺与道的关系有了一层新的理解,恢复了道对技艺的制约作用,故可以在技艺已经与道结合的层面肯定技艺,这时候就不是“反文”而能“重文”了。比如说:“今已为物也,欲复其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强调道散于物中后,要想恢复物中的道是困难的,所以保持道而不散入物中才是最好的状态。可事实上世界是以物的方式呈现的,不使道散入物中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促使物中有道就成为必然的实践。庄子认为,只有“大人”才能得道,为从物中返回道留下了一条通道。由此可知,庄子强调物与道的原本关联性,又在首先承认道的前提下承认文的价值。“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前一句说道的化物是均衡的,不会遗落,后一句说万物各式各样,可是它们总归受道支配。于是,由物中有道进而说技中有道也就势在必然,因为物中有道表明了作用于物的技中也可以有道。既然技也可以通于道,那么技也就非常重要了。正是在这一本体关联中生出技(即文)与道的实在关联性。下面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这一关联的可能性:“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分两步肯定了物、事、技艺与道的联系:先从道、德角度肯定它们对于万物的关联,再从人事、技艺角度肯定它们对道德的关联,进行了“技→事→义→德→道→天”的推论,展示了人事与技艺对于道德的依赖路径与回归路径。于是,庄子进入了另一个论域:在批判物(技艺)离道的泛滥后,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困难连接,却又基于物与道的原本关联性提出了物(技艺)可以回到道那里去,享受道所具有的荣光。结果,庄子否定的文(技艺)是离道的浮华,肯定的文(技艺)是合道的极致。在庄子这里,他所推崇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匠石斫垩”等“道进于技”的故事,都显示了创作者可以通过自己才能技艺的艰苦训练,由不局限于具体的技艺而能够上升到道的层面,从而铸成最后的艺术辉煌,即合道的技艺即合道的文采。于是,庄子以“反文”始,却以“重文”终,所反的是简单地专注于技巧的文采,所重的是合于道的“大巧”,如同天籁一般的恢宏之作。这里的一个标志是,庄子所强调的“大巧”,必然是在重视一般性技巧的基础上才能够达到,所以,当一般的艺术家们以这种“大巧”作为目标时,其实他们都像庖丁那样专注,像轮扁那样用一生来干一件事,像梓庆那样寻求合天然性,像匠石那样寻找心心相印的搭档,这样专注刻苦何愁不能创造伟大的文采、伟大的技艺?庄子在“反文”的路线上开了小差,却不经意间开辟了“重文”的巨大空间。这是理论家的复杂性之一,所主张者与所推崇者往往有些不一致。
四、“作文害道”说是道德主义的宰制
宋理学家提出“作文害道”说既有老庄思想的内在依据,也有宋理学家自身的思想机缘。宋理学的产生就是将原始儒家的修身论述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而实现的,程颢说:“‘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与庄子的“不失其性”而求“性命之情”是一致的。程颐说:“集众理,然后脱然有悟处。”则留有禅宗渐悟与顿悟说的影响。由于追求心性的更加纯粹性,不免用性转换了情,导致对情的压抑,也导致对抒情文章的压抑,故而离情离文,才提出了“作文害道”这样的思想。后世在批判“作文害道”时把板子打在原儒身上是错的,这应该由道家来承担惩罚。
理学家之所以提出“作文害道”思想,是因为执行了一条道德主义的思想路线,其中也混合了与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的对抗。随着他们将道德的社会功用往极端方面推进,以纯正道德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枢纽,也就将道德与文学的关系对立起来,从而必然提出“作文害道”说。于是,即使他们在讨论为文时与苏轼等人有一些相似性,却体现着根本的差异。
如二程认为圣人的创作出于“不得已”,苏轼也说创作出于“不得已”,但二程是指思想见解形成后不得不表达出来,苏轼是指审美构思成熟以后不得不表达出来。二程说作者的内心已经“是非了然”,苏轼也说创作必然有一个“了然于心”的状态,但二程的“了然”是指自我对世界人生的看法清晰了,苏轼的“了然”是指内在审美构思清晰了。二程强调“文之与质,相须而不可缺也。及夫末胜而本丧,则宁远浮华,而质朴之为贵矣”,苏轼也说创作要有道有艺。但二程是对立文与质,以为一工巧就害了质,所以重质而灭华,苏轼则主张道艺两进,于道上用力,也要于艺上用力,讨论的多是从艺上用力而达于道上用力。故二程提出“人能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表面上同于苏轼提出的“学以致其道”,其实,二程讨论的是思辨之文的创作原则,苏轼讨论的包含了文学之文的创作原则,前者要求写出抽象的义理之辩,后者要求写出活生生的物态人情。
在二程这里,谁能拥有天地之大呢?恐怕是理学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达到“知道”“造道”状态,当然具有天地之大境界。二程区分学者类型时体现了这种看法:“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能文的“文士”指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一类,谈经的“讲师”指讲佛学、道学的一类,知道的“儒学”指的是他们自己一类。在二程活动时代里,他们的“洛学”与三苏的“蜀学”严重对立,水火不容。二程以儒学名世,三苏以文学名世。苏轼曾猛烈批判二程的性命之学,认为他们的理性靠不住;二程也批判三苏的文学取向,认为他们的文学不入道统。程颐的如下评价恐怕是针对韩、梅、欧、苏的,他说:“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他推崇吕大临的诗意:“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在这里,程颐赞赏杜预(即杜元凯)那样的学习与著述,反对像司马相如那样极尽铺排地创作文章,以为像颜子那样乐道守贫,才是一个合格学人。如此则是,为学为道不为文,为文则是废了道。朱熹继承了这个观点,他对写诗的评价是:“诸诗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费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著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正在于此。其与玩意于空言,以校工拙于篇牍之间者,其损益相万万矣。”朱熹看出了诗的好,却把诗置于一个极低的位置上,认为它们没有伦常的实用性,所以不值得专心追求。不能看到朱熹夸奖儿子学诗就认为他重视文学,也不能从朱熹写诗词千首就认为他肯定文学的价值。朱熹有时候也看重诗歌,那是认定此诗肯定了他所认同的伦理价值,朱熹从来没有脱离理学标准来独立地重视诗歌的审美价值。
由认定事物具有道德性而发展成普遍的道德主义而排斥事物具有其他特性,那就必然会犯错。道德主义只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与实践,因此无文也许是最好的表征之一。但以道德主义的标准去要求文学家是极其严重的偏见,违背了不同事物的根本属性在于事物间的区别这一条。理学家不明白在人世间必然存在一种关于词章的文学家,把人类对于生活的感受与发现写出来,而非像他们那样只发掘伦常的义理而用概念把它表现出来。伦理的、概念的与审美的、具象的二种价值要求应并行不悖,而非你死我活。理学家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倡导文道结合的文学家才在认真地寻找二者的融合。
黜情张性是理学家与文学完全对立的具体原因。二程非常重视礼学研究,“然所定只礼之名数,若礼之文,亦非亲作不可也”。可见对于“礼之文”的重视。在解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时,程颐认为:“这个只是浅近说,言多闻见而约束以礼,虽未能知道,庶几可以弗畔于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识前言往往而能不犯非礼者尔,非颜子所以学于孔子之谓也。”程颐强调在博约之间,博只是知识性的,而约才是关键性的,文只是表达性的,而礼才是实质性的。因此,在他的文礼论的论述空间里,文具有礼的属性,导致了文处于弱势地位。在解说颇有争议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时,程颐又说:“当时谓之野人,是言文质相称者也。当时谓之君子,则过乎文者也。是以不从后进而从先进也。盖当时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尔。”在“野人”“君子”之辨中,程颐把“君子”视为“文弊”的代表,批判“文弊”,所回到的文质彬彬状态其实已是“质胜”状态,还是走了文礼论的路线。所以,“节文”成为二程“礼之文”的同义语,二程说:“子曰:因人情而节文之者,礼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义也。”“节文”就是从礼。程颢虽承认诗歌创作“发乎情”,却认为必须“止乎礼义”,终究是灭情的。他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有节故有余,止乎礼义者节也。”既然“止乎礼义”是“节文”,那么倡导“节文”,就是主张以礼义为标准进行写作。把文视为礼的表达,受礼的规范制约,文当然不能恣意奔放。
理学家否定情感合法性。他们认为情是低级的,性才是高级的,情受到性的制约才是正当的情;反之,情突破了性的樊篱,就会造成灾害。程颐说:“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主张“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是将性与情完全对立,以为人身上只能有性的存在,不能有情的存在。程颐提出了“以性统情”的观点,防止情感突破性的制约而泛滥,他说:“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地生人,人即秉赋天地精华而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五性,此五性受到外物激荡而生成七种情感,导致人心的混乱。此时只有用性来制情,才能使人心复归静正,通向圣人之道;反之,使情制性,人心就失去静正,不能通向圣人之道。故若认为圣人之道是人所向往的成人目标,那么,就必须通过以性制情的方式来实现。在这段话中,程颐建构了“道→性→情”的三级划分模式,情处于最低端,也是需要引导与规范的对象。这样一来,突出抒情的文学当然也就对应性地处于最低端,与达道隔了两层。故唯有将情交予性,由性将其纯粹化,才能使人心归正,才有可能达到道的状态。于是,从事文学创作而达道则成为文学难以实现的目标,因而也成为程颐看不起的生活方式,将其看作是害道行为。对于情的排斥,使二程看不起表现情感的文学。但程颢也写过一首很著名的《偶成》诗:“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颇有情致,属“吾与点尔”一类。所以,他也偶尔肯定“缘情”写诗,在《新晴野步二首》之二中写道:“阴曀消除六幕宽,嬉游何事我心闲。鸟声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蔼间。水底断霞光出岸,云头斜日影衔山。缘情若论诗家兴,却恐骚人合厚颜。”“诗缘情而绮靡”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特性,肯定“缘情”以论诗兴,则是肯定了诗的审美性。程颢在此还调侃了“骚人”,说明他写此诗时情兴很高,不免嗟叹之、咏歌之、手舞足蹈之。当然,由于程颢所抒情感属于山水之乐,故而不会涉及敏感的人欲部分,也就自动地免除了人欲的干扰,可达性情之正,不与礼义冲突,使其暂时地偏向情感而为抒情说了一句公道话,但整体上还是防范情感而要求止乎礼义的。故不论是程颢还是程颐,他们追求纯粹的道德主义,属于反抒情的理学家,把“作文害道”视为批评的基本原则加以运用。不突破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道德说教的这条界定,就不能走出“作文害道”说的理论陷阱。
即使把理学视为儒家思想脉络的一个阶段,他们提出的“作文害道”说只是这个脉络的一个异变点,不能代表儒家文论的基本思想,儒家文论的传统是主张作文益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