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的平凡世界
Mickey LV 何焜



颜色有多少种?1 6 6 6年,牛顿的三棱镜把光分解成七种颜色;但在约翰·伊登的色环中,颜色被分成了十二种。你看,物理老师和美术老师教的好像有点儿不一样——问题出在哪儿?
在牛顿的颜色理论中,颜色被描述成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
但是,牛顿之所以把颜色分成七种而不是八种、九种,仅仅是为了与当时已知的七颗行星的数量、大音阶里的七个音调以及一周中的七天形成数字上的对位。颜色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歌德反对牛顿,认为颜色还应该是“内在的”、在人脑中产生的。在这些讨论里,歌德把从“什么是颜色 ”的问题转到了“我们怎么知道颜色”的问题。
那我们是怎么知道颜色的呢?
在全球化或者互联网诞生前,人类并不共享统一的颜色概念。1969年曾有语言学家对了2600名来自110个地区操着20种不同语言的人做出调查,统计整理他们语言里的“颜色”。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岛民,他们的语言里只有“红色”“黑色”和“白色”,“蓝色”和“绿色”只作为附加词存在(某些部落中甚至不存在)。或者我们可以说,一切颜色都诞生自我们的生活环境;运用颜色实则是“发明”颜色。
“黑色”是公认的人类“发明”的第一种颜色。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人类已知最早的一副画:阿尔塔米拉洞顶上的牛。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开始用黑炭大篇幅地自由挥洒。那黑炭便来自火化动物尸身后便得到的最早的“颜料”。这让黑色在人类文明刚觉醒的时期,成为了最易得的颜色——那也许就是人类首次从自然界驯化颜色,这时人类对历史的记录也同步开启。

IWC 萬国表飞行员 TOP GUN 系列腕表

颜色不会自己凭空出现,它源于现实生活。随着技术的更迭与贸易的扩张,对色彩的共识才传遍全世界。19世纪,法国人从中国带走了一个小罐子;这个罐子日后将给欧洲的印染业带来一场巨大的革命——200年前欧洲甚至不能为皇室制造一条“长青”的挂毯,那来自中国的罐子里的绿泥巴拯救了欧洲的染匠。那是中国人用树皮制造的几乎不会褪色的绿染料。
不过,重新发明自然里的颜色不总是美丽且幸运的,可能也会带来不幸。人类公元前3世纪把白色从矿石中解放出来,那就像潘多拉解放了盒子里的魔物。当时,白色几乎只源于白铅这一种颜料,而它的纯洁就源自“诅咒”,常年使用铅白的人,先是变得苍白虚弱,后来是呕吐甚至肾衰竭。要到18世纪末,法国当局才开始严肃关注这项风险,并要求使用其他白色来代替。但仍有很多艺术家舍不得放弃白铅。毕竟想要重新发明一种优质的白色,真的非常困难。
2022年3月20日,IWC万国表与Pantone彩通合作,推出“太浩湖”特别版计时腕表。它采用的同样也是一种源于大自然的特殊白色,灵感来源于太浩湖的冬季雪景,打造出新款腕表的白色陶瓷表壳。以高纯度的原材料,将不同原材料按照独特比例进行混合。烧制温度、时长,都必须契合特定颜色的陶瓷的要求,以此通过氧化锆与其他金属氧化物的结合,呈现出陶瓷独有的色泽。工艺上堪称一项色彩上的工程创举。

从最初研制陶瓷材质的那一天起,IWC万国表就一直致力于开发色彩丰富的陶瓷。不只源于雪景的“太浩湖”白色陶瓷特别版,IWC还推出“莫哈维沙漠”沙色陶瓷特别版、“森林绿”绿色陶瓷特别版、“曜黑色”黑色氧化锆陶瓷特别版以及“CERATANIUM”瓷化钛金属特别版。最近配乐大师Hanz Zimmer 还为万国全新系列TOP GUN创作了《The Sound of Color》乐曲, 让人感受到时间的色彩与万国之景。
无论哪种颜色都蕴含着独特的故事,背后也都勾连着丰富的历史。在IWC的推动下,每款颜色都有了自己的声音,也达到了一种全新的意境。每一种“新颜色”的发明都是对自然的再一次理解,一次次地在更精准的刻度下体会自然的演进。

2022年3月30日,《智族GQ》编辑总监Rocco在IWC的一场发布会上邂逅了谷爱凌。谷爱凌成为IWC的品牌大使,理由是“她诠释了现代女性的多元力量”;那么谷爱凌本人是如何理解“现代女性的多元力量”的?Rocco与谷爱凌就这个问题展开
此刻我正幻想:如果今天我和谷爱凌不是在2022年的北京,而是在1974年的纽约,我俩并排站在世贸中心双子塔下的交叉路口,拼命地扬起下巴,紧张得发指,只为看清400米上空的菲利普·珀蒂是否还稳当地行走于那根荡在双子塔间的钢索上——对我来说,这真是我不曾驯服过的恐惧感;对谷爱凌来说,她是否会联想到自己曾经冒险做过的那些高难度滑雪动作?
知道珀蒂确实是恐惧的,恐惧甚至驱使他在那次双子塔行动前的半夜突然醒来,砰砰砰疯狂往木箱盖子上敲钉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钉棺材;我相信谷爱凌也是恐惧的,她曾在训练时重重摔到了地面上,头部震荡,造成短暂失忆。可是,珀蒂凌空之时似乎从未抱着赴死的态度,谷爱凌的招牌庆祝动作——腾空后双腿撑开把雪橇往下压——那就简直是用身体比了一个“耶”哎。
在他们的卓绝与他们的恐惧之间,我似乎看到的是一种恋爱感。这道理貌似很浅白,但是我其实一直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跟自己过不去呢?我们不是也可以在恐惧的保护下,更平安喜乐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吗?
我没有直接问过谷爱凌这个问题。但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的一句话在无意中给了我答案。
这次我是在IWC的发布会上遇到谷爱凌的。在她接受完媒体采访后,我俩索性坐下来聊了会儿天。谷爱凌成为IWC的品牌大使,理由是“她诠释了现代女性的多元力量”;我就很好奇,问她:“现代女性的多元力量是什么意思?”她回答我说:“选择。”这貌似是一个很常规的回答,但我立即将它与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关于恐惧的困惑联系了起来。
恐惧从我们身上偷走的具体是什么?是选择。但是,似乎不太有人注意到的是,恐惧其实不仅仅会使我们不去做选择,更关键的,恐惧会使我们不去创造选择。我这么说可能你会感到很奇怪——难不成我们需要凭空去创造选择吗?


IWC 万国表飞行员 TOP GUN 系列 “太浩湖 ” 特别版腕表
诚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面临选择”,也即我们总是被动地做出选择;我们只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就某事做出选择。但事实上,存在着我们主动去创造选择的情况。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著名结尾:“我觉得你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外出寻找他父亲的驴,却得到了一个王国。”显然,扫罗并没有“面临”着一个什么选择;他去寻找他父亲的驴乃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选择。扫罗如若不去创造这个选择,他就仍然可以稳稳当当地做一个“基士的儿子”,不过,他因而也就永远不会得到后来那一个意想不到的王国。
谷爱凌和菲利普·珀蒂在各自的16岁同时踏入了“新世界”。那一年,谷爱凌第一次拿下了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的金牌,而珀蒂也在一种莫名的感召下站上了马戏团屋顶那条摇晃的钢丝。珀蒂选择与恐惧平衡,谷爱凌选择与恐惧共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他们的王国。
谷爱凌对我说,在她初学滑雪加入太浩湖滑雪队的时候,只有一个类似玩具的手表帮她记录时间——那块小小手表所记录的时光与后来积年累月的动态力量,如今接棒到了她手腕上的那块 TOP GUN LakeTahoe上。這块腕表采用白色陶瓷表壳搭配黑色表盘,设计灵感来源于太浩湖的冬季景色及飞行员的白色制服。
谷爱凌说:“那么多看不见的部位才能做一块表,而我得转1620度,一度都不能少。”这正好可作为“创造选择”的一个注脚— — 那象征着“现代女性的多元力量”的1620度,并非来自上天的刻度,而是出于人类力量的创造。

在森山大道的镜头下,城市在褪去色彩之后,显得更加纯粹的光怪陆离。寂静的商品橱窗与外部建筑的影像交叠,隐藏在街巷暗处、眼睛闪闪发光盯着镜头的猫的族群,偶然闯入镜头构成超现实画面的行人,一些夜晚露骨却又奇怪的广告牌和人类脸部、手或者腿的局部特写。
60年来,森山大道从未停止在城市中的穿梭与漫游,带着他那台理光GR21。他的大多数摄影作品都是黑白的,对他来说,摄影原则上应该是黑白的,但是偶尔用色彩拍摄也很有趣。“黑白代表抽象和梦想的世界,而彩色则代表具体和现实的世界。”
城市被镜头肢解成为碎片,而在这些碎片中,仿佛都折射出森山大道自己。就如同他著名的影像犬一样,眼中闪着欲望的街头野犬,远看仿佛像一只黑熊一样凶猛的庞然大物,却是一只带着欲望,难以被征服,终日游荡在街头巷尾的野犬。野犬是他的化身,是他通过镜头看到的自己。而街道,就是他的居所。从大阪,到京都,到神户,到东京,他一直穿梭在日本土地上大大小小的每个城市和每个角落,一直都沉溺于在路上的状态,无法切换回现实。疯狂地按快门,用疾走的形式,走个不停,狂拍不止。而当他每次站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上,用极快的速度,按下快门,拍完一卷卷胶卷时,更多感受到的,是一场关于时间与记忆的长久探索。森山大道,站在某条街的某一个时间点上,试图去回望和感受这条街的痕迹、记忆以及过去。这条街有可能被覆盖,被拆迁,被炸毁,被重建,在人类欲望中被来来回回地毁灭与构建,但他只是试图捕捉这一刻的存在,以留下一个证明,倾听街道所讲述的过去的记忆,迎向即将来临的新的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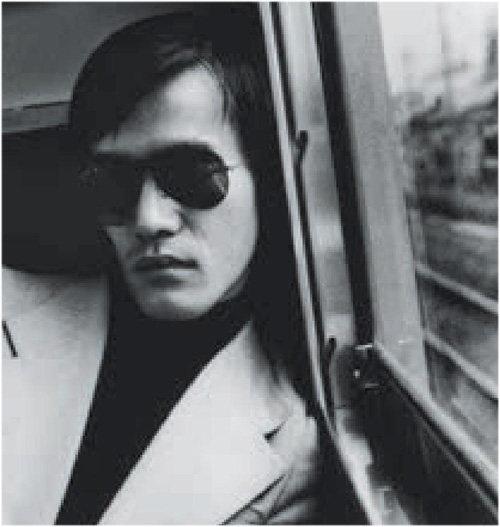
从森山大道的照片中,通常可以看到一种欲望,那并非是肤浅表层地在描述他照片中的红唇与丝袜、旅馆的一角与事后的清晨。而透过照片所呈现出来的欲望,是一种停不下来,想要把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相机的欲望,拍摄眼前的一切的欲望。对于森山大道来说,现实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个时刻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按快门的机会时刻存在。
活着与存在感,是森山大道影像不能逃脱的最终辩题。高反差感的照片,在视觉上强烈的冲击之外,给予人一种强烈的、急切地证明自己活着、存在的感觉。“当人们知道逝去的时光其实半点实体也无存,连想要证明自身存在过也无从着手时,或许会对人生如此无常抱有莫名的不安和恐惧吧。到最后甚至发现,连活在当下的实感都是那么脆弱和不定。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既不能一直维持活着的踏实感,又不能拥有一个确切的明天,可以说人终究只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生物罢了。”森山大道在《犬之记忆》中的某一章节,这样赤裸地呈现出对活着与存在的真实体验。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力去记录,试图留下活着的痕迹与存在的证明。
在森山大道之前,摄影是曝光在18%灰度的完美,色调要刚好,对焦要清楚,细节要体现。森山大道带着极端的影像出现在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摄影界,让摄影不再有约定俗成的定义。更重要的是,那些高反差、颗粒感、晃动、失焦的影像极其精准却无意识地体现了二战后日本社会的焦虑与不安。没有人知道将会走向何方,对战后未来一片未知的不安。这些诞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照片,放到今天来看仍然可以给予人巨大的感触,因为即使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就像一个循环,依然存在着战争与瘟疫,像巨大的阴影潜伏在暗处,时时刻刻都存在威胁,可以让构建了许久的城市与人类社会秩序瞬间坍塌。

“人们常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但我就认为没有一天是平凡的。 每一刻都是不可替代的时刻,永远不会再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捕捉眼前发生的一切。”森山大道不会停止,即使现在,他只是把在他眼前映射出来的事物拍下来,所以跟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看到街上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是一种很奇妙的景象,但这也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拍照片的时候就在想,应该现在就把这些都拍下来。”

看过INTO1赞多(以下简称“赞多”)表演的人,不会怀疑这个男孩是注定为舞台而生的。他五官清俊,个子高挑,额前斜斜一抹微鬈刘海,他的舞蹈表现力极强,即刻可以在乍起的鼓点下起舞,展现灵动的身体语言,甚至当他坐在观众席上,随着音乐微微律动,仪态舒展时,都有粉丝在弹幕里评论:“他的肌肉已经在跳舞了!”
赞多14岁时,就在日本东京举办的街舞比赛“DANCE @ KIDS SEASON7 JAPAN FINAL”中勇夺冠军,17岁拿下街舞比赛“STREET DANCE KEMPEUROPE”冠军并打破冠军年龄最小的纪录,如此佳绩和冠冕带来的光晕,很容易让人将赞多视为“天才”,而忽视他为此付出的努力。
回想最初是何时意识到自己喜欢跳舞这件事,赞多坦言,一开始并没有喜不喜欢的概念,“小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擅长运动,踢足球、打棒球之类的,而我没有太多运动细胞,所以选择了第二个方案”。从此,赞多把视线凝定在跳舞之上。与此同时,家庭成员在演艺行业工作的经历,也让耳濡目染的赞多从小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能做普通的工作。”后来,在聊天过程中,他和我们分享了另一个故事,他与朋友一起去算塔罗牌玩儿,塔罗占卜师看到赞多的第一眼就问:“你不是上班族吧?”得到赞多肯定的答复后,对方说:“OK,你完全不能像上班族一样工作,这样对你太不好了。”

沒有人知道这句话暗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赞多确实站上了舞台,用他的表演征服了大家。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赞多并不认为自己是有天赋的人。在他眼中,天赋显然是一种不知来处的馈赠,他目睹过许多有天赋的人,由此更加明白其间的差异,“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可以自己决定的”,见识过距离,才更加心意坚决地奔赴自己努力的方向。从最初踏上舞台到现在的INTO1,粉丝从三位数到现在的百万级,在跨越荒山与滩涂之后,赞多获得了自己的新天地。
与此相应的变化是纷至沓来的工作。“我没想到可以有那么多工作,出那么多作品。”过去在日本,90%的时间是赞多自己做饭,而今,几乎每天都是点外卖。赞多对这一切感到新奇,也倍感珍惜。压力大的时候,他喜欢吃中餐来排解。“吃串串。”一旁的工作人员补充道。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舞台。赞多享受站在舞台上的纯然时光,“注意力完全集中,听不见其他的声音”。那一刻,他在舞台上散发的光热仿佛形成了一个隔热层,所有与表演无关的思绪都被屏蔽在外。

当他受到邀请成为森山大道的摄影展“記憶· 記録”的艺术传播大使时,他想创作一个舞蹈作品,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用Freestyle舞蹈来表现。在此之前,他观看了森山大道的纪录片,发现他时时刻刻都在捕捉、抓取,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画面都会成为灵感切片,而当自己想到“记忆”这一载体时,则是苦乐参半,爱与哀混融的,这一切交缠在一起,促成了赞多的创作,所见即所得,他将看到森山大道作品的闪念与感受随机地编织进舞蹈当中,让它尽量贴近森山大道作品的气息。四五个小时下来,赞多完成了这一次酣畅淋漓的创作。
事实上,除了舞蹈之外,赞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技能,比如画画,比如B-box,比如打架子鼓。对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赞多来说,梦是不会停止的,他想做一些与舞蹈无关的工作,比如表演,比如模特,在内心深处,他渴望拍一部《La La Land》那样的歌舞片,他离这些念头并不遥远,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用努力一点一点换来的,就像编舞家林怀民曾经说的那样:“勇敢梦想,慎选策略,落实细节,走出困局,向上爬,往上走,高处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