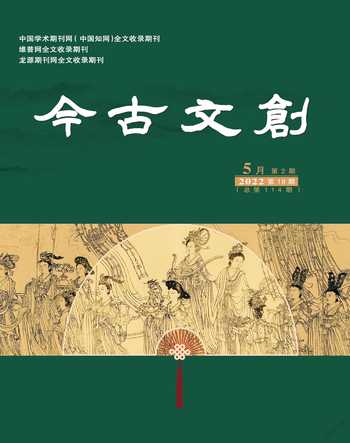福柯权力话语下《看门人》中的监视与刑罚
【摘要】《看门人》是英国著名戏剧家哈罗德·品特的一部三幕剧。本文通过对该剧独特的场景设定及三名来自不同阶层的男性的解析,来展现战后英国人民生活的困境和悲惨命运,更好地了解品特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政治主张。本文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通过监视与刑罚这两个概念,揭露批判了《看门人》中拥有绝对权威的上层监视者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变相刑罚,从而导致其被边缘化,被规训。
【关键词】《看门人》;福柯;权力话语;监视与刑罚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8-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03
一、房间——边沁全景式监狱的再现
福柯在《惩罚的结构》(1975)一文中巧妙地利用了边沁的全景式敞视式监狱来阐释权力的运作。这种建筑打破了长期以来密不透风,昏暗隐蔽的传统监狱模式。取而代之的构造是“四周是环形结构,中间是一座瞭望塔”的模式(《二十世纪》:262)充足的光线透过每一间囚室,每一名囚犯的一举一动都暴露的一览无余。与此同时,只需一名监督者站在中心瞭望塔,就可以监视整个环形监狱,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监视的效率。福柯认为,正是由于刑罚的可见而不可感知性才使得权力可以自动运转,使监视发挥最大的效果。
在《看门人》中,三幕剧的场景几乎没有转变过,一直都是阿斯顿住的一间拥挤的小房间。在第一幕中有对这个房间进行一些零星的描述,如:无法工作的烤面包机,坏了的插头,具有东方风情的佛像,床底下积灰的梯子,盥洗室里弃置的盆子、煤桶、购物车、割草机、餐具柜的抽屉等杂物全部堆在右边的墙角。被垃圾杂物塞满的房间就像“囚室”一样,给人一种无法逃离的压迫感。戴维斯待在房间里,就好像囚犯身处环形监狱中,无所适从。在第一幕结尾,当阿斯顿外出离开,虽然只剩戴维斯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时,他却没有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他开始在房间里四处游逛,一下悄悄地溜到阿斯顿的床铺边,一下又拾起一个花瓶看几眼,接着又摇晃几下盒子。通过这些细小无意义的动作行为,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不安。他不停地用警惕的目光扫视房间,重复开门,关门这一动作。开开关关的房门表明房间进出的自由性,就像阳光可以无障碍地透过监狱的窗户一样,给人一种看似自由,无人看管的错觉。但实际上被囚者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阿斯顿的忐忑不安正是源于权力的可见却不可知性。虽然房间里没有人,但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戴维斯依然感觉处于被隔绝和受监视的孤独状态。即边沁提出的:“在犯人身上始终产生一种有意识地持久的暴露感。”(《二十世纪》:263)有时候不可见性的监视比可见性的监视具有更大的威力。正如福柯在《惩罚的结构》一文中说的:“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出一种真正的征服。”(《二十世纪》:264)
与此同时,居住在旁边房间的黑人,也恰似生活在“监狱”里。黑人拥有极低的可见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超强的本领隐藏自己,而是以白人为主导的西方社会根本没有兴趣和精力去关注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可以逃脱白人的监视和刑罚,获得自由和平等。黑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比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戴维斯还要低。他们始终生活在白人监视的阴影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污名化,被边缘化。文中的戴维斯虽然属于社会底层阶级的爱尔兰人,但是他同样敌视黑人,通过言语暴力来惩罚黑人。文中没有直接出现黑人人物,但文中多次出现关于戴维斯歧视黑人的描写,如他对和黑人共用一个厕所流露出极度的反感,污蔑是黑人的呼噜声吵到阿斯顿休息,试图撇清自己的责任。对于自己这种污蔑行为,戴维斯没有任何的愧疚,阿斯顿在听后也没有任何为黑人辩驳的话语。在白人心中始终存在着优越感和刻板印象,认为自己才是规则的制定者,而黑人就应该逆来顺受,服从自己的领导。一方面,戴维斯是受到来自白人上层阶级监视的规训者,另一方面,戴维斯又是向黑人群体实施刑罚的人。这也正印证了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提出的:“全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即处于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权力是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控制的单纯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流动的网络。”
二、米克——西方权力话语下的惩戒者
作为一位成功的小生意人,弟弟米克在《看门人》中充当了权力的监视者、惩戒者的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刑罚的严峻性在不断减弱。古老的惩罚方式如刽子手砍头,五马分尸,游街示众,在面部和臂部烙印等直接残害肉体的方式已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十几年间,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惩罚的意识逐渐式微……作为一种公开景观的酷刑消失了。”(《规训与惩罚》:8)监狱的诞生使其以不同的方式实施,是因为刑罚的方式以一种看似更温和,更隐秘的方式呈现。“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规训与惩罚》:17)但是其对人造成的精神伤害,远比肉体伤害更难愈合。在《看门人》中,米克采取的语言暴力和无聊的捉弄游戏也属于后者。惩罚在现代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实施,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被中产阶级所掌控。(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11)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作为一名成功的小生意人,米克属于中产阶级话语体系,而四处流浪的戴维斯则属于社会下层话语体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沟通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困难。米克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对戴维斯施行言语暴力,以此来达到刑罚的目的。在第一幕剧的结尾处,当米克第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房间里时,就引得戴维斯尖叫连连,随后米克高高在上地坐在凳子上,对半坐着,蜷缩在一边的戴维斯发起攻击。他不停地询问戴维斯的名字,通过一连串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术语如:现金支付、过期支付、家庭津贴、红利计划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在第二幕剧中,当戴维斯回到房间时,房间的灯却意外的坏了。黑灯瞎火中,极度惊恐的他拿出火柴盒想要点燃火柴,却意外的洒落了火柴。在黑暗中摸索的戴维斯不知道对面的人是谁,有什么目的,而戴维斯的一举一动都被一旁的监视者米克看在眼里。随后,他故意用吸尘器制造出恐怖的声音,捉弄戴维斯让其出尽洋相,以此展示自己是房子主人的身份。米克在“明”处,戴维斯在“暗”处,米克处于主動地位,戴维斯则陷于被动处境。正如边沁提出的,权力应该是可见的,却又无法确知的。这样才能在犯人身上始终产生一种意识的持久暴露感,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发挥作用。(《二十世纪》:398)
与此同时,从剧中的描写几乎看不到亲情的成分。在与戴维斯的谈话中,米克称自己的父亲为叔叔的哥哥,流露出对父亲的不满与厌恶。对母亲的描写也只在第二幕剧结尾处阿斯顿的内心独白中闪现,并且是作为间接强迫阿斯顿接受电击治疗的负面形象出现的。尽管米克与哥哥阿斯顿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兄弟的感情也不融洽。受过电击治疗的阿斯顿丧失了正常人的行动力,只能捡拾一些废弃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弟弟米克认为阿斯顿所捡拾的东西都是无用的垃圾,他希望把房间装饰成软木橡树皮的地板,软百叶窗和蔚蓝色的地毯。米克代表了西方长期以来的形而上学思想,即以自我为标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以自己的话语体系为标杆来审视、监督、评判他人。品特通过米克这一人物,批判了西方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剧中最后一幕,阿斯顿在窗口看着戴维斯离去,留下了一个冷漠的背影。戴维斯虽离开了这一个囚室,但可以想象,處于社会底层的他只能去往下一个囚室。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权力作用的对象,现代社会没有单个的权力中心,而是分散在社会的各个地方,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
三、戴维斯、阿斯顿——西方权力话语下的规训者
品特出生于1930年,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品特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暴力因素与战争的硝烟。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品特在剧中特别关注边缘人物的遭遇。在其威胁喜剧中,品特大量描写了平凡生活中小人物的性格对立,权力的监视,情感的规训。刘明录在暴力、身体、记忆——品特戏剧中的刑罚书写与公平正义政治观(2021)中提到:“在品特的戏剧中,刑罚的对象通常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看门人》中的流浪汉戴维斯和精神病人阿斯顿都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如果说米克是西方权力话语体系中的监视者,那么戴维斯和阿斯顿无疑就是权力话语下的规训者。
在第二幕结尾处有一段阿斯顿的内心独白,他断断续续的流露了自己曾在精神病院被强迫遭受电击折磨的经历。阿斯顿的叙述中出现了大量暴力恐怖的词汇如大的拔钉钳、电椅、人头骨等。医生本应该救死扶伤,可是此处的医生不再是白衣天使,转而化成了暴力的恶魔,言行之中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无论病人怎么解释自己没有精神问题,不论病人怎么反抗,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受到在医生面前,失去了话语权的病人显得如此渺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到:“极端的疯癫从来很少与医学相联系。它也不可能与改造教养领域有关联。脱缰的兽性只能用训诫和残忍来驾驭。”医生以一种对待脱缰的野兽的残暴态度来对待病人,更倾向于把精神病人当作疯子而非病人,没有给予足够的同情,耐心和关心。但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极端的疯癫呢?这种绝对的判断权与其说紧紧地攥在了医生手里,不如说是由统治阶级掌控着。精神病院的医生就像全景式监狱的监督者,时刻监视着病人的一举一动。他对病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力,无论病人是否愿意,最后都无法逃脱被迫戴上头套,进行电击治疗的结果,精神病人沦为权力话语下的规训者。
《看门人》中另一位权力的规训者无疑是流浪汉戴维斯。十五年后战争遗留的创伤依然影响着他的身心。在文中他不止一处提到要去一个名叫锡德卡普的地方找昔日的老友拿回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但是他一直以天气不好为借口推脱,直到最后也没有采取行动。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遭受着来自他人的言语暴力和社会中无形的歧视,戴维斯已然丧失了行动能力,变得麻木自私。而没有身份证明的戴维斯在如今这个以“公平”法律著称的社会中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他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亲人,更没有尊严。没有身份证明就意味着尽管他生存于这个社会中,却没有在这套权力体系内,被正统排除在外,是一个边缘人。上文中曾提到可见性和不可见性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流浪汉的戴维斯在社会中的可见性是极低的,没有人会倾听他的心声,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同黑人一样,戴维斯也无法逃脱被规训的结局,他被阿斯顿收留回家,却难逃再一次流浪的命运。对于权力网络中的边缘人物来说,安定只是暂时的,而流浪却是永久的。品特通过描写阿斯顿和戴维斯这两个人物,深刻的揭露了刑罚的滥用导致了家庭的不幸,个人的不幸。批判统治阶层利用暴力摧毁人的自我意志,达到规训的目的。正如刘明录在战后英国的种族政治焦虑——品特戏剧《房间》中的精神疾病及其病理学分析(2019)中所说:“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人的存在方式是荒诞的,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左右,人与人,人与世界无法沟通。”
四、结语
品特的《看门人》这部荒诞派戏剧处处弥漫着权力的监视与刑罚。家庭的温馨被冷漠所代替;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信任被暴力所取代;不同种族之间无尽的猜疑和诋毁。刑罚以一种更微观,更隐形的方式发生着,在福柯的权力网络中,此时的受害者转身就可以变成加害者。利用不同的话语体系施加言语的暴力,通过对房间所属权的争夺排除异己,人们警惕地监视着他人,却也在无形之中被监视着。品特通过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塑造,表明人们之间沟通的无效性,将战后英国社会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在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1](英)哈罗德·品特.送菜升降机[M].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89,249,239,241,274.
[2]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4):84-90.
[3](英)安妮·施沃恩,(英)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M].庞弘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4]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艺评判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7](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陈怡含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8](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9]刘明录.暴力、身体、记忆——品特戏剧中的刑罚书写与公平正义政治观[J].外国文学研究,2021,43(03):146-156.
[10]刘明录.战后英国的种族政治焦虑——品特戏剧《房间》中的精神疾病及其病理学分析[J].国外文学,2019,(02):110-117+159.
[11]马汉广.论福柯的微型权力理论[J].学习与探索,2009,(06),182-187.
作者简介:
张莎莎,汉族,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