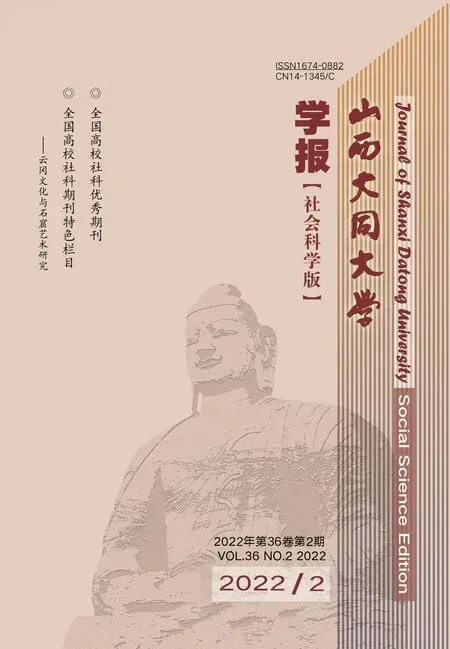北魏平城寺院题刻文化艺术管窥
陈俊堂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北魏平城寺院题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或隐而不传,或传而不彰,这种状况与北魏平城寺院题刻固有的价值不相吻合。北魏平城寺院题刻不仅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还因见证了北魏佛教、道教和北方经学冲突、交涉乃至契合的独特历程而具有较大的宗教哲学价值。北魏平城寺院题刻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的有意味的构型,更具有较为突出的书法艺术价值。文章通过对以下北魏始光、神、太和年间的三件题刻作品的探讨,试在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北魏平城寺院题刻的文化艺术价值,特别是北魏平城书法在早期、中后期的动态衍变过程。
一、始光年间的《魏文朗造像题记》
《魏文朗造像题记》(图1)成于北魏始光元年(424年),高约126厘米,宽约70厘米,厚约30厘米,为柱形扁平四面体造像碑,四面共计五龛。《魏文朗造像题记》发愿文正文约七十字,一些文字已斑驳漫漶,但多数尚可确切识读。该造像题记是目前所知的北魏时期最早的佛教寺塔铭刻发愿文,又因其成于太武帝灭佛之前的北魏初期,尤显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融佛教、道教于一碑,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佛道造像碑,堪称中国宗教融合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此碑为研究我国早期佛道演变史、书法艺术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1 《魏文朗造像题记》
第一,《魏文朗造像题记》收录了不少极富宗教文化特色的词语,为我国早期佛道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们先探究该造像题记中“佛道像”这个较为特殊的词语。就字面而言,“佛道像”即佛像和道像,但是结合北方民族史特别是北朝时期秦雍地区的地域和语言环境,“佛道像”释为“佛像”更为合理。据《魏书》,其有“澡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1](P3026)“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1](P3034)的表述,依上述文献的相关语境,“佛道”均释为“佛法”“佛教”,而这样的例子与释义在《魏书·释老志》中更不胜枚举,甚至在东晋南朝的文献中亦不乏例证,如东晋僧肇在《维摩经注》中认为“菩提,佛道名也”,[2](P167)又如《南齐书》卷五十四有“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3](P931)因此以《魏文朗造像题记》为代表的北朝时期的“佛道像”概念虽字面涉及不同教派,但一般应释为“佛像”之意。其次探讨原文“供养平等,每过自然”中的“自然”概念。“自然”本是出自道家的概念,如在道教经典《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它是较高层级的概念,是“道”这个核心概念师法和服从的对象。在佛教壮大而渐入中国之后,“自然”一词遂为佛教所借用,但是由于佛道两家对于“自然”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从而引发了六朝时期的“佛道之争”,但两家的论争却在无意中促使佛教的“因缘”说与道家的“自然”说在对立中走向了统一。这种统一的现象在北朝造像碑中数见不鲜,如佛教造像碑《北魏佛弟子解保明劝化上下邑子五十人造像记》中有“衣食自然,德如是”,[4](P115)而北魏晚期的道教造像名碑《吴洪标兄弟造像碑》中则有“依食自然,愿愿从意”,[5](P97)不同流派的宗教文献,却有相同的句式和用法,可见北朝造像碑中的“自然”与佛教、道教均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其解读的较大弹性正说明了《魏文朗造像题记》亦佛亦道、佛道一体的特色。
第二,《魏文朗造像题记》的书法堪为北魏早期的隋珠和璧。其字体为较为整饬的魏碑体楷书,其书写的整体风貌呈现粗朴率意、天真拙奇的民间书法气象。具体而言,此铭刻书迹在点画用笔、结体取势、章法布局等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特点。就点画用笔而言,该造像题记起笔、收笔多为棱角分明的方笔形态,刀锋盎然。如第一行“郡”字左半部,第四行“有”字,特别是第七行“平”字、第九行“切”字截直截方,简单直率。其中间行笔,坚定稳重又不失隶书浑厚朴质的意趣,如第一行“始”字、第二行“民”字、第五行“男”“造”等字。就结体取势而言,该造像题记字形注重构型变化,特别是借助形变、增笔减笔、点画部件错位等手段,取得了新奇的艺术效果,如第一行“地”字右半部分极大变形夸张,从而形成收放对比,又如第七行“平”字上边加增一撇,第三行“源”字左下部的点画省减,第四行“朗”字左边偏旁下沉而右边“月”字上提,形成点画部件错位,动感十足。就章法布局而言,该铭刻参差错落,不落普通魏碑书法板结均衡的窠臼,如第一行有七字,第二行有四字,第三行有八字,第四行有八字,第五行有六字……字数参差,且该造像题记字行呈明显的右上左下走势,极具势感。此外,该造像题记虽为铭刻书,也不乏书写的意味,甚至有行草书笔意,如第四行“文”字、第七行“过”字下半部书写的韵致较为突出,又如第五行“为”字、第七行“孙”字的笔画牵连相当明显,流动感十足。
二、神䴥年间的《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

图2 《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
第一,《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在一定层面拓展了北魏平城时期的佛教史料。首先,《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对史载或存世的佛教寺院史料有所增益。据《魏书·释老志》等相关文献,北魏平城建造的寺院共计15处左右,而《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的发现,不仅使北魏平城时期建造的寺院数量扩充为16处左右,而且因其建造的时间为北魏神四年(431年),故能使其和天兴元年(398年)始造的五级佛图等一并列为北魏平城时期建造的较早寺院,从而为研究北魏平城早期的佛教规建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其次,《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对北魏平城时期的僧人名录有所扩充。此造塔砖铭提及了当时的四位僧人,前两位是苴倩和昙云,他们翻译了大藏真经三十部并负责安稳放置,第三位是恬静,主管结塔营造,第四位是永慈,主管规劝化缘和书刻塔记。据《魏书·释老志》、《高僧传》、《续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广弘明集》、《律宗登谱》、《明代佛门教行杰望·律宗》等文献资料,北魏平城时期的僧人计有法果等33人左右,而《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的发现,使北魏平城时期的僧人数量扩大到37人左右。再次,《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译经史料有所增补。据《魏书·释老志》,北魏平城时期的译经,“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1](P3048)我们姑且根据地域把该时期的译经活动大致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鸠摩罗什、僧肇为代表的长安译经活动,第二部分是以昙摩谶、智嵩为代表的凉州译经活动,第三部分是以昙曜、吉迦夜、刘孝标等人为代表的平城译经活动。《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的发现,不仅使得北魏平城译经活动又增加了二人,从而扩充了北魏平城时期的译经队伍,同时表明苴倩和昙云的译经活动要比昙曜主持的著名的云冈译经活动至少早二十年,可谓平城译经活动的先导。
第二,《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使我们对北魏平城早期的书法面貌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此造塔砖铭成于公元431年,依照中国书法史,这应该是铭刻隶书应用乃至流行的时段,但该砖铭却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就字体而言,该作品整体彰显了楷书面貌。其字形外廓呈正方形而不是经典隶书的扁长形态,横画笔势呈左下右上走势而不是经典隶书的平横取向。就具体笔法而言,第三行“庆”、第五行“部”字上部的点已经由经典隶书的平横转化为楷书的点;第一行“二”、第三行“寺”“平”、第五行“卅”“其”等字的横画收笔处强化了顿笔技法,相应地弱化了经典隶书回锋收笔的特点;第一行“未”、第四行“大”等字的撇画尖端平出,相应地弱化了经典隶书翻转回锋而收笔的特点;第二行“级”“长”、第六行“太”、第七行“缘”等字的捺画体量由细小而粗大,其尖端平出,相应地改变了经典隶书捺画体量均匀的特点;第三行“昇”、第四行“真”等字的折画顿笔的楷法明晰,相应地改变了经典隶书折画回锋而牵连的特点。当然该造塔砖铭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过渡时期字体杂糅的特色。如第一行“朔”字左边开头两点、第二行“利”字右半部、第五行“部”字右半部等笔画的牵连,显示了较为明显的行草书笔法;第一行“辛”、第七行“永”等字的平头点,第三行“万”、第四行“昙云”等字的下部都残留了隶书笔法。就结构而言,该作品以工稳谨严见长,又不失书写的流动性。就章法而言,该作品能积字成行、积行成篇,既呈现平正端方的形式美,又不失局部灵巧的变化,如第五行“香泥”、“石其”等字呈欹侧舞动之势,与其它行列的文字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北魏早期书体的基本面貌究竟是什么?这一直是书法艺术史关注的一个热点。始光二年(425年),太武帝为造千余新字而下诏,诏文认为自仓颉始立文字,直到太武当世,“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甚至“文体错谬,会义不惬”,[1](P70)太武帝本意是为颁造新字寻找合理性,但该诏书却在无意中从侧面、从纸上确证了北魏早期多种字体并存杂糅的事实。而《魏文朗造像题记》《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以楷为主、杂以其它字体的面貌又从文献实物上印证了北魏早期书体的基本面目,这也正是这两件北魏题刻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所在。
三、太和年间的《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图3,图4)成于北魏太和元年(477年),据王壮弘考证,石出山东黄县[7](P234),塔铭呈圆形,阳面刻9字,阴面刻约80字,在清代有较多翻刻拓本传世。

图3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阳面

图4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阴面
第一,《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该铭刻书迹以文献实物的形式证实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地理幅员至少已达到山东光州地区。东晋末年,山东地区战乱相继,几易其主,义熙六年(410年)山东大部归属东晋,后武帝刘裕践祚代晋,山东大部又归属刘宋。皇兴元年(467年),北魏大将军慕容白曜率先平定齐、青等地,皇兴三年(469年)又攻略东阳城,山东部分地域遂属北魏版图,其时主要由光州等七州分辖而治。据《魏书·地形志》,[1](P2530)光州治所在掖城,皇兴四年析分青州所置,延兴五年改为镇,景明元年又恢复。伴随着北魏皇兴时期较大规模的攻伐征战,青、齐、光、东徐等地的士族名门被大规模迁徙到代北以充实京畿,史称“平齐民(户)”,大规模的移民举措,在客观上也把山东地区培育了将近六十年的南朝先进文化带到了平城地区。
第二,《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的书法价值不啻拱璧。首先该塔铭展现了北魏平城中后期较为成熟的楷书形态。该塔铭刻于北魏太和元年,此时北魏建国已逾九十年,北魏政权正处于冯太后和孝文帝一并掌舵的鼎盛时期,塔铭书法所展示的“成熟、雄强与王者之风”[8](P154)正是二圣比肩时代昂扬气象的缩影,同时也是该时代书法观念的投射。魏晋以来,传统的儒家文艺观受到了较大冲击,书法等才艺开始成为门阀士族彰显家族声誉和品藻个人才情的重要手段,士人以不善书法为羞耻,因此多聚家族子弟而秘密授习书法,于是善书者日多,家族之中甚至出现汲汲于书名艺名而鄙视政治功名的奇异景象。时至北魏,习书风气踵续,据《魏书》,“魏初重崔卢之书”,[1](P623)亦即北魏初期擅书者当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两世家。卢氏家族世代书业相传,每代都有能书者,卢谌的父亲卢志师法钟繇的书法,卢谌传授其子卢偃,卢偃传授其子卢邈,卢邈以上的几代人皆擅草书,特别是卢渊,精熟家传书法,多为京都平城的宫殿题字。而崔氏一门亦善书,其家族世代传习卫瓘书体而不改其业,崔悦传授其子崔潜,崔潜传授崔玄伯,特别是崔玄伯擅长草书、隶书、行押书,成为时人摹写的楷模。而《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的书法正是赓续并光大了魏初的崔卢之书,亦即钟繇、卫瓘风度。其塔铭阳面中部刻“魏光州灵山寺塔下铭”九字,规格类题额大字,为典型的方笔魏碑体,风貌逼似刊刻于北魏太和年间的《始平公造像记》。其铭文和格栏都是凸起的阳刻,这在传世的铭刻书法文献中并不多见;铭文的隶书形意几尽消失,笔画皆为楷法形神;另外,此铭刻直率方峻、沉浑遒劲、粗悍雄强,展示了金戈铁马般的壮美。就用笔而言,棱角尖锐,特别是点的写法多为三角形的几何形状,装饰性非常强,如“光”“州”“寺”等字的点画;横画多方切入笔,逆锋行笔,回锋收笔,笔势向两头上扬,如“光”“寺”“下”的横画;竖笔多以斜锐之法入笔、收笔,其中段浑厚略外凸,如“山”“下”等字的竖笔。就结构而言,字形扁方,上半部笔画茂密紧致,下半部则相对宽舒拓展,整体呈上紧下松之势;此外,字形抑左而扬右,右边呈居高之势。凡此种种,塔铭阳面的字形结构充满了多元的对比关系,极富艺术感。其塔铭阴面铭刻字数则相对较多,结合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中对于原刻石的描述和后世的翻刻本,塔铭阴刻为楷书,体态端方,古雅清劲,与南朝大明二年(458年)的《爨龙颜碑》气象接近。就用笔而言,塔铭阴刻笔势险劲朴茂,从容雄强。横竖笔画略呈方棱形排叠,整饬有加,形成了简单的形式美,如第二行“年”、第三行“王”、第四行“葛”、第五行“世”、第六行“悟”等字;捺画就整体而言,用笔由轻而重能以压笔平出,已与唐代楷法相埒,如第一行“大”“太”、第三行“八”、第四行“人”、第六行“合”“永”、第九行“文”等字。另外,此塔铭阴刻不少笔画残存了隶书笔意,特别是横画的收笔有波磔之法,如第三行“王”、第七行“苦”、第八行“英”等字主笔横画的写法就是隶法的残留。此铭阴有的笔画能化方笔为圆笔,圆润刚强,又显示了篆籀遗意,如第一行“元”、第四行“百”、第六行“眷”“界”等字通融宽舒。此铭阴就整体风貌而言,雍容典雅而又闲逸温醇,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南朝妍美一派铭石书法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北魏统治之前,山东大部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为南朝所属,其受南朝文化的浸渍化育自在情理之中。就章法而言,《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铭阴布局疏密得当,中间五行每行十字,其余每行四到八字不等,可谓参差错落,寓变化于齐整之中,均衡而不平均,极富布局之匠心。
结语
综上所述,以上三件北魏平城寺院题刻,作为北魏平城书迹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多元的文化艺术价值。这三件作品有助于我们在新的视角中审视北魏平城时期佛教与本土文化观念交融的历程[9](P74);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剖析北魏僧官体制、僧尼制度、寺院经济模式等一系列佛教制度,进而聚焦北魏平城这个佛教政治礼制最先中国化的区域;这三件作品更有助于我们解读北魏平城寺院题刻书法在不同阶段的嬗变历程,特别是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它和北魏洛阳时期多种形制、多种风貌的题刻书法的有机关联,进而使我们准确把握北魏平城寺院题刻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以平城宫遗址百年保护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