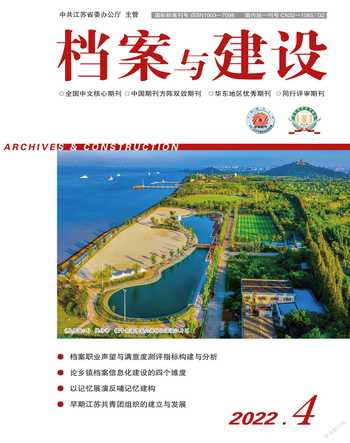忆江阴要塞策反工作(上)
仇英 唐大津 朱芳芳

我的爱人唐坚华(1924—1986),1939年在中学读书时,就随其堂叔(中学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地下党工作。1940年在新四军一支队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和抗大五分校学习。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毕业之后任新四军连队指导员。1945年调到地方之后,历任区、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他在解放战争中担任策反江阴要塞的政治交通员,参与创建了江阴要塞的地下党组织。
1947年春,唐坚华在上冈任副区长。中共建阳(今江苏建湖)县委书记树海派他到江南去從事地下工作,说:“上级党指示,要积极开展打入敌区工作。根据县里掌握的情报,唐君照的弟弟、你的叔叔唐秉琳在伪江阴要塞,他手里有兵权,派你去做他的工作。通过你的父亲(唐碧澄)找唐秉琳同你接上关系。”树海问唐坚华有什么困难,唐坚华考虑到自己是上冈的区长,面目是“红”的,如果被逃亡分子认识了,会有损于党的工作。树海说:“将全家搬到江南去,佯称是逃亡地主,以掩护你的工作。如果有人认识,就说是逃亡出来的。”并写了一封密信交唐坚华带给他的父亲,并嘱咐要绝对保守秘密。唐碧澄原任盐阜地区副参议长,于1946年秋天由曹荻秋和江华同志派往江南,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统战上层人士、待命而动。唐坚华回家做我的工作,要我接受树海对全家的派遣,明确提出要我沿途为他的工作打掩护。当时我在建阳县边区永丰区文教股工作。时值国民党疯狂进攻解放区,天天下乡“扫荡”,形势十分紧张。我们配合武工队、县总队在边区打游击,搞宣传活动,稳定群众情绪。我们常常到封锁线附近贴标语,主要是墙头标语,揭露蒋介石破坏谈判协定、打内战和蒋军的罪恶行为,宣传国民党不长久、共产党必胜,以及组织群众跑反,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等等。唐坚华认为,我作沿途掩护,一是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二是多一个人,可以多注意发现敌人的监视和盯梢,三是沿途买车船票、生活起居、吃住等都可以由我处理,他可以极少露面,少暴露。唐坚华还一再嘱咐,要绝对保守秘密,不要同任何人讲,他的母亲、弟妹也不行。唐坚华母亲长期在解放区,多次见过陈毅、黄克诚、曹荻秋、树海以及其他中共党政领导干部,听过不少革命道理,也是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不对她讲,只是要保密而已。既已定局,我服从革命大局,由树海向政府文教科长孙达伍直接调动。唐坚华的母亲、弟妹随后也搬往江阴,全家一起站在了对敌斗争最前线。建阳县副县长陆逵和粮食局长闲平批准办理了一万斤小麦,作为干部津贴和安家费。自此,策反江阴要塞起义的工作开始了。
唐坚华与唐秉琳接上关系之后,建阳县委考虑策动要塞兵变责任重大,决定上交苏北区党委。建阳县设宴为唐坚华送行,参加的有县委书记王大林(树海已调出),正副县长杨兆熊、陆逵,社会部长苏平,组织部长杨以希等。为了给唐坚华转党组织关系,盐阜地委的社会部长高峰在饭桌上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去苏北区党委社会部侦察科长江华处报到。后江华带唐坚华去见了曹荻秋、陈一诚、宋学武等人。曹荻秋一见到唐坚华,就笑着说:“碧老的大公子来了。”
唐坚华汇报了同唐秉琳见面以及他父亲的情况。曹荻秋、宋学武、江华都作了比较具体的指示:首先,要绝对保守秘密。区党委由宋学武、江华领导唐坚华,唐坚华与唐秉琳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其次,抓兵权,抓实力,做好中下层的工作。拉拢下级军官,团结可靠的人员,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待命而动。其三,如果有人认识,就说是逃亡出来做生意的。以逃亡地主、商人的面目出现,以“灰色”面目出现,坚守党的秘密。宋学武还强调,必要的时候公开身份可以抛一点,绝不能泄露秘密。曹荻秋、陈一诚两人各写了一封信藏在香烟中交唐坚华带给唐碧澄。从此这项工作由区党委书记曹荻秋直接掌握,宋学武、江华具体领导。
唐坚华的工作,我从不过问,保证保密性。要做什么事,只做不问,如收藏密件、通行证、黄金等等。家人之间,和唐坚华的父母、唐秉琳等见了面,也只谈家常。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连唐坚华十一二岁的小妹都知道注意周围的动态,看到陌生人或第一次看见的人都要注意打听这是什么人,房东家有什么人往来,有哪些人到唐秉琳家里去。每次往江南、回苏北之前,唐坚华都要对我交代一番:“要绝对保守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讲,包括家里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宁可牺牲自己,绝不能泄露秘密。”
我们六下江南,在敌区来去共十一趟,四次到达,两次受阻。
第一次是在1947年春,接受树海的任务之后,我们带了唐坚华母亲到上海找唐碧澄。由唐碧澄到南京找来了唐秉琳,在一个姓高的人家里与唐秉琳见了面(姓高的不知道何事)。唐坚华告诉我说,“这次(与唐秉琳)相逢,远远胜过往日叔侄关系的旧情。我正面阐述了来意,他非常高兴。这是同他正式接上了关系。我们还谈了革命形势,革命家常。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曹荻秋等同我们家庭都有过亲密接触,还谈了唐秉琳的大哥唐君鄂在北撤山东时牺牲了,是烈士。二哥唐君照是盐阜地委的组织副部长,三哥唐小石是射阳的县委书记。我的三个弟弟都随黄克诚部队北上……这席谈话更加坚定了唐秉琳的斗志和信心。这一次会见是可喜的,是有价值的,可谓揭开了策反起义工作的序幕。”
第二次是在1947年夏天。唐坚华和我在江阴唐秉琳家中,见到唐坚华的父亲唐碧澄和他的弟弟唐明,他们也已从上海来江阴了。唐坚华告诉唐秉琳,这次工作已转交到苏北区党委,并传达了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和陈一诚、宋学武、江华等人的指示。同时还研究了唐坚华全家迁往江阴的问题。这次唐秉琳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他讲到“老五”(唐秉煜)也在这里(蒋军中)。唐坚华很高兴地说:“好啊!叫他们也来(我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并答应了回去向宋学武、江华汇报。唐坚华曾说过,他“力争”“从速”解决他们的入党问题。另外,唐坚华向唐碧澄转交了曹荻秋、陈一诚的密信,唐碧澄也写了复信交唐坚华带回,仍藏在香烟中。从此江阴要塞地下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
第三次是在1947年秋天,唐坚华和我送唐坚华的母亲、弟妹一家往江阴定居。他们住在青果巷一幢四进大住宅里。唐坚华家住第一进,唐秉琳住第三进,第二进是房东住,后进是厨房和勤杂人员居住。从此,这里就成了掩护唐坚华在江阴的联络点。

第四次是在1947年11月。华中工委成立后,苏北区党委相应撤销,华中工委书记为陈丕显、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为曹荻秋、华中指挥部司令为管文蔚。仍然是宋学武、江华领导唐坚华工作。1948年1月,宋学武、江华通知唐坚华,经工委陈丕显、曹荻秋、管文蔚、宋学武等领导研究决定:同意他的考察意见,批准他去吸收唐秉琳、唐秉煜、吴文广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特别党员,由唐坚华作介绍人。宋学武、江华决定带五两黄金(是金条断开的四块)给唐秉琳作治疗关节炎费用。黄金藏在我特制的棉鞋里,左右各两块,穿在脚上。当时有一支部队要过江,插进江南,宋学武、江华叫唐坚华的父亲和唐秉琳准备火轮(轮船)夜间偷渡过江。后来唐坚华从工委回来说“不要了,部队不过江了”,和我到了江阴他父母那里。他和唐秉琳谈话后,叫我把五两金子送给唐秉琳。我送去,唐秉琳叫我送给四妈(他的夫人)。一个隆冬的夜晚,在唐秉琳的家中,唐坚华带领唐秉琳、唐秉煜举行入党宣誓。唐坚华对我说:“给他们(唐秉琳、唐秉煜)举行一个简单的宣誓,对他们是有教育意义的,时间不长。”我负责放哨,在一、二进来回巡视,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天气寒冷,几乎被冻僵了。入党仪式实际至少进行了两个小时。
第五次在1948年春。宋学武、江华指示,“这次作较长时间地留在江南,至少半年,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积极地进行发展工作,在有关部门安插和布置可靠人员,牢牢掌握住兵权。看样子大军快要渡江了。这次去的路线是从一分区过去,从东边走旱路,由交通站护送过江。要长途步行,准备简单的行李和换洗衣服。”我们从工委所在地射阳县合德镇出发到靖江,长途跋涉,通过重重封锁线,十分艰难。行程约一个多星期。当我们抵达靖江时,敌人突然天天下乡“扫荡”,老百姓家家忙于逃命,交通站自动解散了。我们四处漂泊,心急如焚,吃住都成问题。更重要的是情况不明,无法到达目的地。我们在那里等待了一个星期,仍不见好转,天天如此,只得又折回合德。
第六次,是回到合德之后,唐坚华向江华汇报之后,决定在合德装一船棉花假装商人从水路去江阴。此时已是1948年6月份了。途经泰州,被一些穿便衣戴袖章的敌人敲诈,抄出十几两黄金,扣押到一个警察所里。由于国民党中统县室插手,他们私吞了黄金,把唐坚华和我送到镇江中统江苏省室江照庵监狱坐牢半年。按照组织上指示的“以灰色面目出现”,我们始终坚持是“逃亡地主出来做生意的”,金子是祖上的遗产,拒不承认有任何政治活动。敌人没有抓到证据,组织上多方营救,终于于1948年底交保获释。出狱后,我们绕道无锡回到了江阴,和唐坚华的父母弟妹一家人,以及地下党的同志见了面。
我们往江南有两条路可去,一是水路,从西面二分区乘船前往;一是旱路,从东边一分区步行前往。
从西面去比较冒险,要“闯关”,要经过重重的敌据点、碉堡、哨所,还要防范出没无常的自卫队、还乡团、穿便衣戴袖章的家伙等等。老百姓做生意的一般都从这里来去。西路是一路水乡,有水荡区,在芦苇荡里要通行两三天。我们在那里行船是非常危险的,往往要好几十条船一起“打帮”同行,赶到一个村庄住宿。大家互相传话,“要跟上,不能落单”。十条船中可能就有八条会遭到水荡中土匪抢劫杀害,在那里遭杀害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的。有人说有些小舟是来打脚(探子)的,不能同舟上的女子答话。几十条船浩浩荡荡,似是一支水上大军。只听到撑船的水声,没有讲话的声音,大家配合默契,确有一派壮大的声势。每到一个村庄住宿,大家又紧张地互相叮嘱“不准上岸,夜里要注意动静”等等。进敌据点,首先要通过碉堡,戒备森严,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大家个个神情紧张,全神贯注地应对碉堡敌军的盘查。轮到谁都要先送香烟,说好话,主动塞钱塞物,运气好的查了证件放行。他们认为有油水可捞的,便三五个跳上船,扬言要搜查。这时要立即行贿,要送比较有分量的钱和物给头头,否则麻烦就大了。不仅人和物要扣押,甚至说你通“共匪”“替共产党买物资”等等,货物全部充公,人要坐牢。他们串通一气分赃,发一笔横财。每天都有一些船会受到如此遭遇。到各处车站码头都有哨所盘查看证件,住旅馆也时常半夜来检查证件。每次往江南回苏北都要经过若干次的盘查。真是深入虎穴,深感莫测。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无时无刻不在提防。
一次,唐坚华和我送他母亲、弟妹往江阴,伪装商人装了一船大米,已到沙沟码头即将出售。突然来了五六个穿军装的要搜查,声称要查违禁品。看样子是要大搜查了。他们拿着铁钎在船头船尾、大米中乱翻乱戳,没有查到什么东西。但是一个头头脚上穿着皮靴,接过铁钎,气势汹汹地要重查。唐坚华在船头和他們周旋,我在船舱里看势头不对,分明是敲竹杠的。这个家伙来到船舱门口,我未等他进舱,立即拿了三块银元塞进他的皮靴里,结果他什么也未查,带领几个人到别处去查了。还有一次,唐坚华和我在兴化的轮船上,突然来了十几个宪兵,对船舱上下层都进行搜查,还要看证件。那种阴森恐怖状态下,乘客紧张万分。火车站就更复杂了。一次唐坚华和我去火车站,我们站在远处隐蔽的地方环视了下,看到穿便衣的、穿制服的,腰间藏短枪、不三不四的人逛来逛去。还有一个女的穿一身美国式的黄军衣,烫发很长,面色苍白,可能抽白面子,逛来逛去,所有的人都避开她,就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不敢靠近她。唐坚华说这个女人可能是军统特务。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找了一家偏僻的小饭店,唐坚华在那里等,由我去买火车票。等火车快到站了,我们才进站,混在跑单帮的人群里,立即挤上车。以后我们不敢再坐火车了。长途汽车似乎要平静一些。
从东边去是一条长途步行的旱路。我们随身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和衣服。为了长途跋涉方便,又带了一匹小白马。我们轮流骑,交换休息,但我骑得多。唐坚华和我从工委所在地合德出发,途经龙王庙,在白茫茫的大路上前进。记得经过秋湖(同音)、双楼(同音)、一仓、二仓、三仓、海门、紫石县、靖江县等,途中要经过几道封锁线。交通站只护送过封锁线。沿途是无边无际的荒草滩和盐碱地,既无人烟,也无树木,满目荒凉。来往皆部队同志,三五人、七八人,也有一二十人的,有少数的地方干部,没有老百姓。沿途大家都主动互相打招呼:前面还有多远?到什么地方?有人家可住宿?同志加油呀!这些地方荒凉有土匪,不能掉队!等等。午饭之后,就互相招呼:同志,要赶快赶路!一定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某地方!太阳落山之后,土匪就要上来了!等等。每到一个地方,基本要急行军,才能赶到目的地。老百姓家里差不多都住了人,晚去的住宿往往比较困难,好的是大家都是同志,都主动招呼:“来!我们挤一挤”。沿途没有水喝,更无用水,三餐都是咸水,海风、咸风吹得皮肤干裂,口腔干燥发炎,鼻子不断出血。我当时有身孕,身体就更差了。皮肤、衣服、被子几乎都是湿的,脸上生盐霜。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很热情,帮助烧饭打地铺。老百姓都很苦,杂粮也吃不饱,生活极其简单,没有家具可言,锅盖是玉米秆子做的。大麦枧子、玉米枧子、咸菜、酱就是很好的招待,没有油,没有鲜菜。他们还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好的给你们吃,你们也够辛苦了。”麦草、玉米秆子打地铺,大家累了,也睡得很香。第二天清晨,大家都主动打扫干净,群众纪律很好。早饭后向主人告别,我们多给些钱给老百姓,他们总是不肯多收。一次我们赶到一个地方,看到一家门口有几个老百姓在吃饭。他们一家人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拿行李、牵马、喂饲料,为我们安排吃住。他们的生活很苦,除了一点不丰富的主食杂粮和草,别无其他。菜里几乎没有油,无荤无蔬菜,吃用水十分困难。
我们沿途到靖江要经过二三道封锁线。封锁线是敌人控制的一条交通线,有一条通行军用车的大公路,以及与公路平行的一条大河。由交通站的武装护送,约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由这边交通站护送过封锁线,那边交通站的武装迎接护送到站。交通站护送必须在夜晚进行,在封锁线两边必须各距离15里左右,行动才比较安全。一两个小时前放前哨。等天黑了很久,才能行动。不准大声讲话,不准有任何声音,脚步声也极轻,不准吸烟,不准用照明器。紧要时传话很轻。为了迅速过封锁线,必须跑步前进约各10里,即20里左右。过河的船准备好等待,撑船没有一点水声。我们几次通过都很顺利。我是女同志,已有身孕,站里特别安排了两个人照顾。在跑步前进的时候,基本是他们架着跑。一次一分区留守处干部科的李科长,特地前去交代交通站的同志要用担架护送和派专人照顾。我一再推辞:“派人帮助就很好了,担架就不用了。”交通站的生活既艰苦又紧张,吃的小米,常常饭不熟就催着开饭,一碗还未吃完就又出发了。好的是有一点青菜汤,当时青菜成了最需要的高级营养品。睡的是玉米秆子大通铺,被子自带。交通站离敌区都比较近。一次我们在三仓交通站,是个隆冬的深夜,突然枪声响起,交通站的同志报警,还乡团就在前面的庄子上,带领我们在流弹狂飞、子弹呜呜声中作了转移。我们长途跋涉,来到了靖江县,本应由交通站护送过江,很快就到江阴了。谁知敌人天天在黎明前就下乡“扫荡”,抓人抢东西,交通站就自动解散了。老百姓东躲西藏逃命都来不及,我们也无处安身,安全完全没有保障。而且在那里几乎言语不通。我们心急如焚,主要是为不能过江而焦急。我们在那里等待了一个星期,唐坚华天天奔跑找地方干部,最后地方干部说看样子最近不会好转,情况紧张,得不到情报,不知敌人是什么目的。因此我们只好又回到合德。
我们走的这条路线基本上是边区,是一种游击环境,群众生活不安定,随时要准备跑反。交通站也只是送过封锁线,过了封锁线各自前进。我们身上都有黄金、密件,主要机关又常常转移,为了安全和保密工作,唐坚华往往要跑好多地方,才能找到主要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安排我们吃住和下一站的行程,一天吃一两顿是经常的事情,半夜了才得以安排住宿。东路虽然危险性比西路小些,但也相当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