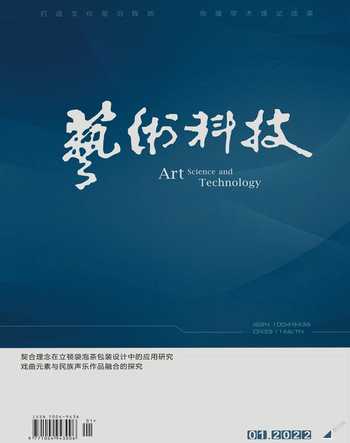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
摘要:人工智能改变了世界,在著作权领域,人工智能冲击了著作权中只有人才能创作的理念,因而产生了许多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具备著作权法的构成要件,理论上能够被认定为作品。由于人工智能缺乏人类理性,同时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故其为非法律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主体应为投资人,但同时须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对于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须在法律上建立一套规则体系对其进行规制,具体包括实施注册登记、构建侵权责任承担机制、强制署名以及适当限缩保护期。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可著作权性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01-0-03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其在交通、医疗、工业等行业大量运用。人工智能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在绘画、写作、作曲等文艺领域,人工智能都参与其中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享受科技带给人们的各种利益的同时,因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问题逐渐暴露在人们的眼前。
在著作权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并非对已有材料的简单拼凑,部分人工智能生成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与人类创作出的作品一争高下。在著作权体系中,作品通常会被认定是人类的直接创作物。但是人工智能系统被设计出来后,其逐渐脱离人类而独自生成内容,这对著作权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法学人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对著作权的巨大影响并积极进行研究,但目前依然有很大的争议。文章试图兼顾技术与法律,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中的著作权问题展开研究。
1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著作权性分析
1.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争议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构成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理论上存在巨大的争议。赞同人工智能生成物能构成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理由。一是目前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著作权领域也是如此,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也使文化领域的发展愈加繁荣。基于此,应当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具备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属性。二是人工智能生成物难以与人类作品区分[1]。三是人工智能冲击了以自然人为创作主体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为作品的判断应当淡化作品的独创性来源于自然人[2]。
有学者认为如果机械地将作品的创作者限定于人,则是一种人类将其自身作为高等智慧生物的优越感,而非基于法律逻辑的分析判断[3]。除了坚持认为作品之创作主体必须为人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人工智能在运作的过程中,只是依据程序设计者预先设定的模式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加工,在生成的过程中并没有创作的空间,其生成物之间具有相当的相似性,无法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化。而作品应当是作者的一种精神表达,人工智能却并没有精神思想[4]。部分学者主张以邻接权对其进行保护,并认为这样在法律上能使人工智能生成物有别于人类所创作的作品,又能维持著作权法的逻辑自洽。亦有学者主张人工智能并非人类,即便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为作品,也不能起到激励其创作的作用。
传统著作权法所坚持的只有人才能创作的观点已经难以回应现实的深刻变化。另外,《著作权法》第三条指出作品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为作品,应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是否为智力成果两个方面分析。
1.2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
作品的独创性含义本身并不清晰。19世纪出现了作者中心主义,其认为某项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需要从作者本身出发进行主观判断,后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支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者中心主义的弊端逐渐显露,部分学者开始从作品本身出发判断其是否具有独创性。此后学界逐渐承认作品并不以体现作者的思想情况为必备要件。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从关注作者逐渐转移到关注作品本身,有学者将其称为文本主义倾向。使用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这将影响到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被认定为作品。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应当采用主观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备独创性更为适宜,即要求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
1.3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成果属性
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为智力成果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在外部表现形式上,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人类作品存在相似之处。二者都能够以戏剧、诗歌等形式表现出来,都能够被人类认知和理解。从内部的运行原理来看,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与人类的思维逻辑相似。人类是通过感官来感知外在的事物并传至大脑,然后由大脑对感知进行加工改造,最后通过创作表达出来。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与人的思维逻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工智能将检索到的信息依照一定的逻辑来处理,最后生成创作物。人工智能对已检索到的素材进行加工,本身就是人类将其智力通过计算机程序等移植于人工智能,故其最后生成的作品实际上就蕴含了人工智能创造者的个性。
2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否定
2.1 人工智能缺乏人类理性
有学者主张人工智能具有獨立意识并且具有自主性,因此可以成为法律主体。但由于其担责能力有限,不能等同于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故其只能为有限的民事法律主体。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法律主体的范围逐渐扩张,法律主体不再仅限于自然人,故主张通过电子人理论来赋予其民事法律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上拟制的人。法人与自然人都具有人类理性,能够通过道德和利益来认识世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人工智能本质上缺乏自主意识,人类无法将只有有机生命才可能拥有的如道德等理性因素注入人工智能上。即便赋予人工智能以身躯使它成为机器人,在成为机器人之后,其可以通过劳动获取钱财并对外承担责任,但关键在于人工智能身上只有人类智力的烙印而无人类理性的烙印,人工智能只是由冷冰冰的代码程序组成的。
2.2 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
部分学者主张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一方面是认为人工智能在思维等方面与人类相似,另一方面是想通过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这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直接影响到其生成物的权利归属问题,因此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显得极其重要[5]。但是事情可能并非这些学者所设想的那样简单而美好。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日渐趋于完美,若是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则极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只有人才是中心,也只有人才能够居于主体地位。人类社会终究是人的社会,其他各种事物能够进入人类社会,但其终究不可能处于人的地位。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而言也仅仅是工具。
3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3.1 权利归属的理论争议
有学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到公共财产[6]。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实为不妥。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为作品的目的是保护隐藏在人工智能背后的人的利益。若归于公共财产,站在人工智能背后的人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并且在实际中,这种做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除了人工智能之外,人类依然会参与到创作中,此时或许可以通过区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创作中的作用来区分对待,或是将其一概视为人的创作物。但问题在于创作中究竟是人类在创作还是人工智能在创作,外界对此难以界定。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由设计人或使用者的创造性劳动生成[7]。故有人主张生成物应归属于设计人或使用者。将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作为生成物的权利人存在一定的困境。当人工智能从设计者转移到使用者时,使用者通过选定素材的范围和调校参数等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此时是使用者而非设计人有创作的意图。设计者本身既无创作的意图,又无设置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行为,此时不宜由人工智能的设计人作为作品的权利人。
另外,若是归属于设计者,其又会获得人工智能转让或许可创作的费用,因而出现设计者得到双重利益的局面。这忽略了使用人的利益,使得利益的天平无限地倾向于设计人。此外,使用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不大可能在无法取得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属的情况下向设计人支付费用,最终这种权利的归属反而不利于设计人。部分学者认为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于使用者不仅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还可以消除是机器辅助生成作品还是机器自主生成作品的难题。然而这种权利的归属同样存在问题。使用者虽然会有选定素材范围和调校参数等行为,但这些行为本身属于思想,其对人工智能创作的贡献在于思想方面而非表达方面[8]。
3.2 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归属于投资者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由创作者独立出资、独立创作的模式难以适应人们对精神产品的巨大需求。投资者出资,创作者为投资者创作,这种模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创作者的热情,也平衡了投资人与创作者之间的利益。
人工智能在创作之前存在一个极为复杂的被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如果没有资金的保障,而仅是依靠个人的热情来制作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就难以产业化、商业化。人工智能在创作的过程中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如计算机、文学等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有程序设计者的辛勤汗水,还有其他专业人员的参与。正是由于各个学科人才的全面参与,人工智能才能够创作出感染人类心灵的作品。而这些人正是由投资者所组织的,程序员和其他参与设计者都只在自己的专業领域内为人工智能作出贡献。但他们的贡献是分散的,都是依据投资者的指示按部就班地参与设计,他们的设计行为实际上是投资者意志的体现。故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归属于投资者,我国特殊职务作品的相关规定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当然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从当事人之间存在权利归属约定的情况出发,进而使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具有一定的弹性。
4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规则
4.1 实施登记注册程序
对于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网络登记规制其行为。人工智能是在利用已有素材的基础上通过加工改造创作出新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为此需要对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进行登记注册,以免日后出现纠纷的情况。
4.2 构建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设立人工智能生成物强制保险制度。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的侵权可能导致较大的损害结果。如果没有一种责任分担方式,那么就会严重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要明确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主体。如果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仅仅起辅助作用时,对责任主体的认定依然需要考察究竟是使用者的过错还是人工智能本身存在问题而导致的侵权。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仅由人工智能单独进行,则可以依据产品责任的原理,认定由人工智能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承当连带责任。
4.3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限制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期应当予以调整。现行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保护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作者死后50年。人类创作的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对人类作品予以大力保护会激励人们创作。而人工智能是在资本的运营模式下产生的,不仅设计人工智能本身所花费的时间短,而且人工智能创作的速度极快。因此如果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周期过长,会严重阻碍人类创作。毕竟人工智能凭借现代高科技,创作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就能创作出大量作品,致使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充斥整个市场,极大地压缩了人类作品的市场空间。
有学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周期缩短至50年,但笔者认为具体保护时间应定为多久,须结合人工智能本身技术的发展和其对人类创作的冲击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5 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普及,相关法律问题也将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但其与人类愈发相似,这使得对其处理问题的态度会产生明显的分歧。如何使法律处于一个变与不变的动态平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生成物急需著作权法的保护,法律应当回应现实的需求,在维持现有民事法律主体地位体系的前提下,将人工智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体系,构建一套适合人工智能的著作权法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 金春阳,邢贺通.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归属及侵权归责原则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21(9):73-81.
[2] 张晓萍,郑鹏.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独创性自然人来源的淡化[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6):106-113.
[3] 袁真富.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8(7):105.
[4] 曾白凌.目的之“人”: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弱保护[J].现代出版,2020(4):56-64.
[5] 朱凌珂.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路径与限度[J].广东社会科学,2021(5):240-253.
[6] 余翔,张润哲,张奔,等.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J].科研管理,2021,42(8):176-183.
[7] 李育侠.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的主体归属辨正[J].出版广角,2020(13):57-59.
[8] 李宗辉.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的正当性及版权归属[J].编辑之友,2018(7):80-87.
作者简介:朱明军(1997—),男,安徽芜湖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