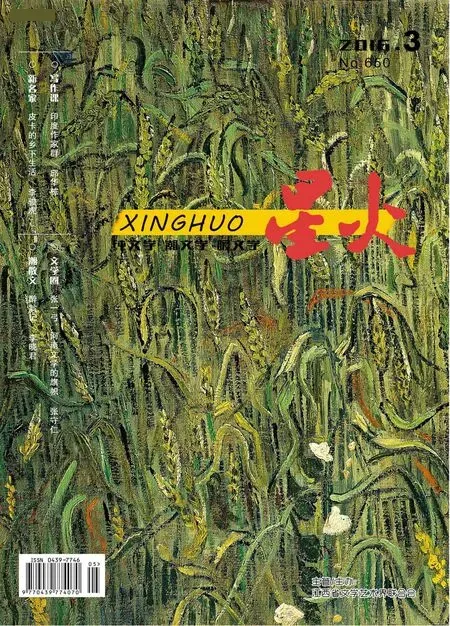失焦的身份
○指尖
初中毕业那年冬天,去林场上班。没有入职手续,没签任何合同,只是被领进会议室,在烟雾弥漫的人前亮相,之后住进三人宿舍。这种既满足,又担忧,既充满喜悦,又充满悬念的情形,让我在不久后,熟练掌握了在脸上敷一层浅笑的技艺,就像瓶子里的雪花膏,用指头将它沾到手心,两只手互相揉搓之后,覆盖在脸上一样。更多时候,甚至连假想都不需要,我的表情循着一条阴暗的专属通道,放大在父母脸上—虚构的笑纹,故意呲开的嘴,紧张而敷衍的语调,慌张躲避的眼神,生怕一不小心,戳穿真实与谎言之间那层薄薄的布幔。
一个月后回家,母亲说老师曾捎话来,让我回学校复读。当老师从同学口中听说我已经去工厂上班后,未发一言。课堂上,他对着四十五名应往届生新新旧旧的面孔,表情古怪:你们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的话,就不用好好学习了,但既然没有被工厂招工的可能,那给我乖乖听课做题上自习。
无人可知,虽有单位接纳,并成功掀开工人生涯的崭新一页,但身份并未发生变化,我依旧是那个落榜的初中生。之前我毕业回村,顺理成章加入青壮劳力组成的收秋队伍,但因对农事的陌生和笨拙,我被熟练掌握庄稼活的劳动力诟病,特别是比我年长几岁的女青年,对我的讥笑可以说是毫不掩饰。我在她们干净的布鞋,捂住大半个脸散发着浓郁洗衣膏味道的头巾,白色线手套中握着的亮光闪闪的䦆头上,看到她们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她们被承认了的农民身份生出无边羡慕。在家里,母亲像藏在门后的那个墨色自行车打气筒,不断在无人的场合,通过夸赞我能吃饭个子高和有力气,来增加我去做个好农民的底气。这段时间很短,不足五十天,我尚来不及做出一个庄重而热爱的姿态,来适应对农民身份的实践、接纳和最终定型,全村的田地一夜之间归各家所有。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农民工人干部还是学生,再无需去通过侍弄庄稼,挣得农业生产工分,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了大喇叭里催促上工的声音,没有了分粮食和交公粮时的你争我夺,大家变得无所事事,连那些农活老把式都闲坐在五道庙,一袋接一袋地吃烟,脸上交替呈现满足和失落的面具。
人们的想象中,我所在的工厂由无数厂房、无数工人以及无数庞大的机器组成,我和同事们穿工作服,吃供应粮,享受工作福利,出入车来车往。那几年我每次回家,都会有人来求证这种描述的真实性。我最好的朋友禾苗,就曾在言辞间委婉表达过让我带她到林场看看的意愿。我目光躲闪,言语嚅嗫,让她以为从小到大延续的友谊即将完结。事实上,他们只看到工厂表面的那层金光,当他们携带满身疲惫从青砖厂、耐火厂、玻璃器皿厂等民办小厂下班时,这层虚幻的金光在远空星辰般闪烁,他们同时也看见一个虚假的我,穿着流行款式的衣服,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办公,极其优雅地读书写字,谈对象,逛马路,潇洒地进饭店,在县城百货商场毫不眨眼地购置一条裙子和一双高跟皮鞋……所有这些,同时也在我脑海里呈现,我不能不说,那也是我渴望的事情。真实的林场,地处高海拔林区,周边除去靠近公路的管村,全是重重叠叠的高山,这里严重缺水,对于从小生活在温河边的我来说,很不适应。场院里有两口深井,一口已经干涸,另一口打出来的水,入口有微微酸涩的味道。师傅们的家,都分散在高山之下的那些村庄,他们吃旱烟,喝烧酒,他们的工作是上山栽树,蹲在苗圃育苗,带着砍刀和锯子去山间伐木,跟农民也无差别。除去每天和同事相处,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去管村供销社,认识许多管村人,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他们跟温河村庄的人并无二致,甚至更愚昧更沧桑更缺少见识。
同宿舍的两位女孩,比我大几岁,她们面临谈婚论嫁,身份问题更令她们焦急。我们当然不敢明目张胆找领导,憨直的师傅们对此又毫不关心,思忖了好长一段,我们最终决定去找会计,通过旁敲侧击,探听领导招收我们来的意图(他只是需要几个临时工?还是会跟我们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在那个满是痘痕的白面会计面前,我们显然还是太幼稚了,即便我们中年龄最大的那位,用极其甜蜜的声音喊会计叔叔,虽然他只比她大几岁,她还给他洗过衣服,打过毛衣,但最终,会计的嘴就像套了一只漏斗,过滤出来的讯息毫无用处。林场停电的夜里,我们坐在凳子上,被黑暗吞没。窗外,猫头鹰的叫声此起彼伏,那种似笑似哭的声音,源源不断传递着对苦难的恐惧。
作为食堂管理员,我每天的工作是将仓库门打开,让食堂师傅进去称足当顿的粮食,然后记在本子上。月末,我爬上单位汽车高高的马槽,去粮食局领回二十个职工的口粮。仅仅这点供应粮是不够吃的,据说前几年,林场通过跟管村村委交涉耕种了少量的田地,每年都能收割玉米谷物和油料作物,来补贴食堂,但后来管村把田地要回去了。场里只能在增加收入上想办法,于是开设了小料加工厂,通过承揽木工活和出售木料,来补贴和改善职工伙食。春节前,场里从河北购回一车粮食,一部分作为职工福利分发,另一部分补贴食堂。当小小的仓库被装满粮食的麻袋堆满的时候,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这也就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继续煎熬在通往林场正式职工的路上。
仓库快要空的时候,又过了一年。那个女孩已经二十三岁了,这个年龄,已算大龄,她对签订劳动合同一事开始绝望,动不动就请假回家,其间竟然还在太原当了三个月的保姆。偶然机会,县里的一个单位需要借调大量年轻工人进行城市区划,她被借调出去。在新单位,她的人际圈开始扩大,各种机会频繁出现。一年后,借调结束时,她如愿嫁入一个城市户口家庭,并通过婆家的关系,彻底改变身份,成为化肥厂的正式职工。两年后,另一个女孩效仿她,通过借调,也将身份改变。
一架照相机适时增加了我身份的砝码,稍稍安慰了我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单位请了师傅,配置了暗房和洗相设备及材料。那段时间,每次按快门前,我的右手食指总是犹豫迟疑,无法将黄色焦点跟相框里预设的那个点准确重叠,这就导致十二张照片里,差不多有十张是失焦的。在暗房里笨拙地冲洗着模糊的相片,失败加失败,浪费着单位的材料,但并没有因此被教训和谴责,让我徒生幻想:莫非自己是被单位承认和接纳的工人?
林区的冬天来得早,中秋节后第二日晚上就起了霜,管村的庄稼来不及成熟就上冻了。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场院里,看门的黑犬懒散地瞟了他一眼,依旧将头趴回前蹄。他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师傅,回来办理病退手续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许多人都看到师傅装在牛皮纸袋子里的档案,一张工资表格,一张裁成窄条的介绍信—由县劳动局开具的就业介绍信,这两张纸,是证明他身份的重要文件。
我最终也选择借调这条路。
我走的那天,新招来的两个女孩兴高采烈,她们用临时工的身份,住进了我的宿舍。
借调之路充满颠簸,我就像坐在一辆快散架的三轮车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借调函上印刷着的单位名字,鲜红醒目,高大端庄,让人心跳。显然,命运是想给我最好的那个,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领导,最好的同事,甚至最好的朋友。它就像一颗绚烂夺目的钻石,绽放着尊贵明亮和快乐的光芒,而我,十七岁的我,在它面前更像一张薄薄细细生锈的铁皮。
在省城那家文化单位,即便三十多岁胡子拉碴,他也被喊作小王。跟我一样,他也是借调人员,我们一起被分到审稿办公室。但没有稿子。办公室有一个书柜,里面稀稀拉拉放了几本文学名著,每天打扫完办公室,我都取出一本书,《白夜》《罪与罚》《白痴》或《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书柜更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用展览柜,只要打开它,看不见的不幸与悲苦便会从书页中扩散。一直到近午时分,阳光穿过对面新建的高楼与高楼之间的缝隙,极不情愿地洒射到我手中的书页上时,小王才回到办公室,通常满头大汗,像是刚刚从蒸汽房里跑出来般,即便外面下着大雪。我从不好意思主动开口问他,而他在我面前也保持着矜持和尊严,不愿打破我们之间厚厚的陌生壁垒。直到有次我下到一楼收发部帮忙,才知道,原来小王一直被下面这些正式人员差遣。
收发部全是未婚的女青年,她们目不斜视,脸上挂着天生的傲气,喜欢抬头挺胸走路,喜欢在办公室吃早餐,她们无一例外都骑着那种没大梁的小自行车,她们的聊天内容不是电影、流行歌曲就是舞会。有次我下去的时候,一个女孩正在教另一个女孩跳华尔兹,随着脚步的移动,嘴里还发出好听的嘭查查嘭查查的声音。那时候,小王就站在成堆的邮件后面,脸上带着一层虚幻的笑意,由于脖子伸得太长,整张脸突兀地浮在空中。不久,就有人喊他,让他帮忙去擦洗自行车,这声不容置疑的喊声,似乎提醒了其他几个人,她们纷纷从抽屉或者包里拿出自行车钥匙,连跳舞的两个也暂时停下,将钥匙找出来,交给他,他似乎很乐意效劳,笑嘻嘻端着脸盆出去了。
另一天,一个女孩迟到了,她气鼓鼓地抱怨,单位门口建筑材料太多,将自行车车胎扎破了。小王呢?她的目光环绕办公室一圈,没找到小王,就推开门,朝楼道里大喊:小王,小王。我第一次听到平时细声细气的她居然有如此高亢粗放的嗓门,跟我想象中文明的省城青年身份极不相称。小王被喊来,他当然是那个替她补胎的人。揣着带着女孩体温的两毛钱,推着自行车出单位院子,向东走不到一百米就是修车铺。那女孩从靠窗的抽屉里取出一块布,很认真地擦皮鞋,洗净手,又拍打了裤腿上看不见的尘灰,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饭盒,里面是她的早餐,半饭盒牛奶和一个五仁月饼。她的吃相文雅极了,掰下一小块月饼,沾一下牛奶,小口咬下,闭着嘴巴悄无声息咀嚼,给人感觉那块月饼对于她来说更像一座大山。这样过了很久,我已装了近五十个信封,她才吃完。吃完又一阵清理,漫不经心地说,小王怎么还不回来呢?人们抬起头,看着她。一个说,是啊,这次够久的了。另一个说,估计修车的人多吧,会不会骑你车办事去了?还有一个说,借调的人,跟咱身份不同,以后还是小心点好。说完瞟了我一眼。
小王回来还钥匙,女孩脸上带着厌烦和埋怨的表情:让你补个胎,要这么久啊。小王弓着背讨好地朝她笑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我看见那女孩正蹲在自行车前端详。别的办公室同事问她,是丢东西了吗?她对着她们摇摇手,嘴里说没有没有。只有我知道,她是在怀疑借调人员小王,是不是偷了她自行车的零件。
我遇见一个老乡姐姐,她已完全忘记了家乡话,一口省城话让她成功而骄傲地证明着自己作为城市人的身份。她好心送给我少量的饭票和粮票,好像我是个衣衫褴褛一穷二白的乞丐。一个成年人的目光,总是犀利的,或许,她隐约能看到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呆坐,不敢在周末出门,怕遇见小偷,怕城市纵横的街道,怕找不到回宿舍的路?她也看到我在其他同事面前的卑微和心虚,看到我的煎熬?于是,一个星期天,她带我去看电影。影院门口,她遇见熟人,一个穿风衣头发微卷的高个子男人,她跟他在那里聊得热火朝天,男人仰天大笑,她捂着嘴回应,直到电影开演很久,他们才分开。我听见她告诉他,小姑娘是个农村小老乡,带她出来见见世面。
借调者的身份,原本就是尴尬的。我成为一个双面人,一面是经历过的、记录并总结的过去时光,带着自我气息和喜好的旧事物,一面是崭新的,白纸般的,毫无经验的当下,不被接纳,如履薄冰,因缺乏足够的信任,无论做得好与坏,都无法令人满意。
进入冬天以后,淋淋淅淅下起了冷雨,常常是中午开始,一直下到傍晚。早上起来,雾蒙蒙阴冷的天空让人绝望。那天,小王跟我坐在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黏稠的沉默在我们之间涌动,他吐出的烟雾,罩住了他,先是脸,后来整张身体都看不见了,要不是他掀翻报纸的声音,我还以为他被烟雾卷走了呢。后来,他从烟雾中走出来,站到窗前,外面的雨水渗入窗框,凝成一个椭圆形的雨滴,沿着玻璃滚下来,最终,啪嗒一下,掉在窗台上,碎纷纷。他转过头来,声音沙哑,对我说,我们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他明显的外地口音,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别扭,而他眼里闪动着的,像泪水的东西,让我忍不住低下头。
其后几年,我先后被三个单位借调过。托付是一个很理想的词,可是,托付也是一个最无情的词,它使物种生出一种理直气壮的悲壮理由,得以消弭而不受指责。而所有人的借调生涯,这种模糊身份的经历,便是一场托付。
我最终离开了省城,这块遍布亮晶晶钻石,到处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车窗外,山桃花在颤巍巍的春风中抖动,像一团又一团拥挤在一起的笑脸,我灰头灰脑,满怀忧郁,怀抱大大小小的豁口,贴着那一张张笑脸,原路返回。
我像一根刺,尖锐而锋利地支棱着,露出丑陋的顶端。妹妹们毕业分配,直接进入机关单位上班。家里五口人中,四个人已成功拥有了市民身份。很多时候,我明明跟他们坐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洗衣服,但还是感觉到被什么东西隔离在外,像一个游荡着的孤魂。有段时间,我刻意不回家,好像被他们遗弃了般。这种萦绕不去的孤独和自卑,让我日渐忧郁,愈发沉默,独来独往。我家从温河边的村庄搬走,家里退还了三个人的口粮田,河边,只剩下一溜窄条的田地,长满蒿草,那是我的。稍微值得安慰的是,因我的身份,我家逝去的几代先祖,得以在荒草萋萋中安眠。
后来被单位招来的那些临时工,显然没有我这般耐心,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对遥遥无期未来的期许,快速离开单位,去往其他地方,寻找尘世上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一批又一批临时工走马灯似地晃来晃去,带起一堆又一堆燃烧的小火焰,烧灼着我的内心。就在我极其灰心的那年秋天,单位启动了招收农民合同工的工作。
我正在县城的另外一个借调单位上班,那天巧合有下乡采访任务,我去请假,领导稍显不悦。我狂奔到汽车站,买了最近时刻的一张车票。面对终于等到的机会,我并没有很激动,好运稍纵即逝,我只是不想错过。我一生中很少有激动的时刻,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性格中有某种强硬而理智的东西。但我知道,远非如此。许多年之后,我生命中发生过无数本该激动人心的事,但我都平淡对待。是的,或许你也猜到了,那些迟来的幸运,与我并没有恰到好处的缘分,太多时候,它们更像上天不忍目睹你成倍的付出和努力付诸东流,而对你的最后恩赐。那天在公共汽车上,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同时我很清楚,即便签订了合同,我的身份只不过从临时工变为合同工,前面还有醒目的两个字:农民。签订期十年,这也就意味着,我有十年时间,拥有工人的身份和待遇,也有十年时间,有机会转为正式工人,最终获取一个市民户口,并有机会离开荒芜的林区,在县里享受财政开支的单位间实现真正的调动。
希望从来都是赋予不言放弃的人的,而时间中,我日渐迟钝,不断涌现的锐利悲伤,被无数虚假的自我安慰所取代。这时候,同龄人大都结婚生子。借调单位的女同事,从不忌讳在人前挤奶,关于婴孩的话题,在奶香中展开,一层又一层,浮在办公室白茫茫的屋顶。父母开始焦急,为我张罗对象,他们给出的条件是,对方最低也得是一个农民合同工。不久,叔叔领着一个人来家里,那是个无父无母的河北青年,标有煤矿正式工的身份,听起来比我高级。他坐在小凳子上,低着头,我从里屋出来,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推门而去。那天,我在外面逛游了好久,遇见一个熟人下班回来,她问我找对象了没,我摇摇头。她说,以你的条件,一定能找个满意的对象,比如煤矿的正式工,县城周边村庄的农民,或者当兵的。我一个人站在河边,泪水不争气地涌上来。身份就像一个标签,而每种标签的位置和排序都是不同的。
在某个工作场合,我顺利完成采访任务,主办方的女领导对我的表现极其满意,不断夸赞,从外表到工作,仿佛我是这世上最完美的存在。她听说我没成家,便无比热心,一定要为我介绍对象。我笑着跟她说,自己是单位的借调人员,而且身份是农民合同工。她略微尴尬地看了我一眼,话题突转,打着官腔,重现高高在上的神情,完全忘记之前说过什么话。告别的时候,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我也有认识单身男孩子的机会,但那些男孩无一不是干部家庭出生,对农村人有天生的鄙夷和冷淡,即便他们的老家也在农村,即便农村有他们成群结队的直系亲属。好在,这世上,也有不嫌弃我身份的人。两年之后我结婚了,他家是县城的干部家庭。“老天不杀苶汉”,小时在村里,人们总爱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上天会怜惜那些苦难之人。
蓝印户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父亲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我记得那个上午天气特别热,银行取钱的人出奇地多,大家的汗水,不断从额头冒出,又不断被手或者袖子擦去。排队的人,都是陌生的面孔,在那一刻,却结成坚实的同盟,共同拥有一个略显拗口的身份。父亲找了银行的熟人,我们最终插了队,才取出钱,之后一路小跑到了公安局,那里同样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是那天上午最后一个办理手续的,父亲把厚厚的三千块递过去,换回一张盖着蓝色印戳的户口证明,满头大汗从人群中挤出来。父亲喜笑颜开,这下好了,我娃再也不是农业户了。
蓝印户口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单位直接转正。我终于成为林场正式工人,距去林场上班那年冬天,已经过去十年了。没想到,蓝印户口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我的孩子。当时政策规定,孩子出生,户口随母,也就是说,我的身份决定着孩子的未来。因为我身份的改变,他顺理成章享受各种免费疫苗注射,职工幼儿园入托,县城实验小学上学,并顺利升为县城第二中学的初中生。倘若我不改变身份,无论幼儿园还是小学,他不止得交纳高额学杂费,而且有可能被同学们孤立嘲笑。所有这些由身份带来的好处,让我欣然。来年,红印户口实施,我毫不迟疑地借钱,将户口本上那个刺目的蓝印转为醒目的红印。
这段时间,我也彻底结束了借调生涯,终于调回县城单位。就像小溪终于汇入大河,因为没有了突兀的标志,我更加享受那种融入的感觉,低下,再低下,做红尘中最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尘粒。
失焦的身份最终聚焦的一刻,发生在二十年以后。单位档案室老式绿色铁皮柜里,我尘封的档案被取出,想象中它早已被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侵占了。事实并非如此,它崭新得像从未被触碰过般,且隐约散发出纸张的香味,让我联想起小时候书本的味道,那种缓慢持久地通过鼻息注满内脏的欣喜味道。
档案管理员跟多年前的我一样,工作关系在林区,因为要照顾孩子上学,借调到局里上班。我从未跟她交流过借调的感受,显然她并不在意这个身份。时过境迁,许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她已不用为孩子的户口和学校问题苦恼了,县城的小学有六个之多,她只要选离家最近的那个即可。学校里,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们可以跟随父母任何一方上户,可以是农业户,也可以是市民户,这对他们的将来上学就业嫁娶没有任何影响。而档案管理员,也不用因为是借调身份而更努力工作,没有人排挤她,也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她无须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无须刻意去讨好哪位领导,她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即可。身份似乎成为一个不再重要的东西。但似乎又不是,对于那些拥有万贯家财的人来说,他们的身份显然比普通人尊贵得多,在银行和消费场所中,甚至来我们单位办审批手续时,他们受重视程度明显优于普通人。
之所以提取自己的档案,是因为我要办理退休手续。档案管理员不无感伤,皱了皱刚纹过的眉,叹几口气说,怎么就到了退休年龄呢。财务室的同事在计算我的退休金,遗憾我的工龄没到三十五年,退休金比例无法达到90%。还有个同事不解地问,你怎么不走职称?那样的话,还能多上好几年班呢。所有的问题,我笑而不答。
早在二十年前那个终于转正的日子里,脱离更改身份带来的忐忑和纠结就成为我最大的愿望,我不想再低下自己的头颅,给任何一个单位、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赔笑脸,说好话。只有办理了退休手续,才能真正证明我曾经拥有过正式的工人身份。于是,我规避聘用制干部和技术职称评定,选择了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的身份,参加技师全国统考,顺理成章自动套入工资级别。我一直记得参加高级技师培训那年,跟同事住在她朋友家里,起早贪黑地看书背题。临考试那天早上,为保证考试通过,同事在手腕手臂上,写满了答题,我们胸有成竹进入了考场。没想到的是,同事被排在第一桌,她跟监考的两位老师面对面坐着,根本没有机会撸起袖子。更没想到的是,同事那天穿了一件呢子大衣,大衣的袖子太紧,即便监考老师允许她作弊,她的袖子也卷不起来。就这样,她端坐在那里,脑子里天马行空。这事成为我们后来的话题,也成为笑话和噩梦,好在几年后,退休前夕,她终是通过了考试。
我的档案袋,比当日林场师傅的档案袋要厚,里面有初、中、高级技师复印件,有历年的调资表,有入党材料,有农民合同书,当然最重要的是调函,半张纸,半个褪色的印戳,却聚焦了我一生终将呈现给世界的东西。
劳动局退休股办公室里,十一月的阳光,明媚得像小姑娘的笑脸,又暖又甜。办公桌后面,是一个熟人。这么多年同处县城空间,一日日出来进去,彼此的面孔逐渐熟悉,后来不知不觉开始打招呼。她一见我,极其热心地招呼,并用纸杯倒了一杯开水放到我面前,才问我是给谁来办退休手续。当她听说是给我自己的时候,惊诧了半天,乃至大呼小叫地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办退休啊。后来,她拿过我的档案,开始查看里面的文件,“认识这么多年,我居然在你退休的今天才知道你在那里上班。”我们同时笑了,明媚的阳光,闪闪烁烁,打在我们身上,出现一些水形波纹,那是对面高楼玻璃的反光。
我把她开出来的一张证明个人档案已交回的收条揣在兜里,无比轻松地下楼。
大街上,车水马龙,两个圆滚滚的妇人,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边说笑边从身边走过。想到此后我也可以像她们一样自在无忧,一种轻松袭上心头。而同时袭上心头的,还有白茫茫的空虚。我用三十年时间一直在证明的个人身份,此刻,重又模糊起来,像从枝头上飞落下来的一片叶子,在头顶轻飘飘地晃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