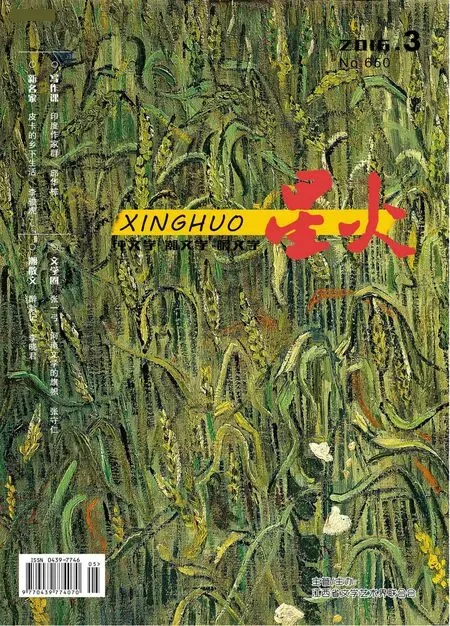寂静之声
○冯秋子
如愿以偿,2003年10月,我去了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集中营遗址,这是1938年纳粹建于德国本土的集中营之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诺因加默集中营关押的囚徒达106000人;至德军战败撤离的这段时间,囚徒死亡过半;在集中营运行的最后几天,即将迎来解放的黎明前黑暗中,约有17000名囚徒死亡。
在地图上找到S21地铁,找到目的地公交车站Bergedort,我就上路了。
我和同伴三天后将离开汉堡。今晚,汉堡市坎普纳格尔剧场举办的“公共空间与个人视野—中国的新视野”艺术节停演。明晚,我们继续演出舞蹈剧场作品《身体报告》,这是这部作品的第五场演出,也是最后一场。这届艺术节,我们演出两部作品,前面的《生育报告》也演了五场。
有一天时间休息,我想去看诺因加默集中营遗址。
结束上午的写作,出门已是午后。乘坐地铁,用去一小时。地铁露天行驶时,看到大烟囱、工厂,还有农田、村庄,这是二十多天里,第一次看见城市外面的世界,有点兴奋。尤其看到农村,由衷欢喜。
换乘大巴。向司机打听,我要去某某地方,需要乘坐几站?重复了好几遍,已经不抱希望对方能够听懂。他问,是去……吗?我说是的,没错。他说再坐15站。定顿半天反应过来,他确实说了15站。还有15站,这是始料不及的。但事已至此,别说15站,即便25站,只能顺应,继续往前走。
若不是当天需要赶回驻地,真想在附近哪个镇子住下来,好好看一看那里,看看小镇上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这天是周六,人们会去酒吧聚集,聊天,饮酒,喝茶。他们关注些什么问题?年轻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当年集中营里发生的事,老人们还有多少记忆?平时会不会谈论那些话题?生活在集中营边缘区域,后辈人的生活、思想和心理有没有受到影响……有的房子旁边或者房子下面,停泊着汽车,每家设有车库。他们有人在汉堡工作?交通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可以自己开车,可以坐地铁,再换乘一两趟大巴。与我同路的不少人,就是这样走到某一个地方下车,回家。从衣着上看不出他们与汉堡的人有什么不同。车上有四个小学女生,有一个提着一只大提琴盒。那个黑人小姑娘,有点特别,长相标致,是那种修长的、正开始发育的身条,脸型有点像惠特妮·休斯顿,内秀而专注。但她少有小孩的童稚,她的目光和表情是成年人的,分布着疑惑,她自己没有特别意识到,举止仍是一个小女孩,只不过比同龄的孩子显得老成持重。我想,待到长大,甚至年老的时候,她的变化可能比较小,也比较少,她比别的同龄女子会更显年轻。我不知道是谁造就了黑人小姑娘这种成熟的质感,其实她没有成年人的哪怕一个动作,没有那种长成的少女对别人的留意,没有想到吸引别人的目光而把自己和别人联结起来的意识。她灿若天使,世事的踪迹不曾在头脑里停留过一般,从内向外既平常又稀缺地金贵。她心里清楚的,除了自己是一个黑人女孩以外,其他与别的女孩一样,但她明显比别的女孩清越,富有意味。世俗经验里有不少女孩,越往大长,越容易走样,这个女孩是紧凑的,也许她会是那种不大容易散失本真与形状的女子。
下了车,四周无人。我想,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怎么没有一个人呢。放眼望出去,除了一条公路,两旁是树木和田野,没有别的。我选择往前走。走,才有可能知道选择的是对是错。很多时候,我感到两只脚的意义重大而深远。脚力,在某些阶段,比别的办法可靠。
走出三四百米,看见左侧路基下停着一辆装运垃圾的机动车,几个打扫卫生的工人正在忙碌。我向司机问路,他说,就是这里。他指着前面大片的空旷场地说,这些地方都是。面前有两条路。我该走哪条路呢?他说,两条路,走哪条都可以,哪条路都对。我用英语,他用德语,外加手势,我们把一排话硬说得不差什么了。我选择其中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走向旷野深处。
这处纪念遗址五点钟关闭。
草丛里有一些雕塑。这是纪念地的中心区域吗?想象这里该有一所房子,展出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我前后左右观望好一阵,找不到房子所在何处。
很远的地方倒是有房子,东一排西一间,散落兀立。房子之间距离遥远,远得走不到似的,而天就要暗下来了—我特别留意到天色的变化,因为四野内外只有我一个人,草木纵横,空寂无声。这曾经是一个生杀予夺无所不用其极的人间地狱,是屈尊受害者的大量亡灵被迫流放之地。随着天色渐暗,越来越感觉到阴森恐怖。须加快速度,多走几条路,多看几个地方,多拍摄一些图片。天黑以后,或者,再过一会儿,但愿我能找到展览馆。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能登上返回汉堡的大巴,然后坐地铁……独自参观无限大的一块渗透过鲜血的土地,我发现自己身体有点抖。我有点恐惧天黑。
见到一方高耸的纪念碑,用青石材料制成。设计、建造很现代,又不失简朴、厚重。距纪念碑的基石几十米远,有一尊铜质雕塑,捕捉了一位瘦骨嶙峋的男性受难者以头栽地一瞬间的形态。远处,大约一百五十米以外,矗立着一座黑色的二三百平方米大的房子,像是纪念馆,有人进出。我走进去,的确是陈列死难者名录的纪念馆。从屋顶顺四堵墙壁垂挂到地面的白布上,密密麻麻写着二战期间死于该集中营的20400个囚徒的姓名及遇难时间,其他22500名死难者,尚未列出。
地处诺因加默市的诺因加默集中营,曾关押了来自苏联、波兰、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匈牙利、挪威、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卢森堡、冰岛等28个国家的犹太人和其他囚徒,还有来自当地犹太社区的左翼人士、同性恋者、妓女、吉普赛人、耶和华见证人、战俘和其他许多受迫害群体中的人。盟军解放该地区,德军紧急撤离时,在诺因加默集中营进行了最后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整间纪念展馆,少有其他陈设。一群中学生,大约十五六个男孩和女孩,跟随老师,倾听或交流,也有少年人独自观看,随手做些记录。
我刚想拍下靠门口一张玻璃柜台里的集中营模型图,一位男子走过来问我,可以讲英语还是德语?我说英语。他说,马上就要关门,请尽快参观。我说再拍几张图片就好。他说好的,抓紧时间吧。
他是管理员?他和另一位成年人,与孩子们在一起。
刚才和我讲话的人锁好门,跟大家一起离开了。
我从纪念碑那里出发,继续往前走。路过一片草丛,里面倒卧着十几块大小长短不等的石碑,雕刻着拙朴的图文。我一一拍照,待后仔细察看。
过四五里路,走近一片房子,没有人可以问询。我朝开着的门走去。这是集中营的另一部分活动区域。纳粹的这个集中营,原来是由一大片土地构造起来的,是特别大的一个存在。那个司机说的就是这里,你随便走哪条路,随便走到哪里,那些地方都是。在那一时刻,我还没有概念,以为集中营是由十几所房屋、一座纪念碑,或者几排房子和一个院子架构而成遗址纪念地。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不曾想到。
几百米以外就看见这排建筑开着一扇门,另一扇门关着。透过那扇开着的门,见里面一片漆黑,我拿不准,该不该再往前跨一步,但还是跨进去了,里面立时亮起几个昏暗的电灯泡。是自动控制的灯,有人进门,就亮灯。灯光亮起的一刹那,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向后退出门外。望向远处,希望有人走来。真就看见两位年轻人正往这边走,其实因为看到我进去,他们才向这里走过来,见我调转头跑出来,他们停住脚步,犹疑了一会儿。
门外不远处,有半裸露、半埋没的铁轨,几辆锈死的铁推车,几间上锁的老旧平房……只有这间敞开一扇门的大房子有点特别。两位年轻人是来参观这间大房子的。我鼓足勇气再次跨进那间大房子。
我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从设想的高大空阔的厂房。它曾经是集中营的生产车间吗?它的后墙,近百米长的后墙,那里又分隔出许多个空间,均在黑暗中,连缀着地狱一般的隔断,层层叠叠,阴霉湿寒,像大车间靠低矮的小窗户连通,粗铁丝把窗户网严缝实。后墙的背后,黑漆漆的看不见底,有点像禁闭狱舍。
拘押在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囚徒以犹太人为主,兼及前述被视为纳粹德国敌人的落难者。犹太人在集中营的地位被设定为最低一级,第七级。前六级,从第一级至第六级,依次是德国人、北欧各国人、法国人、巴尔干各国人、俄罗斯人、吉卜赛人。原本区分的七级囚徒,除犹太人处境分外险恶以外,其他六级在待遇上逐级略有不同。到1943年9月,纳粹当局把“背叛”了他们的意大利人(主要为政见不同者)列入与犹太人不相上下的最底层,以示惩罚。
这八类囚徒是怎样一天天捱过时日的?从展示于大房墙壁上的图片资料看到,他们一天中很少见到阳光,长时间在极限状况中佝偻着身躯劳作。天黑后终于熬到收工,走出车间,能看见的集中营的四周,是纳粹设置的密密实实的电网,每一个区域都被严密监视,每一个角落都被探照灯一遍又一遍轮番扫射。他们睡卧的空间,也在这个大礼堂一样的空间原样展陈出来,简陋的床铺、单薄的衣着……但是仍有人,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了一点对自己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画一个女人,画一双手,或者是一只手;画了一些小人儿,或者是用泥捏出几个小人儿,在一块破木板上编排他们的世俗生活,让他们挑担子,做好吃的,互相拥抱,亲吻,手牵手进出“花园”……“花园”的气息也不乏生动,插些树枝、草叶,用纸团提炼成不同的花朵,也有泥捏的花,木屑卷成的花。在窄小的蹲便空间,放置了一个弹烟灰的铁盒子……种种细节,是他们来这里之前拥有的琐碎生活缝隙里的点滴再现。而现实只呈现了铁青色,他们全部的生活已经东流西逝,生命也不再掌握在他们个人手上。时空已经一泻千里,万劫不复。他们已无法设想哪一天,那些让他们倍感温暖的东西能够回到他们的生活里,哪怕是一星点儿。其实连个人的生命危在哪日哪时也无从料知。他们明白,不能要求太多。问题是人们尚有一个可以幻想的头脑,和很是健康、正常,有规有矩,有文明常识,有基本教养和独立思想的意识,有强烈的对于世界美好进程的向往,有自食其力、重归正途的愿景企望,此时此刻却是无可奈何,不知所终。这一副非自由、非正常的心身,随时可能别离人世。阖家欢乐的景象,在他们几近枯竭的睡梦里,闪烁,然后碎裂,异乎寻常地快速消失。
左侧墙壁上,挂满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历史大事记资料,书籍、报刊和图片,应有尽有。包括希特勒到此视察的讯息。通过全民选举成为德国政府合法总理,并最终攫取统治极权的希特勒,以正当的名义,发动和率领民众,迅速地以压倒性优势向被他们界定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以及收容、渗透了犹太人的其他国家、那些日耳曼民族的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所到之处,掠夺,摧毁,杀戮,兴建集中营关押,最终彻底消灭犹太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所制造的反人类罪孽的集大成者。三千多年中移居欧洲的犹太人,又退回到三千多年以前,摩西率领众人寻求救亡道路之前;退回到摩西领受并传达“……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等“十诫”之前;退回到艰难困苦的驮梦起步的流亡元初。
以神圣的名义向人类自己和文明硕果举刀断劈,将会浸淫出什么样的丛林法则,又会滴流出什么样的示众教义?毁坏了的,永不止是毁坏本身那样简单和易逝,它总是以多出十倍、百倍、千倍甚或万倍的蛮横与邪力,向人类讨偿责罚曾经的孽缘和过失,被施暴者书写在历史的底板上。血债血还,是千万年间自然形成的残酷铁律。而它又有着怎样的背逆与局限,因为,完结不了血债的冤魂又哪里能够还偿他们对于自身生命的支配权利,血还的虚妄显而易见。再说,血还之后呢?罪恶并未减少或者消逝,一切如故,善良人们的愿望,像傍晚的轻风,也像进入昏沉睡眠的少年的梦境,细想一下幻觉与现实的关系,应该能够明了枉然的意味绝不止于深长。以我们有限的生活经验看,哪里的水,能够洗涤、清洁邪恶的灵魂?哪里的雪,能够永久覆盖住累累的白骨?而那些被动流淌的血,又如何能够自行消泯?
图片中,记录了希特勒与他的核心成员先后几番视察诺因加默集中营轰轰烈烈的场面。党卫军一声令下,二百多名骨瘦如柴的孩子排队走向毒气室,随后被焚尸灭迹……自1942年秋,诺因加默集中营建立毒气室起,惨死的两百多名儿童,和其他成年男女的骸骨一道,随四季漫舞的花草败叶,除随风飘散远赴他乡的以外,其余的经风沐雨以后,竞相渗沤进这片广大的集中营遗址的土地里。生不如死的男女老少们失血的脸孔、干枯的身躯、绝望寂寥的眼神,在照片所及的边边角角残留下印记。
这个大厂房,空旷,昏暗,阴冷。待到后来,我两只手冻得僵硬,摁不动快门,拍不了照片。但不想马上离开。与我先后进到这所巨大房子的,是一对年轻恋人,他们是我能够在里面待比较长时间的重要支持。
远处有一排矮小的房屋,走过去,需要跨过一片黑土地。刚犁过地,黑土搅拌了截断的树叶、杂草,慵懒地晒着夕阳最后的余光。不知是些什么草,它们无拘无束往上恣长,大部分高过了庄稼。一股股浓重的湿腥气,被发酵多年的腐殖质的复杂气味,穿过深土与杂草的枝蔓,逍遥自在地扩散到汉堡郊外诺因加默集中营遗址的每一个角落。困厄于此的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的苦难,也在里边吧?一个又一个土堆,像一个个死难者的头颅,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长方形的草地上。
我的脚陷进泥土,脚上沾了泥,沾了一簇一簇的草,脚步滞重,无形中增添了行走难度。翻越一条地沟,进到另一片铺满小草、长着许多高大杨树的林地,阳光从其间忽闪一下,又忽闪一下,那么失心寡意地穿过,把树身照映出金色、金银色,把林地照映出长条形,款款地拽落,凄美地飘泊。一个女人从另一方向的远处走来,往我刚刚走过的那个地方走去。她也是来参观的?显然跟我不同,是前来看望亲人的,还是工作人员?她的一条腿行走起来慢半拍,不知是哪个部位的关节不够给力,或是哪块骨头出现异常带给她阻障,跟不上她愿望的步伐,远远地,感觉她有点吃力。我看到一张抽搐、褶皱的脸。本想跟她打听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存放故人遗物的博物馆,我想先看看那个地方,然后再看这些露天散置的遗迹。但看到她寂寥无着的表情和固执己见的行走姿势,我没去打扰她,让我们各自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吧。这里的土地,太难走出去了,不要出声,只须埋头赶路。
对我而言,这个地方不同寻常。这样大刀阔斧,有计划、有步骤地剥夺、屠戮生命,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其规模和程度,都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不敢过早妄自断言。这里发生的事件离我们今天的生活相距七十多年,不算短也不算长,七十几年间,地球上还发生过许多别样的惨烈血案,可以说,杀戮没怎么停下来过。被屠杀者,反过手来,也有不少做了屠夫。这样的因循传习,以致重蹈覆辙,成为怎样的体统?间有的倒行逆施,又在怎样的进化过程里反转折中,卷土重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需要的呢?是人自身的需要吗?在屠杀他人的问题上,谁能够停顿一下,再停顿一下,或停顿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有人感觉需要节制这方面的“需要”,杀人的行动不去付诸实施,这件事就算暂时在这里、在这个人身上停下。这个世界就是靠这样的人们,腾挪出了一些或再多一些。他们每天都在呼吸着血腥气味,咀嚼着不知是谁的血肉滋养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五谷杂粮,度过不得安生的一系列日子。所以,他们对于血腥事业的住手、停歇,也产生于需要,依循着需要。可是,另一些人不这样想,他们嗅不到血的腥膻味道,精神就会萎靡,灵魂就难以清净,对于未来将要开创的事业,前期设置时,他们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置人滴血、置对手于滴尽血、使其无力还手的境地。他们的生活是靠血和泪供养的。他们的精神是靠血腥沸腾的。握有极端权柄的人,对于血和泪的态度,是超常理性的、决绝的,全然不放任、不存在侥幸和幻想那一类虚弱表征。相因相生地决定了统辖区域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命的存续方式,及其精神的无着和失效状态。
这是一幅机械化图像。生命的河水,被阳光照见了根底,惨白而且殷红,散发着萎靡、浑浊和恶臭。土地被浸染成不可阻挠和假设的荒诞色彩。
东南西北中,世界上的很多角落,捋一捋,尚未被血水浸泡过、冲刷过、滋养过的土地,应该有,我相信有,而且很多,非常广阔。但是信心总是被打击。翻阅了几十年典籍,查阅和观看了几十年文字和影像资料,知悉净土时时复亦喧嚣。非洲的土地上,死亡这件事在太阳和月亮的交替中随时出现。中国的不少土地时有起出的日本人造就的万人坑埋葬的尸骨……欧洲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的屠戮生命的记录至今鲜有超越者。美洲、非洲的暴力屠杀历史一幕又一幕都印刻在世人心目中。人类千百回经历磨难和挑战,刚从死亡的边缘返回栖息的家园,又听见阴谋的窃窃私语和波动。对于血腥味道的嗜好,从极端或激进的人们心中重新溢出,杀人理由和过程又在酝酿和成形。何止是各洲大陆的人间在悲喜剧的舞台,一面抢夺,一面建立秩序,不是牺牲就是被牺牲,仍然行走着千百年以前踩踏出来的老路,但不可小视传统的方法即“以正义的名义”的方法,它相当程度上保障着欲望之路的合法性通畅,并长盛不衰。
曾经,散落在太平洋海域小岛上的人们,不堪回首的记忆里,也有深刻的伤痛和疤痕。他们捡起海浪和渔网捎带给他们的零碎,制作出各种首饰,佩戴在自己的身体上,光耀自己有形的日子,赞颂无限美好的时间和空间。曾经他们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是不是还能看见自己的家人,听见族人继续欢笑出声,是不是有看见他们的孩子往大长的可能。至于生活,他们当时没有的,他们不去向往能够拥有、需要去拥有,他们不需要更多东西,他们只想要一块生活的土地和几根树桩、几片草叶搭建一个居住的屋棚,就足够了。但他们选择了生命,这是最为奢侈的要求。生命里的每一个支点,出落于生活,而他们生活着,上天创造的生命,没有一天不是用鲜血作为代价换取并维系的。但是上天为什么让一个人活得长一些,让另一个人活得短一些?让一个人快乐多一些,让另一个人在短短的生命过程里充满忧伤和悲痛?在这些方面,人们去思想,这就成为上天额外赐予人的禀赋,他让人们去思想,他同时创造了人的思维能力。人们只能这样想。把一切好东西,都当作是圣灵所赐,是超然的上天的同情与恩典;相应地,罪恶相随在身、不得已时施以恶行,也便有了开脱的机会和可能,因为有魔鬼作祟,卑贱而可怜的人被遮蔽了双眼、抑制了心智,以致偏离了正途。可是,非正常死亡的人事,仍然经常发生。那些小岛上的人们,为美好的生活祈求神灵,他们戴着这些美妙的饰品,想让神灵看见,他们以为一切正常,一切会正常的,如他们祈祷和祝愿的那样,而且美好已加持在身上。美好会驻扎在他们的心房,跟随他们的企念持续更长的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们终生。但愿那一点一滴的美好不只存在于今天,存在于他们的记忆和念想,那是他们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建立的信念,塑造的宗教。他们坚信,只要坚持,上天能够体会到他们的领悟和心意,上天会慨然接纳他们的生命誓言,帮助他们实现人人平等并互守条约,此致,美好终会降落得多一点,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他们的信念在这样的企念基础上,萌生并在挣扎中日益加深执守。有的部落,选择一个活人,作为贡献于神灵的诚意,把他作为牺牲,触目惊心地置于神灵的眼前,示于族人面前。所有人没有悲伤,因为他们相信被选择的牺牲者是幸福的,神灵对其是满意的,他的家族是荣耀的,乡人是感激、敬畏的,生命是为大德大义大道大智而幸运前往并得以转世成为慧者灵者圣者,他的灵魂因此会携带着更多福祉来到世俗的生活中间,那个牺牲了的贡品,将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尊重。他的家人也不怀疑,他们的家庭,将比别的人家更多地接近神灵。何谓通往天堂的云梯神阶,那个牺牲和前面一个又一个牺牲,就是搭建这种云梯神阶的凡人,他们朝向上天和天堂,也把众生率领到正确的路径上,既渡己又渡人,渡了人也便能够更好地渡己……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圣子。是集约修习而成仁的先行者。照此看来,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村庄,都需要死亡。他们的小日子,也没有断过滚滚的红血河流。类似案例杂草般四处漫长疯蹿。四五十年前,我读的语文课本收录过《西门豹治邺》(《史记·滑稽列传》),讲的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时期,邺县的三老、廷掾每年向老百姓重征赋税几百万,其中需开支二三十万为河伯娶亲,女巫行奉命令巡查小户人家的俊秀女子,予少量聘礼夺取,将其沉入河底与河伯成亲,以年轻貌美女子的溺亡,祈祷河伯保佑河流不再泛滥,众生免却水患。
从外到中,曾经以活人随葬的权力印记、砍人头祭奠等残俗陋习,不胜枚举。
事实上,人们从未停止暴力血腥的行径,五十步和百步之间的区别罢了。中国古人一针见血,认为五十步和百步,做得多少做得好坏,只不过程度不同,规模稍有差别而已。在本质上,在主观意识里,有一致的取向,原本天性差异不到哪里去,皆为人性悖逆之举。在持续的行为中,因个性不同导致结果有所差池,仅此而已。主观一味向前的趋势,一直缺乏有效的抑制力量,从他们的躯体和灵魂里产生出来,形成与他们自己分裂的,往别处发展的局面相反的情况。没有,我是说想要无端剥夺他人生命的人,若能从他们躯体内部产生反动力,即是他们真正放下屠刀的时刻。但有几人,看见过当年侵略亚洲国家战争中,日本国占绝对多数的军人自动放下过屠刀?那片曾经疯狂的疾速生产杀人机器的土地,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快速地打造着屠刀枪炮、战机军舰,想通过战争改变其生存空间,获得重新整合资源的优势,最大化地获得利益,并藉以转移国内矛盾,使其国家成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世界超级大国。
常常见到,无论付出过怎样的牺牲,承受者缓过一口气来以后,本质上并不比过去变得有所不同。倒是看见了死亡在吞攫人的生命的同时,也比较多地葬送掉了人们灵魂里的一些东西。
“告诉你们往事,”我父亲说,“是想让你们知道历史,仇恨没有什么好处,将来你们能找到比单纯的仇恨更有益的生活办法就好了。”这是他离世前两年对我说过的话。
父亲带着平静,离开了世界。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孩子们也都开始衰老,他看到了他更看重的东西。他感觉到一些新的内容已经出现,像家人之间,也比以前更多地表达爱了。的确,现在已然不是过去那样的时代了,过去很长时间里,谁也没有寻找到埋葬仇恨、迎接宽宥和博爱的好办法,寻找到脱离危险的正确轨道,现在不是那样的情况了。父亲到最后,双手无力,连揉一下自己的眼睛也没有办法做到。
七十几年过去,德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汇集、展示了曾经的国家形式的丑陋历史。
这个世界在追求进步中,往前迈进。
人们的安宁在这些步伐里。
幸福也源于此中。
我们哭泣。我们欢笑。我们生活。我们死亡。
我们从一天走进一世。
从一世走向重生。
如同汉堡城外纳粹时期建筑的诺因加默集中营,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差不多都作为人类受难纪念地了。
纪念。也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