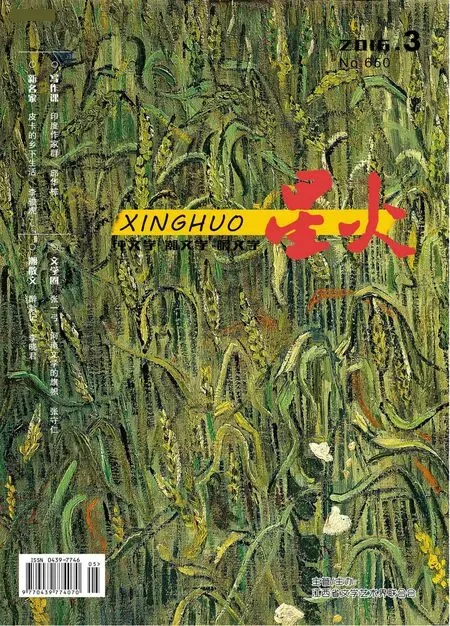瓷上宝石
○王 芸
一
她建造了一个王国,那是她沉迷耽溺了五十多年的“秘境”。那里有她亲手创生的1500多个孩子,他们分处于四十多个家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景德镇传统高温颜色釉瓷。
创生的喜悦,蓬勃的生息,那些孩子奇异,灵动,神秘,每一个都仿佛是世间奇迹。他们,有的像天空中瑰奇幻变的流霞,有的像雾色弥漫的青翠山峦,有的像梦幻般湛蓝的湖水,有的像焰火四溅的流光飞荧,有的像如瀑倾洒的雨丝,有的像瑰丽的凤凰羽衣,有的像被魔指点过绽放的奇诡花朵……无机生命与有机生命、必然与偶然的结合,已知与未知、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万千种可能,在打开窑门的那一刻,定格。
她说:“颜色釉是瓷上宝石,人造天成。但与人造宝石不同,原本只是矿物质的它,必与瓷结合,才能蜕变为宝石。”细腻而富有莹润光泽的瓷肌,源出于平朴无奇的矿物质、高岭土、瓷石,经过木的钝重击打,水的温润化合,火的炽烈煅烧,还有她的手、心、意的点染,有时连她也不知道,会创生出怎样美妙绝伦的“生命体”。
她为孩子们一一命名—郎窑红釉美人肩瓶、秘釉流霞盏、玫瑰紫釉福瓶、彩色丝毛釉葡萄瓶、宝石红釉将军瓶、窑变三色瓷瓶、火焰红釉月光瓶、鹧鸪斑釉笔海、雨过天青釉茶盏、凤凰衣釉醉仙瓶、郎红乌金釉三阳开泰瓶……进入窑膛前,胎体素白,釉色也寡白平淡。窑门闭合,可控的是温度,不可控的是火焰的自由游走、热力的散布、氛围的形成与变化、釉的兀自流淌与神奇窑变。于是,每一次停火开窑,都是让人屏息的揭秘时刻。
无数次的黯然失落,无数次的惊喜欢悦,她的心已被锤炼过万千次,还是会在“人造天成”的美妙造物面前,惊叹不已。
这些孩子被她珍藏在“景德镇邓希平颜色釉陶瓷艺术博物馆”内。美轮美奂的局部,雅致炫美的整体,在灯光下熠熠闪光。
离艺术博物馆几步远,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推开铁门,小院里迎面一棵树下,林立着残破的瓷瓶,密密挨挨,一直铺排到墙角。整个小院被一丛丛瓷器占据。他们,与展厅中那些光彩照人的孩子,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同样的工序,同样的配料,同样的施釉方法,同样的烧制环境,同样诞生于她的手中,可命运在窑火中截然分野。
车间里,摆满高低错落的木架,架上一排排形状各异的粗坯,小木凳上装满釉料的碗碟,还未进行配置的矿物原料,半成品和正待修整的成品,隆隆作响的球么机,显示温度已达1050摄氏度的在烧气窑,处在轮休期的气窑和设备……这一切构成了邓希平真实的工作环境。实验室里的配料研究阶段,是建造王国的流程之一,更多的时候,她穿着粗布工作服,在灰朴、简陋、光线不算明亮的车间里忙碌,选坯,施釉,烧制,或长或短地等待。
辛丑年盛夏,当我走过流光溢彩的博物馆展厅,再跟随邓希平老师走进这座车间,忽然看清了五十多年间她走过的那条路。可见的荣耀和光环,都是以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步步艰辛铺垫。一路走来,她凭恃的,是学院里练就的扎实功底、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富有韧性的探索精神,还有历五十年不曾褪色的挚爱与执著。
真正属于她的“秘境”,不是那个七彩幻美的王国,而是这里。
二
二十三岁、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邓希平,坐着一辆白色救护车抵达轻工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那是三天两夜漫长报到行程的最后一段。
当满身尘灰、难掩疲色的她,走进四野黑寂、亮一盏孤灯的研究所值班室,值班的师傅惊诧地望着她。问明她的身份,值班师傅又惊又喜:“早接到通知说你要来报到,我们等了三天,怎么路上走了这么久?”
那是1965年盛夏,蓄短发、穿白衫的邓希平按照武汉大学学生处老师的规划,先从武汉坐船到九江,为了节省2元一夜的住宿费,她在九江火车站的候车室过了一晚,坐慢吞吞的绿皮火车到达南昌后,又在汽车站过了一晚,赶一早的头班车去景德镇。
坐在开往景德镇的班车上,携带热力的风卷起尘土扑进车窗,车轮搅动的沙粒将车身拍打得“啪啪”响。路边的风景越走越荒凉,车一径向着大山深处、夜色深处行驶,全然不顾邓希平忐忑的心情。她没想到以瓷器闻名的景德镇,竟然这么偏远。
车上还有一位学生模样的男孩,穿着印有“湖南大学”字样的球衣,是来景德镇瓷厂报到的。车上的一位医生听说他们是分配到景德镇的大学生,热情搭话:“陶瓷研究所在东郊,这车到站很晚了,医院里安排了车接我,你们就坐我的车,负责把你们送到……”
车开了整整一天,直到夕阳沉落在远山背后,收尽最后一线霞色,才望到景德镇的影子。
于是,邓希平坐着救护车,抵达了轻工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那晚,她被安排在女生宿舍,托运的行李还在路上,是同室借给她衣裳。洗完澡一身清爽的邓希平,这才有了细细感受这个新地方的心情。山里的空气似有丝丝甜味,比大城市的洁净,清新。她躺倒在床,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一早,邓希平在所里转了一圈,竟是个遍布花草林木、公园般的所在,两层楼房和数座平房散落其间,静雅端丽。第一天上班,邓希平被领进了化验室。实验是绕不开的“日课”。两位组长都很和蔼,其中一位组长周熙颖老师年过五十,待她有母亲般的煦暖。
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实验课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都是学生自己动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邓希平在同级的两百多名学生中算得佼佼者,才有资格分配到国家轻工部研究所(原在上海,又称“玻搪所”),不想分配刚定,该研究所的陶瓷室就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合并成了轻工部的陶瓷研究所。命运就这样将邓希平引到了景德镇,赣东北的一座小城。
眼前的实验设备,邓希平都不陌生,只有酒精喷灯她没用过,在学校做实验都是使用煤气灯。周组长问她:“能上吗?”她迟疑一下,指指喷灯,“能!就是这个,我不会用。”
“我点给你看。”酒精喷灯需要二次点燃,先点酒精灯,促使贮罐内酒精气化,再用火柴点燃酒精喷灯。“嘭—”,高温火焰伴随一声轰响升腾而起。邓希平吓了一跳。看过一次演示后,邓希平走上了实验台,和另一位同事进行平行样品实验。结果在误差范围之内,实验有效。
调配试剂,分析样品,整理结果,实验的每一步骤和细节,都将实验者的水平、态度、严谨度和专业度展露无疑。这无疑是一场考试,邓希平顺利通过了。
对于刚入职的大学生,所里没有压重担,只是让邓希平做做简单的平行实验。日子无波无澜,平淡无痕地滑过。很快中秋节到了,这寄放思亲之情的传统节日,让从未离家这么远、这么久的邓希平,忽然陷落在了浓烈的思乡情绪中。
她的父母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现在在武汉高校当老师,七个兄弟姐妹构成的大家庭,让她从没体验过孤单无依的感觉。可是现在……周组长看出了她低落的情绪,邀她去家里过中秋,月饼、板栗、柚子,还有景德镇特有的碱水粑,围坐赏月的暖融融氛围,天上那一轮玉色明月,融化了邓希平心中淤积的思乡之结。
中秋过后,科室遇到了一个难题。所里做分析实验的样品来自全国各地,样品粉碎后一般都要取出大部分分为等量的三份,其中两份做平行实验,如果结果核对不上,再使用第三份。当时有一个样品,三次实验的结果都比对不上,且误差很大,需要分析的9种元素,始终有几种元素的分析数据不正常……分管理化科室的副所长组织大家开会分析原因。在会上一遍遍问大家:“样品有没有问题?实验过程有没有问题?”
科室已经自查多遍,都没找出问题所在。坐在会场的邓希平默默听着大家的汇报、议论、分析,散会后她去了图书室,终于在书中找到了“答案”。她大着胆子和副所长说:“是上面指定的分析方法有问题!”
样品中有几种元素含量过低,用指定的方法无法一次性得到这些元素的分析结果。这种样品的分析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析出部分元素的含量。样品分离后,用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分析出另几种元素的含量。果然,沿着邓希平的思路再进行实验,所有需测元素的含量一一清晰浮现。解决难题后副所长露出了笑容。专业,细致,沉稳,善于查找资料解决问题,所领导看到了邓希平这个学生娃的优点和实力。
按照惯例,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要下乡参加社会劳动实践一年。来自大上海“玻搪所”的政治处主任却不走寻常路径,将5位新分来的大学生留在了所里的实验工厂劳动锻炼,而且为他们专门配备了4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分别传授陶瓷工艺中的原料、成型、烧制、装饰的课程。
一年结束,其他四名学生被分到了科室,担任工程师助理,只有邓希平被分到了颜色釉组,当学徒。对颜色釉还一无所知的邓希平,心里那个难受,不解,“为什么单单是我做学徒?!”
政治部主任给她讲了一个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为邓希平打开了颜色釉王国的大门,让她找到了属于她的奇妙“秘境”。
三
故事发生在1954年。解放初期,我国迫切需要德国的精密仪器制造技术来发展工业,德方提出用景德镇颜色釉技术交换。
景德镇有几个家族祖传颜色釉技艺,但基本是一个家族一种颜色釉,靠父传子续的方式传承。解放后,当地政府为了传承珍贵的颜色釉技艺,将几大家族的当家师傅都集中起来,由政府提供工作岗位,每月发放不菲的工资,希望将这一传统工艺恢复并发展。
老师傅们都是行内高手,知道怎么找原料,怎么加工原料和配制釉料,在什么窑位烧制颜色釉瓷,但要形成文字材料,他们一则文化水平低,有的连字也识不得多少,二则缺乏分析和整理资料的能力,无法拿出一套完整、科学、严谨又规范的科研资料。国家只好请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玻搪所的陶瓷专家和工程师,到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来帮助颜色釉师傅们整理技术资料,同时又为师傅们配备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和年轻技术人员做助手。
师傅们按照祖传的工艺制作颜色釉瓷器,学生和技术人员则天天跟着师傅,将每个工艺过程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再交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测试,最终形成关于原料、制坯、配釉、施釉、烧成各环节的研究性文本资料。历时半年,终于完成了这份“中德技术合作资料”,为中国换回了珍贵的“德国精密仪器制造技术资料”。这次国际间的技术交换,让景德镇人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景德镇传统颜色釉陶瓷制作技艺的重大价值。
景德镇,偏安赣东北的小城,因为出产一种名为高岭土的特殊泥土,成为瓷业发展的重镇。这座“千年瓷都”,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陶瓷是这座城市的肌肤与骨骼,也构成这座城市的精神钙质,塑造其国际形象。意识到陶瓷的价值与意义的景德镇人,从1954年开始,每年选派几位大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进入颜色釉组当学徒,希望这些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能让颜色釉瓷拥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一批批学徒走进颜色釉组,但真正留下来的不多。有的不喜欢和泥巴打交道,有的觉得颜色釉单调乏味,有的在技术上始终无法提升,有的有更“远大”的志向,他们都成了颜色釉王国的“半途走失者”……邓希平是这些年轻学徒中的最后一位大学毕业生,她留了下来,并坚持到今天。
一个师傅只懂一种釉,通常一个师傅带一个学徒,而邓希平跟着聂物华、陈鸿高两位师傅学习,同时掌握了两种颜色釉。
两位老师,一个擅长宋钧花釉,这是一种以青、红、蓝釉色交错如兔毫纹的窑变花釉;另一个擅长青釉,尤其是孔雀蓝釉色如梦境般迷人。
每一种高温釉,都是由几种,甚至十几种天然矿物按照一定比例调配而成。那些配料“密码”,储存在家族记忆和师傅的大脑里、指尖上。古有“若要穷,烧郎红”之说,因为郎红的成品率极低,百难成一。不只郎红,许多颜色釉因其流动、不稳定性,很难烧制出精品。而每一种颜色釉,对坯体的要求又各不相同,只有能与坯体紧密、和谐、完美结合的颜色釉,才能最终在窑火中蜕变成“瓷上宝石”。
老师傅们在多年的烧制实践中,不断经历失败与成功的反复锤打,才拥有了娴熟精湛的技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保证每一次出窑都是百分百的精品。学徒们掌握配方后,就进入实践环节,从制坯、配料、施釉到烧制,全程独立做完。烧成了,就再按此方法重复一次、两次、三次;烧坏了,就琢磨原因何在,加以改进。实在不懂的,师傅也不懂,那就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偶尔出现一件精品时,那喷涌出的喜悦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它可把反复制作颜色釉瓷器的单调、乏味、辛苦、劳累冲得无影无踪。
组里常用的矿物原料有二十多种,看起来样子差不多,而所里有一条铁定的规矩:不贴标签。用这种方式,逼着学徒下工夫去认、去识、去记。眼看,手摸,舌尝,只有细细体察,才能分辨出矿物原料们之间的不同。它们有的是白偏黄,有的是白偏灰,有的质感细,有的质感粗,还有舌尖舔过时,能感受到不同的味觉。有的学徒怎么也记不住、记不全,几次考试不过关,就面临被踢出组的结果。也有学徒想歪点子,偷偷做记号,一旦被发现,就是不留情面地踢出组去。
除了不贴矿物原料标签,颜色釉组还有许多有形、无形的规矩,学徒稍有不慎触犯了,就会被踢出组。
师傅们脾性不一,进入颜色釉组多半是被动的。原本这是家族拥有的足以养活一代代子孙的独有技艺,现在不能父传子承(按规定其子女不能进颜色釉组。但师傅的工资很高,足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还必须拿出来与外人分享,等于砸掉了家族的“金饭碗”。师傅之间,存在无形的壁垒,原来他们相互间绝不交流互通,各据一方不越界,才能在景德镇的地面上共生共存。如果有学徒不识趣,在师傅间随便走动,会被认为是在捣乱,也面临被踢出组的结果。
邓希平无暇他顾,学习两种颜色釉已经是双倍难度。而且,有那么多工序、环节、细节需要掌握,还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她丝毫不以为苦、累,她彻头彻尾迷上了颜色釉。
十几种矿物原料,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可以实现无穷无尽的组合,但只有一部分是有效组合。配料的过程,邓希平感觉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中医握有古已有之的配方,但那只是别人的经验,行医诊病仅仅靠现成的方子不行,世间多的是庸医,少的是良医,只有将这些方子与个体经验充分化合,在面对千差万别的病患时灵活调配,才能行之有效,药到病除。颜色釉也是如此,配方看似恒定,哪怕是一毫不差同样配比,可因为天然矿物的成分并不是均衡稳定的,配料中的微量元素存在差异,加上施釉的手工环节差异,窑火的任性不羁,必然与偶然结合,让结果无法预料—每一次制作都是一程“探险”,每一次出窑都是一场“揭秘”—无穷无尽的可能,为循环往复的颜色釉陶瓷制作过程,增添了难以言喻的魅力。
各种各样的矿物原料,只有深谙它们的特性和釉料配方的科学原理,才能遵循化学的规律自如地驱策它们,进行不同的组合、配比。由此,可以复原许多古已有之、但失传多年的釉色,也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釉色。
为了摸清烧成温度曲线(温度曲线、压力曲线、气氛曲线),她独自跑去柴窑安装测试管。旧时景德镇有女人不得进入窑房以免倒窑的说法。进入新时代,为了学透学精颜色釉陶瓷制作技艺,柴窑成了邓希平绕不开的学习现场。
颜色釉王国,一个让人越深入越觉辽阔无垠的“秘境”,令邓希平迷而忘返,乐而不疲。
四
有几年时间,深爱颜色釉的邓希平,却不得不远离颜色釉。
那是动乱时期,她响应号召,随“五七大军工作团”去到江村公社,种稻,采茶,摘棉花,教书,制作农药……可一旦机缘让她回到景德镇,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陶瓷,选择颜色釉。1972年,陶瓷研究所还没完全恢复,市政府委托景德镇陶业公司安置原陶瓷研究所的干部职工,邓希平主动要求调到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的建国瓷厂,因为那是唯一可以做颜色釉的瓷厂。她的调令上特别注明了“颜色釉”三个字。
久别重逢,一往而情深。来到建国瓷厂的邓希平和两位颜色釉老师傅一起,成立了厂里的颜色釉实验组。建国瓷厂以均红瓷为主打产品,有技艺纯熟的师傅、成熟的工艺流程和生产线,但邓希平想在建国瓷厂开辟更广阔的颜色釉天地。
一间泥坯房,没有窗户。三张办公桌,没有实验设备。颜色釉实验组从零起步,一点点建构。邓希平年轻,怀抱巨大的热情,是组里的主力。每天在各个科室间来回地跑,矿物原料、仪器设备陆续到位,可还缺少测试用的瓷坯。邓希平跑去成型试验组拿试验用坯,工人看她年轻,觉得她就是一个“给领导拎包的”“开会时写写材料的”,做不成什么事,随手挑了两块残次坯给她。那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依然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邓希平没有争辩,就用残次的瓷坯做实验。在心里,她认定:总有一天,厂里的工人会改变对颜色釉实验组的看法,会改变对她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态度。
没想到,机缘来得那么快。
建国瓷厂二车间专门生产均红瓷,这一年车间进行成型技术革新,变原来的手工拉坯为灌浆拉坯,成坯的效率大大提升,可新工艺实行后的第一窑瓷器开出来,令全厂震惊:满窑均红花瓶全碎了!
这可是重大生产事故。二车间立即停产,查找原因和寻求解决办法。不解决技术上的问题,继续生产等于加大损失。
原因不难找,方法却难求。机器灌浆的坯体厚度只是手工制作的坯体的一半,无法承受均红釉在烧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拉力。这再一次证明了:颜色釉只有与坯体高度完美结合,才能蜕变为“瓷上宝石”。
技术革新必行,用灌浆方法生产的上万件瓷坯摆满了厂房和仓库,现在只能重新调配釉料,以适应灌浆坯体。厂里每天找“均红”组工作人员开会,人人心焦气躁,却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这一事故不只惊动了建国瓷厂,整个景德镇都被震动了。有人将之命名为“均红犯破”事件。
建国瓷厂面向全市贴出“招贤榜”,承诺只要是能解决“均红犯破”的人,都能得到国营指标的奖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可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于是,献计献策者蜂拥而至。
邓希平负责接待来访者,记下他们提供的方法、思路,一一进行测试。有人拿来了祖传的秘制“白粉”,有人写了十多页材料,有的拿来了新的配方……起初,大家的思路往“减少拉力”的方向走。既然是拉力太大,那就追求均红无裂纹,可烧制出来的红色变得很浅,根本称不上是均红。改而追求少裂纹,配方改了又改,还是不行。
忙着接待的邓希平,也在思考解决之道。如果无裂纹、少裂纹解决不了问题,那可不可以换一种思路—让裂纹变得更多,像蛛网一样均匀铺展,以减少单位面积所承受的拉力?就好比,用针尖去戳气球时,所有的力集中于一点,气球轻易就被刺穿。而用双手挤压气球时,气球反而因受力面大,不容易破裂。
思路有了,可心里没底,她没有声张,夜里加班加点进行试验,不断调整改变釉料配比。终于有一天,打开窑门的一刻,呈现在她眼前的是裂纹遍布、瓷身完好、均红色匀亮的瓶体。邓希平的心一阵狂跳。她静静地坐了一刻,待兴奋过去,又进行第二次试验。连试三次,都成功了。她这才将试验结果汇报给组长。
厂里得知消息后,决定不进行中试,直接重启生产。厂里停产数日,损失巨大。可不进行中试,就意味着试验阶段并不完备,一旦出现问题,谁来承担责任?这时,组长站了出来,他得保护年轻的组员邓希平。他提出方案:为确保顺利重启生产,必须全厂各部门、各环节全力配合,不能稍有差池。厂里组成一个临时投产组,组长由分管业务的副厂长担任,保卫科、技术科、供应科、生产车间负责人任组员。以前的原料、釉料一律打上封条,供应科严格按照邓希平提供的配方,派人和她一起去进原料,待釉料球么完成后,先取出三桶釉料,一桶交保卫科封存,一桶交技术科封存,一桶由邓希平亲自上釉进行对比试烧,剩余的釉料交二车间正常生产。
全厂三座柴窑,全部满窑。柴窑从满窑、烧窑到开窑需要四天时间。那四天,每个人的心都仿佛被烈火烹烤着。开窑时,厂领导全部来了,现场围了二百多人。邓希平也站在人丛中,眼睛盯着窑门,大脑异常兴奋却又像是一片空白……
那天,爆竹声震天炸响。满窑均红瓷器,一个都没破!
这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厂子,也传遍了景德镇的角角落落。
转天,厂里召开总结大会,厂长在台上说:“读了书还是有用的……”
短短的一句话,让坐在台下的邓希平,顿时泪流满面。
这句话,应和着她的心声。远离颜色釉的这几年,来到建国瓷厂的几个月,有一种力量从未从她内心离开过。
这一刻,它被一句话在台上宣示,明证,令她百感交集。
五
景德镇有四大传统名瓷:青花、玲珑、粉彩与颜色釉。
颜色釉是最独特的一种。釉料由天然矿物配比组合,进入窑火后,随着火焰的跃动、气流的回旋,她便“活”起来,动起来,形神莫测地蜕变。“不能去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这些年,沉迷于颜色釉的邓希平,所做就是尽量去摸透每一种矿物的脾性,再以精准的组合,赋予每一种颜色釉华彩绽放的可能。
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颜色釉瓷。每一件颜色釉瓷的烧成,就如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她,是这个新生命的创造者、孕育者、呵护者。
在颜色釉王国里,邓希平不断挑战既有的难题,又不断自设难题。她相信每一个难题,都有破解的方法,只是还没有被世人找到而已。只要解题方向正确,终有一天会拨云见日,水落石出。
1975年,国家轻工部将一项科技创新项目—“零号柴油烧制均红釉”,下达给建国瓷厂,并拨付了15万元科研款。厂里专门成立了科研组,由邓希平主持研究。
在此之前,景德镇用煤、酒精、发生炉煤气等多种燃料进行过烧制均红釉的尝试,都未成功,这一次邓希平的科研小组选用0#柴油做燃料,低压喷咀倒烟式1立方的方形窑炉烧均红,通过几十次配方试验,用一年时间,终于试制成功62#无铅均红釉配方,烧制出了丝毫不比柴窑逊色的均红釉瓷器。
古有“无铅不红”的说法,铅是可以让熔融点降低的金属,可以保证红釉稳定发色,被用于多种釉料配方中。传统均红釉,铅是重要元素。但铅对人体有害,尤其是一线工人长期接触铅,会引发职业病。这次科研在改变均红釉的配方时,将铅含量降为了零。不只是均红釉,邓希平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探索,使之扩展到所有颜色釉配方,结束了颜色釉含铅的历史。她研制出的“无铅均红釉”,在1978年获得了江西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郎窑红,是颜色釉中的珍稀品类。其色泽比均红更为鲜丽纯粹,近乎透明的莹润质感,诞生于康熙年间的御窑。
郎窑红的熔融范围在5摄氏度之内,一旦超过这一范围,就会发生器损、色偏。旧时柴窑烧瓷,控温难度本来就大,烧制郎窑红瓷器,简直像是在钢丝上行走,在针尖上旋转。郎窑红的这一特性,限定了其瓷体无法高大。即便是保持高水平管控和高品质追求的御窑,也难以生产大件郎窑红瓷器,遑论民窑。罕有烧成的珍品,都是娇小器型,作为皇宫特供,只能由皇家品赏。
没有人知道邓希平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又为这种醉人的红,魂牵梦萦了多少日子,她硬是将传统郎窑红只有5摄氏度的熔融范围,扩展到了80摄氏度—只要窑火温度在1290至1370摄氏度之间,郎窑红就能蜕变成理想的模样。
郎窑红釉瓷器,由此得以拓展。1979年,高至62公分的大件郎窑红瓷器在柴窑中烧制出来。凭借这项技术,邓希平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她运用这项技术烧制出的300件郎红釉美人肩瓶,被外交部礼宾司定为国礼,携带着中国人的深情厚谊和传统文化因子,飞向了世界各国。
1984年,邓希平以其出色的专业能力,升任建国瓷厂的副厂长、总工程师,在她的推动下,实验组扩容变身为“颜色釉科研所”,在颜色釉科研之路上发力奔跑。建国厂的另一件经典国礼—三阳开泰瓶,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其名取自《易经》中的卦名,寓“冬去春来,阴消阳长,万物复苏,吉祥之意”。釉彩由郎红釉和乌金釉组成,红与黑的强烈对比,两色交混处自然窑变形成流金色泽,使得整个瓷体明艳大气,又雍容端方。三阳开泰瓶作为国礼,被赠送给多位外国元首。当时三阳开泰瓶的一级品,单件(件,是瓷器特有的体积单位)价4.2元,100件的三阳开泰瓶售价420元,供不应求,基本是还没出窑就被订购一空。
不断推陈出新的颜色釉瓷新品:凤凰衣釉、羽毛丝釉、翎羽釉、彩虹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奖项,也将建国瓷厂推向了最辉煌时期。
十年辉煌之后,转折到来。改革开放的国策,市场经济的逐步铺开,让建国瓷厂和其他国营瓷厂一样,逐渐显现出无法与之匹配运行的种种弊端,积重难返,求生艰难。
1995年,邓希平再次面临人生的重大关口。她为之倾注了二十年时光的建国瓷厂,全面亏损,已经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不得不进行改制,突围求生。一个拥有三千多职工的国营大厂,如一面镜子碎裂开来,分解为四十多个独立核算的经济体。每一实体的承包人,利用原来的厂房、设备分头组织生产,自负盈亏养活实体内的工人。
厂里的领导干部,必须响应国家的政策方针带头承包。这一年,邓希平五十三岁。作为厂领导,她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她实在放不下一手创建发展起来的“颜色釉研究所”。如果她不承包,研究所就面临解散消失的命运。她之所以犹豫,是深知这是一处“老大难”,所里的研究人员年龄偏大,长期脱离生产一线没有在线产品,而且,研究所自身没有厂房,没有设备,这意味着一切又得从零开始。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吗?
许是千百次失败炼就的韧性,许是专业自信带来的内心力量,邓希平拒绝了很多外来单位的邀请,迈出了至为艰难的一步—承包“颜色釉研究所”。
自负盈亏,意味着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没有设备,她就靠自己在厂里积攒的人气、影响力,找其他实体借,约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还有泥料、矿物原料,她都靠这种方式先借来。
厂里给他们一个两百平方米的废弃油库,油库里还有一个50吨重的大油罐,只能动用大吊车移走,可吊车费1000元,厂里也拿不出来。邓希平想了个办法,请来一些朋友买走厂里库存的瓷器,才凑够了这笔费用。
8天时间,终于将简易厂房中的一切准备就绪。选择什么样的首发产品,才能一步打开局面?邓希平想到了曾经俏销的“三阳开泰”瓶。
但“三阳开泰”瓶是两种釉在同一坯体上一次烧成,其难度是双倍的。且所里的研究人员年龄大,手上技艺欠缺,只有反复测试、调整,在一次次试错中寻找最佳方案。他们也没有自己的窑房,只能找别家的搭烧,这又增加了一重难度。一开始,根本烧制不出一、二级品,三级品也不多,四级以下的在市场根本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就意味着没有收益,支出却在不断累加。转眼,第一个月工资发放的日子临近,可账上的钱根本不够。不能让这批跟着自己的老职工寒了心,邓希平将家里仅有的一万多元存款都取了出来,将第一个月工资如期发了出去。而她家里,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
没有退路,只能向前。三年时间,处在巨大的生存重压之下,所里的人没有歇过一个星期天,没有安心度过一个节假日。为了搭烧别人的窑炉,除夕那天满窑,日夜守在窑房里,同事们和邓希平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别的单位想挖人,所里的研究人员一个都没离开。
三年后,所有的债务还清,经营走上了正轨。他们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不断创新的实力,让他们推出的每一种颜色釉瓷都能受到青睐。在看似光亮顺滑的表象之下,只有所里的人知道,每一样新产品,从设想到研发,再到形成成熟的工艺,那鲜亮夺目的釉面之下铺垫着多少艰辛。
六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拥有千峰翠色的“秘色瓷”,隐现于唐朝诗人陆龟蒙的诗句中,世人却无缘一睹其芳容。
传说,“秘色瓷”诞生于唐时的名窑越窑,在五代时达至工艺的巅峰,却在元代以后隐匿了踪迹。仿佛冰雪消融于无形,一千多年间,只闻其名不见其踪。
直到1986年,陕西宝鸡法门寺的十三层石塔在雷电轰击中倾坼,隐秘的地宫进入世人的视野。仿佛历史的地层翕开了一道缝隙,无数稀世珍品曝露于天光之下,令世界震惊。其中,就有色如冰玉的十余件秘色瓷器。“无水现水”,无论从哪个角度凝视,碗中都仿佛盛有半盏清水,莹莹如澈。
1990年,邓希平一行专家来到法门寺地宫参观。工作人员在讲解中提到“秘色瓷”,引动了邓希平内心的好奇。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展柜的顶层,在她的再三央求下,工作人员终于让他们一见真容。
那时,邓希平还不知道什么是“秘色瓷”,只觉其釉色匀净清透,似乎那碗中还装有半碗清水。面对她的疑问,工作人员微微一笑,用戴着手套的手将碗拿起来,翻转,没有水滴下落。再将碗放回原处,莹莹水光又出现碗中。
瓷器竟有如此神奇的光效?这一见,让邓希平与一种失传千年的颜色釉—秘釉结下了情缘。
对秘釉的探索,持续了十多年时光。一切都在狭小的实验室中进行,那是邓希平不肯轻易示人的探索。其间,她制作出一个蓝色窑变碗,依稀可见秘色瓷的神采,“无水现水”,光效神奇。邓希平没有声张,她知道方向对了,但秘釉瓷的成品率太低。秘釉似乎有多色的可能,她还要继续探索,直到洞悉秘釉的奥秘。
又几年,一个电影剧组慕名找到她,请她制作电影中的重要道具—流霞盏。流霞盏是明代景德镇制瓷大师吴昊十九创作的一种名瓷,薄胎如蛋壳,又似蝉翼,流彩霞光于一盏中飞泻流淌,色泽奇幻,有的在盏心窑变出诡丽的花朵,堪称瓷器史上极品。流霞盏的制作工艺和釉料配方,随着吴昊十九离开人世而遁为绝响。
如此高难度的颜色釉名瓷,邓希平并无十足把握,但她答应一试。头发已然斑白的邓希平,与颜色釉痴缠半生,也与失败劈面相逢过无数次,即使她穷尽此生也无法研制出流霞盏,那也不过是增添了失败的次数而已,如若她获得成功,她的颜色釉王国将增添又一个奇异的生命……
许是上天成全,就在她一次又一次失败,几近放弃的时候,一个集秘釉的纯净和流霞的异彩于一体的碗盏,自窑火中端然浮现。奇异莫测的窑变,在盏心,凝结为一朵绿蓝交融、红霞环流的“花朵”。
人造天成,这犹带有余温的碗盏,被邓希平握在手中,凝视良久。心潮如无风而静阔的海面,一种沉缓的力在深水处涌动。她为之取名“秘釉流霞盏”。
2013年,在一次国际瓷器展览会上,邓希平带着自己的颜色釉瓷参展。一位来自日本的朋友来到展区,看到她的作品,感到惊艳,问工作人员:“这些是低温颜色釉吧?”他不知道这些颜色釉瓷的制作者就在现场,邓希平没有言明身份,回答他:“这些是高温颜色釉,在137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烧成……”那位日本人不相信,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师—日本一位制瓷大师,老师告诉他:你不知道,在中国有一位大师可以烧出非常精美的高温颜色釉。他转而问邓希平:“您认识颜色釉大师邓希平吗?”邓希平笑着回答:“我就是。”
经验的丰富、技艺的纯熟,与依然蓬勃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催生了颜色釉王国里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生命。2012年,邓希平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辛丑年初,一头埋首抵角向前、前腿稳伫、后腿倾斜发力的“拓荒牛”,浑身灿红莹润,身披如毫纹理,被邓希平托举在手中。这是她献给挺立于大疫流年中的国人的一份礼物,那埋头奋进、砥砺向前的形象,深契国人的精神写照。
秋风已至,夏暑尚未消尽时,坐在我面前用沉缓的语速讲述往事的邓希平,一头银发,仿佛诸多荣誉堆积成的耀亮光环—高温颜色釉女王、国家级专家、高温色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唯一高温色釉国际金牌得主、“中国好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可我知道,在聚光灯照耀不到的那些时刻,光环淡隐,邓希平还原为那个坐在灰色简陋工作室里,埋头制坯、调釉、上釉,紧盯气窑温度显示屏,内心充满期待,眼神中又流露出些微不安的匠师。
每每在窑门开启的一刻,失意与欢喜的光影依然在她脸上交替闪现……五十多年来,她从不曾放弃这样的时刻,让自己不断与失败劈面相逢,也偶尔领受成功的喜悦,以探索的热忱、不泯的好奇和对生命的炽爱,不断拓展颜色釉“秘境”的疆域。
那一个又一个让世人惊异的生命体,无疑是天赐的奖赏。
——省景德镇老年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