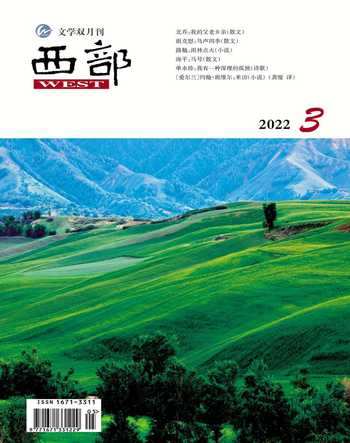肯德基里的杰克李
王国梁
一
六月里的一段时间,我都在离家不远的肯德基办公。那家肯德基有两层,紧挨着利津路加油站,设计为汽车穿梭餐厅。很多到此加油的车辆习惯加完油之后,绕道肯德基,点一份早餐或者午餐,开启新的一天。我是在那里认识了杰克李。
准确来说,是杰克李让我认识了他。
杰克李本名叫李杰,因为之前有过在外企打工的经历,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外国名字。被外企开除后,他仍然使用“杰克李”这个名字。他从离蛤城一百公里外的潍城到此谋生,先在同学胡玉明的网吧里当网管,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网络时代,网吧客流日渐萎缩,同学胡玉明请杰克李喝了顿大酒,跟杰克李哭诉自己要关门的艰难决定。胡玉明说,我要离开蛤城了,家里给我在宁城安排了个工作,朝九晚五,待遇优厚。杰克李说,从此天涯各方,我还在蛤城。胡玉明把杯子倒满,又不小心碰倒,杯子撞击地面,脆生生碎了一地。胡玉明说,杰,别找了,刘薇不会回来了。杰克李不说话,点一阵头,又摇一阵,泪从眼角涌出。
刘薇是杰克李的初恋,还没从潍城一中毕业就回到了蛤城。毕业照上,杰克李站在画面右上角,眼睛却一直盯着左下角,那本应该是刘薇站立的位置。那张照片上的人的名字,杰克李已经遗忘大半,迟迟不肯忘怀的只有刘薇。
杰克李随身带着那张没有刘薇的照片,游魂一样在蛤城大街小巷逡巡。他高中时给刘薇写了十一封情书,前十封都是让胡玉明转交的。到第十一封,胡玉明手脚稍慢了点,让趴在门后的班主任抓了现行。班主任把杰克李的情书当众念出,一边念一边点评,说这句“只有我的心放在你的心上,才能够感受到温度”是明显的逻辑错误。刘薇羞愧地一直低着头,杰克李却始终红着眼睛盯着刘薇。在全班同学的哄笑中,杰克李高昂着头,像个无畏的勇士。
刘薇到潍城一中本就是借读,“情书事件”发生后,刘薇父母便让她转回了原籍。从此,杰克李便再也看不见那条印满黄色碎花的连衣裙,看不见那倾泻而下的乌黑长发,闻不到刘薇身上丁香一般的迷人气味了。
杰克李一下子垮了下来,背着“警告”和“留校察看”的处分,无心读书,整日浑浑噩噩。班主任让杰克李叫家长来,杰克李就站在墙角拼命扇自己嘴巴,直到嘴角沁出血丝。后来,班主任不敢再刺激他,把他调到了教室最后一排靠墙的角落,任他如一把野草自生自灭。
其实没出“情书事件”之前,杰克李在班里也鲜有朋友,这源于他在初中时得了个“岳麓不败”的名号。杰克李总是留一头半短不长的头发,穿一件发黄的白衬衫,藏蓝色的卡其布裤子和一双破旧的布鞋。他的布包是单肩的,但从不斜背。包里除了装书和笔,还备有一个粉色的水壶和一面印有“HELLOKITTY”的镜子。
杰克李家离学校步行二十分钟,每天杰克李从家出发,走五分钟到胡玉明家楼下,喊一声胡玉明,然后一起去上学。杰克李捏着书包带,总是走得慢吞吞的。胡玉明就在一旁催,说你就不能甩起手来走,每次都是卡点到。杰克李也不说话,只是从鼻子里闷生生发出一个“嗯”来就当是同意了,可依然步履蹒跚,像尊移动的雕像。
“情书事件”之后,杰克李不再叫胡玉明上学。为此胡玉明跟杰克李好一阵道歉,得到的答案仍然是一个“嗯”。同学们渐渐发现,角落里那个闷闷的杰克李开始衣着乖张,甚至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书包涂满颜色,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蓄起的指甲修剪成椭圆形状。他在阳台上养了一盆多肉绿植,每天放下书包要么盯着那盆绿植发呆,要么就趴在桌上睡觉。
毕业后,胡玉明也搬去了蛤城,临走时给杰克李留了个电话,说去蛤城的话就去找他。此去三年,杰克李都不曾打过那个电话。他毕业后也去了蛤城,托亲戚关系在一家外企干保洁。每天员工下班他上班,十五层的大楼,他和另外四个保洁每人负责三层,倒垃圾、拖地、擦玻璃,一直忙活到凌晨。杰克李被开除,是因为有一次一个晚走的员工发现他走进女厕所,把这事报告给了后勤部部长,后勤部长第二天就把杰克李赶走了,说不报警抓他变态就不错了。杰克李也不反驳,勾着腰把随身行李塞进背包,走进蛤城如蛛网般的街巷。
二
蛤城自五月开启旅游季,六月已近沸腾之势。海边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体型庞大的旅游大巴在略显逼仄的海滨路上辗转腾挪,晃来一车又一车操各地口音和各种肤色的游客。很多游客第一次来蛤城,甚至是第一次看海,不免激动,又因准备不够充分,一阵清凉的海风过后,就开始瑟瑟发抖。
当全国大多数地方陷入高温炙烤的状态时,蛤城还处在穿短袖配不配外搭的暧昧期,且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七月中旬。因依山傍海,岛上多生薄雾。特别是晴天朗日,前一刻还阳光遍洒、蓝天白云、空气通透,立于海边可远眺小蛤岛,几乎是同时,肉眼可见的薄雾从海面生发出来,进而簇拥着向城市方向进发,高楼被薄雾环绕,若隐若现,颇有几分魔幻的味道。
杰克李自从被外企辞退,就蜗居在鲁迅公园附近的自助银行里。来蛤城时身上带了一千块钱,加上在外企挣了三个月的工资,刨除路费和日常吃饭,现在全部家当总共三千五。在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前,他必须精打细算。蛤城房租贵,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地下室每月租金也得一千五,再加上水电费,没有一千七八下不来。杰克李不想麻烦亲戚,况且也不算多么亲近,是母亲同村的邻居家的孩子,能帮忙介绍第一份工作已经仁至义尽,何况被开除,哪还有脸再去叨扰。
杰克李算过一笔账,在自助银行里省了房租,对面有公厕可供洗涮。每天吃馒头、咸菜和辣椒酱,完全可以应付个一年半载的。白天,杰克李收拾好行李,转战到利津路上的肯德基,找个临窗的位置坐定,可以喝免费的水,充免费的电,还能享受免费的空调,最关键的,没有人来赶他走。他有大把的时间来寻找刘薇。
杰克李的行李中,还有两封情书,那是他来蛤城后写的。他准备找到刘薇后當面给她,至于给她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没有想过,也不去想。
利津路肯德基平时只开一层,为了节能减排,也为了节约成本。杰克李选择一进门靠窗的位置,长条座有三个座位,外侧有充电插口,也能直接插电源。这排长条座没有靠背,久坐并不舒适,是专供给匆匆就餐的独身者。杰克李每天七点半起床,收拾停当后奔赴此地,卸下背包,充上手机,带好耳机,便开始了一天的煎熬。
我来临时办公后,行李放在中间,又占去三分之一,跟杰克李毗邻而坐,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同桌。我测了一下网速,达到了专线的水平。如此,杰克李便有了一处得以栖身和消磨时间的绝佳场所。
我买了肯德基的咖啡月卡,每天花一块钱就能换一杯中杯美式咖啡,白开水是免费的,可以随时续加。我拿出电脑,处理公务或写作,一天的时间过得充实而高效。中午,我用APP里之前攒下的金币兑换一个汉堡,权当简易午餐。杰克李从不点餐,甚至连免费的白开水也不要。待我吃完,他便从包里变魔术一般掏出馒头、咸菜和辣椒酱,头也不抬地吃起来。他有一个随身的杯子,奇大无比,可以称之为“暖瓶”。他似乎喝水也很少,一上午的时间,我几乎要起身三到四次,要么出门到路边抽根烟,伸伸胳膊,活动一下腿脚,或者去上厕所,续一杯白开水。他除了上厕所,几乎不起身。唯一专注的就是刷手机、看视频,偶尔爆发出低低的笑声。有一次,我见他从包里掏出了痒痒挠挠后背,差点喷出刚喝到嘴里的咖啡。杰克李到底在等什么,在找什么,不禁让人怀疑,他究竟是不是在找刘薇。
三
我在蛤城海洋研究所下辖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平日的工作是从邮箱里挑选全国各地的投稿,然后审稿、送二审,再就是在出刊前校对一下。工作轻松,节奏缓慢,基本属于养老单位。
杂志社坐落在信号山路三十六号,是蛤城典型的老城区,地形复杂,道路狭窄,且单行林立,进出都不方便。平时上班,我大多坐公交车。中间倒一站,步行不到一公里,也算是难得的运动机会。
杂志社租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座老楼,日占时期的建筑,是时任蛤城伪市长给闺女修的陪嫁楼,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用作单位办公。这座老楼见证了蛤城百年兴替、风雨飘摇仍屹立山脚,经历过几次修缮,面貌已不同往日,基本看不出原本肌理,恍若一位老人化了濃妆又穿上了戏服。
去年雨水多,加上蛤城持久的阴霾潮湿,老楼里生了不少霉斑,楼顶也有多处漏雨,机关事务局统一安排进行修缮。我们被通知三个月内不能上班。家里孩子小,也没法办公,只好找个临时办公地。经过一番比对,我相中了利津路上这家肯德基。
和杰克李同桌已经半月有余,我们彼此没说过一句话。直到有一天,我放在中间的电脑包不慎滑落,杰克李见后帮忙拾取,递给我,微笑着点点头。我接过电脑包,说了声谢谢,算是正式打过招呼。
每天都见,慢慢从打招呼开始断断续续地聊几句,但仅仅维持在几句。仅是每天简单的几句,也让我拼凑起了杰克李和刘薇的故事。杰克李不善聊天,也不愿聊天。他有自己的世界,而我也不想浪费难得的创作时间。
码字和审稿的间隙,我常出门放松,点一根烟,看路上匆匆驶过的车辆,以及面容倦怠、在路边等红灯的老人。偶尔回身,透过玻璃打量窝在窗边的杰克李,他竟然穿了一双女士凉鞋,黄色的短袖T恤配白色短裤。一连一个礼拜,都是这身打扮。因为坐得近,偶尔我也能用余光窥探一些他的举动。
他的背弓着,双眼不离手机,间或从包里掏出一把镜子和剃须刀,对着镜子刮胡子。刮完后又掏出指甲刀,一会儿剪手指甲,一会儿又俯下身去剪脚指甲。他的脚很大,几乎要从女士凉鞋里挣脱出来。脚上遍布黑色灰色的污点,那是被蚊子叮咬后留下的痕迹。
因为坐的时间很久,起身的时候往往要慢慢先把脚从位置上挪出,进而身子跟着扭动出来。我发现他好像直不起身子,一直弓着腰走,双手在身边甩动,像一只在水中游走的章鱼。
他不说话,我也不说,我们就这么相安无事地占据着肯德基店内的一角,像两个末日武士,彼此空虚又彼此暗中蓄力,可惜的是始终没有任何外力来打破这一平衡。
四
百年难得一遇单位整修不用上班,单位上下欢欣鼓舞,但天算不如人算,单位安排我出差宁城。
宁城在蛤城东北方向,相距两百公里,同享渤海湾。从蛤城到宁城没有直达的动车,坐长途汽车需要四个多小时,中间还得在淄城高速服务区停一会儿。
一路上我都在听一首叫《白日梦》的老歌。歌手嗓音很具特色,中音区饱满,高音区通透,低音区虽然稍弱,但他用气息加上诉说式的唱法进行了巧妙的弥补,听起来很走心。听到半路,长途汽车驶进服务区,车门打开,乘客们纷纷下车。车里顿时安静了不少,我忽然想起杰克李,不知他此时正在干什么,是不是还在肯德基里看手机。
这不是我第一次到宁城,海洋所在这里有个研究点,负责人老徐是从所里调过来的。老徐是宁城人,本来在蛤城有望混成副所长,但有个身患自闭症的孩子,所以主动提出调到宁城来。
我刚到海洋所杂志社的时候,带我的师傅老华曾与老徐是所里同事,后来老华酒后中风,抢救过来又恢复了半年,最终还是瘸了一条腿。所里照顾老华,安排他到杂志社,待遇和副高一样,但几乎不用看稿,偶尔来开开会、举举手、发发言就行,算是提前享受了退休生活。老徐几乎是同时申请回到宁城,有一次所里领导到宁城视察,负责宣传的所里同事临时有事,杂志社派我陪同,给领导拍拍照、写个小信息什么的。老华知道我去宁城,惦念老徐,还托我捎去两瓶蛤城特产小琅高,说当年跟老徐喝酒量上经常谁也不服谁,喝蛤城啤酒分不出高下,就喝高度白酒。有一次两人在小酒馆,喝了啤酒又喝白酒最后两人都喝大了,互相搀扶着往家走。两人绕着小酒馆走了三圈,一直转到凌晨,海风萧索,两人脑子逐渐清醒,才分手告别。谁知,一别就是十年。
得知我来宁城,老徐老早就张罗了一大桌子人,晚上要给我接风,又亲自开车来车站接我。几年不见,老徐看上去变化不大,除了头顶的头发变得更加稀薄了。老徐这几年在宁城混得不错,跟当地几个朋友投资开了个水产养殖场,养海参和大闸蟹,凭借之前在海洋所积攒的资源,买卖做到了南方和西北,换了房子换了车,老婆辞职在家专门照顾孩子。
老徐开着奔驰,载我来到了位于宁城市中心的一家大酒店。刚进门,酒店经理就热络地迎了上来,徐总长徐总短地照顾,又说都安排好了,还是老地方。房间名字的确叫“老地方”。客人到了大半,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老徐一一为我介绍,这是某某局孙局长,这是某某院张院长,这是某某所宫所长……介绍完了,把我让到主宾,说客随主便不要推辞,又补充道,还有个干物流的小胡总马上就到,咱们先开始。
白的红的啤的纷纷倒满,老徐端起杯,介绍说我是他在蛤城最好的小兄弟,这次来宁城出差,是领导视察工作。我不好意思,说就是个小破编辑,来打扰了,给大家添麻烦。一旁的张院显然是老江湖,马上补充说,一看刘老师就是年轻有为,一表人才,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文气。其他人马上附和称是。
领过两杯之后,我明显感觉肚子里在发烧,于是赶紧吃两口菜压压酒。
这时,一个身影推门进来,老徐摆摆手示意赶紧进来。来人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面容白净,一身正装,利落的短发,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来人面带微笑,直冲我走来,边走边伸出手,笑着说抱歉抱歉,又冲老徐说这就是从蛤城来的贵宾吧,失敬失敬,在下小胡,胡玉明,干物流的。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我在心里打鼓,思緒一下子回到蛤城。
那是我跟杰克李唯一的长聊,起因是我请他吃了个汉堡。其实那天我有张买一赠一的券,第二天就要过期,本来也要吃午饭。像往常一样兑换完之后,听服务员叫号,取餐。
取回两个汉堡后,我从余光瞥见杰克李背包里的馒头,体内某根神经跳动了一下,我把一个汉堡递过去,杰克李愣了一下,进而局促地摘下耳机,说不用不用我带饭了。我说别客气了,两个我也吃不了。犹豫了片刻,见我坚持,杰克李便接过了汉堡,但没有直接吃,而是放进了背包里。
那个下午,杰克李竟然破天荒跟我说了十分钟的话,也是这十分钟的聊天,让我得知他的大概身世,也记住了“胡玉明”这个名字。
酒桌上,我特意关注了这个叫胡玉明的人,并且利用间隙小心求证着是否此胡玉明就是杰克李口中的那个胡玉明。胡玉明在桌上只字未提蛤城任何事宜,仿佛在蛤城就不认识什么人,按杰克李的说法,胡玉明曾在蛤城开过网吧,而且杰克李也在那里打过工,见到蛤城来的朋友,他怎会只字不提呢?
酒宴结束,我们都喝了不少。本来单位安排了酒店,但老徐执意要找个地方再喝点,不好驳他面子,此时胡玉明在老徐耳朵上又嘀咕了几句,老徐听完便跟我说,听哥哥的,一会儿带你去个好地方。
五
老徐说的好地方离市区挺远,胡玉明找了个代驾,一上车就莫名兴奋,说今晚终于开了个豪车。
坐在奔驰大吉普后座上,我和老徐说起老华。老徐问,老华身体还行?我说挺好的,能吃能睡,最近喜欢上了钓鱼,经常几个人包条船,一出去就三四天,钓了黑头钓八带,有时还能钓到刀鱼。老徐说,那就好,我们这个年纪就得自己找乐子。胡玉明在副驾上搭话说,徐总还年轻呢,去年还组织进藏,不少人都高反,您不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身体素质太棒了。老徐摆摆手说,嗨,别提了,人家都说身体好的反应才大呢,我那是身体不行才没事。
代驾拉着我们七拐八转,在冷清的街道上穿梭。宁城也临海,却不似蛤城般潮湿。虽至深夜,城市的霓虹仍然清晰可辨,轮廓鲜明,要放在蛤城,早就蒙上了一层雾,光怪陆离地氲荡开来。
我们在一处私宅前停下车,老徐刚刚打了个盹,停车的一瞬他的头往前一冲,进而喉咙里传送出轰隆隆的声音,哦,到了。
私宅有些徽派建筑的风格,门不大,门口车也不多。胡玉明抢两步上前,摁响门铃,不到一分钟,吧嗒一声门开了,胡玉明把我和老徐让进门。刚进门就看见了满眼的绿竹,在灯光的映照下,更显葱翠。碎石路延伸两侧,有假山、小亭,精巧而不做作。院内有一湾水塘,四五平方米,睡莲环绕,湾边一座小水车汩汩涌动,扬起的湾水也似平添几分慵懒,不喧哗,不张扬,兀自沿水车车道滑下,坠入湾中,并未搅动起多少波澜。
往里走两步,就有一白衣素女子出门迎接,声音和缓,问一声:您来了?胡玉明便接话,这是我的两位贵宾,快迎一下。又回头跟我介绍,这位是苏芸,这里的老板。老徐显然是熟客,带着几分酒气打趣道,苏老板真给面子,还亲自出来迎接。玲玲去哪儿了?苏芸含笑,一边引我们往屋里走一边说,徐总老不来,玲玲等不及,这会儿是不是快到您公司了?一句玩笑话,让老徐笑得前仰后合。我不禁在心里感叹,这女子真不简单。
四人到屋里坐下,桌上已经烧开了水,茶已经备好。胡玉明跟苏芸说,你去忙吧,我来照顾两位贵宾。老徐不依不饶,胡总你真行啊,玲玲不让见,苏芸也不让见,然后跟我使眼色说,刘你不知道吧,这个地方,他指指桌子,又指指胡玉明,意在告诉我,这里是胡玉明的地方。胡玉明不好意思地笑,说都是朋友的地方。又转头对即将离开的苏芸说,苏总,你把我存的茶拿来。苏芸说,知道贵宾来,壶里放的就是好茶,放心吧。转身挑帘进了里屋。
洗茶、泡茶、喝茶,胡玉明操作得行云流水。这期间,苏芸几次进出,端进来六七个小菜,看着就有食欲。胡玉明又从身后的博物架上取下一瓶酒,说是一位故人自己酿的,来喝的都说不输茅台。倒满三盅,碰杯仰脖。果然是好酒,入口绵柔,进而在口腔绽放,香味婉转,又蹿进鼻腔,只一口便让人飘飘然。
胡玉明跟我东拉西扯地聊着,老徐在一旁,看上去有些累了。毕竟年龄不饶人。又过了一会儿,胡玉明提酒,老徐红着脸摆摆手说,你们喝,我到边上先眯会儿。说着便起身扎到了旁边的沙发里,不久便打起了呼噜。
我和胡玉明面面相觑,看着熟睡当中的老徐忍俊不禁。窗外响过一声闷雷,看样子要下雨。果然,不久就噼噼啪啪地下了起来。
一瓶酒喝下一半,我忍不住问胡玉明,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李杰的人?
胡玉明端着茶杯,茶到嘴边忽然停住,稍稍停顿,喝了一口才缓缓放下。
胡玉明说,你认识杰克李?
我说,你果然是那个胡玉明啊。
胡玉明未置可否,捏着瓶子倒酒,边倒边说,杰克李跟你说什么了吗?
我感觉胡玉明显然没有了刚见面时的热络,而是多了一分冷静和克制。这对一个成熟的商人来说并不罕见,但对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份冷静和理性让人发怵。我对他和杰克李的事所知不多,不过是因为刘薇串了个小故事。话题至此,我只好顺着说下去。
我说,在肯德基认识的,也没说什么,就说他来蛤城得到了你的照顾。
说完,我看着胡玉明。窗外的雨下大了,风也不小,沙发里的老徐睡得很沉,脸歪在沙发靠背上压变了形。
胡玉明没急着回答我,先给我倒满了茶和酒,又示意我吃点菜。我夹了一颗油炸花生米,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等着胡玉明的话。
胡玉明又喝了口茶,跟我说,杰克李跟你说他到蛤城是找刘薇吧?
我说,是啊,他说刘薇是他的初恋,高中时候写情书被学校记过。
果然。胡玉明说,他还是那个样子。
我陷入糊涂,不知道胡玉明有一搭没一搭的到底要说什么。
胡玉明看出了我的困顿,没急于补充,而是从里屋喊了一声,苏芸,拿一条薄毯出来,给老徐盖在身上。苏芸从里屋闪身出来,轻轻地把一条淡紫色薄绒毯盖在老徐身上,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回到里屋。
胡玉明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跟我说,刘老师,根本没有刘薇这个人。
啊?我不禁有些吃惊。
胡玉明说,我跟杰克李是同学不假,但根本没有刘薇这个人。杰克李一直被他继父虐待,他继父是个神经病,每天喝酒,喝完了酒就打他妈妈,打完了他妈妈就打他。你看到杰克李的脚腕了吗?我点点头。
那是他继父把他吊在房梁上勒的。
我感到惊愕,颤巍巍地问,难道是吊起来打吗?
胡玉明把一棵散落的茶梗用纸巾擦走,抬起头缓缓地说,何止啊,他爸爸会用钳子拧他的肉,转着圈拧,你能想象吗?
我问,那就没有老师发现管管吗?
胡玉明说,怎么管。杰克李从来不说,再说,他后来就变得神经兮兮的,总是找刘薇。老师见了都躲他。
我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胡玉明说,他让我给刘薇送情书,可班里根本就没有刘薇这个人,我送给谁啊。我怕班主任发现他的秘密,一直替他隐瞒。那次他递给我情书的时候,让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在班上念完情书,杰克李的病就更严重了。
我问,那刘薇到底是谁啊?
胡玉明回忆说,我只记得有一年学校来了个实习的女老师,叫刘蔚,对杰克李挺好的。大概他弄混了吧,谁知道呢?
屋内传来一声声响,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
我急迫地想知道答案,于是追问,那后来呢?
胡玉明不動声色地说,后来他来蛤城找我,我说杰别找了,根本没有刘薇这个人。他就拿出照片给我看,我说你仔细看看,这上面哪有刘薇这个人。他就指着一个人说,这不是刘薇吗?我一看照片,他指的那个人是他自己。
我说,那他说他在你的网吧里打工,还去外企打工。
胡玉明说,去外企是我让我爸给他介绍的,他以为那是他亲戚。后来他进女厕所,被人抓住,他说他去找刘薇。其实根本就没有刘薇,因为……胡玉明茫然地抬头看着窗外,又光顾了熟睡中的老徐,眼神转回到我身上时似乎闪出一丝狡黠。他缓缓地叹了口气说,或许,他就是刘薇。
我感觉酒精一瞬间全部涌上头来。窗外风雨大作,雨点密集地打在窗户上,屋檐上挂的灯笼疯狂地摇摆,灯光甩动,映照着老徐的脸忽明忽暗。
胡玉明说完,又恢复热络,说,好了刘老师,也不早了,叫醒老徐,咱们撤吧。
我愣了半天,回过神来。赶紧说,哦哦,好。
苏芸从屋里出来,说再等等吧,现在雨太大,回去的路不好走。
胡玉明看了眼窗外,迟疑道,也是,这么大的雨,估计路上有积水了,我们再坐会儿。
我说,胡总要不你先去休息吧,我料想胡玉明在此肯定有休息的房间。胡玉明说,那我们都去楼上休息一下吧。说着轻轻推了推老徐,示意上楼。推了几下,老徐醒来,我们被安排在两个房间。关门前我特地放慢了脚步,看到苏芸和胡玉明进了另外一个房间。
第二天,老徐陪我查看了几处海洋所的联系点,又跟各个点的负责人攀谈了几句,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算是完成了出差任务。下午,我执意要离开,老徐很是抱歉,说没照顾好,又从后备厢拿出两盒海参,说让我给老华一盒,补补身子。
告别老徐,我在长途汽车上昏睡了一路。仿佛隔夜的酒还在持续发力,耳机里的音乐仿佛还是《白日梦》,可歌手的声音似乎已经变调,磕磕绊绊地让人烦躁。我摘掉耳机,继续眯着眼,回想着胡玉明说的话,还有那声声响。
回到蛤城后,我有几天没去肯德基,等想起来要干点什么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下旬。利津路的肯德基依然没什么人,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花一块钱点了一杯冰美式,又要了一个杯子,倒了一杯温水,拿出笔记本电脑,接通电源,开机,接通肯德基里的WIFI。中午,我点了一个汉堡,又用券换了一盒薯条和一个蛋挞。一直到下午,我都在电脑上写一篇小说,名字叫《肯德基里的杰克李》。
那天,杰克李没来,我身旁的桌子空空如也。此后,我再也没在肯德基里见过杰克李,仿佛他从未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