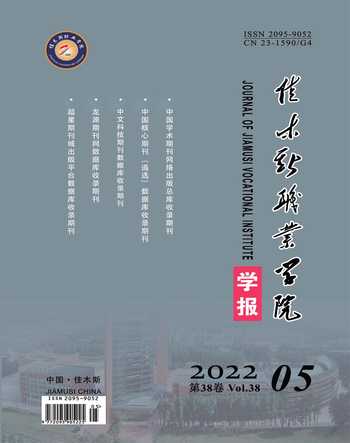镜像关联模式下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蔡开祺
摘 要:此研究旨在扩展和丰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新礼服》中镜像关联的研究课题,其新颖之处在于首次提出小说中具有镜像映照下的象征意义、镜像投射下的隐喻所指以及镜像对比下的反思认知三个层面的镜像关联。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分析,此研究挖掘出以往被忽视的诸多层面的叙事手法和有机关联,弥补了以往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叙事研究的不足,拓宽了国内对伍尔夫小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镜像;象征;隐喻;叙事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2)05-0-03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意识流写作风格的先驱。她著作丰富,被认为是早期女性主义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并且对随后的女性作家作品有一定的影响。伍尔夫的短篇小说《新礼服》(The New Dress)写于1924年,出版于1927年。這篇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描写女主人公梅本尔·沃宁穿着一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新礼服,去参加一个上流社会的宴会时的心理冲突与思想波动。为了参加这个宴会,梅布尔特意从一本古老的巴黎时尚杂志中选取一个心仪的礼服样式,邀请米兰小姐别出心裁地将其设计成一件黄色礼服,希冀能以一个完美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当梅布尔穿着这件黄色的新礼服到达宴会、脱去风衣时,她在镜中看到了自己,和宴会上其他人的穿着相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新礼服是不合时宜、陈旧过时的。她如坐针毡,想象着被人挖苦和嘲笑,心里产生了种种镜像联系。
通过细读文本,笔者发现伍尔夫采用一流的意识流写作方法和叙事艺术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并详细地向读者展现女主人公梅布尔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她也描述了几个生动的镜像供读者去想象。这些镜像具有象征、隐喻与所指的意义。在这些镜像的关联和对比下,梅布尔最后认清了自己,明晰了自我,在心理和情感上获得了新生。因此,从镜像理论的视角分析这部小说是有文本依据和现实意义的。
一、镜像映照下的象征意义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于1936年明确提出了镜像理论。作为镜像理论的一部分,镜像意识是一个神秘的瞬间,是一种将现实与想象所混淆了的意识。这个意识产生于镜像阶段的想象界,想象界属于人的主观意识领域,是文化环境使个体形成其特征的所有一切,不受现实原则支配,遵循视觉或虚幻的逻辑,并继续发展到成人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贯穿于个体发展的始终[1]。
在《新礼服》这篇小说中,镜像映照下的象征之一是小说中昆虫的象征。当梅布尔穿着黄色礼服去赴宴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木偶一样,木然地站在那里,似乎正在被人们别上别针、修改褶边、纠正不足。伍尔夫在这里使用的比喻非常生动和形象,让读者具体地了解到梅布尔是如何被人评头品足。宴会上有个女客人肤浅地说:“梅布尔穿的是什么?!她看起来是多么地吓人!她穿了一件多么可怕的新礼服!”还有露丝·萧,一个穿着时尚礼服的女人,向梅布尔走过来并告诉她这件新礼服很完美很迷人,但梅布尔确信露丝在嘲笑和挖苦自己。在想象的镜子映照下,梅布尔似乎看到自己犹如一只苍蝇,奋力挣扎着向奶碟中央游去,只为分得一些残羹剩饭。她利用不同的昆虫来象征梅布尔和上层社会的人们。她认为自己穿着黄颜色礼服的形象犹如一只苍蝇奋力地向上爬,而宴会上的其他人就像蜻蜓、蝴蝶等美丽的昆虫。梅布尔把宴会上的人们想象成各种昆虫和小动物。她觉得宴会上的人们像成群的昆虫一样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中飞来飞去,他们对所谓的约定俗成的时尚趋之若鹜。当她告诉一个男性客人她感觉就像是一个寒酸而污浊的苍蝇一样,这个男性客人只是虚假地夸赞她。这些叙述细节都反映出宴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沟通和理解而形成了一种疏离和冷漠的人际关系。
镜像映照下的另一个象征是小说中礼服的象征。在这篇小说中,伍尔夫通过赋予新礼服黄颜色的属性和特征,象征着礼服主人梅布尔具有太阳一样的光辉。伍尔夫运用这个叙事手法和艺术暗示出梅布尔是宴会上独一无二、像太阳般闪耀的人。然而,礼服也是女性身份和阶级限制的隐喻。礼服和女性身份的紧密关系通过梅布尔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实际上,礼服是梅布尔身份独创性的象征和隐喻。她对优雅的感觉和审美与宴会上的人们看法相佐。这体现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环境中,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使梅布尔为自己的独创和真实感到心烦意乱,也使她否认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实际上,礼服权威的背后是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它似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主体的认知行为,而人的内在真实欲望也同时被掩盖起立[1]。通过梅布尔的礼服意识,伍尔夫指出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应融合在一起,同时她也指出阶级话语权内在与时尚的社会和文化含义中,也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对于伍尔夫自己来说,礼服也是一个避之不及的问题。她对礼服有一种矛盾和复杂的情感。1926年6月,在她购买一件礼服后,她在日记中写到:想到要去裁缝店里进行量体裁衣这个可怕的、艰巨的任务,我就禁不住颤抖和战栗。由此可见,她对时尚的社会和文化含义不置可否。她对时尚的概念和态度深刻地体现在这篇小说中。
伍尔夫在这篇小说中探讨社会等级的主题。这个叙事艺术不仅是通过梅布尔在宴会上的不安所呈现出来,也揭示出不同的社会阶级沟通和交流的困难和障碍。梅布尔身处平民阶级,从来都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新礼服。在童年时代,她就梦想着能远离这样的生活,嫁给一个英雄一样的男人。但当她在宴会上回顾自己的故乡生活时,她内心是快乐充实的,和在宴会上的心理截然相反。在宴会上,梅布尔不喜欢自己精心准备的礼服,因为它没有达到她所希望取得的效果:展示她独一无二的美丽、风格和身份。当露丝·萧告诉她礼服很美时,梅布尔认为露丝·萧在嘲笑自己,甚至当别人在谈论各自的生活时,她也想象着他们正在对自己的礼服秘密地进行着讨论。在这样的语境下,礼服很明显地代表了一种社会高压,是影响梅布尔个人身份的一种社会力量,使她放弃自己的风格,为自己的选择而心烦意乱。伍尔夫灵活巧妙地运用意识流的文学艺术风格,以第三人称为叙事角度的全知叙述者充分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详细揭露出人物的心理欲望。在这篇小说中,梅布尔的内心想法和活动不是理性地进行着,而是像浮萍一样不稳定地游移。当梅布尔的内心活动和灵魂迷失在宴会上时,她进行了残忍而诚实的自我剖析,探寻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情。伍尔夫有技巧地使用这一叙述视角,运用一些独特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如“odious、weak、vacillating”等形容词来描述梅布尔所处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起伏。
二、镜像投射下的隐喻所指
隐喻是文学艺术表达的方法和途径。隐喻是将意义和形象加以压缩、叠加,意味着受压抑的意义(欲望)通过隐喻取代了表面的意义,从而实现了欲望。在《新礼服》这篇小说中,镜子具有隐喻的功能。镜子并不只是具有单独的意义,而是被赋予宏大的叙事内涵。在镜子中自我形象表面的映照下,梅布尔感到不安和尴尬。梅布尔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犹如一个黄颜色的圆点,露丝·萧犹如一个黑颜色的圆点。在这个层面上,她们都是像圆点一样的存在。从这个层面来看,镜子反映出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投射出女性在社会中具有像一个圆点大小的微不足道的形象。并且,一面不大的镜子撕碎了梅布尔的礼服并使她保持独创性和新颖风格的自信心受挫。在梅布尔感到自我憎恨和懊悔的痛苦时刻,镜子具有压迫性的属性体现了出来。此时,镜子是性别和阶级力量的隐喻,使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无意识地服从于外貌至上主义,并且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中控制着女性的衣着和外貌。因此,梅布尔的恐惧来源于镜子投射下的社会压制。因此,从隐喻的角度看,镜前的梅布尔近似于能指,镜中的镜像则类似于所指。能指在所指链的不断滑动等于由或缺引起的欲望活动,而终极所指则永远遭到压抑[2]。镜子也是文化架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礼服》这篇小说中,镜子在米兰小姐的裁缝店里是友善的。然而在宴会上,这面镜子又是有敌意的,让梅布尔的心情处于低谷。梅布尔通过观察镜子后发觉,她笨拙的社交生活和精致的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冲突。她靠重复莎士比亚的诗句来减少自己对镜中形象的憎恶。实际上,此时的镜子是梅布尔在宴会中痛苦存在的一个象征,将她的自我意识从思想灵魂中分离开来。镜子同时也加剧了梅布尔的焦虑,既反映出她无法和宴会上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保持同一水平的尴尬状态,也使她的意识和心灵处于麻木状态。
三、镜像对比下的反思认知
在《新礼服》这篇小说中,镜像对比主要体现在米兰小姐的裁缝店对梅布尔来说是一个安全可靠、舒适自在的地方,而达威洛夫人的宴会则与此相反。当回想起米兰小姐为她小心翼翼地用别针固定礼服的褶边时、询问她的穿衣尺寸时,她感到在米兰小姐的裁缝店里是多么的快乐和自在。然而,当梅布尔身处宴会时,她快速从这些愉快的回忆中抽离出来。当她清醒明白之后,她为自己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懊悔,她禁不住严责自己随波逐流、摇摆不定的想法和行为。梅布尔回想着自己在普通家庭里的生活。她梦想着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拥有一个浪漫又冒险的生活,但她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嫁给了一个有稳定工作的男人。她回想到过去的普通生活,认为是愉悦和天赐的。因为这些是她唯一感到真正充实快乐的时光,犹如处在浪花的波涛里。她也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时光会越来越少。因此,主人公的心理特征描述和宴会场景和镜像反映出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米兰小姐的裁缝店和达威洛夫人的宴会。伍尔夫深刻描绘主人公的心理意识,从而在这个短篇小说杰作中富有叙事技巧和艺术地描写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性的心理状态。在小说中,梅布尔径直走向宴会房间的尽头,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她凝视镜中的自己,凝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看,当然不只是观看,而是在凝视的时候,人们同时携带并投射自己的欲望[3]。这时,主任公意识到新礼服不合适。这显示出她在宴会上有一种被排外的感觉,也是她从童年时代起就产生的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同时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梅布尔从女孩到成年女性起,总是经受这被凝视、被评价的境遇。然而,人人都穿着最新潮、最时髦的礼服,把固化的社会思维和风俗穿在身上,但梅布尔不愿趋之若鹜,她不禁在内心深处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有所创新?为什么不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新礼服是梅布尔从母亲的巴黎时尚杂志中所选的,因此具有一种历史感。然而,这和宴会上公众的评价存在冲突。实际上,这是先入为主的社会规格纠正的体现,也反映出女性的外表穿著被物化的镜子和有偏见的社会意识所影响。因此,当受到宴会上人们看法的影响,梅布尔并不是由衷地接纳它和坚持自己的风格,而是盲目地受宴会上他人话语的影响,彻底否定了新礼服与众不容的美,正如否认她自己独特的美一样。
梅布尔厌弃自己的新礼服是因为别人不懂得欣赏。她通过别人的看法来认识自我,而不是通过自我意识来认识自己,好像她是自我认识的局外者和陌生人一样。这不是真正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关于我们是谁?我是谁?单个的“我”又是什么?说“我”时意味着什么?好在最终梅布尔被现实唤醒,感觉到自己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她尝试去重新塑造一个自我形象。在宴会上人们看法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下,梅布尔通过质疑自我、剖析自我来改变和完善自己的形象,经历了心理上的改变和重生。她试图寻找某种方式来结束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因此她选择离开宴会。梅决定在离开宴会后的时光里拥有一些与此不同的经历,同时也是伍尔夫的愿景:她明天将去伦敦图书馆。她将会找到一些精彩有益、让人惊喜的书。或许很巧合的是,这本书由一个牧师所写,抑或由一个无人知晓的美国人所写。或者,她将会沿着河岸旁边的街道走,碰巧走进一个门厅,一个矿工正在那里讲述自己在矿井里的生活。就在这一瞬间,她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她感觉自己被彻底改变了,由内到外。她将会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即使会被人叫作大姐;她将再也不会对自己的穿戴多加考虑,并且她也将查尔斯和米兰小姐以及这个宴会上的人和事看得通透。因此在以后一天天的日子中,她将会沐浴在阳光下或为家人切羊肉。
伍尔夫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巧妙地运用心理独白的叙事艺术使梅布尔在心理上产生自然的变化。伍尔夫在此暗示梅布尔不仅逃离了宴会上那些肤浅的看法,开始要掌控自己的生活,拥抱她的个性和魅力。她不再通过别人的看法来看待自我,使她逐渐意识到意欲融入的上层社会生活在现实中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因此,她选择离开宴会,也是离开上层社会虚假的生活,去过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
四、结语
伍尔夫建立了现代心理小说的标杆和趋势,进一步深化了意识流写作。在《新礼服》这篇小说中,伍尔夫通过女主人公梅布尔心理状态的起伏来使故事情节发展,这些心理活动常常由一个转瞬即逝的场面来唤起,即使没有说出来的话语和声音,读者也能感受和理解到小说中任务的内心想法和心理变化。同时,伍尔夫着重探索女性的内心意识和精神世界,描写出女性错综复杂、纷繁多变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新礼服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定义的心理意识过程。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穿着新礼服去赴宴的场景,伍尔夫深刻地刻画出宴会上女性的思想意识变化过程。尽管外表会蒙蔽和欺骗自我意识,使自我认识受限,但伍尔夫强调,女性的自我认识并不是没有出口。女性主体可以通过镜像关系认识自己,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在对象化的镜像关系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从而意识到自我的思想所在、灵魂所在。伍尔夫不是用口号来号召女性进行自我认识,而是在作品中用微妙的镜像关联来强调这一主题,即女性构筑自我精神世界,不受惑于他人,也不随波逐流。
参考文献:
[1]李慧.浅析拉康镜像理论的来源及建构[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9):90-92.
[2]侯入元.陷在心狱里的镜像——论张爱玲《茉莉香片》[J].大众文艺,2010(24):150-151.
[3]王秀芝.爱的毒药与糖果——《苦月亮》:映照人性的镜像之旅[J].电影画刊(上半月刊),2009(3):36-38.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