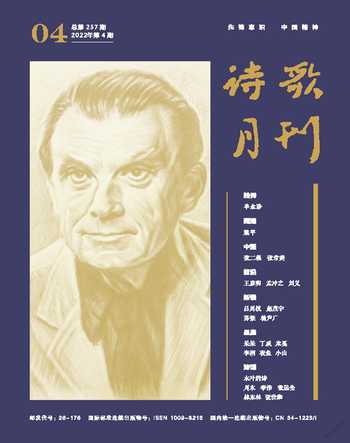搁浅(组诗)
夜鱼
致意
初冬阳光短暂,刚过午
已倾斜软塌下去,离消隐
也就两三盏茶的工夫
闲坐于亭,被密密匝匝的绿
环绕,高楼缝隙间射来的阳光
使得周身的一切
浓淡相宜,明暗有序
也使得虚搭的树林花园
呈现出的光阴
干净、真实,又来去无迹
上周那枝蓝色绣球花
在你左肩后摇曳的那枝
仿佛不是萎谢了,只是向我们
致意后转身暂离
我将记下这座山这座亭
记下每一瞬,活着的
挚爱与悲欣
红枫树下
那棵红枫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
百年老树,该有多少故事
我很想和你探讨,诸如
黄荆山、磁湖
以及这里的张姓原住民
据说他们就是从红枫树下的渡口
船行磁湖,再渡长江
然后在集市里出清鱼获
可惜这一切连同村名已被人从地图上抹去
你也所知不多
有些含糊其词,但你很清楚
此處地产房价高的来龙去脉
浓厚的古红枫翠荫下
你指着隔栏外的一片低矮拥挤
“瞧,张姓人家搭盖的违建。”
搁浅
山路上的野草莓,被我再次摘下
递到嘴边。细竹招摇
高挑的青叶,一片片,随风,时缓时急
摩挲着我们时淡时浓的情绪
将青苔民院来回走了三遍,扯一藤金银花
还有艾,且搓揉一掌来嗅
虎背园的香樟与睡莲,含蓄古典
适合摆茶台,泡普洱,发呆或聊天
我们还有半生,可以搁浅
那么就用搁浅来延拓,用你的缓慢
用你大雨如注的绵厚,像
仙子湖漫过黑夜般淹没我
访通山
春深似海,总有不被打扰的一角
可以悠然长出粗壮的枝
见惯了虚弱的李子树
蓦然惊见它们庞然伸展
密密苍苍的叶海
覆盖我,缓缓向上的行走
有了如虫蚁般
微细的自明
其间露出
一小截水泥柱,几百年前豪雄的名字
以及那些郑重其事的记事碑刻
与捧场般莫名的盖棺论定
都不能减缓一丝这山坳
不屑一切强劲的馥郁
长久的清新
每天早上醒来,都是同样的窗景
去年种的竹,叶未黄也不翠
远处高楼林立
仅露一线天光,一角青山
楼下新修了马路,直通商业中心
卷闸门轰隆隆拉开
喧嚣就要开始,就要逼退日出的新
再躺会儿吧,人群蜂拥之前
还有一小段私密的间隙,可供剃须膏
与脂粉香充分混合。再匆忙
也没忘记亲吻的人
可以存下一整天可供呼喘的清新
夏末
她在蝉鸣带来的寂静里
在一所看不到风景的房子里
想着她的风景
初春甜,暮春浓,眼下有些说不清
也许正在冷却,装满爱情的房子
租期将近
两小时前,烈日炎炎下她路过的小区
正在做核酸检测,长长的队列
有人垂着头颅,一种认命的安静
聒噪蝉鸣都打不破的静
她无力关心人类,低着头默默走过
院子里落下许多枯黄的叶子
脚下沙沙响,有一种慰藉
归来
长久的破损得不到修复
变得天经地义,并提供某种庇护
比如安全的龟缩
懒洋洋地找着事不关己的理由
局部的拆修
除非激起整体更新的能力
否则就是一种冒犯
是对既定秩序的冲撞
我突然掀翻破损屋顶的行为
令自己都吃惊。某天的凝视
带来了发自内心的鄙视
形同虚设的保护荒谬之极
时间带来衰老也带来勇气
我已经老到不需要保护
现在,我需要一声剧烈的坍塌
一次切肤的疼痛
协议
大雪飞降,严寒袭击了对真相的奔赴
被阻滞的车轮陷进不甘的坑洼里
平坦处观望的女人们
亦未得幸免,向内看,人造的温暖
有些可疑,闷燥、窒息
老掉牙的腔调充斥其中
刺耳得让人失措
向外看,无数张女人的脸正在失去辨识度
一些发不出声,一些竭力争辩
还有一些谨守成规
腔调统一
我悚然心惊:我在哪一些里?
要凛然端正,要清新自守
除了关紧门扉堵上耳朵
还能做什么?如果不能破解
就勇敢地质疑、追问,以此打破
一个人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