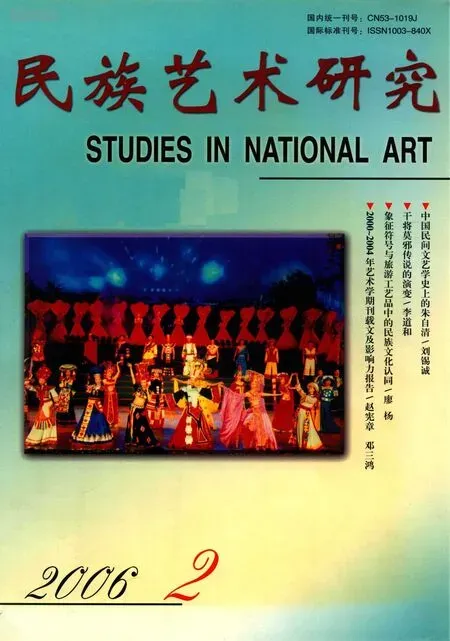音乐民族志
路菊芳
“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人类学和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家采用人类学方法研究音乐,通常是为了解人和文化。采用音乐学方法的人想通过研究人和文化来了解音乐。”①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omusicology.无论何种研究倾向,都为民族音乐学带来音乐对于文化或文化对于音乐影响的独特视角。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是民族音乐学学科(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实践基础,但其并非由学科线或理论观点来定义,而是由一种描述音乐的方法或叙事策略来界定。②Seeger,Anthony:“Ethnography of Music”,Helen Myers,ed.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New York.And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92.pp:88.故,两者一个是学科发展的理论思维语境,一个是学科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或前或后,相互支撑,形成螺旋上升式的两条学术脉络。国内已有学者高屋建瓴地从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论述了音乐民族志在西方的历史轨迹及其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结合的范例,③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综合前人研究理念,根据音乐民族志词源流变及西方书写风格,从微观史学的视角梳理其在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实践。
一、词源与内涵
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也有译为音乐文化志、族群音乐文化志等,它由一种描述音乐的方法来定义,这种方法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记录声音是如何构思、制造、欣赏,并影响其他个人、团体、社会和音乐的过程,它是书写人们制作音乐的方式。④Seeger,Anthony:“Ethnography of Music”,Helen Myers,ed.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New York.And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92.pp.88.其英文Musical+Ethnography可知音乐民族志先天携带的跨学科研究特质。故,欲知“音乐民族志”,必先溯源“民族志”。
(一)汉文中的“民族志”
首先,古代文献中“有民、族、种、类、种人、种落等,但没有称为民族。汉文中的‘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强学报》(《民族研究》1984年第二期37页)。”①程继隆:《社会学大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古文中“族类”称谓主要用于区分华夏与周围之夷狄,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民族”。近现代白话意义“民族”一词,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有识之士从日文直接引进西方nation的概念。②王平:《反思与检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规范化的若干基本保障》,《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第57页。西方nation类似我们“中华民族”或“国族”之意,只是含义完全不同。其次,“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源远流长,唐代颜师古《汉书·叙录》载:“志,记也,积记其事也”;③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95页。南宋郑樵“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④[宋]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页。等,“志”和“记”多通假互用。再则,“志”亦为古代一种记述体裁,如方志之始《越绝书》发展而来的各种志书。但中国方志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志,中国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别史、地理史和地图,是历代史官对本朝时事内容的记载,隋唐之后方志体例始有创新,增加了社会、政治、艺术等内容。⑤吴祖鲲:《中国古代方志及其文化价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5期。而西方的民族志则是考察者根据个人经验,对异文化习俗、社会结构等描写。所以,此“志”非彼“志”。
(二)西方的“民族志”词源流变
西方的民族志(Ethnography,亦为人种志、人种学)和民族学(Ethnology)兴起于18世纪在俄罗斯帝国殖民地工作的德语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等研究实践中,并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名称Völker-Beschreibung⑥首次出现在德国学者G.F.缪勒(G.F.Müller)1740年给J.E.费舍尔(J.E.Fischer)的手写导论中,但该手稿18世纪80年代才出版。Han F.Vermeulen:“Origin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SA,1771-1845”,Fieldwork and footnot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edited by Han F.Vermeulen and Arturo Alvarez Roldan,1995.pp.46-47.、Ethnographie、Völkskunde等。⑦H.F.Vermeulen:Early history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the Germanen lightenment: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in Europe and Asia,1710-1808,PhD thesis,2008.德文Völker-Beschreibung是“民族志”的前身,鉴于当时科学名称必须源自希腊语,后出现了以希腊文ethno(s)(种族,人民)结合graphein(用来写,书写)组合成的Ethnographie(后缀同graphia),Ethnographia就是用来指代Völkerbeschreibung,指对不同民族的描述(复数),或者是对一个民族的描述(单 数)。⑧H.F.Vermeulen:Early history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the Germanen lightenment: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in Europe and Asia,1710-1808,PhD thesis,2008.pp.201.随 着 变 体Völkskunde的 出 现(kunde“学科、研究”),Völkskunde就成为专指德国日耳曼民族的研究,国内译为“民俗学”;而Völkerkunde直译“民族研究”或“民族学”,指对国外民族、异民族或所有民族的研究。⑨杨圣敏:《民族学是什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12页。民族志Ethnography从德语Völker-Beschreibung单复数同词,到Völkerkunde和Völkskunde的各有所指,隐含着18世纪民族志研究范式“从研究风俗习惯到研究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转变”⑩H.F.Vermeulen:Early history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the Germanen lightenment: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in Europeand Asia,1710-1808,PhD thesis,2008.pp.22.。同时,为“民族志”向科学性方法发展,民族学学科成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学者对人类音乐“起源”的比较探索提供了民族志方法和大量资料方面的储备。
二、音乐民族志在西方的学术发展脉络
若民族志是民族学的根源,那么音乐民族志就是民族音乐学书写的灵魂。只是民族音乐学沉浸在音乐的“民族志”中,民族音乐学家使用文字和其他图表形式等手段来传达概念。①Seeger,Anthony:“styles of musical Ethnography”,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edited by Bruno Nettl and Philip V.Bhl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346.当民族志从探险家自发性、随意性和业余性的著述,发展到专业出身学者的科学民族志,以及后来的多元化民族志时;②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58—63页。音乐民族志也从非音乐专业学者研究中的概述、广采音乐,到音乐学的比较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体验、反思、主体等多维度音乐民族志的纵深发展。
(一)音乐民族志的萌芽和积累——20世纪60年代之前
1.蜡筒式音响的采录和收集
爱丽丝·坎宁弗莱彻③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ice_Cunningham_Fletcher被认为是美国印第安音乐研究的先驱,第一位女性民族音乐学家,她实地考察了十多个原始部落,收录了数百首美国本土音乐,《马哈印地音乐研究》(1893年)是其音乐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再如弗朗西斯·登斯莫尔也是位女性民族音乐学家、民族志学者,从1907年之后的50年,一直致力于原住民音乐的收集和记录,并对塞米诺尔人用蜡筒录音的243首歌曲,有些进行了民族志的分析注释④Frances Densmore:Seminole Music,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Xxviii.。此后,更多专业的、业余的学者投入收藏和野外录音工作。而波兰民族志学者奥斯卡·科尔伯格(Oskar Kolberg)被认为是最早的欧洲民族音乐学家之一,他于1839年首次开始收集波兰民歌(Nettl 2010,33)。
2.音乐本体脱离语境“孤独”的比较
蜡筒收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一直是英美德国的潮流,由此造成了比较音乐学时期“扶手椅式研究”。E.M.冯·霍恩博斯特就是根据收购来的蜡筒录音研究⑤E.M.von Hornbostel:“The Ethnology of African Sound Instruments”Africa,Vol.6.No.3.1933.pp.277-311.,很少涉及田野考察。其实当时已有学者提出“(原始的)音乐不是一种抽象艺术,而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生活中的艺术”(Wallaschek,1893年),只是因为当时人们倾向于脱离语境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习惯根据一个或另一个参数来比较他们的音乐形式,而使沃拉谢克的观点有些过时。⑥Seeger,Anthony:“styles of musical Ethnography”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edited by Bruno Nettl and Philip V.Bhl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349.
3.“非位表述”⑦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语境中“位”思维的萌芽
在当时“非位表述”的书写潮流中,也有主位文化出发的研究。如弗朗西斯·拉·弗莱舍是美国第一位代表研究对象发声的局内人类学家,他从主位视角描述部落文化和音乐⑧Francis La Flesche:“Death and Funeral Customs among the Omaha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Vol.2.No.4(Jan.-Mar.1889).pp.3-11.,开创合作民族志,对人类学者权威性解读土著文化进行隐喻讽刺和批判等;⑨K Graber:“Francis La Flesche and Ethnography:Writing,Power,Critique”.Ethnomusicology,Vol.61.No.1.2017.pp.115-139.特别“Who Was the Medicine Man?”(1905年)一题,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些书写思维均是在当今美国人类学界才盛行。总之,弗莱舍的民族志预示了未来民族志的发展方向。
(二)音乐民族志书写方法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60—80年代
人类学从20世纪50年代博厄斯提出注重主位研究方法的新民族志,到70年代转向象征意义和地方解释,以及80年代反思人类学兴起旨在研究民族志文本的叙事体裁、形式、风格、结构和修辞等,①Neil J.Smelser,Paul B.Baltes:“Ethnography”.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Behavioral Sciences,2nd edition,Volume 8.Elsevier Science Ltd.2001.pp.179-181.民族音乐学也经历了60年代音乐民族志方法的确立,由宏观比较转入微观个案研究的第一次学术转型②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如《声音与情感:卡鲁里表达中的鸟儿、哭泣、诗歌与歌曲》开篇所言“这是一项关于声音作为文化系统的声音民族志研究”③Daniel M.Neuman:“Sound and Sentiment:Birds,Weeping,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by Steven Feld”.Ethnomusicology,Vol.28.No.3(Sep.,1984),pp.551.。全书根据卡鲁里的神话展开,音乐也是通过一个基于鸟和人类“变成鸟”联系的符号系统来分析,而“成为一只鸟”是卡鲁里美学的隐喻基础等。④Daniel M.Neuman:“Sound and Sentiment:Birds,Weeping,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by Steven Feld”.Ethnomusicology,Vol.28.No.3(Sep.,1984).pp.551-554.该书被评价为20世纪70年代当代声音人类学建立以来的开创性著作(Meri Kytö,2012年)。
(三)音乐民族志的多元化趋向——20世纪末以来
80年代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音乐民族志书写方式也由微观个案研究方法向“微观+宏观”的多点音乐民族志转型,⑤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如《音乐民族志的产生》一文⑥Catherine M.Appert:“Engendering Musical Ethnography”.Ethnomusicology,Vol.61.No.3(Fall 2017).pp.446-467.就是以多点民族志为范式,以研究者不同地点的考察体验为线索,展开在音乐表演空间之外,如何培养民族志学者认知,性别化的音乐民族志研究。文中无直接描述音乐,研究者不同地点的考察研究对象和不可预期的诸多事件,形成了多条交互存在的书写思路。
三、音乐民族志书写方法论的中国经验
音乐民族志侧重于常规方法论和田野考察实践两个方面,并较多涉及微观、具体的个案及比较研究,这也是维系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百余年历史的关键。⑦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而我们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进民族音乐学理念,音乐民族志书写也由此而始,发展至今40年有余,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在探索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中国经验。
(一)从民族志书写方法论探索
国内民族音乐学学界中,沈洽最先提出音乐民族志架构的理念,如其《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务之急——修纂民族音乐志之必要与价值》⑧沈洽:《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务之急——修纂民族音乐志之必要与价值》,《中国音乐》1984年第3期,第26页。和《民族音乐志的架构》⑨沈洽:《民族音乐志的架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5年第3期,第73—80页。中谈到了民族音乐志的界定、学科定位等。曹本冶根据人类建造文化过程中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提出“仪式中音声”的理论框架⑩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随后张君仁在实验音乐民族志基础上提出了“传记研究法”⑪张君仁:《传记研究法——一种针对个体研究对象的方法论》,《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第18—24页。。
杨民康是方法论方面集大成者,从《宏观与微观:音乐民族志研究规模的方法论取向及其历史发展》⑫杨民康:《信仰、仪式与仪式音乐——宗教学、仪式学与仪式音乐民族志方法论的比较研究》,《艺术探索》2003年第3期,第50—58页。从2003年始,历时19年,仅民族志书写相关论文20余篇。,到《“微观+宏观”“横联+纵合”:当下音乐民族志发展趋向与存在问题》⑬杨民康:《“微观+宏观”“横联+纵合”:当下音乐民族志发展趋向与存在问题——〈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教学与辅导之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39—44页。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均可看出其在民族志书写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且论述问题涵盖了民族志书写的方方面面,如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宏观与微观、主客位双视角、书写风格及类型等20多个。尤其《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①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为近十余年来音乐民族志写作从纪实性向阐释性转变,发挥了关键的导向作用。另一著述《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②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则从音乐民族志分析的塔层结构,结合传统音乐经典个案,给予学人更全面的分析思路。此外,洛秦从音乐文化诗学的视角讨论音乐叙事③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第20—23页。,强调音乐与之相关的“人事”,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中观层、微观层,意在探究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到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音乐社会环境中特定机制的影响。薛艺兵从写音乐与写文化的概念出发,提出诸多值得思考的论题④薛艺兵:《写音乐与写文化——设问与反思》,《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第30—34页。,如何谓音乐文化?怎么写音乐文化等,分别而又相互关联地讨论了音乐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价值及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的目的。⑤薛艺兵:《我们为什么写作?——谈音乐民族志文本的价值及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的》,《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101—108页。另则,陈铭道对《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作出肯定后指出:“这样写论文,人们会问民族音乐学写作究竟是‘科学’还是‘文学’?我们提供给世界的是客观的科学认识还是主观的艺术感知?”⑥陈铭道:《音乐民族志写作——以〈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为例》,《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周凯模根据自己研究实践,认为中国古代很多文献志书都可作为民族志书写的资源;并从学理层明确民族志书写文化事实时,不应以口语化描述代替学术性阐释,应该是建立在鲜活事实基础上的学术性归纳。⑦周凯模:《“仪式音声民族志”文本建构——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民族志书》,《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46—54页。杨殿斛从方志、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关系等方面讨论,也有同于前位学者的看法⑧杨殿斛:《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志的论题价值取向》,《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第26—35页。,并在多篇文章中谈及民族志书写的论题。近期,张伯瑜根据音乐民族志从客观描述到主观陈述,再到学者“自反”的书写发展过程,提出“走向理解的音乐民族志”以及民族志书写值得反思的问题。⑨张伯瑜:《走向理解的音乐民族志》,《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1期,第74—80页。
(二)从田野实践体验中反思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书写的基础,学者们除了从学理方法层上提出真知,也从田野体验中获得灵感。萧梅认为人类音乐文化及其成果创造的过程皆与人的感受、思维、情感、行为方式等紧密相关,⑩萧梅:《音乐本体论》,载《田野萍踪》,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203页。其根据田野考察,从仪式音声中音声声谱的角度,围绕“默声”研究提出多个论题,如是否有必要对仪式场域“默声”现象描写和研究?作为田野体验基础的身体能感性(somatic)是否可为研究切入点等⑪萧梅:《体验的音声民族志——以音声声谱中“默声”的觉察为例》,《大音》2009年第二辑,第51—75页。。此外还有杨红《田野中的音乐体验之研究——试析有关中国民间综合演艺品种的音乐民族志理论与方法》和《田野中的音乐民族志建构》,以及刘桂腾《以身试法:定点·追踪·个案——田野实践中的音乐民族志方法》等。
四、音乐民族志书写经验的中国实践
民族音乐学尚未建立任何的标准或分析方法,⑫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omusicology而是同时转换于人类学和音乐学不同领域的一系列范式中。中国学者在前述民族志书写方法层的探索基础上,借鉴西方前沿理论,也形成了音乐民族志研究的中国实践。
(一)仪式音乐民族志
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始于曹本冶引导的一批大陆中青年学者中,并在方法论方面出版了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如《道乐论:道教仪式的信仰、行为、音声三元理论结构研究》(曹本冶、刘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曹本冶)等。而《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①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年版。是杨民康先生根据持续二十多年仪式音乐考察,围绕“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提出的个人研究感悟。该书从国内外仪式音乐民族志的界定、书写方法,以及同传统音乐研究方法之异同等方面分别做了论述,并将所论方法结合中西经典个案进行透彻分析。如《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②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年版。就是共时性平台上涉入了历时性研究理念,采用由表层到深层、变体到模式的逆向分析思路。而《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则与之相反,将实录作为附录,一百年前基督教音乐文化置入前端,构成由深层到表层、模式到变体的转换生成研究路径,也是一个按“指向未来”的目标顺向展开的历史音乐民族志文本等。③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年版,第239页。并引导了一系列从不同书写策略着手的仪式音乐民族志课题及个案研究。
(二)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
随着当下仪式现象的变化,在仪式音乐民族志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杨民康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一度以音乐表演(或表演行为)之前之后的对象化作为分界,构成分别以“乐谱”或“音声”为不同起点对象的二元对立状况,以乐谱为起点的“表演前”研究多为传统音乐形态学分析,以“音声”为起点的“表演后”研究为描写音乐形态学;而仪式音乐民族志音乐形态分析,则是以表演为中心(或表演活动),以仪式为语境,注重“模式与变体”“固定因素与可变因素”的分析思路,形成在表演前、表演后穿梭的音乐的简化还原、转换生成分析范式等。④杨民康:《以表演为经纬——中国传统音乐分析方法纵横谈》,《音乐艺术》2015年第3期,第110页。《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⑤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年版。汇集了其多年来对仪式音乐的跟踪研究,以及如何将西方民族志方法论理念融化为中国经验的思考等。
(三)体验的音乐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西方音乐民族志书写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表演”研究的视域。萧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过程,是以乐人“表演(演奏)的‘活化’”为其重要的存在方式,其声音结构所表征的不仅仅为“音响—听觉”轴线上的时间维度,亦为身体行为及其空间关系的综合展现。⑥萧梅:《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与音乐形态关系研究》,《中国音乐》2020年第3期,第20—29页。由此,“缘身性”的基本内涵指以身体的感知与实践为主体,以情境、交互/介入性、展示性为条件的身体过程,⑦萧梅:《“缘身而现”:迷幻中的仪式音声》,载《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曹本冶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323页。因为“体验不是一种只有通过内省才能获得的内在现象。相反,体验始于与世界和他人的互动。”⑧Timothy Rice:“Time,place,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Ehnomusicology,Vol.47,No.2.2003.pp.157.由此,萧梅从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以及音乐表演中的“身体感”等理论问题产生并引导了诸多有意义的课题。
(四)音乐影像志
音乐影像志是民族音乐学发展历史上,又一次科技发展引发的转变。其主要以影像视频形式代替了以往文本书写的民族志。赵书峰首先从学理层上对何谓民族志电影、音乐民族志电影等提出讨论⑨赵书峰:《为谁书写?谁在书写?——谈影像音乐民族志文本的建构问题》,《艺术探索》2019年第1期,第65—70页。。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较早关注了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并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高贺杰、刘桂腾、萧梅三位学者以《北方与南方/萨满与魔婆/斡米南与戴帽》为名,组成了影视民族音乐学专题小组。①赵书峰;《中国音乐民族志电影发展前景与展望——由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世界大会放映的6场音乐民族志电影所引发的思考》,《人民音乐》2014年第5期,第74—77页。再则,上海音乐学院影视研究团队于2019年举办了第一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为音乐民族志从传统文本记录到视觉的、流动的文本转换提供了平台。
(五)音乐民族志的实践个案
民族志的微观本质,使诸多经典个案成为其发展的基础。学界一般认为《白族音乐志》(伍国栋)为国内第一本音乐志,该书仍保留了中国传统志书的体例、书写风格等。杨民康评价该书是第一部从音乐文化角度撰写的民族志,为进一步撰写白族音乐史打下了良好基础。②杨民康:《一部富有开拓性的音乐志书——〈白族音乐志〉读后感》,《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第101—103页。杨曦帆认为该书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并具有当代学术意义和研究水平的音乐民族志,在写作方法上可类比于人类学民族志第二个时代所强调的“科学的客观性”写作方法③杨曦帆:《音乐民族志在中国的奠基与多元发展》,《中国音乐》2019年第2期,第36—44页。等。此外还有其他经典个案如《寻找传承与变迁中的文化主题——一次纳西“祭天”仪式的叙事与引申》(萧梅)、《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洛秦)、《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萧梅)、《晋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张振涛)、《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薛艺兵)、《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沈洽)、《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杨沐)、《海南音乐文化志》(杨民康、符美霞)等等。
论文方面如实验民族志风格的《半熟·惠流·动静——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的实验音乐民族志》《书写“全息式”仪式音乐民族志——鄂温克族敖包祭祀仪式音乐研究反思》;虚拟空间视野的《“虚拟空间”音乐田野中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以百度贴吧越剧受众论坛为例》;与教学传承结合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教学与实践》《中国音乐传承民族志的研究背景与书写》;比较视野的复归《音乐民族志栖身于比较》等。
五、中国实践经验的反思
(一)民族志书写方法的亟待实践
从中国音乐民族志学者的书写思维看,无论是对学理层书写方法的探讨,还是就各自方法理念上形成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民族志方法的融入,也仅限最近十余年前始而已。相对于西方民族志范式“十年一更新”的发展速度,我们略有迟缓,且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并未在学界形成规模。
(二)新颖研究视角待规模化、多元化
西方音乐民族志从20世纪60年代确立民族志方法之后,出现了诸多新颖研究视角。反观国内,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成绩斐然;但一些较新的理论探索多偏向于个人化或小群体化,尚未反映出当下中国音乐民族志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去加以解决、最具现实性和普遍性的关键问题。④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所以,如何突破传统思维,与当下世界接轨,形成中国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范式或经验,是我们音乐民族志学者当下思考的问题。
(三)民族志书写风格的转型
民族志不再针对单一的一般类型的读者,本土读者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文本化的解释和知识(James Clifford,1983),国内的音乐民族志面临同样问题。杨民康对迄今为止学者所采用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进行分类,提出五种民族志书写风格⑤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129页。:“非位表述”“客位表述”“主位表述”“对位表述”“换位表述”。第二种是目前常用的书写风格,后三种均考虑到书写中给予研究对象发声的表述方式,当然也是我们音乐民族志书写需转换的方向。
结 语
综上所述,从词源流变看,民族志从德国学者探险之旅的考察手记中产生,几经变迁成就了民族学学科;比较音乐学在多学科学者推动下开创,同时也带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书写方法看,由20世纪60年代音乐民族志方法确立,70年代后始与音乐人类学理念交互存在,形成了民族音乐学“双焦点”(音乐学和人类学两种倾向)的独特研究视野。而我们的音乐民族志在众多学者潜心探索下,虽取得丰厚成果,但仍略显踟蹰不前。“从以现实主义民族志为代表的传统民族志向(后)现代转型过渡的问题,或许是能够解决目前中国音乐民族志固守旧臼、缺少新意以致长期停滞不前等诸多关键症结的途径之一。”①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页。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困境,走出中国的音乐民族志道路?杨民康指出:作为民族音乐学学者,要把相关学术讨论的焦点放在思考怎样结合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环境条件,尽量在观念和思维层面上处理好,两种不同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生成的不同书写方法之间结合的关系。②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故,我们中国的音乐民族志书写尚有很大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