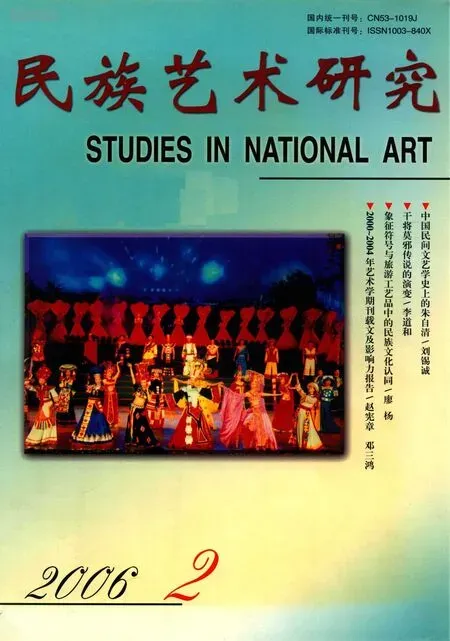文艺思潮衍变下的中国当代舞剧
慕 羽
2021年春,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分别上演了两部中国“当代舞剧”,一部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到那时》(总导演:佟睿睿),另一部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创作的《白蛇-人间启示录》(总导演:王媛媛)。佟睿睿的《到那时》是舞蹈界近年强调的“现实题材”舞剧,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的故事,是比较少的“舞在当下”的舞剧作品;王媛媛的《白蛇-人间启示录》虽取材于民间传说,却也是一个“现实”故事,一个当代人对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的想象。这两部中国“当代舞剧”有相通之处,也呈现出“新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差异。中国舞剧“当代”叙事美学的多面向,恰是对丰富人民美好生活、促进社会文化和谐正向作用的彰显。
“当代”一词指涉特定时空,时间是不断变化的轴线,当下瞬即成为历史;空间则因身处的个体和群体差异而有了不同的美学参照。就时间观而言,当代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需要把握好“当代性”的三个时间维度,即“现时回溯性”“当下现场性”和“未来开放性”。①葛洪兵:《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第51—57页。就空间观而言,在中国当代舞剧的创作中体现了“文化主体性”和“全球在地化”意识的增强。文艺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舞剧的“当代性”维度,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再到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共生,这个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涉及中国舞剧创作思潮衍变过程中,中国舞剧创作模式的守正与创新。
一、中国舞剧创作与现实主义文艺主潮
就文艺创作活动体系而言,文艺思潮是灵魂与核心,流派、运动则是文艺思潮的两翼,创作方法为文艺思潮与创作实践的中介,文艺风格、流派只是在创作成果中表现出来的文艺思潮的审美特征。文艺思潮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动态的体系性文艺思想;它侧重文艺创作,却又不只局限于创作,还涉及理论、批评、鉴赏等领域,且环环相扣,以在文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文艺作品、理论著作、批评著作为实绩。虽然文艺思潮并非专指创作现象,但毕竟“创作潮流”最能反映文艺思潮重要面向。①慕羽:《润物之道:文化力与中国舞蹈创作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8页。
“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艺主导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虽然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无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它是“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进才出现的。但中国传统文论中一直存在着对真实性、写实手法的推崇以及社会关怀的精神,这是源自“文以载道”的儒家教化和积极入世的思想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舞蹈创作路径由“延安开始的艺术道路”延续下来并成为舞蹈创作的“主导”,或被看成是“唯一正确的创作道路”②周扬:《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舞蹈通讯》1956年第10期,第20页。,大多体现为“阶级批判式”“战斗祝捷式”“歌功颂德式”等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现实主义”其实是对苏联模式创作手法的改造,尽管这种方法在苏联的舞蹈创作领域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却成为中国主导性的文艺观,本质上体现为倡导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的“革命古典主义”思潮;如果说,法国宫廷古典主义的政治理性是王权,革命古典主义应是民主,③参见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而中国革命古典主义的政治理性则是人民民主。现实主义舞蹈(剧)作品,树立新政权新的革命典型形象,当时“典型”的本质和标准其实就是“阶级性”。
中国现实主义强调“目标”大于“方法”,④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这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确立的。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将改革开放之前的创作观念和手法看作“(革命)现实主义”,此后加上“新”这个修饰词,表明“方法”和“目标”实现了辩证统一。“典型”的本质和标准也由“阶级性”转型为“人民性”。
改革开放后,在一体多元的文艺政策下,各种新思潮应运而生。当然,不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如何变化发展,对“现实主义”的拓展与创新,仍然是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主潮,只是从过去的“大一统”到如今的“一体多元”。社会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的消长,以及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关系,“新现实主义”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崭新形态和艺术特质。“新现实主义”之“新”,不只是从“革命”到“改革”的新旧对比,也是改革开放时代命题的不断“创新”,借鉴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手法进行创作也成为重要现象。
一方面,传统现实主义舞剧表现出外视角,以及“线性时间”主导的叙事特点,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了视角转移及“空间意识”,可见多面向、跨文化的空间叙事被提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传统舞剧到当代舞剧的坐标上,一些“新现实主义”舞剧兼有两者特性,本身也没有必要经纬二分。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草原英雄小姐妹》《到那时》等舞剧风格化、节奏化哑剧与抽象化、意象化的身体话语都存在,它们均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传统舞剧的“自体反思”和“自我超越”。另一方面,除了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不断更新,中国当代舞剧创作中也有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当代性探索,如“中芭版”《牡丹亭》、“苏芭版”《西施》和“当芭版”《白蛇-人间启示录》等。
换句话说,同样都是当代舞剧,《到那时》体现出具有“时代性”“现实性”意义的新现实主义审美,而《白蛇-人间启示录》则混融了后现代主义的跨媒介探究,呈现出一种超越情节叙事和事件再现的形式建构。当代舞剧创作手法非常多元,更重要的是创作“动因”和舞段配置是否基于人物塑造和观念表达,“经典”叙事手法比如情感叙事、情节叙事在当代舞剧中也获得了继承和新生。
二、现实主义中国舞剧创作传统的形成
中国漫长的乐舞历史上虽然有舞剧基因,但舞剧毕竟是舶来品。中国舞剧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呢?可以间接追溯至西方古典芭蕾舞剧(广义)革新的契机。18世纪中后期,法国情节芭蕾逐渐不再附属于歌剧,成为一门独立表演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模仿论”(再现性哑剧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模仿论”为特色或主旨的传统舞剧,主要包括古典芭蕾(广义)和苏联戏剧芭蕾,以及受它们影响的中外舞剧创作。
古典芭蕾的身体话语和叙述结构由“表演舞+哑剧”构成,其“典型特点”是以“表演舞”为主,内容是第二位的,所以我们会说“舞>剧”,这是特定语境下的表述。苏联戏剧芭蕾的身体叙述话语包括“情节舞+表演舞+哑剧”三类,其中“情节舞”位列首位,遵循的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艺术观;听觉话语侧重强调专门“为观众而写”的舞剧音乐,而非“为听众而写”的交响乐。①参见[苏]罗·扎哈洛夫《舞剧编导艺术》,戈兆鸿、朱立人译,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1984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舞剧人集聚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精神,又秉持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产生了“无变奏的芭蕾”和“无唱念的戏曲”②参见赵大鸣《谈舞剧艺术观》,《舞蹈》1988年第11期。两种舞剧叙事结构,其后中国现实主义舞剧叙事恰恰是这两类叙事结构的衍生,前者接近西方古典芭蕾舞剧和苏联现实主义戏剧芭蕾传统,并未涉及西方现当代舞剧和舞蹈剧场的理念;后者侧重向中国戏曲表演程式中的“做”“打”学习,而“唱”“念”本身尽管蕴含着舞蹈基因,却因其不够舞蹈化而被舍弃。
苏联模式的传统舞剧哑剧叙事就像是“忍着不说话”,更接近于“不说话的话剧”,也被称为“芭蕾舞戏剧”,或被称为“话剧型舞剧”,这都是从苏联戏剧芭蕾舶来的概念。尽管扎哈罗夫并不赞成这一提法,但他极为推崇18世纪诺维尔的情节芭蕾理论,认为舞剧不能缺少哑剧,并将其比作歌剧中的“宣叙调”。在接近现实生活的场景中,以哑剧的方式来演绎系列事件,犹如对“文学大纲”和“台本(结构计划)”的舞台化直译。舞者的此类表情、动作既是“叙述行为”,也像一种模仿、再现现实口头叙事的“话语”。
20世纪后,舞剧的“表现性”本体叙事渐趋西方主流,这是受到摒弃情节、强调心理与情感抒发的现代舞的影响,也与“三十年代才得以兴旺发展和传授”的“舞蹈编导理论”密切相关③[美]多丽丝·韩芙莉:《舞蹈创作艺术》,郭明达、江东译,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欧美心理芭蕾、交响芭蕾的出现让芭蕾获得了情感表达之外的想象空间和哲思探讨。六七十年代后,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也相继长出了独特的交响芭蕾舞剧和心理芭蕾舞剧之花。具有当代审美的舞剧早已不同于“不说话的话剧”,“象征性动作元素、哑剧和舞蹈元素的比例和作用起了根本变化”④肖苏华:《中外舞剧作品分析与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尤其要以“非哑剧化”的身体话语叙述为本质特征,它所独具的身体叙事、空间叙事和视觉叙事有着独特的审美,也超越了模仿论,以及文学性和情节性思维,“可以不说话”的默剧式戏剧行动融合于角色化的舞蹈,必要时也可以用嘴“说话”,但已完全异于再现现实的语境,有了“跨媒介叙事”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舞剧创作上虽然深受苏联戏剧芭蕾模式和现实主义哑剧叙事的舞剧观影响,但欧洲现代戏剧芭蕾《奥涅金》的情感双人舞叙事一度成为中国舞剧创作效仿的对象,“情感性双人舞+表演性群舞+哑剧”模式逐渐成为新的范式思维;舞剧创作虽不再拘泥于再现生活的现实,或遵循某个舞种风格体系,但“接近生活”的哑剧在舞剧中被看作“戏”的思路,以及观赏性强的为舞而舞的“插舞”思路很长时间并未发生质变。李承祥将“舞蹈+哑剧”看作“天然的伴侣”,视为一种“虚实结合”,他认为适当的哑剧有助于“发挥舞蹈叙事的功能,有利于交代情节,增加生活气息”,他也将其比作“舞蹈的台词”。①李承祥:《舞蹈编导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102、161页。当然,无论是独白(独舞),还是对白(双人舞),理想化的状态应该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台词”,即李承祥所谓的“潜台词”,这些提法都渗透着扎哈罗夫的舞剧观。
吕艺生认为,李承祥的《舞蹈编导基础教程》就是现实主义舞剧理论的“集大成者”。②吕艺生:《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其中最核心的创作原则是“三个坚持”,即“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从生活出发……通过一系列的舞蹈,去表现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事件和人物形象”。③李承祥:《舞蹈编导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另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一些现实主义舞剧已经融合了“心理表达”。李承祥坦言,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林黛玉》中“黛玉之死”时就已经借鉴现代主义“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了,④李承祥:《舞蹈编导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用了半个多小时来“渲染”黛玉的心理活动。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现实主义舞剧创作原则是“中国舞风形成早期最重要的根由”,几代编导的坚守与创新,“取得了现实主义写实风格舞剧的成就”。⑤吕艺生:《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三、新现实主义中国舞剧的守正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不少人都认为,舞蹈应该多样化、多层次、多模式、多渠道方式发展,但正如彭松在《从史学角度谈谈舞蹈现状》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舞蹈“正处在一个继承、探索、变革和动荡的时代。”⑥彭松:《从史学角度谈谈舞蹈现状》,《舞蹈》1985年第4期,第17页。抽象派、现代派、意识流、摇滚乐、迪斯科、爵士舞、霹雳舞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糟粕”的外来艺术,对长期封闭的中国舞蹈文化圈是一次猛烈的撞击。其中“现代主义”舞蹈直接引发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现代舞”的重新滋生,而是“现代舞”的创作手法为中国现实主义舞蹈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现实主义”舞蹈以充满意境,又关照现实人生的意象登场。
1994年,吴晓邦曾在《当代中国舞蹈的主流》一文中指出:“现实主义舞蹈或舞蹈的现实主义,其本性从来就是开放的,向着历史传统开放,也向着未来开放。”比较有影响的舞蹈作品,“现实主义精神都在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来。”⑦吴晓邦:《当代中国舞蹈的主流》,《舞蹈》1994年第3期,第3页。几年后,王同礼为舞剧《深圳故事》写评论,提出了“新现实主义道路”⑧王同礼:《舞剧〈深圳故事〉的审美寻踪》,《舞蹈》1999年第2期,第4页。的舞剧创作,以塑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为标志。2002年,冯双白在其《新中国舞蹈史:1949—2000》专著中,也用了“新现实主义舞蹈”这个概念,他针对的是曾“在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下”,以“中国现代舞的名分”进行的创作,比如《海浪》《黄河魂》等。笔者在2007年的博士论文⑨慕羽:《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之关系,1979—2006》,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7年。和2009年的相关专著⑩参见慕羽《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舞动奇迹三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中,继续延续了“新现实主义”这种说法,显示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力量的现代性审美调适。
2013年,吕艺生在其专著《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详细地阐释了中国舞蹈创作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坚守与跨越。20世纪上半叶,舞蹈家们“心甘情愿地选择了革命艺术,选择了现实主义”。新时期后,从舒巧、门文元到张继钢、陈维亚、赵明等“已注入了许多新东西”,新一代如王舸等则“成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强实践者和改革者”,吸收了现代舞的某些观念和技巧,尤其善用“舞蹈思维”的时空观讲故事。①吕艺生:《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第65、246页。“新现实主义”并非“无边无界的现实主义”,而是“对现实主义更加理性、更加灵活的坚守”,②廖文:《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3)》,《人民日报》2012年2月24日,第24版。与现实共振、与时代同步。
“新现实主义”之“新”代表着主导政治文化与精英旨趣的融合,其创作手法从过去的“革命现实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拓宽至表现当下中国时代精神的“积极现实主义”和“浪漫现实主义”;“西方现代舞”的文化交流刷新了舞蹈语汇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舞蹈领域的作用,而把具体的创作方法置于这一目标之下。
舞剧“心理结构”的说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流行起来。③傅兆先:《〈家〉的结构探讨》,《上海舞蹈艺术》1983年第1期,载《炼狱与圣殿中的欢笑:傅兆先舞学文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李承祥在“黛玉之死”中所尝试的,正是改革开放后舒巧所秉持的创作观——把主体意识融进“苏醒”的舞蹈本体意识中,这种观念的更新导引出“新现实主义”舞剧叙事美学的到来,即在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而成。而后者正是西方当代舞剧和舞蹈剧场所秉持的美学基调。这说明,“在接受西方话语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一直以本土的文化现实需要为基本的接受前提”。④张冰:《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与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74—81、255页。
1982年,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现代舞“实验小队”推出了舞剧《蘩漪》,该剧由胡霞斐、华超创作,是“1979年郭明达来该团讲学,传授了现代舞理论,以及后来不断借鉴吸取外来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产生的成果”之一。⑤胡霞斐:《实验小队一年探索之我见》,《舞蹈》1986年第3期,第16页。该剧并非“音乐—结构型”舞剧,而是“取消了作为时空转化的幕间和场次,采用了类似交响诗式的剧式。”这是尚未有正式“舞蹈诗”命名前,出现的非传统叙事性的“舞蹈诗”般的舞剧。赵国政认为,该剧标志着“一种新的舞剧流派绰约可见”。⑥赵国政:《动人的舞蹈交响诗——评舞剧〈蘩漪〉》,《舞蹈论丛》1985第3期,载于《舞境:赵国政舞蹈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9页。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其实《蘩漪》真的可算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派”舞剧的诞生。更难能可贵的是,1985年赵国政提出不要“幼稚、狭隘”地把既有的舞剧“作为尺子”来对后来的作品“进行量长比短”,急于界定“是不是符合人们概念中的舞剧规范”。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蘩漪》也只是这一个,仿佛预示了二十年后王玫具有“后现代”气质舞剧《雷和雨》(2002年)的出现。“后现代”气质的改编不一定要忠于原著精神,而是形成互文性的“故事世界”建构。
对于中西当代舞蹈艺术观的不同,吕艺生先生称之为“反向交替”现象,我们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理论,也恰是法国情节芭蕾和苏联戏剧芭蕾曾经走过的路,而西方现当代舞剧的抽象性、表现性、多义性与“中国古代抒情性舞蹈的大写意雷同”。吕艺生认为,“再现性”与“表现性”都是“人类舞蹈必经之路,不能以此论先进与落后,两种现象在实践中也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两种倾向必定能够共存,为我所用”。⑦吕艺生:《中外舞蹈“反向交替”现象的启示》,《文化艺术研究》2019年第2期,第41—47页。换句话说,中国舞剧需要“化西”,将西方舞剧戏剧规律性的好东西化为己有,而不是走“西化”道路。既然“抽象派”与我国民族传统写意舞蹈美学的相通之处,这说明即便不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向“古人”学习,也可以通向新的艺术化表达。何况我们需要鼓励包容性、开放性的舞剧创作观,既可以充分向中国民间传统或戏曲美学取经,也应该学习西方经典舞剧的规律,这是中国舞剧叙事的守正与创新。
改革开放后,舒巧在她十余年的舞剧创作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新现实主义”舞剧创作观:“抽象而又凝练”“模糊而又多义”的舞蹈语言,不仅不是舞蹈叙事的缺点,反而是“独特的优势”。舒巧认为,舞剧叙事加强结构意识,就可以超越“演事件”,这是因为她理解的“意识流”指的是“顺着作者的同时也是主人公的‘意识’而‘流’,铺陈出舞剧的幕、场、段”①舒巧:《今生另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32页。,这就是舒巧主张的“结构上升为语言”。对舒巧而言,她想要在作品中开掘的是人物“心灵的可舞性”,要“勇敢地面对人,面对今人,面对我们自身!舞蹈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透视出了人、人情、人性和人生”;②转引自于平《舒巧的舞剧和舞剧观》,《舞蹈》1992年第1期。还需要强调的是,作品是编导的心灵世界,民族风格也是由编导实实在在的个人风格、流派汇合而成的。③舒巧:《今生另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324页。将舞蹈“本体意识”和编导“主体意识”紧密相连,恰恰是“新现实主义”舞剧观的特点,可以说舒巧是中国新现实主义舞剧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中国舞剧创作本体叙事意识的提升也与“交响编舞”理念的传播密不可分。1988年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师从格里戈罗维奇的肖苏华归国,开始推广“交响编舞法”,经过十余年努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舞剧从“话剧型舞蹈结构”向“音乐型舞蹈结构”转化。除了重复、对比,具体的技术手法如展开、变奏、再现、复调等都是借鉴音乐的手法,④肖苏华:《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舞蹈与音乐非语言文字的特性实现了同构,这意味着除了强调心理结构的内化情节之外,还有淡化情节,去追求诗歌意象的另一种做法,从而造就了中国舞坛又一种新形态——舞蹈诗的诞生,强调用艺术的想象、写意以至用移情和感情外化来编创舞蹈,有“表现性”却不抽象。在拙著《中国舞蹈批评》中,笔者称其为“中国本土生成的‘形式逻辑’”。⑤慕羽:《中国舞蹈批评》,上海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510页。
有不少中国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编导,尽管不自知,但“迂回地践行着表现主义”,吕艺生称之为“原生性表现主义”,是“中国式传统表现主义的顽强体现”,在高成明、佟睿睿、张云峰、赵小刚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即便是注重叙事性的张继钢、丁伟、赵明、王舸的创作,也融入了或多或少的“表现性”思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韩真、周莉亚)并未打破“情节舞+表演舞+哑剧”的创作模式,但在跨媒介叙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也是此类风格的精益求精。如果说“现实主义舞剧”创作体现为一种“当代中国舞风”,著名舞蹈学者吕艺生教授将其概括为——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技巧高超、舞美华丽、语言混搭、宣传意味等特性。⑥参见吕艺生《当代中国舞风解析》,《文化艺术研究》2014年第3期。那么,“新现实主义舞剧”则是对这种舞风的不断更新,笔者将其概括为主题真挚、结构开放、话语多元、本体突出、制作精良、个体视角、民族国家意识、人类情怀、认同想象。
再看舞剧《到那时》,该剧体现出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共融的“融合文化”特质,可以折射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说它传统,是因为它秉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舞剧的“现实主义”传统;说它“当代”,是因为它呈现出这种“再造传统”的再度更新,可被视为“新现实主义”主流舞剧。作为主旋律献礼舞剧,旗帜鲜明地定位成“当代舞剧”,可以说是一部体现了“现代性”的当代舞剧,它构成了“类史诗叙事”和“类成长叙事”相得益彰的布局,是一部以弘扬时代命题为己任的微宏叙事舞剧作品。
中国传统舞剧在创作上比较重视其教育功能,观众是服务的对象,也是受教育者;由于现实主义舞剧和生活原貌比较紧密,观众理解起来相对容易,观众最大的能动性是对舞剧确定意义的直接感知,以及对编导是否反映了真情实感的判断。“新现实主义”当代舞剧更看重作品与“人民”的共情效果,因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当代舞剧将观众看作“主导”“大众”“精英”“民间”不同群体与个体的融合,各取所需,“关键在于作品结构与其接受者之间的相互作用”。②[德]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载张廷琛编《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当今中国的舞剧生态逐渐向一体多元、多元交融过渡,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转型已是创作常态。编导依然会赋予作品明确的意义,也会使用各种手法让观众感受到这种价值观,只不过更为强调与观众的共情作用。对观众而言,情节和主题集中明确的表达比较符合常规的观赏注意力。如果说“主流舞剧”是主导文化整合精英文化,探讨的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如何创新;那么像《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的“新主流舞剧”则是主流进一步融合“大众文化”,希望在高品质艺术创新的带动下真正走向市场,召唤、吸引观众主动走进剧场。
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贯穿着一根红线,即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当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力助力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谐文化力的营造得益于“一体多元”的文化生态。中国当代舞剧创作既需要历史的传承,也需要时代主题的更新,以及叙事策略的拓展。
四、混融的“现代和后现代”中国舞剧另辟蹊径
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的当代叙事观有区别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谈论“当代”的时候,会设置一个与文化语境相关的时空前提。西方当代舞剧虽注重社会性思考,未必都是现实题材,却都有“现实性”,美学上体现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融后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达,追求的是本体叙事的“表现性”,或是跨文本的“互文性”(如戏仿或借题发挥)以及跨媒介叙事的“去中心化”(不再只突出身体语言)。中国当代舞剧艺术当然不必也不能以西方舞剧的艺术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为圭臬,世界舞剧版图本应丰富而多元的。我们不能迎合“西方中心主义”,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有必要立足中国经验,吸收世界智慧,融汇中西古今,来持续推进中国舞剧艺术创作的发展。
2008年后,肖苏华将“交响编舞法”拓展为“当代编舞法”,这是其舞剧观真正发生质变的关键。广义“现代艺术”虽源发于西方,但中国编导也可以贡献自己的“现代性”,更何况舞蹈的“表现性”本质是无问西东的。对此吕艺生给予高度评价,“如果说新时期以来我们舞蹈创作的基本路径是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话,肖苏华的这一新的观点有望打破创作方法的一统天下。”③吕艺生:《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肖苏华的“红白系列剧”(《梦红楼》和《白蛇后传》)恰是摒弃了苏式现实主义手法,又未顺延中国“新现实主义”的舞步;他借助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社会批判论”,又带上了后现代“互文性”特点,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经典和民间传说的“现代性转换”,以直面“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人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社会的问题”,④肖苏华:《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194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世界性的当代美学进行了思想和形态上的对接。
在理论与实践上卓有建树的还有王玫,她的《雷和雨》《天鹅湖记》《洛神赋》等作品都带有个人化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特质。作品的身体话语和调度话语构成了王玫用以讲中国当代故事的“舞蹈形式”。无论她取材于古典诗词,还是现代文学经典,抑或是脱胎自舞蹈名作,我们在她的作品中,能看到生活中的身体、范式或权力规约的身体和乌托邦的身体,以及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每一种掺杂了人性诠释的身体都带有一种现实态度。
王玫点出了当代舞剧叙事的普遍规律,即舞剧创作需要缝合“行为”和“心理”之事,进行多重复合叙事,可以不再以情节或事件为中心,去单独编“情节舞”“情感舞”和“表演舞”,而要充分挖掘“心理之事”,且将人物塑造和“动因”放在重中之重。当代舞剧注重“叙述”而非“展示”,注重“认知”而非“宣传”。从新世纪初的《雷和雨》开始,王玫就已经比较广泛而深入地实践了“当代舞剧叙事”,出现在此类舞剧中的“生活动作”已不同于“模仿论”的哑剧,而是“仿像”,①仿像(Simulacrum)出自鲍德里亚的重要理论。在他看来,仿像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仿像的形成不再是对某个指涉对象或实体的模仿,只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它不再是对现实生活动作的模仿和再现,而是对行为的重新发现和阐释,情境象征意义大于再现,它的运动方式隐含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在王玫的舞蹈理性思考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王玫的舞蹈和舞剧调度“有效表意”研究,这种对于“具有空间品质的动作形式”的研究,可称之为原创的当代舞剧“空间叙事”理论。王玫的调度强调动态的立体空间结构关系,她的研究基于观众的“前视角”,即观众与舞台整体的关系②这与日本现代舞流派的创始人之一江口隆哉的一个舞蹈构图观不谋而合,他认为“使人从正面看到舞台前部的舞蹈构图也是很有必要的”,与“俯瞰图”联系在一起便是“立体式舞蹈构图”。,强调舞台的内视角,即从“前视角”出发研究身体面向呈现出的角色之间,以及角色与环境的关系,“空间中的细节互构人物关系”强调的是“空间的立体性及其限定”③王玫:《舞蹈调度的王玫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概述”第8页。。
近十来年,中央芭蕾舞团的费波,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王媛媛、韩江,以及苏州芭蕾舞团李莹、潘家斌的创作走向都彰显了他们将芭蕾舞剧创作“当代化”的决心。他们的创作与肖苏华的《梦红楼》《白蛇后传》、王玫的《雷和雨》《洛神赋》等在舞剧叙事美学上有相通性,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编导的意志和情感,却又不囿于此,而是在“互文性”基础上关联着观众的创造性接受,只是程度有所差异。此类舞剧的魅力不在于契合编导的看法,而是观众不断被激发出的丰富的观感与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对改革开放后中国舞剧编导影响深远的《奥涅金》(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版)中虽然也结合了心理编舞,但还不同于现代主义意识流手法。意识流手法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舞剧创作中就有呈现,只不过在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新现实主义”和“混融的后现代”阶段运用得更自如。比如佟睿睿创作的《记忆深处》中就着重突出了张纯如的“意识流”之舞,体现为时间与空间的重叠、分解与重组,既有顺流、倒流,也有明流、暗流。《记忆深处》何以成为近年出类拔萃的中国当代舞剧作品?因为该剧创作源于主创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同时让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创作诉求,通过当代舞剧叙事的艺术化表达充分地呈现了出来,尤其是编导以“心灵的眼睛”开掘了“生活深层的可舞性”,是“内动契机”大于“外动契机”的成功探索。
结 语
近年体制内外的青年舞蹈人登上了官方“扶持计划”的艺术创造平台,获得了追求独立身体语言和剧场表达的机会,体制内外舞蹈家的创作近年也产生交互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当代社会的文艺思潮和中国当代舞剧创作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混融,造成了“当代性”认知上的多元。中国当代舞剧的当代性意识,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守正与创新,兼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包容性。《到那时》和《白蛇-人间启示录》虽然分别代表了当代舞剧叙事美学的两条路径,但这两部作品都承载着一种超越创作思想、态度和方法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方法、原则、流派、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指,那么,“现实主义精神则是一种泛指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艺术思潮所共有,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文艺精神。”①崔志远:《发现精神的“眼睛”》,《文艺报》2006年6月29日。这种精神由人文精神、现实精神、历史精神、科学精神与舞剧艺术本体精神汇聚而成,构成了复杂的交互关系。以当代舞剧的形式表现现实社会、文化、心理的广度和深度,应该在舞剧创作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