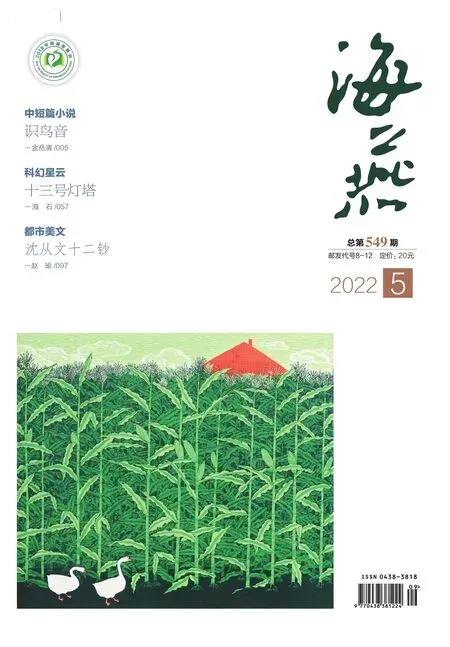识鸟音
文 金岳清

一
涉及到丈的案件发生时,丈父亲作古已经三十年,但丈的案件与他父亲有关。所以,话应该从丈父亲说起。
丈祖上历代经商,到丈父亲这一代,已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丈父亲开米行,这是承袭上代的,上代又承袭上代。丈父亲在世时曾经追溯过,但只能半途而废。因为,家族史料记载的仅数代而已,丈父亲也只好放弃后半截追溯。在有限的追溯过程中,丈父亲有两点欣慰而悲哀的发现。其一,从丈父亲开始上溯,先人逐渐满腹经纶,呈阶梯式递进。其二,从丈父亲开始上溯,米行的气魄却逐渐递减。丈父亲自愧前者弗如祖宗,但后者却能让他聊以自慰。有时三两黄酒润过喉,捻须小嚼,倒也踌躇满志,但想起眼前,膝下并无一子半女,又常常暗自落泪。
某一日,丈母亲忽然告诉丈夫,自己已有身孕。丈父亲立即喜形于色,搂着妻子,不停地抚摸妻子柔软的肚皮,又每每在妻子熟睡时,把耳朵贴在妻子的肚皮上听胎儿的躁动,以致每次都把妻子从甜梦中惊醒。日里丈父亲更是温酒不离手,小曲不离口,怡然自得。但好景不长,正当丈在母亲肚子里住到七个月左右,丈父亲却和人家打了一场关于米的官司。结果,因少喝墨水之故,以输得焦头烂额而告终。丈父亲咽不下这口气,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又一日,他自知难以支撑到孩儿出世,便让妻子眼泪汪汪地坐在床边,对着妻子姣好的面目说:“要是男儿,让他读书吧!”丈母亲凝视着面目憔悴的丈夫,顿时声泪俱下。他伸出右手在妻子抽搐的肩上轻轻抚摸。妻子收住眼泪,默默点头。这天夜里,他便瞑目了。也许天知人意,半个月后,他妻子生下一男孩,取名丈。但丈父亲却无法目睹这玲珑剔透的孩儿。
时间又过去二十年,丈母亲在丈二十岁那年匆匆谢世。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有生之年目睹丈金榜题名,聊以慰藉的是她在行将瞑目的时刻,她的丈已是乡里秀才,她觉得她已对得起九泉下的丈夫。另一个是她在有生之年给丈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小夫妻如胶似漆,一年之后,她自己却悄悄谢世。谢世的那天夜里,她本来也不想惊动这对小夫妻,但她记起该留点遗嘱。所以,才把丈叫到床前,淡淡地说:“读书吧!”丈便把这话记在心上,一直到行将就木时,他还能亲切地回忆起那晚灯光暗淡时母亲说这话的情形。相依为命的小夫妻过了三年,丈那位如花似玉的妻子经不起生活的磨难,也早走一步。丈记得妻子撒手而去时,家中已经绳床瓦灶。丈还清晰地记得妻子走之前,妻子最喜欢的那株春意盎然的紫藤骤然间枯萎。这是那天早晨发现的,他妻子路过后院的紫藤时,当时尖叫了一声。第二天,妻子的脸便同那株紫藤一样也开始逐渐枯萎。后来紫藤连同妻子都没了,丈舒舒扬扬地哭过一场,把妻子葬在紫藤生长的地方。此后,丈仍然每日里摇头晃脑,读他的子乎者也。
二
七年后,红灯县出了一起人命案,罪犯很快被捉拿归案。据说案发时,正下着鹅毛大雪。被害者是一个商人,出事地点在一条山间小径。两个当差的执行某一差使路过那条山间小径时,发现山间小径上有一具被积雪掩埋的死尸。被害者死时留下的一摊血早已凝冻,周围的雪却被衬托得一派通红。现场除留下一排脚印外,还留下一根有十二个花纹图案的白色带子。因为脚印落在积雪上,所以格外醒目。这很方便,两个当差的便趁这脚印追踪。大约过了两里之遥,脚印在一座破山庙门口戛然而止。当差的从破庙里抓出一介书生。书生乃是丈,丈见当差的如狼似虎,战战兢兢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吃官司,当差的没有回答。他又问是否是他父亲留下的官司,当差的说不认识他父亲。其实,他母亲早已告诉过他,他父亲的官司老早以一败涂地而告终,并无留下什么后遗症。当差的不说话,不说话的当差如虎似狼地用麻绳把丈反捆个结实。
丈说:“我要告你。”
当差说:“你告你自己。”
丈说:“我为什么吃官司?”
当差说:“你比我明白。”
丈说:“我乃一介清白书生。”
当差说:“清白书生不清白。”
丈说:“为什么?”
当差说:“不为什么。”
丈说:“不为什么你为什么抓我?”
丈想听当差的话。当差的没有动嘴,没有动嘴的当差却动了水火棍。丈的屁股颤抖了一下。丈觉得屁股被人割去一块肉。丈又记起《水浒传》里李逵将冒充李逵的李鬼打死,在他股上割了一块肉的情节。丈突然想到自己要死,和李鬼一样的死。不同的是李鬼先死后割肉,自己先割肉后死。丈想不到自己比李鬼还惨,丈想哭。
丈和当差的一行三人沿着老路走,老路上有了六排脚印。丈恍惚记起这条路好像走过,当时只留下他走的两排脚印,现在却有六排。
当差说:“走过这路?”
“走过这路。”丈说。
当差说:“哪个时辰?”
丈说:“午时。”
当差的又不说话,雪在三人脚下发出脆响。临近那具尸体时,丈脸色十分难看,当差的脸色十分好看。当差的还露出满意的一笑,在当差的这一笑完毕时,丈开始清醒,于是丈感觉到某种灾难的降临。而在当差的这一笑的动作没有完全完成时,丈已完成了对那个神奇故事的复习。

插图:李金舜
三
相传春秋时期,有一奇人能听懂鸟语,此人名叫公冶长。一天,公冶长坐在破败的山庙里,对着牖,牖外面是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大雪把大树小树山岩全盖了。
突然间,公冶长听见有鸟音,像是叫他。公冶长把头探出牖外,牖外的一块雪地上有很多鸟,鸟们摆出觅食的姿态。公冶长环顾左右,见瓦灶边的缶,公冶长在缶中取粮,缶中唯底壁而已,公冶长有饥肠辘辘之感。俄顷,公冶长又听见有声音叫他,公冶长复把头探出牖外,四周全是白得灿烂的雪和在雪中觅食的鸟。公冶长很纳闷,他怀疑这鸟音与饥肠辘辘有关。公冶长把头缩进牖时,又听得真切,有声音真的在叫他:
公冶长、公冶长、公冶长,
后山有只虎咬羊,
你吃肉来我吃肠。
四周仍是没有人,惟见一羽毛十分鲜艳的鸟,停在树杈上含情脉脉地看他。少顷,那鸟真的又张开嘴叫公冶长。公冶长大骇,惊得书从手中滑落。公冶长以为奇鸟,犹豫再三,决定去后山找羊。
那只羽毛十分鲜艳的鸟在前面飞,公冶长跟在后面走。公冶长走得很快,鸟飞得不紧不慢,但公冶长还是跟不上鸟,总是相距五十步上下,这距离后来一直保持到那个预定地点。预定地点到了,鸟先停下来。公冶长走过去一看,鸟停在死羊肚上,死羊颈项已被咬烂。地上血已凝冻,好像红宝石一样灿烂夺目,把周围晶莹的雪映得通红。这晶莹的雪和灿烂的血交相辉映,形成辉煌世界,公冶长感觉到一片温暖。
接下去仍是那鸟在前面飞,公冶长跟在后面走,羊在公冶长后面。公冶长与羊之间多了一根白带,公冶长腰间却少了一根裤带。公冶长记得那带子是母亲在他十岁那年的冬天给他结的。
后来的事情,公冶长知道自己错了,错得明明白白又稀里糊涂。公冶长拿那羊饱餐数日,鸟一直蹲在公冶长身边没有离开半步。当公冶长将最后一块肉咽下时,公冶长摇摇晃晃地去提羊肚肠,鸟跟在公冶长后面。公冶长把羊肚肠提到后院,鸟跟到后院,公冶长看了鸟一眼,发出阴冷的笑,鸟颤抖了一下,落下一根疼痛的羽毛。接下去是公冶长把羊肚肠扔进粪坑里的声音。
又一日,公冶长坐在破败的山庙里,对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大雪把大树小树山岩全盖了,大地一片银装素裹。
公冶长又听见有鸟叫他,鸟说后山又有虎咬羊,鸟又说公冶长吃肉它自己吃肠。公冶长想起羊肉味,口水止不住流在书页上。公冶长用宽大的衣袖轻轻拂去书页上的口水。鸟又在叫公冶长:
公冶长、公冶长、公冶长,
后山有只虎咬羊,
你吃肉来我吃肠。
仍然是那只羽毛鲜艳的鸟,停在树杈上看他叫他。公冶长这回没有犹豫,合上书,掩好门出去。鸟又飞在前面,公冶长仍然跟在后面。鸟飞得快,公冶长跑步走。公冶长仍然追不上鸟,鸟折回老路引公冶长。出事地点到了,鸟背着公冶长骑在尸体鼻梁上,又有很多鸟飞过来停在尸体的脸上。公冶长看不清,远远看见以为这只羊大,公冶长解下腰间的裤带。公冶长走近时,鸟轰的一声全部飞走了,公冶长这回看见的却不是羊,而是一具死尸。死尸脸色苍白,颈项稀烂,地上的血已凝冻,周边是血色的雪。公冶长觉得血是自己身上流出来的,冷得发抖。公冶长头皮发麻,牙齿打颤,两脚发软,转身想逃走,裤掉在地上差点把他绊倒。公冶长两手抖抖地提着裤腰,裤带落在雪地上。裤带是上次的裤带,是母亲给他结的。公冶长没有捡,逃命要紧,公冶长就提着裤子逃回破山庙。
四
县官坐在府堂上,三响鼓鸣之后,有人高叫升堂。声音宽阔而洪亮,结尾时却把余音拉得如缕缕青烟袅袅升腾。差役分立两旁。县官令差役押上罪犯,差役把丈带上来。丈见了堂上气魄,一时昏昏然,怀疑自己是否已进入天堂。差役见丈木讷,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丈两膝着地。丈看见穿禄袍的县官正襟危坐,头上乌纱帽两边长出两块长方形的小黑布,县官说话时,小黑布上下跳动。丈觉得当县官很有意思。丈记得母亲在世时对他说过:“官是书读出来的。”丈想,县官也肯定是书读出来的,可自己读到现在还没当官。丈感到悲哀,自己不及坐在府堂上的县官。正当丈悲哀时,丈忽然发现县官胡与须都很长。丈摸摸自己胡子,没有县官长。丈觉得县官年纪大,读的书多,所以当官,所以坐府堂,等自己胡与须也有县官这么长时,自己肯定也会当县官。丈希望自己胡与须快长,越快越好。丈又发现,县官座位后面有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大老虎。丈想,虎是什么意思,是否代表县官?虎会吃人,那么县官是否也会吃人?丈又想,坐在府堂上的县官是好官还是吃人的官?
丈正想时,惊堂木被县官拍响,丈突然间被惊堂木惊醒。
县官说:“姓名?”
丈说:“丈。”
县官说“姓?”
丈说:“丈。”
县官说:“名?”
丈说:“丈。”
县官觉得好笑,觉得好笑的县官没把笑露在脸上;县官又觉得好气,觉得好气的县官把气表现在脸上,脸气歪了半边。
县官说:“何方人氏?”
丈说:“红灯县。”
县官说:“红灯县什么地方?”
“山上。”丈说。
县官说:“山上什么地方?”
“山上庙里。” 丈说。
县官说:“什么活儿?”
丈说:“读书。”
县官说:“读书算屁活儿。”
丈嘴上没说,心里在说:“县官算屁县官。”
县官说:“你杀人?”
丈说:“我没杀。”
县官说:“那是谁的脚印?”
“是我脚印。”丈说。
县官说:“是谁的裤带?”
县官说是谁裤带时,差役李把那根有十二个花纹图案的白带子掷在地上。噗一声,丈抬头看见地上的裤带就在自己眼前。
“我裤带。”丈说。
丈捋开褴褛衣衫,县官看见丈裤腰上多了一根草绳。
县官说:“你杀人。”
“我没杀。”丈说。
县官说:“先打三十大板。”
丈还懵着,丈正在想应该怎样回答。水火棍落下来,丈先是杀猪般嗥叫,后不再嗥叫,单是呻吟。缓了好一会儿,丈气若游丝,趴在木凳上断断续续讲公冶长的故事。丈讲完故事时已满头虚汗,脸色白得吓人。
五
县官听完故事,似有所悟。离开大堂案,慢慢转到丈的边上,轻轻地说:“你亦有此遇?”
丈抬起头来,吃力地说:“是。”
县官俯下身说:“会听鸟语?”
丈又低头说:“是的,老爷。”
县官捻须沉思。当县官再次把目光落在丈身上时,县官说退堂。差役们都发呆,互相对看几眼再看堂上时,县官只留给他们一个可笑的背影,差役们在莫名其妙中退堂。
县官传差役李。差役李在西书房里见了县官。县官反剪两手望着窗外世界沉默不语。差役李站在他后面不敢抬头。过了好久,差役李才轻轻地说:“老爷有何吩咐?”
县官转身的动作十分缓慢。差役李在心里寻思:老爷心里可能又在酝酿着计谋。因为老爷过去酝酿计谋时转身动作都这样缓慢。县官轻轻挥了一下手,婢女们都退下,连师爷也退下了。屋里只剩下县官和差役李,差役李受宠若惊。
县官说:“去抓把米。”
差役李说:“是。”
县官又说:“去倒杯卤。”
差役李说:“是,老爷。”
差役李完成这两件简单事情后,县官指点差役李把米倒在卤杯中搅拌,又把搅拌后的米放在一个青瓷碟里。接下去县官和差役李耳语了几句,差役李有惊愕之色呈现于脸上。差役李又有欣喜之色呈现于脸上,因为他又一次证实自己的猜测。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丈醒来时,见一注阳光漏进狱中,坐起来伸伸懒腰。丈见一狱卒走近,丈对着狱卒说:“我要读书。”狱卒给他一个凶恶的眼神,还有一张狰狞的脸。丈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丈记起水火棍落下时差役的眼神和面容也是这样的。丈不再说,丈怕水火棍。丈木然时,狱卒踱开,丈又轻轻说:“我要读书。”
“读鸟书。”狱卒说。
有人叫狱卒,丈听不清狱卒名字,狱卒没看丈就走。丈想叫他,丈没叫时狱卒就走开,丈把目光留在狱卒的背上,又跟狱卒背影一起被吸进门里。
这时候,丈突然听见有鸟叫,声音在屋檐上,有些嘈杂,似乎在埋怨什么,又有打翻碟子的声音。
有声音高唱升堂,声音仍然宽阔而洪亮,有股漫延之势。差役们仍然分立两旁,各人手里都拄着水火棍。丈被差役押上,丈这回没有让差役蹬脚就跪下。丈看县官身后屏风上的虎比第一次温和,丈想县官是否温和。丈看县官时县官正好看丈,目光相遇时,丈屁股又颤抖起来。丈忙把目光向下压,目光落在县官靴上,丈感到脚冷。县官把惊堂木一拍,丈冷得发抖。
“半个时辰前听见什么?”县官说。
丈木讷,目光停在县官靴上。
县官又说:“半个时辰前你听见什么?”
“有,有鸟在说话。”丈猛然醒悟过来。
县官说:“鸟说什么?”
丈抖抖地说:“米好吃,咸些。”
县官心里咯噔了一下,变了脸色。
县官说退堂。县官在心里说:书生是凶手,但我要留他性命。
六
县官退了堂,背着双手,腆着肚子笑意盈盈进了西书房。西书房中竹笼里的那只长尾巴鸟叽叽喳喳地叫着。县官高兴,高兴是因为他自己聪明,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一个懂鸟语的人。师爷见县官高兴,他也高兴,师爷佝偻着细腰,笑着山羊皮的老脸跟在县官一旁,说道:“老爷,明镜高悬,老爷明镜高悬呐!”
县官走到书案前做出一个伸手的动作,师爷便捡起案头上的细竹签递给县官,县官踌躇满志,接过细竹签,便拨弄起竹笼里的长尾巴鸟来。长尾巴鸟也十分兴奋,享受着县官的挑逗,上蹿下跳,色彩斑斓的羽毛闪耀着亮丽的光芒。
天快黑下来时,下起了雨。雨不大,但能听见“沙沙沙”的声音。丈很纳闷:县官莫名其妙为什么又退了堂?丈蜷缩在墙角边寻思了很久,也不得要领。到了后半夜,丈想睡,但又睡不着,丈想起妻子曾经告诉过他一个办法:数羊。丈内心狂喜,差点笑出声来。丈调整了一下躺姿,开始默默数羊,但脑子一点都没有混沌起来,反倒越来越清晰,羊数到一千,外面的雨也被丈给数停了,再也没有听见雨的声音。月亮的清辉从牖外面倾泻进来,泥地上似乎多了一层薄薄的雪,搞得周遭寒彻,丈干脆不睡,看着地上明晃晃的白光,在黑暗中想起妻子。
七
多年以前,丈记得是一个秋天。秋天是丈的秋天,一年四季,丈最喜欢的是秋天,每年到了秋天,丈就会感到一身轻松,舒适,时刻有雀跃的感觉。已是乡里秀才的丈,这一天仍然是坐在书房里读书,从书房的牖看出去,外面是一条大路,大路从远处延伸而来,在村口拐了一个温柔的弯,就流进村来。其实,丈早已无心读书,这天早晨穿衣时他就记起邻村徐媒婆三个月前说的话:“这媳妇儿恁个标致呵!”
徐媒婆说这话时,喜形于色,那神形依然鲜亮。丈手中捧着书,屡次抬头看看牖外面,大路上是否有他的媳妇儿袅袅走来。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丈真是有点望眼欲穿。后来,丈累了,趴在书案上睡着了。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美人儿在竹林里羞涩地向他招手,那方红手帕在翠竹间闪烁,映得小脸儿通红。丈还在疑惑,一阵风吹来,翠竹林嗖嗖作响,丈刚抬起头,美人儿倏地一下子不见了。丈大惊,就醒了过来。这时候,牖外面大路上锁呐声此起彼伏,一顶小花轿款款而来。丈扔掉手中的书,狂奔而去。到了门口,丈看见花轿上落了一只小鸟,欢快的锁呐声早已把空气渲染成玫瑰色,小鸟叽叽喳喳地在花轿上雀跃。丈远远看去,心头涌上一句:这一队人马喜气洋洋。等到新媳妇出轿那一刻,丈用手去搀扶她时,丈听见站在轿顶上的鸟冷不丁说了一句:
“百年好合。”
丈内心一振。这在丈听起来既含糊又清晰,丈想倾身再听,那鸟又飞到轿顶上自个儿啄着花布,偶尔抬头看看人群。那天晚上,洞房花烛时,丈几次想问新娘听见没有,又怕骇了她,所以就一直不敢开口。当然,丈也怕自己听错了音,这鸟怎么会说话呢?简直是荒唐。或许是自己偶然间的恍惚。
八
天快亮时,丈真的撑不住了,这回,丈不需要数羊就迷糊起来。
第二天,丈醒来时,牖外面阳光普照。师爷来了,师爷说自己奉老爷之命,请丈到西书房茶叙。丈在心里嘀咕:屁茶叙,还不放人。
丈在嘀咕时又担心破庙里熬粥的炭火是否熄灭?如果炭火没有熄灭,那瓦罐里的粥是否会熬糊。丈记得那天差役来得很急,容不得他盖上炭火,就连大门也没有掩上,丈是想先盖了炭火,再关上门,用绳索系上,免得有野东西闯进来。差役不管,差役只知道挥动手里的水火棍。丈看见差役手里的水火棍两股就发抖。结果是连大门也没有掩上,半扇门还敞开着,丈回头往里看了一眼,桌上的书还被凛冽的雪风吹得呼啦啦作响。那头顶上的水珠呢,有无掉下来落在书页上?头顶上的水是从瓦片里渗透出来的,大概是这老庙年久失修,山风把瓦片挪了位置,也可能是瓦片破损了,留了缝隙,这瓦片上的雪化为水,这水便渗透进来。渗透进来的水会沿着梁和椽蜿蜒而来,偏偏到了书案的顶上停下来,不走了,凝聚成水滴,滴下来,落在书上,啪的一声,书页上便有了一点圆圆的水晕。丈马上把衣袖按上去,吸去水,才不至于让水渗透下去,坏了书。有时这水珠也落在丈的头上,啪一下,冷不丁掉下来,打在丈的天灵盖上。丈吓了一跳,以为神,慌忙跪在地上,请山神保佑。可跪了大半天,却不见动静,丈又抬起头来,骂顶上这该死的水滴:“你这蠢货。”
丈的意思是:你这蠢货,为何不再往前走几步?但水滴不管他,只顾自己爽快,只要是蓄够了,蓄满了,就照样吧嗒一声落下来,至于是落在书上,还是落在人上,抑或落在地上,这不管。有几次,丈仰起头骂头顶上的水珠时,水珠冷不丁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他的嘴里。丈还没反应过来,水珠就被咽到肚子里。丈大惊失色,扑通一声跪在泥地上,对着顶上又在集聚的水滴纳头便拜,口中念念有词:
“水滴大人在上,小的冒犯大人,望乞恕罪,望乞恕罪。”
奇怪的是硕大的水滴竟然停在那儿,粘在梁上,引而不发,圆圆的,亮亮的,像一只小眼睛看着丈,似乎在笑。丈突然又涌上一句:
“头上三尺有神明。”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九
师爷在前走,丈在后面跟着走,跟在后面的丈惴惴不安。师爷把双手相互插进袖口里,躬着背,深灰色的绒帽已经褪去了光泽。丈也躬着背,踩着师爷的脚印走,清涕不断流出来,落在雪上,太阳已三丈高,天地间一片光亮,没有风的时候有些暖和。
进了大门是二门,过了二门是大堂,往大堂西侧走,出小门是迎宾馆,穿过迎宾馆往北到了西书房。走进西书房,看见中央置一只巨大的铜火炉,火炉里烧着白炭。室内温暖如春,丈伸了一下腰,看见县官一个背影。县官穿绿袍,头戴黑缎帽,后背搭一根长辫。县官正在逗鸟,听见背后有声音,便慢悠悠转过身来,丈早已伏在地上叩首。县官手里拿着一根细竹签,笑意吟吟,让师爷扶起丈。丈看见书案上放着一个鸟笼,鸟笼高大,圆桶形,是青竹丝编织的,泛着淡黄色光亮。笼子里一只色彩斑斓的长尾巴鸟上蹿下跳,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丈一时也听不出所以然。
县官让丈坐,丈不敢坐,红木大椅油光水亮的,丈怕自己的屁股脏了红木大椅。师爷也示意丈坐下,师爷给丈来了个示范,妥妥地坐在旁边的红木大椅上,用手捋了一下旁边茶几上的那盆兰花。丈战战兢兢走到红木大椅边上,用手摸了几下油光水亮的红木大椅,抖抖地坐了上去。
“十万雪花银。”
丈的屁股刚挨上去,鸟笼里的长尾巴鸟突然高叫了一声。这声音饱满、洪亮,中气十足。
丈吓了一跳,从大椅上滑落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县官和师爷都哈哈大笑。丈看见长尾巴鸟眼露凶光,从笼底猛然往上一跃,两只锋利的尖爪紧紧抓住笼壁,回过头来盯着丈看了两眼,又用尖锐的嘴啄了十几下笼壁上的青竹丝,才安静下来。
十
县官让丈留在衙门做个书吏。
这是师爷告诉丈的。夕阳西斜,师爷和丈从西书房退出来走到墙角边时,师爷才兴冲冲地对丈说:“恭喜了,老爷有意让你留下来做些笔墨文章。”师爷以为丈会千恩万谢,或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他叩个响头。但丈没有,丈无动于衷。无动于衷的丈跟着师爷走到西书房北面的两间小瓦房前,师爷推开门,里面早已被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各种家什,一应俱全。书案上还有一叠旧书,书边放着一个粉青色梅瓶,一支蜡梅从瓶口斜出,黄花淡韵,清香四溢。小瓦房西侧是一条大道,大道尽头是绵延的山恋,山峦上白雪皑皑。西沉的夕阳斜照着地上的积雪,房间里明亮,整洁。丈有些喜欢,就住了下来。
这一夜,丈辗转反侧,丈几次想起西书房那只色彩斑斓的长尾巴鸟突然间高叫起来,心里不觉暗自好笑。“十万雪花银,十万雪花银……”丈在被窝里模仿了好几回后,觉得味道寡淡,又在黑暗中胡思乱想起来。丈先是想起如花美眷,想起自家后院那株春花烂漫的紫藤,有一日早晨莫名其妙地突然枯萎下去。
后来,丈又在黑暗中想起已经十分遥远的少年故事。
十一
也是一个下雪的冬天。那时候他还小,十几岁吧!十几岁时他寒窗苦读,整天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诵读四书五经。每天读书前,他都要沐浴、更衣、焚香,然后在父亲的牌位前跪下来,上三炷清香,叩上三个响头,再正襟危坐在书案前,轻轻打开书,认真诵读。他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上午,牖外面飘着雪花,他读累了,伏在案上闭了一会儿眼。待他再睁开眼睛时,看见一只羽毛漂亮的小鸟从雪花纷飞中斜穿过来,落在自家院子里,小鸟裹着瘦小的身子,冻得发抖。他已无心读书,出了门,踩着厚厚的积雪到院子里看小鸟,小鸟玲珑剔透,羽毛五彩缤纷。他突然间有了眩目的感觉,也动了恻隐之心,蹲下来。小鸟注视着他,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小鸟漂亮的羽毛,小鸟啁啾低吟,惹他爱怜。他伸出小手捧回小鸟,把小鸟轻轻捂在怀里,小鸟轻轻地啾了一声,把落满雪花的身子往他胸口贴过去。他把小鸟捧到书房里,书房要比院子暖和多了,冬天的日子里,母亲都会在他书房里红起炭火,炭火在瓦罐里泛着暗红色的光,蒸腾的热气从瓦罐顶口散发,房间里便渐渐暖和起来。他把小鸟放在书案上,书案上放着一卷《论语》,一把青竹戒尺,书案右上角还有一杯温热的糖水。青竹戒尺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用来惩罚有时候昏昏欲睡的自己。温热的糖水是母亲刚送来的,母亲说,冬天太冷,给他暖暖身子。他把温热的糖水倒一半在青花破碗里,放在小鸟面前,小鸟喝得很兴奋,叽叽喳喳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听不懂,但他看见小鸟的眼睛晶莹发亮,他再看时,小鸟突然跳到他的肩膀上欢呼雀跃。母亲进来是给他送点心的,母亲看见了,没有责怪他,只是转过身去暗暗垂泪,他用青竹戒尺打了自己左右手掌各二十大板。手掌通红,浮肿,火辣辣的,生痛。他又摇头晃脑读《论语》,小鸟蹲在书案上目不转睛看着他。到了午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大地一片耀眼,小鸟飞出去了,又欢快地飞回来,停在他的膝盖上,不停地啁啾,如此反复了多次。小鸟最后一次是从牖口飞出去的,小鸟在牖上停了好久,看着他,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谢谢你!”
他大惊失色,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小鸟对他莞尔一笑,飞了出去。他浑身一抖,手中的《论语》滑落在地上。这一夜,他一直没睡着。
十二
县官病了。这是从伙房里传出来的消息。
丈暗自寻思道:怪不得这几天都没有见老爷了。这几天也没有什么关乎人命的诉状,只是本街清河坊南货店的陈三发为半垛墙基与侄儿陈和令发生口角,双方争执不下,陈三发要把侄儿陈和令扭送衙门问罪。侄儿陈和令怒不可遏,认为这事情本来就是叔叔的错,这回还六亲不认,要把他送官处置。所以,火气攻心,一拳直捣叔叔脸颊。陈三发正好回头,这一拳恰好打在陈三发嘴上,当场就断了两颗门牙,鲜血淋漓,嘴唇肿得与涨了水的海参一样。陈三发一纸诉状把侄儿告到县衙,等待县官老爷重重处置。
丈翻了诉状,放在一边,站起来伸个懒腰。突然听见鸟笼里扑扑作响,抬起头一看,又是那只长尾巴鸟在竹笼里闪转腾挪,那鸟五彩斑斓,腾挪起来更是让丈眼花缭乱,丈只觉得一面斑斓锦旗在他眼前恣意漫卷。丈背着手,慢慢踱到鸟笼前,一缕阳光斜照进来,落在鸟笼上,长尾巴鸟兴高采烈,一边跳跃,一边啁啾个不停。还对着丈,不停地挤眉弄眼。丈想捡起书案上的细竹签轻轻拨弄鸟尾巴,长尾巴鸟倏地蹿下来落在笼底,笼底垫着厚厚的印花蓝布,上面有很多白花花的鸟屎。长尾巴鸟低头啄了几下印花蓝布,又用爪子抓了几下,发出嘶嘶的声音。这时候,长尾巴鸟突然张开翅膀,伸了一个大懒腰,丈眼前忽然间展现出一片宽大的织锦,亮丽而炫目,并袭来阵阵温暖。丈正木讷时,长尾巴鸟突然叫了起来:
“赛西施,赛西施。”
丈听得真真切切,这声音清亮,平稳,有厚度。丈把手中的细竹签惊落在地上,一时傻在那里。长尾巴鸟看见呆头呆脑的丈,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地又笑又叫,上蹿下跳个不停,那片美丽的织锦早就收起来,又变成一串抖动的彩色音符。
县官得的是伤寒。夫人传令请太医过来问诊,太医给县官号过脉,又问县官早几天安寝如何?去了哪里?县官表情淡漠,反应迟钝,半闭着眼睛支支吾吾,说得不明不白。夫人怒火中烧,好在能压住,但脸色铁青,柳眉倒竖。太医早有所闻,县官倾心清河坊,醉意摆酒营。那里夜夜笙歌,处处莺语,即使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也春意盎然。县官乐不思蜀,常常陷入温柔乡彻夜不归。太医又让众人且先退下,让夫人也退下,请小童帮忙,揭开老爷内衣,看见一片玫瑰疹。太医附在老爷耳边轻轻说道:“不碍事,得的是伤寒。不过,还有,还有,老爷您那个一点吧!”太医诡异地笑笑,县官把刚睁了一半的眼睛又闭上,嘴里嘀咕着:“春宵一刻呐!”
师爷把太医引到西书房给县官开了处方。太医看见坐在书案前看书的丈有些异样,师爷说,刚来的书吏,帮老爷整理文案,起草文字,还有,还有……
“闭嘴。”
长尾巴鸟突然大叫一声,从笼顶一跃而下,丈压根儿没有想到这鸟声如此骇人。师爷与太医被弄得莫名其妙,俩人都回过头来看着鸟。鸟又若无其事,自顾啄着青花瓷杯里的米,一边惬意地理理自己色彩斑斓的羽毛。
十三
半个月后,县官恢复了状态。
那天早晨,丈在睡梦中听见西书房那边有琴声悠扬。丈醒过来,侧耳倾听,原来是县官在抚琴,弹的是《高山流水》,琴声沉静古雅,又有潺潺流水蜿蜒曲折之韵,丈如饮甘露,豁然间神清气爽。丈在床上回味琴声,再三咀嚼,仍有余音绕梁。过了一会儿,丈又转身看牖,牖外面有丝丝亮光。丈正待起床,门口已有小童在叩门,说老爷有事吩咐,让他速速起来。丈推开门,外面空气十分清新,但琴声更加清纯,仿佛有一丝丝甜意。有几只鸟零星地落在屋檐上,侧着头,似乎也在欣赏县官的手艺。一阵风吹来,空气依然凛冽,屋檐上的鸟都拥进院子里,静静地落在树枝上,丈听见很多鸟七嘴八舌,声音嘈杂,听不真切,好像在抱怨这鬼天气冷得要命。
师爷和县官已在等候。师爷站在县官边上,手里提着西书房的鸟笼,那只长尾巴鸟在笼子里不停地腾挪,师爷手里的鸟笼晃荡不安。
丈在县官面前停下来,接过师爷递过来的鸟笼,三人从县衙出去,穿过紫阳街,向右拐了弯。走在大路上,丈远远看见西山上有四塔,四塔星罗棋布,高低点缀,错落有致,等走近仔细看时,风格也各异。县官指点着四塔,对丈说这都是旧物,隋、唐、宋、元各一,一山四塔,自己为官几十年,南北辗转,也不多见。山下有一亭,亭为六角,飞檐已有损,木柱上红色亦已褪去大半,看上去斑斑驳驳,柱上刻有一副联:
四面云山供点笔,
一庭花鸟助吟诗。
字迹遒劲,又不失风雅。底下石栏杆犹存,栏杆上面留有残雪。亭中有一巨碑,然字迹已模糊不清。师爷说:“县志上有此碑记,内容为修塔记。”丈仔细察看,果然有“重修西山千佛塔记”篆额,篆额虽有残损,但能依稀辨认。
再走过去是一片缓坡,此时天地间一片清亮,缓坡上树木高大,大多为古柏,间或有青松,树林里有很多鸟叽叽喳喳地在诉说着什么。丈手中笼子里的长尾巴鸟也兴奋起来,在笼子里扑腾、欢叫。丈把手中的鸟笼高高举起来,对着树林里的鸟,树林里的鸟鸣声刹时间响成一片,问好声、招呼声、笑声、歌声、嬉闹声,长调短音,高亢的、温婉的、激越的、舒缓的各种声音互相交织,树林里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丈侧耳倾听了半天,感觉这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快活。县官问丈树林里的鸟说了什么?丈说这鸟音太嘈杂,自己辨不出来,只是感觉到树林里有五彩的流星雨在飞倏,闪亮闪亮的,让人眼花缭乱。县官说这个感觉他也有,关键是如何听清楚,鸟们在说什么?丈说自己再仔细听听。县官嘴上没说,心里却打鼓:这小子胡芦里卖什么药?要命的时候听得十分清楚,现在又在装糊涂。县官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一棵古柏下侧耳倾听,不想古柏上的大黑鸟往下看了一眼,兴奋地叫了一声:“着!”
一坨热屎掉下来,刚好落在县官的左肩上。丈差点笑出声来,师爷慌乱中掏出怀里的手绢一路狂奔过去,看见县官已经跳出三步,苦着脸,杵在那儿。师爷用手绢擦去县官左肩上热气腾腾的鸟屎时,县官哭丧着脸,用手捏住鼻子,嘴里不停地说:
“臭,臭!”
“咯咯咯,咯咯咯咯……”丈手中的长尾巴鸟突然开怀大笑,这笑声十二分清亮,仿佛是一道白色亮光飞入树林里,树林里的鸟全都大笑起来。这笑声宏大,宽阔,震耳欲聋,一浪一浪,此起彼伏,丈似乎感觉到有浪花在飞溅。县官先是一惊,后来就呆在那里,再后来似乎有所悟,才把僵硬的脸渐渐松开来。丈说:“好像是笑声。”县官独自浅笑了一下,点点头说:
“我听也是。”
丈内心一惊。丈回头再去看县官时,县官脸上已经看不出喜怒哀乐。
太阳已经两丈高了,地上的雪一片耀眼,树林里的绿意更加明亮起来,树上的积雪开始往下掉,有些尖叫着化为水,雨一样滴下来,这声音清晰可见。县官早已站在一块空地上,他无法判断哪些是水滴,哪些是鸟屎。他只好躲得远远的。树林里的鸟又欢快地在树枝间上下跳跃,不停啁啾。丈手中的长尾巴鸟也在鸟笼里拼命扑腾着,丈知道长尾巴鸟想出去,它也想站在高枝上跳跃,并且一展歌喉。丈有些累,随手把鸟笼挂在枝桠上,长尾巴鸟扑腾了一会儿后,安静下来,裹成一团彩球。树林里的鸟突然间鸦雀无声。县官对着鸟笼掷过一个雪团,长尾巴鸟依然不理不睬。县官走过几步,摘下鸟笼提在手里准备下山,长尾巴鸟忽然瞪着眼睛,歇斯底里大叫了一声:
“人命关天!”
这声音振聋发聩。县官大骇,惊得脸色发青,手中的鸟笼差点掉在地上,师爷赶紧抢过来,扶住县官。丈迟了一步,接过县官手中的鸟笼,用十分诧异的目光打量长尾巴鸟。这时候,树林里鸟声四起:
“人命关天!人命关天!”
这鸟声如山洪爆发,震耳欲聋,汹涌而来,并且一浪高过一浪,有漫掩和碾压之势。三人吓得脸色大变,急忙下山而来,走了好远,后面的声音仍在起伏……
十四
第二天早晨,丈踏进西书房便惊呆了,那只长尾巴鸟横在鸟笼里,两翅紧裹,两脚笔直,身体僵硬,长长的细竹丝已经洞穿了它的颈项,细竹丝上留有一截两寸多长的血凝。长尾巴鸟怒目圆睁,看上去好像秋天里一粒刚打下来的白豆。丈啊地叫了一声,冲到院子里,浑身发抖,嘴里发出的全是鸟音。
县官站在二楼,瞟了一眼说:
“这鸟人。”
县官话音刚落,师爷连滚带爬跑过来大叫道:
“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老爷,鸟……鸟来了!”
县官愤愤地说:“怕个鸟。”
县官说话时抬起头来,看见西边有一片黑云正漫掩过来,遮天蔽日,并伴有洪大的声音。县官正疑惑着,眼前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又厚又稠,那鸟们像蝗虫一样蜂拥过来,成群成群地落在县官头上。
少顷,县官头上的肉没了,只剩下一个白骨头颅。白骨头颅下是一袭簇新的绿袍,绿袍上粘满了恶臭的鸟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