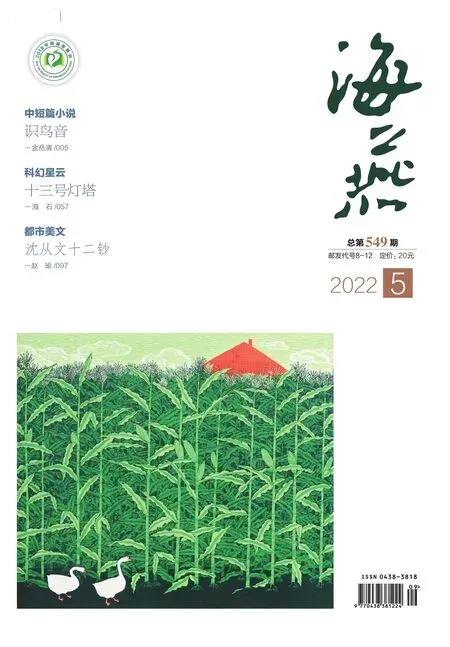瞿爹的小院
文 照 川

一
纠结来纠结去,纠结了好几个月,瞿爹到底还是决定回老家去。
瞿爹不是个含糊人,决定一旦做出,就是铁的了。他当初来到佛山也是一样,决定了就不再更改。
还是有些不舍。
瞿爹在佛山已生活了整整二十年,这里算得上是他的第二故乡。相比老家江汉平原的一个县城,佛山更为亲近。这二十年的时间里,老家的县城因拆迁和扩建,弄得他回老家时,竟处处要向人问路;而在佛山,他倒是经常给别人指路。他的根,已经深深扎进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南方城市。何况,他从老家出来时,就发誓不再回老家。
来佛山之前,瞿爹是县瓷器厂的第一批下岗职工。他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哪个都认为,只要瓷器厂还存在,他就会是最后一批留下来的人。但是他为人耿直,得罪过厂里的主要领导,所以他这个先进工作者,也在下岗的事上先进一步。而晚几年下岗的职工,最后都争取到了一份养老保险。瞿爹算是白白为单位奉献了二十五年。
下岗之后,瞿爹按熟人的指点,进了佛山的一家民营瓷器厂。尽管他因耿直在老家的单位吃了大亏,他还是改不了直脾气,好几次为工作上的事,都不给老板面子。老板却还是重用他,给他一档的工资和一档的社保。瞿爹感慨:还是私企老板好,只要你肯做事,一心为厂,你就是天天跟老板抬杠,他也会包容你。所以,他把佛山看成了自己的福地,决定就在这儿养老送终。
七八年前,老家县城的房子拆迁,瞿爹选择了现金赔偿,在老家,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几个走得近点的亲友,有的到大城市里去打工创业,有的随着子女迁移,上海、武汉、广州……散得哪儿都是了。所以,他十年前就在佛山买下了这套房子,堂客也早跟着来了佛山,丫头从小学时就在佛山上学,大学毕业后也在佛山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五年前,瞿爹办了退休,拿着佛山的退休金,老两口就等着抱外孙了。可是,丫头带堂客去长隆逛动物园时,路上不幸双双遇车祸丧生。
这几年,瞿爹一个人过日子,感到越过越不顺心,越过越孤单,人也老得很快,他头上的灰发添了将近一半。有人劝他再找一个伴儿,他不。屋子里摆着堂客和丫头的好多相片,不舍得收起来,人家哪接受得了?他还种着许多茉莉花和兰花,还有丫头抱回来的一条狗,人家也会接受不了。一个人过着,好歹还有相片、花草,还有黑黑这条狗呢。
二
瞿爹正要带黑黑到珠江边去遛遛,阿英骑着电瓶车来了。
阿英在附近的房屋中介公司上班,本科毕业的一个女伢子,做中介实在委屈了她。她说累是累点,但是时间比较自由,可以照顾儿子非非。阿英的老家也在江汉平原,是跟瞿爹的老家紧挨着的一个县。瞿爹像遇上了亲人,把房子出租的事都委托给了她。他跟阿英说,房子出租不急,有合适的就出租,没合适的自己就先住着。他回老家后,也是准备先租房住,住得好就买一套小房,住得不好就再回佛山。
阿英高兴地说:瞿爹,终于替您找到了合适的租户,是个退了休的中学老师,从河南来的,姓王。她的儿子,就是前几年在城南化工厂大火中牺牲的一个消防兵,她老伴儿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突然心肌梗死,也走了。她的儿子和老伴儿都葬在这里的公墓。退了休,她便决定来佛山养老。王老师爱干净,爱种花草,她要我把您的小院子拍给她看看。
瞿爹的心一颤,原来王老师的命运竟然跟自己一样!他说:你拍吧,但愿王老师能满意。又说,我还真有些舍不得呢。
阿英说:我晓得,您不缺这点钱,但房子一空,就容易发霉,特别是一楼,坏得快。
瞿爹笑了,笑得有些勉强。他心里替王老师难过,也替阿英难过。这好人,怎么都那么多磨难呢!
阿英安慰道:反正出租合同只签一年,刚好王老师也是想先签一年。还有啊,你们两个老人家想得都一样,价钱无所谓,都由我做主。我就定了个整数,因为您要留下一个房间装自己的东西,相当于是一房两厅带院子,按市价可以租到一千二,我就定了个月租一千,您看合适不?
合适,合适。瞿爹顿了一下,说:王老师这个情况,你还可以低点,六百吧,足够我在老家租房了。他这副样子,好像是跟阿英换了个身份,自己成了中介,为王老师讲起情来。
阿英惊讶地说:六百?这个价王老师不一定接受呢!这么便宜,我怕她会不安心呢。
你就说我不缺钱,是要找个人看房子,打理小院子。瞿爹期期艾艾地说。
阿英有点为难地说:我试试吧。又说,我还真舍不得您搬走呢。有您在这儿,我多一个家乡人,可以说家乡话。我家非非也喜欢您呢,他说星期六要来看您的狗呢。
阿英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舍不得搬了呢,我回老家去,也不一定遇得上你这样的好邻居呢。瞿爹顿了一下,又说,王老师要租,就租给她吧。
阿英笑道:您反正没事,回老家后也可随时来玩,现在高铁又方便。再说,我回老家也会去看您,中途转一下车也方便。

插图:王译霆
阿英说着,用手机拍起视频来。瞿爹跟着她看,越发露出舍不得的样子,好像她这一拍,他的小院就会吸进了手机,再也没有了似的。
阿英看出,瞿爹的眼睛里又多了一层复杂的东西,似乎又很希望房子租出去。她想起自己的父母,当初真是既希望自己嫁出去,又十分舍不得。她心里叹道:这老人家,把房子看得跟亲生丫头一般呢。
瞿爹,您也可以再住一段时间,我给王老师另外找房子就是了。
瞿爹下意识地咬了咬牙,说:租,我已托人在老家县城看好一套房,就等我回去看呢。他又迟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可不可以先见见王老师?
可以呀,王老师也说,房东和租客,互相见见面最好。
瞿爹笑着,脸却莫名其妙地有些发烫。
阿英说:我打个电话,问下王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望着满面笑容打电话的阿英,瞿爹的笑突然又有些发僵了。他的眼睛有些发直,嘴巴也半张着,仿佛阿英的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阿英收起电话,说:王老师说明天早晨过来,她就住在半岛酒店。
半岛酒店就在小区里,是半岛花园小区的配套酒店。半岛花园就在珠江边上,一楼院子外的小区马路一过,就是珠江,风景不错。当初这儿离市中心比较远,价格不太高,瞿爹才买得起。现在,一楼带院子的二手房都卖到两万五一平了。
瞿爹叹息道:难怪她看上了这儿的房子,原来就住在这儿。
阿英微微眯起好看的眼睛,说:瞿爹,我还是那句话,您真舍不得,就别勉强自己。
瞿爹一下就显出几分为难来了。他的眼里,甚至闪起了泪水的光亮。他哑着声音说:我一回老家,就离堂客和丫头远了。
瞿爹终于没能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了下来。
您别难过了,都好几年了,您还是看开一些。阿英递过一张纸巾说,您回老家住住试试,换一下环境,兴许也很有必要呢。
我堂客那时吵着要再生一个,我好歹是个党员,不愿拖单位的后腿……你看,现在都号召二胎了,我真后悔啊。
瞿爹,过去了的事就不说了。您还是找个伴儿,就回老家找吧,生活习惯一致。
唉!不说了。这都是命。我一个人过也好,有的是工夫想念堂客和丫头,多了一个人,反而不好处理。瞿爹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阿英,我一直想说,你年纪轻轻的,得再找一个人,拖久了,非非跟新爸爸相处就不那么自然了。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气死那个负心汉!还有,阿英,无论怎样,你今后还是要再生一个伢子。
阿英红着脸笑道:瞿爹,现在的男的,不比上一代的实在重情,我带着非非过挺好的。她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说下去,说,明天,还让王老师来看房吗?
看,说好的嘛,我不拖泥带水。
三
瞿爹又是一夜没睡好。
瞿爹做出把房子租出去回老家的决定时,觉得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个大老爷们儿独自过日子,家不就在腿肚子上吗?大不了一年之后再回来。他还想像别人那样时兴一把,全国各地转转,这儿住上一阵,那儿住上一阵,过一下旅居生活呢。佛山的这套房子,别说是出租,就是卖掉,也会是迟早的事。可是事到临头,一切就变得不简单了。房子租出去后,堂客和丫头的那些照片和衣物,关在一个房间里会不会长霉?从此以后,也不能想去公墓看看就去看看了。还有,院子里的花草长得不好,王老师会不会全给换了?一年后王老师还想住,那又怎么办呢?除了这些,他脑壳里又多了一层复杂:王老师的儿子,可是为国为民牺牲的烈士呢……
嗨,问题越冒越多,瞿爹心里乱糟糟的,心脏也有些隐隐发痛——这是堂客和丫头遇难后,落下的病根。
瞿爹刷了牙洗了脸,本是想到小区外吃早餐的,但他担心王老师过来看房子,只好自己做早餐。
他夜里想过,以前的想法是,找不到合适的租客,房子也可以空着。隔壁的老肖老两口,就是坚决把房子空着,住到深圳的儿子那儿去了。可是,现在要租这房子的是王老师,他就不能按以前的想法来了。
瞿爹的早餐是煮面条,简单。锅里翻起乳白色的泡沫的时候,阿英的声音在院子外响了起来。
瞿爹慌乱起来,切葱的刀切到了指甲盖上。幸好切葱用的力很小,大指甲只切出了一条白痕。他责备自己:这把年纪了,还这么不镇定!
他出门一看,见阿英身后跟着一个清瘦白净的大妈,看样子,年纪应当小自己好几岁。这王老师,头发也跟自己的一样花白了,瞿爹不由生起几分同病相怜的心疼。不少人这个年纪都儿孙满堂,快快乐乐,头发都还黑着呢。
王老师是一个少见的打扮朴素的人。这年头,这个年纪的人都被称为中国大妈,多少带点贬义,小区里、大街上,她们不是穿得大红大绿,就是紧身束腰,再就是弄成黄头发棕头发,还文上眉毛,涂上口红,看上去就别扭。半年前有人硬给介绍一个,就是这种打扮。这王老师多好,白衣黑裤,宽宽松松,自然短发,穿得还是平底白鞋,一看就叫人舒服。只是她的笑里,始终藏着几分忧伤。这忧伤别人可能看不出来,反正他瞿爹是看出来了,或者说是相同的命运使他感觉出来了。
王老师点头一笑,说:您好。
瞿爹也慌乱地点头说:您好。又说,是王老师吧?
王老师轻轻笑道:我退休了,不是老师了,叫老王就好。
瞿爹乐呵呵地说:老王这样的称呼,只适合我老瞿,我还是叫您王老师顺口。又说,您也可以叫我瞿师傅,我做了一辈子瓷器,说是工艺师,其实也就是一个工人,或者说手艺人。
瞿爹的嘴巴突然变得利索起来,利索得没有道理,一点过渡都没有,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仿佛他突然间不再是原来的他。不过,这样乐呵呵的样子,也是瞿爹的本性,只是自从没了堂客和丫头,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了。瞿爹清楚,他此刻的乐呵呵是装出来的,装得连他自己都觉得生硬。但是为什么要装呢?他自己也不清楚。
没想到王老师的脸上也添了几分笑意,她轻声笑道:手艺人也就是艺术家呢。这样,您称我王老师,我称您瞿师傅,我们互相抬举点儿,自找一份快乐也不错。
王老师说得对,一样命运的人,彼此不多些快乐,还有哪个来给我们快乐呢?
瞿爹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开朗了,原来是他装出来的乐呵呵,使王老师脸上添了笑意。这使他想到,自己好歹还有点价值,还能让王老师多一份开心。所以,他就自己逼自己更加开朗。
瞿爹在心里说:这也是缘分呀,一个要出租房子,另一个要租房子住;一个没了老伴儿和儿子,另一个没了堂客和丫头。用年轻人的说法,这不是同在一个频道上嘛。反正,就是她了。租。只要她不嫌弃!
瞿爹正想着接下来该说什么,阿英在屋里叫起来:瞿爹,锅里的面条!
瞿爹回过神来,他顾不上客气,急忙往厨房里跑。面条不比别的东西,得赶紧捞进碗里。他捞好面条,接着是放调料,头上尴尬出一片汗来。
王老师跟进来看房子,见面条里只加了酱油和葱花,笑道:煮面条调料直接下到锅里更入味,放点肉丁或猪肝丁,就更好了。
瞿爹尴尬地笑道:我一个人吃,就不愿麻烦了。他怕王老师认为他不会做饭,不懂生活,又说,我以前下面条,比您说的还要讲究呢。
王老师好像看到他心里去了,笑道:讲究到什么程度?
瞿爹有些得意地说:我们江汉平原,自古是富饶之乡,对吃的特别讲究。就说下面条吧,有普通白面,有碱水面,有鸡蛋面,有绿豆面。不管是什么面,我们都兴加码子。
王老师也来了兴致,问:什么叫码子?肉丝肉片,或者牛肉盖浇?
瞿爹兴奋地说:对,就是你们北方说的盖浇面,但又不完全一样。他有些卖弄起来,说,盖浇面太简单,我们江汉平原的面码子,各种肉,各种鱼,各种蔬菜,二十种都有呢。嗨嗨,我都把自己的口水给说出来了。
王老师笑道:真的?还真没听说过这么丰富的面条呢!我们那儿可是专门吃面食的。
瞿爹怕王老师认为他吹牛,便求助地望向阿英。
阿英对王老师说:瞿爹说得一点不假,面食在北方是饭,当然简单,但在我们江汉平原,它就是风味小吃,所以花样多。
瞿爹听了十分开心,说:还是阿英说得好,面食在我们那儿就是风味小吃,除了面条,还有油条油饼油墩子,还有锅盔烧饼水晶糕糖食果,加起来,不少于五十种。
王老师说:哇哇,那我真要向往了!
瞿爹见王老师真的乐了,十分开心,说:等我回老家后,你可以跟阿英一起到我老家去玩,我天天带你们吃早餐,保证一个月不重样儿!
王老师笑道:街上吃一个月,我没那个习惯,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吃,现在还闹着疫情呢。
瞿爹听了,有些失望,但他马上打起精神,说:不要紧,大不了我自己做,别的不说,面、粉,还有零食,都加起来,不说三十种,二十种我还是做得出来的。
王老师说:那好,房子我就租定了。等明年春天,我去你们江汉平原走一走,那时候,那里不冷了吧?
瞿爹和阿英异口同声说:不冷不冷。
阿英又说:那个时候,紫芸英开成一大片。再晚点,油菜花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千里江汉大平原啊,真叫一个美!
王老师笑出一脸菊花,说:我一定要去看看。
王老师让阿英陪着,又去看屋外的小院子。
瞿爹想:多善解人意啊!她这是要让我自在地吃早餐呢。
四
瞿爹收拾好碗筷出来,王老师还在院子里,一副欢喜的样子。
瞿爹算是看明白了,王老师看中的正是这个院子。也是,两室两厅的房子属于小户型,却能配六十多平方米的小院,这样的好事,也只有十年前的佛山才会有。后来建的高层小区,一楼大都是架空层,即使有地面的一楼,花园也是公共的。如今,就是很多别墅,也难得有这么大的院子了。自己当初看上这套房子,考虑的正是老了的时候,既方便出行,又接地气,还可以种花种草打发日子。堂客在世的时候,还种上了一点菜呢。现在,城区已扩大了好几倍,这里也不再偏僻了。想到这里,瞿爹不禁又生出几分莫名的失落。房子是自己愿意租给王老师的,失落个什么呢?这简直没道理嘛。当然,这个时候不出租,只要私底下跟阿英说一下,也完全可以。但是瞿爹把王老师的事一听,人一看,就觉得自己不能出尔反尔了。这个时候,他甚至有些担心王老师看不中这个房子了。于是,他又向王老师说起房子的优点来。
这瞿爹,真是有些自相矛盾了。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矛盾过呢!
王老师突然问:瞿师傅,您这些花草会搬走吗?
不会,我还能千里迢迢搬到老家去?
这么说,这些花草都留给我了?
当然,如果您不嫌弃。
那我先谢谢您了。我教了一辈子生物课,就喜欢种花种草。有剪刀吗?
瞿爹赶紧找出剪刀。
王老师笑道:瞿师傅,您肯定是舍不得修剪。您看,它们都长得黄黄瘦瘦的,有些都快要死掉了,正是没有修剪的缘故。还有浇水,施肥,也都是有讲究的。说着,她的剪刀一响,一株茉莉的主杆就被剪掉了。瞿爹不由心疼地哎了一声。
王老师抬头看了看他,笑道:这花草,有时候就得大刀阔斧地剪,否则它永远也长不好。说着,她又将这株茉莉剪去了好几根枝条。
瞿爹看出王老师是种花种草的高手,但脸皮还是一抽一抽的,像是剪在了他的身上。
王老师自信地安慰道:不用半个月你再来看,它保证长得有模有样了。
瞿爹连忙说:您说得对,您尽管修剪。
王老师又说:您这里花草也不多,但差不多都是茉莉和兰花。我也喜欢这两种,但我还会增加别的花草。
瞿爹听了,笑道:您尽管增加,但是……我希望……您,尽可能保留我种的茉莉和兰花,可以吗?
王老师认真地看了瞿爹一眼,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说:这两种花草,我还会增加一点好的品种。过些日子您再来看,会有更好看的茉莉和兰花。
瞿爹放心地笑了。他的眼里,甚至充满着感激。
莉和兰,分别是堂客和丫头的名字,都是瞿爹心尖上的东西。
瞿爹一辈子与陶泥打交道,手艺十分出色,还被评为高级陶瓷工艺师,但他对花草的种植,实在懂得太少。他之所以决定回老家,正是因为这两年来,院子里的茉莉和兰花越长越差,都已经死过好几拨了。他见它们都有继续死去的势头,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现在听王老师一说,他才突然醒悟过来。这些花草虽说是自己买来栽下的,但是日常的侍弄,都是堂客和丫头。是他自己不善于种花,才使它们长得不好的。而他则以为是运气不好。他听人说过,运气不好的人,种花花死,种草草枯。所以他不想种了,想先离开佛山。
五
阿英办好了房屋出租合同,到了月底,房子就正式租给王老师了。只是无论如何,王老师坚持租金还是一千。阿英好说歹说,才折了个中,定在了八百。瞿爹有些不安,阿英劝了好半天,他才作罢。
虽然还没正式搬进来,王老师每天都要过来侍弄花草。到了瞿爹交出钥匙的时候,那些被修剪过的花草,已经生出新的芽头,长出新的枝叶,眼看着就有喜人的景象了。
瞿爹回老家的时候,阿英请同事开车送他去广州南站。上车的时候,瞿爹一步三回头,又是看他的小院,又是看王老师,又是看黑黑。直到他坐进小汽车,还透过窗子回望。
王老师挥着手喊:瞿师傅,想这个院子了,就随时回来看啊。
阿英喊:您回家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打电话啊。
瞿爹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他的眼睛被泪水搞模糊了。
黑黑不停地往前冲,但被绳子拴住了,只能急切而委屈地汪汪直叫。王老师蹲下身,不住地抚摸黑黑的头。瞿爹到底有些安慰。王老师这几天来侍弄花草,黑黑早跟她混熟了。
六
两个月后,瞿爹出现在了半岛花园。小区的门卫说:瞿爹到哪儿旅游去了?
瞿爹红着脸笑:是回老家了。
两天前,瞿爹从老家直接坐高铁去了深圳,从老邻居老肖那儿拿到了钥匙,终于租到了老肖空着的房子。这回,他要跟王老师商量一下,他会把老肖的房子粉刷一新,跟王老师换回自己的房子。他还会按王老师的要求,买来她喜欢的花草,种在两家的小院里。他想,即使王老师不同意换,那也无所谓,反正,他又天天可以守着自己的小院了。
突然回到佛山,瞿爹既没有跟王老师说,也没跟阿英说,他要给她们一个出其不意。一想到自己的这个出其不意,瞿爹就有几分暗自得意,就像一个小伢子冲着父母家人,耍着一个小小的聪明,玩着一个调皮的游戏。
瞿爹认了真,他要跟王老师学习种花种草,就当王老师的一个老学生吧。
瞿爹急切地来到他的院子,屋门关着,迎接他的只有黑黑。黑黑激动得又是汪又是哼,尾巴摇得像风车一般。可是它被绳子拴着,虽然蹿得都立了起来,但也拿绳子没有办法。几年来,黑黑从来没被绳子拴过,瞿爹这是第二回见它被绳子拴着,不由十分心疼。他想,王老师现在还拴着黑黑,难不成黑黑还要到处去找老主人?
瞿爹解开黑黑的绳子,黑黑一下就扑到了他的怀里。瞿爹抱着黑黑,眼里溢出眼泪来。
王老师呢?瞿爹问黑黑。黑黑似乎听懂了,它一连叫了三声。黑黑的声音不大,有些迟重,尾音拖得很长,带着由高到低的颤音。
瞿爹的心猛地一震,这种叫声,只有在堂客和丫头遇难后,黑黑才叫过好多天。
王老师肯定是生了病。
瞿爹的心跳骤然加速,并且突然痛了一下,像被扎了一针。
瞿爹晓得自己受到了刺激,刺着了受过伤的心。
他靠在墙上,捂住胸口,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他前天还跟阿英通过电话,阿英说王老师一切都好,让他放心。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她会告诉他的。但他哪里放得了心,他清楚老年人的病,是说犯就犯的。而王老师又是个坚强的人,有什么事,她是不会让别人为她操心的。
瞿爹掏出手机,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黑狗立起身子,用爪子抚摸他的胸口。他一边按住黑黑的爪子,一边冲电话里说:黑黑,您在哪儿啊?
电话里响起王老师虚弱的声音:瞿师傅……黑黑?黑黑在家里呢。
瞿爹苍白的脸突然变红了,他笨拙地说:哦哦哦,王老师,我糊涂了,我不是问黑黑,我是问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