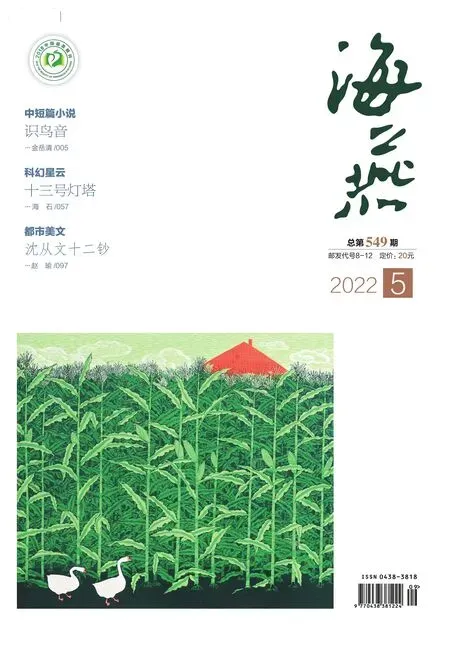借猫记
文 于永铎

有一年冬天,连续多日,飞雪撵着西伯利亚寒流从家属区的上空倾泻下来。人们就敲着脑袋说,好冷的天,把这里面都冻结实了。那年,家属区里发生了许多怪事,事后想一想,许多怪事中就属永德家发生的事最怪。这天晚上,永德带着老婆孩子回来,打开家门的刹那间,一只大老鼠突然窜出来,先一步钻了进去。永德愣怔了一下,抬腿朝老鼠踢去,老鼠钻进了沙发底下。
永德家顿时就乱了套。
永德媳妇将女儿放到床上,也顾不得换上居家衣服,直接就撸袖子参战。两口子一前一后,开始了地毯式的捕鼠行动。沙发被永德猛拽出一截儿,背面连个老鼠影子都没有。永德又趴在地板上朝沙发底下看,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只老鼠。他找来拖把,在沙发下乱捅,就听见吱吱几声乱叫。永德喊:“戳着了!戳着了!”老鼠窜出来,朝永德媳妇那边跑。永德急问:“老鼠呢?”媳妇说:“跑了。”永德问:“你怎么不打呀?”媳妇说:“我怕。”永德跺了下脚,擎着拖把,警惕地盯着每一处可疑的地方。卧室里传来女儿的哭声,永德脚下安了马达一般,一阵风似的冲进卧室。女儿指着枕头哭叫:“呜!呜!呜!”永德紧盯着枕头,举起了拖把,他朝媳妇努了下嘴,示意掀开枕头。媳妇慌忙抱起孩子,不但不去掀枕头,反倒一步步往后退。永德挑起枕头,挥着拖把狠狠砸了下去。老鼠又窜到了客厅,又从客厅窜到卧室。折腾了半夜,家里就像被打劫过一样乱。
第二天一早,永德刚在楼道里冒出头,邻居于姐便询问夜里发生了什么事。筒子楼不隔音,一家有事,别人家想不知道都难。永德说:“家里进了一只老鼠。”邻居于姐说:“今年冬天实在是太冷了,从没有这么冷过。”于姐的丈夫说:“今年冬天实在是太怪了,从来没有这么怪过。”他说童牛岭矿的徐云皓家刚会说话的儿子竟然说他不是他们家的孩子;李家沟矿的杨晓良更是倒霉透顶,一辆重型卡车冲出公路,三拐两拐,偏偏撞向了孤零零的杨家。还有几个邻居也围过来,跟着叹气,都说今年冬天真是怪。见永德要走,邻居们又提起灭鼠的话题。张婶让永德赶紧到居民委去领灭鼠药,说最近下来的灭鼠药绝对安全可靠。听姐们儿说此药是专门根据老鼠的口味设计的,对老鼠来说,绝对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张婶这么一说,永德就动心了,送走了媳妇后,永德赶紧去了趟居民委,拿回了两包灭鼠药。永德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放了药,尤其是在沙发下面和厨房等重点地儿都放了药。都整利索了,永德坐在沙发上,猜想老鼠此时藏在哪里,猜想老鼠是不是闻到了药的香味。永德忍不住掏出一把鼠药,放在鼻尖儿闻,就闻到了熟悉的牛油火锅的味道。永德伸出舌头,想舔一舔,尝一尝。猛地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
晚上,永德媳妇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她宁愿在外面冻死也不一个人进家。永德赶回来时,心疼得直哆嗦,他紧紧地搂住老婆孩子,拥着她们进了家。永德担心媳妇害怕,就站在她的前面,仔细地搜索着老鼠尸体。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蹲在沙发前,伸手摸了摸,灭鼠药还在,他贴着墙缝朝柜角里面看,灭鼠药似乎有被吃的痕迹。永德又到卧室里查看,床底有只黑影子,永德连忙拿来拖把,将拖把小心地伸进床底,猛地扫打了一下,黑影子飞出床底。原来是一只拖鞋。媳妇问:“老鼠死了吗?”永德说:“没有。”媳妇就进了卧室,搂着孩子坐在床上。
夜里,永德梦见了老鼠,老鼠朝他吱吱乱叫,还像人一样站起来用前爪比画着。这个梦还没有做完,永德就被媳妇推醒了。媳妇轻声说:“你听。”永德屏住呼吸,就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声音。像是跑动的声音。永德的脑子一下子就大了。老鼠果然没死。永德就想起了梦里朝他挑衅的老鼠,心里一阵阵发急。
两天后,老鼠依然在家里跑来跑去,永德坚信灭鼠药不好使,灭鼠药也确实是老鼠的美味大餐,几乎都被吃光了。邻居王师傅给永德送来了两个老鼠夹子,这是他花了一天时间焊制的。王师傅说如果这两个铁夹子收拾不了老鼠,他就把脑袋砍下来让永德当球踢。根据王师傅的建议,永德买了一斤上好的羊肉,切成小肉丁,拴在灭鼠夹的销子上。永德试了试,一旦销子上的羊肉被触发,销子就会启动,翻板便会携风雷之势砸向座板。永德用小棍捅了一下,那一声巨响惊得永德的心都颤了几下。永德媳妇感激王师傅雪中送炭,也没跟永德商量,竟然拿出一瓶藏了好几年的酒送给王师傅。王师傅烫了手似的惊呼:
“这合适吗?”
“谁喝不是喝?”永德冷着脸子说。
第二天早晨,销子上的羊肉丁不见了,灭鼠夹没有被触发。也就是说,老鼠居然从虎口里夺了美味。永德重新拴了羊肉丁,将肉丁拴得更紧一些。没多久,羊肉丁又被吃掉了。可恼的是,灭鼠夹子的旁边还有几粒老鼠屎。这几粒老鼠屎就像一根刺,突然扎进了永德的肉里。有了一粒就有两粒,没多久,墙角旮旯都发现了老鼠屎。就好像有无数根刺刺进永德肉里。永德媳妇看都不想看一眼,更别说让她去收拾了。只要在家,她总是坐在床上,搂着女儿一动不动。永德把灭鼠夹收起来,一把丢到楼下。
王师傅有些不甘心,还要再做两个更大一些的夹子。王师傅发狠地说如果再不好使,他就真的要把脑袋切下来让永德当球踢。永德拒绝了。王师傅查看了永德家,指责永德没有按照要求布置灭鼠夹。他要求永德将夹子伪装起来重新放置,再在前后设置几个小小的障碍。他保证万无一失。永德媳妇显然对王师傅失去了信任,她连连使着眼色,示意永德赶紧把这个醉鬼打发走。永德媳妇平时并不这样毛躁,甚至对邻里们很有耐心,只因这只老鼠搞得她失去了方寸。

插图:包 蕊
永德媳妇感到回家是一件非常沉重的选择,甚至想到了离家出走,把家腾给老鼠。单位里,永德媳妇讲起家里进了可恨的老鼠,同事老何忽然想起一件惨案,提醒说,1972年的时候,矿区医院里就发生过老鼠祸害人的事。有一天,妇产科接生了一个婴儿,不巧的是,婴儿的母亲需要转到别的科室治疗疾病。夜里,照顾婴儿的护士麻痹大意,婴儿的鼻子就让老鼠给咬下吃掉了。惨案发生后,婴儿父母大怒,要矿区医院负责赔偿,矿区医院当然没办法赔出婴儿的鼻子,这家人就把婴儿扔给医院。同事老何说:“婴儿在矿区医院里一天天长大,除了没有鼻子,其他的部位发育得都很好。18岁时,就被医院招工留下,也是坏事变了好事。”老何说到这里,永德媳妇突然就掉下了眼泪,她说她的心就像被车轮碾压了一般。
“可惜了一个孩子了。”老何说。
永德媳妇捂着脸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同事们面前失态。她真怕自己的孩子被老鼠祸害了。
永德安慰着媳妇,轻轻拍着媳妇的后背,捧着媳妇的脸,说宁愿让老鼠咬掉自己的鼻子也不能让它祸害了孩子。永德媳妇眉头舒展了,看着表情滑稽的永德,不禁破涕为笑。想了想,突然又说:“那也不行!”说完,便紧紧地抱住永德。为了防备老鼠夜里偷袭,永德把床的四周都粘上了胶带纸,只要老鼠踩上,准能被胶带粘住。有了这层保护,一家人还能睡上一觉。只是每到夜深的时候,永德都会被老鼠吵醒。要么听到“扑通扑通”响,要么听到“哒哒”响。前几次,永德还能开灯捕捉,后来,他实在困乏无力,就使劲儿拍一下床沿,每拍一下,声音就会突然消失。
邻居张婶说她有一个好办法,只是不知能否行得通。永德朝张婶鞠躬,永德恳请张婶知无不言。
“永德你得借只猫去。”
“借猫?”
“永德你得让猫替你去捉老鼠。”
张婶一句话点醒了永德,是啊,捕捉老鼠本应就是猫干的事。张婶更是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她伸手朝楼上点了点,永德恍然大悟,顿时就应验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4楼刘芹家养了一只猫,每到春天的夜晚,那猫叫得那个瘆,就像一个没妈的婴儿,缠缠绵绵,钻入心底。叫得狠了,周边就聚起各路货色,二重唱变成多重唱。一群发情的猫能把深夜顶上的盖子掀开。人们都厌烦刘芹家的猫,虽然不说,每个人心里头都恨不能立即阉割了它。
永德央求说:“张婶,你帮我去借猫吧。”
张婶面有为难之色,春天时,她曾和刘芹大吵过一架,彼此都骂过一些难听的话。让她去借猫,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张婶不愿意去见刘芹,永德犯了难。他和刘芹只是点头之交。刚搬到家属楼来的时候,听说刘芹和这个屋里的上一家有过一段纠葛。永德和媳妇都不是喜欢听闲话的人,更没有随着别人的调子起舞。虽然如此,永德和刘芹却有些疏远,每次见到刘芹,永德都不由自主地垂下目光,仿佛上一家附体了一般。即便如此,为了家里的安宁,永德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敲开刘芹家的门。刘芹的丈夫吃惊地看着门外的永德。永德解释说他是来求援的。刘芹从屋里头闪了出来,见是永德,立即嚷着:
“大诗人,快请进,快请进。”
刘芹的丈夫将永德放了进去。屋里顿时就像烧开了水似的哗哗直响。刘芹说话的腔调昂扬向上,刘芹的丈夫则截然相反,他紧闭着嘴,与永德保持着距离。永德看出他们两口子之间有些不自然,甚至还有些敌意,永德猜他们刚刚有过争执。
“大诗人,你别理他。”
“我是来求你们一件事的。”
刘芹递给永德一个苹果,永德瞄了一眼刘芹的丈夫,手已经伸出一半又抽了回来。刘芹俯身将苹果塞到永德的手里。永德就把家中进了老鼠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我想借你们家的猫。”
刘芹的丈夫突然放松了,他拍了下大腿,笑着说:
“我还以为啥了不得的事。”刘芹的丈夫从卧室里抱来了一只猫。永德一眼就怔住了。这是一只漂亮的花猫,那眼睛,清纯得就像少女的眼睛。永德的第一感觉确实如此,他甚至下意识地瞄了一眼刘芹的眼睛。刘芹的丈夫将猫递过来说:
“快抱走吧。”
“不行!”刘芹一把抢过猫,紧紧搂在怀里,只露出一张小小的猫脸。刘芹抚摸着猫的后背,轻轻地抬着猫爪,朝永德摆着说:
“大米粒,知道吗?他是矿区里有名的大诗人。”
那猫看着永德,朝永德伸了下爪子,仿佛真的和他打着招呼。永德注意到,刘芹的脸上写满了“得意”两个字。“大米粒属于名贵的金吉拉种。”刘芹说以前养的波斯猫和安哥拉猫都是无情无义的家伙,几乎每年春天都会弃她而去。唯有大米粒经受住了考验。无论野猫叫得有多委婉,大米粒都会强忍着不走。有时,尾巴撅得像根旗,在屋里转来转去,一边转还一边叫。每听它叫一次,刘芹就哆嗦一阵子,她说只有她听得懂大米粒的心声。刘芹说大米粒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这一句,就算把话堵死了。永德有些不好意思,真后悔自己冒冒失失地来借猫。他还不能站起来就走,那样就显得太没风度了。永德盯着大米粒,嘿嘿笑着,还朝它摆着手势。大米粒也朝永德伸着爪子。刘芹的脸贴在猫身上蹭来蹭去,露出很陶醉的面容。刘芹的丈夫有些不耐烦,伸手去夺大米粒,刘芹挺直了腰,身子一扭,朝丈夫尖叫了一声。刘芹的丈夫顿时就收回了手。见到这个场面,永德就是脸皮再厚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婶见永德下来,就跟着进了永德家。张婶问借没借到猫。永德摇摇头。张婶撇了撇嘴,说一只破猫有什么了不得的。永德心里头也有些郁闷,就没有回应,没有回应就是回应了。张婶的嘴撇得更大了,冷笑着说她知道谁有能耐把猫借出来。张婶夸张地朝楼上指,说6楼的魏科长有面子。张婶见永德没有顺着说,就打住了。
永德很沮丧,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除非把家搬空了才能捉住老鼠,把家具都搬出去?想一想就让人头痛。媳妇给他打来电话,说不打算回家了。问她住在哪里,媳妇说准备带孩子住快捷酒店。永德听得出是气话,却也想不出好听的话安抚她。沉默了一会儿,媳妇哭了,说自己命苦,如果亲妈还活着,怎么的也能回娘家住几天。说到这儿,又提起了永德父母。永德就怕她把水火引到自己这边,便连忙发誓,一定能把老鼠消灭掉。
永德还发誓一辈子爱她。
永德请了一天的假,他打算把家具全都搬到室外。该死的老鼠,这回可是死定了。永德还找了一个带盖子的铁桶,打算将老鼠扔进去,拿到外面活活冻死。永德还想到一旦没冻死,就在桶下点一把火,将老鼠活活烤死。永德还准备了一个合手的铲子,只要发现老鼠,定能将其拍成肉饼。永德把椅子搬出去的时候,楼道里站满了邻居。他们都很同情永德,都争着来搭把手帮永德往外搬东西。王师傅更是激动得不能克制,他骂天骂地骂老鼠,浑厚的骂声在人群中穿梭,在半空中飘荡。人们都皱着眉。刘芹的丈夫在楼梯口那边看了一会儿,又匆匆地上去了。永德和王师傅将饭桌抬出来的时候,刘芹一扭一扭地来了,怀里抱着大米粒。大米粒的头顶上系了根漂亮的头绳。人们的目光都聚在刘芹的身上,不但是看她怀里的猫,还看她一扭一扭的身姿。
“大诗人,给你猫。”
“猫?”
“你可小心点,大米粒可是从没离开过家。”
“这是真的借给我吗?”永德看着刘芹,看着刘芹怀里的大米粒。王师傅捅了他一下,努了下嘴,永德慌忙说:
“放心吧,我会看好大米粒的。”
“放心?有几个让人放心的?”刘芹嘟囔了一句,声音很小,永德却听了个清清楚楚。他的脸竟然有些发烧。刘芹抱着猫进了屋,站在门口,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着屋子。永德连忙将沙发上的东西挪开,划拉出一块坐的地方。永德请刘芹坐下。刘芹抚摸着大米粒的身子,轻声说:
“大米粒,看在他家有个小孩子的份儿上,咱帮他把老鼠捉了吧。”刘芹将猫放在了沙发上,一步一回头地走了。王师傅带着永德又将家具搬了回来。大米粒趴在沙发上,眼中闪闪发光,似乎刚刚哭过似的。永德心里不忍,去厨房接了点水放在沙发上,就像给客人沏了一杯茶。又去厨房把昨晚没吃完的一条鱼夹出来,放在碟子里给大米粒吃。刘芹恰好进来,尖叫一声,将碟子拨到一边。刘芹狠狠地瞪着永德。
“你想干什么?”
“怎么了?”
“别乱给吃的,猫会生病的。”刘芹将一只闪着光泽的猫食碗放在沙发上,又掏出一包猫粮摊放到碗里。王师傅顶了一句:“人能吃,猫不能吃?”刘芹给大米粒系了一条鲜艳的带着斑点的围脖。大米粒喵了一声,脑袋蹭着刘芹的手,然后才低头开吃。永德朝王师傅使了个眼色,耸了耸肩膀,两人出去把椅子拎了回来。
邻居们走了,王师傅也告辞回去。刘芹抱着大米粒,四下里转悠着,她的目光一直朝卧室瞄着,似乎卧室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她。永德突然想到了刚搬来的时候听到的绯闻,心里一阵紧张,仿佛那一段与自己有关。永德只想赶紧躲开,躲得越远越好。刘芹不走他也不好张口往外撵,永德就只能在家里陪着。永德有一搭无一搭地收拾屋子,刻意地与刘芹保持着距离。刘芹问永德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永德说大概在17岁的时候。刘芹问好端端地怎么就想起了写诗。永德说荷尔蒙太旺盛了就给女同学写诗。刘芹抚摸着大米粒,盯着永德的眼睛说:
“你女同学真有福气。”
“你认为那是福气吗?”
“我17岁的时候就没有给我写诗的男生。”
永德笑了笑,感觉有根绳子在牵着自己,感觉自己像头驴。刘芹也笑了笑。怀里的大米粒喵了一声,永德恍惚听到了一声冷笑。刘芹说17岁的时候,无论认识和不认识,男人都是盯着她看,那时,男人给她的印象就是随时都能把她吃了。那时,刘芹怕男人。后来就不怕了。再后来,男人女人都不怕了。刘芹将大米粒捧起来,贴着自己的脸颊说现在就怕大米粒跑了。
当天晚上,永德一家都要睡了,刘芹才不得不起身告辞。临走时,嘱咐大米粒要听话,嘱咐大米粒千万别乱跑。刘芹前脚刚走,永德媳妇就扔了脸子,狠狠地啐了一口。如果不是永德拼命打手势,媳妇都能骂出声来。永德紧紧搂着媳妇,摩挲着她的后背,请她息怒。媳妇低声告诫永德,以后少和这样的女人接触。永德慌忙点头,又给女儿把了尿,送到媳妇身边。
永德刚刚睡着了,就被大米粒吵醒了。开始,是隐隐约约地叫,后来,是轻声叫,永德以为大米粒发现了老鼠,就屏住呼吸听。大米粒一声接着一声,一浪接着一浪,叫声越来越急,叫声凄惨无比。永德起身到客厅观望,只见大米粒在餐桌上团团转。永德问:“老鼠呢?”大米粒喵叫了一声,听起来受尽了委屈。永德走到跟前,大米粒突然抵住了他的手,顺势钻进了他的怀里。永德抱起大米粒,像抱着孩子一样轻轻颠着。大米粒还是叫,声音低缓下来,仿佛在诉说着委屈。永德坐在沙发上,轻轻摩挲着大米粒,手感光滑柔软,一把一把,舍不得停下。卧室里有了声响,媳妇似乎摔了什么东西,永德慌忙将客厅的灯关掉,抱着大米粒摸索着在每个角落里转,摁着大米粒的脑袋,让它嗅,让它看。永德低声吼着:
“臭老鼠,你敢出来吗?你出来呀!”
大米粒一声一声喵叫,仿佛在向老鼠示威,又仿佛在哭诉委屈。门铃响了,响了又响。永德开了门,门口站着刘芹。刘芹脑袋和肩膀上都是雪。刘芹可怜巴巴地说:
“大米粒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大米粒从永德的怀里闪电般地跳到刘芹的怀里,就这么一用力的时候,永德就觉得胳膊被挠得火烧火燎。刘芹搂过大米粒,脸贴着脸,脑袋顶着脑袋。刘芹奶声奶气地哼哼了几声,大米粒也奶声奶气地哼哼了几声。
“大诗人,明天我再给你送来。”
永德一言不发,撵人似的目送刘芹回家。刚到楼道口,一眼看到黑影地里站着刘芹的丈夫。刘芹的丈夫说:“刘芹,你真能作。”刘芹嚷嚷着,让丈夫少管闲事。永德转身回家,也不开灯,也不回卧室。他坐在沙发上,怒视着每一寸黑暗,感觉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挑衅地看着他。永德将灯打开,到厨房抄起一把菜刀,拖开桌子就劈,拽开沙发就砍。直到黑夜被他砍得乱七八糟,直到窗外浮现出道道凌乱的白印,永德才瘫倒在沙发上。
早上,永德在楼道口遇见了刘芹的丈夫,刘芹的丈夫气哼哼地说:“大诗人,你等着,我这就给你借只管用的猫。”永德苦笑了一声,想起了娇贵的大米粒,不禁摇了摇头。永德忽然怔住了,刘芹丈夫的手背上有几条血痕,脖子上也有几条,像蚯蚓一样。
刘芹的丈夫是个说到做到的男人,这一点,出乎了永德的意料。本来以为只是一句随口说的话,没想到,天还没黑时,刘芹的丈夫就敲开了永德的家门。他的身上披了一层雪,带着一团冷风进来。刘芹的丈夫从编织袋里放出了一只大肥猫。永德差一点没坐在地上。这是一只他想都想不出来的巨大的猫,从头至尾,起码能有半米长。脑袋像只足球那么大,看着不像是猫,倒像是一只小老虎。刘芹的丈夫甩着胳膊,揉着胳膊,又摘下帽子,脑袋上冒着腾腾热气。永德问这是从哪儿弄来的猫。刘芹的丈夫嘻嘻笑着,撸起了袖子,胳膊上露出几条血痕,他又慌忙褪下袖子。永德假装没看见他胳膊上的挠伤,他只看着巨猫。刘芹的丈夫说:“这是从瓦房店老家借来的。”永德算了算,瓦房店到这里少说有100公里的路程。看着他冒着蒸气的头发,永德心里暖暖的。
“城里的猫都是大小姐,中看不中用的破玩意儿。”
“猫小姐。”
“能捉耗子的还得是俺农村老家的猫。”
“这只猫今晚就在我家?”
“那当然。”
送走了刘芹的丈夫,永德和媳妇盯着巨猫,竟然有些慌乱。担心夜里叫起来声震四邻。永德拍着沙发,招引巨猫到沙发上歇着。巨猫没有反应。永德切了根火腿肠,送到巨猫的脚下。巨猫的眼睛眯缝着,蹲坐在地板上,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永德媳妇扯了扯永德,低声问:“这是生气了吗?”永德说:“放心吧。”两人关了灯,走回卧室,没等关上卧室的门,巨猫跟了进来。永德吓了一跳。永德媳妇慌忙爬上床,紧紧搂着孩子。巨猫跳到椅子上,蹲坐着,尾巴垂下。永德注意到,它的眼睛一直眯缝着。
永德上了床,心里一阵忐忑,觉得太糟糕太荒唐。如此大的猫一旦失去理智,那和老虎有什么区别?永德忽然轻轻打了声呼哨,巨猫睁开眼睛,眼珠子像玻璃球一样闪闪发光。永德慌忙关了灯,屋里一片漆黑,那对玻璃球依然闪光。永德媳妇推了永德一把,小声说:
“我害怕。”
“怕什么呢?”
“我就是怕。”
永德朝椅子上看了一眼,巨猫的影子比夜还黑,玻璃球比月光还要明亮。永德也觉得心里头怦怦乱跳。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挤了进来,把如水般的夜切成了两半。
“永德,你这辈子没骗过我吧?”“瞎说什么废话?”
“永德,你陪我说说话吧。”
“说什么呢?”
“猫呢?”
永德猛坐了起来,对面椅子空空如也。不用开灯就知道巨猫没了。永德朝客厅指了指,媳妇再也不敢露头了。永德想下去看看情况,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多大的一只猫啊,简直就是一只小老虎。一旦发了威风,一口就能咬断永德的喉咙。永德猜这只巨猫一定是找吃的去了,从瓦房店到这里来,多远的路,多冷的天,巨猫能不饿吗?永德想接一碗水给它,还是下不了决心,他担心突然和巨猫撞个满怀,那样,吓也吓死了。永德提醒自己,天亮后一定要去买一袋猫粮。无论这只猫捉没捉到老鼠,一定要买一袋上好的猫粮。然后,让刘芹的丈夫赶紧把它抱走。永德觉得这两天就像是上演了一场荒唐的戏。他、老鼠和猫互为戏中的角色。
又是一个清晨,永德一眼就看到了椅子上蹲坐着的巨猫。巨猫的眼睛瞪得像一对玻璃球。永德坐了起来,巨猫也伸直了脖子。永德推了推媳妇。媳妇的脑袋埋在被子里,使劲儿朝被子里缩。女儿被挤醒了,发出一阵啼哭。媳妇伸出一只胳膊,拍哄着女儿。永德掀开被子一角,媳妇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永德,我梦见我妈了。”
“别瞎琢磨。”
“永德,我妈一直看着我。”
永德看了一眼巨猫,巨猫像座雕像一样。永德说:“起床吧。”媳妇背向一边快速穿衣。永德下了床,朝巨猫拱拱手,算是道了早安。巨猫表情还是那么冷峻。永德收拾了卫生后打算出去买早点,顺便买点食物给猫吃。他故意轻松地问:
“嗨,猫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巨猫朝他喵了一声。永德没在意,巨猫又喵了一声。永德注意到是在叫他,一眼就看见它身边有个带血的骨头,仔细看,是老鼠的脑袋和一条大尾巴。
“老鼠!老鼠!”
“在哪儿?”
“让猫给吃了。”
媳妇拥过来,也看见了老鼠血淋淋的脑袋和尾巴,她一把抱住永德,扎在永德的怀里。永德的眼里涌出了一层泪水。
永德和媳妇商量着买些礼物送给刘芹的丈夫,感谢人家不远百里借来的这只管用的猫。永德临出门的时候,还朝巨猫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朝巨猫伸出大拇哥。永德媳妇也不怕了,还摸了巨猫的脑袋和脊背。巨猫一动不动让她摸。永德媳妇一阵激动,说自己都有些舍不得这只懂事的猫了。
永德急匆匆地出门了,不是急着买早点,是急着去超市里买火腿肠,他想犒劳巨猫。下了楼,却见一群人围在楼道口看热闹。如果不是听到刘芹尖锐的叫骂声,永德根本就想不到是他们两口子发生了争执。刘芹抱着大米粒,一只手展开,像眼镜蛇一样攻击她的丈夫。刘芹的丈夫一手捂着脸,一手朝刘芹还击。永德朝看热闹的王师傅喊了一嗓子,两个人一人扛一个,将他们分开了。刘芹的丈夫满脸是血。
“这是怎么了?”永德问。
“你问他去。”刘芹说。
“泼妇!泼妇!”刘芹的丈夫骂。
两人又要厮打,永德和王师傅又奋力扛住了,永德媳妇也跑下来,拦住了刘芹。永德顶着刘芹的肩膀说:
“别冲动,我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老鼠被猫逮住了,这只猫太伟大了,把老鼠吃得只剩下一条尾巴和脑袋。”邻居们一阵欢呼。刘芹的丈夫说:“逮住了就好。”刘芹啐了一口。永德拽住了刘芹的丈夫,扯着他往楼上走,一边走一边说:“你快去看看你的猫吧,可立了大功!”刘芹的丈夫态度软化,跟着往楼上走。
永德说:“谢谢你,还要谢谢这只猫的主人。”刘芹追上来说:“大诗人,你是得谢谢,谢谢那个狐狸精。”刘芹的丈夫扭头骂:“泼妇!泼妇!”刘芹骂:“狐狸精!狐狸精!”两人又厮打在一起。永德夫妻和王师傅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分开,永德扯着刘芹的丈夫往楼上走,苦苦地劝他不要激动。永德媳妇在身后护着,还叨叨了一些感谢的话。永德要媳妇拿500元钱给刘芹的丈夫,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钱送给猫的主人。
“大诗人,你这就外道了。”
“大诗人,你以为他有多好心?”刘芹喊,“他是以借猫的引子去见狐狸精了。”
三个人进了屋,永德请刘芹的丈夫去看老鼠的尾巴和脑袋,奇怪,椅子上什么都没有,隐隐约约有一点血渍。永德下意识地朝床上看一眼,女儿好好地坐在床上,仰着脸看着他们。永德转身在屋里找,连床底都看了。
“猫呢?”
“猫呢?”
永德冲出家门,朝楼下喊:“谁看见猫了?”刘芹大声嚷嚷着:“活该,狐狸精!”刘芹的丈夫冲出来,朝着楼下骂:“泼妇!”说完朝楼下冲去,永德使劲儿追撵,连喊着:“兄弟,你可别冲动!”刘芹的丈夫冲到楼下,他并没有冲向媳妇,他直接冲出了人群。永德喊:“你去哪儿?”刘芹的丈夫头也不回地说:“找猫去。”这话突然就凝固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从家属区上空呼啸着掠过,时间就被冻成了几截儿,棍子一样戳在那里。
若干年后,永德又回到家属区,向老人们打听着刘芹,老人们说刘芹早就搬走了。永德又打听刘芹的丈夫,老人们说始终也没见到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