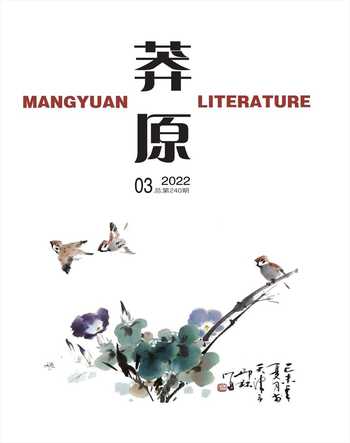家乡散记
秦学书
老虎山
老虎山生在大别山和桐柏山的交界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谁也说不清楚。我从小看到大,也没看出一点老虎的眉目。父亲读过两年私塾,他告诉我,山也像人,得有名字。有名字,山就能活起来。
老虎山海拔三百多米,重重叠叠,逶迤绵延,像一幅水墨画,平淡恬静。山里有一条羊肠一样的弯曲小道,联系着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山里人少,也走不远,有这条道就够了。小道有时从河床的乱石间蹦蹦跳跳地过去,有时就像一条草绳弯弯曲曲从山脊梁牵到山沟里。从王洼进老虎山,起初只是浅山,起伏不大。但慢慢走着,由浅入深,猛回头,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高了。
老虎山的主峰,有座娘娘庙,建在山顶南侧,有的地方石牙作路,荆木横生;有的地方路就悬在山崖边沿。夏日,山顶常常被云裹着,风尖尖地在山谷间吹着哨子,置身其中,让人胆战心惊。老虎山有豹子和狼,我记事时,就常听大人说牲畜被豺狼叼走,还咬伤过谁家的孩子。娘娘庙就三间不起眼的石砌瓦房,却保佑着一方百姓。每逢庙会,十里八村的人都前去上香求福。到了旱季,几十天不下一滴雨,田地冒烟,庄稼能点着火,人们也会去娘娘庙祈雨,很灵验,往往雨马上就来了。大家调侃说:这是杨八姐尿的——北宋末年,老虎山曾是宋金作战的前沿,杨八姐曾在此挂帅出征,至今还残留着石砌寨墙。
老虎山属于我国南北过渡带,四季并不分明。春天来了,绿色已经漫过山野,冬天的料峭寒意却迟迟不退,有些树还吊着冰挂;冬天到了,山涧里叮叮咚咚的溪水依然飘着热气,指抔菊争芳斗艳,乌桕树和枫树的叶子红红的就像火焰。老虎山的颜色在季节的拉扯中变幻,夏季凉爽,冬天暖和,四季有花,五彩缤纷,气候也像人一样,平和可亲。
我的家乡老湾就在老虎山脚下,坐北朝南。山是它的依靠,也是山里人祖祖辈辈的依靠。山里盛产铁,靠山吃山,我家祖上就靠打铁为生。我父亲是个文弱书生,但三叔却是有名的铁匠。我看着三叔打铁长大。他身体消瘦,却很有臂力,疙疙瘩瘩的肌肉,大锤一挥,叮叮当当的锤声,铁屑像火花一样飞溅——这时就开始春耕了,然后就开始开镰割麦了,接着就开始修房架屋了——老虎山于是也兴奋起来。
三叔不识字,但能讲勾践卧薪尝胆和荆轲刺秦的故事。从三叔嘴里,好像铁匠铺与勾践、荆轲多少有些联系。大概与山里民风彪悍有关,我们这里就出过好几个开国将军。
葫芦堰
葫芦堰坐落在老虎山的余脉与湾东岗坡之间,不长,也不雄伟,却一望无际。小时候没有江河湖海的概念,葫芦堰就是我心中的湖和海。
传说葫芦堰是孙叔敖留下的遗产,历史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坝的西侧是溢洪的出口,条石已经被流水剥落成老人的牙床。葫芦堰连着方圆几十里大山,没雨的时候,山沟里流水潺潺,从没干过。堰两侧的山坡生长着茂密的果园,一到春天,桃花似锦,李花如雪;坝下一望无际的农田,夏季翻着麦浪,秋季翻着稻浪——葫芦堰给十里八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特产。
葫芦堰坝里口长着一排历尽沧桑的老杨树,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但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层层老皮蜕去,又生出层层新皮,老干都空枯了,新干却旁生左出,根系连着根系,就像给堰坝生了一道挡水墙。老杨树趴在水面上,湾里人往往踩着它的身子往水中间去找乐,人们插秧累了,也会坐在杨树身上,脚泡在堰里,吸着烟,调侃几句笑话,或讲一些与老杨树有关无关的故事。
在城市住久了,葫芦堰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儿时记忆里,葫芦堰就像个平静的孩子,一望无际的水面像蓝色玻璃,周围的山色草树、日月白云,都真切切地映在水中。人们路过这里,总会停下来,掬几抔水洗洗脸,喝一口。水面起了微风,葫芦堰波光粼粼,像脸上的笑纹。山洪暴发,山山岭岭的水都夺路而下,冲向葫芦堰,卷起汹涌的波涛,堆起排排巨浪。这个时候,堰里的鱼虾都一群群溯水而上,好像要争相投向老虎山的怀抱。葫芦堰的里口是浅滩,生产队种了莲藕和芦苇。夏天,东边莲花红了,西边的芦苇正绿;冬日,西边的芦花白了,东边的莲藕正肥。大雁、野鸭和一些不知名的水鸟也来葫芦堰安家,像是赶一场约会,把葫芦堰的水面都布满了。
我是喝着葫芦堰的水长大的。母亲说,你命硬。我知道母亲说的啥。五岁时,爷爷就开始教我凫水,先是在门口的塘凼子让大人带着,似会不会时,就往葫芦堰跑。哪知道一钻到堰里就沉下去了。但葫芦堰保佑我,瞎碰乱撞间,竟扑进在老杨树边游水的表兄怀里,得救了。妈妈买了一叠纸钱,把我牵到老杨树旁,一边烧纸,一边拈着我的耳朵,念念有词为我招魂。妈妈是在感谢葫芦堰,也祈愿葫芦堰继续保佑我。
家乡的雾和云
云是雾生的,雾是山生的。云脚低,就是雾脚低。起雾了,老虎山,葫芦堰和它周边的乡湾都笼罩在雾中,几竿子远就看不到人。周遭湿漉漉的,树木和各种植物的叶子都沾满了水。走在其间,你会听到水滴打叶的脆响,裤脚,鞋面全湿了,头发上也全是水。
有雾的天,炊烟升不上去,只能在屋顶上徘徊游荡。家家户户做饭飘出的蒿草味,墙角的霉菌味,牛粪味都夹杂在雾中。
太阳慢慢爬到后山,雾也悄悄收了。山那边吹来了时有时无的风,一望无际的天空透亮清澈。除了耀眼的太阳,再就是在山腰山顶上移动的流云。云舒缓轻盈地向上飘,三五成群地组成一个个军阵,像当年二爷带着几个本家参加红军走出了山外。
老家不缺水,因为有葫芦堰,有老虎山中几条长年不断流的沟涧。但偶遇大旱,或连日淫雨,爷爷就瞪着一双干涩的眼睛朝老虎山望。“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爷爷总希望天边的云脚随他的心意。
雨云和旱云也只有爷爷分辨得清。乌云铺满整个天空,连筛眼大的空隙也找不到,天地都压抑着,风扯着闪电,响起咔咔嚓嚓的炸雷,追逐着撒野,这时就会大雨倾盆。这种雨来得急走得也快。雨要下得密实,还是那些灰云。它不张扬,风也平静。这种雨有定性,不急不缓,连日不开。爷爷说这些时,旱烟袋忽明忽灭。
山是雾的家乡,也是云的家乡。头天有雨,隔夜放晴,家乡总是沉浸在曼妙的云海中。清晨,太阳刚刚探出头来,金光早已漫上山顶。云被太阳镶上金红透亮的花边。眨眼工夫,太阳就像浑圆的火球钻入云端,把金灿灿的花絮漫无边际地平铺在它底下,云的游丝残片就像稻草人在花絮上游走。春天的云是灰蒙蒙的,总想滴水;夏天的云是凉丝丝的,看一眼就让人感到浑身清爽;秋冬的云都穿上了色彩斑斓的花衣,这时,云全憑自己的爱好装扮,像长在深海里的珊瑚玛瑙,像被人推着赶着的金山银山,像在原野上狂奔的苍狗。你觉得它像什么它就是什么。
从老虎山里长出的云从来都是自由闲适的。
老 宅
我家老宅坐落在老虎山下的一片台地上。后面有山,左右是河,在湾前交汇,往南不远是葫芦堰——很有些前青龙,后白虎,左朱雀,右玄武的气象。老宅压在老湾的中轴线上,应是龙脉所在。明三暗五,土坯叠墙,杉柱松梁,石鼓门礅,条石廊沿……可见祖上给后人留下了一片不错的房产。
爷爷弟兄四个,大爷住最里的正屋,三进院是二爷的;再往南,左右各延伸一个院落,也明三暗五,东边住三爷,西边住我爷。要说,三爷和我家的宅子都南向开门好,但在兵匪成灾的年代,门户还是少开为好,所以几家只能共一个门楼进出。从后山看老宅,像一个“王”字,但总像缺了半拉身子。
我记事的时候,大爷已经不在。大爷单传,只一个儿子,我叫他老爹。二爷跟了新四军就再没回来,于是我爷把我二叔过继给了二爷。三爷是打铁的好手,手艺一直传到三叔这一代。新中国成立前夕,三爷靠从指缝里抠出来的一个个铜板,买了葫芦堰西边的半坡水田。还没开犁,就解放了,三爷家划成了富农,之后的日子就可想而知。我爷运气还好,生性愚钝,但仗义疏财,箪食瓢饮与乡邻共。再就是省吃俭用,让后人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做了教员,可见读书的好处。父亲有了我们,也继承了祖父的传统,勒紧裤带供我们读书。
“文革”时期,湾上要进行新村改造,大爷的后人嫌房子住得深,阴气太重,率先搬到村东口;过继给二爷的二叔也嫌自家房子闭向,搬到了村的西口;我家老宅没动。父亲在前边加盖了门楼和两间茅草横房,门朝南开。我家的宅子虽旧,但青山后靠,绿水前照,葫芦堰和四面铺排的层层稻田尽在脚下,父亲说是最好的地儿。可房子刚完工,父亲就离世了。父亲去世时还不到五十,我才十七,几个姊妹都没成人。姑父多少懂些阴阳,说是我家老宅改了大门。但母亲不信这些。也许母亲是对的,就是在这座改造后的房子,我考上大学又留在了大学;姐妹也有较好的生活出路,小弟退役后回了老宅,为父母生了两个孙子。这时姑父早已经去世了。
今天,我们都成了市民,但老宅在我的记忆里却总是那样美好。老宅后边有一片竹园,正好阻挡山上的流土。竹子是爷爷种的,当然不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农家没那份雅趣,只是生活中离不开竹。把篾匠师傅请到家里,打床凉席,打担箩筐,打副筛子,簸箕,啥用具都有了;横房压脊也需要竹。父亲是读书人,重品节,更爱竹,他知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句,可那时哪有肉吃?大雪天的竹园,老竹托着厚厚的积雪,却压不倒,而一到日中,竹园总是传出扑扑哒哒雪块掉落的脆响,觅食的麻雀全都惊吓得飞向房顶。老宅西边有一个几户人家合伙开挖的坑塘,湾里人洗衣饮牛都靠它。夏天,牛就泡在塘凼子里,老母猪也躺在泥沼里享受清凉。老宅的前面栽有石榴、柿子,还有两棵壮硕的桂花。秋天,红黄的石榴柿子压满树枝,像一个个小灯笼;柿子吃不完,就让鸟雀在上面啄洞;两棵丹桂的甜蜜清香把整个老湾都香透了。
传说我们这一族是从陕西过来的,后来又流落到江西,又折转到豫南,到王洼落地生根应是晚清的事情。祖上筚路蓝缕落脚王洼,而今,它只能成为我遥远的记忆了。
母 亲
父亲去世早,八十多岁的爷爷已是风烛残年,母亲成了全家的依靠。
母亲有山一样的脊梁。她长得瘦弱,却能挑一百二三十斤的担子,担稻子上谷垛男劳力都比不上。收工了,母亲还要到田里拾漏,要不就挽着竹筐打猪菜。田野里,那个单薄的身影总是我放学要找的依偎。那时照顾户只分口粮,柴米油盐全靠母亲。她大字不识,却会操持家庭。姐姐和我上中学,伙食吃不起,就让我们带饭带菜——母亲把腌菜炒好,装在玻璃瓶里,再添一勺猪油。母亲说,都是饭桩子,饭要吃饱,身子才不亏——把这些打理好,母亲才转身去吃或多或少的剩饭菜。
那个时代,缝纫机在山里是很先进的物件。父亲在远乡教书,从微薄的工资里省下一点钱,给母亲买了一台缝纫机。母亲就用它做裤子,做褂子,最后竟学会了裁剪。大孩的衣服穿不上了,就修修剪剪让小的穿;邻居有啥要帮的针线活,母亲也总爽快,从不会怠慢人家,宁可自己苦点累点,对乡邻却大方。所以,母亲在王洼人缘很好。原先,一到凭照顾工分分粮草的秋上,劳力大户总认为我家占了便宜,就不咸不淡地说些闲话,有了缝纫机,湾里的叽咕就少了。父亲去世后,再不能靠父亲的工资买照顾工分了,但母亲并没被难倒。她吃够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再苦也要让我们读书。后来,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母亲把我送到龙头山山口,打开一层层用手卷包着的五分一角的纸票,硬是塞进我的口袋。
我们都没有让母亲失望,兄弟姐妹都很争气,让我们家成了王洼的风光户。爷爷去世后,姊妹也都进了城,我想把母亲接出来,感受一下城市的生活。但母亲认为我刚成家,房子又小,总不愿来。二妹在县城有一套大些的房子,就劝母亲到她家住一段,车都开到了王洼堰口,母亲却怎么也不肯上车。我曾几次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国外,但一想到母亲把我们培养成人,她自己连小车都没坐过,就感到无比内疚。
有两次回家,我发现母亲走路气短,就劝母亲到医院检查一下,母亲连声说没事。她一生从没看过病、吃过药,总说病都是看出来的。无奈,我带了一位医生朋友回到老家,想有个医生陪护她坐火车到省城,母亲还是不愿。我劝母亲,你在那样封闭的年代就会坐缝纫机,可到现在还没坐过汽车火车,就不感到憋屈?你哪怕去短住几天,也让儿子好受些……可我哪里知道,母亲早已患上心梗,已经不能承受出门的颠簸了。
不到一年,母亲就去世了。我在坟前长跪不起,姊妹几个都哭成泪人。母亲和父亲合葬一起,那是祖上留下的坟地,一层层坟冢葬着一代代先人。母亲葬在这里是她的临终交代——这地方好,朝阳。
老 爹
老爹中等个儿,平頭,方脸,眼光平和,几道抬头纹像刀刻一般,蜡黄的手指间总是夹着半截烟头,走路总是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
刚解放时,除了祖上留下的那份房产,老爹没有尺田寸土,所以是个贫农。贫农优越,于是成了土改积极分子,风里来雨里去,最后当上了老虎山的大队长——那可是我们这一族人的荣光。
老爹的双脚从没走出王洼这块地面。其实,他有许多次走出去的机会。刚解放那阵子,到处都需要工农干部,可老爹家里有一大群孩子,都离不了他;“文革”期间,需要一批贫宣队进机关学校,可赶上父母年迈,他又没走出去。老爹是种田的行家,根生土长的山里人,三村五里都熟,此后就不愿意再出去了。这家农活干不完,老爹去帮帮,那家撩秧下种了,也会去叫老爹。解放初期,扫盲班进村入户,老爹才识得几个字。就是这几个字,老爹用了一辈子。他讲话时,总好打开一个小本本,其实,那小本本有时只是个符号,但就凭这个,他却常常能讲半天。村民有了纠纷,他去了,也拿着个本本,并不打开,只是一直捏着,却能把复杂的矛盾给化解了。别看老爹字不识几个,前秦后汉和外面的世界却总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他仿佛是王洼的诸葛亮。不过,诸葛亮还六出祁山呢,老爹却像一棵树永远定格在老虎山上,挪出去就会不服水土。
红卫兵串联武斗那阵子,老爹戴上了右倾帽子,被大会小会点过名,但碍于他在当地的威望,谁都没对他咋着,不过最后还是下台了。不当官了,老爹十里八村还有话语权。开荒造田时,老爹说:动不动就打着靠山吃山的幌子,把山砍光了,都喝西北风啊?这才保住了老虎山上的林木。
老爹一辈子和老妈厮守在一起。老妈说话不清楚,声音像是从鼻孔钻出来的,一到天冷,手就伸进肥厚的袖筒子里,靠墙根晒太阳。就这么个老妈,老爹却从不嫌弃。俗话说“独生子发人”,果然,老妈为老爹生了九个孩子,都为人本分。大哥石滚碾不出个屁来,却忠厚实在,从不惹是生非;二哥早年进了社办企业,在街道服务部做熟食,干了两年,娶了邻村大队支书的闺女,就又回到了王洼;老三读完小学就务农了;还有五个闺女,都嫁在农村,相夫教子,安居乐业,有两个外甥都读书考上了师范。
王洼的田不多,山不大。老爹到老虎山中承包了一片林场。这是老爹当大队长精心保护的一片混交林,密密麻麻的橡树、松树、板栗、油茶……如世外桃源一般。老爹在山半腰搭起两间茅屋,清晨,赶一群牛上山;擦黑,踩着夕阳回家;阴雨天,就歇在山中。
老爹九十岁谢世,老妈也活到八十八岁,他们活成了一对老神仙。
责任编辑 吴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