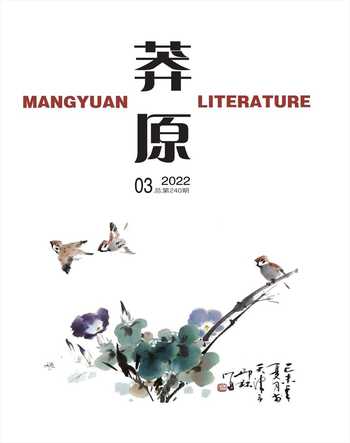小说讲堂:人物
张炜
传统和现代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
谈到读过的小说,大家都会说出其中的几个“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感动了我们,或者因为十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常常时不时地回到脑海中,徘徊不去。可见小说中的“人物”有时比我们身边的人、比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还要让人难忘,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似的。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看看作家们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究竟使用了哪些方法、怎样给他们注入了灵魂,才让其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地一直活了下来。
这里的“人物”两个字之所以需要打引号,是因为作家有时写的并不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只动物、一棵树。但我们不妨把它们都作为“人物”来对待。比如托尔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三死》,就写了三种生命的死亡:贵妇、农民、白桦树。
“人物”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作家赋予他 (它)们生命,让其有了性格,并且很独特很有趣,让人过目不忘。实际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越深,这个“人物”也就越是非同一般。一个作家有很大的雄心和能力,就会塑造出与以往文学画廊里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的形象。这当然是很难的。谁如果做到了这一步,他笔下的形象也就永远地活了下来,读者过了很久以后还要谈论——对作家来说,也可能因此而写出了一部杰作。
我们读小说,常常觉得有些“人物”虽然也算鲜明和生动,可就是有点似曾相识,好像类似的形象在哪里出现过。这样我们就容易将他们混到一块儿,时间一长,一个个面孔也就模糊起来。可见这些形象还不够奇特和深刻。
评论家分析一部小说,常常要从“人物”入手,围绕着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从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剖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一部作品没有丰满独特的形象,其他也就谈不上了。小说中再高明的见解,最后都要归结在“人物”上,通过他们体现出来。比如说“思想”,如果仅仅是说出来的,是作家本人的议论,就很难在读者心里生根,也很难打动人。理论文章的“思想”,是由作者直接宣示的,是以理服人,不是以情动人,不会伴随着人的情感深入读者的内心。而小说把情和理紧密结合了,将这二者粘合到一块儿的,就是“人物”。
所以在小说的多种元素中,居于核心的还是“人物”。有人问:小说早就现代化了,各种怪异的小说都有,各种精妙的手法都在使用,难道“人物”一定要牢牢占据作品的中心吗?是的,因为只要是小说,就要努力塑造“人物”,这方面暂时还找不到例外。
其实写作中的十八般武艺,最后总是将其中的大部分收到了“人物”身上:一切都为塑造“人物”服务。如果只有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只有好的语言,而没有一个“人物”使人记得住、没有一个“人物”打动读者,让其历久难忘,那么这部小说可能还不是成功的。
过去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位年轻人读了一部小说,被里面的主人公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脑海里都是这个形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生活的中心内容都被一本书里的“人物”占据了。这里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的歌德,他写了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当时竟然有不止一位年轻人因为读了它而采取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行动:自杀身亡。舍弃自己最为宝贵的、只有一次的生命,这种事情竟然是由于读了一部小说,这可信吗?是的,因为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因为那些自杀者弱智,而是因为他们难以摆脱文学的魅力。这种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当然主要还是来自“人物”。
读者谈论阅读中的感动,谈的最多的往往就是书中“人物”的命运、命运的曲线怎样与自己暗暗地重叠与吻合——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最能触动他人心弦的。每个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读者,他在閱读中肯定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同样要感受这些“人物”的感人力量。
“人物”的背后隐下了一只手,那就是写作者的手。
可是我们知道,感人至深的不是作家们使用的写作技术,不是什么方法之类,不是作家的三寸不烂之舌,而是其他。这个“其他”是非常神秘的、不容易说得清楚。我们知道,自己被深深打动的,如果是一些言辞,那么这言辞是来自“人物”的;如果是某种令人战栗的思想,这思想也要来自“人物”。“人物”分明有自己的灵魂,这灵魂顽强到不死不灭,强大到足以自主行动、不受一切力量约束——甚至不受作家本人约束。
只有这样的“人物”才会把我们深深地感动,才算真正居于了作品的核心。
这个“核心”是读者和作者共同拥有的——作家在创作这部书的时间里,也是围绕这个“人物”生活的。“人物”只有具备了这样强大的力量,才会在时过境迁、在远方的某个角落里,产生出这么不可抵挡的神奇,让我们着魔。
其实我们在阅读时,不过是回到了作家写作时的那样一个世界里——作者和读者之间被文字连接起来了,二者处在了同一个时空中。在这个世界里,“人物”是起主宰作用的。
所有杰出的、感人至深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作家本人取代了笔下的“人物”,站到了这个核心的位置上,那就是一种“僭越”——作品将不会有超强的魔力征服读者。
给人物说话的机会
作家一般都想让“人物”体现他的思想和志趣,让“人物”替他们表达。这是一种代劳,也是“人物”的一份责任。可是这往往又让作品中的“人物”不堪重负,被赋予的重大任务压得踉踉跄跄。如此一来,作家所要达到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其实“人物”一旦出生了,就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作家这时候等于他(它)的生身父母,即便有养育之恩,也不能左右和决定一切。就孩子与父母的相处之道来看,小说发展到今天,父母(作者)与孩子(人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变得更现代了,而是变得更封建了。因为父母的威权越来越大,什么都说了算:作家在作品中常常是非常粗暴的。
作家为了体现和显示自己的技术和思想,常常把作品中的“人物”推到一边,越俎代庖。如“家长”动不动就“意识流”,就不加标点大说一通,或宣讲起高深的理论;再不就做起杂技演员那样的高难动作,像现代结构主义,设置了一些古怪的房间和回廊——结果作品中的“人物”一旦出门,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甚至有时还要剥夺“人物”说话的权利,只让他们站在一边。
结果这样的“人物”永远都长不大;或者四肢长成了,大脑没有发育起来。
作家的思想观念通过人物去表达是难免的,但应有个限度。通常是作家给出一个环境和空间,给出足够的自由,一切由“人物”自己去做即可。开始的时候作家或许会主动一些:“孩子”还没有长大,大人难免多做一些多说一些;等“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得由他们自己行动。
的确如此:一部小说越是写到最后,作家就越是要迁就他的“人物”。作家这时候应该是“糊涂”一些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一个家长过于强势,任何时候都要事事作主,那就容易把事情搞砸。
但强势的“家长”很多,动不动就把作品中的“人物”晾起来,自己出来大说一通。中国现在或以前的小说有这种情况,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家也有这个情况,像托尔斯泰、陀思托也夫斯基、巴尔扎克,都是这样的作家。不同的是有的作家虽然强势,但胸襟是巨大的——他们有忘情大说的时刻,也有超人的理解力和包容力,会对自己的“人物”特别欣赏和纵容。他们好比这样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严厉起来十分吓人,可宠爱起来又极为宽容,敢于撒手让他们满世界奔驰,直到跑出边界。
这就不是一般“家长”所能做到的了。
原来不但要给“人物”说话的机会,还要允许他们说出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左的话;原来让他们说话,不是让他们成为作家的传声筒,“人物”既然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就必定会自然而然地带出作家的所有特征,会确定无疑地染上作家的一切,从语言到其他——因染色体和基因的缘故,其一举一动都会有作家本人的个性倾向。
到了现代,看上去作家直接出面大篇言说,把“人物”晾在一边的情形似乎少了,但实际上却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把“人物”当成现代技术的傀儡、当成牵线木偶——看起来一切都是“人物”在台前活动,其实等于是一些道具,作家是隐在后面提线的人。
给人物言说的机会,不仅是让他们对话和发言,更是真诚和放任,是给他们真正的行动的权利。如果作家预先设计好了一切,“人物”也只能在一个既定的轨道里运行,不能由着性子来,不能酣畅淋漓痛痛快快地活着:说什么不说什么,哪个地方要激动地说,哪个地方要痛苦地说,哪个地方要语气温柔地说,都由作者事先设定好了——这种“人物”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丧失了自己。这样的小说就不能从生命深处感动读者,不能使人的灵魂为之一颤。
小说中“人物”的言说,现代人或许已经变得非常吝啬,不再让他们开口放言。这不像十九世纪,那时候打开一本书,一个“人物”一口气说下的话就可以占满一两页。现在不行了,或者是作家不自信,或者是“人物”不自信,担心读者不听,总之说得不多:句子很短,欲言又止或吞吞吐吐,再不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确,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人物”说话越来越少。有时行文中甚至不打引号,让“人物”的话变得模模糊糊:既像他们的对话,又像作家的叙述。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两个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海明威塑造“人物”很倚仗对话,他的对话含蓄简约,点到为止。但就是这些对话,成为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他有时也让“人物”接连说下去,但这是真正的“对话”:话能够对得起来,对话双方如果抽掉一个,另一个就不成立。而时下的一些作品,所谓的“对话”许多时候双方是可以随意抽换的,抽掉了一方,另一方也照样在说。
而福克纳一般不给“人物”太多的说话机会,他的“人物”主要是“无声的语言”——行动。他更爱写人物的动作,很细,细到了让人不太耐烦——一个人怎样牵过一匹马来,如何拍一下马背,整一整鞍子,给它刷一下毛,再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那儿……这些琐碎的具体动作往往占去小说很大的篇幅,所以有人觉得福克纳的小说读起来很困难。
海明威总的来说还不像福克纳这样大肆铺陈人物的动作,似乎更长于对话,“人物”说的很多。他和福克纳一样,情节走得缓慢,但随处都是好的细节,对话意味深长:很短的句子,又很艮,一点一点往深处走。这些“人物”是充分自立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出的都是自己的话。
如果“人物”不能说自己的话,那就不如不说。
我们看一下十九世纪那些强势作家们,拿托尔斯泰为例,他在对待“人物”言说这方面是极其质朴和诚实的——或者让“人物”暂时闭嘴,或者索性让“人物”好好地说上一通,一口气说个透彻。在这里,作家本人和“人物”是平等的,要说都是淋漓痛快,都很直爽。他的那篇有名的短篇小说《卢塞恩》,作者自己站出来说了好长的一通话。还有,在《战争与和平》中,“人物”们想怎么说就说个痛快、说个尽心尽性;最后作家本人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大量的话要说,就另起炉灶,在第四册用了第一部相当的篇幅、再加上整个的第二部,痛痛快快地说了一番。
那时候,“人物”说的和作家说的,二者界限分明。可见十九世纪的大师们在对待“人物”的言说方面,比起一些现代作家隐晦曲折的心计,如“代言法”和“傀儡法”,还是显得更大气、更质朴和更畅快一些。
塑造人物的两个倾向
通常我们认为,作品中的“人物”越复杂越好,比如他的性格,要由许多个侧面组成,这才会是一个真实饱满的、说不尽的形象。一般来说所谓的纯文学就是这样,它不像一些通俗读物,劝诫意味分明,其中的“人物”往往非好即坏,性格特征或聪明或愚钝,或单纯或狡猾;再不就是恶毒的、善良的、美好的、丑陋的、阴险的……如此种种。我们知道,真实的人物是具有多面性的,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人会在不同的场景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要写出真实的“人物”,既不能人为地简化,又不能过分地强加上一些烦琐。自然真实,这才最具深度、最有说服力。可见“人物”形象并非是越复杂越好,因为我们不能为了让其特别“深刻”,而要故意找出人性中各种不同的元素,像糟糕的大夫开药方那样,把几十味药统統搅在一起。
十九世纪古典主义稍稍有点区别,那时作家们手中的“人物”往往是黑白分明的,但我们读了并没有简单贫瘠的感觉,“人物”同样十分饱满和真实。这是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而在现代小说中,作品中的有些“人物”很难让读者作出判断,说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人物”不再是黑白分明了。
动辄对“人物”进行道德判断,在今天是犯忌的;有人认为做出这种判断直接就是一种虚假和简化,是思想的肤浅,是人的幼稚病——到了最后,我们竟然一时弄不清该不该进行道德判断、该不该保存这个最古老的判断尺度。我们对于人和事的模棱两可、犹豫和两难,几乎成了一种常态。这究竟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理论素养太深,还是因为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了原则、没有了起码的道德准则?
但是,写出“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这是没有争议的,也是必需的。在现实生活中,有时的确很难说出一个人是好还是坏,因为人是多面的,难以一言以蔽之。有时候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举动上,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看的人不同,标准也就不同了。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还需要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观察。
这就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没有感情的写作是很糟糕的,这样的作品没有精神力道,也不会感人;可是有人又会说,现代主义的所谓“零度写作”,讲的就是情感的零度——但那更多的只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并非真的没有了情感。实际上,写作者的感情越是深厚浓烈,就越是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深刻的情感是写作的基本动力,但是怎样处理这种情感、怎样表达,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没有情感不好,可是有了情感,也需要使用得当才好。一般来说,要写出一个复杂的“人物”,这个“人物”往往不能过多地带有作家的倾向——作家的倾向不显露,他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不会清楚地贴上个人好恶的标签。想想看,如果作家急于把对“人物”的好感或憎恶全部倾吐出来,那么“人物”身上的许多其他元素就会被忽略掉。这样做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要说的全说了,留给读者自己判断的余地和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了。
有人说:写作是不能太冷静太理智的,写作就是要充分保持感性能力。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是不太可能离开理性的把握。
现代小说突出的倾向是“人物”的模糊化和复杂化,这增加了分析的难度。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深入认识,人们对很多事物不是越来越肯定了,而是越来越游疑了。最吃不准的还是人本身,现代人对自己都有些恍惚——有些现代小说常写的主题就是对自己真实身份的追究,比如卡夫卡的作品。在现代人眼里,人本身实在是变得空前复杂了。在千变万化的高科技、在极度膨胀的现代都市面前,人变得渺小虚弱,无能为力,疑虑重重忧心忡忡。这一切大概都加剧了现代小说中“人物”的复杂和内向,他们变得越来越难以定性和分析了。现代小说中的“英雄”不见了,“小人物”却比比皆是,他们像微尘一样随处乱飘,无处不在又可有可无。
这一切,比较一下十九世纪或更早的经典作品,就会看得清楚一点。那时“人物”的复杂与今天还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那时的“好人”“坏人”大致清楚,一般不会发生站错队的现象。当然好人身上有弱点,坏人身上偶尔还有一些很好的方面,但总不至于影响到定性。像《贝奥武夫》《伊利亚特》这些史诗中,英雄就是英雄,妖怪就是妖怪。中国的古代小说也是这样,冯梦龙编的《三言二拍》,蒲松龄的《聊斋》,其中的“人物”都是不难判断好坏的。
说来说去,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大致有这两种倾向——两种倾向都产生过伟大的作品,所以我们不能说哪一种一定就是最好的。如果再探究下去还会发现:这两种倾向的形成除了因为时代的原因,还有另一些原因,如个人审美理想的不同,也可以造成不同的追求。
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在塑造“人物”方面具有不同倾向。现实主义作家往往把“人物”写得比较复杂,很难给予简单的道德定性;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好坏则泾渭分明。这两种作家无法区别高低优劣,因为都给文学画廊留下了难忘的文学形象。
今天我们很容易将浪漫主义给予曲解,因为在当今这样的物质主义时代,人是很利益化欲望化的,已经没有多少浪漫情怀。所以,从体裁上看,我们的诗歌是衰落的;从审美上看,浪漫主义是萎缩的。过去正好相反:打开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古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似乎更多,这在东西方都相似。文学一路走过来,好像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内向、越来越现实化物质化,再出现一个李白和屈原式的诗人,似乎想都不要想了——这里不仅是指他们的规模,而主要是指他们的浪漫气质,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
浪漫主义作家也在写“人物”的复杂性:他们写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那么这个“坏人”就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坏人”;反过来写到一个“好人”,也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好人”。这里并没有简单化符号化,而同样表现了人性的极度复杂性和深邃性。它塑造出的人物会给人以极大的冲击力。比如雨果。雨果的作品具有永恒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激情像海潮一样汹涌,直到老年还是如此。《九三年》已经是他暮年的作品了,也还是激越澎湃。还有《悲惨世界》,其中的所谓“好人”“坏人”一开始就已定性,但却在一个既定的方向下越走越远,一直走到一个出人预料的、让人瞠目结舌的人性的深渊。就是说,他笔下的“人物”在一个方向上被规定了,却能走入更加深刻和饱满的境界。比如写可怜的孤女珂赛特落在了狠毒的妇人手里,雨果这样描述这位恶妇:“如果给她描上两撇胡子,就是一个马车夫”,“睡着了还露着两颗獠牙”,“她说自己一拳就能捣碎一颗核桃”……
古代的英雄史诗也是这样的道理。文学走入了小时代以后,对浪漫主义巨匠会产生一些误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现在某些文学理论会说,作品的好人族坏人族区别分明,即是“二元对立”。这等于说脸谱化标签化是用以批评作品的理论依据。其实这只是皮毛议论。东方艺术有一个写意的传统,常常是高度浪漫的。比如京剧,是最有代表性的——其“人物”一上台,花脸就是花脸,白脸就是白脸,小丑就是小丑。各种“人物”的性质从服装和脸谱上一下即可看得出来,当然是先予定性的。它似乎犯了现代艺术的大忌:这是“坏人”、这是“奸雄”、这是“鲁莽”、这是“英雄”,我们早就知道的。但看下去,却没有人会觉得京剧这种艺术概念化,不但不觉得它浅薄,相反会觉得它高妙精深,魅力无限,呈现出斑斓色彩。
看来“人物”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不在于写意和浪漫,不在于这种表现手法,而是作家艺术家本身的低能和贫瘠苍白。浪漫主义看上去把角色固定了、色彩固定了,却并非是笨拙或弱智——从技术上看,这样做的难度更大。浪漫主义一开始用“减法”,接下去却用了烦琐的“加法”:呈现这个角色全部的复杂性。
与通俗读物的“类型化人物”所不同,浪漫主义艺术不但没有在“类型”面前止步,而是愈加深入地走下去,直走入人性的纵深。
写意的艺术和写实的艺术在塑造“人物”方面具有不同的方法和倾向,但在文学表现上,却不能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还有更加复杂的情形,像托尔斯泰,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文学史会说他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可是他的浪漫主义气质也十分浓烈。屠格涅夫是他的同代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可能不宜简单划分,不能机械和死板地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许多时候它们是相互交融和渗透的。
有人会问:这就是前些年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吗?不,这只是对作家作品的阅读感受,而不是对创作方法的建议。
人物的疏朗或拥挤
有的作品塑造了很多人物,虽然这其中也会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但仍然有一群人让读者记得住。这就是所谓的“人物群像”。比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人物”多极了,却大多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有一些作品恰恰相反,读者掩卷之后仅仅对一两个人物有印象。像《少年维特之烦恼》,读者大半只会记住维特和那个女子。《茶花女》也差不多是这样。笔墨比较集中地用在一两个“人物”身上,是比较单纯的写法——无论从情节还是其他方面看都是单纯的。这不光是篇幅的问题,也还有写法的原因,是作品的格调所决定的。像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也不算短;还有《红与黑》《飘》这一类,给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也比较集中。果戈理写哥萨克的那个著名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只有八九万字,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组“人物群雕”。
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会有一些不同。我们很难设想在万余字的短篇小说里能够写出十来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如果是一个四五万字以上的中篇,就会写出三四个、四五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是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长篇,能写出一两个激动人心的“人物”形象,这个作品也就算成功了。
从物质层面来讲,“人物”数量与他们生活的世界的广度还是相应一致的。这就像一个国家,地场太窄,土地面积太小,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比较起来,短篇小说就属于“小国寡民”了。人口最多的要算“长河小说”,这是沿用了欧洲的说法,它不包括“系列小说”,指的是一套很长的书,就像一条长长的河流,无论分多少册,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致由同一批“人物”来演绎故事——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或许会有一些新的“人物”加入进来,但主要的还是原来的那一批,他们是小说中的骨干;从故事上看,无论有多少独立的单元存在,大的故事也肯定是同一个,它包容了其他一些不同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都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系列小说”有一个大的题目,然后把不同的小说拢在一起,“人物”和故事或偶有串堂,但各书独立。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它们选择了一个总题,将不同的小说归于“旗下”。
无论是“长河小说”还是“系列小说”,都是一个足够大的世界,可以容纳无数的人口,却不会显得过于拥挤。“人物”拥挤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得不到作者的悉心照料。有时“人物”拥挤的原因,是作家创作时的内在动力不够,只好不停地添加人口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是糟糕的情形。
像《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蒂博一家》这些“长河小说”,不可能只有三五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它的人物画廊很长,所以就需要很多的人在里面,这样才不至显得空空荡荡。如果是极小的一个空间,过多的人物在里面活动就伸不开手脚了。
那么多的人、数不清的场景,会有驾驭的难度。比起“长河小说”,“系列小说”好办一些,因为它的“人物”之间没有情节上的交融,每一本都是另起炉灶,所以更为自由。“长河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同一批,要分成很多册,每一册要求有一个相对集中一点的故事——除了最重要的“人物”每一册都要出现而外,总要有新的“人物”不断加入进来,给故事注入新的活力。
长篇小说的“人物”可以用一棵树来图解——这就像欧洲人的家世图谱一样,用这样的“大树”表现世代血缘,使我们看起来十分清楚——它的主干和粗一些的侧枝就是家族中的几个老祖,细一点的枝杈就是分开的家庭。小说也是如此,基础有了,随着情节发展加入进去一些“人物”,就变得枝叶丰满,成为一棵很大的树了。如果光有一个主干、几个侧枝,就不是一个蓬勃茂盛的树冠了。果园技术员讲过果树的修剪,他说了一句顺口溜:“大枝亮堂堂,小枝闹攘攘”。由这句顺口溜来理解长篇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分布,是很形象很有道理的。“大枝”是需要疏朗的,所以就“亮堂堂”;但那些不断增添的新的场景和人,都是“小枝”,所以要“闹攘攘”。
回头想想《红楼梦》,那些“大枝”果真是清晰亮堂的,而那些“小枝”密挤的,真的是很热闹的。这就是理想的长篇,它的确像一棵大树一样有生气,茂盛而且饱满。
以地域为结构坐标和参照,写出不同的长短作品,中外作家都有。作家总要有一个生活基地,它可能是出生地,也可能是后来长居的地方,反正作家对它有许多话要说。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福克纳的那个县,巴尔扎克的巴黎和外省,后来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地方,成了文学的“地标”。这是他们划出的一块文学土地,如果用世家图谱来表示,那么这个地界里栽了很多大树——每一棵都是独立的,枝叶丰茂。这些树的根脉在地下联结着,长出地表的却不是同一个主干。
说到底,作家漫长的阅历和复杂的生活经验,还有体悟能力、敏感性格,这一切综合起来,使他心里装下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杰出的作家与一般人不同,他的好奇心特别重,这主要就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究上。作家一生可以不停地写下去,因为他的心灵世界里活着的“人物”太多了,他的世界又太大了,那怎么会写得完?
作家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太爱了,可能也因此而更加失望或愤怒,结果就会有格外强烈的表达。他对各种有趣的“人物”情有独钟,所以一有机会就讲他们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
每个作家都希望写出几个经典形象来,让他们长久地留在读者心里,不被遗忘。这些“人物”或者因为境界不可企及,或者因为思想极为深刻,或者因为语言、经历、行为的特异——反正是真正的非同凡响才行。
这些“人物”要足够真实。回头想想我们读过的各种作品,以我们个人的人生经验来参照对比一下,就会判断出这个“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真实的“人物”无论多么怪异,都会让人感到与生活中遇到的某人有点相似——读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拿来与生活对照,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可并感叹比生活当中遇到的某个人更精彩、更极端、也更孤注一掷。
同样是名著,同样是塑造了一些“人物”,细细体味起来,他们的成色仍然是不同的。最容易对比的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将它们的“人物”作一下对比是很有趣的。《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其实是超过《红楼梦》的,民众谈论“三国”更津津乐道,刘备关羽张飞挂在嘴上,谈宝黛情爱的就相对少一些。“三国”更通俗易懂,从“人物”到故事都比较外向,有利于口耳相传。“三国”塑造人物很生动,也简单明快,有人称为“类型化人物”,也说成“扁平人物”。
这与书的形成方式有关。《红楼梦》是文人创作,而《三国演义》是由文人整理出来的民间文学。前一部小说是个人的运思,后一部是一代代人众手合成的——照理说,一个人怎么会抵得过众人的劳动?可见文学创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它是生命的创造,有些不可思议。出自个人的,他的创造是独一份的、不可重复的;如果许多人都参与了,就会留下一些他人痕迹——好在时间是漫长的,经历一代代人修改下去,总有些极好的东西留在里面。这和组织一个“创作班”搞集体创作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创作班”在时间和人数上仍然是有限的,而民间文学几乎是无限的——这种无限带来了艺术上的巨大能量,大到了不可估量的地步。
民间文学在文人整理之前不是以书面形式保存的,而是需要说出来听——只有格外动听别人才不会忘记,才有兴趣继续讲给别人、并且“添油加醋”一番。讲故事的人要说得重点突出、简明扼要,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拎清。就是这样的一种形成方式,所以“三国”里的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语言行为夸张。这种鲜明往往也和某种简单连在一起,比如张飞,勇敢鲁莽而已;比如诸葛亮,足智多谋就够了。其他“人物”也大致如此,外形清晰棱角分明,大线条勾勒,很通俗,一说就懂。反过来,如果把这些“人物”进行复杂的人性镂刻,将一些最难以言说的、自相矛盾的部分凸显出来,必然会变得晦涩、不好理解,也不好流传了,听起来也不过瘾。
一般来说,通俗文学在塑造“人物”方面,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应用了这种百试不爽的手法。这样做事半功倍,极受大众欢迎。这样的“人物”鲜明自然鲜明,但却经不起细细的文学阅讀,没法更多地琢磨和品味——总觉得缺少一点厚度——从正面看五官眉眼周全,从侧面看则十分模糊和薄气。他们就像民间的“驴皮影”艺术,投在幕上的是正面剪影,侧看是不行的。这就有了“扁平人物”一说。
再看《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就立体得多了,像生活中的实际存在一样血肉丰满,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体内的脉动和五脏器官,不仅是看上去鲜明,而且还有说不尽的人性的神秘。这就是“圆形人物”。
通俗文学不需要写出“圆形人物”,因为情节快速发展,难以完成对“人物”的细细刻画;从另一方面看,复杂而又内在的“人物”性格也会影响理解和传播的速度,不利于吸引大众。可见这是不同的艺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不同要求。
通俗文学采用了民间文学塑造“人物”的手法,却在文学水准上无法与后者相比——因为它在创造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一部通俗文学的写作时间是半年或一年,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民间文学可能要历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参与写作的人散布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所以说空间大到不得了。从这方面看,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实在难以同日而语,它们的品质是不同的。民间文学尽管写出的也是“扁平人物”,却可以由文学创作上的无限可能去弥补一切。
“扁平人物”即“类型化人物”,它们通常存在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当中。
可是在纯文学写作中,如果出现了“扁平人物”的倾向,那就是失败的。有人举出了马克·吐温的例子,认为他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就接近于通俗文学,并且采用了那样的手法。可是我们认为它绝不是写了“扁平人物”。还有人提到《白鲸》等,指出这些外国名著的通俗性、“人物”的传奇性、鲜明的特性,都接近于通俗文学——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写的也绝不是“扁平人物”,而是“圆形人物”。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也绝不是通俗文学作家。
那些浪漫主义的艺术,比如中国的京剧,其中杰出的代表性作品,也绝不是刻画了“类型化人物”。
“类型化人物”在民间是很容易得到流传的,通俗文学和一些畅销书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艺术的要求。
而雅文学(纯文学)的“人物”塑造绝不可以追求“类型化”。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有性格非常突出的方面,也有很难概括和表述的方面。把一个生活中的人全部真实地表现出来,是最复杂的工作。生活中没有“类型化的人物”——我们如果在理解上把某个人“类型化”了,但最后还是会否定这种结论和印象。比如一个人非常勇敢、豪放,甚至有些简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发现其粗中有细,足够狡猾;有的人特别善良,心软无比,遇到事情就流泪,但交往日久,又会发现他还刚烈固执,甚至残酷,有特别坚硬的一面。原来人在不同的环境里会呈现出极为不同的倾向。
回避“类型化”,是为了接近生命的真实。
“扁平人物”的生动是浅表的,如果太深了就费解,就会有一些流传上的障碍。让通俗文学写出复杂深邃的人性来,不仅困难而且没有必要——它只写出人性中的几个侧面、强化几个侧面,也就足够了。通俗文学和曲艺是同宗同族的,因为它的主要功用是娱乐。
小说人物絮语
人物多少与小说的物质空间
一部作品中,到底“人物”多了好还是少了好?这很难界定,需要根据写作时的实际情况来定,还有审美追求方面的差异。我们一开始就讲过,有的名著尽管“人物”很少,但看起来也很过瘾,并不会觉得单薄;有的作品“人物”很多,读来却不觉得拥挤。
不过一般来讲,从写作难度上看还是“人物”少一些更好,因为这样可以集中笔墨,让结构变得相对简洁一些,好掌控。像索尔·贝娄那样在众多的人物堆里穿梭自如,这得具有超人的本事才行。“人物”像走马灯一样,哪怕是一个匆匆过客,作家都不能冷落他。这样高超的技能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
有人善于写相对单纯的书,写简单的故事,其中不过是清清楚楚几个人的过往,读来却十分动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主要写了一个人,一个打鱼的老人,他的对手是酷热的太阳和一群大鱼。这个故事在一般人那儿是没法讲下去的,可是海明威却讲得兴味盎然,读者也津津有味。这本书给人十分厚重的感觉。类似的还有马尔克斯的一部写海上遇险的中篇,叫《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人,也在海上,同样写得惊心动魄。
看来“人物”多少不是一个问题,关键要看作家的能力怎样,比如他的洞察力、他的激情,这一切够不够用的问题。
每个人的叙述方法、架构作品的方式不一样,他会根据情况选择自己的“人物”,从性格到数量,都要自然而然地考虑周到。一切都要做到高度和谐,服从自己叙述的需要、表达的需要。
一般来说,作品较短“人物”就少,因为它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物质空间,没有那个铺张的条件。写一万字,写到了二十个“人物”,而且每个都鲜明饱满,这不可能;反过来说,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作品,只写了一两个“人物”,就未免太空洞了,撑不起来。这好比一座大房子有八百平方米,只有两个人在里面生活,太空荡了。如果四十平方的屋子却住了五六十个人,那就太挤了。这是从小说的物质层面谈的。
但这只是一般的道理,它在有大能的写作者那里常常是被忽略掉的——他们不太在乎,而且乐于和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挑战。
每个人的结构方式不同,表达欲望不同,这些因素都决定着“人物”的多与寡。我认为一部中长篇,在五六万、十几万字的篇幅中,能写好两三个人物就已经是很成功了。
文气的长短和小说的物质、精神空间
有的书架构很大,有的则比较小。在写作的过程中,进入了特定的语态,渐渐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情节和人物都将得到调整,这是必然的。但是书的长度还是取决于一开始的心理准备——作家会在构思之初给出一个边界、一个规模,这会影响到它的“文气”。“文气”的长与短,即从根本上决定着一部书的长与短。但“文气”的长与短,并不决定着“人物”的多与少。
作家设定的作品长度如何,给它的“气”是不一样的。作品里面真的有一股“气”,当“气”断了以后,再好的故事也讲不下去。“气”只要没有使尽,没有走到底,这个作品的长度就会继续往下发展。
“气”作为一个概念,好像有些神秘,它属于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小说物质层面的空间加大了,“人物”少了就不好办;但精神层面的空间加大时,里面的人物却不一定多。精神的空间、思想的空间,这完全要靠感觉去把握。一篇小说可能只有一万字,但它的精神空间却会非常辽阔和雄伟;有的作品长达几十万字,它的物质空间已经很大了,但精神空间也许并不大,给人十分狭窄的感觉——这时候加入再多的“人物”也仍然无济于事。“文气”、“空间”,这些谈起来虚一些,但并非不可理解,只要有较长的写作实践就会感受到它们。小说的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有关系,许多时候甚至是紧密相连,但毕竟还不是一回事。
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当作家的“文气”不足时,就会不断地给作品添加“人物”,拉长篇幅,追求时间的大跨度,想依靠人数和场面来做以补救。这样只会热闹一时,却不会有什么性质上的根本改变。这让人想起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很多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警惕自己写作上的好大喜功,不要一味追求作品的浩大场面和众多的“人物”,而要脚踏实地、尽可能地简短才好。这样时间长了,“文气”就会养得充沛——那时候的“长”与“大”才会是有意义的。
小说人物的烟火气和清贵气——情趣和水准
小说与散文和诗都不一样,它一脱胎就有比较重的烟火气。比如会有一些肉体描写,性描写,等等。在这方面,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都一样。所谓的纯文学,并不能保证如数祛除它的烟火气。
我们常常会觉得某些作品的烟火气太重了一些。有人认为作品既然塑造的是一个粗鲁低俗的“人物”,他当然会说一些粗俗的话、做一些粗俗的事;更有甚者,将龌龊下流的文字当成了深刻反映时代的“杰作”,理由是:生活本就很龌龊很下流。
这显然不是什么理由。托尔斯泰写到了妓女、流氓、社会最低层最下作的人物,人们读了以后却并不觉得难堪;他写得淋漓尽致,却从不让人觉得下流。还有索尔·贝娄,他也写了一些粗俗“人物”,甚至直接搬上一些粗口,但我们仍然不觉得脏。杰出的作家有清贵气。
《红楼梦》中的烟火气偏重了一些,《金瓶梅》則有许多黄色段落,但它们的本质仍然不同,书的品格是藏不住的。这里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聊斋志异》是极有趣极有魅力的,可惜字里行间好似有一股不洁的气息。《红楼梦》要比《聊斋志异》好。《聊斋志异》里面的烟火气更重一些。
在这个欲望满涨的特殊年代,只要写得脏腻,有人就会兴奋起来,说生活比它还要脏,越脏也就越是真实。这是一种末日论调。那些大师们其实更有力地写出了生活的脏与黑,可他们并没有随之烂掉,而仍然是清洁的。
有一部外国书很像《红楼梦》,但要早上好几百年,叫《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个女官(紫式部)写的,丰子恺翻译得也好。这部世界上最早的纯文学长篇小说,虽然烟火气也有,但比《红楼梦》澄明纯美。它写的那些爱恋男女比《红楼梦》还多,它诞生的时代又那么早,却写得高雅,细腻,有一种特殊的才情、别致的意境。
它和《红楼梦》一样,也主要写皇族和京都的生活,写王公贵族的往来,特别是贵公子与宫女之间的爱情——也有一些不是爱情,无非是爱欲和性的东西。男女在一起,分手的时候掏出一首诗——这诗或是她自己的,或是抄白居易的,大半都是歌颂和回味爱情的,留给这个人,然后就走开了。类似的情节不断地重复,奇怪的是读来不觉得它的表现手法平直苍白,而是趣味无穷。每个人物就像在眼前一样。
作者的权力,人物的自由,作品的主观与客观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当然是作者。作者的幸福也在这里。可是当他拥有的权力过大,有时就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比如过分地干涉其中一些“人物”的行动和思想。
这个世界里包含很多的思想、很多关于生活的独到解释和表达。但我们知道,作家一旦创造了这个世界,就像上帝一样,不要轻易地现身、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随意地大声宣讲,要让思想通过“人物”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就是形象的作用,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东西,往往大于直接说出的所谓“思想”。
米兰·昆德拉有最好的两本小说: 《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玩笑》是早期的作品,更动人更饱满,它的“人物”是比较自由的。后来作家名气更大了,权力好像也更大了,表现在作品中,似乎就多出了一些专横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运用的技法,包括探索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也许很高明,不过这种高明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由“人物”体现和流露出来的,而是出自作家本人的言说和宣讲。他的“人物”只是作家的道具,本身并没有什么自由。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获得了较前更大的反响,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了作家的代表作。但我觉得作家既然自己站出来了,干预得这么多,“人物”已经没有大的作为了,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虽然这本书写得极为聪明和漂亮,那么随意、和谐而又极其巧妙地把思想、哲学、绘画和音乐融合在一起。这让人想到一个高超的杂技演员,娴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让观众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每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做到那个火候是很难的。从结构上看,一会儿来个“误解小词典”,那些词汇辨析插在里面,却不让人觉得突兀,在情节发展上与主人公情感的波澜起伏揉在一起。它讲故事,讲背叛,讲反抗,讲个人主义,讲自由和独立……这方面的思辨又结合了当年捷克布拉格的社会生活现象,算是浑然自如。但总有点卖弄,虽然还可以忍受。
这是一部主观性特别强的小说,作家本人是这个世界里的绝对主宰,“人物”基本上没有了地位。
现代读者其实是讲究小说客观性的。客观性就是把作者全部的意图、观念,用茂长的语言和曲折的情节、壮硕的“人物”覆盖起来,使人觉得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有了诠释不尽的、无穷的魅力。
反过来,小说的主观性太强了,读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它:作者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越多,我们的反抗就越多。读者只需要看书中的“人物”,看他们的行动和故事,不需要作者的观点,尤其不需要作者在一旁解说。所以,聪明的小说家会把自己的意见掩藏起来。
米兰·昆德拉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令人耳目一新。但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更喜欢前一本《玩笑》。
伟大的尺度。大动物的野心。借气,勇气无所不在
我们生活在现代时空里,我们作家的“说”,已经与十九世纪的大师们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他们更为直率和勇敢,该说就说,奋不顾身。只要是质朴的,就会格外感人。我们今天再读托尔斯泰的那些言说,仍然会被那种固执、朴实和真诚所打动。只有大师们才有这种感人的力量,这来自他们的人格。
从这儿来看,所谓的“客观”还是“主观”,完全是因人而异的。我们现在的小说家太聪明了,一会儿自己说,一会儿伪装成作品中的“人物”来说,可惜总是让人觉得有些问题:不那么真切和感人。这种言说很难产生崇高感、很难获得一种力量。当年的大师们要说就自己说,他们不会伪装成某个“人物”来说,这其中的区别就在这里。“现代主义”只有卓越,没有伟大。
在评论“伟大”的时候,我们的尺度也许很难更换。这是没有办法的。后来的作家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刁钻,机灵得就像一只猴子,或者像黄鼬一样,无比狡猾无比漂亮,花样无限,灵巧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古典的大作家,只会让人想到一头大象或犀牛。他们动作稳健,甚至有些笨拙。但他们毕竟是大动物。
西方有一位作家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这更加让我们明白,小动物才不停地折腾。
由于时代的变迁,食物、水和空气都变化了,人在变,人的精神在变,我们已经长不大了。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极少那种可能。山水污染了,食物污染了,各种农药和工业废气散布在空气中,要呼吸就无法逃避,所以不再会产生那种大动物了。恐龙绝迹,老虎罕见,大象减少,这是时代的命运。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某种野心一块儿灭绝了。向往大动物的心情还是要有。这就要试着回避一些“现代”毒素,吸收一些不同的营养,更多地阅读古代经典,它的精神力道、它的气概,永远存在那儿。看《古文观止》,何等的气魄,何等的精湛。这些都来自古典时期,来自那个时候的山脉天空。现在时过境迁了,天地之间没有那种气了,于是我们就要回头借气。借司马迁的气、苏东坡的气,还有,借托尔斯泰和雨果的气。呼吸一点那时的空气,这太重要太难得了。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比谁更“现代”,一味地追赶现代的怪异,不问青红皂白地模仿“垮掉派”及其他,或更后来的什么东西,连日常生活也学:喝酒狂饮,吸毒,同性恋……这不过是一种可笑可悲的自戕。
一个人的精神坐标找不準,写作的动力也不会强大,技法也不会精湛。作家如果始终保有强大的道德激情,就会拥有难以遏止的表达欲望——其他的一切也就好解决了。
所以,作家具备了强大的道德勇气,他在艺术技法方面的探索就会同样执着。或许我们要远离那些现代病毒的感染,不必相信某些奇谈怪论——有人认为一个现代作家越是没有是非感、越是没有伦理道德、越是下流,就越是能够写出高超的杰作,这真是一派胡言。
一个杰出的作家当然要永远站在弱者一边,对不公正耿耿于怀。这个身份决定了他始终是一个反抗者,一个愤愤不平者,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如此善良多情,怎么会忍受生活当中的黑暗和压迫?有了这种冲动和牵挂,又怎么会在区区技法上输给他人?你的勇气将会无所不在。
作家的基本能力:生活的专注和真诚
无论是人性里极其阴暗的,还是极其美好的东西,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力是基本的能力,这种能力越大,当然就越是卓越。
比如说一位很善良的作家,却写出了最阴暗的“人物”心理。他当然没有做过那些阴暗的事情,但是却会洞悉。这在读者那儿也是一样,读者心理不阴暗,在阅读中却会理解作家所描述的阴暗。这种理解力是自然而然的,既来自先天的素质,也来自后天的经验。
不要说写人,就是写动物,比如我们写一只猫,也要依赖这种人性的理解力。我们不是猫,我们怎样把它写得更像一只猫?猫有猫的世界,这与人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猫的世界,都是我们人类所能理解和感知的那个世界——这仍然要借助于自身的全部体验和经验。在写这只猫时,我们个人的经验就给了它。原来猫作为一个生命,既有你所理解的它们的独特的生活内容,也有像你一样的喜怒哀乐——它在深入人性的洞察者面前,可能也并不神秘。
对待一只猫尚且如此,对待一个人就更应该如此了。有人为了增加对人性的理解力,就积极“体验生活”——这虽然没有什么坏处,可也没有多少好处。因为认真生活就是最大的体验,日常的积极和专注比什么都重要。反过来,在一种专门的方向下、过于明确的目的下去体验,反而会降低了对生活的专注和诚实。
还能听到一些奇怪的议论,说某位作家写的那些人物之所以太浅表、太软弱了,关键问题是作家本人太善良了,不愿把人往坏处或狠处想。这不算个好理由,因为这与作家的善良没有关系,只与他体悟和洞悉事物的能力有关系。善良的人把握起那种美好、丑恶和阴郁反而会更有力,因为他会更敏感,面对那一切的时候会更冲动。
责任编辑 丁 威